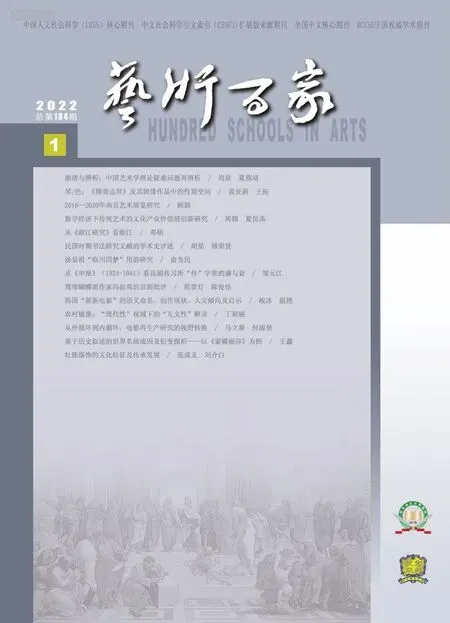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如何能有新视角和感染力*
——兼评江苏梆子现代戏《母亲》
孙红侠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北京 100029)
当代戏剧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数量不少,影响很大。新民主主义革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那些激荡人心气度恢弘的故事是革命历史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和精神气质,不仅是当代仍需继承的精神财富,更是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联,更是对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的重拾和再讲述。正因如此,时代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作者不能停留在题材选择的优势之上,也不能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展示和英雄人物事迹的宣扬,以艺术的方式将事件和人物表现得感动人、教育人、塑造人才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应有的初衷、原则和宗旨。在这种情势之下,如何写好和演好革命历史题材,成为创作者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需要我们共同思考和推进的,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江苏梆子剧院原创现代戏《母亲》的创作和演出为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这部曾在2019年12月9日演出于中央党校礼堂的革命历史题材剧作以淮海战役为故事背景,以淮海战役中真实的英雄母亲为人物原型,艺术地再现了淮海战役是“人民的战争,小车推出来的胜利”,作品继承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传统和红色的气质,同时又在视角的选择、剧种的气质、表现的方式等方面体现了戏曲的特质,在大与小、情与理、生与死的冲突与架构之间展现了创作的能力,更因为对剧种气质与题材协调性的把握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这些都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提供了有益的积累和探索。
一、以微观视角与时代对话
革命历史题材的价值与意义不言自明,也正因此,这一类题材的作品,无论是舞台剧还是影视剧,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以来都有丰富厚重的积累。电影作品领域有《大决战》系列那样的经典之作,电视剧创作领域的《北平无战事》《亮剑》等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佳作,这些作品既有题材优势,又有群众基础,都给舞台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就戏曲作品而言,并不缺少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但如果客观评价,尚缺高峰作品。
那么,面对革命历史题材剧作创作更高的要求,创作者如何精深挖掘,而非停留在题材选择的层面之上?如何沿着淮海战役如此深厚宏大的历史背景,去深入其中挖掘和触摸人物的生命轨迹和心灵空间?从什么样的创作视角切入,才能不停留于一般层面的战争故事表现,而能挖掘出更深沉动人的细节?又如何解决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艺术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从这些角度看,江苏省梆子剧院出品的现代戏《母亲》是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剧作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品。淮海战役波澜壮阔,激荡人心,但舞台作品和电影电视剧作品表现起来却完全不同,影视剧作品可以全景式或者艺术角度纪录式展示历史,同样的创作策略用于舞台作品却只能破坏艺术表现规律,尤其是以抒情性见长的戏曲,更是很难直接表现战争场面,更是不可能以电影那样切换自如的手段来讲述两个以上的平行推进的故事。从这个角度上看,《母亲》一剧的创作视角堪称独具匠心,创作者选择的是以“母亲”个人命运的书写、母亲一家个人情感的表达来折射战争的宏阔、展示历史的风云。由于选取的人物身份是传统农村最底层最普通的老百姓,更是做到了贴着地面行走,贴着心窝写戏。剧中的主要角色母亲李秋荣是淮海战役大后方徐州地区的普通百姓,她的丈夫范栓根是老实巴交的传统农民。母亲的三个儿子以大柱、二柱、三柱命名,表达和隐含的都是传统社会中劳动者最朴实无华的种族繁衍愿望。一家人的形象设计都非常传统而典型。纵观《母亲》全剧,由于没有正面表现战争场面和相关情节,因此并没有出现领袖人物,也没有相关场面的呈现,而是更多地选取能让所有基层观众感同身受的微观视角和叙事语境,用“大树栽不进小瓦盆”这一类平实和生活化的语言以及生存的真实状态来产生戏剧的能量。
母亲李秋荣是一个传统中国乡村里的女性,她和她们有着勤劳坚忍、善良朴实的共同品质。有时这一类艺术角色常常会因为具有共同性而略显得个性模糊,但是现实却正是如此,传统社会的乡民百姓就是个性不甚鲜明而共性突出,这是传统文化对人格塑造的模式和力量所决定的。意识到这一点,创作者的创作重心就不是再如何煞费苦心地去寻求西方式的人物的鲜明个性,而应该转换到如何突出“这一个”母亲的形象如何与以往舞台的创作有所不同。
那么,“这一个”的母亲和以往舞台上那些因为具有相同身份而具有共性性格的母亲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创作者的用力没有放在如何去挖空心思突出个性特点之上,因为那样并不可信,而是选择了做减法。没有让李秋荣有着传统戏台上佘太君式的深明大义和家国情怀——至少不是过多地拥有和强调这些。佘太君是送子疆场,李秋荣也是,但后者并不是因为多么深沉的家国大义,创作者也并没有在唱词和念白中让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农村妇女去阐释革命的重要性和战争局势的紧迫性,也许在有些创作观念里,让人物说出很多并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大词和话语能够很轻松地达到突出主题的目的,但那却不符合现实。其实,母亲李秋荣与佘太君的深明大义有着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所有行为的驱动力就是简单的四个字——知恩图报。也正是这个看上去极为私人化的表述更加突出了剧作所要着力表现的主题: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选择谁,就去用生命跟从谁。谁分了田地给苦水里泡大的中国百姓,谁就是老百姓的大恩人,谁能给予百姓现世安稳与对幸福生活的期待,谁就是老百姓的领路人。如此简单,如此朴素,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代代相传的核心和精髓,更是中国人传统性情中最珍贵最可爱的所在。而历史给了这些以庄严的答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正是这份对于新中国的期待与新生活的承诺,老百姓选择跟着共产党走向新生活,母亲的选择正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正确选择。创作者也正是通过对主人公这一性格特点的“放大”来回答了淮海战役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秘密——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母亲》一剧更是以舞台创作的方式响应和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2月13日视察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时所做的重要指示:“淮海战役深刻启示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未必一定是武器和兵力,军队的战略战术的运用,将士门的信心和勇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往往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以这种创作视角和时代对话,从生活层面展现宏阔背景需要深厚的艺术感悟和生活积累,这种微观的视角和从生活中来去的创作意识会形成更细腻持久的风格。姚金成的作品都不难看到这样的努力和表达,从《香魂女》到《焦裕禄》《村官李天成》《重渡沟》……他善于把大事业的激情和小情感的美好做以对接,从而形成更现实、更民间、更真切的表达。
二、艺术感染力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生命力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其艺术感染力。也就是说,无论其表现的内容是什么,都需要以艺术的形式来对其进行呈现。内容和价值是作品的灵魂,但一个优美灵魂仍然需要优美的形式。能让艺术作品以艺术的方式得到承认和留存的也一定是其中艺术的部分。遗憾的是,很多作品误解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与意义,以为题材的选择可以成为作品成功的尚方宝剑和免死金牌,从而疏忽了形式和技巧上的精雕细刻与深耕细作,假大空的作品就是这样错误的创作观念之下产生的。《母亲》一剧没有依靠题材优势而忽略艺术的形式。不仅没有吃题材的老本,这部剧作在艺术上还呈现出高度的准确性,这体现为题材与剧种气质和演员特色的结合。而这两点对于戏曲作品,尤其重要。
其一,剧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剧种的选择,这直接关系到艺术感染力的产生。地方戏时代留下的300多个剧种在世界戏剧的范围里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剧种的特点、表现力各有不同。每一个剧种都有独特的、适用于自身的题材。昆曲旖旎幽婉则适合表现才子佳人“十部传奇九相思”,京剧慷慨大气则适合于英雄草莽与宫廷袍带,众多的民间小戏则会因为气息轻灵而更擅长于表现民间生活的活色生香。那么,《母亲》这部剧作和其剧种选择是否是相得益彰?通俗地讲,江苏梆子是豫剧在江苏徐州一带流布发展以后形成的新剧种。无论是徐州梆子还是沛县梆子,都是梆子腔系随地域和方言的走向与流布产生的支脉,这些古老声腔的共性是——“酸心热耳”。所谓高音和旋律硬重但小腔又轻柔婉转,节奏鲜明适合搬演悲剧,但在旋律上又极其具有委婉性而能表达深沉悲凉的感情,这样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千百年来传统社会的底层民众为了吐露心声而代代相传、层层叠加形成的,是地域的声音,更是民族的声音,是任凭多有才华的作曲家凭借一己之力耗尽个体一生时长都无法做出的曲调。广而言之的梆子腔系就是适合与擅长表现振奋和感动的情感,因此《母亲》一剧找到了最适合也最切合的剧种和声腔体系来表现这个故事,是剧作的题材和剧种气质与表现力的完美结合,也是其产生艺术感染力的根基。
其二,江苏梆子——也就是徐州梆子,作为淮海战役的主要战场发生地徐州的地方戏,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此次演出《母亲》是用自己的声音唱自己的故事,观众的接受与基础是其艺术感染力能够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依托。徐州有深厚的梆子戏表演基础,丰县、沛县、邳县和铜山、睢宁各县均曾有梆子的专业剧团。有记录的传统戏近三百出,《胭脂》《小秃闹房》《太君发兵》《审诰命》都是梆子腔系里有全国影响力的剧目。江苏梆子剧院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存在的徐州豫剧团、徐州专区实验豫剧团和江苏省豫剧团基础上得名,是一个有深厚现代戏排演经验和传统的演出机构。上个世纪70年代豫剧版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就是这个团的作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江苏梆子剧院有过《银杏坡》《心事》《四方楼》等现代戏作品,《三断姻脂案》《又一村》等戏曲电视剧,还有过新编历史剧《新台啼血》和根据《金瓶梅》改编的七场梆子戏《李瓶儿》和根据《宝莲灯》改编《华山情仇》等。这些作品作为院团的艺术积累都取得过荣誉和盛赞,但是,江苏梆子剧院始终没有相应的革命历史题材现代戏剧作。作为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更是少有以表现淮海战役为内容的作品。从这个角度上看,《母亲》不仅是重大题材现代戏的一个尝试,更是江苏梆子剧院革命历史题材剧作的一个新的起点。因此,《母亲》这部戏的创作,不仅对于地方戏院团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意义,更是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其三,在剧种气质和地域题材优势以外,演员的表演仍然是舞台作品产生艺术感染力最重要的一环。《母亲》一剧的主演是江苏梆子领军人物燕凌。当电影电视剧女演员因青春流逝和少女感消失而感叹无戏可演之时,戏曲演员却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更具有人生的体验和表演的韵味,1964年出生的燕凌正是这样。在《母亲》的表演中,燕凌将江苏梆子演唱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活生生我的儿,只留下军帽一顶”“咱范家祖祖辈辈老实本分”“儿为穷人打天下,儿是大英雄”“穷人家的孩子路难走”等等唱段都做到了在旋律中以情感进入人心——有生活积累和体验的艺术家与普通演员的区别正在于此。她的演唱,充分体现了梆子声腔的演唱美感,体现出曾受教于常香玉、马金凤等老一代表演艺术家的优势,体现出对传统的传承和忠诚。有常派表演“正”与“圆”结合的特点,拖腔合理又艺术化,甩腔力度通达。装饰音、鼻音、喉音都能找到纯熟的运用。母亲这个角色的音乐形象某种意义上超越角色形象才能达到具有高超艺术感染力的境界,生活气息和阳刚之气的声音处理是形象塑造的重中之重,对演员的技术性提出非常繁难的要求。燕凌在这一角色上的成功得益于出身梨园世家的她,文武昆乱不挡,演过文小生、娃娃生、刀马旦,青衣,文武双全;青衣小生也能两门抱,又拜过上海昆剧团“武旦皇后”王芝泉,是一个非常优秀、全面的演员。对于一个戏曲演员而言,体验性的表演经验更为宝贵,难得的是燕凌得过各级别表演奖,江苏省首届文化艺术“茉莉花奖”、第十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还获得第二十四届中国电视“飞天奖”,这些表演经验显然是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更能对舞台剧的人物驾轻就熟。燕凌在《母亲》之前的角色,都是《情梦》里的王魁、《沉香救母》与《华山情仇》里的沉香一类,一直到穆桂英、秦雪梅、贾宝玉……走的是传统戏的路子,技艺和功夫的展示居于首位。这样的角色不仅对于演员自身有年龄局限性,观众的欣赏程度也会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获得飞天奖的电视剧作品《又一村》是她的一个突破,下岗女工李玉琴贴近民生现实与时代生活,人物的形象取得了不依托演唱而存在的独立性。李玉琴是燕凌现代戏的尝试,更是为《母亲》所做的积累。这些厚积薄发在母亲这个角色身上都能看到宝贵的痕迹,也是艺术感染力产生的重要的基础。
在形体表演上,燕凌饰演的母亲做到了戏曲化的松弛。现代戏演出,不能完全抛弃程式和戏曲化动作,但也不能局限于此,做到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夸张并不容易,这是戏曲现代戏表演面临的共同问题。豫剧在这方面是地方戏中积累最深厚的,《朝阳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样本。《朝阳沟》不是化用传统豫剧程式而创作出来的新戏,更不是学习京剧的产物,并没有走一条先学京剧传统戏、再在现代戏中化用传统程式的路子。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地方戏发展的参照系是京剧,地方戏的演员通过拜师学艺等方式向京剧靠拢,大家认为这是提升剧种艺术层次的必由之路。而其实,这恰恰是一种束缚,排演《朝阳沟》的三团不是这个路子,也就是说《朝阳沟》没有走一条模仿京剧的路,也没有受到演出必须“戏曲化”和“程式化”的束缚。杨兰春对演员的要求是体验生活,观察人物,寻找典型细节来表现人物行为。这些宝贵的创作经验在《母亲》里都能够看到,燕凌的动作姿态即是戏曲化的,同时也是去戏曲化的,做到了从人物出发而不是从单纯的展示技艺出发,做到了生活化的动作艺术化,而不是用艺术手段套用生活动作。“雪地行路”一场戏,还在表示行路的圆场之上加入了“摔叉”等技巧展示,但符合戏剧情境和人物的心理,做到了有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又能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而不拘泥于程式。儿子三柱的死是震撼人心的高潮段落,接下来则是月色摆酒祭奠这样一个冷热场次交替的戏。这两段戏对于演员的情绪处理是巨大的挑战,所有情绪都要在形体基础上完成。母亲时而是一个踉踉跄跄的耄耋老妇,时而又要挺直腰板,成为一个革命化和意象化的英雄母亲形象。演员要在这两者之间实现一种巧妙自然而又顺畅的转换,这时的处理如果向京剧那样高度程式化的大戏学习和靠拢将不伦不类。京剧老旦的表演程式对人物的表现是衰朽有余、气度不足的,这时候杨兰春的表演理念就凸显了重要性的一面,《朝阳沟》等现代戏人物创作的经验积累就凸显了价值和意义。梆子腔系的民间戏曲,在程式体系上与昆曲、京剧并不是一路,如果因循未必正确的常规向京昆等“大戏”看齐和靠拢,就会遮蔽了自身宝贵的表演体系和积累。我们无从得知,作为江苏梆子领军人物的燕凌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江苏梆子——这个在体系上古老而在名称上尚显得“年轻”的剧种对于梆子腔系母体艺术和豫剧的因袭关系,但从表演的显现上看,不仅在演唱和形体上做到了对传统戏与传统表演方法忠诚的传承,也在现代戏的人物塑造上有意无意地继承着豫剧最宝贵的创作原则。这些,都是《母亲》一剧给我们提供的思索与视角,也正是因为这些宝贵的继承与思考基础上的推进与发展,因为题材与剧种气质的契合,表演与受众等诸多要素,共同促成了作品产生艺术的感染力,而只有感染力才永远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生命力。
三、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问题与路径
当代戏剧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剧作数量不少,影响很大,但佳作并不多。而革命历史题材舞台作品,不仅与现实政治要求紧密相联,也是在对革命故事的讲述中,以舞台艺术的方式对民族精神的一次次重拾与重塑。革命历史题材的范畴有着明确的要求,表现范围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业绩以及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戏曲舞台作品领域,革命历史题材不属于历史创作,而属于现代戏范畴。从评剧《金沙江畔》、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创作开始,就开始了这一类剧作经验的积累。近年以来,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从数量上看堪称高潮与高原,京剧《浴火黎明》《西安事变》《党的女儿》《江姐》、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沪剧《回望》、芗剧《生命》、评剧《母亲》、闽剧《生命》、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吕剧《大河开凌》等等,甚至不太适合这类题材的昆曲,也排演了《飞夺泸定桥》。
从这些戏曲舞台作品呈现出的创作态势来看,与影视作品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呈现出鲜明的不同。影视剧作品从《大决战》《开国大典》等经典作品开始,一直到《建军大业》《南昌起义》《古田军号》等新近作品,都进入的是文献记录式拍摄的路径。历史人物的塑造和历史事件的再现,要求以真实为原则,秉承历史主义的原则与创作态度,也就是摒弃戏说,要求历史精神。这种忠实于历史的叙述策略,陆续被创作实践证明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正确与可行的路径。反观戏曲舞台,这样的创作原则虽然也适用,但从表现手段上看,则有诸多障碍。戏曲舞台的表演原则与生活的真实相去甚远,也不擅长以宏大的舞美设计表现壮观的历史场面,更不可能盲目借鉴传统武戏的表演方式用“七八人百万雄兵”“双人对打”的方式去展现现代战争的场面。这种表现手段上的难度构成了戏曲舞台作品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戏曲舞台对这一类题材的表现就需要转变创作思维,首先走出影视剧的影响,其次要在叙事策略和艺术观念上秉承戏曲的原则和特色,不去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的同时,更不要放弃自身艺术体系的优势和传统。《母亲》这一类作品的创作实践其实就是避开宏大叙事和场面铺排而走向精细化、抒情化、人性化和诗意化的一种策略,是放弃历史场面的简单还原,走向生动和艺术感染力的一种路径。这样的创作模式,是对以往优秀创作传统的一种继承,同时也是推进和提高。也只有这样不违背历史真实,也不以宣讲和教育面孔出现的作品才能做到诚恳地面对观众,做到对历史革命题材的真诚与尊重,做到发挥创作者的使命感,使革命历史题材避免因宏大而虚假。题材的庄严性也因其“小视角”而能得到确立,做到贴着地面行走,贴着观众创作。同时,没有宏大,也就没有虚无,没有矫饰,才能以其诚恳、淳朴、厚实保持价值取向坚定不移,以民间的情感和手法让历史题材光芒重现。从这样的角度思考,《母亲》一剧带给我们的启发还应该更多、更深入,我们也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思考的基础上会有更多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作品以真诚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