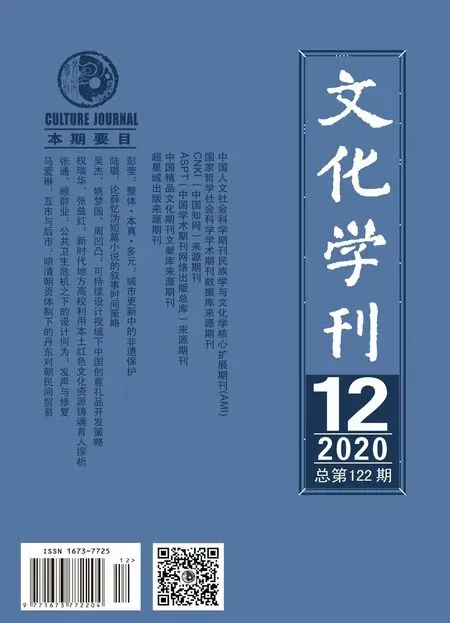从《毛诗注疏》看“周公东征”一事
程子莹
《诗经》中集中讨论“周公东征”一事的篇目有《鸱鸮》《东山》《破斧》《伐柯》和《九罭》五篇。从毛传、郑笺及其后注疏中,可见毛公、郑玄及孔颖达对东征所涉“周公摄政”“周公居东”等事的看法。本文将从《毛诗注疏》文本出发,厘清毛亨、郑玄对“周公东征”系列事件的叙述方式和观点。
一、周公摄政
通观上文提及的五个篇目,大致可以将毛亨、郑玄二人思路归纳如下:毛亨以为,五篇诗所涉及的事件发生顺序为,管叔、蔡叔传流言于国,周公为稳固周室基业,遂一人东征讨伐,此时成王惑于管、蔡流言,疑周公将篡夺王位(《鸱鸮》《东山》《破斧》);周公东征事毕,成王仍不信周公,不以礼迎接(《伐柯》《九罭》)。从中可见毛传无周公避居之事,符合如今所见《毛诗》的篇章排列顺序。郑玄以为,周公将欲摄政(即未摄政之时),管叔、蔡叔流言于国,周公于是出居东都(《鸱鸮》)。周公避居之时,成王有感于雷风之变,欲以礼迎周公,群臣质疑(《伐柯》《九罭》)。既得金縢之书,群臣无疑,周公返而摄政,然后征讨四国(《破斧》《东山》)。郑笺周公东征和居东二事泾渭分明。可见毛亨、郑玄二人对五篇诗文顺序和史事的诠释皆不相同。
虽然毛传、郑笺史事发生顺序不同,但都认为东征之时“周公摄政”确有其事。依孔颖达疏对《鸱鸮》至《九罭》毛传的疏解可知,毛亨以为,成王俱不知周公之志。纵观毛传,此点之证,应在《九罭》诗“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二句下。毛传言:“无与公归之道。”上文言王有衮衣,当是有见周公之服,此处却无迎公归之礼,当是成王仍疑周公,惑于流言。此外,《鸱鸮》诗序言:“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若依孔颖达之意,《诗序》为子夏、毛亨合作,此处诗序所言,自可补足毛传注解省略之处。依此,则周公必一人往征。《礼记·王制》言:“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1]周公若未摄政,不得于王未信己之时往征伐。故此时周公必已摄政。郑玄于《鸱鸮》诗序下明言“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意为“未知其欲摄政之意”,而《破斧》诗“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句下,郑笺云:“周公既反,摄政,东伐此四国。”此已明言周公有摄政之事。孔颖达疏存郑玄《尚书》注文,其言:
郑于《书序》注凡此伐诸叛国,皆周公谋之,成王临事乃往,事毕则归,后至时复行。然郑意以为,伐时成王在焉,故称成王。(《破斧》)[2]751
即郑玄以为,周公东征之时,成王与之俱往。《破斧》主美周公而不言成王,可见周公于时实摄政。不然,当如《六月》之例,即《六月》言宣王北伐之事,诗文专美吉甫,孔颖达疏言:
若将帅之从王而行,则君统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专归美于下?若王自亲征,饮至大赏,则从军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独多受祉?故郑以此篇为王不亲行也。[2]904
仿此,则王若亲征,则当美王,以君统臣功。郑笺既以东征之事,成王俱往,则诗应主美成王而统周公之事。王国维认为,周公与成王的关系类似古代希腊、罗马的“两头政长”制度。周初还在奴隶社会阶段,周公东征之时在军事上是将军职,可以独断专行;政治上是祭司职,可以称天而治[3]。笔者认为,王国维此论,在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四国叛乱威胁国家根基时,是成立的。周公辅佐成王既久,摄政有效地集中了成王初期可运用的力量。因而《破斧》诗以“周公东征”为诗文内容,体现了当时周公摄政主事的状况。即单就《毛诗》诠释体系而言,“周公摄政”于东征之时,确有发生。
二、周公居东
除“周公摄政”外,“周公东征”涉及的另一史事是“周公居东”一事。郑玄在解这五篇诗时,依据的是《古文尚书·金縢》的内容。可以明确的是,郑玄处“周公居东”和“周公东征”完全是两回事。《金縢》言: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4]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郑玄对“我之弗辟”之“辟”和“罪人”的解释。郑注以“避”解“辟”,“罪人”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5]。即“周公避居”以敌流言为单独一事,而“罪人斯得”为成王处置周公属党。《鸱鸮》因被注解为,周公劝谏成王,若诛杀众人,毋绝世家子弟爵位,毋夺其土地。
历代很多学者主张“东居”和“东征”为一事。单从郑玄注解内部逻辑而言,郑玄以为“周公东居”和“周公东征”为两件事,是逻辑自洽的。《东山》序下郑玄笺:“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乃东伐之。”[2]739结合上文提到的郑注《书序》,东征之时,成王俱往。若“东征”与“居东”为一事,那么成王在未信周公之时,即亲助征讨管、蔡,战后仍信二人流言,对周公持疑,周公此时才作《鸱鸮》明二人当诛之意。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所以,应为郑注所言,成王得雷雨大风之变后,即信周公,启《金縢》之书后,群臣释疑。此后成王迎周公从东都还,周公摄政,主谋东征,成王、召公予以支持(1)有关成王亲自参加征伐这一点,可以今文材料证明。《禽簋》铭文云:“王伐奄侯,周公谋。”(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清华简《系年》亦云:“成王伐商盖,杀飞廉。”(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41页。)此外,关于金文材料和《诗经》中罕见周公之名一事,夏含夷认为,当是周公还政后为避险隐退,政治影响力式微,故罕为人提及。(《周公东居新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至于毛公无避居之事一点,孔颖达于《破斧》疏中已直言。综观毛传,毛传中无提避居处,从《鸱鸮》至《九罭》的编次,即依东征事件从“明诛二子之意”到“成王不以礼迎周公战毕返还”的过程。毛传不破经文之字,则《破斧》中“周公东征”应为周公一人东征,不涉及成王亲往征伐,支持之意。上文已言及周公东征之时必已摄政,罪人既诛,政事未完,自无避居之理。且若《诗序》为子夏、毛公所作,《东山》诗序明言“周公东征,三年而归”,无再避居停留之事。则《九罭》中“公归无所”“公归不复”“无以我公归”等句,当言周公东征在东,不得归返迎接之礼仪。郑玄此处认为有“避居”之事,与毛公不合,当因郑玄注《诗》,采三家《诗》,且遵《古文尚书》,故改毛传之意。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时郑玄与《诗序》字面观点相悖,但由于郑玄认为《诗序》乃孔子所作,因而选择以笺另解词义的方式转换《诗序》之意。如上文所及《鸱鸮》诗序言“成王未解周公之志”,郑笺即以“周公之志”为“未知其欲摄政之意”;《伐柯》《九罭》“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郑玄将“朝廷”解为“朝廷群臣”,而非“成王”。以此来诠释自己的史实认定。
三、结语
毛亨、郑玄对于“周公东征”及其相关之事的看法大相径庭。尽管二者都承认“周公摄政”一事存在,但毛亨认为武王去世后,周公直接摄政,无避居之事,并且在成王听信管叔、蔡叔流言之时,即往讨伐叛乱四国,直至遭雷雨大风之变,启金縢之书,成王才以礼迎接战毕的周公。此点可由《九罭》毛传和《诗序》佐证。且非天子不得专征伐,周公不摄政,又不见信于王,不当往伐四国。朱熹有关事实的观点,基本从毛说,但着重强调圣人无私,笃厚大公的思想。郑玄认为周公摄政当在避居之后,东征之前,周公东征之时,成王亲往。郑玄注解五篇诗俱与《尚书·金縢》文本内容相联系,将“东征”和“居东”定为二事,且此番事件顺序设定逻辑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