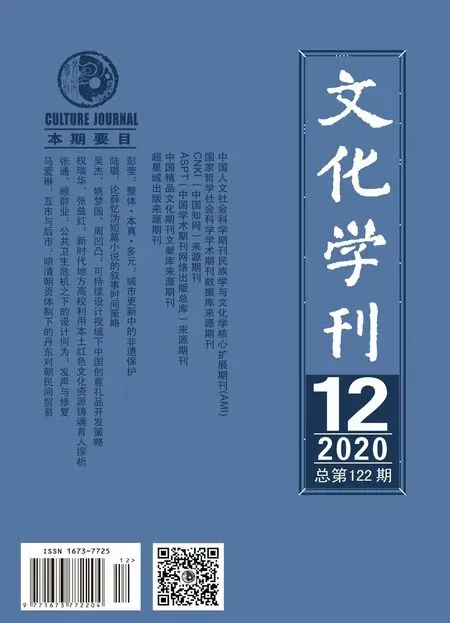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生命伦理研究
鲁 琳
生命伦理学自产生以来,由于不同研究者处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划分方法,所以它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关注领域也非常广阔,尚没有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并且始终处于开放的态势。当代生命伦理学已经从生物医学扩大到人口、污染、贫困、政治这些关乎人类生存的一切研究领域。然而,历史上几乎所有领域的研究都处于男性强势话语的控制中,社会的道德标准多以男性视角衡量的价值评价标准设定。如生命伦理学的四大基本原则之“尊重自主”,正是基于对主体个体的理性自主权的尊重。四大原则的提出者——比彻姆和邱卓思也意识到:“通常,道德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遵守原则和规则,而是可靠的品格、良好的道德感和情感反应。当父母充满爱意地与孩子们一起嬉戏、养育他们时,或者当医生护士对病人及其家人流露出同情、耐心和共鸣时,即使是具体的原则和规则也无法传达其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对他人的感觉和关心驱使我们行动,这些行动不能归结为遵守规则的行动。我们都承认,没有各种情感反应,没有超越原则和规则的震撼人心的理想,道德不过是冷冰冰的、麻木的东西而已。”[1]同情、共情等情感反应通常被认为是理性的对立面,正如女性是男性的对立面,但这些情感反应与理性思维一样,都是个体的主体性特征表现,而且情感反应更能贴近活生生的人的日常生活。体现女性特征的关怀伦理学对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关怀伦理学认为,传统以理性自主为核心的伦理学过分强调绝对独立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太过于抽象,在实际中也不可能存在。因此,我们应朝向一种动态整体的、联系的思维方式,将理性自主理解为一种注重相互依赖的整体中的个体理性选择。可见,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生活意义及人类生存价值与发展的学科,生命伦理学需要引入性别视角,需要女性文化的填补和解读。
一、生命伦理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的相似性
(一)研究内容都具有历史性
女性主义与生命伦理学都起源于20世纪中期以后。女性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逐渐发展成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系统和讨论范畴被用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的建构中。生命伦理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随后在欧洲及亚洲甚至全球迅速发展的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产生后就受到各界学者、决策者及公众的共同关注,并且很快体制化。从女性主义和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来看,虽然它们都是近期才兴起的,但它们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于历史中,因此常要回顾历史来进行研究。比如女性主义虽然源起于现代西方,但在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如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娲补天、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武则天和慈禧太后身上皆可以找寻到女性主义的一些踪迹;生命伦理学研究临床诊疗道德,而无论在庄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或是古典传统医德文献《大医精诚》中,都有医学义务论、美德论的明确要求和具体阐述。
(二)研究方法都具有跨学科性
女性主义一般不能单独存在,作为一种学术思维方式,它总是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结合起来,形成女性主义哲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政治学、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生命伦理学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而且,自波特1971年在《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书中第一次提出“生命伦理学”术语时,就已经阐明了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特点,即“生物医学与其他丰富的人文知识结合起来的科学,为人类物种的生存提供医学和环境的最佳体系”[2]。因而,生命伦理学总是与哲学、艺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人类学、宗教这些人文学科密切关联。
(三)研究理论都具有多样性
由于以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政治观点来寻求妇女解放之路,女性主义内部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等。虽然女性追求平等的目标具有一致性,但女性也是千差万别的,不同女性主义对女性民族、社会阶层、种族、健康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敏感。如同某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不能解决不同种族、民族、社会阶层的女性问题,生命伦理学也不可能让天下所有人信奉同一个道德体系。无论是性取向评价还是放弃治疗,不同民族传统、社会阶层都会产生不同的道德判断和选择,生命伦理研究不可能消除道德多样性,不能为某种特定的、具体的道德体系作论证或辩护,只能寻求如何将某个标准的、内容充实的道德理论应用于医疗卫生实践中。
(四)研究意义都是世界性的
生命伦理学与女性主义的研究都是世界性的事业追求,促进两性平等已经成为世界人民普遍认同和遵循的主流价值观。女性主义的运动在于反抗父权社会对女性压制的传统观念,致力于将全世界女性从所有压迫形式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全球妇女团结以及两性和谐发展。生命伦理学关注人的生命意义、人类生存的评价与实践思考,其不仅仅是各人文学科的理论结合,也是一个团结全世界共同解决现代医学健康和进展中的生命科学所遭遇的道德难题的学科。尤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人类社会与病毒奋战的关键时刻,整个人类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肉体创伤、精神世界的情绪和信念、卫生经济政策与分配、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生态这些生命伦理学重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深切关注的重大问题。
二、生命伦理学中涉及很多女性伦理问题
(一)生育控制伦理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如今已有非常有效的控制生育的手段,但控制生育女性始终承担更多的责任。女性主义思潮普遍认为,让女性过度承担避孕责任不符合负担公平分配的伦理学原则,因此,如何保护女性的生育自由不仅是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内容,也是生命伦理学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在避孕、人工流产、绝育术这些生育控制的具体实施中,女性享有的选择权、尊严权、生命健康权等重要权利不容忽视,同时生育控制也是关乎国家、民族、人类整体和子孙后代利益的重大问题,生命伦理学应思考如何实现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生育自由合理合法的限制。
(二)辅助生殖技术伦理
从技术上来说,辅助生殖技术基本可以解决不孕不育的问题,但医学从来就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更多的是对人的伦理关怀。辅助生殖技术干扰了自然生殖的步骤,也产生了激烈的伦理冲突和社会矛盾。由于女性在生育中的特殊地位,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必然与女性密切相关。首先,他精人工授精不仅与女性传统贞操相冲突,而且切断了婚姻与生育的必然联系,这是否破坏了家庭和睦?其次,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孩子可有多个父母,包括遗传父母、孕育父母等,如何界定谁是孩子真正的父母才能让各方面有最佳获益?再次,母爱是一种纯洁质朴的自然情感,能否为了满足治疗不孕不育而允许商业代孕的出现?这些问题因其与女性身体权利密切相关,不仅是当代生命伦理学讨论的问题,也是国内外女性身体伦理与性别政治最为关注的问题。
(三)性权利与生殖健康
性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话题。生命伦理学研究个体生命健康就不可能忽略性伦理问题,如性权利、性少数群体、妓女及色情问题。从性权利来看,性反映了人类的本真,是一种正常的自然欲望和心理满足,女性也有依法表达自己性意愿和进行性行为的权利。无论是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禁欲,还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都严重压抑了妇女对性的表达。女性性权利的复归,就是对传统的性文化模式的否定,也是一次性健康观念的革命。性权利应该建立在男女平等、互相理解、互相交流的基础上。性与生殖密切关联,女性的性权利要充分实现,生殖健康尤其注重以妇女为中心的生殖健康必须得到保障。
(四)美容伦理
医学美容是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观念转变及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医疗美容以美化健康人体为目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医疗美容技术使用不当,就会对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造成伤害。在美容产业中,女性的美始终以社会标准来衡定,而社会审美要求总以牺牲女性的健康为代价,如古代的缠足、束腰和现代社会的丰胸抽脂手术,还有各种整形矫正术。女性美不仅在于外在美,女性应当充满自信,不断地关怀自身,更多关注内在美的价值追求。
(五)基因医学中的女性伦理
基因医学是指利用最先进分子医学的技术,从婚前检查、孕检、产检不同阶段进行的优生保健服务,以满足民众有关遗传学疾病的检查、诊断及医疗等需要,减少严重缺陷先天儿的发生。基因医学技术应用包括基因治疗和基因诊断,在具体操作中都与女性密切相关,如在产前基因诊断中,国家有义务为所有女性提供必要的资助,不允许利用产前基因诊断操纵胎儿的性别,并且要鼓励女性流产掉有严重基因缺陷的胎儿,从而符合孩子、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利益。
三、女性主义与生命伦理学都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
西方传统文化提倡理性、重视中心、维系结构、尊重历史,后现代主义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推崇非理性价值、关注边缘与弱势、解构与重构以及历史断裂。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始终处于边缘与弱势地位,要想突破困境,就要打破传统“逻各斯结构”的权威统治。显然,女性主义与后现代思潮不谋而合。后现代主义特别提倡对弱势的关注和尊重,重视差异的存在,后女性主义理论受到启发,也提出了尊重两性差异的平等观。男女应该平等,但如果不顾及性别差异,那么不但不会使两性平等,反而会形成更大的不平等,因为这样的两性平等仍然让女性禁锢于男性标准中。因此,男女平等必须兼顾两性差异,正是差异使男女有了对自主的不同认同,才可能取长补短,让男女双方沟通与合作,才能“创造出一种交错配列或双回路线圈,使每一方都可以向着对方运动而又能回归自我”[3]。
生命伦理学也具有浓厚的后现代特征。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如尼采、福柯、德勒兹、德里达、拉康的理论体系庞大而又复杂,生命伦理学也是一门具有多个研究方向、汇聚融合各个知识体系的复杂思想体系。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范围涉及哲学、建筑学、艺术、文学等广泛的学科,鼓励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和倡导对世界的关爱[4]。生命伦理学是一种伦理生命学,它也倡导对生命的尊重及对世界的关爱,正是如此,它就必须表现出对不同宗教、文化、习俗的宽容与接纳,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及尊重差异的思想为生命伦理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总之,生命伦理学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吸纳各种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理论成果。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生命感受及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学科,生命伦理应该引入女性的观察视角。而且,生命伦理学研究中的很多议题与女性伦理密切相关,它们也都具有非常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当代生命伦理学正在朝向身体伦理学的研究,身体伦理学就是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视域[5]。在生命伦理学的身体理论重构过程中,女性主义的身体研究成果是可供借鉴的重要资源[6],生命伦理学要积极借鉴女性主义的思想分析,以推进理论建构和丰富生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