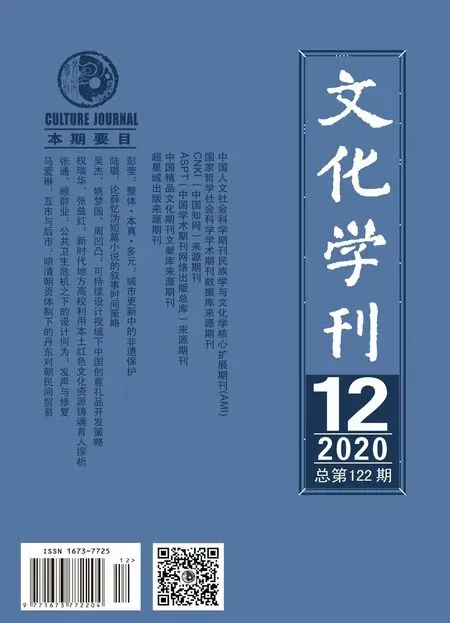回到霍克海默、阿多诺:论启蒙的背反性
陈 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是“标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发展里程碑的一部分著作”[1]143,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色彩。《启蒙的概念》是《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中的首个章节,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文本内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当中论述了启蒙如何“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的问题,即“什么是启蒙的辩证法”的问题。
一、启蒙和辩证法的语义指称
贯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宏大叙事的一个核心要义即“什么是启蒙的辩证法”。想要厘清一个问题,首先要厘清该问题所涉及的诸多范畴。因而,要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语境中关于“什么是启蒙的辩证法”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梳理该文本指涉的诸多概念范畴。从书名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来看,“启蒙辩证法”是由“启蒙”和“辩证法”黏着建构而成的复合词汇。
“启蒙”一词在中西两种不同语境中的内涵基本一致。在中文语境中,按《辞源》的解释,“启蒙”具有开导蒙昧、使之明白贯通的语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则具有两种基本语义:一是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入门的知识;二是普及新知识,使人们摆脱蒙昧和迷信。转向英文语境,“启蒙”的对译词是“Enlightenment”,其词根的“light”兼具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分别指称“光”和“点燃”(或“照亮”)。故而,在清末民初时,有将西方的“启蒙运动”译为“光明运动”的译法。不论是中文语境还是英文语境,就其语义来看,都有“祛除蒙昧,使人豁然开朗”的意味。
“辩证法”一词属于西方哲学中的概念范畴,最早出自希腊语,可指称“语言的艺术”。在之后的不同哲学家那里,“辩证法”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但若置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视域,或可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来界定“辩证法”的语义内涵,即“思辨”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思辨”,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和提炼事物本质的方式;“实践”,则指通过运用真理性认识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场、演绎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动活动。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将辩证法视作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
二、启蒙的逻辑起点:神话的生成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语境中,启蒙精神不是某场开化运动,也不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启蒙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是一对同义的概念范畴。他们从整个西方文明进程中提炼出了启蒙精神的概念,并对其进行深入的解构和批判。
在一般的认知中,启蒙是一种对包括巫术、神话以及封建等时代“残骸”在内的蒙昧的超越,神话在现代文明面前亦属蒙昧的范畴,当中更不可能存在启蒙的思想或是精神。但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语境中,神话生成的事实本身就已初具启蒙的意味,在之后,才又走向断裂。
神话缘何能够具有启蒙的意味?启蒙诞生于神话(包括图腾、巫术等)。如果没有神话,启蒙也就不会出场。在《启蒙的概念》开篇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有过这样的按语:“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1]145而人类在尚未能掌握火种,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时,对自然界中所发生的本我的主格不能理解的他者的自然现象(如天地的形成、人类的生死、风雨雷电的生成等),表现出了极大恐惧,彼时原始的神秘主义便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一切的“不能理解”都被神化。在面对神秘的自然力量时,原始人类深感自身的渺小,但同时又好奇地打量着世界且试图斗争。在试图抗争自然的过程中,为克服“不能理解”所带来的未知恐惧,原始人类便根据自己的理解创制了图腾和“神”。从这一维度来看,神话的生成,是人类同自然界斗争,是“文明”同“野蛮”分离的必然产物,因而可将神话的出场视为启蒙的逻辑起点。
三、神话与启蒙的断裂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叙事中,人类社会已经历两次启蒙。神话与图腾的生成,象征着理性启蒙在蒙昧人类视域中的出场,此即人类摆脱原始蒙昧的第一次启蒙。而技术工具与逻辑工具的广泛应用,意味着人类社会实现了由“他信”向“自信”的转向,此为人类对抗封建蒙昧的第二次启蒙。因而,在《启蒙的概念》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就进步思想的一般性意义而言,“启蒙想消除神话,用知识替代想象”[1]145。
不可否认,在人类史的开端,神话的生成与启蒙的出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关联性,甚至于在人类创制神话的事实本身中就可窥得人类从原始蒙昧转向启蒙开化的转化过程。因此,从该维度来说,神话即启蒙(理性启蒙)。但人类凭借自己的理解,用神话、图腾、巫术等具象的符号来指代“神秘”以消解恐惧的活动本就是一种历史的吊诡。一方面,人类对“神秘”畏惧的内在生成力和对改造生存环境渴望的外在动力,共同交织形成了神话,换言之,神话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人类对“神秘”仍有想象和畏惧;另一方面,用神话来替代或表示“神秘”,尚属于“他信”阶段的启蒙,利用“他信”克服自身恐惧,即意味着人类尚处在“神秘”的控制之中。
人类创制神话的行为本身,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类作为类的存在,其主体性觉醒的开始。就从这一维度来说:“神话其实是主体性的成长史,即便降格为巫术也毕竟教会了人相信自己的力量,不再听任自然的摆布。”[2]而随着人类主体性的不断成长,人们对自然的打量愈发深刻,对自然规则愈发了解,进而具备了运用自然规则的能力。这不仅是人类的主体性的壮大,而且是人类启蒙史的前进。主客体之间,也开始了“质壁分离”的演绎,世界成为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的客体和对象。此时,人类的神话叙事越来越清晰,逐渐脱离“神秘”而接近理性,当人类的启蒙思想对自然的统摄能力强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彼时人类就不再满足于神话的暧昧叙事,而要求用更为具体的理性符号来替代神话。于是,启蒙开始“逃离”神话,进入“自信”的阶段,二者间的断裂也就由此产生。
四、启蒙向神话的退化
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过去启蒙的纲领曾经是使世界清醒。”[1]145启蒙的出场,使人类得以从蒙昧的状态中清醒。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天然蕴含强大的物质力量,造纸术、印刷术使文化得以传承,指南针使航海贸易、金融得以出场,火药使现代战争得以根本转变。科学启蒙的出场,使科学替代图腾,实现了人类对自然更为有力的统摄,这象征着人类从“他信”向“自信”的飞跃。
但是,“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1]149。在启蒙摧毁旧神话以科学技术替代神话、巫术之后,又以数学、形式逻辑等技术理性来统治世界。正如旧神话在原始人类看来是不可动摇,“启蒙”在这时亦转化为新的“不可动摇”的神话。消灭了神话的启蒙,在彼时却成为自己过去意图消灭的对象本身,“甚至启蒙精神的概念变成了泛灵论的巫术”[1]152,走向自我背反。启蒙的原初纲领是要使世界清醒,是要根除神秘的泛灵论。“启蒙精神使神秘的恐惧心理彻底发生了变化”[1]157,人类通过启蒙精神实现了对“神秘”恐惧的克服。但它的最终产物又成了一种普遍的禁忌,因而启蒙又倒退回了“神话”。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主张用数理科学工具统摄一切,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但是,思想之境建构起的存在物未必是现实之物,因而思想家在运用形式逻辑三段论进行推导时,其“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逻辑本身虽可成立,但大前提本身就可能不是现实之物。又或是通过不同的假定前提所推导出的不同结论,由于符合形式逻辑的推理过程,虽从形式逻辑来看都是正确的,但这两个结论却彼此矛盾,不符合现实。因此,不论它们的逻辑如何强大,往往都会在自身推演之中趋于瓦解,走向背反,形式逻辑确保思维的真值的功能随之崩塌。“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1]150,启蒙家自视甚高的启蒙(科学启蒙和技术启蒙)精神,又陷入了新的蒙昧之中,启蒙随即退化为神话。
五、结语
启蒙使原始人类摆脱蒙昧,但在被技术工具理性支配的布尔乔亚(bourgeoisie,即资产阶级)现实世界中,人们在追逐科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的同时,又使价值理性日渐萎缩,甚至已然忘却对事物价值本源的探求。启蒙在帮助人们逃离神话之后,却又坠入了“神话”,因而呈自我背反的吊诡状态。代入霍克海默、阿诺多的语境来理解启蒙:第一,在原始野蛮的时代,人类通过刻画神话图腾、创造巫术实现了对未知神秘的原始克服,彼时神话的出场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即启蒙;第二,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的统摄进一步增强,人类以科学技术替代神话图腾,彼时技术工具理性对于跪服在神话之下的人类而言就是一种启蒙(理性启蒙);第三,当人类堕落于技术工具理性的支配,形式逻辑便以强势的姿态统治人类世界,对现有启蒙(科学启蒙和技术启蒙)的反抗,对此时的人类而言就又将会是新的启蒙。笔者认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布尔乔亚现实世界的批判,所想执行的也正是当代启蒙的职能。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