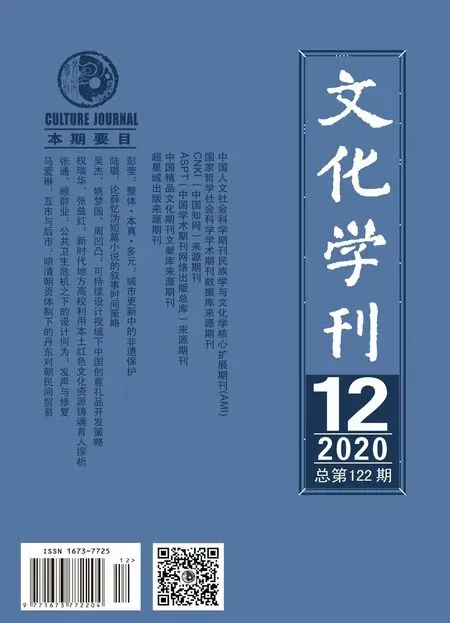论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伦理思想
张家赫
1835年至1837年是马克思的大学前期,也是他一生中极为短暂的一段浪漫主义时期。在这一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了马克思对周围世界的审视,隐喻了马克思之于社会的道德判断和伦理选择,生成了马克思文学作品中的社会伦理思想。
一、对社会现状的沉思和解构
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摇摇欲坠且动荡不安的时代,各种思潮冲击着社会的思想文化,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当时的德国社会。这一时期,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拿破仑法典》的精神已经在马克思生活的德国特里尔广泛传播,人们长期浸润在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的氛围之中。但是,拿破仑战争后的德国还保留着专制统治的传统,德国联邦议院也完全由王公贵族组成,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一改之前的革新之风,抛弃改良派,打压异议人士。马克思就读的特里尔中学受到了严密监视,校长被辞退,一向奉公守法的父亲也不问理由地被审查,这让正值敏感年纪的马克思亲身体会到腐朽落后的专制制度所带来的压抑和屈辱。而被视为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对国家力量的依赖性,使其在面对强大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国家时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社会现状,各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聚积让整个社会已经岌岌可危,森严的警察制度和封建专制严重限制了人们的自由。1835年,17岁的马克思离开特里尔,开始了波恩的大学生活,次年,他转学到了柏林。这是“一个异常没有传统根基的城市,它没有长期形成的贵族阶级,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没有新生的工人阶级”[1],却有着和波恩大学迥然不同的学习氛围。马克思在诗歌中抒发着自己的愤懑,在叙事诗《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中,马克思实质上探讨了“人是社会的存在物”这一主题,人的主体性不决定于人本身,而是现实境况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诗中,恩格尔伯特是一名戎马倥偬、功勋显赫的战将,但不同于战场之上的威武英勇,随着时光流逝,他离开战场,他的面庞经受了岁月的沧桑,再没有英姿勃勃的形象。这时,一位睿智精明的神秘僧人出现,他苦口婆心劝骑士伪装自己并要行事隐晦,还为他限定了一整套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但诗歌的后半部分,年轻的骑士陷入情网,现实的困境让他身体扭曲、神色慌张。好在马克思为故事安排了一个温暖的结局,老僧再度出现,他告诉年轻人:“你能对天使倾心向往,那就说明你的第一颗果实已经飘香。”[2]907诗歌最后并没有交代骑士是否已魂归泉壤,但从僧人的话中能看出他已经肯定了年轻的骑士。人受制于社会外在因素,没有活成想成为的人,而是成了条条框框下的社会角色,成为循规蹈矩的“类存在物”。在这样的条件下,打破社会的框架可能付出的会是生命的代价。
马克思在诗歌中对社会现状进行解构,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容克地主(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而人民群众成为这个特殊的黑暗年代的牺牲品。在《钟楼上打钟人之歌》中,钟楼之上,雷鸣电闪、雨骤风狂,钟楼之外,四野昏黑,一片迷茫。“钟楼”象征着强大的封建势力,虽然德国取得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在19世纪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且大部分邦国已经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但在德意志各邦国中,贵族特权仍然在不断加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是其他阶级不能比拟的。资产阶级的出现为这落后黑暗的社会带来了曙光,“它呼啸而过锐不可挡,它震天动地倒海翻江”[2]557,但是它也有强大的破坏力,它在消灭封建势力将贫苦大众解救出牢笼的同时,也留下了“断壁残墙”和“破败景象”。马克思发觉到资产阶级的强大能量,但它是否能真正带来自由与平等,拯救人民群众?在诗的最后,这股力量“渐渐变暗,失去光芒,它在毁灭自身的力量;它也在毁灭四周的一切”[2]558。人们通过这场革命争取自由,最终换来的却是心灵的挫伤,可见马克思在当时已经洞察到资产阶级革命在具备进步性质的同时,其杀伤力也会最终消解革命胜利的果实,自由不过是假象,人们正在被新的锁链束缚。
二、对社会中人性的审视和嘲讽
在马克思的部分文学作品中,有着对现实社会的伦理批判,他在诗歌中运用反讽的手法进行着自己的感情宣泄,这源自他对20世纪初德国社会的思考,也源自他对社会中人性的审视。
马克思对德国人的保守性进行了反讽。在《讽刺短诗集》中,他谈到第六次反法战争同盟军在莱比锡会战中取得胜利后,街头巷尾传出的新闻与民族大会战的胜利毫无关系,人们谈论的竟然是“世人很快就会长出三只脚”[2]736这样一条荒谬、离奇、可笑的谣言,虽然一些人迅速反应过来,并为自己传出这样的谣言而感到害臊,但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的愚蠢,而是想到如果多收集一些这样的奇闻轶事并汇编成书,一定畅销。马克思在这首小诗中用精练的文字就把德国人亦步亦趋的思想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马克思所批判不只是人们蜂营蚁队的行为,更是人们对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缄默,对于新潮和变革的拒斥,这种国民性格中的保守性是国家停滞落后的根源。
马克思嘲讽了社会中一些人的虚伪和功利。在《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中,一个穷人决定去豪华剧院享受下看歌剧的感觉,但在当时社会,穷人一般是看不起歌剧的。他穿好用自己仅有的积蓄购买的单层燕尾服,却没想到剧院没有暖气,再也没有了看剧的心情,服务生见他行为怪异过来验票,他低声悄语自己的手已冻得僵硬,服务生不知其因,问道:“你为何不戴上手套?”他不堪嘲笑,只能故作姿态地回答:“因为戴上手套我就心慌!”[2]784在《讽刺诗和短诗》的《医生的人类学》中,医生不惜编造和夸大药效,不管穿堂风多么厉害,只要把医生们的油膏抹在肚皮上,病人就不会得伤风感冒。《医生的伦理学》中,他们虽然被称作医生,却用一些人尽皆知的常识来打发病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治疗。正如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中所说:“他笔下的庸人,诸如医生和数学家,都基于对问题有条理和理智的认识,而从事着功利主义的职业。”[3]
三、对真实而自由社会的思考和探求
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浪漫主义的风靡鼓舞着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展望,人们在肯定理性精神祛魅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强调对理性主义的反拨和矫正。这促使马克思在理性中反思现实社会,又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完成对理想社会的建构。像德国其他进步青年一样,马克思自始至终有着对权贵的仇视和对自由的向往,但他自中学时期就树立起来的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却超越了同龄人,也成为他一生坚持革命的动力。
在马克思的诗歌中,有诸如山妖鬼怪的形象,也有天使幽灵之类的形象,像《魔竖琴》《海妖之歌》《老水怪》看似荒诞奇怪,其实都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对人性的压抑,隐喻了马克思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对自由、光明、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命运悲剧《乌兰内姆》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一部戏剧作品,这部作品反映出马克思反抗压迫的精神,马克思在剧本中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对于自由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于社会变革的渴求。这部具有《浮士德》痕迹的命运悲剧,包含了马克思对于人性矛盾和自由悖论的思考,人的自由取决于社会现实,但在当时的德意志,无法保证个人的自由,人所获得的自由是扭曲了的自由。
马克思在文学作品中并没有着力去描绘理想社会的样态,他认为这个社会就在每一个人心中,只要胸怀天下、不断求索,终能砸碎身上的“镣铐”,达到理想的彼岸世界。纵览马克思的文学作品,能够发现他总是站在宇宙的高度反思整个社会。在他的笔下,自己既是创造者也是拯救者,在《献给燕妮的两首歌》的《找到了》一诗中,他接连提出四个问句,意在解答何为真正生活。或许我们掀动双翅向上飞腾,却依然撞上山崖,但是光明其实就在我们眼前,“迎候你的将会是金光灿烂的自由”[2]793。终于,马克思悟到了:世界就在我们心中,“又何必叫它到别处把世界寻找?”[2]794。但是,他绝不是在自己的诗歌王国中逃避社会;相反,年轻的马克思充满壮志,他要在实践中、在不断探求和抗争中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难道我永远应当焦渴地面对暮色苍茫,怀着急切的热望,充满焦虑和惊惶?难道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蕴,难道我就不能去求索,而只能坐享?”[2]892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他对德国社会的伦理审视,他厌恶现实社会中的丑陋现象,在文学创作中宣泄着浪漫主义的情绪。正如他在《人的自豪》一诗中所述:“面对青云直上的无耻之辈,难道我应该击节赞赏?难道我应该过这种浮华生活,浑浑噩噩地白活一场?”[2]482马克思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承袭了中学毕业论文中所表达的济世情怀,这种福泽天下的崇高理想激励着他一直保持着反抗压迫、反抗专制的革命主义热情。浪漫主义之后的马克思走向现实,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创造自己诗歌王国中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