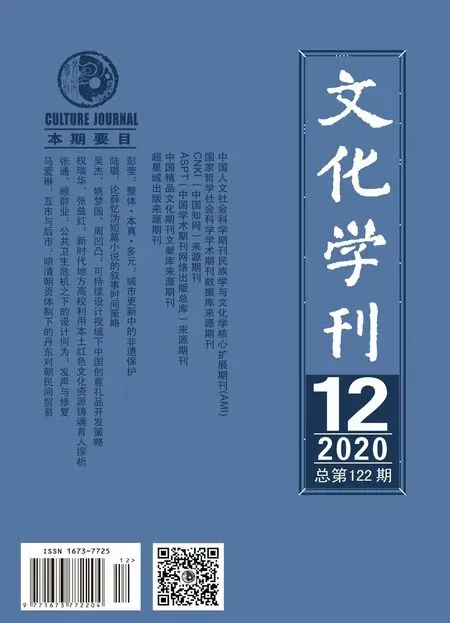饮酒与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以《世说新语》为考察中心
彭永瑜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诗经·柏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诗经·山有枢》),自先秦以来,无论忧愁抑或欢喜,饮酒都是个人疏解情感的必然选择,而到了内心情感极度奋发、不断探寻个体意识的魏晋时期,饮酒行为更是被极力推崇,社会参与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说新语》中明确出现“酒”字的史料有100余条,“酒”渗透了文人的生命意识,折射出士人面对追求理想和回归现实这两难之境时的复杂心绪。本文以《世说新语》(1)下只称《世说》或篇名,注文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龚斌校释本,所引文字皆据此书,不再一一出注。为例,看魏晋士人如何借用饮酒之行为进行沉重的生命抉择。
一、饮酒与礼教文化
中国“饮酒”文化历史悠久,经过考古学家发掘,已经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品中就有了专用的酒器。《战国策》有仪狄作酒献夏禹的传说;《尚书·商书》亦有用酒曲酿酒的记载,如“若作酒醴,尔惟曲蘖”等。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的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人工酵母,更是从出土实物方面佐证了至少在商代之前汉民族便有了饮酒习俗以及完整的酒酿造工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任何一种早期的习俗,都会从最原始的物质性功能逐渐演变成具有多种社会性的功能,“酒”也不例外。在魏晋之前,酒就经过了一系列向礼制与教化靠近的嬗变:仪狄献酒,夏禹害怕饮酒误事而严词拒绝;而《周书·酒诰》作为中国第一篇禁酒令,提出酒只能在祭祀的时候饮用,过度饮酒将会使国家遭受灭顶之灾,周王更是将商代灭亡的原因归结到过度饮酒之上,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中”“节制”不谋而合。随着祭祀和人民对自我欲望与需求的增加,饮酒不再成为一个“闲置活动”和“禁忌品”,反而开始与世俗联系起来:《周易》中,饮酒与占卜吉凶相伴,如“九五,需于酒食,贞吉”“九二,困于酒食……无咎”;《天官冢宰》则将饮酒与政治秩序相结合,对于饮酒所享用的等级有严格的划分,并设酒正一职掌管酒的酿造与使用。酒外显为礼教与规范的象征,对内则可以养生保健,如“有疾饮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礼记·杂记下》)、“身有疡则浴,首有创则沐,有疾则饮酒食肉”(《礼记·曲礼》)等等。“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说文解字》),酒亦与人的性情相系,人们通过饮酒可以摆脱烦恼或者是愉悦性情。总之,在魏晋前,“酒”作为一种食用物,从一个导致灭国的“禁忌品”到被赋予各种制度的标签,即所谓“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满足了儒家维护政教充实情感的需求,成为具有规范作用的“畅销品”。到了魏晋时期,饮酒风气在沿袭前代之风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展现出了当代士人超绝前人的生命意识。
二、魏晋饮酒文化的特点
上文概述,“饮酒”出现在祭祀、保健、颐养性情等地方,具有维护礼教与保养身心的作用,处处体现着“中”“节制”的特点。在《世说》中,“饮酒”行为展现最多的则是《任诞》篇,达40多条,可见,对于礼教的放诞成为这一时期饮酒行为的总趋势,其具体特点如下:
(一)嗜酒为荣
自酒成为一种文化标识以来,饮酒已经成为礼制的具象化,所以它必然倡导节制饮酒,反对嗜酒。但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却以过度饮酒为荣,甚至愿醉不醒,纵酒成为名士风貌的标杆、风流之士追逐的炫耀品。这样一种畸形的社会面貌,脱离不了其时代的影响。魏晋是一个士人在政治上极其无助的时期,在“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氛围中,魏晋知识分子们对生死的抉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沉重与清醒,名士们不愿意向统治阶级低头,又不能逃离对死亡的恐惧,嗜酒、醉酒便成为其保全生命的必然选择。所以,《任诞》篇有“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选拔标准,也有《赏誉》篇“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的“可矜”行为。编者将饮酒、嗜酒的行为放入“赏誉”篇,不难得知当时人对于纵酒与酗酒是十分支持且身体力行的,饮酒已经化为魏晋士人的身体,成为血液中的一部分。
(二)追求短暂欢愉
有控制的饮酒利于身心协调,而过度饮酒则非养生之道。《任诞》篇“刘伶病酒”一则主要是刘伶与妇人之间关于戒酒的对话,二人皆知纵饮非养生之道,但是刘伶依然不改并以此为人生之乐,追求一时的欢愉。《任诞》篇“张季鹰”一条也记载当时的江东步兵张季鹰愿为身前“一杯酒”舍弃身后名。可见,酒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远远超越了时人对儒家所倡导的“功名”“身体”的关注,及时行乐成为“饮酒”的具体所指。
(三)服散饮酒
服散之风的盛行也导致魏晋饮酒行为出现新的改变。五石散自汉末便有,但到了魏晋时期才成为风尚,而何晏首开魏晋服散之风,其食用之法多是以冷水散之、热酒饮之,这也直接导致饮酒之风的风靡。《世说》中有两例服散后饮酒的记载:一为《任诞》篇王忱服食五石散后桓玄为其温酒之事,二为《言语》篇钟毓兄弟小时偷食药酒之行为。此处的“药酒”《书抄》注为散酒,《太平御览》饮食部也特别注解“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可见此种药酒即服食寒食散之后的发散之酒,非传统意义上的保养身体、延年益寿之用。服食寒食散盛行其时,而酒又是散发寒食散的必备之物,所以饮酒就不得不成为一种生活中的泛滥品。
三、士人好酒的原因
服散饮酒、任情纵酒、放诞饮酒,魏晋时期的饮酒风尚已经和前代之风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魏晋士人对政局的疏离、对内心世界的追索。
现代科技已经证明,酒中含有大量的乙醇,饮用过多会麻痹大脑以至于做出不合世俗的行为。魏晋士人早已明了酒的作用,借用饮酒之后可能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规箴》篇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一条,在君臣共饮场面上,晋武帝想要传位给太子,而卫瓘则认为太子之资不堪任帝位,然而直截了当地否决天子提议不但不符合君臣之礼,更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故而借醉酒之态委婉表达自己的观点。饮酒成为异礼异俗行为的挡箭牌,也成为魏晋士人在迷茫徘徊间的一条保身之路。魏晋时期社会动乱,士人时常徘徊在不同政治力量的相互倾轧之间,从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争权夺利到永嘉南渡,偏安江左,魏晋名士们在保全自我与追求心志之间得不到平衡,就只有借助酒来放诞自我,消解自我,保全自我[1]。《德行》篇载晋文王评价阮籍之语——“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并用一个“慎”作为总结。此时晋文王称赞其“慎”,其意不在夸奖,而是以此来警告其他士人,谨言慎行。在这样一个时代,谨言慎行、远离政治才是明哲保身之上策,但心怀天下的士人们却做不到视死如归的决绝,也不愿服从于强政,那便只有寄情于酒,在酒醒与酒醉之间徘徊消解名教与情志,以此稳固自我的精神与现实家园[2]。
如果说政局是魏晋士人选择酒的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对于内心世界的开发则是士人们的自觉选择。东汉汉末,外戚和宦党相继扰政,儒家所确立的君臣顺位关系被打破,臣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下乱上,以君臣为代表的礼制关系动摇。于是,士人们不得不远离政权,日益疏离朝廷,逐渐将目光由聚集大一统的统治转向了对于自我需求的接纳,开始从皓首穷经、法古崇圣的状态中重新审视自我的价值[3]。被认为“文学自觉意识觉醒”的一代士人们逐渐重视自己的欲望与需求所在,而饮酒能一定程度解放人的性情,自然成为他们反对礼教、回归内心的一个选择,所以有《德行》篇王戎以孝期饮酒博得美名,《任诞》篇王子猷饮酒后深夜冒雪访戴成为后世绝唱。“吾本乘兴而行,尽兴而返,何必见戴”,士人们尊于内心,所行所为不拘于目的任情而动的种种行为,体现了晋人追求生活的情趣和自由放达的精神气质。
魏晋士人饮酒、纵酒正如王羲之爱鹅不为食用、支道林养马不为骑射一般存于世俗却又异于常理,不管是选择还是被选择,魏晋士人们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借由饮酒来达到自我需求的平衡,他们疏离政权,纵情任欲,与传统所倡导的入仕辅君的政治理想、克己复礼的君子之风相违背,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背离世俗,放浪形骸。恰恰相反,他们通过对于“形而上”礼教的挣脱,发现了自我价值,有情不为世俗所累,有欲不让礼教所拘,他们特立独行却又不厉色他人,顺应时代又创造了属于魏晋士人独特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