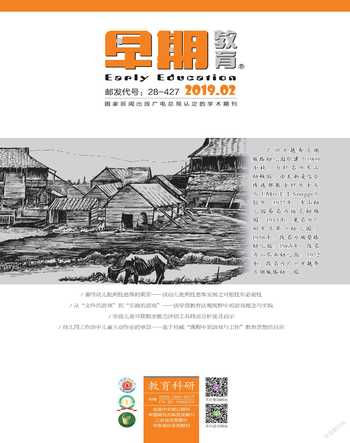善待幼儿批判性思维的萌芽
【摘要】幼儿批判性思维发展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通过对幼儿阶段有无批判性思维、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是否违背皮亚杰的認知发展理论、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可能范围进行澄清和追问,论证幼儿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可能性。通过满足现实需求、促进幼儿整合发展、获得有意义知识、转变教育观和儿童观四个方面论证幼儿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必要性。
【关键词】幼儿;批判性思维;萌芽;可能性;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9)02-0002-04
【作者简介】彭怡(1982-),女,四川乐至人,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讲师,四川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生。
我国教育思想中不乏对批判性思维的论述,如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要求学生“每事问”, 认为“疑是思之始, 学之端”;朱熹也认为“读书无疑者, 须教有疑”;陆九渊也说,“为学患无疑, 疑则有进, 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1]。但我们在实际的教育中对儿童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严重不足甚至扭曲,过多地强调服从权威和被动地接受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儿童的问题意识、质疑精神、独立思考和反思习惯。
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发展较晚,以往主要以介绍国外的研究为主,近十年呈上升趋势,但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医生等批判性思维培养上,对儿童尤其是幼儿批判性思维的研究非常少。已有研究主要是通过哲学课程的团体诘问、绘本教学、信息化手段、谈话活动等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这些研究是在默认幼儿批判性思维是存在的,默认幼儿批判性思维是应当培养且可以培养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对幼儿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笔者认为,幼儿批判性思维发展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应善待幼儿批判性思维的萌芽。
一、幼儿批判性思维具有发展的可能性
(一)幼儿表现出了批判性思维的萌芽证明幼儿阶段存在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高级思维,在幼儿阶段有没有批判性思维呢?如果在理论层面,从逻辑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用现有的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去衡量幼儿的话,很难说幼儿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但从教育者的角度,在事实的层面,可以发现幼儿实际表现出来的诸多语言和行为体现出思维的批判性,比如不少幼儿善于提问、追问;为自己的观点给出理由;能进行简单推理;能提出猜测,并通过简单的方式进行验证;会质疑他人的观点;评价别人的观点;也能倾听他人的想法和理由;在成人的引导下可以反思自己的想法甚至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些事实层面的表现至少可以让我们这样说,幼儿表现出了批判性思维的萌芽。
幼儿批判性思维的萌芽是指幼儿的批判性思维发生和开启了,这是新生的未长成的状态。这种萌芽的状态显然是与成熟的批判性思维存在差别的,如幼儿推理不严密、反思不合理、举出的例子与其观点不一致等。萌芽状态的批判性思维虽不成熟,但已经发生和开启了,就说明幼儿阶段是有批判性思维存在的。笔者在对幼儿批判性思维的表现描述、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幼儿的气质特点和思维习惯、培养幼儿批判性思维的要求等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幼儿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如下:幼儿对物体、事件、观点、行为等所展现出的好奇、质疑、比较、分析、判断的过程,是幼儿提出问题和进行论证的态度倾向和能力。
(二)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是否违背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中,“2~7岁儿童的思维属于前运算阶段,这是儿童克服各种心理障碍逐渐向逻辑思维过渡的时期。这一阶段儿童主要是表象性思维,思维的基本特点是相对具体性、不可逆性、自我中心性和刻板性”[2]。既然幼儿的思维是具体的那就欠缺了抽象的逻辑,幼儿的思维是不可逆的、刻板的那就没法反思和批判性思考,如此去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是否违背了皮亚杰的理论?
王海英在《智慧的跷跷板——幼儿元认知研究》中指出,幼儿的元认知发展一直在路上,既不是“无”的状态,也不是“全”的状态,而是处于从“无”到“有”的状态[3]。从事实层面可以发现幼儿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萌芽,但幼儿的批判性思维萌芽显然是与处于“全”的批判性思维有差异的。差异在哪里?这种差异既是由幼儿认知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比如幼儿不能只在纯语言的逻辑层面上进行批判性思考,他们需要基于动作和具体形象的事物进行思考;幼儿的推理很不严密,观点和理由不一致;对问题的探究需要在具体的活动中进行;需要别人的引导才能进行反思等。这些表现恰恰又是幼儿的具体形象思维的最好体现,是符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的。这也说明幼儿的批判性思维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发现和认识。
美国批判性思维专家的共识声明中强调了批判性思维的两个维度:能力与习性。批判性思维能力包括: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自我校准;批判性思维习性包括:求真、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信、好奇、明智[4]。幼儿天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或习性,比如幼儿好奇心强,喜爱提问,具有探究的热情,较少有固定思维的限制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方面是强于成人的,也是教育者应当重视、尊重、欣赏、保护和支持的,并需要通过关注和发展这些倾向不让其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而消失。而同时幼儿在批判性思维能力或技能方面是弱的,如何寻找到适合于幼儿学习方式的内容和方法去促进他们的发展是重要的课题。因为批判性是一种思维品质,思维品质体现了个体思维的水平和能力的差异,因此,培养幼儿的思维品质是发展其思维与能力的突破口[5]。
马修斯等人关于儿童哲学的研究充分地证明了儿童具有爱智慧的哲学家品质,其中就包括了批判性思维[6]。李普曼等研究者采取群体探究的方式进行哲学课程的教学,极大地促进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7]。
在幼儿语言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大班幼儿能有意识地运用举例质疑的方式证明自己观点,主动回应、反驳他人观点,初步思考提出新观点[8]。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到幼儿晚期,在其经验所及的事物的范围内,幼儿也开始能初步进行抽象逻辑思维……并且到幼儿晚期,在其所能理解的事物的范围内,儿童一般都能很好地进行合乎事物本身逻辑的判断和推理[9]。因此,大班幼儿的批判性思维的表现应该能被发现和研究,且在幼小衔接时期,其批判性思维发展也最应当得到关注和促进。
(三)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可能范围
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具有一定的范围,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里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才具有可能性。已有研究通过提出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目标,澄清了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可能范围。如将“具有敢冒风险、敢于怀疑和批判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否定、质疑,大胆运用假设手段通过各种途径验证自己的观点”[10]作为对大班幼儿在活动中批判性思维表现的要求。幼儿批判性思维主要指幼儿学会质疑、分辨和表达,将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明确分为问题意识的培养,区分事实与观点的培养,观点表达能力的培养这三个方面[11]。有研究认为对幼儿而言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对所接受的语言、所经历的事件进行客观分析、客观评价、客观表述的思维。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幼儿具有这样的思维习惯:能独立思考,不盲目相信,喜欢问问题;能愉快地接受和自己不同的观点,不用消极情绪对待;善于发现细节,事物(事件)发展的联系,表达有理有据[12]。也有研究提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幼儿应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探究的精神、开放的心理、不迷信权威以及积极的反思的特征[13]。
从中可以发现,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可能范围主要在思维的倾向性方面,而不强调幼儿批判性思维的技能水平。如幼儿愿意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观点,但是并不要求证据与观点相协调;愿意进行推理,但是不要求其推理的严谨性;能够在引导下进行反思,但是并不要求反思的主动自发性。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幼儿批判性思维培养是具有可能性的。
综上所述,关注并促进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并非是超越皮亚杰理论试图对幼儿认知发展进行拔苗助长式的提前教育,而是基于幼儿认知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充分地关注、尊重、欣赏幼儿批判性思维萌芽的表现——幼儿天生具有的好奇心,把习以为常的事物变得不寻常,他们爱思考爱发问,乐于刨根问底,喜欢质疑、想象和猜测,乐于操作探究,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据(证据和观点可能并不协调),借助于活动和动作进行“直线式”的推理和反思等。实质上,正是在欣赏和尊重具有“幼儿特点”的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提出关注、保护和发展幼儿的批判性思维,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展开和揭示幼儿思维中更多的秘密和宝藏,这也是建立成人与幼儿间平等关系的尝试。
二、幼儿批判性思维具有发展的必要性
(一)现实的需求: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思想独立和观念创新的重要前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14]。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保尔曾断言批判性思维将会成为21世纪教育的本质性基础[15]。当前,批判性思维同协作、交往与创造性是世界共同追求的核心素养[16]。但是,现有研究表明,批判性思维教育在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被严重忽视[17]。只有在少量的中小学中将批判性思维的方法纳入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中;寥寥几所高校在哲学专业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但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学生只获得了一些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基本原理等,缺乏深刻的理解和锻炼,更无法将其有效地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学习中[18]。2010年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指出,中国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说明,我国学生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效果确实还非常弱小。面对急速发展的技术变革和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澳大利亚把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探究性与合作性能力的儿童作为应对时代挑战的核心对策,并通过在学前教育或小学阶段设置儿童哲学的课程来形成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品质进而提升教育质量[19]。可见,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品质,不仅应当在大学培养,在中小学阶段培养,而且应当从学龄前阶段就重视和培养。因为幼儿具有极强可塑性和发展潜力,对其进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应当是最有成效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正如余保华等人所言,透过澳大利亚儿童哲学课程的发展我们能看到,首先,逻辑推理与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应该从儿童开始,而錯过了关键期想在儿童成年后再去实现这样的目标则十分困难[20]。
对于生活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中的儿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综合、复杂的世界,更加需要建立起独立思考和自我判断的意识。儿童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已成为了极具时代特点的国际性课题[21]。
(二)发展的整合: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促进幼儿全面整合的发展
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提出了以下要求:关注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22]。培养幼儿的批判性思维,能够促进幼儿在语言(倾听、理解、表达自己的观点、阅读查找资料等)、社会(具有自尊、自信、自主的表现、与他人互动、理解他人看待问题的角度等)、科学(质疑、积极探索、判断、推理、论证)、艺术(用多种方式表征自己的观点)等方面获得全面整体的发展。具备批判性思维的幼儿往往能够通过自主的学习和探索获得直接经验,能够在生活和游戏中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独特的思维和表现,表现出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主动与坚持,质疑和反思的精神。因此,培养幼儿的批判性思维与《指南》精神是相契合的,促进幼儿获得全面整合的发展,对幼儿的未来学习和终身发展具有奠基的作用。
(三)知识的获得: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促进幼儿进行深度学习
发展幼儿的批判性思维,促进幼儿在具体的情境中,与教师、同伴相互提问、讨论、争论和辩论,为验证自己的观点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证据,改变原有的观点认同新的观点等,实质上是促进幼儿进行深度学习,即在目的维度上指向内在动机、在内容维度上指向知识背后的深层意义、在方式维度上指向问题解决学习、在结果维度上指向意义。深度学习是有意义的知识获得的重要途径,是幼儿自主建构的过程,有助于打通教育与幼儿的生活,知识与幼儿经验之间的壁垒,有助于提高幼儿知识学习的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
(四)观念的转变:发展幼儿批判性思维促进科学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建立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成人的绝对权威,对儿童的要求和期待是“乖”“听话”,评价儿童的标准是“顺从”“循规蹈矩”的孩子是好孩子,“调皮”“越轨”“不安分守己”的孩子是坏孩子。持有这样评价观的成人显然是抱有“成人中心”的观念,采取的也大都是强制、灌输和命令的教育。发展幼儿的批判性思维,并不是鼓励幼儿的任性和叛逆,而是去发现真实的幼儿的存在,建立平等的成人—儿童关系,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热情,认真地关注幼儿的思维,真诚地尊重幼儿的想法,并能用适合于幼儿的方式去支持他们进行有意义的学习,鼓励其主动积极地建构。这是全社会都需要建立的科学儿童观和教育观。
三、结语
幼儿批判性思维的萌芽是存在的,具有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应当在启蒙语境下对幼儿批判性思维进行关注和促进,珍视幼儿好奇的天性和探究的热情,尊重幼儿思维的独特视角,保护幼儿的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鼓励幼儿进行判断和推理,引导幼儿为观点寻找证据、进行反思,在与外界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的过程中经历有意义的学习,获得精神上的成长。
【参考文献】
[1]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二卷) [M] .上海:華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89.
[2][5][9]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210,285,218.
[3] 王海英.智慧的跷跷板——幼儿元认知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6.
[4] 田莉莉.近十年来国内批判性思维研究及其教学反思[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10.
[6] 钱雨.儿童哲学的意义——马修斯与李普曼的“对话”[J].全球教育展望,2009(08):19-24.
[7][21] 方展画,吴岩.李普曼以对话为核心的儿童哲学课程及其启示[J].教育研究,2005(05):70-76.
[8] 周兢.学前儿童语言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
[10] 陈洪波.讨论式学习中大班幼儿批判性思维的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6(05):31-33.
[11] 朱顺理.信息技术环境下基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儿童绘本教学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7:10.
[12] 范灿灿.在绘本阅读中“教幼儿批判性思维的过程”的实践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7:2,11.
[13] 鲍梦玲.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儿童哲学课程——基于lAPC文本的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24.
[14] 陈振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模式之争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4(09):56-63.
[15] 钟启泉.课程的逻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44.
[16] 张华.论核心素养的内涵[J].全球教育展望,2016(04):10-24.
[17] 冯艳.论批判性思维与创新的关系[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4):22-25.
[18] 干咏昕.用批判性思维方法打造批判性思维课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51-54.
[19][20] 余保华,刘晶.澳大利亚的儿童哲学课程发展及其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15(03):46-56.
[22] 李季湄,冯晓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287-288.
本文系 2017年度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幼儿批判性思维及其启蒙教育研究”(课题批准号:GS[2017]GHB1944)、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2015年校级科学研究立项项目“学前儿童批判性思维及教学促进研究”(课题批准号:2015001KA)的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彭怡,54047966@qq.com
(助理编辑 王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