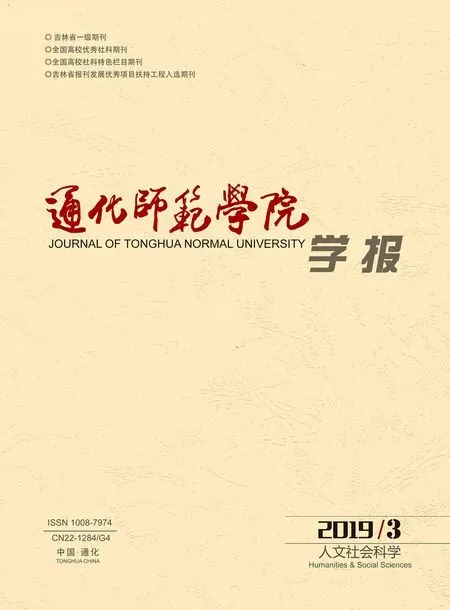《新安女行录》的影响与价值
赵 敏
关健词:《新安女行录》;徽州女性;体裁
程云鹏(1663—约1729),字凤雏,一字丱斋,号华仲,歙县人,撰《新安女行录》二十卷,乾隆十五年(1750)刊本。此书长期未见传本,因此没有学者介绍、研究和实际利用此书,仅见数处关联引用,均是引用《(民国)歙县志·艺文志》收入的沈一葵所撰之“叙”①如王传满《明清徽州知识精英对节烈妇女事迹的张扬》(《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一文仅列三种方式:“地方志采录”“家谱录入”“文集记载”,未及专门著述。。近年来,随着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孤本《新安女行录》的披露,该书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童岳敏《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新安女行录〉述略》主要从“史传文学”的角度出发,简要概括了《新安女行录》的“史学价值与文化意义”[1]。拙作《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孤本〈新安女行录〉》则详细考订了该书作者程云鹏的家世、生平、交游,成书过程、刊刻年份、版本情况等,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文献解读与利用的方便。《新安女行录》主要记载节妇烈女的事迹,无疑是一部徽州妇女的血泪史。但其在编纂体裁、选录标准、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使它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并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限于篇幅,言有未尽,另草小文,供方家批评。
一、体裁变新及其影响
我国的女性人物传记出现很早,先秦文献《国语》《战国策》就有部分篇目专叙女性的事迹,说明古代史家是密切关注并充分肯定女性的社会与政治作用的。司马迁撰《史记》,更是为“临朝称制”的吕后立“本纪”,表彰她“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群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521同时,他也重视社会下层妇女,如《刺客列传》中聂政之姐“荣”,《货殖列传》中的巴寡妇清等。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向领校中秘,他采撷古代妇女故事,撰成《列女传》,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八类,以类相从,记载了一百一十位女性的事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女性专传。《列女传》所收女性既有“有虞二妃”“周宣姜后”等帝王后妃,“鲁季敬姜”“柳下惠妻”等贵族妇女,也有“鲁漆室女”“齐义继母”“晋弓工妻”等社会下层普通女性,不少甚至连姓氏都没有留下来,而“孽嬖”则收录了被认为“淫妒荧惑,背节弃义”的反面女性,诸如“殷纣妲己”“周幽褒姒”等。举凡兴国匡主、孝亲节烈、相夫教子、睦族敦邻、田桑绩织,以至败德乱行、祸国破家,无所不涉。《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3]1957-1958。说明刘向编撰此书,是希望通过对古代女性品性德行所造成的不同后果的表述,达到劝诫君主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保存了古代女性史的珍贵资料,同时也体现出刘向对于女性在家庭、社会、政治等方面重要作用的充分认可。发凡起例,功莫大焉。
《列女传》之后,关注女性问题者代有其人,出现了不少有关女性的专门著述,大致分为三种形式:
首先是《列女传》的各种续、补,或某一特定时期的女性传记总录。如署名曹大家的《续列女传》一卷、晋皇甫谧《列女传》六卷、明解缙等《古今列女传》三卷、明邵正魁《续列女传》九卷、清刘开《广列女传》二十卷等等。多数以《列女传》之“ 母 仪 ”“ 贤 明 ”“ 仁 智 ”“ 贞 慎 ”“ 节 义 ”“ 辩 通 ”“ 嬖孽”七类立目,或略有变通,主要收录历朝自后妃到民间的著名女性。而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皇后纪》,又有《列女传》,记“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更显出其对女性历史作用的高度重视,开纪传体史书为女性设立类传之先河。明代以后,出现了分专题的女性人物传记总录,诸如明吴震元《奇女子传》四卷、清洪饴孙《历代后妃纪》、清童岳荐辑《善女人传》二卷等。像清人杨锡绂所撰《节妇传》,就是专门搜集采访节烈妇女事迹,各为小传而成。自全国“一统志”而下,省、府、州、县方志以至乡镇志中的“列女传”或“烈女传”也可以归入这种形式。
其次是女诫类著述。如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女论语》,明徐皇后《内训》,黄希周《闺范》六卷及《闺鉴图集》六卷,吕坤《闺范》,夏树芳《女镜》八卷,清陆溥《闺训图咏类编》等,专门对女性进行基础知识与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同时会选择一些典型女性的事迹作为例证。
再次是见于女性文学作品总集中的人物传记。从南朝梁殷淳《妇人集》始,历代续有编纂,亦多以“妇人集”名之。入清尤多,如陈维崧《妇人集》一卷、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卷、《随园女弟子诗选》六卷等,这些总集大都附有作者小传,可略见其生平事迹。
以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划为界限的郡邑类人物传记总录出现很早,东汉赵岐即撰有《三辅决录》七卷。两晋南北朝,受士族门阀制度的影响,蔚为风尚,著述众多,各主要地域都有“先贤传”或“耆旧传”,记载历史,表彰乡贤。男女人物传记合编也已出现,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为“先贤士女赞”,包括“蜀郡士女赞”“广汉士女赞”“犍为士女赞”“汉中士女赞”“梓潼郡士女赞”等五部分,先士后女[4]。这种形式一直沿袭至清代,如黄希声撰《东雍士女志》二卷,是山西绛州(北魏太武帝时曾立东雍州)的人物传记总录,卷一包括士传十四附传二,卷二则为女传十九,每篇后附简评[5]。
程云鹏撰《新安女行录》(以下简称《女行录》),变体裁为郡邑类女性人物传记总录,专载徽州府辖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婺源六县妇女“诸淑德”,包括传、表、叙(序)、记、哀辞(诔)、墓志铭(墓表、墓碣)、祭文等多种传记文体,二十卷计一百二十余篇文章(其中卷十九《懿孝程孺人行状》,是江苏布政使牟钦元为其母所撰),记载了数百位女性的事迹,是为滥觞之作①汪洪度《新安节烈志》早已佚失,未知其编撰年代及刊刻与否;曾任崇明县训导的华亭人张荣(1659—?),致仕归乡后撰《崇川节孝录》六卷,录崇明县得到崇奖的贞女、节妇、孝妇二百人。但此书并未单独刊刻,而是附于张荣《空明子后集》末,于康熙五十九年(1710)印行(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此时,程氏《新安女行录》已经基本成书。。实际上,程氏对其他地区女性的事迹也极为关注,撰写了不少传记,但因此书体例所限,“他郡女行,另载拙著文集,与士大夫纪传共传,兹不录”[6]《凡例》,惜其文集不传,难知详情②程氏文集,文献所载仅见《北征集》,《(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艺文志》有著录,据说是其匹马塞外,穷河源所作。另外其孙程雨鄂说:“先祖母……诸闺行,散见王父大人别集。”(《新安女行录》卷十八《亡室潘孺人墓碣》评语)外孙吴宽说:“外祖丱斋先生著述等身,集所为文近百卷。”(《新安女行录》跋)则程氏于《北征集》外,尚有文集近百卷,并不传。。
这一新体裁的出现,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清中叶以后,郡邑类妇女传记总录陆续出现。如汪辉祖(1730—1807)《越女表微录》五卷《续录》一卷,正录分“录事”“类叙”“述谱”“外姻”四部分,续录则别为“识轶”,记载历代绍兴府属六县节孝妇女事迹,共三百三十余人。汪氏出于侧室,其父早逝,赖继母与生母守节教养成人,后乃请得旌表,立双节坊,刻《双节堂庸训》及《赠言》以纪念。他亲历两母守志之苦辛,推而广之,为本邑女性编成《越女表微录》,以报母恩,兼彰女德。从书名、体例、结构来看,《越女表微录》是与《女行录》一脉相承的。到清末,余杭人孙树礼(1845—1936)仿汪著,撰成《杭女表微录》十六卷首一卷,“采录杭州一郡之女,以县名为纲,而分节妇、烈妇诸目”[7]16。虽承汪氏书名,但体例却有变化,这是因为孙著本为《杭州府志》所撰《列女门》,内容全数收入府志,后来又单刻印行。
二、选录标准与文献价值
程氏在“凡例”中说:“刘中垒《列女传》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六科,近世施行旌例,仅登节烈,是集尽载诸淑德。”委婉表达了对前代此类著述收录范围的不满,并强调自己的撰集宗旨是“有一端可表,见皆为撰录”[6]《凡例》。因此,他的传主类型范围有明显扩展,凡在某一方面有过人之处或突出贡献者,皆予收录,不仅限于节烈与贞孝,基本恢复了《列女传》的传统。
《女行录》所载徽州妇女,大多被载入了乾隆(1736—1795)以后修纂的《徽州府志》与各县县志,但地方志的纂修有自己的程序与规则,“列女”或“烈女”传所载,首先是获得官方认可,由国家或各级政府旌表建坊者;其次是通过采访程序,先登入“采访册”,经共同商议符合入志标准者,一般并不标注来源。不过乾隆《歙县志·列女传》中,有几位人物传记后注曰:“见《新安女行录》”或“传载《新安女行录》”,保留了自《女行录》采集资料的痕迹。如“程其猷妾吴氏”条,出自《慈节二程母传》,“汪予襄妻谢氏”条出自《汪母谢孺人家传》,“闵汉龙妻吴氏”条出自《闵汉龙孺人传》,而《傅溪三节记》则被分成“吴门双节”与“程朝桂妻吴氏”两条收入。沈一葵撰《新安女行录序》,于程氏之功,体会尤深:“新安故多女行,奉圣天子奖励,岁有旌扬。而穷乡僻壤,采录未尽者,程生云鹏编入《女行录》中,或已经题请,而其人懿行不得悉列条奏,亦皆拾遗撰著,以为其人家乘荣褒,里巷程法。”[8]此序为乾隆《歙县志·艺文》收入,其为程氏及《女行录》之幸欤?
《女行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地方志纂录中,卷十九所载程氏为其侍妾童英所写“传状”,因为剜改导致佚题、脱文,已非完璧,不能详其始末。但结合他篇记载,可知梗概:童氏负父仇,匿身为妓,后自赎籍而归程云鹏为妾,随即辞别,手刃仇人于三峡,重归程氏,年二十二染疾亡。程云鹏以其事迹及同人挽诗刊为《怀梦草》,其人其事本属罕见,所撰传状又跌宕起伏,颇类唐人传奇,有好事者遂将童氏复仇故事改编为戏曲《梦香楼传奇》[6]卷十九,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徽州地少人多,成年男子多离乡谋生,妻子在家庭生活中承担重任,《女行录》中除大力鼓吹女性的贞孝节烈之外,对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也给予了肯定与赞扬。女性在丈夫外出经商、游学或者亡故的情况下,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如经理生计、赡养翁姑、抚育子女等,有的还要夫家、娘家兼顾。如歙县项氏,成婚甫旬日,丈夫即赴常州,次年即亡。“继怀瑾嗣夫后,翁纳婢举子,遭家人柔践,母曲调护,语怀谨曰:‘汝善视之'”。“兄淇四十外,未有自息男,……及淇举子本忠,即归任嫂劳,市乳乳之,滌浊秽,燥沴湿,无异己出。稍长,母教以孝弟之道,……母循谨有家法,亲族妇女知母贤,时有质成,咸去其诟厉变化归于良善。”“节母造两家之福。”[6]卷十八
明清以来,徽州女性受教育程度颇高,在子女教育方面,女性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类例子,《女行录》中比比皆是,不烦枚举。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些妇女出自书香门第,却能不顾旧俗,鼓励子弟弃学从商,颇有远见卓识。丛睦汪文焕,父亲与叔父皆早逝,母亲谢氏与叔母程氏共抚文焕,两门一子。程氏为学者程弘志之女,母家富藏书,“素娴《内则》、《孝经》,明晓当世得失,文焕就外傅归,必叩其所学。尝训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尔家自曾王父大参公至今成进士者,代有其人,尔一身系两父母之重,未可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也。……及长,安人乃曰:‘吾乡地狭人众,非贸迁不足以资衣食,天下事有权有变,宁甘执兔园册子?'”[6]卷三汪文焕遂弃学而营商,家至富。
《女行录》既记官宦、富商等上层妇女治家育子的事迹,也有中下层女性迫于生计的艰苦劳作。如歙县汪伯善妻郑氏,十六岁出嫁,伯善家贫,外出营生,客死不还。郑氏“支吾甘旨,糠豆不赡,终日矻矻,养二人及太姑……茹菽不足,朝锉烟不举,穷乡丝枲无所用,孺人亲执揪耫,薙草种蒔。”[6]卷六还有甘贫积苦,助夫读书者,江永之妻许氏,与丈夫“同艰苦六十有六年,操纺织以佐……方饩廪,资用乏绝,孺人娩身五日强起缉布,助规例之费。”因此,江永非常感激:“余贫窘,甚赖先妻甘淡泊、耐勤苦,故足读书。”[6]卷十六又如歙县江万里妻项氏,夫客死,项氏“樵牧耕织,办翁事,改葬姑于吉壤,归万里櫬而附姑侧”,且百般督护万里诸弟,使一家得以周全。[6]卷十七
《女行录》中尚有不少女性赡族睦邻、多行义举的记载,如卷十九所收《公祭汪母文》:“筑义舍以居族人,虽始夫子之志,实出太君之成,是杜少陵之广厦万间,太君真见之行事也。族女为人掠售,太君倾筐倒箧百折曲存,不顾是非利害,卒直其事。”[6]卷十九充分体现出在徽州传统社会体系中,妇女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功能与作用。
《女行录》所收女性传记,除节、烈、孝、贤、慈诸属外,尚有不少为人忽视的社会下层妇女事迹及有其他社会作为的女性,如卷十四所收《义井记》《潭渡女祠记》,卷二十所收《贫婆传》《乳孙朱母传》《施兰如传》《冬梅传》等,《施兰如传》为娼妓传,记黄汝材侍妾施兰如,“兰如幼亡父母,有殊色,为人掠卖,既而归汝材,汝材故浪子,嗜酒废业,兰如藉针绣自食十二年”[6]卷二十。更深层次地揭示了明清妇女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及作用。
地方志《列女传》记事非常简略,甚或仅载名氏,程氏《女行录》则注重交待事件的来龙去脉,长于细节描写,充分体现了传记的体裁优势。加上所记多为程氏亲自采访所得,有不少还是亲属、邻里、故人,史事相对真实可靠。很多篇章详细叙述了妇女的婚嫁、生育年龄,以及丈夫亡故后经营生计、打理家政、赡老抚幼等事务。其中不少人物史事不见于方志与其他文献,是进一步研究徽州妇女史的重要史料。书中尚有许多姻娅关系的说明,这在其他史料中也比较少见,能够帮助研究者结合家(族)谱,深入梳理徽州地区程、胡、吴、汪、方几大姓氏之间的通婚情况,也可以借此厘清一些著名人物的家世与行实。同时,该书还保存了大量社会风俗史的资料,如居处衣食、节庆祭祀、建坊立祠、继宗迎养、慈善恤抚等等。
三、议论简评中所反映的女性观
程云鹏服膺司马迁、班固、范晔、欧阳修等著名史学家的“史传”之作,因此,《女行录》一书采取史传写法,“或畅发人事之当然,或讬物比兴,以彰其人,传其事,总归于扬扢风化,鼓舞彝伦”[6]目次后,“备国史采用”[6]凡例。他用“程云鹏曰”“云鹏载论曰”“华仲载论曰”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认识与观点。全书每篇之后,皆有亲朋故旧及徽州文人的简评,除品评文采外,点评者也都抒发了针对女性与社会的相关议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号称“闺门邹鲁”的徽州地区知识分子的女性观念,足以为研究者开启新的视角。
首先,表彰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关键作用。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母亲在教育子女上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母亲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学识和品性。《韩非子·显学》就说:“慈母有败子。”[9]355程云鹏等人对明清徽州妇女的家教、家训都特别重视,并认为是家庭兴旺、子孙发达的重要因素。在《双桥郑氏六节母表》中,程云鹏他说:“予过贞白里,慨慕其先世多贤,及闻郑星焕代兄缧绁事,岂忠孝节义,数百年犹佩服于人心,虽闾巷之子,尝慕悦而为之欤!乃询其家训,则皆由节母之教。”[6]卷十并将她们与先周之太姜、太姙、太姒相比美。无独有偶,卷四《二吴母传》:“方二于曰:二母同秉礼度,知大义,贻厥孙谋,固宜益大昌厥后也。吴本理学渊源,自宋适今,族日益大……是知西岐之开国,非特男子之圣圣相传云尔。”[6]卷四也是以先周初兴时太姜等杰出女性的重要贡献作比喻。而卷四《宋贤母传》后,有王啇齐简评:“宋安人贤声藉藉,姻族奉为女师,两嗣君咸秉家教,而为诚笃君子,将见崔山南昆弟子孙之盛,悉由于母德矣。”[6]卷四唐代崔琯祖母唐夫人以己乳饲喂婆母长孙夫人,后琯仕至山南节度使,一家贵盛。王氏以唐夫人喻宋安人,表彰其母德家教。
其次,肯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女行录》一书的出发点是维护与表彰传统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程云鹏家族(樟森塘程氏)在繁衍流播过程中,妇女曾经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予先世每值不造,则赖母德以佑启后人。及观之閭左,徵之郡邑,考之书传所记载,亦往往而然”[6]卷十。他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幼年时父亲客游,母亲理家抚子,后来迁至江夏,又是依外家而居。所以,程氏对女性在徽州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认可的,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予读浦阳《郑氏家训》曰:‘守家规不听妇人之言。'未尝不叹其深入人情也。然而风移俗易,事或不然。大丈夫纲纪四维,经营四方,而门内之政,不得不诿于妇人。此非贤明而仁智,能为一室之母仪者,孰能当此者乎?”[6]卷五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文化教育发达,科甲鼎盛,徽商经营,遍于天下,男性游宦贸迁,妇女的家庭、经济与社会作用尤显突出。程氏感叹道:“呜呼!扶舆磅礴之气,不独钟于男子,亦自钟于妇人;盛衰兴替之悲,不独系于国家,亦且系于里巷。”[6]卷十九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再次,不满传统礼法,同情女性遭遇。在《奇节徐氏许氏列传》中,程云鹏直抒胸臆:“读圣人论妇人之七出也,曰‘恶疾去',窃讶圣人非人情。妇人从一而终,终身无一可,苟不幸而撄疾患,当怜悯之,何至去之唯恐不速也?”而且“妇人于夫之恶疾则安之,则亦奉圣人之教,而兢兢乎不敢怠也。”[6]卷十明确指出了古代法律、礼制、习俗中歧视妇女的“七出之条”与传统封建伦理“从一而终”的妇德之间的矛盾。而在《慈节二程母传》中,程云鹏针对明代以来庶妻不得诰封、庶母许封受限①徐溥等《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凡诸子应封父母,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并封。”“应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如正妻生前未封已殁,继室当封者,正妻亦当追赠,其继室止封一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再造善本。,“凡诸子应封父母,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等制度,引汉文帝自称“高皇帝侧室之子”为据,表达了对传统嫡庶贵贱观念的不满以及自己对妇女的同情与关怀[6]卷五。
总之,《女行录》的议论和简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程云鹏等人重视女性家庭与社会作用、同情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遭遇的进步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