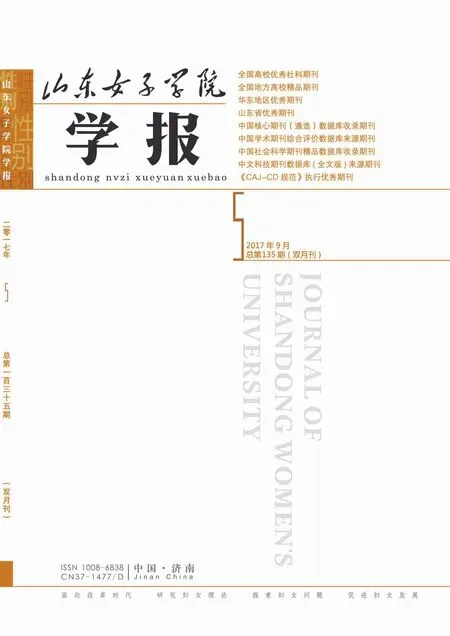论《列女传》的刻印和传播
靳 力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妇女史研究·
论《列女传》的刻印和传播
靳 力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 250014)
宋元明清时期,《列女传》的刻印呈现出官、私两旺的盛况。从刻印的主体来看,有官府和私人两种类型;从刻印的内容与形式来说,有插图本、纯文字本与增删本等;从刻印的国别划分,有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刊本;从流布的形式而言,有刊印《列女传》的单行本与被类书、旧注称引者;另外,还有对《列女传》补注、校注、集注等研究著述的刊行。而就传播来看,多样化的传播路径,广袤的传播范围,多重性的传播效果,极大地增强了《列女传》的传播力,使之不仅畅行全国,而且还远播域外。《列女传》的刊印与传播互为依托与因果,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效果明显,对当时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而切实的影响。
《列女传》;版本;刻印;传播;图书;出版业
西汉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1](P1957)编次而成的《列女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反映妇女生活的历史故事集。该书的编撰,主要针对元、成之际,外戚擅权、后妃逾礼的社会现实,根本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礼制。刘向所倡导的礼制思想、女性教化理念,在《列女传》这部将女性德行与国家兴衰治乱相关联的著述中,得到很好的阐释。由此,《列女传》因契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化民成俗”、影响深远的女教典籍。而在体制上,《列女传》的文本极似史书,真实性辅以故事性使之在形式上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与《列女颂》《列女图》一并构成了严谨而完善的传播体系,在当时的传播条件下达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2]。早在西汉末年,《列女传》一书已流传至边郡,就是很好的例证[3]。其后,为《列女传》作注、颂、图者,代不乏人。例如,东汉的班昭、马融等曾为之作注。又如,据《隋书·经籍志》载,三国时期的曹植,曾为之作颂——“《列女传颂》一卷。”其注曰:“曹植撰。”[4](P978)再如,东晋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为《列女传》作图。凡此种种,无疑都极大地增强了《列女传》的传播力。尽管如此,在隋、唐之前的抄本时代,图书的复本制作周期较长,成本很高,这就使《列女传》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上述自东汉到魏晋所作《列女传》的注、颂、图,今皆佚,就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直到雕版印刷技术较为成熟的宋代,这种状况才得到根本改观。《列女传》被广泛刻印,流传甚广,已成为民众,特别是妇女的必读之书。现仅就《列女传》刻印与传播等问题,叙论如下。
一、《列女传》的刻印
(一)官、私刻印的《列女传》
宋代以降,刻书活动的经营者主要包括官府和私人两种,私人刻书又分家刻与坊刻两种类型。明代官刻的《列女传》主要有以下几种。据明代周弘祖所撰的《古今书刻》所载,明朝中期,南直隶苏州府和江西临江府均刻印了《列女传》。另据明代徐图的《行人司重刻书目》所载,行人司于万历年间刻印了《列女传》。此外,据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明朝正德年间刊行六卷本刘向的《古列女传》。由该书作序者为辽州知州与汝州知州,推测此《古列女传》应为官刻之书。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为重振儒学,由曾国藩倡导,始建江南官刻书局。其后,各省纷纷效仿,湖北武昌设有崇文书局。出于“维世道”“正人心”等目的,崇文书局刊刻了《列女传》。
明清时期私家刻书风气甚盛,大多集中于富饶且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如江浙一带。许多刻书家,如清代的鲍廷博、顾广圻、阮元等,都是藏书家,因藏书而提倡刻书,在刻印《列女传》方面贡献良多。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黄鲁曾所刻印的刘向《古列女传》七卷、续一卷,被收入《汉唐三传》,故又称为《汉唐三传》本,影响较大。明末太仓张溥就是根据此本,于崇祯年间重校刊行《古列女传》。明代徽州的黄嘉育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刊刻刘向的《列女传》,为私人刻书中的精品。鲍廷博以业商致富,致力于藏书与刻书,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收书207种,内容广泛,校刊精良,世誉善本。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鲍廷博得到万历年间汪氏增辑的《列女传》十六卷,重印此本,为知不足斋印本。顾之逵好藏书,家多宋元善本,为吴中乾嘉时期四大藏书家之一[5]。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得到建安余氏《列女传》之内殿本后,于嘉庆元年(1796年),请其弟顾广圻整理刊印。顾广圻喜校书,所刻印的小读书堆本《列女传》为难得之精品。这由后人对《列女传》注释、校勘多选用此本作为底本可见一斑。阮元精通经学,长于考证,家有文选楼,小琅嬛仙馆藏书、金石甚富。道光五年(1825年),其子阮福按照南宋余仁仲勤有堂《古列女传》行格图画影摹刊行,为《列女传》小琅嬛仙馆本,又称“文选楼丛书”本,简称“阮本”。
坊刻是以刻印图书为主营业务,以获取利润为终极目的,极具鲜明商业特性的图书出版业[6]。《列女传》因受众多,社会需求量大,易获利,而成为坊刻业主乐于刻印的图书。早在宋代,福建建安余氏就以刊书为业,世代经营,历时700余年[7](P293)。传世的《列女传》刻本就是以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本为最古[8]。明代坊刻业最发达、最集中的是南京、杭州、福建建宁府建阳县等地,均有《列女传》的刊刻、重刊、重印。明代南京的书坊在全国城市中位列首位,于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期。其中,以唐姓十五家为冠,刻书数量也最多[9]。唐锦池文林阁重印了黄嘉育的《古列女传》。明代杭州书坊刻书最多的是胡文焕的文会堂。据记载,胡文焕刻印的图书达450多种,其中就有以黄嘉育本为底本略加改进模仿翻刻的《列女传》。福建北部的建阳县是我国古代印刷的重镇,到明朝嘉靖年间已成为当时全国印刷业的中心。《古今书刻》著录明朝中叶建宁府书坊刊刻《列女传》一种,《(嘉靖)建阳县志·书坊书目》著录坊刻《列女传》一种。至清代,《列女传》仍然是各地书坊刻印的书目。有印刷传统的地区自不待言,就连地处闽西山区的福建四堡也加以刻印。现在确有具体记载或见实物的,四堡书坊共刻印图书489种,马益保的翼经堂、邹步蟾经营的堂号为云深处的刻书坊均刻印了《列女传》[7](P316-339)。
(二)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列女传》
《列女传》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列女传》的篇数为八篇,包括传七篇、颂一篇。班昭注《列女传》,分传每篇为上下,合颂成十五卷。其后,《列女传》十五卷本流行,原八卷本渐佚。北宋嘉佑年间,集贤校理苏颂、长乐人王回对《列女传》先后进行整理,将全书删为八篇,包括七篇传、一篇颂,称《古列女传》。属后人掺入的二十传,以时相次,号《续列女传》。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武夷人蔡骥在苏、王定本的基础上,整理刊刻《列女传》,题《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或通题八卷[10]。现在所见各种刻本的《列女传》都由此而来,只不过在各种心态作用及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出现的形式与内容不同罢了。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其后随文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1](P1727)。由此可知,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分传、颂、图三部分。插图配画既可增强读物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使空洞的说教变得生动形象,又符合我国古代读书左图右史的传统。《后汉书·皇后纪》载顺烈皇后小时候好史书,“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11]。可见《列女传》的价值观已随列女图等的流传,开始深入人心。宋代福建刻书的版画水平很高,形成了粗犷古朴的建安派画风。建安余氏作为坊刻业主,为追求利润,便附以列女插图,并署名“晋大司马顾恺之图画”,以迎合读者崇古心理,使《列女传》更为畅销。明代图书多以精美的插图吸引读者。许多刻印图书者,特别是坊刻业主都争相聘请技艺高超的图版雕刻能手,并让知名画家为图版起稿画样。于是,多种插图本的《列女传》在赫然冠以“全像”等字样的形式下应运而生。例如,南京唐富春的富春堂刊刻了《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万历十五年(1587年),藏书家茅坤又增补了唐富春刊的《列女传》。又如,万历年间的汪氏增辑《列女传》十六卷,号称风俗画家仇英为之绘画,刻工讲究,为精致婉丽、气韵生动、刀法精细徽派名版。再如,黄嘉育与唐锦池刊刻的《古列女传》,插图精美,似出仇英一派手笔[12]。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七》中尝言:“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13]这在明人所刻的《列女传》上表现得格外突出。许多《列女传》的改编本对刘向的原著随意增删,使刘向的《列女传》面目全非。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解缙等人在刘向《列女传》的基础上,重编《古今列女传》三卷,收录虞夏至明朝可为“永作世范”女性的懿言嘉行。因刘向《列女传》中的第七卷《孽嬖传》为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等的反面教材,与圣旨相违,故遭到了封杀删节。古谚曰:“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明代的许多官、私刊刻的《列女传》都相沿此例。例如,明朝正德年间所刊刘向的《古列女传》、唐富春刊刻的《新镌增补全像评林古今列女传》,以及茅坤增补唐富春所刊的《列女传》,都缺失了第七卷。与之相反,有的刻印者擅自篡改,增添内容。例如,黄鲁曾刊本在刘向《列女传》原书每传的颂言之后,增加了自己新创的四言赞文。不仅如此,有的刊刻者还将本地列女增添入图书。例如,徽州汪氏以自己的亲戚徽州汪、程两姓女子事迹,增补刘向原书,使《列女传》由七卷扩充至十六卷。其书后因鲍廷博的重印,以及图画精美而被后世推崇。
如前所述,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是配以图画的。不过,在汉代社会,丝帛虽是优良的书画材料,却过于昂贵,难以广泛使用,也不易长久保存。而古代图书在流传过程中,常遭水火、兵燹等厄运,易受毁散失。王回在《列女传》序中,并未提及亲见列女图;蔡骥在《列女传》跋中,也未言及列女图。由此可知,汉代的列女图至宋代盖已佚亡。至于南宋建安余氏所刻的《古列女传》,上图下文,插图多至123幅[7](P228),并云顾恺之绘画,实是坊刻业主惯用的招揽生意、吸引读者的一种营销手段。此“晋图”实为宋画,应是题中固有之义。加之古代雕版图画成本较高,工艺繁复,一些私家刻印者或因资金所限,或出于疑古等原因,往往省略《列女传》的插图,使《列女传》成为纯文字刻本。例如,黄鲁曾刊本《列女传》就没有图画。又如,顾广圻认为建安余氏的《列女传》图画非顾恺之所画,而为余氏所补绘,故在付梓时,未将图画摹刻刊行,顾氏小读书堆本《列女传》由此便没有了插图。
(三)韩国、日本刻印的《列女传》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早在东晋时期,汉文图书已在朝鲜流通。至宋代,儒家经典已在朝鲜半岛广泛流传。明朝后期,中国古典小说大量传入朝鲜,其中就有《列女传》。出于教化的目的,《列女传》在韩国不仅以中文直接翻刻,而且早在1543年还被翻译成韩文予以刊行,并有多次再版记录[14]。宋元明清时期,大量中国图书输入日本。据粗略统计,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约占中国古籍总数的70%[15]。这些古籍在日本加以翻刻,以广流布,被称为和刻本,《列女传》位列其中。例如,胡文焕刊刻的《列女传》传到日本后,于日本承应二年(1653年)翻刻为《新刻古列女传》。现在,日本多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均收藏此种翻刻胡文焕文会堂本《列女传》[12]。
(四)类书、旧注中的《列女传》
《列女传》进入流通领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发生内容文字的缺损,这在抄本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为之所作的注释、颂、赞、图等,甚至今已亡佚。不过,借助于类书、旧注中的称引,《列女传》的部分篇目内容得以重现。虽是吉光片羽,但愈显弥足珍贵,对《列女传》的整理完善多有裨益。《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多摘录了《列女传》的内容。《世说新语》《水经》《文选》《史记》等图书的名家注解中,亦多次称引《列女传》。现仅就类书与《史记》注释中所涉的《列女传》,简而述之。隋末唐初的虞世南在隋代任秘书郎时抄辑而成《北堂书钞》。该书多处引用《列女传》,版本有明代万历年间陈禹谟校刊的《补注北堂书钞》等。唐高祖时,欧阳询等人编纂了《艺文类聚》。该书征引典籍有1431种,其中就有《列女传》。《艺文类聚》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刻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初学记》是开元年间唐玄宗为便于诸皇子写作诗文时查找典故辞藻,命徐坚等人编纂的。该书有十多处引注于《列女传》。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无锡安国的桂坡馆刻本,较通行的为乾隆时期的古香斋袖珍本。北宋初年,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御览》。该书征引典籍多达2579种,多处称引《列女传》。《太平御览》的版本很多,宋代刻本较为流行。现存《史记》旧注有三家,即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旧注对《列女传》多有称引。现存三家注最早的版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
(五)《列女传》研究著述的刻印
清代以前对《列女传》校勘注释的著作,现今已经亡佚。清代考据学甚盛,古籍的校注备受关注。反映在《列女传》的校勘、注释、疏解等方面,则有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梁端的《列女传校注》、萧道管的《列女传集解》等研究著述的相继面世。
清朝嘉庆年间山东栖霞郝氏家刻《列女传补注》八卷、《叙录》一卷、《校正》一卷。前两部分为王照圆所撰,《校正》一卷系臧庸、王念孙、王引之、马瑞辰等人的研究成果。校勘者为郝懿行的儿子郝文虎与女儿郝文则,后又经郝懿行的表弟海阳人赵铭彝的覆校[16]。现有嘉庆十七年(1812年)郝氏晒书堂刻本。梁端的《列女传校注》八卷,有道光十一年(1831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后收入振绮堂丛书。萧道管好考据之学,著有《列女传集解》十卷,有光绪年间刻本,后收入《石遗室丛书》。
二、《列女传》的传播
(一)多样化的传播路径
在我国传统社会,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妇女在稳定社会秩序、调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于是,出于这种政治意图的考量,《列女传》便成为官府刻印的必选图书。一方面,官府可直接出面,以充裕的资金作为保障,从底本、校勘、刻印、装帧等方面,确保《列女传》的刻印质量;另一方面,官府又可依托非同寻常的行政权力,以非市场化的营销形式,强行将官刻本的《列女传》颁行天下。例如,明朝永乐皇帝即是以此使《古今列女传》印本在城镇与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的全国范围内流传。
私家刻本的刊印群体往往由官吏、地主、商人等组成,其目的或是为宣传其著述,或是为传布其喜好的图书古籍。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人、好友、门生等又多参与图书的校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校勘质量。因此,私家刻印的图书大多底本好、校印精、纸墨优良。不过,由于缺少了谋利的动力,私家所刻图书的流布范围通常有限。而一些专业研究成果的深奥难懂,也制约了其向民众的普及。为扩大其影响力与传播力,一些私家刻本的《列女传》也借助于官方的力量进行传播。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王照圆的《列女传补注》被官员进呈御览。上谕“博涉经史,疏解精严”等首肯评语[17],的确为当时学者所称誉的这部《列女传》研究著述的传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坊刻业主刻印的《列女传》,主要通过图书市场进行销售、传播。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两代,在图书刻印业较发达地区、主要城市与交通枢纽,通常都有图书市场的存在[6]。例如,明代的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已成为全国图市重要的集散地。而至清代中前期,通俗图书销售已经拓展至乡间村落[18]。如此方便的图书销售网络,使长途贩运图书成为可能,极利于《列女传》的传播。例如,前述清代福建四堡的马、邹两姓家族,总共近700人有在外销售图书的经历,遍及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各省。在西达重庆,南至海南岛,北到曲阜的更远地区,也有四堡书商的足迹[7](P318),其刻印的《列女传》便随之行销各地。
(二)广袤的传播范围
宋元明清时期刻印的《列女传》,传播地域很广,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远播国外。就国内而言,主要得益于便利的交通,统一的全国性图书市场的日趋完备与成熟,以及遍布于城乡各处的图书销售网络。相关情况,之前已有叙述,故在此不再赘言。现仅就《列女传》的域外传播,简而述之。
清代以前,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各国中,不仅是经济大国、强国,而且文化发达昌盛,处于先进国家之列。其高度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甚为外国尤其是亚洲邻国所羡慕。外国把输入中国图书作为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而中国政府则把图书输出当作其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列女传》由此便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当时,《列女传》传入外国主要有5种途径:中国政府赐赠;外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中国使臣赐予外国;外国商人从中国购买;中国商人带入外国。例如,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暹罗(今泰国)有使臣来访中国,明朝政府便“赐赉有加,并赐《列女传》百册”。同年九月,明朝政府的礼部受命装印《列女传》一万本,以“给赐诸番”[19]。
(三)多重性的传播效果
伴随着宋元明清时期《列女传》多种刻印本的出现,庞大的刊印数量,加之多样而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使其所宣扬的价值观等,在对世人特别是妇女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其多重传播效果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列女传》的刻印与传播,在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推进文化进步与学术发展,保存古代文献,以及助推汉文化圈形成与汉学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与《列女传》的传播如影随形,《列女传》的母仪、贞顺、节义三传中的女性形象,已为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各阶层所普遍认同,熏染成风,可以促进家庭的和谐。而其宣扬的伦理道德因契合“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得到统治者的肯定与提倡,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作用较显著。另外,《列女传》倡导妇女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安心于生产劳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利于经济的发展。此外,随着一些相关《列女传》图书逐渐走向平民化与通俗化,给了下层劳动妇女读书识字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列女传》的研究成果,如王照圆《列女传补注》的相继刊行,则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与演进。《列女传》传至宋代,原八卷本渐佚。得益于宋人的整理与刻印,八卷本的《列女传》才大行其道。这已成为保存古代文献的成功范例。最后,汉文化在向国外传播的历史进程中,宋元明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大量《列女传》刻印本向国外输出,使中国文化远播域外,对输入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颇利于以汉文为中心的东亚、东北亚文化圈的形成,也对国外的汉学研究趋于成熟有所助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宋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列女传》的刻印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强化皇权统治与压迫妇女的工具,消极作用不可低估。其倡导的节烈等理念,固化为禁锢妇女思想行为的习惯势力,是与追求人身自由、个性解放等近代社会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诸如此类的封建旧礼教的陈词滥调,常与《列女传》的传播相伴而行。
总之,《列女传》的刻印与传播互为依托和因果。一方面,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多种《列女传》版本的刻印,为其传播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与路径;另一方面,传播渠道的多元与畅达,又为《列女传》的刻印提供了出路。这种良性互动效果明显,使《列女传》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对民众,特别是对妇女的生活、行为、思维与价值理念等的切实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超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应是不争之事实。
[ 1 ]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 左康华.《列女传》的传播机制及其当代启示[J].现代哲学,2013,(3):112.
[ 3 ] 吴敏霞.《列女传》的编纂和流传[J].人文杂志,1988,(3):124.
[ 4 ]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 ]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362.
[ 6 ] 张弘,韩帅.明清时期坊刻图书业经营之道探析[J].东岳论丛,2014,(11):5-9.
[ 7 ] 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8 ] 张涛.刘向《列女传》的版本问题[J].文献,1989,(3):250.
[ 9 ] 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30.
[10] 张涛.《列女传》注释·前言[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1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438.
[12] 刘赛.明代官、私刊行刘向《列女传》考述[J].明清小说研究,2008,(4):198-200.
[13] 叶德辉.书林清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50.
[14] 刘僖俊.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研究[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0.
[15] 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90.
[16] 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758.
[17] 郭蓁.清代女诗人的成长与家庭教育[J].东岳论丛,2008,(5):30.
[18] 向敏.清代中前期图书市场探析[J].出版科学,2011,(6):98.
[19] 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74-1475.
(责任编辑 鲁玉玲)
On the Different Versions and Spreading ofBiographiesofExemplaryWomen
JIN Li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versions ofBiographiesofExemplaryWomenwere prosperous. From the subject of engraving, there ar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ponsors; and from the content and illustrations, there are illustrated books, plain text and added or deleted books, and so on; from the countries that produce such books, we have China, South Korea, Japan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from the existing forms, there are printed booklet, collections and excerpts; in addition, some research works ofBiographiesofExemplaryWomenare published, such as annotations and variorum editions, etc. The diverse spreading paths, the vast scope it reached and the multiple effects all enhanced its publicity, making it not only popular in China, but well-known abroad. The publishing and spreading ofBiographiesofExemplaryWomenobviously benefit each other as mutual cause and effect, whic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people’s life at that time.
BiographiesofExemplaryWomen; version; engraving; communication; books; publishing industry
2017-06-30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古代图书市场与儒家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1BLSJ01)
勒力(1968—),女,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献学、出版文化研究。
G255
A
1008-6838(2017)05-00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