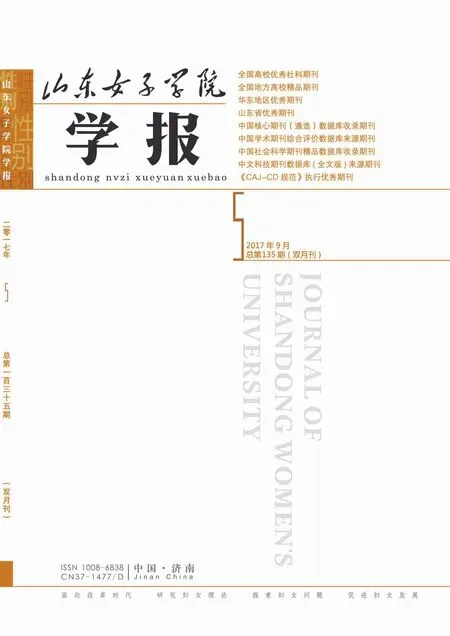论新世纪拐卖妇女叙事
刘传霞
(济南大学,山东济南 250022)
·女性文学研究·
论新世纪拐卖妇女叙事
刘传霞
(济南大学,山东济南 250022)
新世纪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拐卖妇女叙事,向陶醉在现代化想象中的当代人暴露了一个底层百姓的生存世界,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的复杂性,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关于拐卖妇女犯罪的一些刻板印象,既让人们看到与现代化相伴的金钱崇拜以及古老的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又让人们目睹了这一犯罪的受害者们的深重苦难、痛苦挣扎,发现了底层百姓在与苦难命运抗争中所闪现出的人性之光,感受到了他们的坚忍与大爱。对新世纪被拐卖妇女叙事而言,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艺术家们怎么进入才有可能更接近真实的确是一个问题,同时,如何通过叙事改变人们的理念和认知,消除拐卖妇女犯罪,为被拐卖妇女的人生出路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拐卖妇女;新世纪;现代化
买卖妇女是人类的古老罪恶之一,从古到今、从中到西,这种罪恶交易都在或显或隐地发生、进行着。在女性没有获得人权的时代,买卖妇女是合法的。妇女没有独立的人身地位,从属于父家和夫家,这两个家庭的掌权者以及其他掌握女性生存权的人,都可以公开地买卖妇女。进入主张平等、人权的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制定法规条律禁止买卖人口,严厉打击人口贩卖,买卖妇女成为非法犯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从法律政策上保障妇女权益,严厉打击买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并且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使买卖妇女这一古老罪恶在中国大陆基本消失。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启动,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开始浮出水面,19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一度猖狂,甚至出现职业化、集团化的倾向,买卖妇女犯罪活动发生地也由四川、云南、陕西等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扩展到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买卖妇女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活动,与其他刑事犯罪不一样,它侵害的不仅是财产和身体,更是人的精神和心理,它严重地践踏人的尊严,击碎女性的主体性,给女性和社会都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动摇。因为有国家政策法规的保障,当代中国妇女不再是夫家的财产和商品,妇女获得一定自主权,所以当代被买卖的妇女绝大部分都是被拐卖的。有研究妇女问题的社会学学者将“被拐卖”解释为“人或/和物被骗后又被具有出卖意图的欺骗者以获利为目的进行出售”[1]。在中国大陆被拐卖的妇女大多被人贩子贩卖到农村,被迫与当地男人缔结婚姻,作为传宗接代或发泄欲望的工具。文学是人类认识现实、体验生活的场域,也是人类干预现实、创造生活的场域。在新世纪伊始,具有强烈人文情怀的当代作家就将目光投向拐卖妇女这一严酷的社会问题,创作了一批书写涉及拐卖妇女犯罪的作品,如小说类有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2000年)、星竹的《中西部》(2000年)、刘增元的《断侉子》(2000年)、鲁人的《买媳妇》(2001年)、胡学文的《飞翔的女人》(2002年)、王安忆的《姊妹行》(2003年)、葛水平的《喊山》(2003年)、蒋韵的《北方丽人》(2003年)、李锐的《青石碾》(2005年)、阿来的《自我拐卖的卓玛》(2007年)等;影视类有沙碧红导演的电视剧《又见花儿开》(2003年)、《明天我不是羔羊》(2006年)、李扬导演的电影《盲山》(2007年)、胡明钢导演的《嫁给大山的女人》(2009年)等。这些作品涉及这一犯罪行为的方方面面,通过具象化的故事和形象,创作者们一方面对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拐卖妇女犯罪高发的原因进行探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问题进行追问,对中国传统性别文化观进行质疑,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勘探;另一方面关注被拐卖妇女、买入妇女的男性及家庭命运,通过他们多种多样的遭遇写出这一犯罪活动的受害者的身心创痛以及无奈、认命、抗争、救赎等复杂心理。
一、城市幻象与妇女被拐卖
中国大陆拐卖妇女犯罪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且被拐卖妇女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陕西等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偏僻乡村。其实,中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在计划经济和政治文化大一统时代这种差异性被遮蔽。在与农业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道德教化和现代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下,处于闭塞状态的贫困乡村,处于相对平稳之中;乡民在物质困乏之中大都保持善良平和之心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都市化和商业化以及现代传媒业的发展,乡村的闭塞与“宁静”被打破,城乡之间的差异与距离日益凸显。韩少功在解读中国城市爆炸原因时指出:“九十年代以后视听传媒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包括电视‘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信息闭塞的状况得以缓解,也使很多乡下人对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别和文明差别耳闻目睹,有了突如其来的强烈感受,难免巨大的心理震荡,难免急迫的变化要求。”[2]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现代传媒都在制造城市生活神话。乡村与城市原本是一个并置的空间概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性话语叙述中变成了先后的时间概念,城市成为现代文明的符码,先进、自由、富裕、五光十色、充满机会,而乡村成为愚昧文化的代码,落后、封闭、贫穷、单调沉闷、没有出路。乡村与城市的差异被叙述为文明与蒙昧冲突,逃离乡村奔赴城市意味着挣脱愚昧奔向文明。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快速发展给乡民进入城市提供了机会,进城打工的确也给乡民带来物质生活上的显在改变。在这种话语鼓动与现实诱惑之下,离开乡土成为心怀梦想的青年人的自觉追求与行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离乡进城不仅是男性的追求,也是期冀改变命运的女性的选择。一方面,由于城市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女性需求量大,女性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在乡土女性不承担自我家族繁衍与光宗耀祖的责任时,女性更容易离开乡土,所以在中国离乡进城大军中青年女性占据很大的比例。
巧巧(《谁家有女初长成》)、红叶(《断侉子》)、银鱼(《北方丽人》)、杜鹃(《又见花儿开》)、石秋果(《明天我不是羔羊》)等单纯的青年女子都是怀着到城市开阔眼界、改变命运、过上新生活的梦想,被人贩子以带她们到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打工的名义被拐卖到更加贫困闭塞的山村而跌入黑暗之中。这些被拐卖的青年女子都来自贫困的山区,摆脱贫困、改变受苦受穷的生活是她们逃离乡土的重要理由,但绝不是唯一的理由。她们的行为里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追求,厌倦日渐凋敝的乡村生活,渴望见识外面的世界,追求流光溢彩的生活也是从乡村出走的原因。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追求理想并敢于付诸行动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标识。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批判或指责巧巧、银鱼们这些生活在大山皱褶里的女性走出大山看世界的愿望和行动,况且由于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规训,身处被大山怀抱或者围困的乡村的女性,其精神、身体、心理都受到相当大的束缚,其生存空间极其逼仄狭小。问题是中国社会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城市化为目标的现代性话语,严重地割裂了乡村与城市,造成城乡间的新对立,而现代媒介构建的城市幻象又制造了乡村女性对城市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片面的认知。这种对城市与乡村的偏执化、刻板化认知不仅增加了乡村女性被拐卖的风险,而且还严重扭曲、异化了人性。为了实现城市梦,这些单纯的青年女子往往会孤注一掷,放弃每个人原本应有的羞耻感与道德感甚至生命。在被拐卖的真相暴露之前,巧巧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怎样能到深圳,所以当人贩子在路途上骚扰她时,她没有发出反抗之声,而是质问“哪天到深圳”。李锐的《青石碾》中那个被拐卖到陕西偏僻山村的四川妇女“马翠花”原来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郑三妹”,正是渴望成为城市人的身份欲望让她走向犯罪的道路,成为在她家乡拐骗妇女、贩卖人口集团的主犯之一。
二、金钱崇拜与拐卖妇女犯罪
金钱最初是人类为方便交易而创造的一种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或符号,以后渐渐“具有价值表现、价值度量、交易中介、价值贮藏等的职能。这种职能源自于交易世界的认同”[3]。金钱古已有之,但是金钱被当作宗教一样来崇拜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使金钱职能和功用发生了变化。“在前现代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就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4]西方现代社会尤其美国社会的发展史表明,合理或有度的金钱崇拜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它会刺激个人、家庭、企业、团体等为了自身更好、更高地发展而发愤图强,从而带来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富裕强大。但是,“当个人金钱崇拜不合理时,狂热崇拜或过界崇拜下的行为,就一定会对外部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人人都想侵害他人的利益,并且事实上人人也都在谋求侵害他人的利益,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对立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化”[3]。
当代中国金钱崇拜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启动以后。在“文革”时期,每个人都会或自觉或被迫地交出个人的权力与利益,国家集体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个人的欲望都被压抑到最小化。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随着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启动,不仅个人欲望表达与获取都具有了合法性,而且对金钱、财富的追求还拥有了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获得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的嘉奖与鼓励。对金钱财富的追逐使中国社会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不仅部分人、阶层获取了财富,而且国家社会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随着政治权力对个体管控的日益松动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钱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大,金钱越来越深地参与到了个人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建构之中,而且成为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金钱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物质生活,还是个人的社会身份。金钱崇拜逐渐成为一部分人的唯一人生目标。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金钱崇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对从极端政治专制时代走出转而进入现代化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不仅因为缺失宗教文化的规约,而且传统诚信、友善的道德价值观被击碎,现代平等、人权从来都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因而,金钱的作用被无限放大,金钱崇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远大于西方现代国家。“以金钱为标准的等级形成,并且差别越拉越大,阶级、阶层对立和阶级、阶层对立意识形态形成,社会因为金钱的狂热追求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磨擦和斗争,并且还酿造出了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大量悲剧。”[3]在当代中国,这种被金钱崇拜所鼓荡的极端事件、犯罪更加触目惊心。
狂热的金钱崇拜扭曲人性,将人完全物化。在金钱崇拜的控制之下,人们不仅敢于不断地突破人类在文明社会形成的被人们共同认可的道德底线,把人情、人伦、诚信、友善等人类道德底线规范置之度外,而且不惜触犯法律法规。拐卖妇女这一违背人性、违背现代文明的犯罪之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死灰复燃与转型社会流行的金钱崇拜有关。在这一时期拐卖妇女已经不是个别犯罪,而是一个重要的犯罪类型。也许初始的犯罪者是个人的偶然性行为,后来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拐卖妇女犯罪已呈现组织化、家族化、集团化。从事妇女买卖的人男女老少、各个阶层都有,他们完全被金钱所控制,不仅将受害的妇女当成没有灵魂的物化商品,而且自身也变成没有人性的金钱奴隶,乡情、友情,甚至亲情等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都被金钱欲望所吞噬。
人贩子不仅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而且许多还是有乡邻亲戚关系的熟人,更令人诧异的是还有遭遇过惨痛被拐卖灾难的妇女。曾娘(《谁家有女初长成》)是巧巧表舅的远亲,就是她以招工的名义,组织人把自己家乡的姊妹们一批一批地倒卖给其他人贩子,从中牟利;白彩馨(《断侉子》)当年也是被人以招工的名义卖到山西山区,可是她在经过买家摧残之后不仅认命,而且开始从事拐卖妇女的营生,不断地把她的乡亲拐卖到这山区,甚至她把自己的远方亲戚17岁的初中生党红叶拐卖到山村,使其遭受非人般的摧残与蹂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由高一功导演、赵冬苓编剧的电视剧《满天星》里的周慧,这个美丽的女子在经历两次被拐卖之后,最后自己做起贩人勾当,把自己从一个被他人买卖的受害者赵巧萍变成买卖他人的施害者周慧,而她长大成人后的儿子在遭受情感挫折后也加入到人贩子的行列。当然,被拐卖妇女由受害者转身而为施害者人贩子,这其中不排除被打入黑暗牢笼之后女性对社会的报复与反抗,但是能够将这行动付诸实施也是源于对金钱崇拜的信服。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被拐卖的女性都是无知、见世面少的,因而盲动、轻信,所以容易遭遇拐卖。新世纪的被拐卖妇女叙事打碎了人们的这一刻板印象。如果说巧巧、李玉英(《中西部》)、哑巴红霞(《喊山》)被拐卖的部分原因是她们没有文化知识,缺少应有的判断力,在被拐卖的过程中丧失了一次次的逃走机会的话,那么其他几位女性却并非如此。党红叶、分田(《姊妹行》)、杜鹃、石秋果、周慧等都是接受过中等教育,具有自觉、理性追求、聪明伶俐的女性,白雪梅(《盲山》)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当代大学生。麦子(《飞翔的女人》)一个为寻找被拐卖女儿,多年走南闯北与各色人打过交道的坚韧女人,在寻女的过程中同样遭遇被拐卖,甚至连郑三妹、周慧这些精明的做过人贩子的妇女也没能逃脱被拐卖的命运。郑三妹在被通缉的路上被自己的同乡拐卖到山西;在从事了多年贩卖人口的罪恶买卖之后,周慧为了救儿子又被与自己合伙做买卖的同伴卖掉。随着买卖妇女犯罪的猖狂,被金钱利益所驱使,买卖妇女犯罪的发生形式不仅是拐卖,还有更加原始野蛮的掠劫抢夺。鲁人的《买媳妇》一开始就把这种惨无人道的买卖妇女交易展现在人们面前:“人贩子总共带来了五位女子,为了避免买货人挑肥拣瘦。五位女子全装在了麻袋内,被系好口,就像一袋袋粮食那样,堆放在房间里的一角。五位分别交了两千元钱的男子,在人贩子的带领下,各自挑选了一只麻袋。”[5]四川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玉棉就是在傍晚归家的途中被人贩子掠走装进麻袋之中待售的女人之一。在《谁家有女初长成》中,边防站站长、刚从军校走出的金鉴曾有两段同一腔调的话语,一段是当他听到巧巧编造自己辍学的生活与经历时对巧巧发出的慷慨激昂的说教:“你们先是拒绝受教育,选择无知,无知使你们损害自己的长远利益,长远的利益中包括你们受教育的权益,包括你们进步、文明的物质条件,你们把这些权益和条件毁掉了,走向进一步的无知愚昧——越是愚昧越是无法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越是没有教育越是会做出偷伐山林这样无知愚蠢的行为!”另一段是得知巧巧的真实身份与经历后,违背众人的意愿,坚持将巧巧送交司法机关时的自我辩护:“是她从拒绝受教育,因而变得愚昧、虚荣、轻信,是她的无知送她去任人宰割,送她去被人害,最终害人,最终送她去死的。”[6]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持有这种论调的人很多,尤其在以悲天悯人自居的知识分子之中。在物质至上、金钱崇拜的时代,面对着巧巧这些遭遇被买卖这一摧毁人性罹难的妇女,这种包含着人文情怀的论调既是空白无力、高高在上的,也是不道德、反人性的。
三、传统性别文化观念与被拐卖妇女的命运
买卖妇女是一种残酷、非人道的罪恶,人贩子为了控制、驯服被拐卖的妇女,在被拐卖的路途中往往就恐吓威胁、殴打辱骂她们,甚至强暴蹂躏她们,有的更因为逃跑失败被殴打致死、致残。新时期的被拐卖妇女叙事对此作了一些揭露和批判。鲁人的《买媳妇》中的玉棉“自四川到山东,这一道她在人贩子的挟持下,挨过许多次打,也受过许多次污辱[5]。《断侉子》中的党红叶因为反抗,被人贩子白彩馨丈夫殴打并强暴。如果说人贩子因为利益驱动摧残被拐卖妇女,那么,“买媳妇”的男性及其家庭、乡民,甚至党政干部、有过同样凄惨经历的妇女,这些并非凶恶之人为什么也加入对被拐妇女的摧残与迫害的行列,成为施害者或帮凶呢?
在人类发展史中有相当长的时期男性占据霸权与主体地位,妇女处于屈从客体地位,妇女被当作家庭私有财产被男人掠夺、霸占、交换、抛弃。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盖尔·卢宾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妇女受压迫是在以交换女人为基础的亲属制度下产生的。亲属制度是男人有支配妇女身体之权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内,男人在彼此交换女人之间,用以达成联盟,或者得到地位,又或者作为互惠往来的礼物。”[7]婚姻是这种交换的最基本形式。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建立了男女平等的婚姻观,但是妇女被作为家庭私有财产、作为男性交换的物品的陈腐传统性别文化遗存仍然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现代婚姻中的“彩礼”就是这种文化遗存的表现形式之一,一些贫困山区出现“光棍村”的原因之一就是男性家庭出不起“彩礼”费用,而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山东、浙江、广东频繁发生从云南、四川等贫困山区“买媳妇”的事件也是基于此,这些地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当地解决婚姻问题的男性及家庭选择花较少的钱从贫困山区“买媳妇”。
既然被拐卖的妇女是男性及其家庭花钱买来的商品,那么,这些妇女就被视为男性家庭的私有财产,他们就获得了对妇女的绝对掌控权、支配权,而这些妇女也就丧失了一切人身权利和自由。这种理念不仅被男权文化既得利益者——乡村的一些男性所接受,也被男权文化受害者——部分女性内化,甚至接受了一定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青年和代表国家政府的乡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也自觉遵从或无奈接受。正是这种传统性别观念的存在,使得平时善良质朴的乡民会显示出“狰狞”面目,变成没有人性的凶手、打手、帮凶;也是这种观念导致妇女一旦被拐卖到乡村就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逃脱,整个乡村各个阶层的各种力量就会构筑一个严密的天罗地网共同监视、管控被拐妇女,制造着、观看着、鉴赏着被拐妇女的人生悲剧。
《断侉子》里的党红叶、金枝女被拐卖到乡村后,都遭遇过被男性买家转卖和残酷毒打的痛楚,乡民和乡村干部对违法人口买卖和对妇女非人道的摧残不仅不加阻拦反对,反而认为合理合情,加以袒护、鼓励、怂恿。党红叶的“嫂子”当年被迫嫁给党红叶“丈夫”的哥哥,曾经作过激烈反抗、遭受过非常惨烈的毒打,现在却毫无怜悯与同情之心,成了囚禁党红叶的严厉看管者;身为村长的赵扛印认为,人贩子解决了他们村男性打光棍的问题,不仅为村里猖獗的妇女买卖做挡箭牌,而且鼓励村民以暴力方式来驯服试图逃跑的女性;身负保证社会治安、打击人口买卖的派出所熊所长因为金钱利益放任拐卖妇女犯罪在当地泛滥。《中西部》里被拐卖的李玉英被强暴的一幕实在令人咂舌,村里一群妇女帮忙、教唆买媳妇者石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人的观看中完成了对她的强暴,强暴完成之后竟然是全村人杯盏交错地庆祝。在《盲山》里黄德贵老实懦弱的父母置白雪梅绝望、恐惧、羞耻、身心痛楚于不顾,竟然帮助儿子按住白雪梅,让儿子强暴了她;乡村干部漠视白雪梅的求助;邮递员把白雪梅求助的信件交给黄家;司机因为白雪梅交不起车费就拒绝其搭车并出卖她;黄德成——黄德贵的表弟,一个温文尔雅的乡村教师,他同情白雪梅并救助过割腕自杀的她,但是也是他不敢、不愿帮助白雪梅逃走,在白雪梅身上满足了他的情欲之后选择了躲避;当公安机关前来解救被拐妇女之时,全村村民出动,用武力阻拦解救行动。
其实这种男主导/女屈从的性别文化观以及中国社会极端重视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不仅伤害女性,也伤害了那些性情温和的男性。正是这种性别文化观让这些男性倍受歧视,承受极大心理压力,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大和男子气概,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伤害被拐卖妇女的行为,黄德贵、二有(《断侉子》)、石天等男性之所以要“买媳妇”并不是为了满足性欲,而是为了完成父母强加给他们的传宗接代的家族任务;面对买来的“媳妇”一开始他们并不想用用暴力征服,但是,他们对女性的退让却遭到全村人的耻笑,并面临在村里丧失做男人资格的危险。所以,从某些层面来讲,对被困在贫困山区被迫参与拐卖妇女的男性来说,他们的人生也是一场悲剧。
在经过最初的抗争之后,被拐卖的妇女的命运大致两种,一种是认命,接受现状,留在被拐卖的家庭,甚至在被解救后又回到买入的家庭。被拐卖妇女之所以会放弃逃跑、被解救的机会,最终选择留在被拐卖家庭,大致有3种情况:一是相比买入她们的地区,被拐卖妇女的家乡更加贫困,回乡后她们的生活更加辛劳贫苦;二是买入妇女的男性忠厚老实,勤劳能干,对被拐卖的妇女还比较尊重、有些许呵护,那些在家乡备受歧视、冷落的女性在买入的家庭中反而感觉到“温暖”;三是生儿育女后,割舍不下对儿女的牵挂。玉棉被善良的买家兰采和送回贫穷的老家后又选择了归来;在贫困的丈夫家倍受歧视的李玉英对实诚的石家人和当地的生活产生留恋,拒绝被解救;巧巧若不是发现自己不仅要做郭大宏的媳妇,还要做傻子二宏的媳妇,体会到人伦道德底线被突破后,她有可能就选择留在山村做养路工郭大宏的“妻子”了;银鱼生儿育女多年之后,获得回乡探亲的人身自由,但她在探乡之后却又自觉地归来,与丈夫、孩子艰难地生活在贫瘠的异乡。
这些被拐卖妇女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留在流入地与买入自己的男性生活在一起,其背后都是深深的无奈、满满的伤痛。其实,许多女性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一旦遭遇被拐卖,她们就失去了家、失去了家园。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女性的身份焦虑主要是来自社会的道德规训”[8]。在中国乡村甚至城镇针对妇女的单向度贞操观仍然左右人们对女性人生价值的认知,人们关心女性贞操超过她们的生命,将失贞妇女视为可耻、可憎、可鄙的,失贞妇女甚至其家人都会遭到唾弃。妇女被拐卖很难挣脱被强暴的厄运,这种创痛本身必然会带来妇女,尤其是未婚妇女“身体和心理主体性的粉碎性毁灭”,可是,更大的伤害与毁灭来自包括家人、朋友在内的社会对她们的歧视、拒斥、敌视、仇恨。玉棉被兰采和送回贵州老家后,因为“失贞”被任教的学校开除,被丈夫责骂、殴打、抛弃,无处可去的时候她才回到老实厚道的山东人兰采和身边。李玉英被解救回来以后,他的丈夫并没有任何兴奋感,反而唉声叹气、愁眉苦脸,被深深的羞耻感控制,被人耻笑为“窝囊”,当李玉英再次失踪时,他忧虑的不是妻子的生死去向,而是如何从妻子被拐卖事件中追讨钱财。《姊妹行》里水的父母知道女儿被拐卖后拒绝分田要去寻找的提议,以“嫁哪里不是嫁”理由让其自生自灭;同样分田虽然全身而归,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因为怀疑分田已经失去贞操,乡亲、父母、未婚夫等已经将分田从他们的生活中剔除了。
在这种贞操观念和性别文化观念规约之下,“强奸体验和任何创伤性体验一样,是一场永不能结束的事件。它不是一次性发生并结束,而是不断延宕的。在事件发生之后,受害者永远成了一个“被强奸过的女人”,并有可能在任何一个不经意的时刻变成‘二次强奸’的二次受害者。正是因为这种重复性,给受害者带来了比事件本身更具毁灭性的打击。”[9]从主体与心理建构层面来看,这种无形、非暴力的伤害,比遭受拐卖、强暴的伤痛更严重,来自亲人、无辜人的“二次伤害”或者说“二次强奸”会让被拐卖妇女彻底绝望,如果受害的妇女自己也将这种物化女性的“贞节观”内化成自我规训与自我认知,那么,在内外双重精神双重围困之下,被拐妇女原本就脆弱的主体性必然会彻底崩溃。
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与围剿之中,并非所有被拐卖妇女都安于现状,顺从命运。第二种被拐卖妇女拒绝与反抗女性被物化的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在困顿生活、坎坷命运中努力保持生命的尊严,动用各种人生智慧寻求救赎,搭建起女性的自我主体,维护人性的尊严。《飞翔的女人》《姊妹行》《盲山》塑造了一个个“不放弃、不抛弃”,努力自我救赎的被拐妇女形象。
《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一个女儿被拐卖而在寻找女儿过程中自己也遭遇拐卖的普通乡村妇女,在她瘦小而衰弱的躯体内却有强大的内心力量与坚韧的精神,不向现实妥协,不向命运低头,顶住来自家庭、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坚守做人的道德与良知,与人贩子和不作为的公安执法人员斗争,居然依靠一己的力量抓到人贩子,惩罚了邪恶的犯罪者。这个来自社会的最底层的苦难而不幸的妇女,在与苦难与罪恶斗争中获得了生命的超越,成为一个在生命尘埃中飞翔起来的女人。
《姊妹行》是王安忆依据在山东省妇联采访时听来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品书写了两次姊妹行,第一次是中国乡村妇女受难之路,第二次是底层妇女自我主体成长建构之路。分田因为去探望在徐州当兵的未婚夫,与小姐妹水结伴而行却遭遇人贩子,分别被拐卖到到穷乡僻壤给陌生男人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分田保住女性贞洁并逃回到了家乡,可是归来的她却不被家乡人所接纳,在寻求他人、妇联组织等帮助都无果的情况下,分田居然孑身一人沿着被拐卖之路重新行走,成功营救已经为人母的小姊妹水,最终带领水再次主动离开故乡,开启了奔往上海的第二次姊妹行,到包容开放的现代大都市寻求新的人生之路。从被拐卖归来后对自我贞操的无力辩护、寻求他人为自我证明,到勇敢地踏上孤身解救同命运小姊妹之旅,再到决绝地告别家乡,姊妹俩携手奔向大城市,一路走来,分田这个活泼单纯、未经世事的农村青年妇女,从“一个残存父权文化意识、主体意识匮乏的女性”,一步步锻炼成为“一个已经抛弃传统性别规范,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具有明晰自我意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人”[10]。
电影《盲山》的主要故事线索就是决不放弃的“出逃”。大学生白雪梅为了帮助家里还清债务急于寻找工作而被拐卖到狭隘封闭的山村,经历了被强暴、被毒打、被迫怀孕生子、被欺骗等的一系列身心摧残,她却从未动摇过逃出去的意念。因为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不认同山村中所流行的不平等的女性文化规范,不认命也不认输,她就像一个击不倒的斗士,一次次失败之后总结经验调整策略再次投入战斗。最后,终于在她帮助过、教育过的天真孩童的帮助下,被公安机关解救出“牢狱”。在逃出去的最后关头,电影中同样被拐卖来的妇女陈丽因为听到孩子的哭喊声放弃了逃走的机会,而雪梅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身后追跑着的婆婆和襁褓里的孩子,毅然向前奔去。对电影的这一结局有人批评“这样的弃子行为,很难说是一种文明”[11],其实这种批评过于抽象而高调,在这种极端的特殊境遇之下,苛责女性母爱缺失,无疑是对女性自我生命、自我主体的剥夺。
新世纪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拐卖妇女叙事,向陶醉在现代化想象的当代人暴露了这样一个黑色的底层百姓的生存世界,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的复杂性,打破了人们头脑中关于拐卖妇女犯罪的一些刻板印象,既让人们正视与现代经济相伴的金钱崇拜以及古老的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对人性的扭曲,又让人们目睹了拐卖妇女犯罪的受害者们(被拐卖妇女本身及家庭、买媳妇的男性及家庭)的深重苦难与痛苦挣扎,发现了这些底层百姓在与苦难命运抗争中闪现出的人性之光,感受到他们身上所隐藏的坚韧与大爱。
当然,在具体叙述中有的文本还存在着将拐卖妇女现象简单化处理的问题,如《中西部》《盲井》把造成这一悲剧的成因归结为村民的贫穷与愚昧;有的潜隐着俯视式的精英主义视角,如《谁家有女初养成》;有的作品流露出传统男权文化意识,如《断侉子》将女性的“轻佻”叙述为农村妇女遭遇拐卖的重要原因,把所有抗争妇女的人生结局都安排为凄惨的悲剧;有的作品为被拐妇女设计的大团圆结局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被拐妇女的人生悲剧,如《买媳妇》挖掘了乡村的温情,书写被迫加入买媳妇行列的男性的无奈与善良,但是,由于作品缺乏对被拐女性的复杂心理抒写以及对这一大团圆结局所隐含问题的探究,反而强化了乡村女性的宿命感,冲淡了对拐卖妇女犯罪的批判力度。根据“感动河北人物”郜艳敏的人生经历而改编的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在再现与叙述被拐卖妇女山菊的命运经历之时,有意淡化了被拐卖遭遇对女性的巨大伤害,回避了拐卖妇女这一犯罪所折射出的各种社会问题,突出了女性对苦难的忍耐与承受、对他人的宽容与感恩、对各种责任的担当,彰显了女性的伟大与崇高。其实,这种对社会阴暗面、社会矛盾有选择性的忽视与沉默,是对拐卖妇女犯罪的纵容;而对受伤害女性诗意化、道德化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对女性的道德绑架和规训,这是对女性的另一种压榨和索取。“面对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艺术家们怎么进入才有可能更接近真实?”[12]对被拐卖妇女叙事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同时,我们的艺术家们如何通过叙事改变人们的理念和认知,消除拐卖妇女犯罪、为被拐卖妇女的人生出路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 1 ] 王金玲.质性研究中情景脉络的理解和诠释[J].云南大学学报,2006,(6):19-23.
[ 2 ] 韩少功.暗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56.
[ 3 ] 陈彩虹.现代社会中的金钱崇拜[J].文景,2007,(12):4-5.
[ 4 ]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刘小枫,编.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5.
[ 5 ] 鲁人.买媳妇[J].北京文学,2001,(4):73-77.
[ 6 ] 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J].当代,2000,(4):4-49.
[ 7 ] [美]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7.
[ 8 ] 徐先智,范伟.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J].湘潭大学学报,2014,(3):107-110.
[ 9 ] 谢琼.书写强奸:被转移的言说[J].南方文坛,2010,(6):67-72.[10] 刘传霞.论中国底层妇女的主体性与救赎之路[J].文艺争鸣,2014,(7):108-112.
[11] 李智伟.生命不能承受之重[J].飞天,2009,(10):26-27.[12] 李云雷,盘索.《盲山》、性与“文明”的链条[J].黄河文学,2008,(4):119-120.
(责任编辑 赵莉萍)
On Narratives about Trafficking of Women in the New Century
LIU Chuan-xia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In the new century, narratives about women trafficking created by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in the new century exposes the livelihood of the lowest class to modern imagination, explor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rime, and breaks people’s stereotypes about women trafficking. Such narratives not only let people see the distorted human nature caused by money worship and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gender culture, but also let people witness the deep suffering and struggling of the victims, the grandeur of human nature exposed in those suffering and struggling, and their perseverance and profound love. In the face of complex social problems in the new century, it is indeed a question how artists can enter closer to reality. Meanwhile, for such narratives, it is really a problem for the artists to find the proper way to approach this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 What is also important is how to improve people’s idea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problem through narrative, eliminate this crime, and illuminate the life of trafficked women with more possibilities.
trafficking of women; new century; modernization
2017-07-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阈中的十七年女性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6BZW152)
刘传霞(1965—),女,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山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
I206.7
A
1008-6838(2017)05-007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