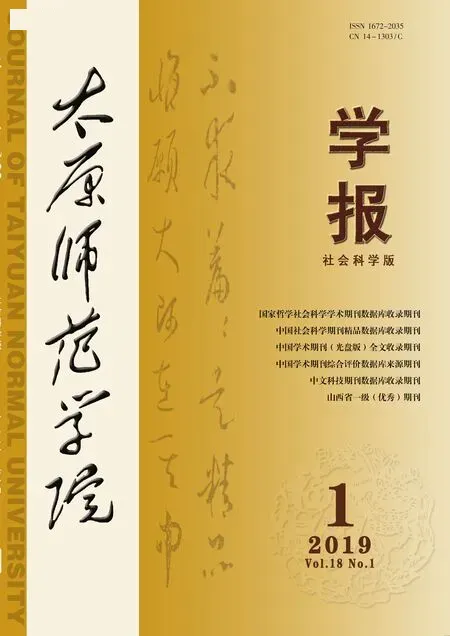论林庚诗歌语言的诗化与主体化理论
(1.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2.长治学院 中文系, 山西 长治 046000)
林庚作为诗人,“一切开始的开始”是在1930年看了源于温庭筠《梦江南》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的诗与画以后。[1]
在《漫话诗选课》中,林庚所期待的诗,是用诗化与主体化的语言为诗歌赋形,疏离我们与我们的熟悉物(语言与生活),同时为双方进行不一样的“交通”制造可能。他说“诗所以不可以谈”“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里的诗,无论新旧,乃是就诗的本质而言,强调诗就是语言的艺术、艺术的语言。其结尾又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们从什么地方认取这一只妙手呢?必在更多的偶然之上,而不是一般现成的概念、辞藻。”[2]189这是林庚一经形成就终生坚持的新诗形赋的两个要素:和生活语言有距离的语言的诗化;作为“妙手”独具者的诗的主体化感觉与形式。
一、语言形赋:“话说不出来”的问题与诗化翻译的出路
博尔赫斯认为诗歌不可以翻译,实际上对林庚来说,翻译首先是在义与言之间的难题,其次才是言与言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诗能不能用语言赋形才是个首要问题。在《问路集·自序》中林庚说:“语言原是建筑在抽象概念之上的,艺术却需要鲜明具体的直接感受;诗歌作为最单纯的语言艺术,除了凭藉语言外又别无长物;换句话说他所唯一凭藉的,乃是他所要求突破的。”[2]2十年后,他在提及“诗化”的概念时又有类似的观点。作为诗人的林庚,一生都在寻找那无法言说的最佳言说方式。有鉴于传统诗因为“一切可说的话都概念化了”而逐渐枯竭,[2]167林庚对新诗的发展,一则聚焦于语言问题,二则聚焦于语言的概念化与感性化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并试图在这一关系中寻求诗的语言对“一般可说的话”的突破。
林庚以为真正的诗“本天成”,诗人不过是“妙手”独具的翻译者,诗人的工作就是为那艺术境界的诗在概念境界中寻找或者创作“感受”而非“抽象的概念”的语言。所以,诗歌创作其实就是不同语言方式之间的语言翻译问题。概念性的语言属于有限世界,感悟性的诗歌属于无限世界,二者之间就是诗人。林庚认为,诗人不创作诗,因为诗是“天成”的;舍去“天成”于心底和星空、草场与车间、高楼与边塞、峰巅与谷底的诗而去“独创”者,类似于在光电时代发明蜡烛。诗人只是“妙手”独具的搬运工,他听命即可,不需要“作”什么。作得越多,搬运来的诗的非诗成分就越多。歌德说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而非反之,艾略特主张自我在作品中的稀释,都是诗的至理。[3]5简单说,诗不是诗人自我的声音,相反,诗人自我是诗的“如是我闻”“如是我见”者。所以,没有“我”的诗才是好诗。但这并不是说诗人可以坐享其成,相反,诗人在写作的时候是很焦虑的,因为他要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写出不能作、不能说的诗来。赋形于诗,绝不是无动于衷的“赋得革命,五言八韵”,而是对无形无限世界的有形有限化,这个过程是常说的客体主体化的一部分,即去主体意识后剩下的那部分——客体主体化往往沦为六经注我的意思,这对诗歌创作而言太粗放、太暴力了,事实上没那么便宜的事。有限世界只能给人以粗糙暴力的所谓快乐/痛苦,无限世界或许只有借助诗歌感受之,诗人就是二者之间的翻译者。所以说,诗人的任务就是将作为音像结构的语言赋形于诗,形成一个有待被激活的自足的符号系统,这就是诗的产生。其实,这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产生”,严格地说,只是诗的语言形式的产生,而非诗的产生。总之,诗人不创作诗,诗人组织象征诗的音像结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焦虑就是语言的焦虑。
林庚的《甘苦》就是对诗人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语言焦虑的喟叹:“当你有一点感受想写出来时,便会觉得一切表现的语言都是不现成的;话说不出来,还得要去找这表现的语言”[2]188。这是刘勰“意翻空而益奇,文征实而难巧”的困惑,是唐人“推敲”时的辛苦,也是鲁迅“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式的中国现代作家的群体焦虑。
林庚以为,诗歌创作的任务既是语言的追寻又是语言的防范。诗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所忘之言,既是诗人对所见之义的翻译,又是诗人抵抗的“言筌”。诗就是从无向有的翻译,作为关键的语言问题弄不好,诗就成了弗罗斯特所说的“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即“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4]110因此,诗成为语言的过程要么是诗被现存语言同化以至消亡、“失掉”的过程,要么就一定是成功打破现状,树立自我,将“刹那的心得”“瞬间的紧张”发现、留住的诗化过程。因此,成功的诗歌语言,不仅仅是诗,更是诗人的艺术手段——对语言施加暴力使之变形、陌生,最终使之成为主客体之间的某种纯粹的符号或者隐喻。[5]7可见诗人的写作,也就是林庚所谓妙手“偶得”的过程,不是诗的生成过程,只是诗的语言形赋,是在诗的无形与有形之间的翻译。
翻译,可以看作是林庚所说的从“无限”向“有限”的转换、交通,甚至是普罗米修斯意义上的偷盗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用语言无限逼近意义的过程,是危险的、辛苦的,甚至是徒劳的。林庚对诗歌语言“翻译”功能有更深刻的认识——诗是语言的艺术,而生活中的语言天生具有一种概念化惰性,诗人的作用就是对生活语言向诗歌语言的翻译,以此来“突破”概念,甚至不惜自我突破,从而长保诗歌语言的新鲜感、生命力。对林庚来说,诗面临的是一个悖论:它所赖以生存的生活语言正是它所要突破的,它所要突破的也正是它所要凭借的。诗歌语言突破生活语言的逻辑性和概念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翻译,或者说翻译只能是“意思”的交通,却很难有效地交通意思之外的形式、韵味、背景文化等难以言传的美学感受,林庚宁愿在不可说、不可译的立场上,把诗歌语言对生活语言的翻译称作“诗化”,这个诗化只在很小的部分指代意思,它主要指的是诗的句式、语法和词汇等不可说、不可译的那部分。[6]243在诗化的过程中,诗人必须同时既是有限意思的翻译者,又是无限的艺术美感的创造者。
Into the rainy street I came
and heard the motors swiftly splash away.
Cascades from the caves like “water from a high mountain”
with my Hangchow umbrella perhaps I’ll saunter forth…
Water has drenched the endless pavement.
Aloft in a lane there is somebody playing the nan-hu,
A tune of abstract long-forgotten sorrow:
“Meng Chiang Nv, to seek her husband,
Has gone to the Great Wall.”
这是学生时代的林庚创作的、被选入《中国现代诗选》的现代诗《沪雨之夜》,也是20世纪30年代最早被翻译成英语的中国现代诗之一。原诗是这样的:
来在沪上的雨夜里
听街上汽车驶过
檐间的雨漏乃如高山流水
打着柄杭州的油伞出去吧
雨水湿了一片柏油路
巷中楼上有人拉南胡
是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
孟姜女寻夫到长城
译者选译林庚的诗而搁置更为著名的胡适的诗,理由是林庚的诗源于一个“更有力的资源”,[7]话虽如此,译作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变形,比如将“雨夜”变作rainy street,“柏油路”变作pavement,首句也作了必要的倒装,但是译作还是无法体现原诗中的客居、愁雨、知音、西湖故事、南北音美学差异、反讽、对话等意蕴,并且原诗的零标点、两节八句结构的形式与传统律诗的呼应也失去了。这些“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或许才是废名称赞林庚此诗是“神品”的所在吧。
诗意的语言赋形不仅仅是生活语言向诗的语言的翻译,西方人翻译中国现代诗如此,中国人翻译传统古诗也如此,遇到的问题和林庚的《沪雨之夜》有异曲同工之妙:
Kwan-kwan go the ospreys,
On the islet in the river.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
Here long,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Waking and sleeping,he sought her.
He sought her and found her not,
And waking and sleeping he thought about her.
Long he thought;oh!long and anxiously.[8]40
这样的翻译还不是林庚所苦恼的诗意的“道成肉身”,即赋无形诗意以有形语言的过程,这不过是诗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而已。即便如此也不难看出,这首英文译诗,或许有《关雎》的一些意思,但诗的韵味失去的实在太多了。在此译诗中,“实”的有了,“虚”的则不足。比如young lady对“女”,已经有了年龄、性格、气质、面目的差异,“淑女”“窈窕淑女”就更难体现在译诗中。至于“求之不得”“悠哉悠哉”等句,是亦实亦虚的字句,一半表意,一半表音,还有叙述者轻快调皮的语气的变化,但在这里都坐实了,此外的汉语诗形、蕴藉、赋比兴的妙用,都失去了。而“关关雎鸠”其实是无法翻译的,因为这四个字作为诗的语言是在能指的意义上成立的,但这里的翻译只能处理所指的一面,能指丢掉了。由此可见,翻译和诗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想通过这首译诗让“外国人”明白《关雎》的魅力,进而明白中国是诗的国度,确实有些不太现实,除非遇到真正的“解味人”。这还都是“有限”之间的翻译,若要将“无限”的感觉翻译成“有限”的诗,林庚那种“话说不出来”的焦虑有多折磨人,估计是“如鱼饮水”,不足为外人道。
这个焦虑问题就是新诗的语言形赋问题,其解决程度,就是对一般语言的诗化程度。而语言的诗化,在林庚看来,与诗人“内在”的主体化及其形式建设紧密相关。
二、主体化形赋:“内在”的感觉与新格律尝试
诗歌语言离开主体的生命感觉就成为空泛的概念排列。前面说,“传统诗泉枯竭,原因是一切可说的话都概念化了”,概念化,就是没有感觉的文字,就是主体缺失,就是胡适批评的“言之无物”。现代新诗要避免重蹈旧诗的覆辙,就得设法突破词的概念化,这就涉及诗化语言与主体经验和私人情绪的关系了。在《谈新诗》中,废名选讲了林庚的四首自由体诗,理由是“自然,真切,最能见作者的性情……写实……都是自己的私事”[9]132。写实、私事、自然,都源于主体生活,都是主体性情的一时兴会,这是偶然的、可遇不可求的。林庚主张,写出好作品的妙手,“必在偶然,而不是概念、辞藻”。不是概念、辞藻,但也不离概念、辞藻。林庚的意思,在强调诗的发生机制,不是存在机制。“偶然”在哪里呢?在独特的、有生活感觉的主体那里。这样的主体存在于文化生活的语言共同体中,但在诗歌创作上依然能够自由地用共同体的语言来言说与众不同的自我“发现”。上文说过,诗人主体在林庚看来如同一位“述而不作”的学者,他的工作就是在诗与非诗之间几乎达到无我程度的客观翻译。“30年代,我在清华读书,一天可以写三四首诗,一拿起笔来诗就往外流。”[10]一个“流”字,尽显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创作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主体能动性的无关轻重,相反,诗人在无与有之间的翻译工作——诗歌的语言形赋的成功程度,取决于林庚主张的对生活语言的诗化水平,也就是诗人对其生活语言的主体化程度。只有在充分主体化的语言里,诗才能存活而不僵死。
对主体化的强调,是“现代”这个词在过去—现在、中国—西方和各种主义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意义上,林庚虽和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有诸多不同,但他们毫无疑问都属于当时的现代诗人。[11]1
据钱理群回忆,1984年,林庚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节课”上,以“什么是诗”开始,举例论证之后,结论是:“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12]。这段话再次说明,林庚关于诗歌主体的功能,从20世纪30年代的“偶得”说到80年代的“发现”说,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观念没有改变。发现,从诗的角度来说,发现周围的世界、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都没有发现本身更重要。诗源于生活,但是同样的生活却因主体的不同“偶得”/“发现”而有了不同的诗。举个例子,在“偶遇”这一“生活”中,徐志摩“发现了”《偶然》,戴望舒却“发现”了《雨巷》。对诗人主体而言,一种生活有多样的“发现”,更别说丰富多彩的生活。生活与诗人,就像波特莱尔的自然与人,“自然是座象征的森林,人从那里走过”,森林/生活用熟识的目光关注人的同时,人也歌唱精神与感觉的激昂。在诗的世界里,客体世界是个充满无限可能、无法本质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对诗人而言,“客观”只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存在,而所“发现”的客体,只是因为发现主体的存在而存在、不同而不同。诗无达诂,因为诗并不诉诸主体的观点,而是诉诸主体的情绪。
林庚常用情绪、感觉来强调主体,在《诗与自由诗》中,他是用英文“mood”“feeling”来表示的。在英语中,有两类表示情感的能指,一种表示外在的、有征兆的,如“affaction”“attachment”;一种表示内在的、难以言传的,如“mood”“feeling”这两个词。巧合的是,同时期的戴望舒也说“诗不是某一个感官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13]。巧合不是偶然的,而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诸位诗人所共同追求的感觉,因此有一种时代和艺术的必然性。这暗示着诗的语言不但要触摸人的情感,更要触摸人内在的、难以言传的、偶然一现甚至连自己也未意识到的那部分心理世界。据冷霜研究,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诗与自由诗》在收入80年代的《问路集》时有很大变动[14],比如:
其实诗与自由诗的不同与其说是形式上的不同,毋宁说是那形式是因其不同的内容而决定的。(1934年《现代》第六卷第一期)
其实诗与自由诗的不同与其说是形式上的不同,毋宁说是更内在的不同。(1984年《问路集》)
由此可见,经过半个世纪,林庚表述上的变化是,将诗(传统诗)和自由诗的区别从“内容”改为“内在”,突出他在同文稍后部分要说的“情调”(mood)或“感觉”(feeling)。这种变动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追求新诗“质与文”的“内在”的统一。这样,在辨析新旧诗区别的基础上,林庚逐渐走向后来的新旧诗歌优势互补的、以“自然诗”为内核的新格律诗的理论和实践上去。这个过程和努力,部分地被废名认可并放大了。[15]林庚对自己貌似“开倒车”的行为很自信,是“古岂能拘牵”,也是“今岂能拘牵”的态度:“戴先生屡次提到我的诗与古诗一样,我其实倒不曾去想到他们的分别。我只知今日有北平而古时无此名,今日有蓝天而古人亦已有之,那么我用北平亦用蓝天,如此而已。”[16]“如此而已”中这个“此”就是无论新旧,只要是“我”的,是“生活”的,就不妨是诗的。
如果说主体性的诗意捕捉是20世纪30年代诗人群体的共同追求的话,那么可以说林庚还有自己的保留地或者说试验田,那就是他一直致力于以诗歌“新格律”的形式来建设主体的差异性诗学存在。[注]二者的共性更为人所关注,即使在林庚自己,也深为批评他的戴望舒的《小曲》诧异(见林庚《从自由诗到九言诗》,《文史哲》1999年第3期)。此外,在创作上,从林庚的诗《朦胧》到戴望舒的诗《印象》,也能看出二人在现代诗方面从感觉到表述的共性而非差异。
在《诗的韵律》中,林庚说一个文学作品有三件基本的东西:情绪、事物和感觉。而感觉的作用就是保证主客体互化的方式与众不同,从而使“亘古不变的情绪”和“似变而其实不变的事物”在普遍性中产生出种种不同,而只有不同才能保证主客体的价值,即感觉,那便是怎样会叫一个情绪落在某一件事物上,或者说怎样会叫一件事物产生了某种情绪的关键。[2]178
可见,主体需要诗,反过来亦然,诗需要主体。
在《唐诗综论》中,林庚说中国诗歌有三个特点:一是抒情,“中国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才成其为诗的国度”。二是和主体统一的语言,“人的创造性正是从捕捉新鲜的感受中锻炼语言的飞跃能力,从语言的飞跃中提高自己的感受能力,总之,一切都统一在新鲜感受的飞跃交织之中”。三是作用,避免概念化,保持永不结冰的主体活力,“是生命的觉醒,可以避免我们成为自己创造物的俘虏”[17]170-171。
真正的诗永远制造主客体之间的疏离感、异质感(除非现实生活也是诗的),以此表现主体那独特的“情调”(mood)和“感觉”(feeling),并为之立此存照,作为主体存在的见证:“(现代诗)要求的是在瞬间的紧张中提取新的激情,将诗意或挫败转化为觉醒的可能,回到经验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粉碎他,重建它”[18]4-5。这里的“瞬间的紧张”和林庚“刹那的心得”意思一样,都是指诗歌写作和阅读过程的独特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什么、做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作用,即林庚说的“避免我们成为自己创造物的俘虏”。
林庚对诗歌语言和功能的看法确实不俗,但他对诗歌形式的具体探讨,即对诗歌主体化理论的宏观思考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在《问路集》和《新诗格律和语言的诗化》中,林庚对新诗的形式探讨最多。这种探讨是必要的,正如广为征引的歌德名句:“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其实,对自由诗,上文提到的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说过一句更贴切的话:“Writing free verse is like playing tennis with the net down”(写自由诗就如同打网球而不用网)。[19]180诗歌,无论古今中外,必须有自己的形式。
林庚对新诗形式的探讨集中在韵律、建行、字组、“半逗律”等方面。对韵律和建行的探讨很必要,林庚、郭沫若都是在传统韵律的启示下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但林庚从1935年开始的新格律实验,不走传统之路,也不效法“三美”理论,而是致力于九言、十言诗等“豆腐块”的建设。这种探索要想成功,有待时间,更有待经典的示范效应。戴望舒所说的“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使诗情变为畸形的;所谓形式,绝非表面上的字的安排”[20]691,可以看作是对林庚“新格律”理念的一个有益的质疑。比如关于《正月》的修改,将“蓝天上静静地风意正徘徊”改为“蓝天上静静地风呀正徘徊”,从阅读习惯上来说并不十分必要。首先,将风意改为风呀,口语化了,大众化了,但诗意淡了。其次,无论九言、十言、十一言,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四言、五言、七言的组合,在诗的意味上,能否超越传统诗的成就,很难说。就这两句诗而言,原句似古而俗,改动句则不新不旧,似民歌非民歌。当然,这种感觉主要源自律诗、五四自由体诗和民歌的传统,或许真如张桃州说的,林庚先生另有宏大的诗歌抱负,非这三个传统所能包括。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唐诗的语言》中,林庚说五七言的形式是东汉至唐四百多年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很多经典。[21]125他的新格律探讨,尤其是对固定字数格式的探讨,如果现在说是失败的尚属武断,而其成功则有待时间,也有待经典和新的接受习惯的产生。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强调,新诗问路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问路的人。请看林庚的这首诗:
店主
我们的世界是个玩具店
店里陈放着各色的物件
我们一样样玩的真快乐
可不知店主他又在哪儿
一天我们要离开这座店
它会让人们真有些留恋
也许那时候认出这店主
他原来每天和我们见面
1992年2月[22]475
这是新诗还是旧诗,是格律诗还是自由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诗,是诗人偶得的无限,并用妙手把它“翻译”为这样的一个有限。它就是酒,它就是瓶。林庚在《诗的韵律》中说,旧瓶之所以变成旧瓶乃是由于酒先旧了,则如欲造一个新瓶,自然也必须先有新酒。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诗歌发展经常处在林庚所说的某种“不平衡”的位置,这与其说是缺乏新酒即诗歌感觉,莫如说是缺乏感觉的形赋——诗化与主体化的诗歌语言形式。“一个作家最值得称道的贡献,是语言上的贡献”[23],对诗歌尤其如此。简单说,现在诗歌发展的问题还是当年林庚的老问题,“我们从什么地方认取这一只妙手呢?必在更多的偶然之上,而不是一般现成的概念、辞藻。”这是林庚推崇的五四精神和“盛唐气象”的经验,也是他的创作经验。
诗人气质和禀赋尽管各不相同,但他们不会因为有限世界的力量失去对无限世界的感觉,没有让生活的语言淹没诗的语言。在庸常生活中,能够不断地“发现”生活,并用“妙手”将“发现”赋形为充分诗化与主体化的语言形式:这就是诗人,这就是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