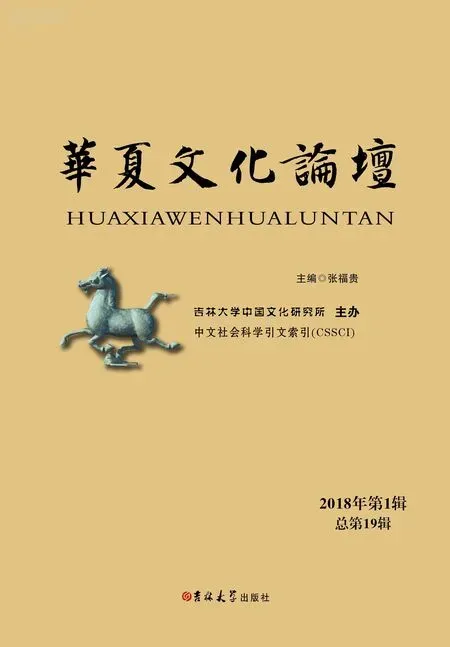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对“东方专制”的构拟
王向远
【内容提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在西方人“东方观”构拟的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全书建立在“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上,在“东方—西方”的对比对照中阐述“法的精神”,为此把前人对土耳其奥斯曼“专制”的评价扩展到整个东方世界,抹平了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把“专制”视为东方各国普遍固有的政体,从而在法学意义上构拟了同一的“东方”与清一色的“东方专制”,在此过程中不惜扭曲、误解、丑化、妖魔化东方国家,也必然出现史实与逻辑上的种种缺陷与问题,直到今天仍有批判考察的必要。
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Secondat,baron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1769—1755)的《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作为法学理论原理的奠基性名作,读书界人所共知。他所提出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分权说,“以权力制约权力”制权说,以及“自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的“自由”界说,都对现代政治学与法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论法的精神》作为一部法学理论著作在法学原理上的独创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方面的论述评说已经汗牛充栋并形成共识,无需赘言。但从西方的“东方学”与西方人的“东方观”的角度看,《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东方史料的使用有欠严谨之处甚多,关于“东方专制”的论述充满傲慢与偏见,矛盾重重、逻辑混乱,因而有必要对它做另一视角的批判考察。
一、“专制”及“东方专制主义”界定的含混
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专制”一词是作为一种政体概念使用的,他认为:“政体有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一人依固定和确立的法单独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也是一人单独执政的政体,但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全由他个人的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是承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但《政治学》虽然提出三种政体之别及“东方的专制”的问题,但并非是把所有的东方国家都视为“专制”的,而是认为它是在东西方都可能存在的一种政体类型,但是孟德斯鸠对此则不以为然,他写道:“亚里士多德把波斯帝国和斯巴达王国都归入君主政体之列,可是谁不知道,波斯是专制国家,而斯巴达是共和国吗?”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做出的最大修正,就是将专制政体仅仅视为属于东方国家的政体,西方则只有另外两种。这样一来,所谓“专制”就等于“东方专制”,所谓“专制主义”就等于“东方专制主义”了。
那么,“东方专制”的特征是什么呢?孟德斯鸠首先区分了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这两种看上去有相似之处的政体。两者都是“一人单独执政”,但区别是前者为“依固定和确立的法单独执政的政体”,后者为“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全由他个人的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的政体。也就是说,专制政体的要害并不是“一人单独执政”,而是“既无法律又无规则”。但是,这种界定实际上是似是而非、暧昧含混的。他说的是在“专制”国家里本来就没有“法律和规则”,但是事实决非如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任何一个国家,倘若真的是“既无法律又无规则”,那么这个国家就不算是一个国家,甚至都不算是一个文明社会,哪个国家没有“法律和规则”呢?就说古代东方流传下来的有文字记载的法律,两河流域有一系列楔形文字法,如《乌尔纳姆法典》《苏美尔法典》《苏美尔亲属法》《赫梯法典》《亚述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等;希伯来人有《摩西五经》等五部希伯来法典,古代印度有《摩奴法论》《那罗陀法论》等一系列法典,伊斯兰法体现在《古兰经》和《圣训》中,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例如唐代《贞观律》《唐六典》等,日本有《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等。这些都早已经不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自然法”,而是形诸文字的“人为法”了。孟德斯鸠作为法学理论家,对这一基本事实并非完全不知。例如他承认过日本有法律,但“日本法律的暴烈曾经胜过它的力量,它成功地摧毁了基督教。然而,闻所未闻的努力恰恰证明了它的无效。它曾试图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治理,却进一步彰显了它的无能。”他也承认中国有“甚多的各种法规”,中国人“曾经试图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不悖,但是,任何东西一旦与专制主义沾边,就不再强有力量”。看来,不是东方国家“既无法律又无规则”,而是东方没有孟德斯鸠所理想的西方那种“法律与规则”。这种双重标准在逻辑上就出了问题:究竟是“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决定了“东方专制主义”及其特点呢,还是“东方专制主义”政体中的任何法律与规则都不算是“法律与规则”呢?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东方国家显然都是既有“法律”也有“规则”的,那它们还算不算“专制政体”呢?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为什么要用“既无法律又无规则”来界定“东方专制”呢?
或者他说的是,虽然有法律和规则,但是在东方君主眼里却是“既无法律又无规则”,“全由他个人的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然而,这样的假定也不合逻辑。因为所有法律和规则都是当政者主持颁布的,在“一人单独执政”的“专制”国家里,法律要么就是这个君主颁布的,要么就是他的前任颁布、而他认可有效的。既然仍然在使用这些法律法规,那么它们就是有效的;既然是有效的,那么君主又为什么不把这些法律法规放在眼里,而“全由他个人的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呢?他拿什么来治理国家呢?有法不依,不等于无法可依。君主不依法行事,“全由他个人的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那就是自毁江山。这样的自毁江山的“暴君”,古往今来、东方西方都有,但是我们判断一种政体,主要应该根据其政治体制,而不是依据君主个人的品质德行。因为在同样的政体下,执政者都有德行好坏之分,专制政体下有明君,其他政体下也有暴君,这一现象每每见于政治史。在不得不承认“所有国家包括古代东方各国都有自己法律法规”这一前提下,孟德斯鸠的“专制”政体的界定标准实际上只剩下了“全由他(君主)个人的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这一条了。这正是暴君的作为。但是,这样的暴君,在孟德斯鸠所说的西方“君主政体”中,也是代不乏人的,而且绝不比东方国家少。这些暴君的基本特点也都是“全由他个人的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西方的“君主政体”的属性仍然不会改变呢?只有在东方就成为“专制”的了呢?由此看来,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区分及“专制”的界定具有明显的双重标准,是模棱两可、充满矛盾的。从根本上看,孟德斯鸠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东方各国都有自己的法律与规则这一事实,但另一方面却坚信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是没有法律与规则的。换言之,只有西方的法律才是法律,东方的法律不算是法律。这样一来,西方的法律就成了东方法律的衡量标准了。
实际上,任何一个有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的国家,都像是一台按一定规律运转的机器,君主个人纵然如何跋扈和残暴,恐怕“全由他个人的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所能“处置”的,不会是“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而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因为任何个人的为所欲为都是有限度的,突破了限度则会适得其反。历史上那些暴君的下场每每是自取灭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看来,孟德斯鸠给“专制”政体所下的定义,是严重忽略了“专制”的“制”(制度)的因素,而以君主个人德行作为评价标准了。也就是说,他采取的实际上是道德的标准而不是政治的标准。他对专制君主的批评,也多放在私德方面以及后宫,是让君主的私德或后宫生活方式来决定政体的属性。他这样写道:“东方的君主们也是这样。在牢狱般的深宫里,太监把王子们伺候得胸无大志,精神萎靡,几乎与世隔绝。当他们被拽出来登上王位时惊愕不已。但是,当他任命了一个宰相后,就在后宫里越发纵情声色,在一群死气沉沉的殿臣面前,他们喜怒无常,蠢举迭出,此时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当国王竟然如此容易。”皇帝把权力交给宰相,自己只管纵情声色,这是说东方君主的昏庸。这样的情况在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确实都存在。但君主的昏庸与专制并不能等同。昏君兼暴君者固有之,但昏君并不等于暴君。君主耽于享乐不勤朝政,而将权力交给宰相大臣,若是这样,那就好比是所有权者与经营者相分离一样,岂是君主“一人单独执政”呢?孟德斯鸠又说:“在专制政体下,接受委托形式权力的人握有全权。宰相就是专制君主,而每一个官吏都是宰相。”照这么说来,专制国家就有了许多的宰相、许多的君主,又岂是“一人单独执政”呢?
孟德斯鸠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涉及到了一些东方古代国家的权力结构问题。实际上,在东方古代各国的分权社会里,君主往往难以“专制”。例如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社会上的婆罗门阶层权力大,而政府的作用小,关于这一点泰戈尔已经明确指出,印度作为宗教文化区域是很辽阔的,但作为政治单位却有成百上千个各自为政的小国,国王也是小国寡民的国王,难言是“专制君主”,印度是靠着“社会制度”而不是靠“政府”来维持的。日本在进入幕府时代后,则是天皇、幕府两重权力的国家,是天皇的“权威”与幕府大将军的“权力”相分离的国家,而到了江户时代,则形成了天皇的权威、武士的权力、町人(城市工商业者)的财力,这三者相互鼎立的格局。
接下来,孟德斯鸠就从东方国家中举例,来论述“专制”的特点了。他承续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三种政体分别以“美德、荣宠、畏惧”得以维系的观点,认为“共和政体需要美德,君主政体需要荣宠,而专制政体则需要畏惧。在专制政体中,美德根本不需要,荣宠则是危险的。”没有荣宠,即没有荣誉感可言,是因为在那种政体下“人人都是奴隶”。
关于专制政体的所需要的“畏惧”,孟德斯鸠写道:
在专制政体国家中,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的服从,君主的旨意一旦下达,就应立竿见影地发生效应……根本没有调和、修正、妥协、交情、对等、商榷、谏议。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相等或更佳的谏议提出,人只是服从于那个发号施令的生物脚下的另一个生物罢了。
这里所说的就是对专制君主的机械的绝对服从。但是,他在得出“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普遍结论的时候,却只举出了波斯为例,说波斯国王对某人判刑后,谁也不许再向国王提起此人,即便当时国王是在醉酒状态下做出的判刑决定,那也必须执行。但是他似乎没有说明,这种现象在东方是普遍的、绝对的,还是偶然的;君主的随心所欲是表现在一切事情上,还是表现在某些事情或个别事情上,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如果这种君主的随心所欲是普遍的,那古代东方各国为什么还要制定那么多法律呢?君主颁布那些法律岂不是要自缚手脚或自毁声誉吗?如果是个别的、非常态的,那么这种事情在古代任何一个君主或执政者那里,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绝不是东方国家的君主才有的。翻翻历史记载就知道,那些为所欲为的荒唐霸道的君主,西方历史上恐怕比东方更多。从古希腊的僭主,到现代法国波旁王朝的许多国王们都是如此。
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不过,对于那些愚昧和萎靡的民族来说,法律无需很多。在那里,有两三个概念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新概念。驯兽时更换主人、课程和姿态,要让牲畜牢牢记住的只是两三个手势,无需要更多。”这里又从“畏惧”提出了“畏惧”者的特征,就是“被专制”者即臣民的特征,那就是类似“牲畜”般的机械服从。对于这一点,孟德斯鸠又称之为“奴性”。“奴性”这一概念,作为专政政体的一个附属特征,也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氏说:“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有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有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但是亚氏的判断是带有柔软性的,是说无论欧洲还是亚洲,哪个民族都会有奴性,只是“亚洲的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有奴性”而已。但在孟德斯鸠这里,奴性成为东方专制的特有产物,是东方人所独有的,是东方的“普遍精神”。他断言:“人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习俗、风尚等多种因素的支配,其结果是由此形成了普遍精神。”而且这种普遍精神的形成是有“物质原因”的,那就是为亚洲国家的地理条件所决定了的,他们的国土太广大了,又没有天然屏障,所以“在亚洲必须永远行使专制权力。因为,倘若不实行严格的奴役制,就是形成自然条件难以形成的割据局面。”而“自然条件把欧洲分割成许多面积不大的国家,实行法治不但不损害国家的存续,而且十分有利,以至于倘若不实行法治,国家就会渐趋衰微,落后于所有其他国家。”结论是:“与此(欧洲)相反,奴役精神主宰着亚洲,亚洲从来不曾摆脱奴役精神。在这块土地全部历史上,找不出任何一个能表明自由精神的标记,除了敢于奴役的气概之外,再也看不到别的精神。”而相应地缺乏所谓“自由精神”。其实,“奴性”与“自由精神”是人性即“普遍精神”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每个人身上都有“自由精神”,也难免有一些“奴性”,因而它不应是区分“东方”与“西方”的标签,孟德斯鸠却只把“奴性”的标签贴在了东方人身上,显示了他的东方观中的傲慢与偏见。
这样,总括起来,《论法的精神》中“东方专制”这一概念似乎就有了两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东方专制”需要有专制君主,君主行使专制权力靠的是暴政,国家没有真正的法律,君主是国民的“奴役”者;第二,拥有甘于受奴役的人民,这些人民的“普遍精神”就是具有“奴性”。这样说来,在东方,从君主到臣民,是自上而下、彻彻底底的“专制”了。但是这样的界定在逻辑上似乎仍然充满着矛盾悖论:只有面对不畏惧者,才有恐怖;只有面对反抗者,才有镇压;只有面对自由的追求者,才有牵制和压迫。一群“奴性”十足、甘受奴役的顺民,应该是不需要残暴的“专制”的,君主也无须通过令人“畏惧”的恐怖暴政来统治他们,因为他们本来都很温顺。如此,所谓“东方专制”、东方暴政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气候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东方专制”的宿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了“东方专制”的概念,并做出了界定,描述了一些现象例证,但还需要论证“东方专制”为什么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必然的,这就需要寻求一些决定性的因素。要说决定的因素是东方人自身,是由人种所决定的,那就等于说是由东方人本身决定东方人的法的精神,这个决定因素显然不够客观,也不够自然。而且,东方国家的民族众多,人种不一,为什么在“专制”这一点上却是同一的、普遍的呢?因而必须寻求一种客观外在的决定条件。于是,孟德斯鸠选择了地理与气候决定论。
用地理气候来说明人的性格与文化,并不始于孟德斯鸠,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中就说过:“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民族(指不包括希腊半岛的欧洲大陆——引者注)尤甚,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府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擅长技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种姓,在地理位置上既处于两大陆之间,其秉性也兼有了两者的品质。”这里比较的是希腊半岛人、欧洲大陆人、亚细亚人因冷热不同气候而形成的民族性。这种观点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从气候的角度首先断言:“统治炎热地区的通常是专制政体。”他所说的炎热地区,是他所了解的当时的土耳其、波斯、印度、阿拉伯半岛等东方地区,而与之相对的,是他所最推崇的“温带”地区即欧洲的中北部。在“东方专制”的预设中,只有欧洲中北部是温带,因而有着最为适宜的政体,上述东方地区是炎热的,因而又是专制的。为了支撑这个结论,孟德斯鸠首先得否定东方有温带地区。他引用了当时的旅行家关于亚洲气候的描述,指出亚洲北部存在极为寒冷的地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一点却与他在此前几章中,把相关论述与结论建立在亚洲“炎热”的气候条件下,就显得不协调了。他在这里承认了亚洲也有冷热不同的区域,由此承认“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朝鲜的南方人也不如北方的勇敢”,但是他却根据旅行家描述做出了这样的推断:“亚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温和地带,与严寒地区紧挨着的就是炎热地区,诸如土耳其、波斯、莫卧儿、中国、朝鲜和日本……而欧洲则截然相反,温和地区非常广阔。尽管欧洲各地的气候差异很大……可是气候由南而北不知不觉中逐渐变冷,大体上与各国所处的纬度成正比。因而毗邻各国的气候条件基本相同,彼此没有太大差别,正如我刚才所说,温和地区相当广阔。”现在看来,孟德斯鸠的这个说法显然与气候学的常识不相符合。在亚洲,存在与欧洲相似的广大的温带地区,例如中国的黄河、淮河流域,朝鲜半岛、日本本州岛等,总体上都属于温带气候。孟德斯鸠之所以断言亚洲“无温和地区”,首先是要支撑这样的结论:
因此引出的结果是:亚洲各国的形势是强弱对峙,好战、勇敢和活跃的民族,与纤弱、怠惰和胆怯的民族面面相觑,于是乎,一方必将成为征服者,另一方必将成为被征服者。与此恰恰相反,欧洲各国的形势是强强相对,毗连的国家几乎同样骁勇。之所以亚洲弱而欧洲强,欧洲自由而亚洲奴役,重大原因即在于此。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依然由于这个原因,亚洲的自由从未增多,而欧洲的自由则随情况不同而有所增减。
在孟德斯鸠看来,这就是“欧洲自由而亚洲奴役”的规律,东方注定没有“自由”,天然活该受奴役。他认为同样是对外征战,欧洲的征战与亚洲的征战其后果截然不同,因为“欧洲北方民族以自由民的身份从事征战,亚洲北方人则以奴隶身份从事征战,而且仅仅是为了一个主人而征战”。这一看法显然继承了希罗多德《历史》中关于希波战争之本质的看法,但孟德斯鸠却把这一看法推广到整个东西方:凡是东方人发起的征战,就是在推行“奴役”;凡是西方人发起的征战,都是在传播自由。这里他以鞑靼人代表东方,并举例说:“鞑靼人虽是亚洲的天然征服者,自己却也是奴隶。”所以鞑靼人打到哪里,就把奴役带到哪里。“在被称作中国鞑靼的那片广阔的土地上,这种情形如今显示得特别清楚。皇帝对鞑靼地区的统治与他对中国本土的统治同样专制暴虐……鞑靼人摧毁了希腊帝国,在被征服国家中推行奴役。哥特人征服了罗马帝国,到处建立君主政体,确立自由。”这么说来,难道当初哥特人南下,所建立的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是自由的吗?如果是这样,那“黑暗的中世纪”之说是如何而来的呢?宗教迫害,教会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对异端的镇压,对言论与思想的钳制,没有法律而只有宗教的“宗教裁判所”的跋扈,这些都发生在哥特人南下所建立的罗马帝国,其实它的“奴役”与“不自由”的程度远甚于当时和后来的东方各国,而且持续时间极长。否则,欧洲近代史上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运动与“革命”思想,都是在“革”谁的“命”呢?难道不是欧洲人对来自欧洲自身奴役的革命吗?亚洲人的近代革命是摆脱欧洲人的殖民压迫,而欧洲人的近代革命是摆脱旧制度的压迫。若像孟德斯鸠所说的西方历来没有奴役只有自由,那么启蒙主义运动的指向又是什么呢?没有中世纪的黑暗,哪有照亮黑暗的“启蒙”运动?
除了用气候来解释东方西方文化的上述重大差异之外,孟德斯鸠还以此推论出了与气候相关的决定东方专制的必然的一系列客观条件和因素。例如他写道:“人在寒冷的气候下精力比较充沛……一个人若处在闷热的气候中,鉴于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因,心神就会高度萎靡不振……炎热地区的人怯懦如同老人,寒冷地区的人骁勇如少年。”说的是民族性格与气候的关系。谈到冷热两地的人对痛苦与欢乐的感受时,孟德斯鸠说:“对愉悦的感受度,寒冷地区的人较低,温暖地区的人较高,炎热地区的人极高……疼痛也一样……〔寒冷地区的〕俄罗斯人不被剥皮就不觉得痛……炎热地区的人器官敏锐,凡关乎两性相悦的事,心灵极易为之所动,无论何事都能因为男欢女爱。”这段感受性的描述中显然充满了矛盾。试想,一个“精力充沛”“骁勇如少年”的寒冷地区的人,怎么会对痛苦和欢乐感受迟钝呢?同样地,那一个个“如同老人”的“萎靡不振”的炎热地区的人,如何会一转而为“器官敏锐”,而特别地热衷于“男欢女爱”呢?他进而把气候冷暖与道德水平相联系,断言:“北方气候下的人恶习少而美德多,非常真诚和坦率。一旦接近南方地区,你简直就以为远离了道德。强烈的情欲导致罪恶丛生。温暖地区的人风尚不定,恶习无常,美德也无常;这是因为那里的气候缺乏确定的性质,难以有固定的风尚与道德。”按他的这一标准,俄罗斯人处在北方,是寒冷地带的人,应该属于道德水平高的一类,但孟德斯鸠却对俄罗斯人的道德、法律水准等完全不认同;同样地,蒙古人原本是北方寒冷地区的草原人,也应该是拥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但孟德斯鸠是把蒙古人视为野蛮民族的。实际上,他的“南方—北方”或“冷—热”的分别,只是为了说明南欧与中北欧的区别,为了说明他心目中的“欧洲北部人民”即他所理想的“我们的祖先”日耳曼人的文化的先进。至于东方国家,实际上无论南北、冷热,都属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范畴,不仅君主是暴君,而且人民也都是甘为奴隶的。因此,实际上他并没有认真去区分东方各地区的气候的冷热之别。当他指陈东方各民族的恶德,而又拿不出实在根据的时候,就用“气候冷热”这个前提来说事。例如,说东方人的懒惰、甘为奴役,就举印度人为例,因为印度“酷热”。转而却又说:“印度人生性温和、亲切,富有同情心,深得立法者的信任,立法者制定的刑罚很少,也不严酷,甚至不严格执行。”结论是:“良好的气候使人憨厚,法律也随之宽和”。他在这里说的“良好的气候”显然是对印度而言,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刚刚指出了印度气候“酷热”造成怠惰、缺乏勇气、具有奴性。他同时谈到了“日本人生性残忍”,说日本的立法者对人民没有信任,法律严苛,人民“动辄得咎,处处受制”;那么日本人的“残忍”究竟是由它的什么气候条件造成的呢?因为日本历史上文化发达的中部地区是典型的季节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总体属温带。这种“残忍”究竟是由炎热还是寒冷造成的呢?孟德斯鸠语焉不详,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科学上的论证与阐述,纯粹是经验性的感受的描述而已。
孟德斯鸠常常把极为复杂的文化问题直接与气候因素挂钩,就不免将问题简单化。例如在论述东方的“家庭奴役法”的时候,他断言:“欧洲的一夫一妻制与亚洲的一夫多妻制,显然都与气候有关。”他仍然把“炎热”作为一个条件,说亚洲的女子早熟,女性魅力不持久,“因此,只要宗教不加制止,一个男子遗弃发妻而另觅新欢,从而产生一夫多妻制,就是一桩再简单不过的事。”但是,在这里,他只是以印度、阿拉伯等炎热地区为例,却不能说明为什么在亚洲气候条件寒冷的地区(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女性并不比欧洲更早熟,女性魅力的持久性也堪与欧洲相比,而又如何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呢?为什么中国的中原地区及古代日本那样的属于温带气候的地区也是如此呢?这究竟跟亚洲的哪种“气候条件”有关呢?显然,孟德斯鸠是拿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作为天经地义的最文明的婚姻制度,并以此作为全人类的婚姻制度的楷模,为了强调它的客观必然性,便强调“气候”这一客观的地理环境因素。实际上,人类婚姻制度千差万别,即便在“一夫多妻”的条件下,也不排斥一夫一妻,也有“一夫一妻”的选择,这与气候条件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而且,基督教社会的一夫一妻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从来都对男女的婚外情采取宽容态度,事实上,“情人”在欧洲传统的贵族社会(包括在孟德斯鸠时代),甚至成为一种通行的“制度”或“潜制度”。从这一点上看,欧洲的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只是表层的,不是绝对的。总之,东方的“一夫多妻制”与欧洲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并不能成为衡量“法的精神”的一个硬性标准。
气候决定论也被孟德斯鸠用在人口问题上,他说:“中国的气候出奇地有利于人口的增殖。那里的妇女生殖力之强为世界所罕见。最残忍的暴政也不能抑制人口的增长……暴政归暴政,气候将使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并最终战胜暴政。”把中国的人口多归为“气候”,那么是中国的什么“气候”呢?中国很大,南北东西、冷热干湿等不同的气候类型都有,哪种气候类型有利于强化中国妇女的生殖能力?为什么同样的气候条件在其他国家不能造就这样多的人口?难道是由“人种”所决定的吗?假如是人种所决定,那就不是“气候”的问题了。实际上,人口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人口众多与生殖能力、与气候的关联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出生率、死亡率、平均寿命。在专制暴政下民不聊生,战乱频仍,饿殍遍野,哪会造成“人口越来越多”的现象?人口多,只能证明社会的安定甚至生活条件的具备,最起码在古代社会就是如此。
三、被构拟的“东方”与“东方专制”
在孟德斯鸠时代或之前,欧洲的学者、旅行家,都从不同角度对东方世界及其政治社会情况都有过很多的评论与描述,但是大都只是对当时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及政体做出“专制”的判断,而不是对整个东方政体都做出“专制”的结论。而且,在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政体评价中,“专制”这一概念是被逐渐地专门用于东方政体的。起先也多用“暴政”一词,一位当代西方学者指出:“16—17世纪,‘暴政’(tyranny)这个概念使用极广,而且到18世纪初的时候,欧洲人则更多地使用‘专制’(despotism)这个概念来描绘奥斯曼政权。从‘暴政’到‘专制’,术语的转变表明,在欧洲人之中,奥斯曼帝国的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中,尽管这两个概念都用来指称那些腐败和堕落的政权,然而在‘暴政’与‘专制’之间,他们还是做了区分……‘暴政’同时含有正面与负面的特征,而‘专制’并没有自我修补的特征。”到了18世纪,西方有一些旅行家和评论家,如琼斯、希尔等人,多使用“专制”这个词来评价土耳其奥斯曼的政治,这样就把“东方”与“西方”政治与政体做了区分。当一个政府和政权是“暴政”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合法性,离崩溃为时不远了;但是,“专制”的东方政体尽管也是暴政,却是合法的,因此是会持续不改变的。另一方面,“暴政”常常是统治者个人的行径,而“专制”却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可见与“暴政”相比,“专制”更为顽固、更为可怕和更令人无望。
孟德斯鸠进一步把此前一些人对奥斯曼的“专制”评价扩展到了整个东方世界,并把它看作是东方各国普遍固有的现象,并从法律、法学的意义上,构拟出了一个清一色的同一的“东方”。在《论法的精神》中,东方因为有了“专制”才是“东方”,多元的“东方”成为“一元”的东方。在孟德斯鸠构拟“东方”的过程中,东方各国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性都被抹平了。奥斯曼帝国的教俗合一的体制,印度建立在种姓制度下的“强宗教、弱政府”的体制,中国的“家”与“国”同构、官府与乡绅相互牵制又协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行的体制,日本武士文化的重刑罚与宫廷贵族文化重人情的法与情相济的体制,还有东方各国几千年间漫长的历史阶段的不同、政体的变迁,都被他以“东方专制”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实际上,东方各国之间存在种种差异,不可同日而语,根本就不存在政体上相同划一的所谓“东方专制”。而且另一方面,在孟德斯鸠看来,东方的“专制”不仅是一种东方的政体,也是东方民族与社会的普遍的奴性特征,即一种甘为奴役的精神状态,而且是由气候地理等客观条件预先决定了的,是宿命性的、与生俱来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东方人的民族性格千差万别,气候地理条件差异很大。面对这些差异,孟德斯鸠在“东方专制”的独断论述中,常常会显得捉襟见肘、自相矛盾。例如,连孟德斯鸠也不得不承认,从民族性格上讲,“阿拉伯人是自由的”,这一看法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对阿拉伯人的观点相同。但是既然如此,“专制”这种政体如何是适合于“自由”的阿拉伯人的呢?连孟德斯鸠也承认,“中国的立法者还是不得不制定优良的法律,政府也不得不遵守这些法律”,但“中国人由于气候而自然地倾向于奴役般地服从”,因而中国仍属于专制国家。但是,如果承认中国的法律是“优良”的,人民服从这些优良的法律岂不是在履行遵规守法的义务吗?制定法律的目的难道不是要人民遵守吗?这岂不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吗?这还算是“奴役般的服从”吗?这与“气候”有什么关系呢?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思想性的著作,但在写法上不是体系建构的、思辨的,而是漫笔随想性的、断片的,古今、东西的相关材料为他的思想阐释所利用,因此在涉及历史问题的时候,往往信手拈来,特别是在东方、东方文化方面的论断,不可靠之处尤多。他既没有像希罗多德那样亲自到东方各地踏查采访,也没有像伏尔泰那样做过大量的纵向的系统的历史研究,他的“东方”只是服从他的“法的精神”的建构,对东方材料的使用没有严格的出处来源,也不经任何佐证、旁证或验证,所罗列的事例大多是他对材料加以主观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真实的、全面的东方世界的反映。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孟德斯鸠曾读过当时法国学者约翰·夏尔丹1735年出版的关于东方的著作《远行》,夏尔丹在书中观察和研究了波斯,他指出波斯帝国的政权是专制的,但他把“宫廷”与“国家”做了区分,认为波斯专制主要体现在宫廷政治斗争中,而宫廷争斗对国家中的多数人民并没有多少影响,人民的生活甚至比西方基督教国家更为稳定舒适。但孟德斯鸠对夏尔丹书中这一分析显然有意加以忽略了。在《论法的精神》出版后不久,更有专门的法律学者对《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东方的基本结论加以否定。如法国法律学家安奎特-杜培宏,曾在1778年出版了巨著《东方法律》(Législationorientale
)一书,指出在土耳其、波斯与印度莫卧儿帝国,都有成文法,并可同时约束君主与臣民,而且人民都可以拥有动产、不动产等所有权并受到保护,因此,有关“东方专制”的相关说法是根本无效的。《论法的精神》出版后,在法国之外的一些著作家也对孟德斯鸠关于土耳其奥斯曼的专制论断表示出强烈质疑,例如当时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詹姆斯·波特爵士(Sir James Porter)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孟德斯鸠的看法是夸张的和虚构的,其实奥斯曼帝国中既有法律的存在,也有最高统治者苏丹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故而它“比一些基督教国家政府更少专制”。即便是对奥斯曼的政体,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其为“专制”的。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随着欧洲本体民主政治的进程,随着西方对东方殖民侵略的全面展开,一切关于东方传统政治与文化的正面描述都不合时宜了。西方人宁愿相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断,也不愿相信安奎特-杜培宏《东方法律》中基于对东方社会的专门研究而得出的较为客观真实的结论。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逻辑:倘若东方世界本来是美好的或正常的或具有正当性的,西方人闯进东方岂不就是入侵和破坏吗?于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实际上就为欧洲人颠覆、取代东方各国的政权,并殖民东方国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借口,那就是在东方世界传播和推行先进的政治体制与先进的社会文化,这样一来,即便是西方的殖民统治,也比东方的“专制”要好些。孟德斯鸠所说的“西方”,主要是指日耳曼人居住的中北欧那一片文化区域,他的理想的“法的精神”的基础与价值标准也体现在两点:一是基督教,一是日耳曼文化。因而他断言:“宽和政体宜于基督教,专制政体宜于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不折不扣的专制主义相去甚远”。他认为:对于西方人而言,“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心中的基督教教义,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远远胜于君主政体下虚伪的荣宠、共和政体下人类的美德以及专制国家中卑劣的畏惧。”基督教的价值远在各种政体的价值之上。基督教的这种感情甚至决定了他对日本政体与法律的评价:“日本民族固执、任性、坚毅、古怪的性格令人吃惊……专制主义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滥用专制主义。在日本,专制主义做了一番努力,结果变得比专制主义更为专制主义……日本法律的暴烈曾经胜过他的力量,它成功地摧毁了基督教。然而,闻所未闻的努力恰恰证明了他的无效。”他丝毫没有掩饰对日本及其法律的恶感,原因显然来自江户时代日本政府对基督教的严禁。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根本理想,是在法国实现当时英国那样的权力分立并能互相制约的君主立宪的政体。这样一来,“东方专制主义”就成为孟德斯鸠政治理想的反题与对立物。他不但要以邪恶的“东方专制”劝诫统治者,也以东方人的卑劣的“奴性”来警诫法国人,这当然是一种用心良苦的高明策略。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这样做比起在西方自身的政治历史与现实中找出“专制”反面例子来,要安全得多,也有效得多。但这却以肢解、扭曲、误读、丑化、妖魔化东方为代价的。18世纪下半期之后,随着《论法的精神》的广为传播和逐渐经典化,欧洲的“东方专制主义”论广为流行,逐渐成为不刊之论。像此前一些思想家如莱布尼茨、魁奈、伏尔泰等对中国儒家仁政及其治理能力的推崇,都销声匿迹了,转而是对中国及东方专制主义的否定与批判。一方面西方人从中获得了一种制度的自信乃至自傲,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西方式的对于“东方”的整体想象。“东方专制”成为西方的一种主流观念,以至于西方在此后所有的理论建构与思想阐发中——不仅仅是在法学与政治学的建构中——“东方”都被作为一种对立物、衬托物而存在,“东方”越来越被西方对象化了。可以说,正是从孟德斯鸠开始,“东方—西方”被完全想象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形成了难以跨越的疆界。那个“东方”世界与其说是真实的、实体的东方,不如说是西方人观念的“东方”,即后来被称为“东方主义”的那个“东方”。那个“东方”只是一种无言的被动的客体,是供西方人想象、评说、对照、比较、批判的时候加以使用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特别是“法律东方主义”(Legal Orientalism)的最早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