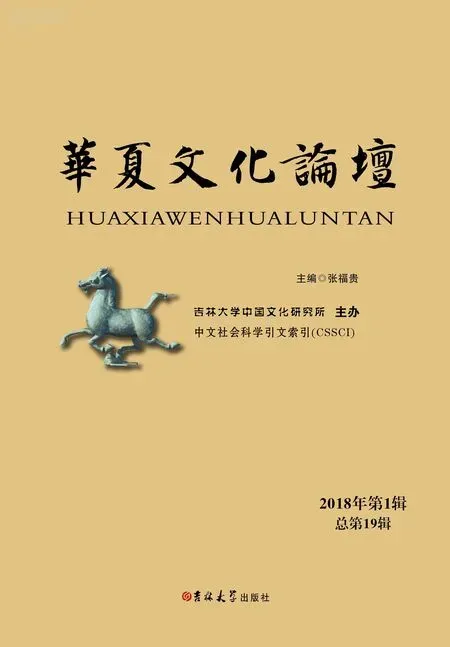生态电影的观众与公众
[美]唐思凯 刘 倡(Chang Liu) 译
【内容提要】西方对观众接受的研究在文学、电影、媒体、表演等学术领域里都占有一席之地。观众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的文化界内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影响力,其中的原因在于借助了传统大众媒体之外的网络、社交媒体等交流渠道的帮助,观众群体的参与性已经突破了线下集会这一局限。在生态电影的研究领域里,近期的学术成果把研究的焦点从生态电影的形式、心理、历史、物质和跨文化维度拓展到了诸如思考关于个体观影者如何接受特定电影这类涉及到实证研究法的问题。本文中,作者论述了观众与公众二者间在概念上的纠葛,并分析了生态电影在接受过程中引起的美学判断与政治参与间的张力。
观众对内容的接受一直是西方文学、电影、传媒及表演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也是用来分析作者与读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传播者与接受者、表演者与观看者之间交流过程的重要方法。在电影研究领域,Pat Brereton和Pietari Kääpä等学者开始了对观众接受与生态电影之间交集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将生态电影研究的重点从基于电影的形式、心理、历史、物质和跨文化层面的分析转移到了一种更倾向于实证研究的方法,即认真对待观众如何接受特定的电影。这种方法可以让学者更精确地评估某些生态电影作品对观众的影响,以及观众如何表达他们在情感与理智上对这些影片的反应。这揭示了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观众如何解释文化文本? 这是学者们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
“观众”一词本身的含义就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根据观众对内容的接受可以将其分为很多种类:普通观众、目标观众、现场观众、媒体观众、活跃观众、被动观众、理想观众、隐含观众、想象观众等。英语词汇audience “观众”的词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诺曼语和中古法语中的audience ,以及拉丁语的audientia(来自动词audire “听 ”)。最初,观众指代听觉行为。然而这个词后来演变为表明听觉所及的范围,随后进一步演变为举行正式听证会的行为,如审判、面谈或演讲。换言之,观众既包括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的发言者,同时也包括有关注该人所说内容的能力的收听者。因此,观众也可以表示那些出于特定目的而组成的集体:一种召集或一种聚会。例如,观众可以指某活动参加者的集会,也可以指对某一特定的人、物、想法感兴趣的人的聚会。鉴于其语言的复杂性,audience“观众”一词在中文里可表述为观众、听众,甚至公众。
在西方,“观众”在概念上与“公众”是交织在一起的。观众在公共活动中的积极参与可以追溯到古代。例如,在古雅典,把思想放在公共领域讨论的精神是诸如审议、集体决策和参与公民身份等过程的基础。时至今日,观众的参与不再仅仅发生在实际聚会中,除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渠道,观众也常常通过在线和社交媒体进行参与。正如Sonia Livingstone在她编辑的《Audiences and Publics》中指出的那样,“观众与公众之间的区别越来越难以界定”。虽然对于任何特定话题(如网民对电影的评论),观众作出反应的数量和质量往往会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观众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文化生产中一股有影响的力量。根据S.Elizabeth Bird的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一直在系统地揭穿一种观念,即将观众视为一个静态的、被动的和孤立的群体。针对女性读者群体、粉丝文化及群体,以及新媒体技术用户的开创性研究表明,观众不是被动的媒体接受者,而是影响文化生产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事实上,作者与读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传播者与接受者、表演者与观看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观众和公众。因此,生态电影的观众和公众之间的活力值得进一步分析。
一、生态电影学者的汇聚
系统地分析生态电影,完成在生态电影的观众与生态电影的公众之间的身份转换,就这两点而言,学者们是当之无愧的先驱。一些学者通过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研究电影、媒体、环境三者之间的交集,这些学者的汇聚最终促成了生态电影研究这一领域的形成。这一领域,广义地界定,拥有诸多不同的起源和名称:生态电影,绿色电影研究,生态批评电影研究,生态纪录片研究,生态媒体和可持续媒体。生态电影的发展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它的“史前”阶段追溯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它以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学术领域存在的阶段。例如,对电影与媒体中的动物的研究;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故事片进行解读,动画电影中的非人物角色,还有以地域为题材的独立电影。另有,其他的研究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生态批评分析,例如媒体生产的实质性影响,环境改革的历史,媒体研究,修辞学,情感研究和哲学。 这种分类学并不是详尽无遗的,其目的在于说明各种不同研究方法对生态电影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最早使用“生态电影”一词的学术出版物之一是Roger Anderson的《Ecocinema: A Plan for Preserving Nature》。这篇发表在生物科学杂志上的一页长的文章更像是科学家的讽刺幽默。Anderson称“自然爱好者是极端主义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愤世嫉俗”。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保护环境的问题,他建议将所有生物体保存在福尔马林中,在乡村放置动植物的塑料复制品,拍摄自然风光片并送给那些能将景色、声音、气味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特殊剧院展映。无论是讽刺、挑衅,或者离经叛道,他的思考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篇文章讽刺了之前关于林地究竟是该“保存”还是“保护”的争论,特别暗指了John Muir所付出的努力。文章也预示着后来关于“自然”的本体论地位和环境艺术品的模仿性的争论。虽然这样的解读高估了上述文章和内容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影响力,但作为一份历史资料,这篇文章得到了来自学界的兴趣,因为纵观全局,它将电影与环境研究联系在了一起。
几十年后,“生态电影”一词在Scott MacDonald的Toward an Eco-Cinema
中重新出现。这篇文章突出了MacDonald与环境研究的密切关系,并扩展到他早期的著作The Garden in the Machine
,分析了地区在美国视觉艺术和电影中的作用。在文章中,MacDonald关注的是低发行量的独立电影,并将其视为主流环境电影的替代品。这些独立电影莫名让人想起三十年前Anderson的建议(他关于福尔马林和塑料复制品的建议除外):他们关注的是树叶、河流、沙漠、森林等。作为一个框架,MacDonald将生态电影解读为“对认知的重新训练”。在这篇文章的修订版中,他补充说,生态电影旨在“提供新的电影体验”。人们可以就此提出论点,认为MacDonald更喜欢将生态电影视为一个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不仅可以躲避消费主义,同时也能躲避被媒体利用或沦为媒体的工具。例如在他看来,他所研究的稀少的16毫米独立电影就是一种存在于普通观众或电影史学家所具有的视野之外的“濒危电影物种实例”。与主流电影不同,这些电影往往不易获取,即使在大学图书馆也是如此。对MacDonald来说,这些电影充当了“电影花园”,观众在此可以从现代社会的需求中解脱出来,培养对地方和风景的欣赏。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关注人们“视野之外”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电影,MacDonald将生态电影视为一种伊甸式的观影经历,观众可以从中找到远离大众媒体的庇护。由Stephen Rust,Salma Monani和Sean Cubitt编辑的Ecocinema Theory and Practice
是美国首批将生态电影视为学术研究领域的出版物之一。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指出的,电影学者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了而今所谓的“生态电影”展开了研究。与此同时,由于“不同的学科基础”,学者、电影制片人、环保活动人士并没有准备好在各自的作品中进行相互支持。由此,研究人员在本卷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参考点。虽然这些人对生态电影的观点多种多样,而且往往各不相同,但是编辑们总结了三点共同之处:(1)“所有电影都明确地嵌入了物质和文化”;(2)电影表明,人们可以如何与“占据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手段”合作或对抗;(3)“所有电影都呈现了富有成效的生态批评探索”。伴随这卷论文集,生态电影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具有理论和实践意识的领域。二、生态电影观众的汇聚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通过生态批评的视角进行观赏的电影即可称之为生态电影。除去观众的性别、阶级、种族、文化和个人经历之外,电影的生态评论层面还受到观众的认知、接受、情绪和理智反应等因素的影响。个体观影者的聚集构成了生态电影的观众,通过他们对影片的讨论,又形成了具有共同话题的生态电影的公众。生态电影研究的话语倾向于吸纳学者对电影的解读以及针对生态电影制作的历史和物质条件的分析,还有电影制作者、发行商、电影节组织者在其中的参与。从观众接受的角度分析生态电影,Pat Brereton和他的合著者Chao-ping Hong已经开始努力将这些个体观影者的参与纳入到研究的范畴之内。他们所采用的实证分析法包括调查问卷、Q因子分析等手段,这对侧重于生态电影观众的研究而言不啻为一种创新。正如Brereton在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Film
中进一步提出的那样,“对基础广泛的观影者展开实证考察的需求正在逐渐增长,因为这将有助于检验诸多针对生态电影的学术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在Brereton看来,对生态电影观众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对生态电影学者和个体观影者对电影作品所提出的不同解读进行对比,从而既可以进一步延伸对这些影片的研究,也有利于让进一步评估生态电影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成为可能。这种方法将进一步照亮生态电影的观众与公众之间的动态关系。生态电影研究从这种见解中获得了益处:学者们现在可以着眼于普通的媒体用户,即每一个个体。作为生态电影的观众,当他们彼此之间表述着各自对于生态电影的解读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了生态电影的公众。在这个过程中,观看同一部电影的观众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解读。例如,我观看一部电影,并选择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展开讨论。这样一来,我通过将一部电影视为生态电影而做出了“美学判断”。我的结论并非武断而来,因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这部电影唤起了我对情感和理智的回应,而这种回应与生态批评息息相关。我不会去假设我个人的美学判断也符合其他人的美学判断,但我把这种可能性赋予每个人,所以每个个体都可以就我的判断表示认可或否定。相应地,每个人都被邀请根据自己对电影的观赏而作出美学判断。这种方式鼓励每个人都应邀参与到讨论中来,共同参与集体性阐释的构建,同时为生态电影话语的构建做出贡献。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美学判断来决定是否以生态批评的视角来观看某一部影片,并开始由生态电影的观众过渡为生态电影的公众。这个过程的本质可以总结为“各抒己见”和“抛砖引玉”这两个中文典故:为了征得更好的观点,欢迎每个人都来各抒己见。
在这个框架内,任何电影都有被作为生态电影作品解读的潜力。从传统意义来讲,确定一部电影是否是生态电影作品的标准通常仅限于该电影是否包含明确的“生态”内容,例如对动植物种群的描述,风景和荒野,生态系统和环境过程,天气和气候等。这些标准有时还进一步受限于该影片是否有着明显的“环保主义”意图。通过将生态电影的美学维度降低到仅仅是环保主义的范畴,这种有着局限性的解读束缚了以一种政治参与形式介入的美学判断,并拒绝了与“环保激进主义”不相称的生态电影理论和实践形式。
美学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对Brecht和Boal来说,美学甚至有着激进的政治性。Bertolt Brecht的疏远效应(早期翻译为“失和效应”或“异化效应”)旨在扰乱观众的身份认同和感情宣泄过程。凭借他的学习剧,Brecht将注意力转向了排练,而不是最终成品。演员经常受邀参加没有观众的“表演”,以便可以探究彼此之间的关系、剧中的主题以及文本本身。Brecht的方法意在消除戏剧表演的虚幻性,并将观众的精力重新引向外部世界,这些观众可以在外部的世界里成为变革的动能。Augusto Boal后来在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中将这些方法加以扩展。对Boal而言,剧场像一个论坛,演员和观众都可以在其中为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找到解决的途径。在他的“论坛剧场”中,参与者走进了一个场景的重演,并预计“在戏剧性的行动中果断干预并将其改变”。他将那些在舞台上或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的人称为“旁观-演员”。从这个意义上说,Boal的论坛剧场鼓励其观众转变为公众,并对所描述的社会问题作出回应。Brecht和Boal都打破了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第四面墙,将“观众”的范畴从传统的界限中解放出来。对Theodor W.Adorno来说,电影的本体(不论是银幕上或是胶片中的呈现)犹如电影世界的“第四面墙”,而电影的启迪潜能源于它是美学和政治协商的一种“介质”(Medium)。尽管Adorno在他的一生中写过与电影有关的东西不多,但他的想法与生态电影研究却有着意想之外的关联。在Transparencies on Film
中,Adorno保持了对文化产业一贯的批评态度,与此同时也罕见地为一群新兴的被称为“Oberhauseners”的电影制作人而欢呼。Adorno指出这类独立电影的优雅之处就在于其对蒙太奇的使用,因为它让观众摆脱了文化产业更倾向采用的平滑的叙事制作过程。与此同时,他不主张杂乱无章的蒙太奇,这样的剪辑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倒退。最终,他希望看到电影达到一种在观众看来具有“可读性”的写作,不是一种要为之遵循的脚本,而是作为一种可细读、咀嚼的文本。众所周知,Adorno并不热衷于对艺术品的接受进行实证研究。事实上,从《启蒙的辩证法》到《美学理论》,Adorno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保持着这种态度。Adorno所说的“影响研究”,除了“影响研究”之外也可以译为“社会效应研究”等,在几个方面都存在着问题。(1)它将美学体验简化为一套实验程序,要求通过量化的方式衡量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影响。(2)它瓦解了艺术品的社会维度,仅仅将其视为个体的接受,忽视了艺术品的生产及其文化背景。(3)打着理解“他们想要什么”的旗号,它与文化产业创造并迎合消费者欲望的生意进行合作。(4)它抑制了艺术品内在的那部分只能通过非经验手段解码的内容。正如Miriam Hansen对Adorno的解读所说的那样,通过“对观众的反应做出细致入微的计算”,电影成为了将艺术作品拆解为“可用元素”的一种缩影。虽然Adorno的观点在这里并不是对“受众调查”的全面批评,但这确实说明了某些学者对这种方法的抵触。
然而,Adorno的著作中也是对受众研究有着些许支持的。Adorno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电视》的分析中指出“电影容纳了各种层次的行为反应模式”,因此认可文化产业的模式与潜在的抗拒模式是共存的。换句话说,他指出在电影向观众所传递的“意图”以及观众对此的接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道缝隙。他认为媒体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探索这道缝隙的潜力。他补充说,“获得解放的电影”将本着解放事业的精神召集一个集体对文化产业发出抵抗的集体没有太大的不同。Adorno以这种方式向Oberhausen电影制作人以及批判理论和媒体研究之间的联盟提供了支持。他的见解不仅证实了美学判断在媒体接受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也承认了受众研究在生态电影研究中的潜在价值。
许多生态电影研究者以生态批评的立场解读流行电影(这种解读通常有悖于对这些电影的流行解读)。对生态电影研究进行受众研究的部分原因在于验证一般观众是否能够按照研究者们提出的生态批评模式观看这些影片。然而,受众研究多少要受到一些来自商业利益的影响:电影行业在电影的制作上总是离不开对目标观众和营销数据的依赖。以下引自Adorno的《文化工业再思考》:
因此,尽管文化工业不可否认地对它所指向的数百万人的有意识的状态和无意识的状态进行推测,但大众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计算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文化工业滥用其对大众的关注,以便复制、强化和巩固他们认为是确定不可改变的心理。从始至终,这种心理会如何改变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即使文化工业本身在不适应大众的情况下几乎不存在,但大众并不是衡量的标准,他们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生态电影研究要采用受众研究的方法,那么它就需要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它与文化工业的“研究目标”合作该由什么构成?当有人参与到测试研究的时候,存在着哪些道德伦理问题?通过让观众自行发展他们的思想,进而使观众成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这将意味着什么?对生态电影生产中的民间、非商业或独立成果进行研究将如何促进对文化工业的抵制?这些问题指向结合了Adorno及生态思维受众研究的方法。以此种方式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预示了媒体伦理学的实践。
文学理论有一个老派的工具可供生态电影的研究者与观众使用:文本细读。在阅读文本中,假设必须接纳或抵抗主导解释可算是“意图谬误”的一种形式。相反,文本细读并不做这种假设:它以认真和开放的方式研究文本(电影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文本)。它不认为作者理解了文本内部可能覆盖的所有含义,更不用说他或她“原本”说了些什么。正如Wolfgang Iser所说,“文学文本中的‘星’是固定的; 连接它们的线是可变的”。为了进一步展开Iser的类比,人们可以想象这些“星”起起落落,构成无数星座。并非所有的恒星都很容易被看到:仰望夜空,人们可能会发现星尘星云和气体星云,短暂的超新星,所有形式的恒星死亡,或许是黑洞——变得比没有光的时候“更暗”的恒星。文本细读是一种保持接受的状态:它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可能性、细微差别和陌生性。这即使不是冥想,也算得上沉思。在生态电影研究中,能与之相比的是MacDonald所谓的“以耐心和正念为模型的电影体验”。以生态批评的方式观看电影,就是向其他学者、其他观众以及电影的他者性敞开心扉。
三、观看生态电影的四种模式
生态电影的公众建立在其成员富有创造力的对话上。生态电影观众中的成员应邀解释电影如何在生态批评问题上唤起他们做出情感和理智的回应。这种参与和审议的过程有助于生态电影的观众转变为生态电影的公众,鼓励美学判断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下是观看生态电影的四种模式:行动式、寓言式、联想式、现实式,旨在帮助和促进观众之间的讨论:
行动式:影片邀请观众以特定方式参与到其他的实体活动中。这一模式通常强调对生态电影进行带有政治色彩的解读。这部电影的功能和目的是什么?一部电影与它的制作人的议题有什么样的关系?电影制作人期望观众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例如,观众可能在观看Tapped
之后抵制包装饮用水,或在观看Food Inc.
之后开始购买当地的“有机”食品。根据多次民意调查显示,An Inconvenient Truth
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影响了公众舆论,甚至影响了一些观众的生活习惯。环境电影节将观众、活动家、教育家、电影制作人和发行商聚集在一起,他们除了观看电影之外,还相互进行交流(韦罗奎特-玛瑞康迪,2010b,43-44;莫纳尼,2013年)。寓言式:电影除了把故事或内容呈现出来,还在另一层面上发表一种批评。“实际内容”是由什么构成的,“另一层面上的批评”如何产生?什么样的历史或文化脉络会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电影?应以什么(及谁的)标准评判电影?例如,The China Syndrome
在一个层面上看似是一部关于由核电站事故引发危机的好莱坞惊悚片。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它可以被视为对一场批评核能工业的炒作剧。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辩论中,这部电影常常与三里岛事故一起被引用。此外还有具有散文特色的电影。Jennifer Baichwal拍摄的Manufactured Landscapes
在一个层面上所关注的是Ed Burtynsky的摄影作品,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意味着对中国的工业化和环境问题的批评。联想式:电影通过唤起交叠的世界的这种方式重新定义了观众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电影制造了哪些非现实的环境和实体?通过这样做,电影是如何向电影技术和语义局限发起挑战的?电影中的电影世界对我们的世界有什么影响?这种模式特别适用于科学、幻想和动画电影。例如,WALL-E
唤起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在那里,地球由于污染和垃圾变得寸草不生,无法居住。在那个世界里的人类的命运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电影Avatar
也以类似的方式强调了不道德的资源提取方式会破坏其他众生的生存和福祉。人类能够在潘多拉星球上操纵化身和机器人的技术类似于演员通过动态捕捉来演绎电影角色的这一技术。在Andrei Tarkovsky拍摄的电影Solaris
中,具有感知能力的星球索拉里斯通过使用化身人模仿主角记忆中的人进而与主人公展开交流。在电影世界中,索拉里斯星球通过化身人向主角进行自我介绍;在现实世界中,索拉里斯星球通过Solaris
这部电影向观众进行自我介绍。这部电影邀请观众一起想象与具有感知能力的星球共存会是怎样的体验?现实式:摄影机充当了观看的主体,给影片带来了一种虚幻的即时性。对于电影而言,“真实世界”为之提供了哪些内容?电影何以成为了对这些内容的一种诠释?电影是否造成了“电影”世界与“真实”世界难以区分的幻觉?总的来说,电影如何进一步肯定现有的感知和认知模式,或者对其发出挑战?这种模式适用于各种电影类型,从纪录片到野生动物电影,抑或是好莱坞传记片。由活动家Erin Brockovich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Erin Brockovich
讲述了太平洋煤气和电力公司所造成的水体污染,并戏剧化地再现了Erin代表遭受污染影响的居民们奋起抗争的故事。而在The Cove
这类纪录片中,摄影机充当了真实事件目击者的角色。镜头传达出一种存在感,使观众仿佛亲眼目睹了日本渔民残忍屠杀海豚的场面。在其他电影中,摄影机也可以充当讲故事的设备。为了展示人类以外的生命在不受人类干扰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这些影片将人类观察者的存在感降至最低。纪录片March of the Penguins
用来自南极拍摄的纪实影像构建了近似“现实主义”的叙事,而The Adventures of Milo and Otis
则选择了一只橘猫和一条巴哥犬作为主角,在一个虚构的背景里讲述了重逢和归家的故事。这四种模式不是用来规范生态电影的讨论,而是帮助学者和观影者描述观影体验和参与审美活动的词汇。尽管每个模式都包含了具体的示例,但这些被用来作为例子的电影并不仅限于这些模式。一部电影可以通过多种模式观看。对于他人如何观看生态电影,我们所持的态度越开放,所能够挖掘到的——而非压制——电影潜在的丰富性就越多。
进行“受众研究”的最佳方式之一是“让我们去向他人学习”。在生态电影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正在通过参考观众的声音来研究生态电影的新的理解方法。这不仅承认了观众成员所具有的能动性,而且还允许学者向观众学习(这些观众不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了)。观众的成员能够,也经常,转换为公众的成员。通过促进学者和观影者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对代表了生态批评思想的共存意识更加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