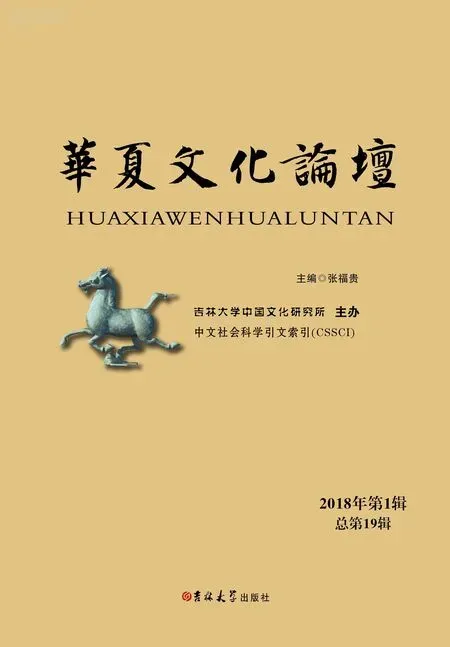世界文学与环境
[美] 厄休拉·K.海斯(Ursula Heise) 刘 倡(Chang Liu) 译
【内容提要】本文概括出探索世界文学与环境二者关系所要涉及到的几项主要任务,并侧重论述了世界环境文学经典作品的取舍这一“形态学”问题。通过讨论梅拉·蒙提罗的《在黑暗的掌心》,阿米塔夫·高希的《饿潮》,因德拉·辛哈的《人们都叫我动物》,以及姜戎的《狼图腾》,本文指出环境危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文化差异在理解生态问题时所造成的挑战以及跨文化思维在解决生态问题时所具有的优势。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生态批评以来,生态批评家所研究过的大多数文本都已在各自国别文学内的自然写作传统中获得了高度的认可——例如那些来自不列颠、德国、美国的文学作品——然而由于这些作品缺乏国际性的流通,从而导致它们没能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学的经典之列。探索世界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涉及到若干不同的任务,对每项任务的分析都各自伴随着一系列的挑战。首先,“世界环境文学”这一概念让人想起19世纪至今那些启发了环境主义思想家和环境主义运动的超越了自身背景界限为自然环境的保护挺身而出的作品。其中许多作品拥有全球范围的读者群体,比如从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著作,到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加里·斯奈德的自然诗歌,又如印度活动家范达娜·席娃和阿兰达蒂·洛伊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所创作的作品。然而大多数这些作品是通过它们所传递的思想来发挥影响的,而不是通过它们自身的美学价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作品依旧停留在人们通常视为“文学”的那个范畴之外。
第二项任务包含在世界文学作品中追踪与环境有关的思考,这些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虽然并没有直接处理有关自然的题材,但是它们对自然却有着某种先决的假设,尽管这些作品所集中关注的问题往往是自我、主权或是国籍。生态评论家承担了从莎士比亚、歌德、拉什迪这类作家的作品中挖掘这些观点的工作。第三类问题涉及到诸如威廉·华兹华斯,马里奥·安德拉德或埃梅·塞泽尔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倾向于非常明晰地点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却不是从环境主义的立场点出人类对自然景观以及其他物种所造成的威胁。这些作品也已经被生态批评家深入研究过了,假若不是通常着眼于它们的跨国流通的话。本文将承担起迄今为止尚未从生态批评家和世界文学研究者那里获得过多关注的第四项任务(尽管后殖民生态批评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迈步):为形成中的世界环境文学经典勾勒出一幅轮廓,此世界环境文学经典著作的范畴涵盖那些当下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在不同的文化间得以流通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旨往往是——但不限于——过去半个世纪的生态危机。
我将要讨论的文本全部是小说,原因在于此种题材可使环境主义作品最为便利地跨越文化的沟壑。以英、德、美三国的环境诗歌为例,它们各自都有着深远的传统,但这些作品的传阅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局限在本国的读者群内,迄今为止为数甚少的环境戏剧也是同样的情况。本文中我所关注的环境主义小说在文本最基础的情节层面上就建筑了文化边界、文化碰撞、文化误解等意识,从而得以在虚构的形式中探索诸如“自然”“生态”“污染”“动物”等基本概念何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拥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并由此导致在环境主义与反环境主义上的分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不同的文化视角对生态的看法是彼此互补的,且终能达成谅解;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却依然处于分歧的状态。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生态的问题与另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搅在一起纠葛不清的,而这另一系列的问题源自种族、民族、性别、国别、国际政治等因素对特定个体或群体与环境危机这二者关系的塑造。通过以此类围绕着“自然”这一概念而产生的文化与政治含义网络为参照,这些小说有助于突出文化差异在理解全球生态危机是如何自我展示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又该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将被我作为开启当代世界环境文学“形态学”(此处为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意义上的形态学)论述的小说样本包括一部加勒比海文本、两部印度文本、一部中文文本:梅拉·蒙提罗的《在黑暗的掌心》,阿米塔夫·高希 的《饿潮》及因德拉·辛哈的《人们都叫我动物》,姜戎的《狼图腾》。所有这几部小说所展现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环境危机这一情形而展开的文化视角的碰撞——或是就某些个案而言的文化冲突,这些情形中的环境危机有时候明确有着全球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又是隐晦的。古巴裔波多黎各小说家梅拉·蒙提罗和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通过读者熟悉的极端现代主义技巧中的平行视差这一手法呈现出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两位作家都把他们的叙述建立在了一位美国科学家的发展中国家之旅之上,以借此达到突出南北半球两种自然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辛哈迫使他的读者通过一位由于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而致残致贫的人物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并通过这个人物联系起其他为数众多的受害者,从而允许各种不同视角的涌现成为可能,其中的一位美国医生在这个框架之中显得尤为的异国情调。姜戎所展示的是来自城市的汉族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经历的——相对于汉族而言——十分陌生的内蒙古牧民的游牧生活,并试图将他们融进这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一种不一样的生态文化的扭转。所有这些文本都显示了不同文化模式与生态模式下的理解与译介都是紧密交融在一起的,尽管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
在这部《在黑暗的掌心》——一本被评论家称为加勒比海的第一部“公开的宣扬环保主义的小说”——当中,美国爬虫学家维克多·格里格前往海地寻找一只血红卵齿蟾的样本,这是蛙类当中极为罕见的一种,可能是仅存于世的唯一一只。他对此次搜索的叙述,同时还有他的回忆与反思,与他的海地向导蒂埃里·阿德里安的叙述交替出现。这位海地向导对海地的生态系统谙熟于心,他曾经见到过这种蛙,能带格里格去那个可能找到它的地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国族、教育背景以及家族史通过二者的对照而显现出来,由此导致了两种彼此不同的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的碰撞。格里格所体现的是西方科学所热衷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分类、编目以及保护,而阿德里安所体现的是第一手的观察、经验以及与当地动植物群的长期共居。格里格是受过教育的,因为他把自己的科学发现记录在笔记本上,把文盲阿德里安的故事和信息录在磁带上。他天真地以为他在科学领域的探索可以使他免于政治危险,以为“当一个人所寻求的全部仅仅是一只无害的小蛙,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极为严重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与之相反,阿德里安清楚地明白,政治立场的中立远远无法保证格里格可以安全的在这片处于几股武装政治势力斗争中间的领地里展开研究。他们之间的生态意识也是不一样的,格里格的关注所针对的完全是两栖动物种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濒危与灭绝,而阿德里安所知道的是某一地区内的更大范围的物种消失:“您想知道蛙去哪儿了。这个我说不好,先生,但是让我给您提个问题:我们的鱼儿去哪儿了?它们几乎全都离开了这片海,还有在森林里的野猪也不见了,还有迁徙的鸭子和用来充饥的鬣蜥,它们也走了,”阿德里安说。尽管他们所代表的自然观各不相同,但是二者在普遍存在的生态恶化感上汇合了。
是那种自然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的共性补充了作为小说背景的海地在生态与政治上所具有的特性。蒙提罗长篇累牍地强调寻找濒危物种在世上仅存的样本远非一名科学家个人的执迷。在海地,在他们徒步前往偏远的栖息地的路上,格里格与阿德里安遇见了另外一位生物学家,那是一位正在寻找一种极其罕见的雌株仙人掌样本的植物学家,该仙人掌名为叶仙人掌,仅有雄株存世。好像是格里格自己的笔记本上所记载的世上不同地区的濒危蛙类物种仍然不够似的,小说在各个章节里点缀着简要客观的插图,每一幅插图都就当前已经掌握的知识总结出从澳大利亚到瑞士、从哥斯达黎加到美国等地区的蛙类物种濒临灭绝或是彻底灭绝的情况。正是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动植物大规模生物多样性丧失,构成了蒙提罗小说中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相遇背景。
最终,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差异、受过教育和没受教育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全球性的灭绝景象面前统统变得黯然失色,因为它们均无法阻挡这一趋势。格里格与阿德里安终于找到并抓住了这最后一只血红卵齿蟾的样本,杀了它,把它准备成标本以便将来仔细研究。但是海地的政治乱局压倒了他们,这两个人出于不同的原因而被迫陡然撤离伊斯帕尼奥拉岛,于1993年登上了同一艘撤离的船。这艘船遭遇了暴风雨并且沉没了:“将近两千人在这场悲剧中遇难。科学家和他的海地助手蒂埃里·阿德里安先生的遗体下落不明。那个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的最后一只血红卵齿蟾的标本与他们一起在大海中遗失了,”小说做出了上述总结,在诸多分门别类地记载下来的灭绝物种名录上又简明扼要地增添了另一个物种的灭绝。然而即使格里格和阿德里安的相遇在科学上和生态学上都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自然世界的消失却依旧在短暂的时间里跨越了语言、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将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且不论这纽带究竟是何等的脆弱,这就是蒙特罗在其小说中所投入的叙事资本。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可能会由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勾勒出来,但是对大规模物种灭绝的感受超验了这些不同。
高希的《饿潮》所呈现出的文化-生态的碰撞在很多方面都与蒙特罗的小说是相互平行的,尽管高希小说的视角更为复杂,同时也引入了译介的问题。一位拥有印度血统的美国生物学家皮雅丽·罗伊,只身前往位于孟加拉湾的孙德尔本斯群岛去研究一种稀有的淡水豚。与格里格相似,她也得到了一位当地向导的帮助。这位向导是一名叫作福克尔的渔夫,他很像阿德里安,一方面他也是那样的目不识丁,而在另一方面,他对这一地区谙熟于心的了解以及他神秘的观察能力又弥补了他在教育程度上的缺失。但是在她的旅途上,她遇见了身为翻译与商人的卡奈伊·杜特。他来自德里,前往孙德尔本斯拜访他年迈的婶婶。对于习惯了城市环境的他而言,湿地的丛林比皮雅对生物学的热情还要更为陌生。他以翻译的身份为皮雅与福克尔提供服务,并试着让皮雅在兴高采烈地说着胡话的时候——“作为一名观察者,福克尔拥有超凡的能力。我希望自己可以告诉你在过去的那些天里跟他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那种感觉称得上是我生活中最最兴奋的体验之一了”——清醒过来。他干巴巴地回应道,“事实上他说了些什么你一个字都听不懂,是不是?”
“没错”,她点头以示同意。“不过你知道吗?我俩有着那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那并不重要。”
“听好”,卡奈伊用扁平刺耳的声音说。“你不应该自欺欺人,皮雅:彼一时你们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之处,此一时你们二人之间同样不存在任何共同之处。不存在的。他是一个渔夫,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所看到的动物种群在他眼中不过是充饥之物。……你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星球。”
读者或许会误以为这激烈的反驳是卡奈伊嫉妒的标志,因为显而易见他已然对皮雅产生了情欲上的兴趣。
然而一系列的事件印证了他的看法。次日,这一队人在附近的一个村落里发现了一只困在牲口棚里的孟加拉虎,还有一群想要将这只动物烧死的暴怒的村民。无比惊恐的皮雅想要找到一种办法来阻止这种在她看来毫无意义的杀生。她出现在福克尔面前讨要帮助,但他正忙着帮一位村民削尖用来杀戮的竹矛,仅仅把她从暴民那里送回到船上。“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一只点着了火的老虎,”皮雅惊叫着,在不自觉中暗指了布莱克的著名诗歌。第二天,她出于自己对福克尔自然观的错误解读而向卡奈伊道歉。“‘但是你期待的是什么呢,皮雅?’卡奈伊说。‘你当他是什么赤脚生态学家吗?他才不是呢。他是个渔夫——他以捕杀动物为生’”。“他说当一只老虎走进人类定居的地方,那是因为它想死”。然而杀戮的场景不仅揭示了科学的视角与村民、渔夫之辈的维持生计之道之间的差异,也同时突出了将动物视为对人类的威胁与将动物视为受到人类的威胁这两种针对动物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濒危动物的权利是该优先于那些赤贫人口的权利,或是反之?相同的思索出现在了小说另一条次要的情节中,背井离乡的印度村民试图在孙德尔本斯定居;他们所经受的驱逐与屠杀就摆放在印度政府的股掌之间,他们的这些遭遇提出了另一番迫切的问题,那就是当贫困人口与濒危动物为了满足相似的需求而相互争夺来自政府与环保主义者的支持。这些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被环境正义运动推到了台前,处在了该小说的文化与生态误译/互译的核心。
如果说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使跨域语言障碍的文化互译成为可能,而这一希望似乎又在火烧老虎的场景中幻灭了,那么小说在剩余的部分里将使这一结论变得更为细致入微。卡奈伊,那位通过他的叔叔所写下的文字深深地沉浸在该地区关于自然世界的传说里的多语种翻译家,尽管真实的野外环境令他气馁、转变,但他最终的计划是即使他将来回到城市,也依然要再次造访这片存在于野外的环境。皮雅计划在孙德尔本斯进行长期的研究项目,并继续与福克尔合作。他们二人在一次飓风中被困在了一棵树上,目睹了一只庞大的老虎潜入河水以躲避被风暴刮起的东西砸中,这与此前的那出老虎场景截然相反。但是其中的一个物体砸死了福克尔,留下皮雅一人与他的尸体困在一起,等待风暴结束:“就像是风暴赐予了他们那些生活所不能给予的东西一样;他们二人由此得以彼此融汇,合二为一”。虽然有一丝戏剧性,但是这一场景却再次强调了皮雅最初的直觉,那便是跨越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一种对自然世界的隐秘的存在主义的承诺而实现,因为是这股纯粹的自然之力将他们的身体熔炼在了一起。在福克尔死后,皮雅继续着她的工作,而卡奈伊则投身于书写他叔叔那本不同寻常的笔记本的故事:不论是对孙德尔本斯生态系统的科学的、人文的、神话的,还是叙事的探索,都能够在高希广阔的全景画里向前发展,尽管这一结局也指出了福尔克的土语话语以及通过直接与自然共存而获得的与自然的联系只能通过文字的书写才能留存。这一点也直接得到了来自小说结构的证实,皮雅和卡奈伊在小说的构架中充当着叙事视角的功能,而福克尔则不然:我们通过皮雅和卡奈伊交替的视角观看这个世界,而福克尔仅仅是被观看而已。
因此,高希不仅仅把自己从南北半球的二元并列中解脱出来,同时也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视角与本地视角二者之间的张弛和反差,进而向前推进了蒙特罗的叙事视差。因德拉·辛哈在《人们都叫我动物》这部小说通过迫使读者从在一场由美国人引起的环境危机中幸存下来的印度文盲受害者的双眼来看世界,从而进一步将蒙特罗的技巧推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Janvaar,又名“动物”,是在考夫波尔城(一个乌尔都双关语,为“恐怖”之意)——一座与博帕尔相对应的虚构城市——比穷人还穷的那群人中间长大的,1984年联合碳化公司的一座工厂在那里发生了爆炸,随之释放出的有毒气体旋即夺去了至少两千人的生命并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人们在随后几年里死去。之所以为自己取名为动物,是由于孩童时期他在毒气下的暴露导致了他脊柱的严重变形,以至于他只能四肢着地爬行,他拒绝将自己视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而这并非出自任何挑衅的意味。好似与接手了联合碳化公司的陶氏化学公司所展开的那场真正的谈判,考夫波尔城的居民们在灾难发生的二十年后依旧深陷在这场纠缠不清的谈判中,而“康帕尼”公司甚至不屑于派出一位代表来参加这场诉讼,更不必提就死亡、伤害以及不曾间断的用有毒物质污染居民的水井等事宜向受害者提供补偿了。
动物的不修边幅,以及他深陷在贫困、疾病与污染的泥沼中的讽刺生活,皆因一位名叫埃莉·巴伯的美国女医生在考夫波尔城开设的免费诊所而出现了不曾料想的转机。由于当地的领导人怀疑她与康帕尼公司狼狈为奸,从而导致全体居民对她的诊所发起了抵制,尽管这些人同时也迫切地需要医疗救治。为了来这里帮助弥补在她看来是由来自她的祖国的犯罪集团的鲁莽所造成的损失,巴伯放弃了她在美国的事业。而这里的文化对那些无所不在的不公正、疾病和污染所做出的回应在她看来完全是不可理喻的,这使她越发地怒火中烧:
“关于考夫波尔城的众多怪事之中最为奇怪的一件就是人们忍受了如此之多。看看吧。不仅仅是漆黑一片的街道和要命的交通,这座城市里的人们还容忍着敞开的下水道、随处可见的垃圾、有毒的水井、中毒的婴儿、玩忽职守的医生以及腐败的政客,以及数以千计的看似无人照顾的病号。但是等一下,让某个人带着一片至诚前来提供帮助,同样是这些居民对这件事儿却不能容忍了,事实上他们觉得这件事儿实在太无法容忍了,以至于必须要发动一场抵制运动。这座城市里的人想必不是瞎了就是疯了。我搞不懂考夫波尔人是怎么想的。”
来自北半球的访客的视角在这里是鲜有出现的,在这一罕见的视角转换之后(这种转变在蒙提罗与高希的作品中所占据的空间则更大些),不轻易服输的巴伯在自己的指导下向考夫波尔城居民发起了一场要求取消抵制运动的请愿,然而由于另一番误解,她把矛头指向了一个自始至终反对抵制运动的人。巴伯在试图让诊所运转这一事情上所倾注的精力与活力令她可以与一位名为安布罗西尼的上了年纪的法国修女相提并论。这位堪比特雷莎修女的法国修女自从毒气泄漏伊始便出现了精神障碍,然而她拒绝离开这座她度过了大半辈子的城市。经历了那一夜的创伤,她便失去了用印地语流利交谈的能力,事实上她所丧失的是法语之外的一切语言能力,而且只有法语依旧被她视为人类的语言。北半球在处理对南半球的经济与生态剥削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共鸣与施助的不同模式,这一切都通过动物的视角得以在此呈现。尽管动物看似是一个不具有任何能动性的人物,但是作为一个“流浪汉”式的人物,动物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有接触,并加速了一些核心情节事件的发展进程。
在动物这个人物身上,起初目不识丁的他,逐渐掌握了多国语言以及读写能力,尽管与打印相比,动物更倾向于把他的故事录在磁带上:“可说的东西很多……这世界上无声的语言纷纷涌入了我的头脑,”他在开始的时候坦白道,暗示着他在语言能力上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界限。他大声说道:
“哈!这个故事已经锁在我心中很久很久了,它挣扎着想要获得自由,我能感觉到它就要来了……当诗人卡伊夫·考夫波利年老体衰的时候,他的诗歌也一同在他的身体里干枯了,一个溃疡后来爬到了他的腿上,像一张大嘴张着不走,直到有一天它开始朗诵如此甜美的诗篇,是他的诗歌想从他的身体里喷涌出来。我的情况也是这样,一则由溃疡唱出来的故事。”
由于环境危机而形态扭曲失去人性的身体在这一景象中成为了传播叙事的方式。与其说是自然世界本身,更像是这具变形了的躯体在辛哈的小说中创造了一座文化的桥梁,创造了一种理解生态关系如何在广阔的文化与社会经济背景下自我展现的方式,以及理解它们将自己植入全球网络的手段。
目前为止,我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崛起中的世界环境文学所关注的均是南北半球不同视野的碰撞。但是接下来所要探讨的文本则不然。中国作家吕嘉民在2004年以姜戎的笔名发表了《狼图腾》这部小说。乍一看,这部小说所涉及的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主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位北京学生与内蒙古中部牧民的游牧文化之间的碰撞。尽管如此,二十种不同语言的即将出版或已经出版的译本——英译本《狼图腾》已于2008年出版——证明了这本小说的国际影响力。该书获得了诸多的文学奖项。此外,包括此书盗版在内的销量已在中国达到数百万册之多。学生陈阵迷上了蒙古族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与草原野生动物的紧密关系,他特别着迷于被蒙古族人猎杀与尊崇的狼。在某些时候,姜戎把这种碰撞发展成为较为愚笨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寓言,并以此把被比喻为狼的狂野、凶悍、强健、独立的蒙古族牧民与被比喻为羊的弱小、顺从的汉族农民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尽管后者在政治力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他们却没能成功地理解被他们占据了主导的草原文化。
通过圈养狼崽这种注定失败的方式以及其他一些手段,陈阵期望融入这个更为野性的、更为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狼图腾”的崇拜。陈阵的期望所唤起的这种反现代、反科技、反智慧的情绪——或者是这类情绪的残留——在很多先进的现代文化当中是并不陌生的。这些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狼图腾》所取得的超凡的流行,与此同时,这本书也不惜笔墨地在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与崩溃这些问题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书写——但是姜戎的笔触却不曾过多地提及任何来自现代环境主义的词汇。蒙古族人对狼、瞪羚羊、旱獭等动物的捕杀显而易见是残忍的,但却又是极度遵循原则的、并且充满了节制与克制;而汉族人为了筹备将草原转变为农用耕地而对各类动物所展开的杀戮则是不加区别的斩尽杀绝;二者被姜戎放在一起形成了对比。尽管西方读者很难不对姜戎所构想的男权主义和固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抵触,但是小说中很多蒙古族人物所说的话也很可能从现代环保人士那里听到。比如他们中的一位是这样说的:“我们蒙古人打了几百年旱獭,到这会儿还有獭肉吃,有獭皮子卖,有獭油用,就是因为草原蒙古人,个个都不敢坏了祖宗的规矩”——这种做法可以归属到西方环保词汇当中的“可持续利用”这一类。猎狼也是如此:尽管蒙古族猎手在他们的杀戮仪式上毫无仁慈可言,但当他们目睹了汉人是如何驾驶着车辆用新式的来复枪、毒药、陷阱等手段几乎不给狼群留有任何幸存的机会的斩尽杀绝时,蒙古族人惊呆了。正如陈阵惆怅地反思的那样,“紧张的人狼之战,忽然变成了轻松的娱乐游戏……称霸草原万年的蒙古草原狼,此时变得比野兔还可怜”。
一位名为毕利格的老人向北京学生所发表的一番关于蒙古族生活方式的长篇大论可能乍一看显得十分迂腐,然而在仔细分析之后却能够发现其中对生态理解与生态误判做出了相似的精彩思考。姜戎所探究的是侧重可持续发展的传统文化被肆意妄为地剥削自然的现代文化取而代之的这一问题,这一问题以及此问题以隐喻的形式向十年动乱所提出的批判引起了诸多中国读者的共鸣。但是对姜戎的国际读者而言,是这种对现代化进程对生态系统和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改变进行更为宏观的反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当陈阵重返内蒙古的时候,距离他的学生时代已经过去了三十个年头,他发现狼群灭绝了,这里的土壤遭受着侵蚀,地表也已经沙漠化了,牧民的游牧文化也成为了过去:
“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
正如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告诫人们的那样,地球上的生命正经历着历史上的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地球上现存的六千种语言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在快速的消亡。在这种被不同的文化广为体验的悲叹之中,姜戎将《狼图腾》作为一首挽歌献给了消逝着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可以说,这便是此书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出于它们将生态危机与跨文化的碰撞所交织在一起的方式,近年来在国际上流通的其他一些作品可以轻易地为我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几本书提供补充。在与衰败的自然世界的相遇中,这些文本指出,通常由语言的误解和误译而造成的文化差异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生态世界主义”的出发点,从而动员多种多样的文化资源来应对环境问题。在蒙特罗和姜戎的小说中,这种“视野的融合”依然是暂时的,所以最终无法阻止生态的衰退,然而在高希和辛哈的文本中所萌发出的更为持久的联盟以及面向未来的展望至少有了一个轮廓。暂且不论这些生态世界主义的场景是如何自我呈现的,这种场景表明了那些在国际上流通的文学作品为探讨日趋紧迫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所。与之相反,它们也表明了世界文学开始接纳了越来越多的明确包含着生态与环境维度的作品。尽管人类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在《吉尔伽美什史诗》《李尔王》《丢失的台阶》等世界文学名著中清晰可见地出现在背景当中,而这些系统性的关联在近期涌现出的一系列虚构性文学作品中被推到了最前沿,这些作品走出了它们的归属地,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