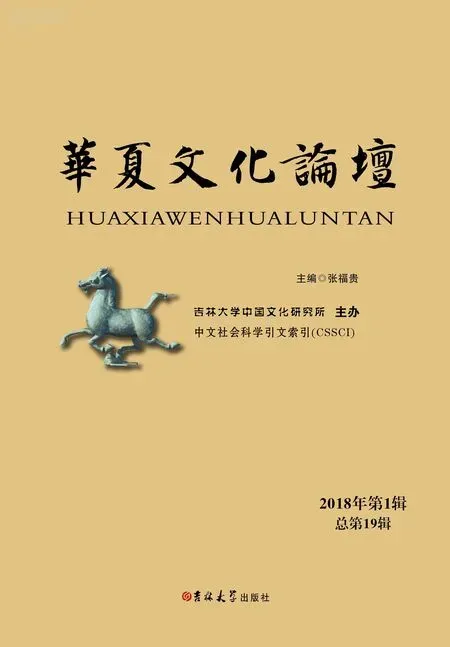跨国及跨文化视角下的生态学与生命写作
[德] 阿尔弗雷德·霍农(Alfred Hornung) 王小木 译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我认为自然与文化的相互性是生命写作流派的一个例证。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作为浪漫时期这一相互关系实际应用的典范,覆盖了我以跨文化和跨国界的视角对于4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美国、亚洲、加拿大等国家与地区有关自然与生命的表述中对于生态思考的全面考察。根据梭罗对亚洲资料的解读以及他与原住民生活的关系,这一研究包括了对以下内容的讨论:中国诗人陶潜(365—427)的诗歌,明代(1368—1644)中国的园林文化,泰莉·坦皮斯特·威廉斯的女性生态主义作品《避风港》(1991),高行健的《灵山》(1990年),喜马拉雅山脉藏族村落中关于大山的生命写作,以及加拿大籍日裔动物学家戴维·铃木的生态作品。
人类生命的自然过程符合所有生物普遍共享的自然循环。所有有机生命的进化原则,如果没有被人为干预所阻止,也意味着自然的终结。很多人努力延长这一自然周期并坚持到最后。文化的形成以支持或对抗的形式伴随着自然界的有机过程。总的来说,文化的任务是商讨潜在的干扰并建立确保生命在地球上的延续。
一、作为生态文体的生命写作
自然和文化的关联性可能在生命写作这类囊括了对人类生活所有形式表现的文体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比如自传、传记、日记、画像,新社交媒体中的博客和自拍,旨在捕捉叙事结构和具体图像中的短暂瞬间和生命进化阶段。历史上,代表生命过程的隐喻各不相同。因此,Peter Alheit区分了五类用于主体立场的隐喻:中世纪生命世代循环的思想;16世纪向上或向下的拱门或阶梯的隐喻;现代资产阶级假设在职业生涯中的上升线;在工业性作业中后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后现代时代的拼图或拼接物。焦虑导致了各种自我表征和精神分析的解读,这些焦虑与生活中上升与下降阶段有着无法回避的关联,并以往往体现为中年危机的经历。例如,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假定生命分为第一与第二两部分,并把生命视作从自然向文化,从个人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生物因素向跨越个人意识中更为永久的精神成分的过渡。这种转变与通过回顾所带来的重新定位有关。荣格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一切顺利,保守的倾向会得到发展。人们不会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由自主的。人们也开始考虑生命发展到现在的方式。因此,真正的动机得以被寻求,真正的发现得以被进行。对自己和命运批判性地审视使得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个性,但这种认识并不容易得到,而要通过最严重的冲击才能获得。
自传作者与自传评论家都已意识到并评价了这种对生命所做的个人评估进行回顾所具有的幻像特征。天主教堂圣奥古斯丁神父用他的作品《自白》(397—400)从永恒的角度来研究时间;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构想的个人生平的回顾成为了他的《自传》(1771—1790)第二版中的修改内容;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他的自传《诗歌与真理》(1811—1833)的题目中就强调了幻觉与现实的相互作用;自传评论家Roy Pascal以歌德的观点为他的学术著作《自传中的设计与真理》命题;后现代评论家Ihab Hassan认为自传是一个“不可能的”“致命的”“被鄙视的”写作形式,其秘密主题是死亡。与这种存在主义的观点相反,作为向重生的过渡,死亡的浪漫解读也是人类生命过程与自然循环过程相关的出发点。
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为自然与文化的诗性关联展现了典范。在这一系列自传体散文中,作者将两年零两个月(1845—1847)的实际经验浓缩成为一年,并将这种生活体验与季节循环协调起来。梭罗的生命写作始于他的小屋建成的那个夏季,经历了秋冬两季,并以大自然在春季的重生结束。季节的自然循环以类比的形式服务于叙述中对于生命更迭的诗意化的描述。一个相关的特征体现在政治这一方面,有爱国精神的自我在七月四日搬进小屋,并以此宣告他自己的独立宣言。这些将肢体的经历和政治信仰转化为自然进程的诗意的过程,与超验主义的哲学思想相一致。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设计让梭罗超越了具体经验的现实细节,将他在瓦尔登湖的地区视野扩大到跨文化/跨国界的背景。在他的生活叙述“结束语”部分,梭罗提到非洲、南美洲和中国,只是建议他的读者在自我想象中成为“一个新大陆和新世界的哥伦布”,“一个居家宇宙学专家”。
亨利·戴维·梭罗和他的生命写作《瓦尔登湖》被视为有关生态关注的重要文本和主要表达方式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仅是马萨诸塞州瓦尔登湖旁他那个被重建了的小屋变成了环境神殿,以及向自然表达敬意的场所,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所有生态批评学术研究的起点。就我的目的而言,梭罗和《瓦尔登湖》为生命写作中自然和文化的相互关联,生态与生命写作的一致,提供了完美的起点。同样,Hubert Zapf支持协调的认识论和伦理价值,这种协调体现在文化生态与“符合自然和文化,人类和非人类世界基本关系的生命写作形式”之间,他还“强调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群体中,文学知识在生产与接受是处于跨国纬度和全球互联的背景下的”。因此,梭罗的作品不仅在浪漫主义的模式下将整个宇宙融入到他个人的生活当中,同时他对亚洲哲学的阅读以及对美国本土生活的观察使《瓦尔登湖》变成了一个生态全球主义生命写作项目。
二、梭罗的生态全球主义模式
亨利·戴维·梭罗在他的生命写作实践中诗意地再现了他对自然界进化过程的关注,这与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中发展的进化生物学,以及德国动物学家Ernst Haeckel(1866)于1866年创造的用于描述生物环境和家务形式的生态学术语相一致。20世纪晚期对“人类生态学”的规范,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运动之前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支持了对生态作家的研究。终于,生态批评得以形成,从美国传播到欧洲,并由欧洲的Hubert Zapf发展成为文化生态学。对于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的研究自然而然地从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所例证的浪漫主义模式开始,逐渐进入了被忽视的现代主义中的大自然和原住民栖息地,最终将重点落在了处在20世纪之交的后现代及后殖民背景下日益严重的环境危害和由此带来的人类疾病。21世纪对生命的关注包括对所有生命机体的关注,对深层生态学的促进,以及跨文化跨国界视角下对地球视野的预测。在下面的章节中,我的讨论将以美国、加拿大和亚洲为例,强调在跨文化跨国界的层面上生态学与生命写作的相互关联。
在梭罗的《瓦尔登湖》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经验构成了整体的超验自我,得到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并在最近得到了来自对自传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研究的补充。在世界范围的受众中,亚洲读本对梭罗就自然和自我的定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印度哲学的印度教经典。此外,Birgit Capelle“指出对于时间经验的叙述表现出与佛教和道教对于时间的诠释极为相似”。与单向的基于行动的时间顺序概念相反,道家主张“无为或不作为”以及基于周期性的时间观念的观点。在引用《瓦尔登湖》的过程中,Capelle认为梭罗是“跨时代的幸运存在[…]像觉悟的佛陀”。
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的余地。有时候,在一个夏天的早晨,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伊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者默不作声地疾飞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或者远处公路上传来一些旅行者的车辆的磷磷声,提醒我时间的流逝。我在这样的季节中生长,好像玉米生长在夜间一样,这比任何手上的劳动好得不知道多少。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超出了许多。我明白了东方人所谓沉思以及抛开工作的意思了。大体上,虚度岁月,我不在乎。白昼在前进,仿佛只是为了照亮我的某种工作,可是刚才还是黎明,你瞧,现在已经是晚上,我并没有完成什么值得纪念的工作。我也没有像鸣禽一般地歌唱,我只静静地微笑,笑我自己无尽的幸福。
对梭罗来说,这种自然界的生命形式是不间断的“造物之诗歌”的一部分,他在他的生命写作中重复了这些特点,这是他自己的造物之诗歌。Bernhard Kuhn实际上称他为“诗人-自然主义者”,他认为“在自然界中,从无机到有机表现自我的创造力,与赋予梭罗生命和生命写作的创造力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造物之诗歌与库鲁艺术家的态度和成就类似,这种永恒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员工梭罗,他在“结束语”中提到:“单一的目的与决心,高度的虔诚,在他不知情的条件下将永久的青春赋予了他。由于他对‘时间’毫不妥协,‘时间’为他让路,只能在远处叹息,因为他无法战胜他”。
三、道教与自然中的生命
梭罗对于沉思生活的实践是在一种无限循环的孤独的自然过程中进行的,这符合中国哲学家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老子在孤独的自然中坚持生活的隐逸,是不同于儒家哲学在公共生活和集体社会的纪律和行为的另一种选择。早在欧美浪漫主义之前,中国诗人就已经形象地宣扬了通过归隐于自然的孤寂生活以实现道教的信仰。尤其是生活在魏晋时期的伟大的中国诗人陶潜,又称陶渊明(365—427),为回归自然隐逸的生活而辞去官职,用他的诗歌将道家生活方式和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进行了比较。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早于亨利·戴维·梭罗1500年,中国诗人陶潜就已经对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在生命写作与生态之间的互动进行了预示。像梭罗一样,陶潜自传式地将他为了自然而放弃公共生活和自己有意识的决定联系起来,类比了自己的本性和自然景观:“性本爱丘山”。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第一章里所写的,他将“简单”奉为自己的经济原则,即使他的家比美国人的小木屋宽敞得多。相比于集体的生活,他更推崇隐居和农耕,并选择了一些土地耕种。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异化于周遭的世界。若隐若现之间他仍然能看到村庄中人们家里升起的炊烟,听到狗吠和鸡鸣。与其被人类活动繁忙的生活所束缚,他更享受自己生活的闲暇,并乐于“回归自然”。这种对自然的回归既是指他自己的本性,也是指实际的自然环境。根据张隆溪的观点,这种自然概念是指老子哲学的“自然理念”。与儒家行为相比,他认为“道家哲学家主张无为,或者说不作为,就是让自己的行为不受干扰,让事物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发展”。这种不作为状态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为生命的沉思方式提供了特权,相当于梭罗的“高等法则”。这个真理也作为“未受干扰的造物之诗歌”被包含在梭罗的自然观中,既在中国有着千年传统的园林文化中找到了其对应的部分,又在陶潜的诗中有所体现。
在中国园林文化中,创造一个大自然的微缩版本在传统上是服务于从官职隐退之后的生活,而生命的园丁们追求的目标是取得水、植物、山石和建筑之间的平衡,以达到放松和冥想的目的。这些皇家园林工程最初是为中国的皇帝而建造的,在11世纪至19世纪间被私人、退休的官员、学者和知识分子所模仿,并在明朝(1368—1644)达到顶峰。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规划景观的努力似乎预示着梭罗的造物之诗歌既是整体园林环境中的生命,又是生态生命写作的表现:
将自然景观转化为园林文化的实际工作,辅以各类精神文化活动,例如诗歌、绘画、书法、音乐、古典文学研究和禅修。花园里的许多凉亭都是供个人休息或集体聚会的地方。人类建筑和自然艺术的摆放遵循所有元素相互依存的整体和谐设计。
从早期中国诗歌和园林文化表现出的沉思生活及道家哲学崇尚的不作为到梭罗的《瓦尔登湖》所体现的具有超验主义思想的生态生命写作,这一主张生物界所有生物和谐互动的思想脉络在20世纪深层生态学运动中得以重现。当现代科技和城市生活方式对人类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甚至威胁到对地球的保护时,这些深刻的生态思想浮出表面便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从对自然看似奇异或陌生的方面进行发掘和欣赏,看出人们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例如在Mary Austin《The Land of Little Rain》(1903)中出现的美国原住民的栖息地和沙漠,或者B.F.Skinner在《瓦尔登第二》(1948)中规划的乌托邦社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环境运动之后,作家们以身心疾病比喻大自然的毁灭。生命写作与生态的结合目前正在为人类与物质的自然提供弥补和治愈。
四、疗愈自然与生命
泰莉·坦皮斯特·威廉斯的《避风港》代表了当代一个生态与生命写作之间进行类比的例子,其中对自然的“非自然”对待是主要话题。在她的人生故事中,这位犹他大学环境人文学学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将她的家庭及他们所在的摩门教徒居住地与位于美国西南部以大盐湖和沙漠地区著名的犹他州生物环境联系在了一起。盐湖的水位和邻近的鸟类自然栖息地构成了全书的各个章节,而上涨的水位预示了鸟类的生存危机。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洪水毁掉了大熊河候鸟保护区后,威廉斯哀悼着穴鸮的消失,对她来说“这种鸟可以用来评估生活”。所有有机生物之间亲密的相互关系是作者的重要线索:“鸟类和我分享自然历史,这是牢不可破的事,是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心灵和想象力的融合”。对这种和谐环境造成的干扰同样影响着当地居民。“[…]从1951年1月27日至1962年7月11日在内华达州做陆上核弹试爆”,由此引发的湖水泛滥及对鸟类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相当于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基于所有有机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威廉斯感到湖水水位上涨造成鸟类消失,正如核试验场所与患癌比例有关一样。在序言和后记“单乳女性部落”中,她将痛失的七位家庭成员连在一起,包括她的母亲、祖母和外祖母,以及她的兄弟。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她提到多年来在梦里常看到“夜晚的沙漠里有一道闪光”,而父亲提醒她,她曾于1957年9月在公路上听到过一次爆炸,看到了蘑菇云,其落尘导致了对大自然的污染,也毒害了当地居民。尽管被教育要做一名顺从的摩门教女子,她仍然决定与其他九位生态女性主义者“按照郊狼、敏狐、羚黄鼠和鹌鹑的暗示”非法进入试验基地。当她们由于这一“公民非暴力抵抗行为”被捕时,十位女性开始同唱“他们[印第安]姐妹的声音飞过高山”。
在序言中威廉斯记录了一个大盐湖的发展和倒退的自然循环,这里本是大熊河候鸟保护区,被洪水破坏后,开始恢复,这也使她在自己的一代人中走上类似的循环。
正如我试图重建我的生活,志愿者们开始重建沼泽。我坐在书房的地板上,周围都是日记。我打开它们,羽毛从页面落下,沙粒撕裂了书脊,白纸上的段落间压着的鼠尾草的嫩枝增强了我的嗅觉——我记得我来自哪里以及它如何影响我的生活。[…]我借着说这个故事来治疗自己[…]。
鸟类重返自然栖息地,这增强了泰莉·坦皮斯特·威廉斯对各种有机生物相互依存的信念,也引发了她的生命故事:“我曾一直退却,这个故事使我回归”。
为了通过重新融入有机生命循环以达到疗愈的目的而退居自然这个避难所也激发了高行健沿长江而下的旅程。高行健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灵山》中回忆了这段经历。这位出生于中国,在1988年移居巴黎的作家和剧作家,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父亲罹患肺癌过世,而他于1983年也被确诊患了肺癌(不过后来的一次检查将这一检查结果证实为误诊),之后他便决定离开北京,去到位于南部的四川省偏远林区进行自然疗养,从位于喜马拉雅山的长江源头沿江漫游而下至东海,历时十个月,行程总长1.5万公里。这本代表了这段人生路程的书于1983年在北京开始创作,至1989年高行健移居巴黎后完成。尽管自传人物以三股叙述话语进行自我陈述:客观的叙述者“我”,热情的叙述者“你”,还有一个中立的叙述者“他”(也包括“她”),而且因为这个叙述是由“游记,随口说教,感受,笔记,随笔,胡乱讨论,不像寓言的寓言故事,[…]一些民歌,[…]一些貌似传说的胡言乱语[…]”混合而成的“所谓的[…]小说!”,所以它不符合任何西方或东方的文体,但是生命写作和生态学之间的类比是最重要的。在一次采访中,高行健肯定地说:“在除了自然以外就别无他物的环境中生活了五个月之后,我的小说《灵山》见证了我的幸存。”这部作品的标题本身就代表了他在第一章所讨论的精神生活之旅,它使“生态学家”和“原始荒地”保持着密切接触。他从肺癌和其他约束的多重生命威胁中得以康复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与当地少数民族、佛教僧侣和道教哲学家的自然接触。正如梭罗和威廉斯与原住民有联系一样,高行健从居住在山区和长江沿岸的羌族、彝族、苗族文化以及他们整体自然的生活方式中学到了东西,他也接受了他们的佛教信仰。高行健转而探寻佛教和道教,并重新发掘了传统中药的潜力,这与儒家戒律形成鲜明对比。作为治疗的一部分,高行健的朋友向他推荐气功疗法,这是一种源自道教,以治疗为目的,将体育锻炼和冥想结合在一起的传统运动方法。这种基于自然资源对整体中国传统的信赖也体现在《灵山》这一精神之旅的整体特征和高行健的叙述结构上,这种结构重复了论述老子道家思想的《道德经》(共计八十一章)。
五、跨本土区域的环境联盟
高行健曾去过的四川省有灵性的群山风景,似乎代表了生命写作和生态学近乎完美的融合。这里也是藏族人的自然栖息地,他们至今仍在喜马拉雅山上放牧牦牛,过着游牧生活。风景、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用闪光的白色字体写在山壁上的佛经中的神圣词汇。五彩经幡,转经筒,以及进烛焚香的习俗,这种自然中富有灵性的生命形式是亚洲崇拜自然的一种表现。总之,这些对自然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展现可以理解为在群山之上,以藏文咒语的形式体现了生命写作的包容性,这咒语象征了建立信众团体的神圣脚本,也表现了人和自然中的一切元素的关系。山壁上的神圣经文,即是生命写作所表现出的精神富足,同时那些飞舞的经幡、仪式性地旋转着的经筒也跨越了不同的界限。这是所有有机生命相互联系进而扩大到与宇宙相联的信仰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及美国的原住民社区里也发现了这类信仰。这种原住民的生活形式与日裔加拿大籍动物学家戴维·铃木和他的合著者Amanda McConnell一起制定的深层生态学理念有共同之处,他们试图恢复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并重获一种神圣的平衡:
每种世界观都描述了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万物相关。星辰,云朵,森林,海洋,和人类都是一个单一系统中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系统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孤立存在。[…]许多世界观赋予人类一项更加伟大的任务:他们是整个系统的管理者,负责保持星辰按轨道前行,生活世界完整无缺。通过这种方式,很多早期创造了世界观的人们构建了一种真正的生态上的可持续、可令人满意且公正的生活方式。
在原住民习俗和自然生活中清晰可见的跨文化和跨国界的相互关系,这是加拿大日裔动物学家戴维·铃木在中年时期认识到的寰宇视野的前提。在他的生命写作中,他也倡导相互依存的信条。在《变形记:生命中的阶段》和《戴维·铃木:自传》接连两本自传中,他把自己从一个对遗传学感兴趣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跨国生态活动家。虽然铃木在他五十岁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时候完成的《变形记》里回忆了珍珠港事件,他们全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同时也回顾了他职业生涯的发展,但是在《自传》中,他将重点转移到了与原住民相遇后进行的跨国界跨文化分析中。在《变形记》中,他将常见的果蝇(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与人类生命联系起来:
三十年来,果蝇一直是我生活中的激情。在反思它们的遗传、行为和生命周期时,我已经在许多方面都看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变化与苍蝇生命中发生的显著变化阶段相同。所有的生命形式都通过DNA从祖先那里获得基因遗产,这是塑造我们的化学蓝图。
这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科学并将人类与动物有机体进行类比是早期一种对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含蓄承诺。它最终与铃木的政治意识紧密相连,在他的第二部自传中脱颖而出。他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呆了两年(1961—1962),在此期间,对于非洲裔美国人在民权运动中的诉求表示的认同,这也让他认识到在“原子城”核武器发展中的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在北美和纳粹德国被过度传播滥用的优生学所产生的弊端,这为他看到他与原住民之间跨文化的联系做了铺垫,那是他与父亲的一次蘑菇采摘之旅,在弗雷泽河沿岸,靠近波士顿巴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山区:
我感到惊讶的是,与我父亲相比,我觉得自己有些紧张。我是一位年轻的遗传学教授,从来没有见过原住民,只在媒体的片断中了解过他们。我对爸爸的朋友或他们的背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爸爸很放松,很容易就接受了他们是在鱼类、树林和自然方面与他有共同兴趣的人[…]。
当回忆在自然中与原住民接触的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把学界中科研与教学视角的果断改变与一个更广阔的框架联系到了一起。一方面,他认识到“我们共同的基因遗产”和“我们的身体特征”, “让原住民立即变得更容易接受”他,也让他看到了过去和现在的亚裔人群之间共同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邀请,于1979年将他的课堂教学扩展到面向电视观众,作为主持人加入了CBC电视台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事物的本质》,这档节目涵盖了广泛的科学和哲学问题。相信一切有机生命和跨文化原住民族群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他关注环境的基础,也为构想生命写作中的生态使命和计划搭建了平台。
铃木的《自传》共十八章,其中有十三章描述了生态项目,其范围从加拿大原住民的环境工作到巴西、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雨林中的原住民生活。特别有启发性的是以他的电视节目《事物的本质》为出发点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群岛及亚马逊地区的原住民展开的联合项目。在《自传》第六章中,铃木讲述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这部作品是关于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夏洛特皇后群岛上的一片美洲雨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岛的自然栖息地受到岛上毁灭性采伐的威胁。在本土环保主义者与伐木公司的斗争中,戴维·铃木基于共同的基因遗产,支持源于自然的海达人文明。这些海达人在加拿大海岸附近的岛屿上保留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以自然为基础的群落生活方式形成的共同纽带联系起了巴西雨林,在那里铃木的环保组织与海达活动家Guujaaw通过一起巡游的形式以支持亚马逊地区原住民与森林砍伐之间的斗争。这些初步接触最终发展成为植根于巴西和加拿大的联合项目及共同环境活动:“加拿大原住民明白,卡亚波人正在经历他们自己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于是立刻感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巴西和加拿大公民之间这种跨民族的联系,使铃木得以成立一个跨国环保组织以及戴维·铃木基金会。对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雨林及原住民族群的进一步探访,完善了铃木努力促进的生态全球化方案,并使他能够影响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及京都气候变化公约所做的政治决定。他的目标是全人类结成联盟并以保护地球作为共同目标。他在科学和人类学方面的领悟转化为一个生态计划,同时也是Ursula Heise所说的“生态世界主义或环境世界公民的理想”的发展基础。
对于亚洲、美国、加拿大从四世纪到21世纪关于自然和生命的写作的研究显示了不同地理位置处理所谓的自然文化鸿沟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在所有情况下,生命阶段与自然进化循环的协调超越了固定的政治或文化框架的狭窄边界,提供了跨文化的视角。为了放松、获得安慰或休养而回归自然,往往使人发现在自然环境中保存的原本的生命形式族群,从而获得新的见解。在这些经验的斡旋下,各种各样的生命写作似乎成为了表达生态关注的特权模式,并产生了一个以信念团结起来的全球公民跨国联盟,他们相信生物界的共同有机基础及参与保护地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