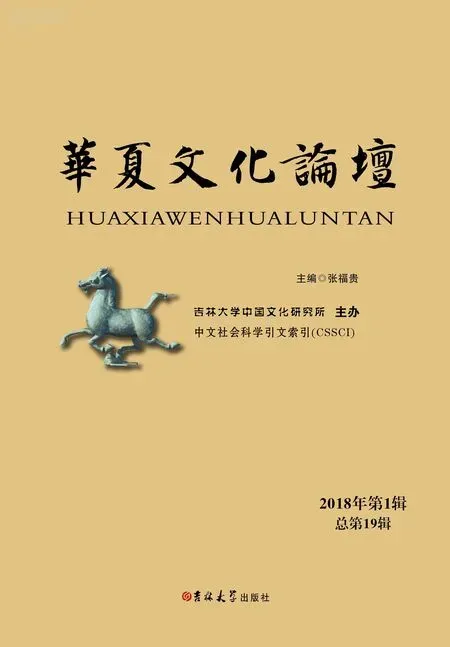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向
刘 倡(Chang Liu) [德]蒂莫·穆勒(Timo Müller)
【内容提要】生态批评可以理解为一门旨在以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对文学文化进行解读的学术领域。在生态批评诞生至今的短短几十年里,它已经从最初的一股小范围的学术风潮发展成为一门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通过梳理欧美生态批评运动的发展规律,本文试图为中国的生态批评指明发展方向。根据对杨金才、李程、布依尔(Buell)三位学者就中国生态批评的现状与未来所展开的论述,本文指出中国的生态批评的发展体现出两大方向:其一,以欧美生态批评为参照,译介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与文学作品,从而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展开对话;其二,基于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以及自身的历史特性,开展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创新。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来自欧洲和北美地区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以一种可能危及到人类未来生存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空气、土壤和水源的污染;动植物种群的灭绝;核能源潜在的危险;全球气候变暖:这些问题逐渐出现在公开的辩论中,并促成了一场充满活力的环保运动。尽管文学自始自终都是表征自然与解释自然的核心工具,但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研究可能对这些争论作出重要贡献这一点的认识却是相对滞后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形成了一种系统地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如今以“生态批评”这一名称为人所知。
“生态批评”一词是由学者William Rueckert在1978年首次提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呼吁文学研究者将他们的研究视为声援环保活动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观点被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生态批评著作所认同。Lawrence Buell、Cheryll Glotfelty、Karl Kroeber和Glen Love等该领域的先驱性代表人物都坚信,文学能够且应该让人们更接近自然:这一点是通过提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而达到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述,使读者对自然的美感和价值产生较为敏锐的感知。实现此目标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新界定哪些文学作品可以归为经典文学著作之列。早期的生态批评家推广了那些符合环境文学标准的时期、体裁和作家,例如浪漫主义时期,对自然的非虚构性写作,以及像John Clare、Henry David Thoreau和Wendell Berry这样的作家。早期生态批评的目标不亚于在现代思想和行为中发起一场革命:从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向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进行转变。
自21世纪伊始,早期生态批评的目标、论点和预设便开始不断地被修正和扩展。在生态批评家之间,最先引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对“自然”的定义。自然一词在西方传统中被用来表达许多不同的概念。宇宙中物质生命的整体;地球上的有机生命;一切非人类的事物;所有非人工制造的事物;未受到人为影响的一切事物;平衡和谐的生活秩序;事物应有的状态;事物真实存在的状态;人性的本质:所有这一切都曾被称为“自然”,尽管其中某些定义彼此相互矛盾。
早期的生态批评家谈及自然时并不总是清楚他们所说的自然为何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倾向于假设自然是每个人都直接以同样的方式所体验的事物。这种普遍的假设可能是由于这些批评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他们来自现代的英语语系社会,是相对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21世纪初,随着生态批评运动开始向这个小圈子的外延扩展,这两种假设的谬误便越发变得明显了。Dana Phillips和Timothy Morton等学者指出,我们对自然的体验是以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思想和期望为指导。来自其他族裔和国家背景的学者提高了人们对自然观念的文化特殊性的认识。例如,美国原住民与自然的关系比起那些将美洲土地视为荒野并前来征服控制这片土地的白人定居者与自然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日益增长的就文化对自然环境的界定能力的强调所引起的两种发展将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对生态批评与环境写作进行思考。一方面,它将生态批评的范围从文学扩展到了更加广泛的文化。今天,学者们研究各种文化因素在环境问题的协商中所做出的贡献,例如音乐、电影、电视,以及政治、经济和宗教话语。所有这些都隐秘或明晰地包含着关于人类生命与其环境二者关系的信息。大多学者现在都同意,这些信息不仅影响了我们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也影响了我们对所居住的世界的看法。这种从文化协商的角度对自然展开的研究通常被称为“环境研究”或“环境人文学”,这些术语试图将生态批评的范围扩展到文学批评之外。
其次,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看法背后的文化特殊性,这种日渐增长的觉悟把环境正义问题推向了生态批评的前沿。“环境正义”一词是指人们在环境问题的范畴内针对侵犯平等与自决等基本原则的思考。环境污染的益处和风险的分配往往是不平均的,例如,那些在遭到污染的环境里受罪的人并不总是那些制造污染的人。即使那些看似亲善环境的做法也会使这种不公正的现象长期存在。例如,假设政府试图通过借助水力发电取代煤炭的方法来减少对空气的污染,那么修建水坝和人工湖可能会导致相关地区的原住民颠沛流离地搬出他们的原居住地,然而空气污染主要是由富裕的城市居民与他们不成比例的能源消耗所造成的。
这些例子表明,环境问题往往是与全球现象联系在一起的。生态评论家需要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视野。如果他们局限于颂扬地区性的风景,他们就会遗漏全球生态系统这一重要层面。如果他们局限于抽象地讨论全球环境问题,那么他们就会遗漏这些问题在特定区域(和文化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地方意识”和“星球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是当今生态批评的核心问题。要提高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方法之一便是扩大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绝大多数生态批评家仍然来自西方国家,他们大部分的研究内容都集中在关于西方作家和西方世界的问题。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将为拓展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并对生态批评的某些前提假设发起质疑提供一个宝贵的契机。
期待中国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在这一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合情合理的。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Lawrence Buell表达了类似的期望,并坚信中国生态批评家在进入生态批评运动时将大有作为。Buell的信念来自对三个方向的观察。第一,Buell强调通过在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内部寻找资源,人们可以发现值得通过生态批评视角进行研究的材料。第二,根据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杜维明关于新儒学与环境的研究,Buell指明了中国本土哲学对生态批评可能做出的潜在贡献。第三,中国现代化的独特经验也保证了中国生态批评家可以为这一学术领域带来独到的见解。Buell为中国生态批评所设想的蓝图既是具有说服力的,又是令人值得期望的。然而,中国生态批评家的所作所为却与这一蓝图有所不同。
Simon Estok与Won-Chung Kim合编的East Asian Ecocriticisms: A Critical Reader
(东亚生态批评:一部批判性导读)在这一领域中称得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这本书中,Estok与Kim召集了中日韩三国学者,让这些学者自己发声,与更广阔的国际性的英语读者展开对话。该书关于中国文学的部分以杨金才的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当代中国文学与批评中的环境维度)一文开始,在该文中,杨金才指出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1)重述;(2)比较,跨文化理论化;(3)中国文化生态研究;(4)外国文学研究”。在一篇发表于一年后的论文里,李程指出了中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两大障碍,从而补充了杨金才的观点,这些障碍是:第一,与生态批评相关的美国文学文本和学术论文没有被及时地译介到中国;第二,生态批评这一学术范畴内的一些分支领域尚未在中国的生态批评领域里得到发展。李程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学者,并批评他们“保守”,批评他们代表了“城市中产阶级汉人的偏见”。李程对中国学者的描述更像是一种未经批判的假设,而这种假设本身便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中国后革命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男性气质危机以及女性知识分子在学术话语中的式微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挑战了李程的假设;而汉族、少数民族、国家政体三者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从批判性汉族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复杂化李程的论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程对性别和民族不加批判的假设再次证明了他所呼吁的中国生态批评需要提升性别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迫切性,并为西方女性生态批评理论和环境正义批评进入汉语言文学研究铺平了道路。杨金才和李程的研究表明,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与Buell的预测并不完全一致。与其通过从自身内部寻找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答案,中国的生态批评以美国的生态批评为原型,力争达到理论上的复杂性,展开跨国对话,并急切地着眼于中国的外部,想要在西方生态批评的话语中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
出于不同的原因,来自世界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值得注意的。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与Djelal Kadir三位学者主编的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收录了Ursula Heise撰写的一篇题为《世界文学与环境(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的论文,这篇论文把中国作家姜戎的作品《狼图腾》送进了形成中的世界环境文学经典作品之列。尽管Heise的论文在这本厚厚的世界文学参考书当中只占据了薄薄的几页,其意义确实非常重大的,因为Heise和几位编辑把中国环境文学带进了世界文学的讨论范畴之中,并强调了对何为文学经典这一问题进行反思。两年以后,来自拜罗伊特大学的美国文学文化研究学者Sylvia Mayer为该校美国研究以及跨文化英语语系文学文化研究等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一门名为“生态与文化多样性:世界文学与环境”的讨论课。这门讨论课的内容涵盖了具有代表性的批评理论以及对文学文本的分析讨论,其中所涉及到的文学文本便包含了姜戎的《狼图腾》。这些学者并不是经过专门学术训练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环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却有一点相通之处,那就是他们帮助中国文学走出了原有的学科领域的限制,把中国文学带进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列,使中国文学触及到了传统的中国文学专家之外的更为广阔的读者群体。上述两大类学者及其研究对中国生态批评的学科发展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有三。首先,像杨金才与李程这一类中国文学专家试图通过回应由西方学者所构建的庞杂的生态批评理论与方法论来为中国生态批评寻找自己的位置。其次,通过探讨何为经典以及文化多样性等问题,Ursula Heise、Sylvia Mayer、Simon Estok等学者将中国文学文本置于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之外的学术范畴,比方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然而这两组学者也代表了两种局限。例如那一类热衷于向中国译介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与方法论著作的学者们,不论他们的译介速度有多迅速,他们终将处于步西方学者之后尘的尴尬地位。再次,通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环境文学的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来展开各自的研究,而这将严重地局限这一类学者对文学文本的选择空间。由此看来,Lawrence Buell为中国生态批评所构想的蓝图就重新拥有了现实意义:对中国的生态批评家而言,通过探索中国自身特性来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有可能帮助中国生态批评家们实现潜在的突破。
Buell的建议有三层含义。首先便是考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正如许多环境史学家所论证的那样,中国与环境问题的纠葛绝不简单是现代化进程所衍生出的一个问题。然而关于中国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中国确实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比方说,在中国各大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提到了1950年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时任北京市长彭真一番关于烟囱的对话。毛泽东说:“从天安门望出去,应该处处都有烟囱”。这则轶事的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怀疑的,但它确切地表明,烟囱与雾霾曾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被视为中国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象征与衡量标准。考虑到环境恶化的巨大影响,即便是在当下,中国的环境意识也是明显缺失的。当杨金才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过于有限”时,他也正确地表达了类似的担忧。然而这在未来的几年里将有所改变,中国的环境问题也会得到解决,如果中国人民可以足够重视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生态文明思想。鉴于中国在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环境恶化等方面的独特经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何缺少足够的生态意识,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给国际生态批评话语提供独到的贡献。
Buell的第二点建议是利用中国哲学思想这一资源。除去李程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汉译迟缓这一问题的批判之外,杨金才还指出了另一个与翻译有关的挑战。杨金才写道:“翻译质量低劣、误读,以及时有发生的过于牵强的解读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更快更好地提供高质量的汉译确实是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也有它自有的局限性。知名生态批评家Simon Estok所代表的这一类的学者所希望看到的是讲汉语的学者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并与他们那些来自西方学界的同行们展开对话。然而这对话的质量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果中国学者所做的仅仅是痴迷于制造西方理论的相似品或变异品。对这一局限的有效回应便是重新重视Buell所提出的从中国本土哲学思想内部寻求理论话语与突破。这一回应将促使中国学者利用中国本土哲学思想对环境问题进行理论化。杜维民的论文《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便是用新儒学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一种堪称典范的创新运用。陈广琛的论文《个人的环境:沈从文和高行健的自传体作品》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证明如何在道教话语的范畴之内理论化环境问题。由此可见,杜维明与陈广琛所代表的此一类由中国本土哲学思想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性论著是中国生态批评领域中所急切需要的。
最后,Buell呼吁学者们积极寻找相关的中国文学作品,并帮助这些作品在由生态批评所塑造的文学经典以及批评话语中确立应有的地位。通过王德威、唐丽园、Ursula Heise、Sylvia Mayer等学者的努力,中国的自然写作和环境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环境文学等领域得到了相应的认可,姜戎的《狼图腾》也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并在环境人文学领域中被频繁地讨论。但是中国的另一些文学作品呢?那些在生态批评话语中同样重要却还不曾得到足够的认可与研究的中国文学作品呢?例如,贾平凹的《怀念狼》是一部比姜戎的《狼图腾》早四年出版的小说,两部作品所处理的内容都是极为相似的,如果说这两本书中的某一部比另一部更优秀,那这样的论述注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然而这样一部重要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尚无明晰的定位。《怀念狼》同样也没有得到世界环境文学领域的关注,这或许是由于该书目前仍然没有英译本问世造成的。因此,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迫切地需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翻译成其他语言,并为之在中国文学史以及世界环境文学经典作品之中寻找合适的地位。这也是中国生态批评家们不容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