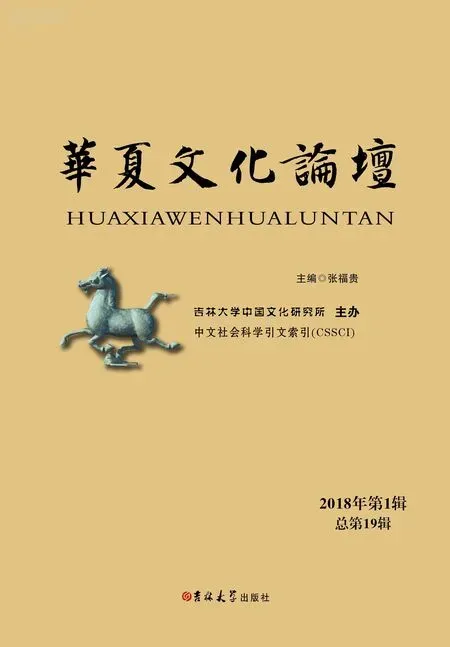先锋与自由
——新世纪以来旅加诗人洛夫的创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白 杨 田诗洋
【内容提要】洛夫是台湾现代诗运动中具有先锋意识和引领性地位的代表诗人。新世纪以来,旅居加拿大的洛夫相继创作了长诗《漂木》等多篇诗作,以对“天涯美学”的诗性书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融合中,达到思想与艺术的自由境界,并呈现了汉语新诗的根性特质和世界性意义。
2017年6月,89岁高龄的旅加诗人洛夫携妻子陈琼芳女士,告别了他们在温哥华的寓所“雪楼”,重返台湾。从1996年4月抵达温哥华,洛夫共在加拿大生活了21年。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21年,特别是对夕阳向晚的老人而言,堪称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洛夫曾在诗作中写有这样的诗句:“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时间/还来不及做完一场梦/生命的周期又到了”。但他并不自甘沉寂于“生命的周期”的限制,在时间之流中,他以一支智性磅礴的诗笔逆流挺立,旅加期间,他创作了3000余行的长诗《漂木》,出版了诗集《背向大海》,还创作了《掌中之沙》《如此岁月》等多篇诗作。这段流寓时光的写作,使他的生命再度绽放出浑厚瑰丽的色彩。
应该说,如果没有旅加之行,并不影响洛夫在汉语诗坛的经典诗人地位;但因为有了这段独特的经历,他的诗歌世界获得了丰富和提升。龙彼德曾借用艾略特在《叶芝》一文中的观点评价洛夫,艾略特在该文中指出:“一个有能力体验生活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会发现自己身处于不同的世界;由于他用不同的眼睛去观察,他的艺术材料就会不断地更新。但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诗人才有能力适应岁月的变嬗。确实,需要一种超常的诚实和勇气才能面对这一变化。”龙彼德认为洛夫堪称是这“很少几个诗人”中的一个,这并不是过誉之词,在洛夫的创作生涯中,他表现出了旺盛的创造力,生活际遇的改变,成为促发其艺术灵感的契机。以长诗《漂木》为代表,新世纪以来洛夫的诗歌创作标示了海外汉语新诗的突出成就,由思想观念、写作意识的先锋性所形成的创作的自由挥洒状态,其纵横捭阖、笔力覆盖海内外的气韵,其对天涯美学的诗性阐释,无疑使这部作品成为汉语文学版图中的一个经典之作。
漂木与鲑鱼之喻:“出走”与“回归”的意象化表达
洛夫曾多次在访谈中谈及自己移居加拿大的原由,称自己把“这次移居异域称之为‘第二度流放’”,“第一度流放是在1949年,为时势所逼,孑然一身来到异乡的台湾,由混乱而安定”,但80年代末期以后面对台湾“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突萌重作选择的想法,希望在这地球上找到一个既可安度晚年,又能在写作上再创佳绩的一方净土”,因此“这次二度流放到温哥华,自我选择的意图远大于被迫的因素”。但临老去国,远奔天涯,割断了与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联系,却割不断生命记忆中那些血脉相连的情愫。“秋日黄昏时,独立在北美辽阔而苍茫的天空下,我强烈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却又发现自我的定位是如此的暧昧而虚空”,“这种空荡荡的茫然乃缘于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认同对象。”叶维廉曾用“郁结”一词形容历史创伤给他们那一代离乱中求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影响,对外在社会动荡的无奈,内心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使他们在内心体验中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纠结的状态,这种“郁结”的情愫投射到文字中,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暂时的释放渠道。长诗《漂木》也是洛夫疏解心中“郁结”之情的产物。
在《漂木》中,“漂木”与“鲑鱼”,作为一组具有互为映衬关系的意象,以一体两面的特质建构起立体的海外游子的形象。“漂木”侧重展现“离散”的经验,在历史洪流中他既不得不被动地承受来自外力的各种冲击,又孤寂而坚韧地从现实中超离出来,追索存在、宇宙、宗教等形而上的思考;“鲑鱼”则着重突显其“回归”的意义。“鲑鱼”的出走与回游,艺术化地展示了游子内在情感中与故土的复杂扭结关系,这是一种孕育更多主动性选择,貌离神合的过程,其出走是为了成全生命的成熟和丰富,其回归则源于一种根性的呼唤和自觉的使命意识。在《鲑,垂死的逼视》一章中,抒情主人公以鲑鱼的视角展开叙述,这是一个决绝的,具有怀疑、叛逆精神的形象,“我们不能放弃怀疑/我们不能/只靠昨天的腥味/来辨识今天行进的方向/不能因/满嘴的泡沫/就说自己/是一个极端的虚无论者”,“革命,首先要推翻自己/彻底消灭自己的影子/不能寄望牙齿有一天会成为化石的一部分”,因为怀疑与叛逆,鲑鱼成为“流浪者”,流浪是他们的宿命,更是他们的选择!同第一章的“漂木”意象相比,鲑鱼的形象气质中包含着更多主动选择、主动承担的意味,他们历尽千难万险,以“全生命的投资/参与一个新秩序的建构/一个季节之外的太和”。然而,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他们“不吃不喝游过数千里的旅程”去“寻找原来的家”,为的是在那里产卵,“完成绵延后嗣的伟大目的,然后无牵无挂,无声无息,却无比庄严地死去。”诗人在鲑鱼的生命轨迹中,感受到同自己以及更多海外游子相通的经历,虽然不知“生命周期的终点”,尽管“回家的路上尽是血迹”,但回归故园,留下新生命的愿望从来不曾动摇过。
洛夫曾说:“我相信诗是一种有意义的美,而这种美必须透过一个富于创意的意象系统来呈现。我既重视诗中语言的纯真性,同时也追求诗的意义:一种意境,一种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实质内涵”。从创作伊始,他就非常重视意象的塑造,在其笔下曾塑造出众多内涵丰富、个性突出的意象,而“漂木”与“鲑鱼”则是他新世纪以来贡献给汉语新诗的又一组典型意象,独特而且意味深长。
“诗人之思”:“漂木”的物性与超验性
在洛夫的很多诗作中都有对亲情、友情的描写,或对日常生活中器物、景观、经历等的描摹。前者如《血的再版》《给琼芳》《赠大哥》《致商禽》等,后者如《镜子》《悬棺》《看云》《夜宿寒山寺》《再回金门》等,这些由生活中取材的诗思,体现了他对日常生活的亲近感,是具有物性意义的抒写。这构成了洛夫诗歌的一个层面的特点。洛夫曾自述:“其实我内心是十分真诚而谦卑的,……我以悲悯情怀写过不少一向被人类鄙视厌恶的小动物。早晨看到太阳升起,内心便充满了感恩,黄昏看到落日便心存敬畏。”对日常生活的关切和省思,构成其诗歌创作中富于理趣和情致的风格。如《背向大海》集中的《苍蝇》一诗,透过苍蝇与人类的关系,表达一种生态思考。
然而,诗人一生中经历了太多苦难痛苦的遭遇,战争、逃难、流放、漂泊,“在战火中、在死亡边缘,最容易引起对生命的逼视、审问和形而上的思考”,因此,洛夫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生命内涵的创造,精神高度的创造,尤其是语言的创造。”因此,他在其作品中对生命进行观照,对时代与历史的病症和痼疾进行质问与批判,并由怀疑与反思上升为“行而上”的思辨,他渴望追问那些具有超验性的思想。在《漂木》中,抒情主人公与时间对话,与历史上著名的中外诗人对谈,并对诸神发出责问,“洪水滔滔/风雨以绞链勒死这个城市/方舟在水涡中急遽地打转/诺亚抱着自己的尸体登岸而去/神啊,这时你在哪里?”在质疑、求索的过程中,诗人颠覆既往的成规和理念,建构起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精神,“我是万物中的一/独立于/你眷顾你掌控你威逼之外的/一个由钢筋水泥支撑的/个体”,“我不必从书本中找到信仰/不必从读经,祈祷,声泪俱下中/找到爱”,我是一个“无限小/也无限大的宇宙”。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者对存在本身的威胁。”洛夫用诗去探寻存在的本质、疑虑和悖谬之处,对他而言,“语言只是手段,诗使它成了目的”,并因而“创造了稳定和永恒之美。诗是一个来自内在的平衡力量。诗是他的一种特殊思考方式。”
洛夫说,诗人的终极信念是在扮演时间、生命与神这三者交通的使者。因为他的存在,海外汉语诗歌显示出他的高度与硬度,并成为20世纪汉语文学版图中不能忽视的一翼。
先锋与自由:天涯美学的“前世今生”
《漂木》中有一个独特的设计,每一章前面都有一个近似音乐前奏的“序诗”。它们以互文性的存在方式,既引导出后面诗行的意义,也打破时空的界限,将洛夫以往作品中的某些段落与当下的思绪对接,从而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浑然交融的网格。
第一章《漂木》,前序是屈原的《哀郢》;第二章《鲑,垂死的逼视》,则以其早期超现实主义诗作《石室之死亡》第十一节为序;第三章《浮瓶中的书札》,交替使用了诗人自己的作品《血的再版》节选,及海德格尔、尼采等人的言论;第四章《向废墟致敬》,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序。前序言简意深地表达了诗人的思想观念,而其内涵则容纳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这种书写方式大胆、前卫,在一种极富包容性的格局中展示出通达的文化立场。
研究者们经常会提及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由洛夫、张默和痖弦创办的台湾现代诗刊《创世纪》,在60年代以后曾以“超现实主义”为旗帜,带动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但在7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整体性的回归传统、关注现实潮流中,放弃了其现代主义追求,回归传统。如果宏观地描述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这种概括有一定的道理。但无法忽略的弊病是,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绝对化地评价历史现象,时常会暴露出片面性的问题。洛夫曾明确地表述:“如果从我整体的创作图谱来看,我早期的大幅度倾斜于西方现代主义,与日后回眸传统,反思古典诗歌美学,两者不但不矛盾,反而更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我这一心路历程,决不可以二分法来切割,说我是由某个阶段的迷失而转回到另一个阶段的清醒,而这两个阶段的我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其实在我当下的作品中,谁又能分辨出哪是西化的,哪是中国的、传统的。至于现代化,乃是我终生不变的追求……对我来说,现代化只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创造。”洛夫用他的诗歌创作证明,他是一个不想被定型化的诗人。
由对现代与传统关系的反思,使他获得了一种世界性视野。他进一步提出了“大中国诗观”和“漂泊的天涯美学”的观点,在60年代曾引领台湾现代主义诗潮之后,再度以先锋意识拓展了汉语新诗的文学版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洛夫在其一些诗论和访谈中提出了“大中国诗观”的观点。他强调“这一主张乃企图整合中国新诗的历史版图”,藉此消除“因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大陆、台湾及海外各自为阵、各以自我为中心而造成的尴尬和困扰”。作为从青年时代就被迫流寓异地,在生命中经历了两度流放的诗人,洛夫对局限于狭隘的地域性、族群性意识形态而给文化艺术造成的伤害深感失望,他认为真正伟大的诗人应该是“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世界人类的良心,他超越一切界限而独立于宇宙万物之中,中心与边缘之争确属无谓”。对他而言,“大中国诗观”是与“世界文学”相呼应的美学定位,在此基础上,他在长诗《漂木》问世时,进一步提出了“漂泊的天涯美学”的概念,着力探求将个体性、民族性经验提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理境界的方法。何谓“漂泊的天涯美学”?洛夫用“悲剧意识”和“宇宙境界”来描述其内涵,他认为:“广义地说,每个诗人本质上都是一个精神的浪子,心灵的漂泊者。”因此,在创作长诗《漂木》时,他有意识地要将其“定性为一种高蹈的、冷门的,富于超现实精神和形而上思维的精神史诗。”“诗中的‘漂泊者’也好,‘天涯沦落人’也罢,我要写的是他们那种寻找心灵的原乡而不可得的悲剧经验”,对悲剧经验的书写和对个体生命意识的悲剧性体认,使其作品获得了超越文化版图限制的世界性意义,“汉语性的‘天涯美学’与全球性的‘天涯美学’是一体的两面,汉语性是它的根,全球性则是它的翅翼,它的飞翔,它的梦幻,它的理想。”洛夫强调:“文学的特性本来就是个人风格的特殊性与世界观的共通性二者的有机结合,而个人风格又无不是建立在他民族语言的特色上,这两点可说是所有伟大作品的基础。”在世界性视野中思考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化问题,洛夫力求创造一种基于民族根性而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的诗歌美学。
在洛夫的诗歌世界中,主体同其置身其中的外部世界之间似乎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中,他注目、审视、拷问存在的困境及其意义,抒发一个痛苦的灵魂在上下求索中所捕获的哲理之思。在其诗歌美学的建构中,他获得了写作的自由,这是一种不受既定的陈规戒律限制,而渴望以先锋性探求拓展汉语现代诗的思想境界、艺术秩序的写作状态,他的生命意识在写作中得到延伸,并示范性地带动了同时代中同道者的写作,这是他对于中国现代诗史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