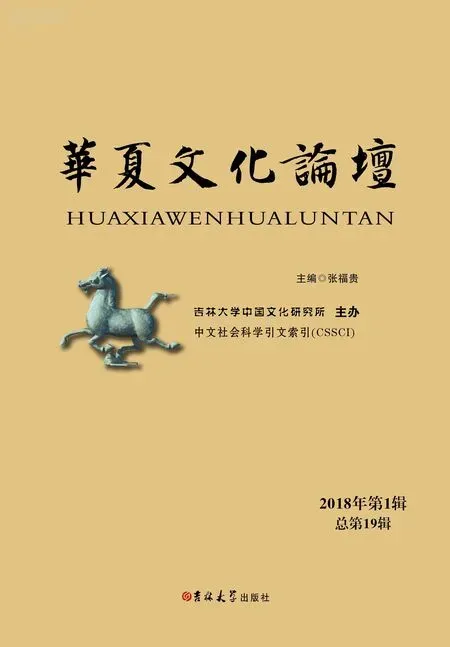当下中国文学的状况
孟繁华
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要看高端成就
当下文学的状态是好还是不好?大概从2004年一直到今天,关于当代文学的价值评估问题一直没有终结。后来有一些媒体,包括一些作家和批评家,把当代文学评价的情况分为了唱盛派和唱弱派。唱盛派就是认为当下中国文学是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唱弱派认为现在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低谷。
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的真伪。假如说这个问题是真的,显然我是一个唱盛派。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学是百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评价一个时段的文学,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能和当代文学进行比较的,就是现代文学。指责的人士讲,当下的中国文学红尘滚滚、泥沙俱下、肉欲横流、一无是处、乏善可陈,但真实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学恰恰如此。比如现代文学里面有张资平、有红玫瑰、有三角恋爱、有十里洋场,它才是红尘滚滚、肉欲横流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我们有了鲁郭茅巴老曹,我们就建构起了一个伟大的现代文学史。所以评价任何一个时期、一个时代、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看它高端的文学水准。我们谈到英国文学,总要谈论莎士比亚;谈到美国的文学,我们就谈到海明威、斯坦贝克;谈到日本文学会谈到川端康成;谈到印度文学就谈到泰戈尔;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就谈到鲁迅。这个高端文学难以超越,它能够表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高水平的文学。有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作家和作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就是伟大的文学。现代文学经过了历史化和经典化,当代文学因为是近距离的文学,我们没有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能够深入当代文学内部的人都会知道,当代文学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否定当代文学的人,一般来说是因为对当代文学不甚了了。
我为什么是个唱盛派?
关于当代文学的成就,我会一一举出。我为什么是个唱盛派?当代文学没有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时候,你就迅速地对它进行好坏判断,过于简单了。究竟好坏,还是要通过历史来判断。再过几十年,我们可以回头看看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或者新世纪的文学究竟是好是坏。我觉得不要急于做出判断。另外,挑起这种话题的人,我觉得可能缺乏一点常识。唐代的人不会评价整个唐代的文学是好是坏,宋元明清的作家和批评家不会谈论那个时代的文学好坏。某些人挑起了这样一个话题,本质上来说它是个伪命题,我觉得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有一个情况我们必须要正视,就是当下文学或者当代文学整个被关注、被阅读的情况逐渐在下跌,这是没有问题的。最好的比较就是和20世纪80年代比,那是中国文学最辉煌和被读者念念不忘的一个伟大时代。当时的《人民文学》大概发行100多万册,《诗刊》都发行近百万册。这个情况我觉得非常正常,80年代我们情感的沟通,唯一的通道就是文学。今天大家进行文化消费的场合和方式太多了,可以到星巴克、嘉年华、健身房等,有无数的场合可以去。用广告的话来说就是必有一款适合于你。今天爱好文学的人口被分流了,过去集中阅读《人民文学》的人,可能被其他的文化消费形式吸引了。这种情况不是说当下的文学不好。我曾经多次讲过,当下的文学有了百年的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80后、90后的一些作家一出手,包括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构思,他们的人物,灿烂逼人,不同凡响。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百年文学经验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滋养。文学作品写得越来越好,为什么不被关注,是其他的一些文化消费形式把大家的注意力、关注度、热情分流了,是这种原因造成的,这和文学写得好与不好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今天的阅读不是读者阅读,是粉丝阅读。《哈利·波特》的英国作者罗琳非常著名。《哈利·波特》现在的各种语言版本印数已经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记录,世界上除了宗教类的书籍以外,她的销售量可能最高了。她后来又写了一部作品,是侦探小说,叫《杜鹃的呼唤》,她用笔名发表以后,只销售了1500册。出版商着急了,换上了罗琳的名字,立即销售了30万册,而且仍在加印。这不是粉丝阅读吗?这个书发生变化了吗?没有发生变化,就是因为是罗琳写的,是《哈利·波特》的作者写的,大家趋之若鹜。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当下的中国,诺奖获得者莫言的读者远远不如《小时代》作者郭敬明多。《小时代》是什么样的作品?大家都很清楚,也是粉丝在读。这些东西是文学的成功吗?包括罗琳的《杜鹃的呼唤》,包括郭敬明的《小时代》,不是文学的成功,是文化产业的成功。图书出版好似文化产业之一种。《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暮光之城》一直到《小时代》,当然还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詹姆斯的《五十度灰》《五十度飞》《五十度黑》,《五十度》系列都出了几千万册。这是文化产业的成功,不是文学的成功,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清楚。
作家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大概在2012年以后,文学状况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一些不同的议论,我觉得非常正常。在这个时代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中国人,作家莫言当之无愧。这里我要为莫言辩解几句,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就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祈使句,在这个话语结构里面,我们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文化,或者文学的弱势国度来认知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还认为中国文学没有进入到世界格局,所以才呼唤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那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的文学强势国家所承认。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评奖制度,包括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一种政治。承认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所以80年代、90年代以前,诺贝尔文学奖不授予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他们可能会授予共产主义国家的“叛徒”,比如说授予给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苏联那些不认同斯大林时代政治的、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国家“叛徒”的作家。评奖不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吗?诺奖评委也讲,诺贝尔奖的上空,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政治阴云。所以说评奖本身也是政治。莫言获奖,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肯定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诺贝尔奖评委会冷战思维的终结有很大的关系,你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已经不再作为考量的标准了。
莫言获奖后,一是缓解了我们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焦虑,让中国文学走上世界的焦虑缓解了。在世界文学政治格局当中,中国文学有了一席之地。第二点我觉得,在短时期里面提升了中国读者,包括有关部门对文学的关注度。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莫言获奖之后的第三天,全国各大书店关于莫言的所有作品销售一空,这个消息太让人震惊了。文学读物从来没有如此地抢手,莫言获奖之后,在短时期里面,带动了我们读者对文学阅读的热情。
当然,莫言获奖之后,并不是说中国文学所有的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被世界所尊重,所认同,重要的不是什么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的是他的价值观。不是他有多大的权力,也不论他有多少金钱和财富,这个人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从乡土文学到农村题材的变化
下面我们切入到正题里面。谈谈中国当下文学的状况。百年来,中国文学最大的成就就是乡土文学。当代文学成就最大的是两个题材,一个是农村题材,一个是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两个领域里面我们取得的成就最大。
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不同。现代文学都叫乡土文学。由北大严家炎先生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选》中有一部就是乡土文学,我们可能最发达的也是乡土文学。从新文学诞生那一天起,乡土文学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一起发展。鲁迅、沈从文、彭家煌、许地山、沙汀等作家写的都是乡土文学。为什么乡土文学最发达?它和中国的社会性质有关系,中国的社会性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乡土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写过一本书——《乡土中国》。他对乡土中国的价值观、道德、习俗、礼仪、差序格局等讲得非常清楚。至今我也认为,关于乡土中国的研究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比较起来,还无出其右者。乡土文学什么时候发生变化呢?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乡土文学开始发生变化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农村题材。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乡土中国是描述性的一个词语,讲的是中国社会的性质状况。农村题材是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我们的作家才第一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面建构出两个阶级的冲突和对立。比如《白毛女》,是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冲突,这是农村题材。1946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1948年周立波《暴风骤雨》发表后,农村题材逐渐趋于成熟。这样一个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在这个时代里面有没有合理性呢?我觉得当然有合理性。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1942年的中国是一个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中国共产党要动员一切手段,包括文学在内,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有什么错误吗?当然没有错误,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那个时代所取得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在今天或者在未来,无论怎样评价都是正确的。农村题材里面有一个隐结构,就是当我们主流的文学政策方针和路线号召去书写工农兵的时候,这个隐结构里面有一个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拒绝。延安讲话以后,知识分子题材最为萧条。在进入当代文学17年的时候,大概我们只有两部作品,北面叫作《青春之歌》,南面(广东)有一个《小城春秋》,作家叫作高云览。后来在文学史的叙述里面,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也看不到了。这和书写工农兵背后这个隐结构,对知识分子的排斥有直接关系。知识分子的身份多年一直处在非常暧昧的状态。
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构成的伤害,后来在不同的文本里面都已经叙述到了。农村题材从延安开始,一直进入到共和国的门槛之后,在今天我们看来有一些问题出现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延安时期的战时文学主张挪移到了和平时期,把延安时期的局部经验放大到了全国。这个时候我们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文艺方针、路线政策不断地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后来我们讲到,中国现代性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西方缔造了现代性之后,中国在回应西方现代性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就是不确定性。
到现在这个不确定性可能仍然在过程当中,当然文学也是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里面。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三里湾》到“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就是八部经典作品。“三红”就是《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就是《创业史》。“保山青林”就是《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这些经典作品里面书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作品是主流作品。特别是《创业史》的出版,不是说塑造了梁生宝或梁三老汉这样一些人物,关键是为当下的中国建构了一种价值,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农村题材的思想路线走不下去了
在文学里面我们逐渐地发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从延安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在1942年有一个新文化猜想,或者叫作新文化想象。我们不会要旧的封建文化,也不会要资本主义的文化,我们要的是什么文化呢?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所以1950年以后,我们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所经历的就是不断被清理和不断被整肃的过程。1951年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然后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然后批评胡风,然后是反右等,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样一个不断整肃的过程当中,文学领域越来越干净。在延安时期,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文学确实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的文学人物就是阿Q、华老栓、华小栓,祥林嫂、老通宝等,他们都是病态的,肮脏的,愚昧的中国农民形象。到了延安时代,中国农民印象焕然一新,我们有了二黑哥,有了大春哥,有了红军哥哥。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伟大创造。但是这几个哥哥,逐渐逐渐地就变成了李玉和,变成了郭建光,变成了江水英。中国文学变得越来越明朗,越来越透明,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只有一个关系,就是革命同志的关系。
文学是干什么的?文学是处理人类精神事务的一个领域,就是处理人性的领域,外部的事情由各个部门来处理。到了样板戏时代,或者走农村题材的思想路线,人们在舞台上都是“孤男寡女”,不要说邻里关系、同事关系、夫妻关系。只有一种关系,就是革命同志关系。走到这一步,不仅文学走不下去了,整个时代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也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之前,我们一个伟大的承诺落空了。也就是在梁生宝,在肖长春,在“高大全”的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于是我们才实行了改革开放。1979年有两部重要的作品,一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另外一部是古华的《芙蓉镇》。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从农村题材重新回到了新乡土文学。通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样的作品,我们发现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的体相,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生活水准和阿Q、华老栓、华小栓、老通宝、祥林嫂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1919年到1979年60年过去了,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发生。我们的文学创作也重新回到了乡土文学,当然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和改革。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置换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经济生活在我们社会生活整体结构里面的核心地位获得了确立,当然也获得了全体人民的支持和欢迎。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富国强民。初期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承诺,遇到了问题。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富国强民这个承诺,在今天它部分地实现了。2007年前后,我们去江苏华西村,那是中国第一村。大概有200多人参加全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文学研讨会。华西村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村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到了华西村,才发现在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每一户人家都住400平方米左右的别墅,村里面就是高楼大厦,轧钢厂里面空无一人,全都是自动化。这和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当时去了很多西部的作家拿着DV到处拍,说如果这是我的家乡该有多好啊!西部作家在感叹。但我说这幸好不是你的家乡。中国可能只有一个华西村,如果乡村中国都变成了华西村,13亿中国人喝西北风吗?农村是干什么的?是生产食品(吃的)和纤维(穿的)的。如果中国农村都变成华西村,我们基本的生活材料肯定就处在一种非常不安全的状态。
当时老书记吴仁宝给我们讲华西村的发展史。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村发生的这些变化,但是现代性是一个与魔共舞的过程。乡村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都走了华西村这样一条道。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在文学作品里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反映和表达。
一批新乡土文学的作品出现了
从新世纪以后,在新乡土文学的作品里面,我们发现类似《创业史》《艳阳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这样的作品,能够把乡土中国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给读者的作品,越来越少。后来我们甚至发现,很多作家在书写乡土中国的时候,完全碎片化了。有几个典型的作品,比如说孙惠芬的《上塘书》,这都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贾平凹影响最大的作品当然是《废都》,我在后面再讲。
《上塘书》里面写的乡土中国是什么呢?它用村志的方法来写,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交通、上塘的通讯、上塘的教育、上塘的贸易、上塘的文化、上塘的婚姻、上塘的历史等。它的结构不可能出现梁生宝、梁三老汉这样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阿来的《空山》也是这样的,把这个小说读完了以后,你可能觉得是几个中篇构成的,讲机村,讲山火,互相之间没有建构成完整的、作为文学作品内在的逻辑关系。贾平凹的《秦腔》也是这样的,很多批评家朋友就认为贾平凹的《秦腔》大概是《废都》之后写得最好的作品。如果没有《秦腔》,贾平凹作为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秦腔”是陕西的剧种,小说里面的重要人物——白雪又是个秦腔演员。在小说里,这个白雪渐行渐远,最后成为历史的一颗“痣”。“秦腔的声音也渐行渐远”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乡土中国,逐渐会在我们的视野里消失。
前几年我提出一个看法,就是乡村文明的崩溃在这些作品里都有表达。改革开放之后,发达的东部地区确实富裕起来了,但是更广大的中国乡村越来越空心化。乡村中国的空心化,只有留守儿童、留守老人。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社新创办了一个栏目叫作非虚构文学,2010年第10期发表了青年学者梁鸿的一篇非虚构作品叫作《梁庄》。后来出版了《中国在梁庄》,最近又出版了一本叫作《走出梁庄》,可以看作是作者的《梁庄》系列。从2010年到今年,《梁庄》系列可能是当下中国文学作品的核心读物之一。《梁庄》是非虚构文学,它不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并不完全相同。它用极端写实的方法,讲述了梁庄——自己家乡的衰败过程。这个衰败不是说教育和乡村生活的衰败,最重要的是乡村文明没有了载体。
在我刚才讲的这些作品里面,都表达了乡村文明的整个破败或整体溃败的现实。这当然和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直接的关系。2011年,中国整个城乡人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城镇人口超过了乡村人口。现在大概有超过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这个变化不是乡土文学逐渐消失或逐渐衰落的一个依据,不是说乡土文明崩溃了之后,乡村文学也随之终结了,这是不对的。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就是对当下的追踪过于密切,对于历史事件的关注,缺乏持续的耐心。乡村文明崩溃了,不是说乡村文学随之终结了。我甚至举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文明即将崩溃的时候,恰恰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我们也期待伟大的作家能够书写出乡村文明在我们现代性的进程中是怎样崩溃的,就像封建社会怎么在《红楼梦》里崩塌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这样的作品,让我们有些耐心,慢慢地等待他们。乡村文明崩溃之后,用我的看法来说,就是另一种新的文明正在崛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不同的作家试图重新用文学的方式建构乡村文明和乡土中国社会。有几个作品,如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还有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关仁山的《麦河》。热爱文学的读者,可能都读过这些作品。他们还试图在乡土中国里面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讲述给读者。对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从整体上来说,特别是在当下中国文学的环境里面,我给了很高的评价。
《湖光山色》讲的是楚王庄的故事,楚王庄是楚王的故乡。改革开放以后,楚王庄发现了楚国的一段长城,历史学家带着他们的学生不断地到楚王庄来考察楚长城。村里面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叫暖暖,发现了商机,建造起了一个家庭旅馆,就是农家乐这类的乡村旅馆,就是每天收10块钱,吃住全管。这个农家旅馆办得越来越大。在乡土中国,有一个问题,叫作不患寡,患不均。少可以,但是不能没有我的。楚王庄有这么一个资源,暖暖一家把它都变成个人的资源了,这样就出现了问题,一些人就欺压暖暖。村支书有一个弟弟,特别想向暖暖示好,要结为连理,被暖暖拒绝了。她找了村里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叫旷开田。暖暖发现村支书不断欺负自己的时候,她跟旷开田讲,“如果我们在村里面不受欺压,必须由你当村长。”旷开田说,这怎么可能呀,但通过暖暖的运作,终于把他运作成了村长,终于掌握了这个权力。
楚王庄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不断地招商引资。用文化产业很时髦的用词来说,他们要编演一出情景剧,就像“印象丽江、印象刘三姐”一样。楚王庄要搞一个大型情景剧,叫作《离别》。离别,就是楚王要出征了,楚国的臣民来为楚王送行。那谁来演楚王呢?只能村长来演。尽管旷开田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是演这个楚王,三天之后他就非常自如了。周大新在《湖光山色》里讲的是什么呢?是中华民族传统里面对王权的迷恋,对权力的迷恋。一个农民做了村长以后,权力给他带来了快乐,带来统治的快乐,带来的这种成就感、荣誉感,让他念念不忘。但是周大新在讲楚王庄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有强烈的,或者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就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但是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王权思想依然在这里面具有支配权和统治地位。
关仁山的《麦河》写的是切近的乡村。近几年我们公布了一个最重要的土地政策,叫作“土地流转制度”。《麦河》写的就是土地流转制度,写鹦鹉村通过一个能人叫作曹三羊,把全村土地集中起来。集中播种、收割、集中加工,不是卖粮食,是卖粮食制品,就是如何使鹦鹉村富强起来。这两种叙事显然都是对乡土中国未来怀有乐观态度的一种讲述方式,和我们刚才讲过的像《上塘书》《秦腔》《空山》这种乡土中国文明破败的讲述方式完全不同。当然,不同的作家对当下乡土中国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讲述方式和阐释方法,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乡土中国,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通过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想象方式。
城市文学已经成为今天的主流
深圳非常著名的杂志《新城市文学》曾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讨论新城市文学。这和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关注的话题有关系。乡村文明崩溃之后,肯定还有另外一种文明在崛起。这个文明就以都市文明为核心,是正在建构的一种文明。为什么不叫作城市文明?为什么不叫作城市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整个城市化不断地加快发展,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所理解的城市和我们过去的城市完全不同。今天的上海还是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吗?不是了。当然也有作家不断地用这种方式在书写,比如80年代的程乃珊写的《蓝屋》、王安忆写的《长恨歌》等。40年代老舍笔下的北京,完全是平民的北京,是《骆驼祥子》的北京,是《四世同堂》的北京。今天北京还有多少骆驼祥子?今天的骆驼祥子都搬到固安,搬到燕郊,搬到涿州去了。北京胡同里面的骆驼祥子越来越少了,今天的北京是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商业精英、白领、中产阶级的北京。这个文明在不断地建构,怎么概括和描述它,我觉得非常困难,因为不断变化,是不确定性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称作正在崛起的新文明。与新文明正在崛起构成同步关系的,以都市文学为核心的一种文学正在生成。这种情况过去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在乡土文学、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其他题材的作品在齐头并进的时候,城市小说并没有引起大家过分的关注。没有成为批评界的显学,但是近两年来不同了。近两年批评界大概把城市文学作为非常重要的考察对象,很多城市,都曾开会集中讨论城市文学。
我们突然把眼光关注到城市文学的时候,就发现当下的城市文学确实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的主流了。我去年参加过几次评奖,入选的作品我发现和乡土文学有关的一部都没有了,这太让人惊讶了,全是写都市生活的。都市的过去我们也有,官场、情场、商场、职场,中产阶级白领都有。包括从2005年以后,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从深圳发生的,叫作“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也是城市文学,或者说是城市文学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你发现城市文学虽然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主流,但城市文学在建构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成功的作品。我也讲过这些例子,比如在19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圣彼得堡,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都产生过和城市文学相关的,和年轻人相关的一些伟大的作品和人物。但是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学没有这样的作品。官场小说,在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像《国画》《羊的门》《沧浪之水》等,都是写官场的好作品。
《沧浪之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医科大学生毕业了,分配到卫生厅。但是这个人对自己有要求:他要做清流,但是七年了他依然是一个科员。同时毕业的同学做了科长、副处长、处长,都升迁了。为什么说承认是一种政治?从黑格尔一直到查尔斯泰勒都讲过,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或者认同,是我们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你要做清流,当然提拔科长和处长的时候不会考虑你。池大为后来要娶妻生子。一个科员可以特立独行,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但是老婆天天在你身边说话,这就糟糕了。她说,你看看人家那个孩子吃的都是雀巢奶粉,我们家的孩子吃的都是三聚氰胺。你看人家一年搬了三次家,我们一家三口还住着很小的房子。男人在女人面前如果抬不起头来,这一生就悲摧了。所以他开始扭转了对人生的要求,三年以后池大为终于做上了卫生厅厅长。它讲述的是什么呢?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生活里面,在体制里面,想要坚持自己特立独行的精神空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部小说非常了不起。
写商场的作品太多了。从20世纪90年代到当下,大概有几个高峰。90年代中期,和商场有关的作品,恰恰是海外文学给我们反哺带来的。比如《北京人在纽约》《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在东京》等作品。这些作品除了表达它的商业诉求之外,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隐含在其间。就是所有到国外的留学生,内心的这种焦虑在这些作品都得到了表达。你离开国门之后,处在两种文化之间,你不可能进入第一世界的文化主流。离开了大陆之后,你在大陆主流文化中也处在边缘地带,就是处在无根的状态。这些走出国门的青年,要表达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怎么办呢?就是成功,你不可能在政治上成功,表达的成功只能是商业上的成功,这些作品带动了我们文学的市场化。
写官场的作品,一定是和商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写到官场,一定会有商场,有商场就肯定会有情场,这些作品对世情表达得非常充分。新文明崛起之后,都市文学正在不断地发展,从以前的潜流逐渐成为主流的一种现象。另外,有个现象很重要,就是“打工文学”,在学界被命名为底层文学。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都不准确,底层和打工都不是文学概念。后来我在《文艺报》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新人民性的文学》。文学的人民性是普希金等人提出的不断完善的一个文学概念。
底层文学持续被读者关注
我们的文学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一直到后来文学的思想方针和政策,都和人民性的文学有直接的关系。写工农兵的文学,为人民大众的文学都和人民性有关。我们暂时延续这个命名,还是叫作底层文学。有很多重要的作家,比如曹征路。2004年曹征路在《当代》第五期上发表了非常重要的作品叫《那儿》,前几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问苍茫》。曹征路是可以驾驭重大题材的作家,他是深圳大学教授。《那儿》为什么重要?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叫作工业题材。这么多年谁还读过工业题材的小说和作品?没有了。我在2005年的时候,参加一个煤矿工人作家作品讨论会。当时我非常感动。工人阶级过去是我们的领导阶级,现在他们的处境怎样呢?
曹征路的《那儿》,这个“那儿”是“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作品里面有一个姥姥,年龄大了,她说不全“英特纳雄耐尔”,她就叫“那儿”。曹征路写的是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倒闭了。工厂的厂房卖给了港商,要和政府合作开发。工人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和港商与政府之间展开了一些矛盾。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工会主席朱卫国,曹征路很有意思,他不断地写到工会主席,后来在《问苍茫》里面也写到工会主席。工会这个角色在我们的生活结构里面现在变得很模糊,在西方市民社会里面,工会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当工会主席为工人维权,或者说代表工人和整个体制战斗的时候,后果可以想象。失败以后,这个工会朱主席跑到自己的工厂里面,把多年没有使用的汽锤点着了,把汽锤一拉,把自己的头颅砸碎,变成了一个无头尸体,悲壮地死去了。小说里面写了一条狗,叫帕瓦罗蒂,后来嫌麻烦就叫罗蒂了。人活不成了,还要养狗?于是把狗赶走,狗又回来了,又赶走,又回来。然后工会主席开着吉普车走了300公里,装在麻袋里面把狗扔掉了。一年以后,这个罗蒂伤痕累累,千里寻家,又回到了朱主席身边。但是这条狗还是不被待见。狗有自己的尊严,后来它爬上龙门吊跳下去死掉了。他用帕瓦罗蒂这条狗来比附中国底层工人这种命运,是否准确可以商榷,但是小说写得极端的惨烈,是我们底层文学的发轫之作,确实很有力量。
在这些作品里面,还有一个和乡土中国有关系的很重要的作家,他是河北作家叫胡学文,他的作品叫《命案高悬》,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有。《命案高悬》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胡学文自己讲的: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叫吴响的流氓无产者,游手好闲。土地、草场都分了,这个吴响没有事情就躺在自己的草场里。突然村里面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牵着两头牛过来了,要吃吴响这个草地的草。吴响说那不可以,这草地是我的,你的牛怎么可以吃呢?这不是分田到户了嘛,不可以吃。他说如果你同意什么什么的,我就允许你的牛吃草。这个少妇一听,这个成本太高了,代价太大了,不同意走掉了。这个风韵犹存的少妇后来被乡政府叫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死掉了。吴响得知后非常愤懑,他暗恋的一个女孩子死掉了,自己很难过,他要把这个案子搞清楚。《命案高悬》说的就是命案,他开始调查。一个乡间的流氓无产者和一个乡政府作对,就像前面工会主席和体制作对是一样的,后果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女孩的丈夫,为了镇政府8万块钱的封口费,任何消息都不透露给他。吴响忙了大半年,命案依然高悬。这就是底层写作。像深圳的打工文学,和底层写作有关的作家作品很多,像吴君、毕亮、谢宏等一些很年轻的作家,都写了很多很优秀的作品,是我们当下文学里面重要的潮流和现象,到现在仍然没有终结。
当然,对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文学界都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太粗糙,我的看法不一样。它写的是底层,写的是打工者,它写的不是小姐的象牙床,肯定是粗糙的。如果写的很细腻,那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那是张爱玲,是白先勇,就不叫底层写作。当然底层写作这个问题逐渐呈现出来了,就是过多的苦难,就是作家想象的底层人的这种苦难,无边无际的苦难和泪水。我曾经讲过,底层文学的苦难文学性上还要提高一下。讲到契科夫,大家都读过作品《万卡》,不足3000字的短篇小说,写了俄罗斯一个9岁的孩子,在圣诞节的一个夜晚孤苦伶仃,无辜无助。主人去过圣诞节了,留下他一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给自己的爷爷写信。整个小说3千多字,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句苦难,最后写“乡下爷爷收”。爷爷没有收到这封信,但全世界的读者都收到了万卡的这封信。这就是它的文学性,我们的底层写作可以说远远地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但是底层写作的出现,使中国文学也从1993年到2005年,12年间淡出了公众视野,重新又被读者所关注。.这是底层文学的功绩。
过去那十几年,文学和我们社会和民众的生活没有关系了,我们当然可以淡忘它,可以不关注它。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矛盾也越来越突出,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底层问题在底层写作里面被呈现出来以后,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这应该说是文学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但是这里面隐含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作家作品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叫作民粹主义。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里面,有非常鲜明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写工农兵,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服务,讲我们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服务于民众。走向民间,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学习老百姓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延安文学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底层写作和我们的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勾勒起来,它是一个文学脉流。
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这个倾向问题太大了。2010年前后,在扬州大学同时开了两个会,一是底层文学“到城里去”,还有就是社会学开的一个会,也是讨论底层的。去听社会学关于底层的发言和讲述,看他们的文章,真是受益匪浅。孙立平教授是清华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教授,他有一篇文章叫《底层的沦陷》,一篇文章把批评界多少年搞不清楚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文章讲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山西黑砖窑现象。这个黑砖窑里欺压这些工友的人是一个只读过三年级的普通农民。他本身也在底层,但是为了金钱,他的道德已经完全没有底线了,所有叫作《底层的沦陷》。社会学学者用社会学的方法和目光发现了这个问题,这和文学的知识分子(作家们)所表达的那种同情、悲悯,那种苦难和泪水的讲述,显然要深刻得多。
很多作家发现了边缘经验
当下的文学创作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有一些主流的经验,讲述的对象和书写的对象是主流的。近些年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很多作家发现了边缘经验。这个边缘经验里面最重要的有这么几部作品,一是广东作家魏斌,还有就是前两年发表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叫《一句顶一万句》,大家可能都看过了。这个作品很重要,我感到这个小说在结构上和它的整个想象力,和我们此前看到的所有讲述历史的作品,发生重要变化。
过去小说为了攀高结贵,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身份,它延续两个传统,一个叫作诗骚传统,一个叫作史传传统。什么叫诗骚传统?就是小说开篇有诗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和诗有关系。小说结束的时候又有诗云,如何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另一方面就是史传传统,小说不重要,但是历史重要。史传传统就是所有的小说一定要和历史建构联系起来,要学习《史记》《左传》。比如《三国演义》。这么多年,我们发现的唯一的一部比真实的历史叙述影响还要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三国演义》,知道陈寿《三国志》的人不多,但没有人不知道《三国演义》。这当然也和从黑格尔一直到斯宾格勒建构的西方巨大的历史哲学有关。我们评价小说的一个尺度叫作史诗,小说一定要跟历史建构联系起来。
《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前后70年,但是当下中国的风云际会和70年中国社会历史生活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它只讲述了一个叫杨百顺或者吴摩西的这样一个人去寻找那一句话。刚才我讲过承认是一种政治,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夫妻之间没话说就糟糕了,肯定出问题了,叫冷战。有话说是互相之间有兴趣,有说不完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寻找的就是这个东西。杨百顺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是个孤儿,非常勤奋。后来娶了一个老婆叫吴香香,是倒插门过来的。男人倒插门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名字改了,不能叫杨百顺,叫吴摩西,跟人家的姓。开个饭铺,每天蒸馒头,两个人过得不冷不淡的,就是过日子吧。有一天,吴摩西要到山西去贩葱。这个地方我讲过多次,我说这是个败笔,一个小饭铺能用多少葱啊?你到超市里去买几斤葱,就是贵几块钱,这个成本也要低得多。让他到山西去了,他惦记家里,原先计划三天回到家里,他两天半就赶回来了,半夜赶到家里来了,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里有说话的声音,又一听是自己的朋友跟妻子吴香香在一起苟且。苟且完了之后两人说话,说完了又苟且,苟且完了之后再说一会儿话。说睡吧,再说一会儿,再说就再说一会儿。作为男人,这个时候肯定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吴摩西(杨百顺)把腰刀就抽出来了。抽出来之后,他又放回去了。他没进去,如果进了房间就变成《水浒传》了。于是吴摩西(杨百顺)想,人家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吴香香跟我结婚一年多了,都没有说这么多的话,她除了骂我也不跟我说话。两个人有这么多说不完的话,那两个人是真好,自己就走了,这叫出延津记。后来自己的养女又有了儿子叫牛爱国。牛爱国遇到的问题和他姥爷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也要找那一句话。于是就有了回延津记。《一句顶一万句》找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就是在《一句顶一万句》70年的这个历史讲述里面,就是它带来新的贡献,这里面和历史没有关系,和历史的风云际会没有关系,就是讲普通民众说话的故事。这个经验我们在过去的小说里面读到过吗?没有,这是边缘经验。作家魏微有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叫《家道》,写官场的。他不写贪官,写贪官被抓走之后他家属是怎么生活的,这都是很有想象力的。其他的还有像当下的青春文学,包括职场小说、80后写作等,都是我们当下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