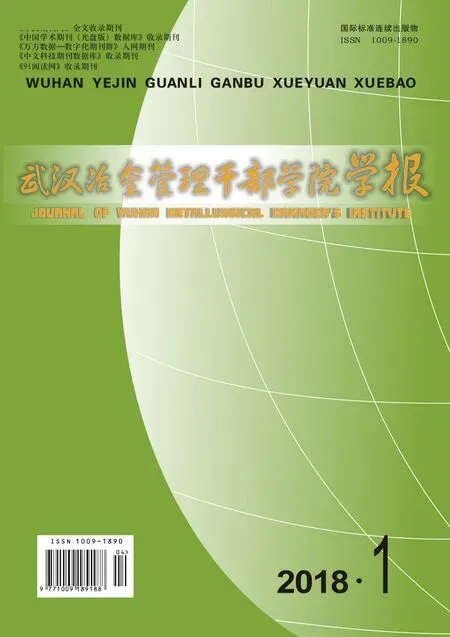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四重性
黄文著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悲剧的核心是冲突,冲突源于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则是矛盾的消解。依据古希腊经典悲剧理论的原则,意志的冲突决定了悲剧的基本特征;力量对比的差异决定了悲剧的结局;主体意志力的强大与否决定了悲剧的审美特征是悲壮还是悲伤乃至悲哀。
具体就《孔雀东南飞》这一作品而言,它的悲剧性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根本性矛盾(历史性冲突);二是内在性矛盾(性格冲突);三是外在性矛盾(误会性冲突);四是偶然性矛盾(干扰性冲突)。这也就是《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四重性。
一、历史性冲突——根本性矛盾
这一矛盾是围绕这婚姻而展开的。在中国古代,因为婚姻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家族的事,它与财产、门第、政治等因素相联系,男女两性的结合是以男女双方姓氏的结合为前提的,所以在婚姻关系中,决定权在父母那里。因此婚姻中的冲突就集中地表现为子女与父母的矛盾。
在焦母与刘兰芝、焦仲卿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兰芝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依然不能讨得焦母的喜欢——“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焦仲卿无论怎样哀求,焦母就是不答应——“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而对于焦仲卿的哀求乃至威胁“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焦母的态度可谓坚定且专横——“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在“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会不相从许”的斥责声中,焦仲卿只能败下阵来,——“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
刘兄亦是这一悲剧的制造者,是帮凶。长兄当父,在封建时代,长兄是家庭的继承人,父亲不在,家庭的主持人自然就是长兄。三从四德是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女性的地位始终处在从属的位置。刘兄的登场把事情引向了深渊——“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对于刘兰芝改嫁“郎君”,刘兄是力促其成的,因为这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利益,而刘兰芝的反对自然就激起了刘兄的恼怒,这种十足的功利心与刘、焦二人的感情誓言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实用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对立中,悲剧不可避免。
在历史的纵向关系上,时间不在刘兰芝和焦仲卿一边,“这就造成了一种两难之境,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种两难之境的解决,就是代表片面伦理力量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的牺牲好像是无辜的,但就整个世界秩序而言,他们的牺牲又是‘罪有应得’的。”[2]
二、性格冲突——人物的内在性矛盾
历史性的冲突并不必然地表现为人物的冲突,因为矛盾双方如果相互妥协的话,也可以相安无事,媳妇可以熬,婆婆可以忍,起码也可以维持一种外在的形式性的和谐。但是如果人物在性格上对立严重,那么历史性的必然则会外化出来。
媳妇的熬和婆婆的忍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第二种和解方式,即“主观内在和解”[3]。前提是双方都认同和遵守某种在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价值和伦理道德,而不是把自己的片面性强化和放大,强加于人,以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在《孔雀东南飞》中,矛盾双双都在坚定地坚守自己的立场,以互不妥协的态度在向对方宣战,这是他们性格的使然,内在的坚守如此的决绝以至于无法达到黑格尔所说的“主观内在和解”,这就只能是以黑格尔所说的第一种和解的方式收场,也就是悲剧的结局。当然由于刘兰芝、焦仲卿和焦母三人的性格各异,他们的悲剧形态并不一样。
(一)刘兰芝
刘兰芝既不是逆来顺受、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也不是义无反顾,我行我素的现代女性,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女性。“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这是她出嫁前所受到的全部教育,是一个封建礼教塑造出来的符合其规范的完美女性。她的内在矛盾是既受制于之又反抗之,形象地说就是戴着镣铐在反抗,这是她的局限性。
刘兰芝的另一个内在冲突是在做人与做女人之间的艰难抉择。在封建社会,女人首先是女人,她并没有与男人一样获得人一样的全部权利,因此妇女被锁定在家庭这个狭小的格局里而无法获得全面的解放,她们所能争取的只能是在成为母亲后在儿子那里取得一些回报。而刘兰芝却不是这样,对于婆婆的无理指责,她做出的回答是“君家妇难为”、“及时相遣归”;对于丈夫的误解,她的应对是“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对于长兄的恼恨,她的反应是“仰头答”。我们可以发现,她对于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是极力维护的,绝不允许自己处于从属的地位而被人任意摆布,她可以忍受身体上的辛苦与劳累,但很难接受精神上的委屈。
(二)焦仲卿
显然,与刘兰芝相较,焦仲卿的性格要软弱得多,用唯唯诺诺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是焦仲卿的软弱并不是自然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在形成的,这主要源于他的生存处境。
一般而论,在家庭生活中,一个男子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母子关系,二是夫妻关系,这两个关系又必须面对一个婆媳关系。这组三角关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任何一对关系的变动都要受到其他两种关系的影响与制约。就《孔雀东南飞》而言,焦仲卿无疑处于家庭的中心位置,虽然他不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家庭中,夫妻关系是好的,母子关系也可以,问题出在了婆媳关系上。当然,婆媳关系不好,并不一定会造成焦仲卿的软弱,问题的关键是焦仲卿性格中的善良的一面使得他无法在二者之间取舍。他爱母亲,也爱妻子,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但问题是婆媳关系的不睦使得他必须二选一,对任何一方的硬心肠,都是他做不到的,他处在一个两难的境界,除了软弱,他别无选择。亚里士多德认为“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4],在《诗学》第十五章中他又重申了关于性格需要注意的几点,即性格的“善良”、“适合”与“一致”。善良体现了悲剧主体人物的合理性,善良人物的毁灭,正是悲剧的根源。故而焦仲卿的这种由于“善良”而导致的软弱,使得他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悲剧人物,诚如鲁迅所说的“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
母子关系的核心是孝,夫妻关系的核心是爱,传统文化的亲亲原则,使人际关系和睦,但也使人背负起了沉重的情感十字架。在母子关系处于强势地位的宗法社会里,夫妻关系必须让位,情感上或许可以不让,但在实际生活中必须退居其次,刘兰芝的回家在所难免。所以焦仲卿的内在矛盾,实际上是爱与孝的冲突。这是他悲剧性的真正心理根源。
(三)焦母
如果仅从文本的角度分析,焦母对刘兰芝的态度是反常的、不合情理的。以家庭论,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刘家甚至要好于焦家;以人品论,刘兰芝知书达礼、情义专一、美丽善良、勤劳肯干;以关系论,夫妻和睦,恩爱有加。因此作为一个正常的婆婆,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拆散他们的。那么问题就只能出现在焦母的身上,她的悲剧根源是人性的弱点,是心理上的嫉妒、性别上的排斥和情感上的占有所导致的人格分裂,焦母这种人格分裂可能与她丧夫守寡有关。这正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中的人物哈姆雷特与奥赛罗一样,在忧郁与嫉妒中毁掉了别人,也毁掉了自己。文章最后的“两家求合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尾,颇有“梁祝化蝶”的意味。虽然冲淡了悲剧的色彩,但对揭示人物性格颇有益处。人已逝去,矛盾消解,人物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切不复存在,一切不再纠结,人回归了理性,回归了正常,回归了现实。
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个体虽然被消灭了,但他们所代表的伦理实体并不因此而毁灭,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出现新的“和谐”与平衡,也即是“永恒正义”的胜利[6]。
三、误会性冲突——人物的外在性矛盾
这一矛盾主要是围绕情感展开的。情感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和绝对性,容不得半点牵强、怀疑甚至转移的成分。刘兰芝与焦仲卿误会,不是主要矛盾,是次要矛盾,虽然不能决定悲剧最终结局,但却影响着事件的走向。
误会的原因是言行的不一致引起的。两人先有约在前,现在却是先誓后悔,这是对爱情的背叛,对感情的亵渎,对人格的不敬,自然会激起人物强烈的反弹。所以焦仲卿的反应十分激烈:“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当失控的情绪蒙蔽了理智的清醒,刘兰芝的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以前的磐石之誓,变成了现在的蒲苇之摇,焦仲卿爱怨难抑,情急之下发出了死亡的宣言,要兑现当时的承诺,这当然当不得真,可是刘兰芝当真了。误会的诱因是信息的不对称诱发的。“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两人的预料,并没有按照他们原来的设计进行,因为命运并不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即使信息是通畅的,他们依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命运的结局不一样而已。
误会的结果不是两人的分手,不是各自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在伤感、幽怨中度过一生,而是以殉情这一极端的方式结束。
四、干扰性冲突——偶然性矛盾
这一矛盾表现为秦罗敷的出现。在对《孔雀东南飞》悲剧性的分析文章中,绝少有人提到秦罗敷的作用,即使提起,也没有把她与刘、焦二人悲剧命运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诗歌中提及秦罗敷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二是“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秦罗敷虽然没有出场,但她的出现有几个特点:
第一,提及秦罗敷的人都是焦母;第二,提及的时间是两个关键节点,一是刘、焦二人将离之时,二是焦仲卿将死之时;第三,都是在与刘兰芝的对比中提到的;第四,焦母对秦罗敷全是赞美之词:“贤女”、“可怜”、“无比”、“窈窕”、“艳城郭”。
秦罗敷对于作品悲剧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秦罗敷没有刘兰芝身上的矜持之气,性格可爱,是焦母可以掌控那类媳妇;第二,在婆媳矛盾尖锐的情形下,秦罗敷成了刘兰芝的替代人物;第三。秦罗敷的存在加剧了焦母驱逐刘兰芝的心思,加速了悲剧的进程。所以她是一个干扰性的因素,虽然她并不负有什么责任。
五、结语
以上从四个层面对《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做了梳理,其中第一重矛盾属于本质性的冲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第二重矛盾亦属于必然性的冲突,随着人的意志而发展;第三重矛盾属于非本质性的冲突,它依附于前两个矛盾,处于从属的地位,随着人的情感的变化而发展;第四重矛盾亦属于非本质性的冲突,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它丰富了这一悲剧的内容。这四重层面对该诗的悲剧性具有不同的作用,其影响力依次递减,完整地、全面地将一幅人生不幸的画卷呈献给读者。
参考文献:
[1]孔颖达.十三经注疏-仪礼丧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98.
[2][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81、284、286.
[3]吴文忠,凃力.浅谈黑格尔的悲剧理论[J].人民论坛,2011(2).
[4]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诗学—诗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
[5]鲁迅.鲁迅杂文集[M].南昌:21世纪出版社,2010:4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原野》中焦母命运倒错的三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