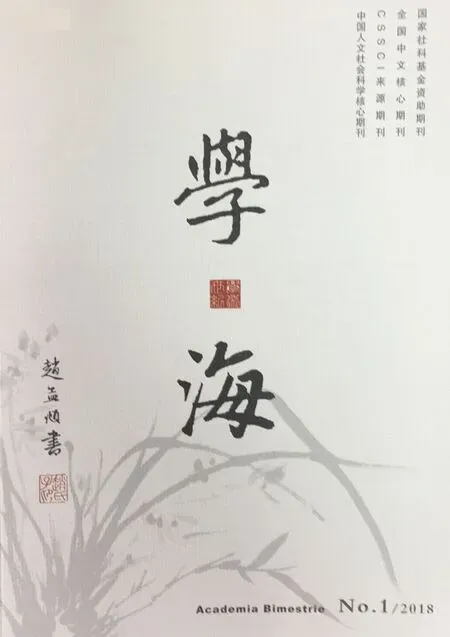胡塞尔的“发生”概念与“发生现象学”构想*
倪梁康
如何才能从混沌中勾画出一种观念的发生?
——胡塞尔(Hua XI, 414)
序 论
与其始终闭口不谈“历史现象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胡塞尔很早便在手稿中使用了“发生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r Genesis,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而对“发生(Genesis)”概念的使用以及对发生问题的思考更是早之又早。他在1918年6月29日致纳托尔普的信中甚至略带夸张地写道:“我在十多年前便已克服了静态柏拉图主义的阶段,并已将超越论发生的观念当作现象学的主要课题。”(Hua Brief. V,137)
不过对于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发生”的观念,我们还需要做更为仔细的界定。通常的看法是胡塞尔在1920年前后、亦即大致在写此信时才真正开始讨论“发生现象学”的问题。
笔者此前曾梳理过胡塞尔关于发生现象学的思考以及他对发生与时间、历史的关系的理解的发展变化,并对他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扼要地概括为:胡塞尔1900/01年的《逻辑研究》没有将“时间”与“发生”置于某种联系、哪怕是对立的联系之中。只是从个别的零散论述中可以看出胡塞尔对“时间分析”的关注和对“发生分析”的排斥。但1905年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对“时间分析”与“发生分析”的态度则有改变。胡塞尔在这里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并试图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但直至1913年,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还以柏拉图①的口吻写道:“这里不叙述历史。对于这里所说的起源性,既不需要和不应当考虑心理学的-因果的发生,也不需要和不应当考虑发展史的发生。”(Hua III, 10)此后,他在《笛卡尔式的沉思》期间(1931)对“时间”与“发生”问题的思考,表现为一种对静态现象学(对“横意向性”的分析)与发生现象学(对‘纵意向性’的分析)关系的讨论。这个思考很可能是导致胡塞尔可以在《笛卡尔式的沉思》把“时间”看作“所有本我论发生的普全形式”的原因。从这里出发,历史问题也开始,尤其是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6)中,以一种与时间与发生内在相关的方式进入胡塞尔的视野,包括历史研究的方式与历史研究的范围、历史与“时间”、“发生”内在关联,以及“形式的”和“内容的”历史现象学的可能联系与区别。②
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就“发生”问题本身而言,根据耿宁的研究,“在胡塞尔1918年前思考的‘发生’问题上可以发现有诸多与纳托尔普的共鸣(Anklänge)之处。但对于胡塞尔自己的发生现象学而言真正具有决定意义是纳托尔普的《普通心理学》的论著以及《哲学与心理学》的论文,胡塞尔于1918年8月和9月第一次对它们做了仔细的研究。”③
所有这些事实确定都会导向这样一个结论:胡塞尔1918年在纳托尔普影响下形成的“发生”观念与他在信中所说十多年前就当作现象学主要论题来思考的“发生”观念,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们的确可以在胡塞尔那里找到各种不同的“发生”概念,或者说,可以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他对“发生”问题的各种不同理解。而随他对“发生”的理解不同,胡塞尔思考的“发生现象学”也就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并且因此也会与不同的学科发生各种联系。
关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这里还可以加入一个回忆说明:在笔者1993-1995年于欧洲做洪堡基金项目研究期间去伯尔尼访问耿宁时,他曾在谈及发生现象学时向笔者意味深长地发问:“你认为胡塞尔有没有说清楚了他的发生现象学?”由于耿宁本人在享有盛名的现象学导论著作《胡塞尔思想的阐释》④一书中负责撰写“静态的与发生的现象学”一节,因此当时笔者只是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由耿宁向笔者提出来,发问的方向恰恰应该调转一下。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耿宁的这个问题很可能别有深意:由于我当时的洪堡基金项目研究的指导老师(Betreuer)是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他是兰德格雷贝的最重要学生,而后者在当时的哲学界差不多就是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的代言人。兰德格雷贝不仅本人编辑出版了胡塞尔的所谓“发生逻辑学”著作《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而且自己一生中也撰写和发表了多部与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有关的论著与论文集;特别还要留意一点: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科隆大学培养了至少四位以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为研究主题的著名现象学家,他们的博士论文均在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组织和编辑出版的《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中发表⑤。由于这四本书都是紧随耿宁在这个丛书中出版的博士论文《胡塞尔与康德》之后出版的,因而很可能引起了耿宁的格外注意。而黑尔德正是兰德格雷贝的四位弟子中最早发表相关著述的一位,同时他既是最重要的发生现象学的研究者和讲述者,也是这个传统最重要的继承者;后来在十二卷本《哲学概念历史辞典》中的“发生现象学”条目,也恰恰是由他所撰写。因而耿宁的问题很可能在于了解:我是否有可能从最知悉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人那里学到了这门学说的真正涵义。
事实上,在兰德格雷贝的任教资格准备中已经涉及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发生学问题。当时胡塞尔的这些思考尚未计划发表。只是因为兰德格雷贝作为助手受胡塞尔委托要整理出版其“第二逻辑书”⑥,如此才得以了解和熟悉胡塞尔在“发生现象学”方面的一再重复并有所修改的思考。这些思考后来主要在胡塞尔后期发表著作《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1929)、《笛卡尔式的沉思》(1931)、《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1936)和《经验与判断》(1939)中得到了零散的表达。但关于“意识的普全发生”(Hua XI, 24)问题的专门思考和讨论,实际上还是在他身前未发表、死后才作为遗稿出版的研究稿和讲座稿中,例如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1912-1929)、《第一哲学》第二卷(1923/24)、《现象学的心理学》(1925)和《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中。概括地说,这些讨论大致从1912年开始,在1916-1921年期间达到一定的系统性,最后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得到集中而概括的阐释。
尽管在胡塞尔本人看来,他的关于发生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到可以作为系统论述发表的地步,但是由胡塞尔开启的这个发生现象学研究的路向,的确为后人在此方向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可能性。
下面对胡塞尔的“发生”概念与“发生现象学”构想的阐释,可以算是笔者对耿宁多年前的问题的回答尝试以及对笔者以往相关文字的补充说明。
胡塞尔的“发生”概念
要想理解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首先需要把握他所使用的“发生”概念。我们可以在不同时期的胡塞尔那里发现含义不同的“发生”概念。在前引1918年6月致纳托尔普的信中,胡塞尔所说的“超越论发生的观念”就是其中的一个,而它更多是指胡塞尔在其时间意识分析中的“时间性的发生”。
1.时间性的发生(zeitliche Genesis)以及与时间现象学相关的问题:
在其后期的纲领性著作《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首先提到的就是“时间作为本我论(egologisch)发生的普全形式”(Hua I, § 37)。但在1905年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胡塞尔并未谈到这个意义上的“发生”问题。在谈及“发生”时,他所指的都是“经验的发生”(Hua X, 9)。不过胡塞尔在此期间已经指出了构造时间的现象与在时间中被构造的对象性的现象之间的根本差异(Hua X, 74)。对此他已经在使用“双重的意向性”的概念,亦即“横意向性”和“纵意向性”(Hua X, 81f., 380)、时间流的“横截面”与“纵剖面”(Hua X, 233, 406, 411)、“横截面的连续统”(Hua X, 232)等等说法;同时他也用图式中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来刻画时间形式的这个纵横双向的特征。
从横意向性的视角来看,纵意向性上的对象都处在不定的发生变化之中,因而“在这里要想去寻找某个在一个延续中不变化的东西,乃是毫无意义的”(Hua X, 74)但如果从纵意向性本身的视角来看,无论各个对象如何变化,它们的时间显现形式始终是统一不变的,它们的流动始终是在滞留-原印象-前摄的三位一体时间形式中发生的。当然,就总体而言,胡塞尔在这个时期尚未将时间形式与发生形式结合起来,而且他始终觉得:“对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还缺少名称。”(Hua X, 74f.)
在十多年之后,即在1918年的“逻辑学”讲座中,也是在给纳托尔普发去前引信函的那段时间前后,胡塞尔才开始将时间问题与发生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逻辑学”讲座中谈及“时间流的原发生(Urgenesis des Zeitstroms)”(Hua XI, 73),并且认为:“发生的原法则(Urgesetze)是原初时间意识的法则,是再造的法则,而后是联想的法则和联想期待的法则。此外我们还具有在主动的动机引发基础上的发生。”(Hua XI, 344)
再后,在1929年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中,胡塞尔开始专门讨论“意向发生的时间形式。滞留的变化。在未凸显之物(无意识之物)的背景中的积淀”等等问题(Hua XVII, 318ff.)。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他对发生的时间性的强调:“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要回溯到意向发生的普全本质形式上,它是内在时间性的构造,这种时间性以一种固执的合法则性主宰着每一个具体的意识体验,并且赋予所有意识体验以一种恒久的、时间性的存在。”(Hua XVII, 318)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的两段文字中,胡塞尔所说的“意向发生”已经不再仅仅是指“时间流的原发生”,而是还涉及在他那里另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发生”概念。不过在讨论这个“意向的发生”概念之前,我们先要对胡塞尔的最严格意义上的“发生”概念做一界定和分析:个体性的发生。
2.个体性的发生以及与联想现象学、积淀现象学、习性现象学、人格现象学相关的问题:
对于胡塞尔而言,最严格意义上的发生是指一种心理的、个体的、经验的发生。他在《现象学的心理学》讲座中所讨论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发生;它意味着心理个体的“人格的和历史的发生”(Hua IX, 488)。这里的“人格的(personal)”一词,与在其他地方一样,都带有两种含义:(1)个体之个性的,以及(2)一般精神生活的。⑦这个意义上的“发生”,在胡塞尔早期被他当作经验心理学的范畴放在一边。但在它获得了现象学心理学的意义之后,胡塞尔也将它纳入超越论现象学的研究范围,⑧而且由此开始讨论“一个单子的发生”(Hua XI, 343)、“在个别单子中进行的发生”(Hua I, 138),或者说,“一个纯粹主体性的普全发生”(Hua XI, 118)。
与此相符的是兰德格雷贝的学生克劳斯·黑尔德对“发生现象学”的标准定义:它“是指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构造理论的终结形态。它的课题是单子的超越论发生,即超越论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个过程导向超越论主体性的完全具体化。”⑨由此便可以理解,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为何在第37节论述了“作为本我论发生之普全形式的时间”之后,在接下来的第38和39节中立即开始分析“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以及“作为被动发生之原则的联想”。
胡塞尔本人也就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发生”问题脉络写道:“尤其是通向现象学的发生的普遍本质规律的通道很迟才得以开启,处在这种发生最底层的,乃是在不断更新的意向性构成中以及在没有那个自我的任何主动参与的统觉中进行的被动发生。在这里产生出一门联想现象学,它的概念和起源获得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面孔。这主要是借助于一个起先是奇特的认识:联想是一个本质规律性的巨大标题,一个天生的先天,没有它,自我本身是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是更高阶段的发生问题,在这种发生中,有效性的构成物通过自我-行为而产生,并且与此一致,中心的那个自我接受特殊的自我-统一性,诸如习惯的信念、习得的特征。”(Hua I, 29)
胡塞尔在这里已经勾勒出了发生问题研究的一个总体脉络。在这个思考线索中,严格意义上的“发生”至少与一个单个主体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形成和发展相关联:
其一,发生是指在单个主体的各个意识体验之间的相互接续和相互引发的关系。按照胡塞尔的描述:“一个指向另一个——尽管这里并不存在一种真正的指示与被指示的关系。此外,这个现象本身给明自身是一种发生,一个环节给明自身是唤起者,另一个环节给明自身是被唤起者。对后者的再造给明自身是通过唤起而引发的。”(Hua XI, 121)他也将这里的“发生”称作“联想性的发生(assoziative Genesis)”(EU, 77)。联想的状况“自身给明自身为发生;这一个环节的特征被意识为唤起的环节,另一个环节的特征则被意识为被唤起的环节。自然,联想并不始终以这种方式原本地被给予。也有一些在越过中间环节的前提下的间接联想情况,即这样一些联想,在它之中,并未明确地被意识到中间环节以及在它们之中存在的直接相似性。”(EU, 78)
无论如何,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联想这个标题标志着在此关系中的一个内在发生的合法则性的形式,这个形式属于意识一般并且是合乎本质的”(EU, 78)。也就是说,联想是一种有规律可循的发生,它被胡塞尔纳入到联想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中。而这个领域十分巨大,是“一个天生的先天(eingeborenen Apriori)的王国”(Hua I, 114)。例如,仅就相似性联想的范畴而言,胡塞尔便已经列出可以做进一步分析的四种类型(Hua XI, 408)。
胡塞尔据此而对发生学说与联想学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联想现象学的领域描画说:“关于再造之发生及其构成物的学说就是关于首要的和更为本真的意义上的联想学说。但与此不可分隔地连接在一起的,或者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关于联想和联想学说的一个更高阶段,即一门关于期待的发生学说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包含了现实的和可能的期待之视域在内的统觉学说。总而言之,这里关系的是前握现象的发生,即那些预测性的特殊意向的发生。”(Hua XI, 119)
关于联想现象学的系统研究,最早要回溯到艾尔玛·霍伦斯坦的基础研究上。他在其《联想现象学:胡塞尔的被动综合基本原则的结构与功能》中不仅根据胡塞尔未发表手稿而给出了胡塞尔的系统构想的基本轮廓,讨论了胡塞尔在不同领域中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联想现象学的思考,区分了联想现象的不同形式、不同结构与不同功能,而且也处理了联想现象学与动机引发的现象学、统觉现象学、共现现象学、发生现象学的关系,以及如此等等。⑩
其二,发生是指已进行的意识体验在单个主体意识生活中的积淀(Sedimentation)。
霍伦斯坦在《联想现象学》中也已经扼要地提到作为一个要素包含在联想领域中的现象:积淀。从前谓项的经验直至谓项的判断,有一系列的成就在进行中,而在达到语言阶段后开始出现的是“积淀”现象:“在一个基质上完成的特性规定与关系规定以及在逻辑层面上由一个主体陈述的谓项判断并不随着它们的成就的短暂行为而化解为无。说明与判断会作为恒久的意义层次而在基质对象或主体对象上积淀下来。积淀是一个杰出的(par excellence)的被动过程。它自己进行,无需自我在意向朝向和主动性中去启动它。”
实际上,这个意义上的“积淀”仅仅涉及胡塞尔使用的狭义的“积淀”概念。而他在手稿中思考的“积淀”现象,不仅出现在作为客体化行为一部分的语言和判断领域,也出现在作为客体化行为另一部分的感觉与表象领域:“每个活的当下成就,即每个感觉成就或对象成就都会沉淀(niederschlagen)在死的或毋宁说是沉睡的视域领域中,而且是以一种固定的积淀秩序的方式,因为一切都持续地处在沉淀之中,在开头处,活的过程获得了新的、原初的生活,在结尾处,一切都是对滞留式综合的某种程度上的终极赢得。”(Hua XI, 178)
就此而论,“积淀”在胡塞尔那里是指在客体化领域中的普遍的发生形态,而由于非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中,因而也可以得出,情感行为和意欲行为及其对象也以特定的秩序“持续地处在沉淀之中”。我们在后面还会回到这些表象的积淀、情感的积淀、意欲的积淀上来。
“沉淀”或“积淀”是指在当下意识的意识活动及其意识对象在意识流动中离开当下,沉入过去,变为或隐或显的背景、或醒或睡的视域。而后这些积淀物一方面有可能会在唤醒的联想中被拽回当下,成为当前的回忆。如胡塞尔所说:“现在我们从最根本的方面来看这个事态。我们假定一个遥远的唤起,从当下一瞬间回引到一个深埋的零度领域的积淀层次,亦即一个下坠了的遥远过去。”(Hua XI, 181)而另一方面,这些积淀物在沉睡的状态中构成在晦暗背景中起作用的无意识领域。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这个清醒意识的过程、清醒意识的构造和下坠至僵睡的过程是一个永不中断的过程,而无意识的积淀因而也始终相互叠加,与此相同,唤醒的潜能也是一个无穷无尽地持续着的潜能。” (Hua XI, 193)
日本动画片《千与千寻》中钱婆婆所说“曾经发生的事不可能忘记,只是暂时想不起来而已”,描述的就是这个状态;而被想起来的、被拽回当下的曾经发生之事,则是指前一种情况。“诚然,所有这些再回忆都回涉到隐蔽的存在者和连续地相互关联的积淀系统上。”(Hua XI, 183)
如果我们进一步询问这个积淀系统究竟属于谁,沉睡于何处,那么我们就会接近这个意义上的“发生”的第三个阶段或第三种类型。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个体自我问题:从结构的角度看,自我是一个点状的极,不断地处在意识构造的过程中;从发生的角度看,自我是一条延续的线,不断地处在意识积淀的过程中。最终这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作为极点的自我和作为诸习性的自我”(Hua IV, 310)。
其三,发生是指单个主体的意识体验积淀成为习性、成为人格。这里讨论的个体性意义上的“发生”已经涉及个体的、具体的、经验的自我通过意识活动而形成的习性,它包含稟好、个性、能力、气质、性情、品格、素质等等所有后天获得的习惯或属性,它们同样也构成人格的具体内涵。即所谓“每个个体都有其习惯。”(Hua XIV, 230)因此,这个阶段上的发生现象学的代表是习性现象学和人格现象学。它们在舍勒那里也在“形态发生(Morphgenese)”研究(GW II, 240)和“人格生成(Personwerden)”研究(GW II, 370, 520)的名义下进行。如果前面所说的发生与积淀的进行有关,这里的发生就意味着积淀的结果。意识流的积淀系统最终是由习性和人格构成的。也可以说,它们就是经验自我的基本组成。胡塞尔指出,“持存的意指”就是“在纯粹自我中的沉淀”(Hua IV, 113f., Hua I, 31f.),同时他也将自我视作“各类习性的基质”(Hua I, 100f.)。
霍伦斯坦将这个意义上的“发生”标示为“习性发生(Habitusgenese)”。尽管胡塞尔本人似乎没有使用过或极少使用这个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但他表达的意思与此相近:“自身(Selbst)的习性的这个整体指明了发生的诸本质形式、它的各个可能的主动性”(Hua IX, 259)。但霍伦斯坦并没有将“习性发生”视作积淀的结果,而是视作与积淀平行的发生过程:“与在基质对象上的意义层次的积淀相关联,在意识的自我极上也有一个类似的过程在进行。在这里得以沉淀的是作为恒久信念的个别意义创造和有效性决断。”“与积淀一样,习性发生是一种被动的构造。”这意味着,霍伦斯坦没有将积淀和习性理解为两个前后相继的发生阶段,而是理解为两个在不同方向上同时进行的发生过程:在意向相关项方面和意向活动方面的发生。这个理解有其合理性,只要我们将“积淀”和“习性”都做动词和名词的双重理解,亦即发生(Genesis)与有效性(Geltung)的双重理解:“积淀”既可以指积淀的过程,也可以指积淀的结果;习性既可以指习性养成的过程或习性化,也可以指习性化的结果,即习性。这两者可以互换。积淀的结果是习性的形成,或者说,习性化的结果是积淀层次的形成。无论用积淀的发生和结果,还是用习性的发生与结果来命名这里的两个发生现象学阶段,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这里更需要指出的是心性现象学与人格现象学的关系。胡塞尔将人格视作一种受各种习性规定的东西:“人格的主体不是单纯的纯粹主体。人格自我有可能会在它的权能(Vermögen)方面出错。但它还会有其他的权能。它必定会具有某种权能,它是自身必然发展着的和已经发展了的,它具有它的必然的发生(圆满[Teleiosis]),而我可以研究这种发生:它始终受到规定,受到在先被给予的具有(Habe)之节奏的规定,受到对一个新的对象性的朝向以及对它的处理的节奏的规定,受到对于新对象性而言的新具有(Habe)的规定。”(Hua IV, 349)在此意义上,对相对恒久的人格的研究要以整个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尤其是习性现象学的研究为前提。
当然,习性现象学和人格现象学这两个概念并不相互涵盖。这里提到的各种习性概念和习性现象学概念,事实上仅仅构成人格现象学的一部分。“人格主体”不仅仅是“主体的、发生的构成物”,而且“必须被视作一个自身发展的主体,它在这个发展的开端上就已经具有其特定素质”(Hua IV, 259)。但在人格的概念中包含着比习性因素更多的东西。胡塞尔认为,“人格自我在原初的发生中构造自身,不仅仅是作为在本欲上(triebhaft)确定的个人性,作为自始至终受原初‘本能’的驱使以及对它的被动的跟随的自我,而且也作为更高的、自主的、自由活动的、尤其是受理性动机引导的、不只是被牵引的和不自由的自我。习惯必定会形成,无论是对于原初的本能行为而言[以至于本能的驱动(instinktiver Trieb)是与习惯的驱动(Gewohnheitstrieb)的力量联结在一起的],还是对于自由的行为而言。对一个本欲(Trieb)的服从论证了服从的本欲:以合乎习惯的方式。”(Hua IV, 255)胡塞尔在这里既考虑到了人格中的习性,也考虑到了人格中的本性(Natur)、本能(Instinkt)、本欲(Trieb)。在后者那里也存在着发生的问题:本能自身的发展以及它发挥的驱动作用。
因而人格现象学或人格的发生现象学必定会涉及被动-主动综合分析、联想现象学、动机现象学、本能现象学、习性现象学等各个领域的思考。
3.历史性的发生(historische Genesis)以及与历史现象学相关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所有“发生”,都可以说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历史性的发生”(Hua XVII, 360)。所谓“历史性的发生”,可以是指单个主体性的意识体验及其积淀的“历史”以及它的人格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但在一般的、更为确切意义上的“历史性发生”,应当是指交互主体的、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前一个意义上的“个体性的发生”与这里的“历史性发生”之间存在着一个交互主体的或社会的过渡。胡塞尔曾谈及这个过渡意义上的“交互主体性的发生”(Hua VIII, 239)。他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也写道:“由于这里涉及的不是一种根据时间上先行的自身经验的经验种类的时间发生,因而显然只有一种对在陌生经验中真正可指明的意向性的准确阐释以及对在它之中本质隐含的动机引发的证明才能为我们提供启示。”(Hua I, 150)在这个意义上,一门历史现象学不仅要以发生现象学的研究,而且也要以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研究为前提。而从人格的角度来看,人格现象学不仅要研究单个人的人格,也要研究交互人格性(Interpersonalität)。
由此可以理解胡塞尔对“历史”的一个重要定义:“绝对地看,每一个本我(ego)都有其历史,而它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主体、它的历史的主体而存在。而由各个绝对自我、各个绝对主体性组成的每一个交往共同体……都具有其‘被动的’和‘主动的’历史,而且仅仅存在于这个历史中。历史是绝对存在之伟大事实(Faktum);而最终的问题、终极形而上学问题和终极目的论问题是与关于历史的绝对意义问题相一致的。”(Hua VIII, 506)
与前面提到的“人格”概念所具有的双重含义相应,人类历史作为总体人格的发生历史一方面表现为交往共同体的历史,另一方面表现为精神人格性的历史。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发生的现象学”,差不多就是狄尔泰追求的那种有着现象学-解释学方法基础的精神科学。胡塞尔本人也在接续狄尔泰的这个传统:“所有精神科学都要回溯到这个[人格的精神生活的]统一之上。但它们的课题是具体的、为了自己和为了彼此而在交互主体的发生中生成的人格主体性,它们涉及具体的个别主体和交互主体的周围世界,它是在各个发生阶段上对于相关的人格性意向地构造起来的周围世界,恰恰以如此显现的方式,恰恰以如此被评判、被估价和以劳作实践的方式被构建。在其内发生中澄清它,通过对规定着它的动机引发的指明来认识一种必然性,即在与其时间发生联系中的历史时代位置上认识这个具体存在的必然性,而且这是对人格构形的任何一个大结构形式而言,以及对人格性本身而言——这就是历史科学或精神科学的任务。”(Hua VIII, 239)
胡塞尔最终也将此称作“文化世界的精神构成物的历史发生”(Hua XVII, 360)。这也是黑尔德所理解的广义的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人类文化的所有对象都曾是通过原创立(Urstiftung)所具有的那种构成对象的成就而构造起自身的。随着每一次的原创立,意识便从此而赢得了一种一再地向新的对象回溯的权能性(Vermöglichkeit);这就意味着,对相关对象的经验逐渐成为习惯。这种‘习性化’,或者也可以说,这种‘积淀’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即不是一个由我作为实行者而启动的过程。原创立的创造行为在这里通常会被遗忘。这种习惯逐渐成为一种亲熟性,即非课题地亲熟了这种对有关对象的经验的权能性。但这就意味着:通过对原创立的被动习性化,一个视域被构造起来,意识便持续地生活在这个视域中,它并不需要在原创立的主动性中一再地重新进行这个视域的原初形成。带着这个思想,构造理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逐渐成为它的基本课题的是视域意识在其中得以形成和丰富的内部历史,它的‘发生’。”
如前所述,虽然胡塞尔至迟在二十年代初便使用了“发生现象学”的概念(Hua XI, 336, Hua I, 141),但他似乎从未使用过“历史现象学”的概念。这很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发生”构成“发生”问题的最后的和最广的部分。在完成对其他部分的发生问题(时间性发生、个体性发生)研究之前,对历史性发生的研究尚无全面而系统地展开的可能。对此,胡塞尔在1925年4月3日致卡西尔的信中有所暗示:“历史的发生是受本质法则主宰的。从超越论的结构以及包含其中的超越论生活的发生的‘ABC’出发,就可以理解一个人类一般的具体发展类型学的必然阶段:现行的、但并非最终有效的世界观的发展类型学,同样还有在已经苏醒的理性阶段上的普全假象与迷惑的类型学。此外另一方面当然还有实际性(Faktizität)本身的问题,即‘非理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它们只有在一种扩展了的康德假设的方法中才能得到处理。这可能是康德的最伟大的发现。当然,所有康德的东西都只是发现,它首先需要得到最终的科学构形、论证、界定。”(Hua Brief. V, 5f.)
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尔晚年对欧洲危机的历史哲学思考,的确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色彩。这种被迫并非是指他不得不在一个他从未涉足的领域中去思考他未曾思考过的东西,而是意味着,他不得不将他认为尚未成熟到可发表的东西付诸发表。
除了以上三种构成胡塞尔“发生”概念的系统内涵的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胡塞尔那里发现另外两种对“发生”概念的非常态用法。
4.构造性的发生(konstitutive Genesis)或意向性的发生(intentionale Genesis)以及与双重意义上的构造现象学相关的问题:
胡塞尔也常常谈到“构造性的发生(Hua I, 111, EU, 328)”或“意向性的发生(Hua XVII)”以及在相应的双重意义上的“构造现象学”。这里涉及的是在胡塞尔那里最宽泛意义上的“发生”概念:“普全的发生(universale Genesis)”(Hua I, 109)。它基本上是与胡塞尔的“构造”概念同义的。胡塞尔认为,根据这种普全发生的形式合法则性,在一种特定的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形式结构中,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流动被给予方式会一再地得到统一的构造。在此意义上,构造是一种发生,发生也是一种构造。它们被胡塞尔当作同义词使用,只是偶尔会加上引号:“所有意向统一都是出自一个意向发生,都是‘被构造’的统一,而且始终可以向‘已成的(fertig)’统一探问它们的构造、它们的总体发生,而且探问它们的可以本质把握的本质形式。”(Hua XVII, 216)
这个意义上的“构造性的发生”在二十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胡塞尔的表达中。他甚至也将它们当作同义词来使用(Hua XVII, 215)。英加尔登在回忆他于1927年秋访问胡塞尔时说,他常常从胡塞尔口中,或从兰德格雷贝口中听到“一切都是被构造的”的说法。而与“发生”相关的类似说法,在1923/24年的胡塞尔讲座中就可以发现:“超越论地看,一切存在都处在一个普全的主体的发生之中”(Hua VIII, 225)。
如果将“发生”理解为“构造”或者反之,那么胡塞尔所说的超越论的意识构造首先可以意味着意向性的构造:意向活动的构造与意向相关项的被构造。胡塞尔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谈及“意识发生(Bewußtseinsgenesis)”(Hua XI, 24) ,即意向活动方面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谈及“存在发生”“意义发生”(Hua XVII, 227),即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发生。这实际上已经属于意识的静态结构或动态构造方面的问题讨论,但胡塞尔在这里也将它们纳入“构造性发生”的范畴。而在“构造性发生的视角下”,胡塞尔还进一步从观念上区分:(1)前社会的主体性,它仅仅知道内经验和外经验;(2)社会的主体性,它具有关于其他主体的经验。(Hua IV, 198f.)因此,从“前社会的主体性”到“社会主体性”也存在一个“构造性发生”的过程。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也写道:“这里会令人回想起早已熟悉的空间表象、时间表象、事物表象、数字表象等等的心理学起源问题。在现象学中,它们是作为超越论的问题,而且当然带着意向问题的意义出现的,尤其是作为被纳入普全发生问题的问题出现的。”(Hua I, 109)
普全的意识构造的问题与普全的意识发生的问题在这里合为一体。但这种术语上的等同是要付出代价的:横向的意识构造和纵向的意识发生的基本差异被遮掩了或被模糊了。
同样,“意向发生”的说法将胡塞尔的“普遍意向性理论”做了扩展,使它不仅包含了“静态释义”,也包含了“发生释义”。
“普遍意向性理论
a)原初的意识与意向变更。静态的释义,对‘意指’与被意指之物‘本身’的释义。关于同一者的可能意识方式的杂多性。
b)对发生的意向释义。经验被给予方式的发生的和静态的原初性。对于每一个对象范畴而言的‘统觉’的‘原创造’。
c)意向发生的时间形式。滞留的变化。在未凸显之物(无意识之物)的背景中的积淀。”(Hua XVII, 315ff.)
在这里依然要付出类似的代价:“纵意向性”和“横意向性”之间的本质差异被忽略了或被模糊了。
5.奠基性的发生以及与发生逻辑学或逻辑谱系学相关的问题:
除此之外,胡塞尔还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使用“发生”概念:奠基意义上的发生。我们可以将它称作“奠基性的发生”。这个意义上的“发生”较多出现在兰德格雷贝编辑出版的胡塞尔遗著《经验与判断》以及它产生于其中的胡塞尔遗稿论题卷宗中。还在1929年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中,胡塞尔便谈到:“据此,在这种发生的视角中,自在第一的判断理论是明见判断的理论,而在一门明见判断的理论(以及随之在一门判断理论一般)中,自在第一的东西是谓项的明见性向那种叫作经验的非谓项的明见性的发生的回溯。”(Hua XVII, 217)
这个意义上的“发生”后来最明显地表现在1939年才在德国境外出版的《经验与判断》中,并且通过它的副标题“逻辑谱系学研究”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它涉及各种意识行为之间的传承关系,亦即奠基关系。这种关系胡塞尔在最初在《逻辑研究》中就曾探讨过,而且对此做出了原则性的揭示:非客体化行为(如情感、意欲)奠基于客体化行为(如表象、判断)之中;判断奠基于表象之中;在表象本身之中,非直观的表象(符号表象)奠基于直观表象之中;在直观表象本身之中,想象奠基于感知之中,如此等等。
而《经验与判断》讨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即:谓项判断如何最终奠基于前谓项的经验之中。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也将此称作“发生”,即“判断模式从经验之中、特别是从外部经验之中的发生”(EU,371),或者,“在其生产的原初性中各个判断的现象学发生”(EU,15)。他进一步阐释说:“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涉及发生问题。这不是第一种(历史的以及在相应意义上与个体自身之中的历史的)发生,而且不是在任何意义上的一种认识的发生,而是一种生产,通过它,认识,例如判断,在其原初形态中、在其自身被给予性的原始形态中产生出来——这种生产会在任意的重复中一再地产生出同一个东西、同一个认识。”(EU,16)
可以看出,这里的“发生”是指“奠基”或“奠基的发生”:指一种类似的意识行为在另一种意识行为中的奠基。因而这里所说的“逻辑谱系”,是指意识行为各种类型的家族传承关系,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发生的逻辑学”,与黑格尔所理解的“逻辑学”相应合。它的意义也从关于判断的学说一直扩展到原初经验的领域。
这里也需指出,将“奠基”等同于“发生”的做法也要付出代价,即“有效性奠基”和“发生性奠基”这个基本范畴的本质差异被撇在了一边:前者是超时间的,后者则与时间有关。此外,这个意义上的“发生”关系的是横意向性,而非纵意向性。不过兰德格雷贝后来还是看到了这个本质区别。但这个等同的做法所造成的影响直至今日还能在学术界看到。
以上第三和第四两个“发生”概念已经偏离开胡塞尔赋予“发生”的真正的和准确的含义,即在前三个发生概念中表达出的含义。
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构想
对一门发生现象学或发生学理论的要求已经预设了这样的前提:发生是有规律的发生,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谈论关于它的理论或学说。因此,在本文题记中引述的胡塞尔问题并非在于“发生现象学”是否可能,而是在于“如何可能”,即“如何才能从混沌中勾画出一个观念的[或理想的]发生?”(Hua XI,414)胡塞尔相信这样一个“在开放的体验领域中的必然结果”:“来者不仅仅是来了,而且是遵循必然结果的明见法则必然而来。我们当然可以将此称作发生的法则。”(Hua XI,345)
胡塞尔曾在“发生法则(Gesetze der Genesis)”的标题下进一步区分:
“(1)这样一些发生法则,它们意味着对在体验流中的事件的相互接续而言的法则之指明。它们或者是对具体的体验而言的直接的、必然的接续法则,或对具体事件或这些事件的抽象时段、因素而言的直接、必然接续法则,例如各个滞留与逝去的体验的必然衔接,或滞留的时段与各个印象时段的必然衔接。或者它们也可以是间接的相互接续法则,如联想法则、在一个体验当下中的再造之出现法则,以及类似的期待意向的法则——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的宽泛意向、充实了的或未充实的前指与回指。
(2)那些支配着统觉之构成的合法则性(Gesetzmäßigkeiten)。统觉是这样一些意向体验,它们将某个在它们之中并非自身被给予的(并非完善地被给予的)东西意识为是在自身中被感知的,而且只要它们具有这种特性,它们便叫做统觉,即使它们也把在它们之中真正自身被给予的东西意识为自身被给予的。统觉超越出它们的内在内涵,而这就合乎本质地意味着,处在连续衔接之段落(Strecke)中的一个充实的体验有可能在这一个意识流中通过充实的综合而提供它的自身被给予之物,而在那另一个意识流中,它却提供非自身被给予之物和自同者(Selbige)。就此而论,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对未来的支配法则,但只是一个未来可能性的法则,关于意识流的一种可能持续、一种观念可能的持续。”(Hua XI,336)
胡塞尔之所以能够谈论“发生现象学”,原因就在于他相信一旦以现象学的方式把握到这些发生的法则,发生现象学的学科便可以成立了。而如前所述,由于所有的构造问题都可以被理解为发生问题,因而广义上的“构造现象学”也就意味着广义上的“发生现象学”。在1921年所做的“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思考中还可以读到胡塞尔记录下的想法:“一门构造的现象学可以考察那些统觉的联系,同一个对象在这些联系中以本质的方式构造起自身,在其被构造的自身性中表明自身是作为这个对象而被经验到的和可以被经验到的。另一门‘构造的’现象学,即发生的现象学,探讨历史,探讨这种客体化的必然历史,并因此也探讨客体本身作为一种可能认识客体的必然历史。客体的原历史(Urgeschichte)要回溯到原素的(hyletisch)客体以及内在的客体一般上,也就是要回溯到它们在原初时间意识中的发生上。在一个单子的普全发生中包含着对于这个单子而言在此存在的客体的构造历史,而在普全本质的发生现象学中,这些是对所有可想象的客体而言、与可想象的单子相关的成就;而反过来就可以获得一个与客体阶段相应的单子阶段系列。——我必须对‘观念’进行一次复核,以便弄清,即使我‘构造地’考察所有内在之物,在关于意识结构的学说与关于构造的考察之间还会有何种区别。”(Hua XI,345)所有这些都属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构想。而这里提到的“观念”,并不是指已于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而是指1912年便写出、但在经埃迪·施泰因和兰德格雷贝多次誊写加工后始终没有发表的第二卷。它的副标题就是“对构造的现象学研究”。
此后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表达了对发生现象学研究的更为坚定和更为具体的信念:“只是通过发生现象学,本我才可以作为诸多系统共属之成就的一个无限联系而得到理解,而且这些成就是构造性的,它们不断地使相对性阶段中的存在对象的新阶段成为有效的。可以理解,自我仅仅是它之所是,存在于发生之中,通过这种发生,它不断地、暂时地或持久地赢得存在着的各个世界、实在的和观念的世界;这是一种源自于本己感性创造的赢得,是在对那些同样作为典型的感性事件而内在产生的虚无、假象等等进行先天可能的和可操作的修正、删除的情况下完成的赢得。在所有这一切中,事实是非理性的,但形式、被构造对象的巨大形式系统以及它们的意向构造的相关形式系统则是先天的,是无穷无尽的先天,它在现象学的标题下得到揭示,而自我作为一个一般自我所具有的本质形式无非就在于,通过我的自身思义而得到揭示并且始终可以得到揭示。”(Hua I,29)
关于“现象学”,胡塞尔曾这样描述说:“‘现象学的’意味任何一种普全的认识论,而且首先是普全的经验态度,它将世界整体转化成为只是在主体性中的现象之整体;被普全地执行的现象学的认识论于是就包含了从属于它且全然不可分者而言的纯粹主体性,而且也包含了所有的世界现象,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作为极之自我(das Ich als Pol)与作为其意识体验之习性自我的自我(das Ich als habituelles Ich)”(Hua IX,445)。
按照这个定义,发生现象学就是一种关于意识发生的普全认识论,一种对意识发生的现象学研究。它不仅要研究作为意识现象的世界的生成和发生,也要研究作为点和线的自我的生成和发生。同时,它不仅要有别于“个体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e des Individuellen)”,即有别于“对个体发生的理解”(Hua VIII,238),也要有别于“外部-因果的发生(der äußerlich-kausalen Genesis)”研究(Hua VIII,238),即有别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亦即有别于历史决定论的进路。唯如此,发生现象学才会得以可能。
这个意义上的“发生现象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凸显于胡塞尔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现象学:
1.发生现象学要讨论的对象是发生的、流动的、时间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现象学的讨论对象正好相对,后者是静态的、无时间的。
如果通常意义上的现象学,即静态的、探讨意识结构的现象学所要把握的是“超越论的有效性(Geltung)”,那么发生现象学所探讨的就是“超越论的发生(Genesis)”。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奠基关系。在胡塞尔看来,静态现象学描述处在较低的阶段上,它最终会导向动态现象学或发生现象学。按照胡塞尔的说法,“这种‘静态的’本真描述最终总会导向发生问题,以及导向一个普全地按照本质法则自始至终主宰着人格自我之全部生活和发展的发生。因而在较高阶段上的第一‘静态现象学’上建构起动态现象学或发生现象学。”(Hua XI,286f.)
2.发生现象学的思考方向是纵向的,不同于静态现象学的横向思考方向。
无论是在发生现象学中包含的时间发生、个体发生,还是历史发生,它们都与线性的、流动的意识纵剖面有关,与意识流的“纵向”(Hua X,91,327)有关,与“纵意向性”(Hua X,81f.,380)问题有关。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区分“双重的意向性”,即“横意向性”和“纵意向性”(Hua X,81f.,380),它们构成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各自的研究课题。
3.发生现象学探讨的是个别的、经验个体的本质发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象学,后者具有普遍性诉求,即以普遍有效的意识结构为探讨课题。
由于“发生”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发生,即个体经验自我的发生,首先是个别主体人格的发生,而后是交互主体人格的发生,因而胡塞尔的发生问题思考始终要面对个体化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每个本我都有其自己的发生和历史,每个共同体也都有自己的发生和历史。这里存在一个张力:一方面,胡塞尔强调发生现象学与静态现象学一样,都是对“本质特性”和“必然形式”(Hua III,§81)的把握,因此“意识发生”应当是一种“先天的发生构造”(Hua XVII,257),另一方面,发生的研究一直要回溯到个体的“感觉材料”以及“身体性”的实际差异上,具体探讨个体与个体化问题。在这里,发生现象学的功能和任务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实际性的解释学。
4.发生现象学依据的方法是动机说明的、理解的、解释的,不同于静态现象学的描述-分析方法。
在后期处理发生现象学问题时,胡塞尔也在思考它在方法上与静态-结构现象学的对应关系。他将早期的“静态现象学”按其方法特征而称作“描述性科学”,而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则被他标识为“说明性科学”,它是对意识发生的动机引发的说明(erklären),带有非直观的构造性因素(Hua XI,340)。胡塞尔在1921年的研究文稿中已经写道:“‘说明的’(erklärende)现象学以某种方式区别于‘描述的’(beschreibende)现象学,前者是合法则发生的现象学,后者是可能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在纯粹意识中得以生成的本质形态现象学,以及这些本质形态在‘对象’和‘意义’的标题下于可能理性的王国中的目的论秩序的现象学。”(Hua XI,340)后来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再次强调并具体阐释说:相对于“描述”的基础阶段,“解释”是一种在更高阶段上的意识成就,“一种超越出描述的领域以外的方法,即超越出一个可以通过现实经验直观来实现的领域以外的方法”(Hua VI,227)。在描述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的研究之间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描述”必须限制在直观领域之内。因此,“描述性领域”也就意味着一个“可以通过经验直观来实现的领域”。而“解释”则可以超越出直观、描述的范围之外而带有构造性的成分。
结 语
还在写于1917年的未发表长文《现象学与认识论》中,胡塞尔便谈到意识的横截面与意识整体的关系问题:“特殊的认识论问题和理性理论问题一般与理性这个首先是经验的权能标题相符合(只要它们产生于其超越论的纯化之中),它们只是意识与自我问题一般的横截面,而一个横截面只有在其整体得到研究时才可能完整地被理解。”(Hua XXV,198)胡塞尔在这里已经隐约地表达了将意识的纵向发生视作意识整体的想法。
这方面的思考在海德格尔那里也可以零星地发现。他在1920年的早期弗莱堡讲座中也已经谈及心灵生活的“横截面”与“纵剖面”(GA 59,157f.)。而他这方面的思考又可以追溯到早先狄尔泰的与心理学研究相关的研究工作中(GS V,101)。他对胡塞尔专注意识生活“横截面”或“横意向性”的知性现象学感到不满足,因而希望有一种用能够直接把握和理解生命进行或历史性的“纵剖面”的历史释义方式来加以补充之。
还可以留意一点:与它们相呼应,而且同样可以追溯到狄尔泰的心理学设想那里的还有伽达默尔对“哲学解释学”和“历史解释学(historische Hermeneutik)”(GW 1,266)的任务划分:“哲学解释学”的任务在于:“它要如此远地回溯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道路上,在那里指明在所有主体性中规定着它们的实质性(Substanzialität)。”(GW 1,307)而“历史解释学”的任务在于:“它要透彻地反思在共同实事的自身性与它应当在其中被理解的变动不居的处境之间的紧张关系。”(GW 1,314)
可以说,现象学的发生学或发生现象学代表了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思想脉络,上续狄尔泰-约克的历史哲学,下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这个思想脉络也可以被称作二十世纪的佛教缘起论。“缘起”指的是心中的有条件的产生,而按现象学的说法就是合法则的发生;而“缘起法”所指的无非就是“超越论发生的合法则性”(Hua I,100)。《楞严经疏》说:“圣教自浅至深,说一切法,不出因缘二字。”于是,一切实相,终归缘起;一切结构,终归发生。
但在胡塞尔这里最终还是需要强调一点:发生是时间性的,有历史的;但发生的法则、历史的规律本身又是超时间的,一如内时间意识的三位一体形式不会随时间的流动而变化一样。这也是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既要反对自然主义,也要反对历史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于如今许多人来说,logos只是一种ethos而已。而对于胡塞尔来说,ethos也有其logos。这与黑格尔对历史与理性的理解是一致的:历史是有理性的,理性也是有历史的,易言之:历史是有逻辑的,逻辑是有历史的。
①柏拉图曾留下“我们不叙述历史”的名言(参见柏拉图《智者篇》,242c)。
②参见笔者《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哲学分析》2010年第1卷第2期。这里只是对胡塞尔在身前公开出版的文字中的关于发生问题论述的说明。后面还会介绍他在其未发表的遗稿中对此问题的思考。
③Iso Kern, “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Phaenomenologica16, Den Haag 1964, S. 350.纳托尔普的《根据批判方法的普遍心理学》(Die allgemeine Psychologie nach kritischer Methode)(第一卷)出版于1912年,而《哲学与心理学》(Philosophie und Psychologie)的长文出版于1913年。
④参见Rudolf Bernet,Iso Kern, Eduard Marbach,EdmundHusserlDarstellungseinesDenkens, Felix Meiner: Hamburg 1996.
⑤参见Klaus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Phaenomenologica23,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66;Paul Janssen, “Geschichte und Lebenswelt.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von Husserls Spätwerk”,Phaenomenologica35,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0; Antonio Aguirre,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 Zur Letztbegründung der Wissenschaft aus der radikalen Skepsis im Denken E. Husserls”,Phaenomenologica38,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2; Ante Pažanin, “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Phaenomenologica46,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2.事实上,兰德格雷贝的大弟子克莱斯格所写的博士论文《胡塞尔的空间构造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发生现象学领域。参见Ulrich Claesges, “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Phaenomenologica19,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64.
⑥这就是兰德格雷贝后来编辑出版的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它一直被胡塞尔称作“逻辑研讨(Logische Studien)”,但被兰德格雷贝错误地记作“发生逻辑学”讲座稿。对此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见笔者的相关书评:“《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1939年)”。
⑦关于“人格”的双重含义以及“人格现象学”双重任务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见笔者的论文《胡塞尔与舍勒:精神人格的结构分析与发生分析及其奠基关系问题》,《现代哲学》2017年第1期。
⑧因为对于胡塞尔而言,任何一个有效的心理学定律在经过现象学还原之后都可以作为超越论现象学的定律起作用。
⑨Klaus Held, “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inHistorischesWörterbuchderPhilosophie, Bd. 7, herausgegeben von Joachim Ritter / Karlfried Gründer / Gottfried Gabriel, Schwabe Verlag: Basel 1989, S. 505A.
⑩Elmar Holenstein, “Phä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 Zu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Phaenomenologica44,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2.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