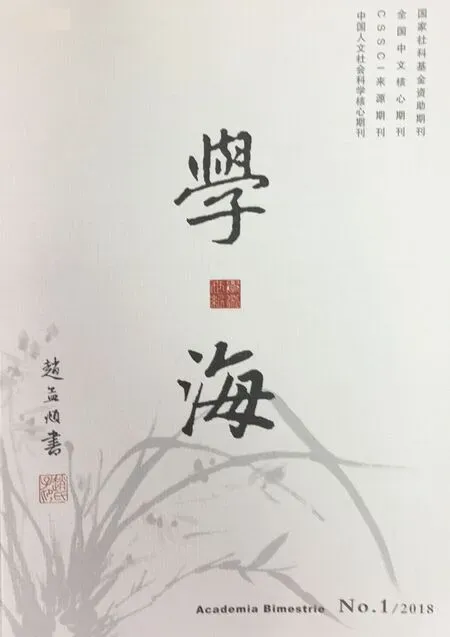政治学与中国研究
蔡永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从学术角度解释这些变化成为必要。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欲望也促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从事与中国相关的政治学研究的海内外学者也逐渐增加。国内不少大学都设有政治学系和行政管理学系,虽然系科有差异,但与政治相关的课题通常是跨学科的。通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政治成为当代中国研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研究也呈现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研究课题是问题导向和事件驱动的。因此,政治学研究的议题不但包括传统的政治哲学和外国政治,更多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发生的重要变化。此外,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规范化特点,这对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发展有直接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在概念提炼和理论建构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理论建构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尚需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
政治学的研究议题
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研究的议题是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的结合。比如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学学科里的一个重要分支,探讨的是人类社会治理和国家形成等一系列根本性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等政治哲学大家的著作本身就构成了一门学科。但是,政治学更多的研究议题是对当代现实的直接探讨,基本是问题导向或事件驱动的。当然,当代的议题也包括一些有共性的课题,比如有关民主体制的产生、巩固和质量等。
问题导向和事件驱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学者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关注的具体议题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高校的政治学课程里,美国政治不属于比较政治学范畴,而是单独的一个领域,即“美国政治”。美国政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是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诸如总统选举、议员选举和民众的投票行为等现象一直是美国政治学界的关注重点。除此之外,国会运作和国会议员的投票表决行为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而欧洲政治学研究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除政党政治这一与美国政治相似的研究领域之外,欧洲的学者们更关注福利国家问题。政府、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个重要议题。随着移民问题的出现,民粹主义及其影响将成为欧洲政治新的研究重点。相比美国与欧洲,不少发展中国家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是民主的转型与巩固以及政权更替问题。近年来发生在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权或者领导人的非正常更迭,也说明这些国家的权力更替还没有完全制度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一系列的变化给中国的政治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议题。中国政治的研究同样有共性课题和个性课题之分。具体而言,这些议题可以粗分为以下几类:(1)党的执政能力及执政理论;(2)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政商关系;(3)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及制度建设;(4)国家能力、政府效能和官员治理;(5)政府的回应性;(6)民众政治参与和政治态度等等。这些议题无不反映出中国发生的重要变化,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外学者针对这些课题做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一个以中国经验为共同研究素材、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的“中国研究”学术群体已经形成。
党的执政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而执政党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政党和社会、政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优势和强大的执行力;而海外学者的研究则侧重于执政党如何通过自我调适应对外部变化。执政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和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直接且关键性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关注执政党的政策调整和在经济建设中表现出来的重大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
政府回应性研究主要包括制度性回应和行为性回应两个方面。所谓制度性回应,是指政府通过搭建正式政治制度的方式——比如人大选举制度和基层选举制度来主动吸纳和回应民意。所谓行为性回应,是指政府在面对民众的具体诉求表达时的应对行为。
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官员或者代理人的治理。官员治理包括两个方面:晋升和监督,治理的基本手段是奖励和处罚。哪些因素影响官员晋升,这已是中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少学者就此展开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官员监督则涉及体制建设和制度执行。近年来,官员腐败现象突出,也因此而催生了一批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研究。
民众的政治参与包括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这两类方式。所谓制度化参与是指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如选举、信访、司法等渠道表达诉求。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指通过采取非常规的个人或集体行动,或诉诸公共舆论等方式表达诉求,并向政府施加压力。随着单位体制的弱化和解体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频发,民众表达诉求、寻求参与的渠道也变得多样化。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不但包括民众参与的具体方式,也包括政府解决纠纷的各种努力。当然,民众的参与也包括他们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以期影响政府政策。地方预算中的公共参与便是其中一例。
这些研究议题有一些重要特征。首先,它们有很强的现实性。这些议题都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的发展变化。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直接促进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理解。比如,社区治理成为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是因为随着单位制度的弱化,社区管理成为居民直接面临的问题。
其次,它们具有广泛性,能反映社会变化的各个重要方面,当然这也体现了学者们的学术敏感度。可以说,有关中国政治甚至社会各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虽然这些议题的现实和学理意义有差别,但它们对理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都很有帮助。
再次,它们都体现共性和个性或者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国家能力、民众政治参与、官员治理等都是政治学跨越国界的普遍性议题。但是执政党的自我建设和调节能力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类议题又体现出中国研究的特殊性。在中国和越南,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显示出强大的调适能力,这一现象就是这两个国家有地方特色的议题。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基于中国经验的广泛议题也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些方法可以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非实证研究以思辨阐述为特征,不需要借助于相对系统的实证数据,这是相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当前政治学研究的明显特征是实证研究大量增加,占据了政治学研究的要地。实证研究的方法包括:个案研究(如某个村庄或社区)、个案比较研究、多案例研究、基于调查或者其他数据的统计分析、数据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等。
很多年轻学者因为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实证方法的训练,更习惯使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计量方法来做研究。实证方法已经成为境外期刊偏好的主流方法,不少学者因为选择在境外的英文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实证方法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通常情况下是议题和材料决定了方法的选择。比如,当探讨单一事件时,个案研究就是最合适的方法。个案研究和个案比较研究被广泛运用于村庄或社区的内部运作和政府的决策过程。而类似官员晋升这类议题的研究,定量分析的方法占据主流。在腐败研究中,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都被采用,定性研究侧重于对腐败案件的深入分析,而定量研究则侧重于对腐败各个维度进行相对全面的测量。
因为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广泛性,实证研究的方法也自然呈现多样性。学者们通常把研究方法分为定量和定性两个类别,有时候还会因这两种方法的优缺点产生争议。其实,每种方法都能产生优秀的研究。应当说,因为议题的不同,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相对合适的方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定量和定性方法的争论来源于争议双方对对方研究方法的了解不够深入。譬如,有人会批评使用定量方法的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不够宏大,不够有意义,只是精致地解释常识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当然存在,甚至更严重的问题也存在。比如,有人通过数据倒推出“故事”;有的裁剪数据,漠视或忽视事件背景,让数据服务于故事;有的通过各种数据或方法,得出各种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结论。但是,把这些现象归咎于定量研究方法则是偏颇的。
定性方法的不足也是明显的。虽然基于田野的定性研究会给人带来灵感和启发,但是这种方法的样本很有限,收集的材料的可重复性比较低。定性研究对资料和逻辑的提炼要求很高。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做出优秀的研究也同样不易。或者说,用定性的方法从具体经验、故事和现象提炼出有新颖解释力的逻辑,需要相当的学术积累。这就是为什么那种“一村一理论”的方法通常行不通的原因。
优秀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力和学术感觉的积累。那些特定方法优越论的想法是不合适的。方法归根到底取决于研究问题和研究者所占有的研究资料。比如,同样是比较研究,Skocpol的名著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用的是多案例比较,①而Putnam的MakingDemocracyWork则用的是量化比较的方法。②尽管方法不同,但它们都成了政治学研究中的经典著作。
对研究方法采取开放的态度,有利于研究质量的提升和认识的提高。中国研究不该只限于中国,把中国的经验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这种比较研究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意义。比如,中国和印度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通过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理解两国发展的不同路径。再如,中国和越南同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会提升我们对政党执政能力的认识。
随着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能力的提高,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和境外政治学的趋同性在提高。方法上的趋同,使得对话和交流变得更为有效。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加入以及中外学者的合作研究,无疑会强化这种趋同性。这种现象不只是在政治学领域,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也同样存在。因此,学者间关于方法上的争论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多种方法并存会长期存在。学者们要做的是,不让方法上的差异影响学术对话和学术进步。
理论框架和理论构建
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构建非常重要。首先,因为理论有强大的概括力和解释力,它是理解一系列现象的重要工具。其次,理论是对话的语言,这在社会科学里尤为重要。因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和名词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没有歧义。没有共同的学术语言,学术对话就非常困难,理论则让这种对话成为可能。再次,理论有利于知识积累,促进研究范式的演变和进步。③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的发展,现有理论的局限会变得明显,这为理论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对理论的重视可以防止研究的过度碎片化和故事化,避免缺乏原创性的研究的大量重复。
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的理论构建有两个层面:一是概括和解释中国的某种现象;二是让别的国家通过基于中国经验建构起来的理论更好地理解自己国家的某些现象。这两个层次的理论构建既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是分割的。换言之,能概括解释中国某些现象的理论,未必能解释别的国家的现象。具有普遍性的统一理论就是既能解释中国的某些现象,也能解释别国的特定现象。
近30年来,经过中外学者的努力,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能够概括中国特定现象的概念,实现了第一层面理论构建的努力。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概念:奥森博格(Michel Oksenberg)和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提出的“碎片化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④;戴慕珍(Jean Oi)提出的“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⑤;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的“威权制度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⑥;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体制”⑦;以及欧博文(Kevin O’Brien)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⑧等等。
相对而言,超越第一层面的理论构建还比较少。这就是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所说的,中国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理论进口阶段”,还没进入“理论出口阶段”。⑨当然,这并不意味现有的研究发现和理论概念在未来不会被用于解释其他国家的重要问题,也不意味着中国研究在未来不会有重大的理论创新。⑩
理论不但是对话的基础,也是学术进步的基础,还是理解现实的重要工具。因此,理论构建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的。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西方的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的现象。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值得认真商榷。
首先,但凡理论都是具有前提条件的,如果理论前提条件不符,西方的理论在西方也不适用。因此,理论是否合适取决于前提条件差别的大小。一味地以中外为标准来划分理论是不确切的。
其次,有些批评可能是批评者基于对现有理论的有限了解展开的。这些批评通常没有指出西方的什么理论不适合解释什么现象,以及如何不适合。批评者忽视的事实是,很多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其实有很强的解释力。比如,“路径依赖”理论对于制度的选择和演变依然有很强的解释力;“集体行动的逻辑”的适用性也是广泛而普遍的。因此,对批评对象缺乏深入了解而做出的批评缺乏说服力,也缺乏建设性。另外,有些所谓的“西方理论”其实未必植根于西方经验,而是西方学者基于西方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现象,或基于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经验的比较研究所构建出来的。如果批评者发现现有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他们或许找到了理论创新的窗口,但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努力在批评者中似乎并不常见。
再次,好的理论一般都有强大的逻辑和解释力。当然,它们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并不会导致它们没有价值。一个统计模型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解释所要解释的现象;同样的道理,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很难百分之百地解释所要研究的问题。然而,这并不代表某个理论没有价值,而意味着它需要完善或者修正。对现有理论的完善和修正直接促进了学术发展。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生搬硬套地运用现有理论来解释背景不同的现象,很可能是不合适的。优秀的研究都不是基于照搬一个理论来解释某种现象的,因为那样的研究没有学术原创性,是研究者会自觉避免的。批判性的运用和发展现有理论才是常见的,也是基本的方法。
构建新理论的一个可行方法,是以现有的但不完整的理论为基础。有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是学术积累和灵感的结合,它们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不宜操之过急。奥森博格和李侃如首次提出“碎片化的威权主义”这一概念的时候,只有几行字,没有刻意为之的痕迹。当然,他们后来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地解释,并因此形成了广为流传的解释中国政府机构行为的概念。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无效概念的出现在所难免,但学界应尽量防止概念泛滥,避免制造过多没有概括力和解释力而又含义模糊甚至晦涩的概念。这些概念对学术进步没有帮助,因为他们不但没有促进学术交流,却反而阻碍了学术对话。一个逻辑清晰的解释远比一个平庸的概念更有学术价值。
结语: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日渐增强。基于中国经验研究的政治学也会迎来新的发展机会。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变化,新的研究议题将不断涌现。它们既包括体现中国独特特征的个性化议题,也涉及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通过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很可能提炼出有意义的概念和理论。学者们要构建的不是“中国特色”政治学,而是“基于中国特色经验”的政治学。
基于中国特色经验的政治学研究,应该在研究议题的设置和理论构建这两个方面体现出自身特征。从中国特色的经验中提炼出有国际社会共性价值的理论就是中国研究的学术贡献。有影响力的研究探讨的一定是有重大和持久现实影响的议题。已故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奥森博格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学者通常有个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很重要,别人的则未必。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合理。如果某个问题连学者自己都认为不重要,那么就没有研究下去的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时候一个议题重要与否,不一定取决于研究者自己的兴趣。或者说,有时候研究者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一定为其他学者所认同。尽管如此,大部分学者还是会依循自身的研究兴趣来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而重要的研究领域终归能获得学界的关注。
比如,执政党和政府的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等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成就。这些议题不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们有潜力成为中国政治学对整个政治学学科的理论贡献。相比之下,用“制度韧性”来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过于笼统,对于机制的探讨尚显不足,这些不足就可能成为激发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的动力。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也必然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学科,它理应接纳和兼容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如今,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学科之间互相借鉴理论和方法的做法已日益普遍,学者之间的跨学科合作也日趋常见。在这种大环境下,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研究也应有海纳百川的姿态,对方法、对理论都应采取开放的态度,在批判审视中前行,在学习借鉴中推进。开放的态度是实现学术进步的重要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学者们可能在研究方法、研究课题、研究发现以及概念和理论的提炼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但学术共同体的目标是促进学科发展,让中国经验得到更好的解释和更广泛准确的认识。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有着广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方面,中国已经呈现的和未来将持续呈现的重大而独特的发展特征将为学界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另一方面,学者们研究能力的不断提高也将使他们有能力更好地运用这些丰富的研究素材,对中国现象做出更具理论意义的解释。而要实现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有赖于学界始终秉持开放的学术态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避免因方法自恋和议题自恋而故步自封。
①T.Skocpol,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AComparativeAnalysisofFrance,Russiaand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②R.Putnam,MakingDemocracyWork:CivicTraditionsinModern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③T.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④K.Lieberthal, M. Oksenberg,PolicyMakinginChina:Leaders,StructuresandProc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⑤J.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dPolitics, No.1,Vol.45(1992),pp.99-126.
⑥A.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ofDemocracy, No.1,Vol.14(2003)pp. 6-17.
⑦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
⑧K.O’Brien and Li Lianjiang,RightfulResistanceinRural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⑨E.Per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TheChinaQuarterly,Vol.139(1994),pp.704-713.
⑩L.Tsai, “Bringing in China: Insights for Build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 No.3,Vol.50(2017),pp.295-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