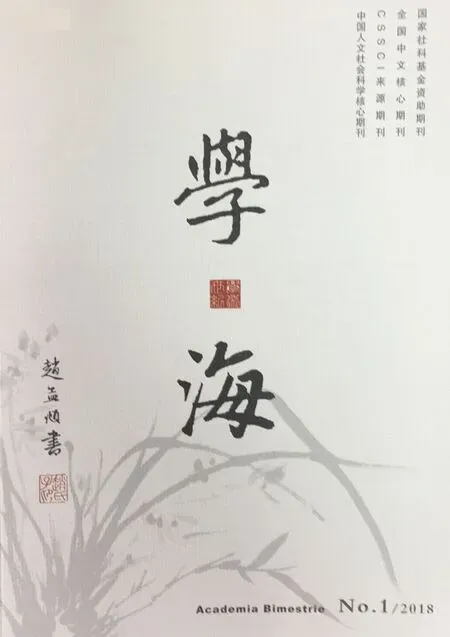西方与中国批评家眼中的图尼埃
陈 沁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以小说家、哲人作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屹立于世界文坛,先后斩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967)、龚古尔文学奖(1970)、歌德奖章(1993)、厄尔巴岛国际文学奖(1985)、卡佛文学奖(1991)、地中海文学奖(1992)、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1993)等诸多奖项,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荣膺法国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米歇尔·图尼埃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是一位属于整个欧洲的作家。他的作品游走于现实与魔幻之间,带有法国,乃至欧洲一代人的特点,充满对文学、历史、冒险、自然以及我们这片大陆的热爱,贯穿了整个20世纪并且成为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他始终努力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隔阂”①,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曾对其作如是评价。20世纪60年代以来,图尼埃就备受西方文学界与评论界瞩目,其作品先后被译成俄、德、意、英、日、韩、泰等三十多国文字。本文以时间为序,从译介、研究与接受三个层面展示图尼埃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评介与产生的影响,同时以“新寓言派”的热议事件为例,指出我国对图尼埃小说风格的不同反应。
神话·性别·哲学·教育:西方图尼埃的身份标签
西方图尼埃研究的开端与其处女作《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1967)的问世同步,自此经久不衰。《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与《桤木王》的相继获奖更是把图尼埃推向世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研究热潮。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西方学者对图尼埃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聚焦“神话”——在“神话学”中寻根的图尼埃。图尼埃神话研究热潮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至20世纪初,成为图尼埃早期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毕生挚友、法国昂热大学教授阿尔莱特·布鲁米尔的《米歇尔·图尼埃的神话小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本专著。“现代文化自觉枯竭,但其实在原初与历史上的神话母题中可以找到力量的源泉。图尼埃的作品通过复现被遗忘的伟大神话来体现其独创性与深度”②,布鲁米尔从列维·施特劳斯与丹尼斯·德·鲁日蒙的神话学理论对作家的影响着手,对时间、空间、人物姓名、人物的神话模型、文本结构与神话的关系五个方面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析读出图尼埃早期作品中所涉及的三个神话原型,即恶魔神话原型、双胞胎神话原型与双性同体神话原型,进而对图尼埃作品的双重性与二元性进行阐释与探究。这部图尼埃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为此后的图尼埃神话研究奠定了基础。布鲁米尔关注图尼埃作品的神话、互文性与《圣经》在当代历史语境下的改写研究,除专著外,她共发表关于图尼埃研究的学术论文近40篇,同时担任图尼埃研究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堪称图尼埃研究的法国首席专家。
聚焦“女性主义”——关注“性别差异”的图尼埃。自20世纪下半叶始,西方学者对图尼埃研究的焦点从神话学角度析出双性同体神话原型逐渐深入为从女性主义视域考察图尼埃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图尼埃究竟是否应该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已然成为这一时期图尼埃研究最富有争议的命题。美国佐治亚大学乔纳森·克雷尔在1997年发表《女权主义者图尼埃?夏娃的故事》,认为图尼埃作品中对女性某种程度的同情心理是“对西方父系制度文化的攻击,是对男性主义色彩集体神话的颠覆,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挑战”③。不过他反对给图尼埃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认为图尼埃摈弃女性“永恒的第二性”的传统意义,但人类社会中男性所赋有的男性特质也不可或缺,他所塑造的完美“新夏娃”人物呈现出性别平衡的双性同体形象。克雷尔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图尼埃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聚焦“哲学”——作为“哲学走私贩”④的图尼埃。自图尼埃首部作品《礼拜五》问世伊始,“哲学走私贩”的标签化形象当即成为解读其作品的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至今对图尼埃创作所蕴含的形而上研究历久弥新。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结构主义大师吉尔·德勒兹的《米歇尔·图尼埃与没有他人的世界》⑤无疑是图尼埃哲学研究的扛鼎之作。文中结合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剖析《礼拜五》所蕴藏的哲学思想。德勒兹认为图尼埃的观点是对莱布尼兹单子论与萨特“他人理论”的回应,指出这部小说的主题既不是反常,也不是鲁滨逊,而是考察一个被推入没有他者世界(荒岛)的失常主体;图尼埃通过《礼拜五》探索“他人”的意义——他人作为一种结构,是可能性世界的表现。科林·戴维斯的《哲人图尼埃》⑥(1998)以《露西或没有影子的女人》对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的映射为出发点,引发对图尼埃哲人身份的思辨;文章担心对图尼埃哲学教育背景的热捧与对其作品背后哲学寓意的追寻可能淹没对其文学本身的探讨与思考。一些批评家热衷于图尼埃与巴门尼德、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直到萨特、列维·施特劳斯的关联,塑造出图尼埃哲学家身份的固有形象。另一些批评家则反对图尼埃“教育家”“哲学家”的说教式形象,刻画出一个具有抵抗与颠覆精神的图尼埃,他们坚持作家的文本呈现出一种哲学体系的“文学等同物”,颇具趣味性甚至后现代主义意味。
聚焦“儿童文学”——作为“教育家”的图尼埃。图尼埃儿童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有莫里斯·杜尔里、桑德拉·贝克特、布鲁米尔等。《为儿童改编作品:为何改,怎样改?》指出作者对作品进行改编是一种再创作行为,并从可读性、词汇、句法与形象化的比喻四个层面对《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与《礼拜五或原始生活》进行互文性分析⑦;《为儿童写作的伟大小说家》通过对作家的访谈考察图尼埃、博思高、吉奥诺、勒克莱齐奥与尤瑟纳尔五位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指出青少年读物“语言的丰富性”与“思维的创造力”对成年读者的吸引力,就图尼埃而言,“儿童读物”并非“适合儿童的读物”,他的作品面向大众,成人与儿童都囊括其中,改编青少年版本的目的是完成一部更好的作品,一部能被所有人都读懂的作品⑧;布鲁米尔通过分析《礼拜五或原始生活》中礼拜五与鲁滨逊的关系、《炮》中路西欧与法贝儿的关系与《埃雷亚扎尔或泉水与灌木丛》中科拉与埃雷亚扎尔的关系,考察图尼埃儿童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即成人无力跨越与儿童之间存在的鸿沟,指出图尼埃儿童文学作品中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始终呼应卢梭与雨果的儿童观:儿童是美好的存在,而成人在社会中堕落。⑨
黄金·低谷·复苏:图尼埃在中国的译介之路
我国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始就对图尼埃展开译介与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图尼埃在西方的享誉度与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图尼埃在中国的热度远不及同一时代的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内译介图尼埃作品历经三个阶段。
我国最早对图尼埃的认识来自1979年《外国文艺》选登的五篇短篇译文:《鲁滨孙·克罗索的结局》(王道乾译)、《愿欢乐常在》(王道乾译)、《圣诞老太太》(肖章译)、《铃兰空地》(郝运译)、《少女与死亡》(陈乐译)。译文均选译自前一年图尼埃在法国刚出炉的短篇小说集《大松鸡》。此后,《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艺》四本重要文学刊物在1982至1999年期间相继推出作品选译,推动了这一时期图尼埃短篇小说译介的繁荣:《世界文学》1982年第3期刊载郭宏安译《维罗尼克的尸衣》;1990年第1期刊载柳鸣九译《皮埃罗或夜的秘密》《阿芒迪娜或两个花园》与唐珍译《特里斯丹·沃克斯》;1996年第6期刊载王钟华译《金胡子》与金龙格译《驴子的故事》。《当代外国文学》1983年第1期刊载王钟华译《夜的秘密》;1998年第1期刊载柳鸣九译《金胡子》与刘华译《小布塞出走》。《外国文学》1983年第9期刊载汪家荣译《愿我的欢乐常存》;1992年第1期刊载唐珍译《怎样成为一个小说家》。《外国文艺》1990年第6期刊载唐珍译《绘画的传说》《兔子和狐皮》《幽灵汽车》。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译文引进几乎与法国出版“零时差”,均选译自1989年图尼埃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夜宵故事集》。除期刊外,1986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画家陈侗的引进下出版首家独立成书的中译本《礼拜五或原始生活:鲁滨孙漂流新纪》(阎素伟/陈志萱译)。继《礼拜五》儿童改编版本引进中国8年后,成人版《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才得以发行,正式开启图尼埃长篇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之路。1994年由许钧翻译的《桤木王》(安徽文艺出版社)影响巨大,此译本先后被收录进由柳鸣九主编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死人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国当代文学丛书(2000)、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2013),成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图尼埃代表作品。
1979至1999年这二十年可谓图尼埃小说译介的黄金时段,这一阶段的中译文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译文数量多但以短篇为主。据不完全统计,第一阶段共计出版两部长篇、两部青少年小说、十九篇短篇(统计数据含复译,不含再版)。图尼埃短篇小说译介与当时的文化发展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短篇小说创作引来一个黄金季节,较中、长篇都要活跃,成为当时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文体”⑩。其二,译介类型广泛但儿童读物与短篇小说的时效性优先。从译介类型来看,长、短篇小说与儿童读物译者均有涉猎,足见这一阶段国内译者对图尼埃的浓厚兴趣。但仅从译文与原文出版时间差来比较,儿童读物与短篇小说首先进入中国读者视线,且时效性明显优先于长篇小说:短篇故事集《大松鸡》与《夜宵故事集》译文均于小说在法发行后一年内即在国内得以出版,而长篇小说《礼拜五或太平上的灵薄狱》与《桤木王》分别与原版时隔27年与24年才在国内发表。译文的选择既体现出“90年代由中、短篇为主到以长篇小说为主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内读者对图尼埃儿童文学作品与哲学寓意小说前后风格反差的接受程度。其三,这一时期的译作影响力持久,再版次数最多。迄今为止,图尼埃最辉煌的两部作品《礼拜五或太平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本)与《桤木王》(许钧译本)均再版4次,形成第一次翻译出版图尼埃作品的高潮。其四,这一时期的译介主要围绕《大松鸡》《皮埃罗或夜的秘密》与《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三部作品,译介内容的集中导致复译现象的繁生。
进入21世纪,国内的图尼埃译介相较于西方研究的热火朝天显得颇为冷清。除2002年与2003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与《桤木王》(许钧译)先后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在台湾发行繁体译本外(分别更名为《礼拜五》与《左手的记忆》),仅有2006年第2期《法语学习》上刊载的张迎旋译《画的传奇》一篇短篇译文。这一时期译介的沉寂状态一方面与作家创作后期重心的转移息息相关——图尼埃自2000年后没有再进行长篇小说体裁的创作,而转以随笔、书信集与青少年文学为文学创作的重心;另一方面从侧面呈现出图尼埃作为“哲人作家”在中国接受呈现的尴尬局面,即对晦涩难懂的哲理寓意艰难的接受过程。
2010年以来,随着图尼埃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壮大,国内的译介逐渐进入复苏期。首先体现在经典译本的再版情况:上海译文出版社接连推出的“法国当代文学丛书”系列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系列均收录图尼埃的经典作品《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本)与《桤木王》(许钧译本);《皮埃尔或夜的秘密》(柳鸣九译本)亦被收录进“法国20世纪文学译丛”。其次,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2年与2016年相继推出《爱情半夜餐》(姚梦颖译)与《夜晚的秘密》(曹杨译)两部译作。代表作的再版与新译的发行呈现出新时期国内图尼埃译介重新活跃的趋势。此外,2016年图尼埃的离世震惊世界文坛,一时间国内各大期刊纷纷推出悼文,译文的转载量也急剧增多,同一时期国内学界的“新寓言派之争”掀起了第二次图尼埃研究的热潮。
西方批评家对图尼埃的分析集中于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影响了中国批评者对图尼埃的态度。第一是图尼埃开创了现代哲理寓意与迭印叙事特色双重叠加的先河,其创作深受现代哲学的影响,作品中充满对当代语境下存在与身份的哲思,“所有伟大哲人都是引导他的灯塔,尤其是斯宾诺莎。文学上的导师是现代作家福楼拜,托马斯·曼与精神之父让-保罗·萨特”。第二是图尼埃解构神话与重塑神话的叙事策略颠覆传统意识中保留的经典形象,使神话原型在全新的历史维度中完成“自我的异化”。“图尼埃作品中的神话建构为析读现实世界而服务。图尼埃的这种写作技巧类似隐迹纸本,‘通过清洗或刮擦消除羊皮纸上的文字,以便能够再次使用’。他曾评述西班牙画家安立奎·马林的作品《西抱岛与西奈半岛》,迂回地用绘画的迭印技法阐释自己的写作技巧”。因为这两个因素,图尼作品一经引进国内,就与中国作家碰撞出思想与艺术的火花:王小坡对图尼埃的文学重要性给予肯定,李银河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王小波》一文辅之以佐证;毕飞宇谈及《桤木王》“图尔尼埃在人性之恶面前的那份冷峻令让我受震动”;王跃文称“喜欢图尼埃尔,他的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以及《桤木王》足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他没有获此殊荣”;马笑泉在《小说与不确定性》中则以图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为例展现长篇小说的不确定性所呈现的旨趣与迷人魅力。
图尼埃在中国首次受到热议离不开作家王小波的推崇,国内读者对作家的认知大多也源自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王小波撰写“我对小说的看法”篇阐述图尼埃写作风格予其的震撼与影响:“我自幼就喜欢读小说,并且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写小说,直到二十七八岁时,读到了图尼埃尔的一篇小说,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必须承认,现代小说家曾经使我大受惊吓。我读过的图尼埃尔的那篇小说,叫作《少女与死》,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因为这个发现,我曾经放弃了写小说,有整整十年在干别的事,直到将近四十岁,才回头又来尝试写小说。”
因小说中暗含的哲理寓意,图尼埃被贴上“新寓言派教父”的标签,并与勒克莱齐奥、莫迪亚克并称新寓言派三剑客。这一标签化形象在继2008年勒克莱齐奥与2014年莫迪亚克相继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热议。
“新寓言派”事件以《柳鸣九谈莫迪亚诺:法国新寓言派最杰出代表人物》为开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是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他所写的故事里有很深的寓意和隐喻,所以授奖词才用‘对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揭示’概括他的文学成就”,“在20世纪法国众多文学流派中,新寓言派是其中最了不起、最闪亮的流派”。然而何家炜反驳对“新寓言派”这一派别的定义与划分,称“有的归类与划分,却似乎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至少还没有成为文学史论著中的一个通行的专题范畴,我这里指的是新寓言派”。董强的《诺奖缘何一再青睐法国文学》为“新寓言派”的法文来源正名,“国内盛行一种说法,叫“新寓言派”,将近年获奖的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列为同一文学流派。这一说法,主要来自柳鸣九先生的一部法国文学史”,“柳鸣九的说法并非自创,而是源于一部法国人自己写的现代文学史。其作者叫雅克·布雷奈。这位布雷奈当时在梳理法国1945年到1978年的新文学时,将这三个人放在了一起,并用了一个标题“新寓言”来统领整个章节。法文叫la nouvelle fable”。
“新寓言派”标签在法国同样呈现尴尬局面,尽管这一派别在法国学界并无理论体系方面的定论,但图尼埃确实曾言“同意并很乐意把我们归在一起,称我们为‘新寓言派’,我们这一个流派,为首的可以说是尤瑟纳尔,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与于连·格拉克也可算上,当然包括莫第亚诺与勒·克雷齐奥”。《二十世纪法国伟大作家:文学选段与故事》中亦将图尼埃、莫迪亚诺等作家归为一派,称这类小说“旨在实现一种神话功能,借叙述形式和‘传说’形式把集体想象里反复出现的主要映像付诸实践,并实现集体想象与小说家个人想象的和谐统一”。回顾这一事件,尽管“新寓言派”划分的众说纷纭呈现出图尼埃接受过程中所面临的窘境,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带给读者的启迪与内心共鸣毋庸置疑,同时也再次证明图尼埃的形象接受过程必将超越单一,走向多元化解读。
①http://www.lemonde.fr/livres/article/2016/01/19/mort-de-michel-tournier-francois-hollande-salue-un-grand-ecrivain-a-l-immense-talent_4849395_3260.html.
②Arlette Bouloumié,MichelTournier:leromanmythologique,Paris:José Corti,1988,p.7.
③Jonathan F.Krell, Tournier féministe?Histoires d’Eve,TheRomanicReview,Vol. 88,No.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97,p.455.
④“Le contrebandier de la philosophie ã la bibliothque municipale,Michel Tournier face ã son public,In:Ouest-France,29 mars 2001.
⑤Gilles Deleuze, Michel Tournier et le monde sans autrui,PostfacedeVendrediouLeslimbesduPacifique,Paris:Gallimard,2013,pp.273-301.
⑥Colin Davis,Tournier philosophe,OEuvres&Critiques,Tübingen: unter narrverlag Tübingen,XXXII(2),1998,pp.27-32.
⑦Maurice Thuilière, Adaption de textes pour enfants:pourquoi,comment?,T.E.M., Texte en main, textes pour enfants,No.5,Grenoble : Atelier du texte,printemps 1986,pp. 31-44.
⑧Sandra Beckett,De Grands romanciers écrivent pour les enfants,Montréal: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1997.
⑨Arlette Bouloumié,La sagesse de l'enfant dans trois récits de Michel Tournier:Vendredi ou la Vie sauvage,La Couleuvrine,Eléazar ou la source et le buisson,Etudes francophones,Vol. XVI,No.2,Lafayette:University of Louisiana-Lafayette,2001,pp.49-56.
⑩李运抟:《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