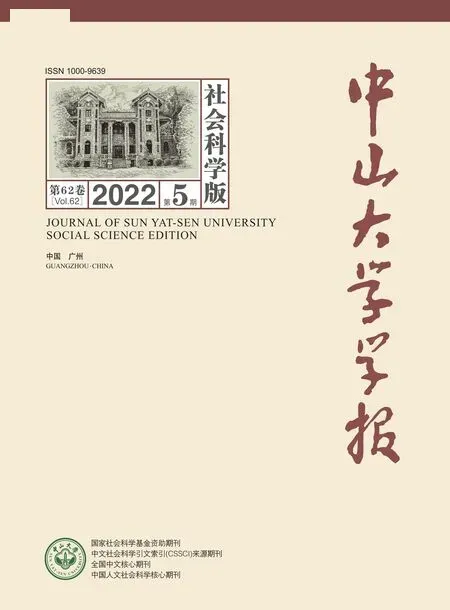语境中的胡塞尔*
——专栏导语
张任之
1933 年,胡塞尔的晚年助手欧根·芬克(E. Fink)发表长文《当下批判中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回应了新康德主义者对胡塞尔思想的批判。在这篇得到胡塞尔本人首肯的论文末尾,芬克表明,被误解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宿命,其根源在于它所包含的超越论幻象。2017 年,丹麦现象学家丹·扎哈维(D. Zahavi)在《胡塞尔的遗产》序言中感叹,即便胡塞尔研究已经非常出色,仍不能避免对其思想的基本误解,而这些误解严重阻碍了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目标与抱负的合理把握。他建议,为了切实评估胡塞尔思想的价值,我们应该追问:“胡塞尔现象学对21世纪的哲学是否仍有意义?”
无论是芬克还是扎哈维,他们都强调胡塞尔思想的当下意义,尽管他们所指的“当下”有所不同。将时间拉远了看,胡塞尔现象学的当下可以延伸至20世纪初。法国现象学家马里翁曾经意味深长地提醒读者,1900 年,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出版,同一年,尼采与世长辞,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完成了交接。尼采终结并实现了形而上学的所有可能性,现象学则肇始了一个新的开端。当马里翁说,“从本质方面来讲,在我们这个世纪,现象学承担的正是哲学的角色”,他指的正是20世纪,现象学是20世纪哲学的新生儿和弄潮儿,是20世纪哲学之子。
将时间拉近了看,胡塞尔现象学的当下则应当指扎哈维所强调的21 世纪。新世纪有了新问题,胡塞尔手稿的持续整理出版对于现象学文献与历史的探本清源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滋养于欧陆哲学传统中的现象学发展出它自身的一套话语系统,这里面有对传统哲学概念的新的意义赋予,有对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等)概念的借用,也有新的概念的创造。这些概念和话语的出现,首先是导源于现象学家们以手术刀式的精细切近到我们意识和精神生活的最精微处。分疏这些概念是出于(当然也应当要出于)一种根本的理论诉求,即跟随着现象学家们一起去面对意识和精神生活的繁复和纵深。意识生活本身并不允许我们在此过多地去使用奥卡姆剃刀,这是现象学文献与概念研究的正当性之所在。然而,阐释并非单纯的重复,新问题和新视角的引入,对于激活和展示经典文本的当下意义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新研究范式的建立与新文本的整理出版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有所偏废,则要么新研究范式因为失去文本的支撑而沦为“六经注我”,自说自话,要么这些文本因为缺乏赋义行为而未能被激活,从而变得僵化,并逐渐埋入故纸堆之中。事实上,现象学既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它既关联于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史,也旁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门其他学科),也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现象学作为一门严格的哲学本身,它始终面对的是人类精神亘古以来的那些大问题,溯源历史的根本关切当然在于,在与思想家的“历史碰面”中有厚度地探究大问题。因此,所谓哲学研究的历史进路和问题进路,本来就不能是泾渭分明的,在现象学研究中,它们可以是而且也应当是一体两面的。
新世纪以来,包括扬森(P. Janssen)、莫汉蒂(J. N. Mohanty)、莫兰(D. Moran)、史密斯(D. W.Smith)、韦尔滕(D. Welton)和扎哈维在内的一大批重要的胡塞尔学者都推出了对胡塞尔思想的导论或整体把握,他们的工作展示出,在新的思想语境中,借助于胡塞尔新文本的整理出版,我们仍然能够持续地从胡塞尔现象学中获得巨大的思想意涵。或者借用上述扎哈维的表述,他们的工作是要对“胡塞尔现象学对21世纪的哲学是否仍有意义”的问题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收录在此专栏的这组论文也可以视为在此方向上的努力与尝试。
人们并不否认,在诸多具体论题上,胡塞尔现象学能够提供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此相应,人们往往对胡塞尔的形而上学立场和超越论态度有诸多诟病。郑辟瑞的《胡塞尔与实在论—观念论之争》和谢利民的《超越实在论与观念论——胡塞尔超越论的观念论新探》是在理论向度上为胡塞尔超越论观念论立场做出的辩护。
21世纪的哲学发展中,涌现出各种形态的实在论,无论是源于现象学还是非现象学传统,它们往往都将胡塞尔的观念论作为其攻击的标靶。依据胡塞尔思想的内在结构,郑辟瑞的文章将胡塞尔关于实在论—观念论的讨论置入他的两组“内在—超越”概念之中,继而通过与之对应的两个意识概念将形而上学问题和构造的两个基本范式联系起来,这样,实在论—观念论之争就落实在这两个基本范式的有效性问题上。正是从这个方向上,胡塞尔有效地辩护了超越论的观念论与自然的实在论的可兼容性,从而证明,他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并未错失超越本身。
谢利民的文章是同一个方向上的努力。人们常常指责,胡塞尔关于“世界毁灭”的思想实验,使得他陷入了笛卡尔式的怀疑论立场,从而失去了作为超越之物的世界。该文认为,这种指责是基于对实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的误解。其辩护的要点在于,作为世界根据的意识并非可能的意识,而是现时的自我和意识,胡塞尔在此维度上颠倒了本质与事实的奠基关系,宣称此实行着现时意识的自我是“原事实”,它先于超越论自我之本质,由此,“世界毁灭”的思想实验在事实上被排除,胡塞尔重新赢得了世界。
胡塞尔将哲学家视为“无兴趣的旁观者”,这也成为胡塞尔在世人眼中的标准形象,其思想的实践向度常为人所忽略。但事实上,胡塞尔赋予其现象学的方法,即现象学的还原以深厚的实践意义,他不止一次宣称,还原类似于宗教皈依,它造就了“新人”。蔡文菁的《人性与方法——胡塞尔论伦理生活》着力于挖掘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实践和伦理意涵。它以方法为中介,将现象学之动机引发与现象学的实践向度勾连起来,充分展示出在胡塞尔哲学中,现象学之动机引发基础在于伦理生活,即一种受到完满理想引导的自我更新的生活,而这种探寻活动也展示出现象学方法独特的伦理意涵。
总的来说,这组论文作为整体是尝试在当下批判中,在理论和实践向度上为胡塞尔绘制出一幅较为整全的图像,如能引发读者的兴趣和争论,则善莫大焉。胡塞尔现象学的生命力或许恰恰就体现在语境和论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