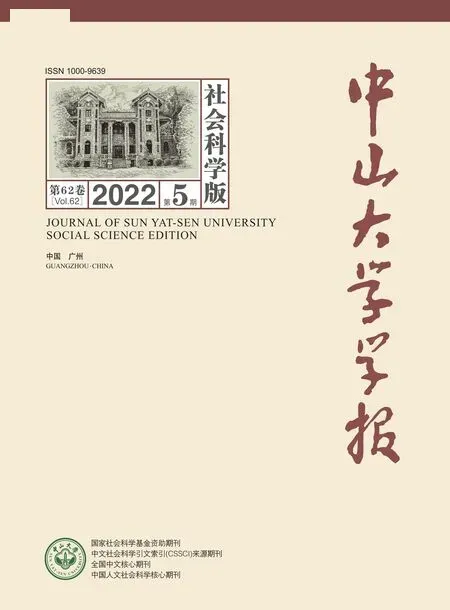编后记
本期含“名家特稿”“现象学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企业并购重组”等专栏,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7 篇。
壬寅中秋前偶读辛弃疾“天问”体《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数句,深为其极符科学的神奇想象而惊讶,王观堂因其与科学家“密合”而称其“神悟”,王评也堪称神评。但煞拍“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一句则常被隐没在此词的科学精神之外,而细思其词,恐此前种种情感之落脚点正在此处。大宋王朝虽曾一度强盛如满月,但何以今日南北分裂“渐渐如钩”?就好像陈亮唱和辛弃疾词“算世间哪有平分月”云云,这才是词人心中真正的“天问”。辛弃疾词的象征意象和灵境往往蕴含在这些地方。陶文鹏精研唐宋诗词数十年,尤其致力于诗词艺术之探究,乃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之典范。本期推出其《论辛弃疾词的象征意象和灵境》一文,乃是对辛弃疾比兴象征词所作的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文章涉及艺术方法、象征灵境等,而终究落在抗金救国之壮志以及壮志未酬之悲愤上,兼有细腻与深刻二者。
古琴是中国古代最为抒情的乐器之一,盖其声幽怨清远,入人深微而有不可形容者。元明两代琴曲承南宋之绪,以浙江之“浙操”、江西之“江操”最为驰名,元初因其作者多为南宋遗民,这一群体雅擅琴曲并切合易代之情,予以旧曲新演,以其传达低徊婉转之孤独失意情感,而被新朝斥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明初编订的《神奇秘谱》等琴谱,便是这一脉琴曲的总结性文献。曹家齐《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对此作了细致入微的辨析和源流梳理,乃是一篇兼有历史、文学与艺术特性的大文。
与曹家齐关注南宋遗民的话题相似,陈斐《〈天地间集〉:赵宋遗民的另一部“心史”》一文的关键词也是“赵宋遗民”,只是研究对象由元明琴曲而转变为谢翱编的《天地间集》,从诗歌的角度探索宋元易代之际遗民身份的认同以及相关的心史。朝代更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激烈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也存在多元选择的空间。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陈寅恪此语虽是针对元稹悼亡诗而发,却不啻为易代之际士人心态的恰切描述。衡诸历史,“贤不肖拙巧之分别”乃是一种客观现实,只是贤者拙者不一定“终于消灭而后已”,而是以多种形态继续生存在天地之间。曹、陈二文关于元明琴曲和《天地间集》的分析研究,就都是未曾消灭的遗民之思的体现。陈斐此文虽然分析的核心对象是《天地间集》,但其实是其从遗民角度展现如何以心史映射诗史,如何寻绎文本隐喻与情感指向之间的平衡点所做出的理论思考。
清代文派,阳湖与桐城二派堪称双水并流,而桐城派影响更为深远,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方才渐渐消逝。而作为文学史上的桐城文派,则依旧以清代文学的经典篇章而令人时时回味。桐城古文以考据、义理、文章三者,相当全面地贴合古文的要义而树立起自己的地位。相形之下,阳湖不仅以古文驰名,其地词学、经学也并有时誉,如此考察阳湖与桐城二地,其视野的大小自然不同。按当今文学史的叙述,阳湖文派时或以桐城支流的面目出现,原因是阳湖古文虽有规模而乏地域文学流派的理论要素。但追溯其源流,实类似星点分散的带有家族性的地域流派。文学史家多少有点截断源流,而以其后期阳湖文人与桐城文人的关系来作为界定二派关系的基础。这是片段的关系,而非两派的原初面目。唐可对此的分析,大率遵循了“了解之同情”的原则。
了解中国历史制度的人,大抵皆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皇帝是一朝政策的最终决定者。用文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皇帝才是一锤定音者。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远非简单如此,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太多特殊的情况需要分别对待。南宋偏安一隅,宋宁宗理政能力的低下,必然带来朝堂权力的松弛和相府权力的扩大,御前决策的重要性既然降低,因之自然带来都堂和相府重要性的增强。宋理宗时期史弥远专权的实现,也就是权相政治,就有着如上的背景。不过凡事皆利弊互参,一旦面临新的情况,权相政治也就随时容易垮塌。韩冠群考察史弥远主政时代的中枢政治运作过程,即为古代国家机器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相当鲜明的个案。
滋生于欧洲哲学传统的现象学,在当代中国依然呈现出显学的姿态。这也印证了一种建基于普泛性认知的理论,其生命力果然是强盛的。本期推出《胡塞尔与实在论—观念论之争》《超越实在论与观念论—胡塞尔超越论的观念论新探》《人性与方法——胡塞尔论伦理生活》三文,既有对胡塞尔基本理论的辨析,也深度介入到相关学术史的讨论之中。胡塞尔把自己的哲学定位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这自然会引起当代实在论者的反驳和批评。超越论是否超越本身?这是一个弹性较大的论证空间,而这一旦成为问题,胡塞尔便只能成为问题的一方,这使得他与另一方的争论难以停息。这其实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哲学状态。换言之,稍经交锋便平息争论的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令人怀疑的。
作为世界文学经典,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已然传播世界。但“战争与和平”这一话题,远非文学可以表现殆尽。历史学家关注作为历史现象的战争与和平,哲学家关注战争与和平内在的哲学机制。一个话题纵横在文史哲三界,也足见其特殊的情感魅力和思想魅力。读《左传》的人,往往感叹何以古代战争如此频繁,而和平如此稀少。而研究上古史的人则认为和平的世界缺少波澜,史家难以措手,一展其才胆识力;而战争的世界风云诡谲,才是史家驰骋才华的地方。这大概是古代史书多写战争的原因所在。与历史学家基于历史史实的分析不同,哲学家各依据其理论,也能导向对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基本的社会生存方式的推断。康德哲学崇尚纯粹之理性,而以理性为底蕴构建的普遍法则的公民社会,最终必然走向永久和平。尼采则庶几反之,他认为权力意志必然导致战争。老子好像是上天派来协调他们的,老子的“道法自然”与“为而不争”等说,则将战争与和平调和为一种自然而生的状态,所有“必然”的导向也就因此失去了意义。杨玉昌比较康德、尼采、老子三人关于和平与战争张力问题的讨论,也因此读来别有趣味。
本期李善民主持的专栏“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企业并购重组”,乃是当下经济学界需要直面的问题。三篇文章各有侧重,从宏观、中观到微观都做了创新性研究,相信能推动中国情境下的并购重组理论创新,助力新时代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此编后记开撰于中秋之前,因为被辛弃疾《木兰花慢》一词的科学精神与隐喻联想所吸引,居然在写编后记的间歇,草写一诗,以迎接中国最为抒情的节日:中秋。录诗如下:
如弦似镜两平常,海底周旋海上扬。
若得人生随性处,闲看冷月伴秋霜。
我依然以一首粗陋的小诗结束这篇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