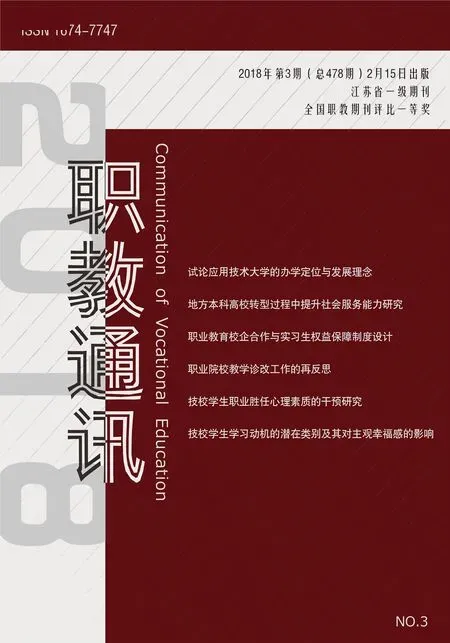沈寿、张謇和《雪宦绣谱》
臧志军
一百年前,有一位苏州女子,发明了一种新的刺绣技法,一改传统中国绣的“板滞而难得画神”的不足,运用油画、摄影作品为绣稿,按肌肉凹凸浓淡、肌理转折施针,绣品栩栩如生,这种融西画肖神仿真的新针法,被称为“仿真绣”。
这位新绣法的创始人名沈雪芝,1874年出生。她七岁弄针、八岁学绣,十几岁时已成名手,后嫁绍兴人余觉。据余觉后来描述,婚后夫妻俩一个以笔代针,一个以针代笔,画绣相辅。1904年,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余觉夫妇决定绣《八仙上寿图》和《无量寿佛图》献寿。慈禧太后观后大加赞赏,称为绝世神品,亲书“福”“寿”二字。从此,沈雪芝更名“沈寿”。
也是这一年,沈寿夫妇创办了同立绣校,从此,沈寿具有了刺绣艺术家和刺绣教育家的双重身份。此校符合许多今人对职业教育的想象:校企一体、半工半读——每期女学生四五十人,学生的绣品作为商品出售,毕业后便为绣厂工人。1907年,沈寿夫妇同赴北京,余觉任农工商部所设的女子绣工科总办,沈寿任总教习。在北京期间,沈寿认识了她一生第二个重要的男性:清末状元张謇。
1914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邀请沈寿担任所长兼教习。沈寿带着姐姐沈立、侄女沈粹缜等人一同前往任教,先后招生15期,共培养学员三百多人,其中,有后来成为苏绣研究所所长的金静芬等大师。资料所限,难以知悉沈寿在南通期间如何办学,但张謇的《追悼女工传习所余沈所长演说》中曾记:“其始绣工外,编有杞柳、麦杆,而织有花边、发网,皆传习所所长为之主任”,可以知道,沈寿的女红传习所至少有三大类专业:绣、编和织。其下又有若干课程,如织花边、织发网。这些课程极具实用性,完全符合黄炎培所说的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的宗旨。而在重点专业——刺绣——方面,沈寿则坚持了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原则,1904年,沈寿夫妇赴日本考察,亲身接触了西洋绘画与日本刺绣,大开眼界,开始在西方的素描、油画、摄影等技法上进行深度研究,发明了西洋美术技巧与中国刺绣艺术相结合的“仿真绣”。正是她在担任女红传习所所长期间的一幅《耶稣受难像》,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
对刺绣教育更为重要的是,沈寿口授、张謇手书了《雪宦绣谱》一书,详细记录了沈绣的技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说到成书的动因,张謇写道:“莽莽中国,独阙工艺之书耳”。尽管之前也曾有绣家的《绣谱》问世,如1821年道光时刺绣名家丁佩就曾专述刺绣技艺,但在此前的中国文化史上以“工艺之书”定位出版的专著十分罕见。
为什么要两人合作,而不是沈寿一人成书?因为沈寿绣艺虽佳,但文化程度不高。这几乎是所有传统技艺传承的共同问题。张謇对此有洞见:“顾其法若何,士大夫所不能知也。虽能绣之子女,亦不必能说”。他还强调:“习之无得者不能言,言之无序者不能记,记之或诬或陋或过于文,则不能信与行”。张謇想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掌握到足够程度,学者们不可能把真正的技艺记录下来,而那些真正掌握技艺的大师却往往因为文字的功力不足不一定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来。所以沈寿与张謇就是一对完美的组合。
那么,是不是一位技艺大师向学者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学者使之条理化、文本化就可以形成一本“工艺之书”?张謇如此描述他们的成书过程:“日或一两条,或二三日而竟一条。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这个过程中,张謇不是简单的记录者,而是一位诘问者、发掘者,促使技艺大师把散落的经验联系起来,形成体系,再由自己条理化地表达出来。
这对那些技艺大师来说是不是显得有点可笑,明明是自己知道的东西却偏偏要别人的诘问才能说清楚。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透明性。以锤子的使用为例,技能熟练者关注的是锤子砸上钉子后形成的敲击效果,而初学者关注的使用锤子的手感对技能熟练者而言则是透明的,不经诘问,这些透明的经验不会被表达出来。
波兰尼还断言,技能无法被按其细节进行充分解释。他认为“一门本领的规则可以是有用的,但这些规则并不决定一门本领的实践……它们不能代替这种知识”。而沈寿和张謇的工作就是想发掘出这些规则,他们的工作也证明,只要技能掌握者和技能分析者真诚地合作,技能规则可以不断细化,也许有一天可以直达技能的“内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比波兰尼更加乐观,因为在传统的工艺品生产上绝大多数现代化工艺都已超过了前人,而工艺的现代化必须以默会知识的显性化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沈寿不仅是一位使刺绣技艺现代化的女子,也是一位使中国的传统工艺学和传统工艺教育现代化的先驱。
张謇应该是同意这个说法的,他在沈寿的追悼会上说,为一个女红传习所的所长开追悼会并无先例,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欲我(南)通人士知世界美术教育之重,广我国职业教育之途”,把沈寿放在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纪念。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
——以传统文化与拼布艺术课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