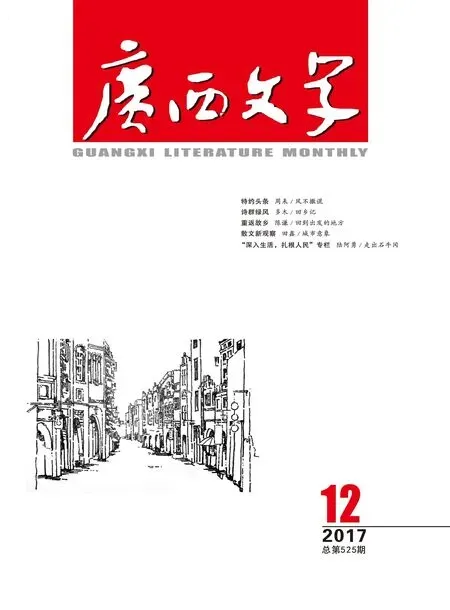梁勇散文三题
梁 勇/著
火水灯
在我老家,人们把煤油喊作火水。这很贴切,燃火的水,火水火水,就叫火水。如此,煤油灯也喊作火水灯。
先前,老家跟许多地方一样,没通电,夜晚看东西,除了星月清辉,就得点火水灯了。因此,火水也是各家日用品。大人让顽童握两瓶去打烧酒和火水,出门再三叮嘱:“记住,一斤烧酒二斤火水!”顽童怕忘记,一路念叨“一斤烧酒二斤火水”“一斤两斤”,结果就买回一斤火水二斤烧酒。火水大多用于照明,有时灶里的柴不够干燥、燃不起,就浇一点引火。我曾看过马戏团表演,上来一个光着上半身的汉子,口含火水喷火把,喷出一条火龙,使人连连惊叫!
天热的夜晚,老鼠纷纷出洞,时常咬坏东西。夜里,人们在老鼠常出没的地方装夹子,第二天发现有老鼠被夹住,顽童们来劲了。给老鼠浇火水,点燃,解开铁线,让它拖着夹子、燃着火团逃窜,又围追堵截、恐吓嚎喊,老鼠最终毙于“火刑”。那时觉着肆意快活,现在回想有对生灵的残酷,也有对“鼠辈”的憎恶。
火水灯像一件艺术品。葫芦(谐音福禄,寓意五福)形状的灯肚,顶着一圆形铁架的灯头,中间吊一根灯芯,汲取火水供火;灯头有一船舵形的小开关,来回扭转,可拔高或坠低灯芯,使灯火变大变小;灯头上戴一灯罩,可挡风,火不灭。
我记得婆太的那一盏火水灯。
婆太是我顽孩时期见过的小屯里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人。她窝在一间老屋里,天稍转冷,就坐在灶前烧柴取暖。她的容貌与别的老人没有不同,脸上的皱纹陷进骨子里,眼眶凹得很深,眼珠像古井里的月影,牙齿掉剩零丁几颗。太婆很空闲,烤火烤火,有时嗑点晒过的南瓜子,就那几颗残牙,嗑啊嗑,半日也才嗑得小堆瓜子壳。婆太怕黑,柴火燃尽,留下一堆火红的炭,她就点燃一盏带着厚厚灯罩的火水灯,使老屋洒满昏黄的光。
有时,我陪婆太烤火,烤些番薯芋头。婆太眯起眼,望望火苗,又望望我,问几岁了、谁生的?我应了,不多久,她又问。婆太记性不好。小屯的人用瓜丝洗碗,水瓜丝瓜长老了,晒干来,剥瓜皮、倒瓜子、得瓜丝。婆太常记不起瓜丝丢哪里了,找啊找,找不到,就喊我剥新瓜丝来用。我剥好了,把水瓜籽或丝瓜籽放在一小簸篓里(留着当瓜种),提醒她,别跟南瓜子弄混了,吃不得的。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还没到冬至,婆太走了,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远得再也回不来了。那时,我们家的一头大猪冲出猪栏,在岭岗跌断前脚,阿公与二伯、六叔、小叔把猪杀掉,做腊肠腊肉,还打肉糕为婆太特制几段。我很高兴,上课肚子咕噜响——呼喊喷香的腊肠腊肉咧。可腊肠腊肉还没风干,婆太就走了,在一个一大家人都睡得香甜的夜晚,悄然走了。
全屯的人为婆太送丧,男丁还在夜里为她守寿。寿棺摆在旧厅堂中间,两边摆满草席被铺,汉子孩子挤着过夜。半夜,我醒了,作法的道爷已歇息,凌乱的烛光和火水灯灯光照着那暗红的寿棺,十分阴冷。太婆生前从没骂过我,此时她睡在里面,却让我觉得惊恐。转念想到等天亮抬上岭岗一埋,从此与她永别,又觉凄惨,总有点不舍。我憋尿咬牙,不时偷望她的寿棺,胡思乱想,天快亮了才迷糊睡着……
后来,我不时梦见婆太,她端着一盏火水灯,走走停停,不知想去哪儿。然后,她手上的灯突然掉下,我就醒了。很长一段日子,对死亡的困惑与惊骇让我的梦狼狈不堪。
我孩童时真顽皮,常惹事,常被老妈打。用树枝竹棒打,真打,边打边训。打着训着,她也掉泪了。
一回,我又犯事、“被人告状”,老妈大发火,把我摁在凳子上,一手拽我耳朵,一手握着剪刀,厉声喝道:“衰仔整日犯事,教总不听,要耳朵有什么用,帮你剪掉咯!”一边围看的二妹三弟吓得大哭,我也求饶了。一会,阿婆赶来劝止:“打就打,别伤到孩子。”阿婆夺去老妈的剪刀,老妈余怒未了,抓起树杈又打。我发狠大号:“就懂打我,打打打,我去死咯,再也不回来了!”我跑出家门,跑出小屯,直奔岭岗……
天黑了,我溜回小屯对面的牛栏,爬上牛栏边的榄木,躲在榄木枝杈间,偷望小屯和我的家。我肚子饿,心痛且恨,想变作牛栏里的一头牛。终于,老妈找我了,唤我小名,喊我回家吃饭。我得意起来,不吭声,肚子都不闹了。夜渐深,阿婆叔伯婶娘也帮忙寻找,望着那些火水灯光、手电筒光,寻找我以前躲过的地方,我的得意逐渐消去。当老妈捧着火水灯、拖着瘦小的影子经过牛栏,用嘶哑的嗓音喊我,我多想应一声,嘴巴张开却没声音,我闭上眼,眼泪一下“突围”出来!
那晚上,老妈喊了多久,找了多久,哭了多久,我分不清了。后来,叔伯发现我,才把我拽回去。从此,我的性子就逐渐改了。
我终于上学了。放学回家就写字,坐小凳,趴大椅,仿课本的字一个一个写,不管懂不懂,全写下来。白天写,夜晚写,夜晚点火水灯写。老妈在一旁剥花生或补衣衫。写着,我拱起身,头靠近火水灯,老妈伸手按我额头,喊我坐好。有一回,她没留意,我额前的一卷头发就被烧了。有时,老妈问,写什么字?我答,舟。什么字?小舟的舟,就小船。她点点头,我家阿石也聪明呢!我道,等我读四年级就买一盏新火水灯,晚上带去学校上自修。老妈问,晚上你认得路吗?我答,捧着火水灯照路,走过田垄、走过小河、走过榄木根的小卖部,就到了。老妈笑了,别跟着河水走,走到大洋咯!大洋是个大镇,我去过那里赶圩,什么都有,大得就像外面的世界。
可我读四年级时,村子、小屯通电了,教室也挂了电灯。再后来,好多人家买电风扇、收录机,甚至十四寸黑白电视,红火极了。老妈给我买的新火水灯就搁在屋角,慢慢陈旧了。
榄 香
在我的家乡福岭屯,乡亲们种的都是乌榄。深秋时节,小屯的几十棵乌榄果实乌黑圆熟,乡亲们用竹竿把榄果敲打下来,洗净,开水烫浸,捞起,稍稍一抹,果肉和榄核分离,果肉用盐腌了,藏好,农忙时腌橄榄拌白粥,好吃。我记事那会,我们一大家人一起吃早餐,有时是木薯粥(就是木薯粉糊的粥),糨糊似的,几颗橄榄浮在碗里,清香诱人。要是没有这拌菜,木薯粥确实很难下咽。
榄核是小屯顽孩酷爱的玩具。常见的玩法有两种。一种是撞榄核,一群伙伴玩,榄核摆地上,轮到你,先肉眼瞄准,再用拇指和食指(或中指)推自己的榄核去撞别人的,撞到就归你,还可以接着撞。另一种是砸榄核,一大堆榄核放入一洼小窝里,出榄核多的先砸,用大榄核砸窝里的榄核,砸出几个就收几个。好玩,玩上半天一天都不觉得腻烦,尤其是大赢家,以一敌众,收了大伙的榄核,还得意地说:“不服啊?不服就回家拿榄核,再来咧!”
小屯对面的果坪有两间牛栏,旁边有一棵老榄树,是我婆太的。婆太年纪比那棵榄树的树龄还老,整天窝在老屋里烤火,看守榄果的大任便由我阿公负责。那是一棵很特别的榄树,别的榄树的榄核一般三棱,偶尔四五棱,但婆太那棵榄树有六七八棱、甚至十几棱的,简直就是榄核里的变形金刚!
午后,我们悄然爬上榄树,猴子似的在榄树上游转,寻觅大个的橄榄摘,扔进嘴里啃咬,吐掉果肉,忍不住叫嚷:“哇,七棱的,厉害吧?”彼起此伏,闹腾起来了。很快,我阿公撑着一根竹竿赶来,大声斥责:“这帮发瘟猪,打断你们的脚咯,还摘不摘榄子!”猴子们赶紧逃窜,两脚落地,立刻就跑,跃过草丛,穿过竹林,奔向岭岗,耳边是萧萧的风。有一次,阿公紧追不舍,到达岭顶,没有路了,我们相视一笑,叫喊着跳下一级又一级梯地……后来,我上学,学到狼牙山五壮士的课文,回想起那一次“跳崖”,觉得很熟悉。
我和堂哥上小学后,婆太有些挂念。小屯头边上有一棵树,根系伸延,长出木疙瘩,有时,婆太坐那里等我们放学。我们问婆太,怎么不在家里烤火?婆太睁大眼睛,眼神像老井里摇曳的月影,她笑了笑,脸全皱完了,掏一把南瓜子给我们。我们就嗑着瓜子,带她回家。有一次,婆太颤颤地掏出一把水瓜子,我们接在手里,趁她不注意扔在一旁的泥沟,又带她回家。
那一年冬天,我婆太去世了,不再留恋世间。冬至前,我们家的一头猪冲出猪栏,在山岭的梯地跌断前脚。我阿公与大伯把猪杀掉,做腊肠腊肉,还特地为婆太打了些肉糕。但是,腊肠腊肉还没风干,婆太就走了。在一个家人睡得香甜的夜晚,婆太悄然走了,谁也没有打扰。
第二年暮春,我和堂哥扔在泥沟的水瓜子,有些发芽,瓜藤攀上榄树,愈发茁壮,爬满半棵榄树。入秋,水瓜和藤叶把半棵榄树的榄果都遮住了,别的榄树收完果实,那棵榄树的大半榄果依旧青涩,只好砍断那些粗壮的藤根,枯死藤苗,晒熟榄果。
我曾看过一篇纪念胡乔木先生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件事:乔木先生平常勤力写作,仍不时抽空养护庭院的花木,姹紫嫣红,仿佛一个小花园。后来,乔木先生离世,满园落红,送别先生,草木通情,遥寄相思。有时,我忍不住痴想:那半树水瓜藤叶为什么长得那么好,顽强地结出那么多水瓜,是不是婆太想给我们送南瓜子,又错拿了水瓜子?婆太,您仍在那边榄树下等我们吗?
小时候,我们家家境贫困,我四叔去读初中,得步行几公里,怕踩坏鞋,脱下鞋拎着,赤脚走山路,快到学校,才洗脚、穿鞋。午饭在学校吃,四叔自己带去,菜是几块萝卜干或两三颗咸橄榄。后来,四叔参军,戍边,成家,考军校,定居桂林,成为走出山窝、走进城市的小屯第一人。
每次,四叔回家探亲,要返程,阿婆让他带点东西,四叔都不要,说什么也不缺。然而,看到阿婆盼望,四叔只好说,带一瓶腌橄榄吧。
著名歌唱家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经久不衰,人们耳熟能详。作词者三毛恰好就是一位童话式的流浪公主,词曲淡淡忧伤,绵绵思念,浓浓乡情,令人迷离。一缕榄香,满怀暖意——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有橄榄的地方就是故乡。
岁寒菜园三友
文人雅士说起岁寒三友,指松、竹、梅。
俗人提“岁寒三友”,似乎柴灶、火锅、烧酒更合适。
(2)变条件不变结论的“变题”。主要是指在以一题为基准,对此题的条件进行变换,而所求的结论不变。通过这一系列的题目的练习,使学生形成完整的与这道题所涉及到的相关知识结构。
作为一枚吃货,我想闲话几句岁寒“菜园三友”:白萝卜、荷兰豆、马铃薯。
入冬,菜园显得有点冷清,逾冬不凋的青菜不多,这时节,萝卜成了大赢家,占不少地盘。
小时候,我家也种白萝卜,种在河滩的沙地。冬日的河床有点“瘦”,菜地干旱,得给萝卜们浇水。对一孩子而言,挑水浇完一个萝卜园,来回往返溪河和萝卜园十几趟,苦差。但一番“闹腾”,满身热乎,又看见那些小萝卜头,又觉有点欢喜:今日还见她害羞探头,摇着蓬松的萝卜苗,过几日就拱起半个雪白身子。那时有部热播的动画片《人参娃娃》,说一个贪财地主千方百计想捉人参娃娃,有点惊讶——人参精和白胖的萝卜差不多,可爱。
大人说,经过霜打的萝卜很清甜。我偷挖过几回,尽管把皮削得很厚,就吃萝卜肉,可还是觉得有点麻辣,舌头都麻住了。其实,大人的口感和孩子的相差甚远,譬如大人说苦瓜不苦、生姜不辣、苦麻菜菜汤清甜等,没有几个孩子会“苟同”。
萝卜丰收,大人小孩拔萝卜,一担担挑回来,洗干净,切去萝卜苗,一只萝卜切成五六片、七八片,放在竹篱上晒晒,然后倒入缸里,半缸萝卜放三两包盐,慢慢用力搓,搓得吱吱作响,萝卜逐渐就变软了;捞起,铺在竹篱上晒干,就成了萝卜干。新鲜的萝卜干和猪肉炒,实在是喝酒吃饭的好菜。当然,更多的萝卜干是贮存起来,留来年天热时候,当作喝粥的伴菜,爽。
张菁的《红尘外的茶香》讲了好多高僧和茶的故事,其中就有弘一法师(李叔同)谈萝卜干的逸闻。李叔同出家后,一回夏丏尊去看他,他正吃午饭,便问夏丏尊要不要一同吃。夏丏尊说吃过了,但看到李叔同的午饭就一碗白米饭和一碟咸萝卜干,不由心酸起来,轻声问:这么咸,吃得下吗?李叔同竹箸微顿,答道:咸有咸的味道。米饭吃完后,李叔同向碗里冲了碗开水,涮涮碗底黏着的几粒米饭一同喝下。夏丏尊想起李叔同从前饭后都要品一两杯好茶,心里更酸楚,又轻轻地问:这么淡,喝得下吗?李叔同淡淡一笑,应道:淡有淡的味道。
这故事历来受人称道,饱含佛理、禅意:人生本如此,咸淡两任之。当然,那是高僧超然的智慧,在我们俗人眼里,萝卜干就是萝卜干,就拌粥的咸菜,可口就大快朵颐,管它呢。荷城大作家潘大林先生在他的一篇随笔提出一观点:来到这世界,吃过了、喝过了、玩过了、乐过了,也痛过了、苦过了、纠结过了、郁闷过了,这才算是人生。一个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县城都没进过的青年农民,忽然就说悟空了,说看破了,谁也不会知道他看破的是什么,悟空的是什么……看来,萝卜干还是吃在名人嘴里更适宜。
冬日,人们喜好吃火锅,锅里也时常会撒些萝卜片,味道还行。有时,肉吃腻了,也搞点萝卜酸来解腻。此外,人若连续咳嗽,就炖萝卜猪肺汤来食疗。可见,萝卜确是好东西。
牛肉面里没有牛肉,老婆饼不是老婆做的,荷兰豆的原产地并非荷兰:用行话说,醉了。
据闻,荷兰豆最早种植于泰国、缅甸一带,此后逐渐盛产于地中海沿岸和西亚。如此,叫做泰豆、缅甸豆似乎更“配”。
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如海蟹横行,有一伙海盗霸占台湾和南洋诸岛,荷兰豆也成为带到当地的一种舶来品,当地人就把它喊作荷兰豆。后来,下南洋的闽南人、潮汕人把这豆带回家乡,成为百姓家的寻常菜蔬。再后来,反清复明的郑成功老爷子带着船队乘风破浪杀上宝岛,把红毛鬼子赶回荷兰种郁金香、造风车了。荷兰人走了,荷兰豆却留下,且日渐茁壮生根于华夏大地了。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种荷兰豆。我阿婆把菜地翻耕好了,就喊我或堂哥点种荷兰豆种。我们捏着豆种,撒进菜畦里,阿婆就一边念叨着一边给豆种掩上一层“土被”。种完,阿婆才说,种东西有讲究,“物似人形”,老人种的东西收成总不大好,她种的丝瓜结瓜总是很伶仃,经过孩子的手就不同。
豆种下去,过几日豆苗就爬出来了。等苗长得半米多,就用竹子或树枝编织一栏篱笆,让豆苗、藤蔓撒欢地爬上去,爬满了篱笆,也确是菜地里的一道好风景。荷兰豆开的花儿有色,雪白的,蓝色、浅蓝的,或者嫣红、紫红的,挺耐看。花谢了,荷兰豆自然就“显露”了。嫩嫩的豆儿,摘下来生吃,清甜得很。另外,豆苗的头可掐摘,冬日吃火锅,洗干净的豆苗烫一烫,捞起,青翠欲滴,原汁原味,味道好极了!
小时候吃饭,我们不喜欢坐饭桌边吃,喜欢饭菜盛在大碗里,捧到地坪去吃。小伙伴集中,就斗菜。大伙通常用米饭盖起,把菜“埋藏”在碗底,斗,屁颠屁颠地问,你家吃什么菜哈?青菜不用提,大抵相同的,直接答“次菜”(仅次于肉类的菜,腐竹、豆芽、丝瓜、菜豆等)。你有腐竹我有豆腐,你有豆芽我有菜豆,你有丝瓜我有苦瓜——我苦煞了你……等对方一一作答,最终胜负如何,自己心中也有数了,就把“底牌”翻出来,不管输赢,愉悦地吃饭吧。那时确是难得吃顿肉,若你的碗里有荷兰豆炒五花肉,大多就获胜了。
转眼就大半辈子,岁随年长,喜好吃荷兰豆的脾性似乎也没多大改变。荷兰豆不但好吃,炒菜也是百搭,荤的可炒牛肉、鸡肉、腩肉、排骨、腊肠、火腿、烧鸭、叉烧、扣肉、鱿鱼、虾仁等,素的可炒莲藕、木耳、豆腐、香菇、玉米、蒜蓉、胡萝卜等,或就单独清炒也别有一番风味,甚合大众的胃口。
起初,我邀请我的对象莅临我租住的蚁窝指导后勤工作,她好奇地问,有什么菜肴呢?我笑道,包领导满意。于是,排骨玉米炖汤,炒一个青菜,主打则是香江烧鸭炒荷兰豆。最后,荷兰豆吃了个精光,烧鸭倒是剩了一些。吃饱了,两人相视一笑,离腐败还有些距离——没得四菜一汤咧。其实,有点“狐假虎威”,上好的香江烧鸭原本就很香,把荷兰豆炒个半熟,混炒几下、起锅,唔,一道好菜。
听说,荷兰那边的人把荷兰豆喊作中国豆,这幽默有点邪乎,荷兰人不认荷兰豆,中国人不识中国豆——又醉了。
马铃薯因形状酷似马铃铛而得名。我生长在南国山窝,没见过什么像样的马,也不大熟悉马铃铛的样子,只觉马铃薯有点像腰子、鹅蛋。若按照吃什么补什么的“原理”,肾虚的人吃了大概挺好,吃马铃薯补腰。
马铃薯在北边种植也不少,却被喊作土豆或山药蛋;还有的地方喊作洋芋、山芋。大概很难统一,喊习惯了。只是时下,叫土豆,无疑带几许贬义——喊你一声土豆,你敢答应吗?
南边的叫法也不一样,广东人把马铃薯喊作薯仔,在我老家却叫薯姑子。“考究”这叫法,有点意思:薯类里的小姑子,待嫁的漂亮姑娘,坚韧谦让,冷冬萧瑟的田野里挺立,等春回,山花烂漫,她在泥土里“怀”上了。
冬日田地空旷,可用上等稻田种马铃薯。翻地,挖菜畦,在里边铺些有机肥或稻草灰,发酵好,就种上长芽或长小苗苗的薯姑子种,之后也不大用管理,就等收成。
挖马铃薯是一件很快活的事。就像挖宝,拔起薯苗,有些马铃薯也跟着“溜”出来,再轻巧地拨去泥土,寻觅那一只只白净的鹅蛋似的马铃薯,抹去泥沙和松土,轻轻地放进菜篮子或小箩筐,感觉极妙。收回去的马铃薯放在阴凉的泥地板上贮藏,可留一两个月,隔三差五地拿几只出来做菜,倒也省去冷天吹痛了脸去菜园摘菜的麻烦。
马铃薯的做法真不少的,油炸薯条、薯球,马铃薯焖排骨,五花肉焖薯片,鱼香土豆,红烧土豆,醋熘土豆丝,等等,风味不一,同样馋人。我们小时候很喜好烤马铃薯。烤马铃薯和烤番薯、芋头、玉米不大一样,烤番薯清甜可口,烤玉米美味生津,烤芋头浓香怡人,烤马铃薯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又“囊括”了这几种风味;更为难得的是,吃着烤熟的马铃薯感觉不像是在吃果蔬,而是在吃荤菜、吃面包,如此看来,烤马铃薯无疑就更胜一筹了。
时下,很多人用马铃薯榨汁来养生。德国人喝马铃薯榨汁由来已久,治胃病、便秘。若嫌味淡,加点蜂蜜或果汁,也好。
年轻人喜好去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炸薯条不可少。总觉得,这是西洋“土豆”的入侵,原本营养而本真的东西,炸成那样,涂点番茄酱,味道倒爽口,却只让人虚胖。还不如返璞归真,就当本土的土豆山药蛋,煮沸滚熟了,就吧嗒吧嗒地吃,那至少是有思想营养的“土豆”!
吃马铃薯,若突然记起,想寻根究底,马铃薯怎么来的?其实简单,只因其酷似马铃铛而得名,这一喊法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松溪县志·食货》。不可忘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