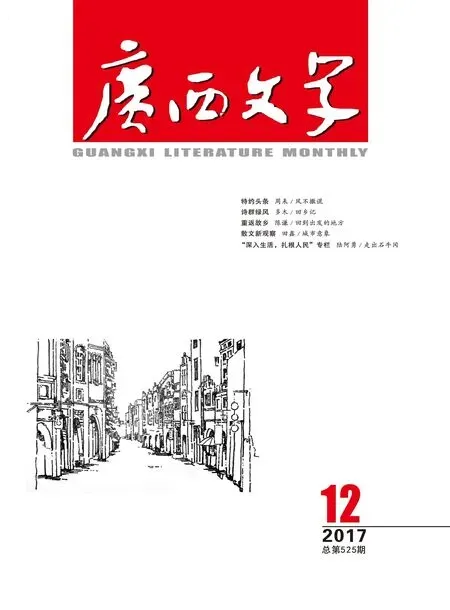哭泣游戏
郭丽莎/著
他去世多日后,化成一团黑影到来,背对着我坐在床上。我瞪着双眼,想挥手喊叫,却动弹不了。一股无名的力量,窃取了我的能力和声音。我用僵硬的身体抵抗,把房间挣扎得摇摇晃晃。这个我,用尽一生的力气,想把清醒的自己,从动弹不得的另一个自己里挣脱出来。
其实,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那儿,安静得似乎要和黑夜融为一体。
我明明记得,自己亲眼看见他被放进棺材里,一群人闹哄哄地,用绳子把棺材吊进坟墓,一松手,坟墓就变成了无底洞,棺材掉下去,连回声都没有。
终于在挣扎中醒来了。房间空空如也,空空的,只剩下空有满身疲惫的我。我渴望来根烟,最好带薄荷味的。可我起身,只给自己倒了半杯水,液体涌入喉管,在体内流窜,一瞬间,五脏六腑被冲刷得干净清凉。
我枯坐在那团黑影坐过的位置上,手握空杯子。路灯把屋子照得昏黄浑浊。马路上,偶尔有车辆提着嗓子,呼啸而过。
凌晨五点,窗外滴滴答答,下起雨了。
很多年以前,我还上小学。也是凌晨,我以同样的方式,梦见父亲过世。我在梦里哭喊,要和父亲一起睡进棺材里。众人拉着我,说爸爸累了,需要休息。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棺材,掉进深不可测的坟墓里。多日以后,父亲以模糊的身影,来到教室外。同学们吓得尖叫奔跑。我也跟着同学们跑,可父亲一直跟着我,伸手要拉我。同学们为了自保,把我推向他。被孤立的我,只好跑出教室,一直跑,一直跑,却永远跑不出门口。
八点,雨停了。我把发麻的身体挪进浴室。人一开始洗漱,就意味着要开始生活了,意味着,时间不再属于自己。
套上白色的蕾丝褶子裙,用手掌印了印脸上的粉底,我就出门了。雨后的空气,像海水一样清冷。绿萝被冲洗得一尘不染。高大的香樟树遮天蔽日,风一来,叶子和水珠哗啦啦地打在身上,吓得女孩儿们奔跑躲藏,以为雨又来了。
我的双脚,在一道落地窗外停下,流水玻璃淅淅沥沥,把坐在里面的人隔得影影绰绰,仿佛只是一个影子。继续往前走,推开咖啡馆的门,一股闷热扑面而来。我走到流水玻璃旁,在他的对面坐下,他抬头,温和一笑:“先吃点东西吧。”随后又低下头,看手上的报纸,眉头微蹙。
我喝了一口热牛奶,看着他低下去的眉眼,想着凌晨的梦。一开始,我以为真的是他,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这是过世的他。我开始恐惧、挣扎,在虚黑的夜里无声呼喊。
梦境如此真实,以至于我都怀疑,眼前的他,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
他才三十七岁,可额头就有了两道深深的皱纹,像两条并行的河流,在广阔的大地流淌。他鬓角的头发略微秃进去一些,线条柔和的脸部,眉毛疏淡,眼睛却异常清亮,湿漉漉的,如同刚刚出生的小动物的眼睛。和所有的记者一样,他心怀正义、忧国忧民,同时郁郁寡欢,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他总是皱着眉头,似乎天下苍生,都需要他操心。他的名字叫江沐。
“这则新闻毫无价值,主编却随波逐流用整个版面报道。”他把报纸摊在桌上,继续说,“人们好像越来越害怕悲伤了,整个社会只注重幸福快乐和积极思维对我们的作用。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近半分钟,我才回过神,急忙低头挪过报纸,掩盖窘态。报纸上公布了新的一轮幸福排行榜,官城荣获全国第一!二十多年前,国家开始用GNH(幸福总值)代替GDP(国内生产总值)和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评估一个城市的发展,人们拥有自己的职业和房子,能够享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幸福总值日渐提高,据统计,官城已长达二十年没有人流过一滴泪,就连出生的婴儿,也是微笑的。
江沐用双手撑着桌沿,两道肉痕刻在眉头中间,“我们真的没有眼泪了吗?”
我想说,有些眼泪是流在心里的,可出口的却是“也许吧。”
“我们来做个游戏。”
“游戏?”
“听说相爱的人对视,会流眼泪。”
我推回报纸,我不喜欢游戏,那显得不够严谨,过于随意,可我还是说:“好吧!”
相恋半年,我们从未彼此对视过。将自己完整而脆弱地暴露在另一个人的目光下,需要勇气和信任,而两者,我们都缺乏。我们各自蜷缩在自己的阴影里,像两只蜗牛,不愿从硬壳里伸出来。
我迎上他的双眼,他瘦削的额头,皮肤开始松弛,眉毛淡得几乎看不见,被地心引力往下拉的,深深的双眼皮褶子,睫毛已所剩无几,眼角旁的皱纹,细密如网。他满脸苍凉,可是眼睛异常清亮无辜,像一口散落在荒野里的井。这一双眼睛,见证过多少光辉岁月,有过多少似水年华,在深夜里对着某个虚无的点发过多少次呆。我都不得而知。
我想起数月前的一个雨天,父亲在给我送伞的路上,滑进河里,再没有回来。
我曾一度怀疑自己对父亲的爱,在梦里,我逃离他归来的灵魂,这让我难以接受自己。我的梦,似乎蕴含着某种预知力量,如果我把梦境告诉父母,父亲是否会免于一难?
父亲下葬后的很多天,我把梦境告诉母亲,母亲疯一般摇晃我,“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一直刻在我的梦里,每次它都能把我惊醒,在无边的黑夜。
“你流泪了!”他说。
“你的眼睛,让我感到难过!”
“二十年来,你是第一个流泪的人!”他兴奋地一跃而起, “不,你是全城最后一个流泪的人!”他的双眼眯成一条缝,嘴角咧开,一连串的笑声,像决堤的洪水从嘴里涌出来。
我把脸转向流水玻璃,用手背擦拭泪痕,凉。外面来来往往的人,一个个像贴在幕布上的有色皮影,来来回回,各走各路。
翌日清晨,江沐拿着连夜写的稿子,双眼通红地到来。稿子上有专家对此事的见解、对眼泪的意义分析、对整个城市的价值所在。人们没有眼泪,不仅仅是因为幸福,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泪腺已经退化,再也没有能力悲伤了。
“你将会唤醒人们的泪水,让人们还记得有‘哭’这种表情。不然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历史书上或博物馆里了解泪水的历史,我来,只想补几张你流泪的照片,你能再哭一次吗?”
十一点,太阳大起来,江沐的声音像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吹在我的脸上,我把稿子放在桌上。
我说:“眼泪不是笑容,说来就来。”
“你试着想一些伤心的事。”江沐像引导学生一样。
我抬头,看到江沐的眼睛。他的眼睛,总有一股忧郁,似乎所有悲伤的形容词融在一起,也无法形容这股气息。不管高兴还是难过,这股气息,都会存在。我想到他也会像父亲一样,将不久于人世,就感到无边的痛苦。
江沐狂喜,拿出相机,在我的正面拍了一张特写。
“继续,让我多拍一点儿!”江沐抓住机会,正面、侧面,在不同的角度拍着。相机的光亮照在我的脸上,咔嚓,咔嚓,一闪一闪的光亮,渐渐地变成了清晨的阳光,在我的脸上、发梢上雀跃,我捧书绕过假山,穿过树荫,和学生们点头微笑。走进办公室,一位女老师把我拉到桌边,上面有一张报纸,我看到报纸上的自己,两滴泪珠挂在脸上。我觉得报纸上的自己,如此陌生。
“我们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哭泣的表情了!”女老师说。
“想不到,现在还有人有眼泪。”另一位老师说道。
他们开始回忆,追溯小时候,那时候一穷二白,可是那时有眼泪,知道它滑下来时的温度和渗进嘴角的咸味。
中午十二点,钟声响起,孩子们你推我搡地涌向大门,却被保安拦住了。校门外聚集了一群人,校长骂骂咧咧地来到办公室:“白静你没事找事,外面一群人堵在门口要见你,学生们出不去,这可是教学事故,要受处分的……”
没等校长说完,我就起身向校门走去,向那群张牙舞爪的人走去,他们像一群蚂蚁等到期待已久的甜食,里三层外三层地簇拥过来,把我搬到校门外旁边的空地上,学生们才得以顺利放学。不一会儿,警车来了,警察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把我带上车。
我在庄严而冰冷的警局里一直待到晚上,江沐来接我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一路上,他都抑制不住兴奋。“太好了,你今天一个字都没说,这样就更吊读者的胃口了,现在,我们报纸的销售量是以往的三倍,主编终于对我刮目相看了。”江沐把我送到家后就回报社了,他说要加班撰写关于眼泪的新闻。他兴奋的样子,似乎明天就能拯救官城,就能飞黄腾达名闻天下。
我环视客厅,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可仍然感到陌生。厨房和卫生间用两道墙挤在一角,房间里,一个高大的书柜占了半面墙壁,书柜旁是书桌兼餐桌,前面是一张棕色的布艺沙发,上面凌乱丢着几个抱枕和书,一张床单皱成一团。江沐离过婚,前妻受不了他的默默无闻和一无所有。江沐净身出户,把房子留给妻子和儿子,妻子转身就把房子卖了,带着儿子远渡重洋,嫁给了一位美籍华人。江沐苦苦相求,想让妻子给他机会,让他证明自己有朝一日会辉煌。他的妻子说:“我已经给你十年了。”
我没有任何食欲,和衣躺上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醒来,看手机不过才五点半,睡意早已弃我而去。
一次讲座上,我感觉到一束目光,在我的背部游离,看我签名、入座、沉默寡言。可当我寻找这束目光时,它又躲闪不见了。讲座结束后,一名瘦削的扛着相机的中年男人追上来,说,白静,我叫江沐。他的笑容很浅,像一层淡淡的光。我才知道,那束目光,来自这里。我们一起走进电梯,从十八楼到一楼,在这狭小的空间,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他们。电梯门敞开的一刹那,彼此的重要性突然就在各自的体内,像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植物,蓬勃生长。
窗外的灯光渐渐被白日覆盖,几声鸟鸣传来,隔壁开着水龙头,水流冲击铁桶的声音响得刺耳,铁桶旁,漱口、打哈欠、咳嗽吐痰,各种声音开始瓦解清晨的安宁。
“疯了,疯了!”江沐带着一股喧嚣进门,“现在外面的人都要一睹你的泪光,我们报社已经和博物馆策划好了,让你到博物馆里展览,通过对你的观看,肯定能够唤醒人们沉睡的泪腺。早上消息一发布出去,马上就有观众来抢票。白静,你将进入人们最柔软的内心部分,你将闪闪发光,你将名留史册!”
没等我回过神,就被拉出门,坐上等在楼下的车子,径直来到博物馆的侧门。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正门处人山人海。售票员是个年过五旬的老头,皱着一张脸,忙得晕头转向、大汗淋漓,他感叹道:“天呐,这是博物馆有史以来客人最多的一次。”
我们走进一间暗沉的房间,一股古老、陈旧、腐烂的气息扑面而来,橱窗里挂着一件件诡异的清朝服饰,房子中间有一座玻璃棺木,一具羊皮纸般蜡黄的干尸,脑袋歪向一边,双眼干枯,嘴巴大张,某个时代最后的呐喊。我的胃一阵翻涌,继而被莫名其妙地推到另一间房,推上舞台。“好好哭一下!”江沐把我按着肩膀坐下,就走下舞台。幕布被拉开,舞台下一双双眼睛像灯泡一样,盯得我如坐针毡,哪怕穿着貂皮大衣,我觉得也如同是赤身裸体。我的胃一阵痉挛,一堆秽物涌上喉咙,从嘴里吐出。我狼狈地低着头,嘴角挂着黏涎。
观众先是小声议论,接着挥舞手中的票:“我们看的是泪水,是泪水!”他们把票扔到舞台上,落在我的脚边,又把用过的餐纸、皱巴巴的塑料袋、果皮统统扔到舞台上,满屋子的愤怒。
幕布被拉起,主持人冲上台前安抚观众。江沐在我旁边蹲下,“你想一些伤心的事,一些伤心的事!”我缓缓抬头,看到江沐蠕动的喉结,布满青色胡茬的下巴,干燥开裂的嘴唇,略向内弯的鼻子,整个脸庞像一片荒芜的山野。可是,他只需要眼泪。
我闭上眼,泪珠终于滑落,再睁开眼,幕布已被拉开,江沐不知去向。观众先是发出惊讶的感叹声,继而安静下来了,细细欣赏。
人们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眼泪了,如果不是这次展览,或许他们永远都不会再想起,人类还有这种表情。许多几岁十几岁的孩子第一次见到哭泣的人,目瞪口呆,想不到人可以这样悲伤,哭起来这么动情。
一夜之间,人们奔走相告,观众与日俱增,很多人连续买了几场的票,一场接一场饶有兴趣地看。好像谁没看到哭泣表演,就会变成另类,低人一等,被人带着鄙夷的口气问:“什么?你没看过哭泣表演?”礼堂的座位不够,人们就站着,摩肩接踵,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生怕错过一滴眼泪。
可是我知道,人们仅仅把这当成消遣、娱乐、赶潮流,我就像一件稀有物品,和博物馆的其他东西一样,供人们欣赏。
博物馆深知人们喜欢新鲜的脾性,第十天就调整了展览方案,除了让观众一睹泪水,还向观众普及哭泣的知识,比如,哭泣产生的原因、哭泣的种类、好处,等等。
“哭泣原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绪,像叹息、打喷嚏一样与生俱来,有声则叫哭,无声则叫泣。哭泣可以排除体内的有害物质,可以缓解情绪,对眼睛还有着保健的作用。但是近二十年来,人们正逐渐失去产生这种情绪的能力,许多孩子甚至不知道哭泣为何物。为此,我们将通过现场展览以及解释说明,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哭泣知识。”主持人激情洋溢的开场白,让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哭泣有很多种,比如啜泣:又叫抽泣、饮泣、呜咽,是指小声地哭,抽抽搭搭地哭。大家请看白静女士的展示。”
我开始抽泣,不停地吸鼻子、抽动肩膀。
“号哭:指放声痛哭,哭得彻底、无所顾忌!大家请看白静女士的展示。”
听到指示后,我立刻号啕大哭。
我像一台机器,随时听取主持人的发号施令。
就这样,展览,展览,一天又一天。我不再受噩梦的困扰了,因为我已经没有能力做梦了。
一次我在洗手间里和自己对视,发现镜子充满了敌意,里面一张陌生的脸,苍白无血、枯瘦嶙峋,红肿的眼睛凸出来,像两个即将被撑破的血泡。
我尖叫起来,江沐冲进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指着镜子,仿佛里面有魔鬼。江沐似乎明白了,拿起一瓶沐浴露砸过去,玻璃破碎的声音,清脆又刺耳,仿佛玻璃划过耳际。从此以后,江沐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撤掉了,我再也见不到自己。
“你们拿我的泪水和痛苦去展览,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仿佛不是来自身体里,而是来自一个地窖,沙哑,带着阴冷的气息。
“把你个人的感受和整个城市的感受、整个民族的感受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个人感受是多么微不足道了。”江沐说。
“总有一天,我也会没有眼泪的。”
“我会用我的一切去换你的眼泪。”
我知道,他要在我身上,证明他在前妻身上证明不了的证明。我越是知道,就越替他难过。他比我孤独,而且时日不多。
江沐大量关于眼泪的文章,一时间洛阳纸贵。为了整座城市的眼泪,他竭尽全力地工作。人们为他的执着感动,称他为 “英雄”“战士”。
可是,人们终于还是审美疲劳了,舞台下看表演的人越来越少。为了扭转局面,博物馆想出了一个招揽观众的新办法,就是通过物理方法来刺激人们的泪腺。观众看完展览后,可依次进入一个小房间,不停地切洋葱刺激泪腺,让观众“体验流泪”。
消息一出,舞台下又重新座无虚席。观众对“体验流泪”充满了期待,排着长队等待进入屋内。毕竟这是送的,不去白不去。可是一天下来,没有一个人流眼泪,人们只感到辣眼睛,辣到无法忍受,待不了几分钟就跑出来。
我被隔离了,这事惊动了医学界。他们要看看我的泪腺到底发达到什么程度。我像一只猴子,在手术台上被研究来研究去,毫无尊严。而且,我的眼泪已经干涸了,或许,多年以后,我也会被制造成干尸,放在博物馆里供人们观看,讲解员在我的面前,讲关于眼泪的历史。
我有多久没见过江沐了?一个月,还是一年?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越来越虚弱,头发掉落、身体残破,连行走也需要人搀扶。
一天,我被安排在一个空房里,房间周围都是白色,中间一张桌子,两张椅子,我坐在一边,不断有人进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和我对视。我知道,这又是他们的新方案。每天,对面的椅子上,变换着不同的人,有的静静地对视,有的则忍不住大笑。一天,一位中年男人坐在我对面与我对视,他眼神涣散,满脸愁容,看我的眼神,饱含祈求,接着他张大嘴巴,捂着脸干号。几个月前,我也许会为之动容,可现在,与我无关。
一天,江沐突然出现在我的对面,凝视我的双眼。他更苍老了,额头的皱纹更深了,依然皱着眉头,眼里的抑郁像一团化不开的云,我似乎看到了他眼角的光亮,一闪而过。他突然跑出房间,冲到走廊,像一只逃离危险的燕子,快速地扑向楼下。
几分钟后,楼下一阵尖叫声、疑惑声、求救声,所有声音混合在一起就分不清声音本身的意义了。
在江沐的葬礼上,各界人士不经邀约、不凭通知,纷纷跑来吊唁,有些人还撑起标语或横幅。在墓地里,大家都争着动手铲土,把江沐的棺木埋成一个大土堆。
我被搀扶着,来到江沐的坟墓前。喧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他们好奇、期待、戏谑地睁大眼睛,暗自庆幸或许能看一场免费的哭泣表演,或许比博物馆的还要精彩。
我在江沐的坟前,跪下,张开双臂,身子慢慢往前倾,整个身体矮下去,闭上眼,拥抱坟墓,苍白的嘴唇,触碰到粗糙冰冷的泥土,柔软和坚硬的碰撞,生命和死亡的亲吻。刹那间,阳光变得强烈而刺眼,光亮而恢宏,从天空垂直而下,像鞭子打在人们的脸上。
人群中开始响起吸鼻子的声音,人们用手摸摸自己的脸,不知何时,上面已是湿濡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