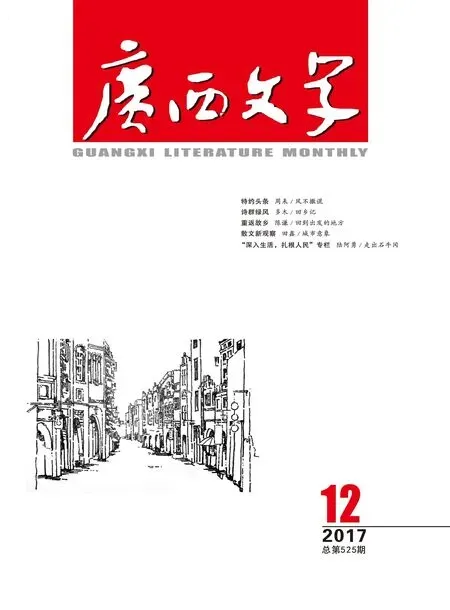一九九八年走失的野蔷薇(组诗)
安乔子/著
深夜,一只蜘蛛在窗口结网
被病痛缠身时
一只蜘蛛在我眼底小心翼翼地织网
看见我起身,又偷偷躲起来
我躺下,它又继续扯丝,编织,布局
时而就地转圈,时而往回跑
有时,它看看我,生怕打扰我
哎,它多像我隔壁房的母亲
在这个房子,只有它陪着我,为我起舞
病痛发作时,它让我感到被缠绕时
沉重肉身的另一种轻盈
让我翩然入梦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痛醒,隔壁有光照过来
它还在继续,一张网就要完成
但窗口有风吹进来
它一边结网,一边又被风撕破
它却不肯停下
一九九八年走失的野蔷薇
她叫罗蔷薇
出生时墙角的野蔷薇正开花
一九九八年六岁的她在文子勒走失
走失时身穿粉红印花布裙子
扎着两根小辫子,刘海齐眉
大眼睛,下巴偏左有一颗黑痣
她走失时下的那场雨
至今还落在她父母头上
这朵野蔷薇如今寄居在哪里
长什么样,是否结婚或者生娃了
她父母朝朝暮暮,日思夜想
他们想着想着就抱头痛哭
想着想着额头就铺满雪花
这二十年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
他们暗地里讨论过:
被割了一只肾,生命垂危
被打断了两条腿,在街上乞讨
拐卖给一个老头做小老婆
最好的情况是被一户好人家收养
大学毕业,有一份好工作
拜神祭祖他们都叫出罗蔷薇这个名字
请神保佑她,赐福予她
请神速速把她叫回来
蔷薇回来啰,蔷薇回来啰……
一声声虔诚的叫唤
像要把一个死的人叫回人间
蚯 蚓
他们躲在大地潮湿、低矮之处
常年不见天日
终日拖着危险的尾巴
掘土,用没有骨头的身体
也没有手和脚
一寸寸,吃力地躬耕
曾被多少人暗算过,多少犁和铲
插入身体
一不小心,一分为二
每次都是一边流血,一边愈合
劈木头
他是一个农民之子,小名叫木头
在八十多岁的分水岭
他的头顶,野草丛生,白雪茫茫
他的体内病魔出没,无力回天
剩下的光阴,他如数家珍
他和木头的命运是一样的
无非是枯老、死去
无非是葬身火海
他开始劈木头
劈开体内的肿瘤
劈开被隐藏的煤矿
把剩下的荒凉劈得七零八落
只是它再没有血肉渗出之痛
这个过程,他付出巨大的耐心
仿佛劈开自己
把自己一片片劈开
又一片片垒起来
等待那一天
一片片把自己送去火葬场
晒谷场的女人
女人呵了一声,顶着一袋谷
走向晒谷场
第一次她接过男人身上的重活
把自己活成一个男人
她咬紧牙,眉眼间露出一截截的皱痕
用力勒紧生活
就怕生活从她身上滑下去
在阳光下她弯曲的身影像一道阴影
阴影里有一道裂开的缝
那是男人离开后留下的豁口
她把左手伸进那道缝隙里,支着腰部
右手小心翼翼地把谷子摊开、推平
翻晒稻谷
如同翻晒自己内心的黑
她五岁的儿子在旁边堆谷子
在她推平的地方
垒起一堆堆谷子,他很认真地堆
他觉得这些谷堆像刚死去的父亲的坟
他嘴里喃喃地叫着爸爸
可是谷堆里没有父亲
也许谷堆不够大,不够父亲容身
女人摁住疼痛
把谷堆又重新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