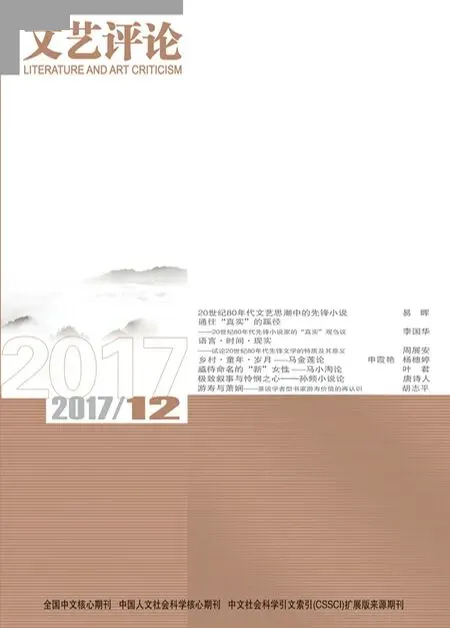少数者之歌
——以《“自省”:反思齐奥兰》为例试论苏珊·桑塔格的激进美学观
○石 佳
少数者之歌
——以《“自省”:反思齐奥兰》为例试论苏珊·桑塔格的激进美学观
○石 佳
苏珊·桑塔格作为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从不满足于“批评家”的身份,而是积极从事着各个领域的探索和思考。从批评到创作,从文学、美学、电影、摄影到政治、社会文化,无一不留下了苏珊·桑塔格激进热情而富有生命力的探索足迹。这也决定了苏珊·桑塔格在写作中拒绝了系统性与理论性,选择使用札记的形式,以便于记录下她丰富而独特的灵感和智慧。在《“自省”:反思齐奥兰》一文中,苏珊·桑塔格提到齐奥兰“显然选择了随笔的形式”①和“支离破碎的论述方法”②,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传统形式的哲学话语业已破碎”,“思考的心灵陷入僵局的见证”③。而显而易见的是,苏珊·桑塔格也同样沿袭了类似的写作和表达方式,除了上述的《“自省”:反思齐奥兰》,记述了其激进美学观的经典著作《静默之美学》《色情之想象》等文章,也均采用了自由漫谈式的个人化写作风格。苏珊·桑塔格用这种反体系化的形式传达了其对于思维复杂性、思想延展性,以及语言与阐释肤浅性的立场,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论述风格和艺术理论。
鉴于苏珊·桑塔格的艺术理论不以系统性见长,本文以《“自省”:反思齐奥兰》为例,联系苏珊·桑塔格的其他美学论述文章,试图寻找到苏珊·桑塔格各个艺术观念的逻辑关联,梳理出其对于艺术与人类思想的思路和脉络,并就其激进美学观念提出一定的反思与探索。
一、激进文学艺术遭受的压抑:语言污染与历史化意识
苏珊·桑塔格对于艺术的激进意识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上述的几篇文章中,她以前卫先锋的姿态站立在艺术与思想的前沿,从各个角度努力尝试破除文学与艺术所遭受的束缚。苏珊·桑塔格在《“自省”:反思齐奥兰》一文中,以一种历史化的眼光,从思想——语言,历史——真理两个对立平衡角度,集中展现了传统艺术话语的过时和落后性,以及给先锋艺术带来的压抑与统治。
(一)思想——行动:语言的含混与内容的枯竭
《“自省”:反思齐奥兰》一文在一开始便以一种历史化的审视眼光,讲述了传统哲学陈述体系的幼稚、世俗及其价值崩溃,以一种新时代的姿态宣告了传统语言系统的破败和失效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反响,引发了两种新形式的语言系统开始占领历史舞台,一种是反哲学话语体系——即各种实证的、描述的科学形式,具体表现是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等开拓者直接干涉进入思想领域;而另一种则是新的哲学化,也是苏珊·桑塔格本人认同、一直在实践的形式——“个人化(甚至是自传性的)的、警句格言式的、抒情性的、反体系化的”④话语形式。这两种形式在历史的语境中均呈现出了反传统的激进性质,但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却担负着不同阶段的任务。
在美国左翼文学和现代性相互纠葛的历史进程中,激进意志一直担当着引领思潮的先锋作用,同时也不断地被其自身局限性所捆绑。在苏珊·桑塔格看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第一种话语形式无疑起到了革新文学话语与实现独立性的重要作用,但究其本质仍然是反文学、反思想的,同时由于其局限性也渐渐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正如苏珊所言,“纽约文人集群”虽然一直试图摆脱马克思主义与苏俄政治形态的控制与主导,重归学术主体和知识自由,但事实上仍然没有能够彻底消除意识形态话语对其深刻的影响,纽约文人“把政治与社会的旨趣扩展到学术的方方面面”⑤,他们反对学术范畴化和专门化,仍坚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融入文学与社会批评当中。这种由“他者”笼罩与干涉下的思想话语体系,在苏珊看来,无疑是无法深刻切入文学本质的,不仅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与思想的纯净,甚至直接束缚了文学的真正自由与发展。
相应地,苏珊在《“自省”:反思齐奥兰》一文中,也给出了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并将这种过度的语言阐释所造成的混乱与浅薄,拓展到了思想与行动的矛盾冲突领域。苏珊·桑塔格引用了齐奥兰的说法说明了行动对于思想的侵袭,“意识的空间在行动中缩减了”,并认为从行动中解放出来是人类自由的唯一真实模式。而类似于思想对行动,内心对头脑、本能对理智等对立,任何一方的“过于简单明了”,都将导致“失去平衡”。对于美国左翼文学发展之过程而言,纽约文人引入了过多的“他者”进入文学思想领域,导致了过度阐释引发的思想扭曲与变形,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文学语言的肤浅幼稚。而这种语言的轻浮含混、内容的枯竭,在很大程度上又难以真正企及到文学与思想本质的深奥复杂,也就在某种意义上亵渎并束缚了真实思想的自由发展。因此,真实的情况是,语言与行动无法完全真实而完整地表达思想,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者的悲观论调,而是在一种人类未知的情况下,对于思想世界的保护、尊重与崇拜。不难看出,苏珊·桑塔格比纽约文人集群更清醒地认识到,思想是极其复杂而严肃的,与之相比,再尽力深奥的人类语言阐释与行动,如果不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展现,却依然作为思想统治的根本法则时,是极度危险的,并且必将成为激进意志与人类自由发展的桎梏。
(二)真理-历史:亦步亦趋的历史化意识
《“自省”:反思齐奥兰》一文,从传统哲学在历史意识与历史化的衰落出发,缓缓引出齐奥兰的哲学思考和存在状态,并以此为切入点,全面展现了苏珊·桑塔格对于历史化意识、对于语言阐释的态度与担忧。而无论是上述的语言阐释,还是历史意识与历史化,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人类思想的本质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语言阐释倾向于回答人类思想能否被阐释、是否该被阐释的问题;而历史化意识则更经验性地回答,在被历史团团包围与重压下的人类,思想究竟该如何存在?
历史意识不同于历史化的存在,在于它仍仅仅作为一种传统意志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历史存在,其权威性或许还没有那么强,但已足以使历史中的人类思想亦步亦趋。苏珊·桑塔格在《“自省”:反思齐奥兰》开头便犀利指出,“我们将事物置于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时间连续体中来理解……意义淹没在生成的潮流中:即毫无目的、连篇累牍的出现和废弃的循环运动”⑥。而这种亦步亦趋和毫无目的的“循环运动”给人类思想带来的最大束缚便是耗尽其可能性。我们不难理解,在历史意识存在的时空中,惰性与奴役性会使人类不自觉地选择传统的、经验的历史意识,在此情形下,新的思想空间与可能性极难被开发与接纳,停滞与愚昧便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历史不断前进发展,而思想却被庇护在历史的黑洞中、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形态时,新思想没有充足的土壤得以茁壮生长,矛盾与危害显露无疑。
历史的野心却从不止步于此,当这种落后于前进步伐的历史意识作为传统正确经验,逐渐被历史化成为正统与权威意志时,其“普遍性”与“永恒性”便开始叫嚣着取代“自然”作为人类经验的决定架构。而更怕的是,当人类思想已经完全被历史化所奴役、新的可能性逐渐被历史意识所耗尽,人类甚至开始自觉地运用传统而单一的意志“控制、操纵和改变‘自然’”,压抑与奴役自我。这样的潮流令哲学迷惑、令人类沉沦,具体的伦理与政治事务占据了哲学主流,并妄图以真理的形式解释一切,令所有的复杂与美妙均被严格控制在这个巨大的武断中。人类逐渐背弃了自我,放弃了本属于自然的多样性和激进性,虚妄的“普遍”与“永恒”抑制住了人类寻找真正自由的步伐,历史成为了人对自己的侵略。
这样的论调看起来未免有些乌托邦式的理想化,众所周知,当我们回望现实,人类作为历史与自然中的渺小一物,因其自身客观存在的局限性、与生俱来的惰性与奴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的控制和束缚,我们总要在历史所划定的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生存,很难真正意义上做到庄子所想象出来的“无所待”。而事实上,苏珊·桑塔格所反对的也并不是人类在历史中这样的一个事实,她所抗拒的是历史中的人类,以历史为保障、以单一为安全的愚昧信仰,并因此为激进文学艺术带来的巨大压抑。在她生活的年代,美国左翼文学也同样经历了历史化与反历史、压抑与反压抑的几个阶段。以知识分子与精英阶层自居的纽约文人,在祛除了政治作为历史化的权威统治后,自身也陷入了新的统治局限中。这种局限体现在其表面宣扬资产阶级文化的自由精神,实质上却只允许一种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虚伪面孔。诚然,纽约文人作为反对政治控制文学的中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学的自由价值。但是,当其以片面的、精英的自由作为新的统治力量控制社会,并作为文学与思想的根本法则重新占领了历史与权威时,则无可否认地成为了抑制美国社会实现真正自由与解放的统治根源。苏珊·桑塔格在齐奥兰的格言式风格中总结出结论,也从某个角度一针见血地点醒美国的权威统治,“每个深刻的观念都注定会被另一观念所击溃,而这个观念正是在原来的观念中默默产生的”。
二、反对阐释及其权威性:新感觉的深度与广度
纵观美国左翼文学激进发展历史,也正如上述苏珊·桑塔格所言:每一个新的阶段和成果,无一不是站在上一个阶段的肩膀上,同时将这个肩膀狠狠击碎。在美国经济与社会危机下产生的、以政治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为纽约文人提供了社会文化批评视野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方法论,却在之后因理论中缺乏自由与艺术性被新时代的纽约文人们驱逐出历史舞台,为倡导知识与学术为主体的学院派腾出了话语空间。而身处第三阶段的新左翼文人虽承袭了学院派追求知识自由的意志,却对纽约文人自身具有的精英意识所导致的片面自由极为不满,也因此将全面的个体自由作为他们所追求的激进理想。因此不难看出,每一个阶段的理论成果所无法逃避的桎梏,必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基础;而这样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自身无法意识的桎梏。
面临着纽约文人的精英话语为美国当代社会与思想界的真正自由所造成的桎梏,苏珊·桑塔格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大声疾呼“反对阐释”,不仅反对愚昧阐释所造成的混乱,更反对阐释、以及背后所支撑着的精英意识作为社会思想的根本统一法则,并以此表达苏珊·桑塔格对思想与社会文化的终极思考——反对一切形式的、对全面自由的束缚与羁绊。
相应地,资产阶级精英文化所积极进行的对社会与思想领域进行多阐释地文化批评,并将其自身锻造成主流与权威的意识,一一成为了苏珊·桑塔格的攻击对象,也就此提出了她在美学领域的全新的激进思考——新感觉及其实现范围的深度与广度。
(一)反对阐释与新感觉:生命的瞬时体验
现实情况中,精英文化过度阐释所造成的断章取义、词不达意,难以企及思想的真正高度与深度,甚至暴力挖掘、拆解、摧残艺术的解释。具体说来,批评中庸俗化、简单化的东西充斥着艺术与思想领域,已经俨然将严肃艺术阐释成为了非艺术的东西,甚至成为了一种应用、一种现实的工具,极度破坏了艺术本该具有的美感与复杂性。
1.反对阐释与消散思想
毫无疑问,思想与艺术是严肃而复杂的,而在苏珊·桑塔格看来,语言又是浅薄无力的,因此,至少在现阶段看来,没有哪种权威思想足以能够完整甚至超越性地展示艺术、阐释思想。那么为了保持相对的平衡,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将语言发展推向极致,极致到足以与艺术的本质复杂性相对等。而这难度与可能性无需多言。另一种则是节制语言、反对阐释。既然无法达到,那么不如回归“纯真年代”,尊重与守护好思想的完整性与人类意识的尊严。
为此,苏珊·桑塔格在不同的文章札记中也提到了几种方式。
首先,从主体上要求消弭其意识。苏珊在《静默的美学》中很多次提到,艺术对于观众地位的消解和剔除,本质上宣告了艺术绝不存在于观众的体验中。艺术不需要观众的回应,观众的体验无法渗入、也无法影响艺术本身的存在状态。这让艺术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贵与独立姿态,也从艺术的外在性角度拒绝了阐释与语言所造成的强制破坏。
其次,从意义上剔除其形式。阐释的主体是观众与批评家,那么其旁体一定是艺术作品被强行挖掘出的所谓“意义”。而这种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大多与现实紧密相联。在《色情的想象》一文中,苏珊通过挖掘色情作品在结构与艺术特征方面的强烈的文学性与感染力,驳斥了文学作品必须紧随现实意义与目的的现实主义观点。当本身作品的艺术冲击力已足够切入人类意识的复杂性本身,那一点点肤浅的意义与表象的现实反作用力,又怎会重要到必不可少的程度呢?既然艺术的现实意义本身就是附加之物,那么怎样阐释、阐释的结果就显得更加无足轻重了。因此苏珊·桑塔格在《“自省”:反思齐奥兰》一文中引用凯奇的话否定了“正确”与“错误”的现实价值,“当人们已经接受‘别再提心理学了’,我们要怎么来谈错误呢?”这一举措无疑从艺术的内在性角度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将阐释的意义以及艺术的“对错”之分剔除在艺术必要性之外。
通过这些形式和手段,反对阐释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应该就是思考的纯粹性。当观众与意义都无法再干扰艺术的独立前行时,思想最终化简为对思考的思考,甚至自觉地自我吞噬与消散思想。至此,艺术家与艺术终于摆脱了限制,如同精神摆脱了物质一般,自由穿行于思想世界。
2.新感觉:创作与接受的生命体验
在驱逐了阐释干扰、把人们引出思想后的艺术,将会走向何方?又会有什么新的作为呢?在反对阐释之后,苏珊·桑塔格又提出当代艺术思想需要依赖“新感觉”(或新感受力),包括“感觉,情感,感受力的抽象形式与风格”,以及对其的分析和拓展。在《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中,苏珊对比了阐释与新感受力的差距,“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或甚至主要不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它首要地是一个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改变(不论这种改变如何轻微)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的构成的物品。”
我们可以发现,在英语叙述中,新感觉(The new sensibility)中的“sensibility”,倾向于指一种敏锐的灵感体验,并不仅仅指向浅层次的感受,更是能深入进灵魂与生命去交流和意会的能力。在笔者看来,与为现实服务的阐释意义相比,新感觉是一种集合了无数的生命瞬时体验的总称,它潜藏在人类的意识与无意识中,不一定能被讲述甚至分析,但一定是体验者最独特最真实的生命意识瞬间。苏珊·桑塔格将这种不太能够把握的、与人类意识相关的“新感觉”引入当代艺术核心领域,并在创作与接受领域不断坚守与推广着艺术与感觉之间的联系。
首先,在创作过程中,只要是能够充分展现人类意识中的独特体验的艺术作品,无论其形式有多么的少见甚至危险,均可被文学艺术所收纳,例如爱欲、色情的极致体验、瞬时的灵感。同时,在体裁上也突破了传统的说教的、系统化规范化的形式,提倡使用更易于接近人类生命意识中的瞬时体验的札记与随笔的形式。其次,生命与生命之间存在着瞬时体验的可沟通性,在接受他人所创造出的、带有自身鲜活生命体验的艺术作品时,如果能够深入到彼此的灵魂深处,感知到体验中的共鸣以及艺术作品所带来的冲击力和感染力,那么艺术作品的先天价值就已经实现了,这也是“新感觉”在创作与接受之间穿梭的核心力量。
“新感受力”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苏珊极具敏锐眼光地将艺术作品与人类关联中的生命瞬时体验,从大行其道的意义与现实作用中提炼出来,并将其构成了文学的复杂意识本身,这无疑在美国左翼文学机械化思潮中极具开拓性。在历史进程中,文学本身所遭受到了太多枷锁和扭曲,其最宝贵的、最本质的灵性与生命体验已经渐渐被世人所模糊和忘记。而“新感受力”将文学从现实的工具这一外在身份解放出来,还原了其本身特有的、独立的复杂意识。这无疑从文学的深度上更进一步地挖掘到了被掩埋已久的价值和内涵,也令今天的我们得以从更深层次的领域探索文学与思想的复杂本质。
(二)新感觉与“坎普”艺术:文学广度的拓展
苏珊自己对于新感受力的评价是:“新感受力(它抛弃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后果已经被人们所提及——那就是,‘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区分似乎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显然,苏珊自己本人也已经意识到新感受力除了对于文学的深度挖掘之外,还有一层对文学广度方面的拓展。而其途径正如苏珊所言,通过缩小“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的区分,达到文学包容领域的真正宽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苏珊在各种艺术形式领域鼓励那些大量存在着的、边缘化、不宜展露的东西,为他们跻身大众视野积极争取充足的话语空间,得以与所谓的“高级”文化、精英文化共享同一片艺术领域视野。包括带有畸形的、特殊艺术旨趣的“坎普”艺术、不入流的情色文学、无意义的艺术形式,在经历了意义障碍的铲平以及新感觉的宣扬后,这些所谓“低级”的文化已经与“高级”文化在本质上再无差距,也因此具有了平等诉说与彰显自我的话语能力。
在谈到这样做的好处时,苏珊·桑塔格在《“自省”:反思齐奥兰》一文中,引入凯奇的观点,解决了齐奥兰在精英主义文化中所面临的痛苦和困惑。如果仍然抱有精英主义,认为有所谓的好坏、低级高级之区分,那么那些所谓不符合精英标准的“疾病”、痛苦、异类才会依旧令人绝望。只有真正抛弃了错误和低级的存在,承认永远都有完美存在的可能性,才能真正地不再受高级与低级的束缚,自由而全面地重估价值观。
暂时抛开其现实性与可行性不谈,苏珊通过这一行为,所希望达成的目的是挤压权威(也即精英)话语的统治范围,并以此动摇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与稳定的内在结构。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苏珊·桑塔格的激进美学观念始终伴随着其热烈的政治思考和主张。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政治立场是反对资本主义而亲近共产主义的。事实上,苏珊始终保持着一颗公众的良心,她反对的永远是精英与权威给民众及其被承诺享有的自由所带来的压抑。精英与权威所使用的话语统治工具,是所谓“永恒”“真理”。而黑格尔哲学体系告诉我们,哲学一旦永恒,便实现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拒绝随历史发展的更多可能性。精英话语的真理并不是不正确,但正是因为其正确,我们才需要推翻它,才能让所谓的“真理”具备更大程度上的解放性、包容性。
三、非主流者的精英文化与苏珊·桑塔格激进美学观思考
苏珊·桑塔格激进文艺美学观中所展现的反对传统意义上的阐述,对于新感觉与坎普的追求,甚至要求推翻“好”与“坏”价值观的标准,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仍然是极具理想化的乌托邦情怀的。虽然当代社会中,非主流的文化相对于以前,已经获得了更大的话语空间和更多人的相对认同。但当我们将苏珊的激进美学观与如今对比观照,我们依然不能自信地宣告,我们已经真正实现了文化之间的平等。不可否认的是,少数者之歌,在当代已然没能嘹亮唱响。
当然,苏珊·桑塔格的激进美学观其实是一种当时的时代大反叛的产物,而对于某种事物的反叛,为了达成目的不可避免地会用力过猛。就比如,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将中国的传统精神驱逐得所剩无几。而面临着美国当代社会思想的片面自由,苏珊·桑塔格将后现代文化情绪宣泄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希图能够通过大火猛攻来撼动资本主义稳固的统治地位与话语方式。
而事实上,结果却并没有取得良好成效,不仅没有产生新的阶层和新的话语形式,相反使得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统治更为广泛,既帮助资本主义获取了充分的文化特征,也扩大了资本主义的消费范围。那么,努力站在资产阶级精英文化对立面、从各个角度去消解其存在基础的新左翼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第一,纵使其怎样反对资产阶级精英文化的存在与统治,苏珊·桑塔格所倡导的激进美学观从本质上来讲,仍然隶属于与真正的大众文化截然对立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只不过,它是精英文化中占据着少数且非主流的地位;但同时,它与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又有着相交融的部分,例如一些边缘的、不宜展露在体面社会中的艺术形式,在大众文化与少数精英文化中均大范围地存在。不过这并不能就此表明,苏珊·桑塔格所倡导的激进美学观就彻底代表着大众文化,有些学者认为苏珊的新感受力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沟壑,也并不准确。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所谓“新感受力”是一种能力,而这种对艺术作品的敏锐感受力、对生命瞬时体验的把握和表达能力,从事实角度讲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具备的,苏珊·桑塔格在《一种文化与新感觉》中将其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科学素养相类比,并认为二者各自代表了各自领域的专业性,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利用的工具。这本身就展现了苏珊·桑塔格心中的激进美学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大部分的、不具艺术感受力的底层大众,那又何以能真正代表大众之间的文化呢?另外,新感受力与“坎普”艺术常常涉及到很多危险的、畸形的艺术形式,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大众文化还是低俗而体面的。因此,非主流的“新感受力”并不能构成大众文化中与资产阶级精英文化的分水岭。
那么不属于大众文化的新感受力,何以仍然存在于资产阶级文化范围内,又正好促进和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统治呢?
第二,新感受力与“坎普”艺术,因其与大众文化的交融之处,为资本主义的消费范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统治空间。资本主义无论何时都在追求扩张的消费,其内在的扩张需求与其文化中宣扬的全面自由交相呼应,相互促进与实现。而如果社会文化与思想领域的全面自由被压抑,那么其对于广阔消费的需求也必然会受到限制。而苏珊·桑塔格所在的新左翼运动正好在文化领域打破了单一的“自由”,要求将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自由解放出来,最终实现每一个个体的全面自由。这无疑为资本主义的消费范围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极大地解放了资本主义的消费需求,同时,使资本主义获得了自身的全面的文化话语,无形中更加巩固了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
而成功为资本主义文化奠定基础的新左翼运动,在其希图实现的全面自由上似乎仍然受着羁绊,这无疑与历史时代的发展局限以及理论体系的自身局限性有关。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人类的天性与意识还不足以使每个人都能够实现完整的、同时不伤害他人的自由。这无需多言。而另一方面,苏珊·桑塔格的理论体系重形式轻内容,而类似这种自我封闭的形式结构,在遇到不可避免的内容、现实问题时,只能选择逃避。苏珊·桑塔格希望通过“坎普”艺术打压盛行的权威思想统治,而对于其涉及到的社会危害性巧妙回避开,甚至使用了“科学也有危害,为何不去节制”的托词,这无疑令其理论主张在实践阶段寸步难行。
其次,苏珊·桑塔格在不自觉中使用了简单的一分为二的分类意识,简单将主流文化与机械阐释的、毫无灵性的工具艺术联系在一起,将非主流文化与解放、快乐、灵感相联系。如果尊重文学艺术与思想的复杂性,那么还应该细细追究究竟是主流文化中的哪一部分元素,对非主流文化真正形成了压迫。非主流文化自身是否也客观存在着局限性,使得非主流之歌难以唱响。作为社会中的非主流群体,是否自身真的有需求被公开到与主流文化群体相同的曝光与探讨程度。这一系列问题,仍需要结合真正属于非主流文化阶层的主体,对其自身现状的清醒认识和未来愿景,再去回答。
①②③④⑥苏珊·桑塔格《激进意志的样式》[M],何宁、周丽华、王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第85页,第85页,第85页,第82页。
⑤王予霞《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