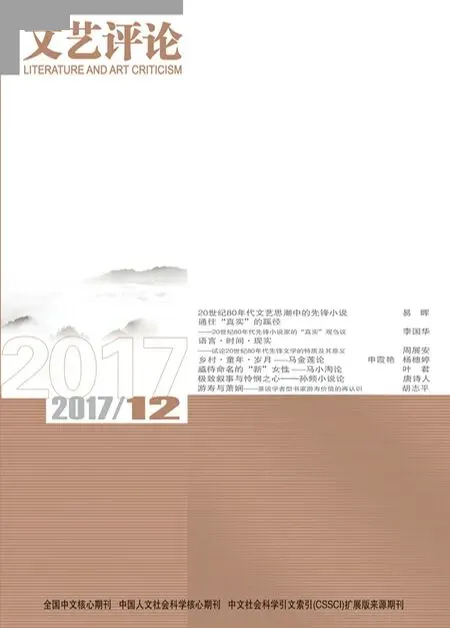仪式·参与·象征
——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
○黄勇军 柳 谦
仪式·参与·象征
——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
○黄勇军 柳 谦
由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本质上就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①《中国诗词大会》抓住受众对于诗词文化的认同,在制作实践中巧妙利用仪式化传播的特征和要素,对场景进行仪式构建,对内容进行参与性提升,对意境进行象征化表达,从而使受众在获得精神愉悦与满足感的同时成为仪式化传播下“观念世界”中的一员。这种传播“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他都把人们连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②。
一、场景仪式性
在仪式观的隐喻前提下,传播可视为“仪式化”的过程或是一种庆典的生成,其目的不是对不确定性信息的消释,而在于共享信仰,强调“场域”及其仪式感的营造。《中国诗词大会》在节目制作上具有象征性、表演性,而这两大特点也正是仪式经典定义中所具有的特征。马丁·埃斯林指出“戏剧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共同根源是宗教仪式”③。从这一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中国诗词大会》可看作是古希腊戏剧仪式的变异体,具有承载这套仪式的物理空间,即演播厅可视为戏剧表演中的戏剧场,而这个演播厅的场景仪式化的设定就是为文化消费个体提供一个特定的场所并且进行特定的情感宣泄。从演播厅的布景格局来看,区位设计注重继承类似于古希腊埃皮达鲁斯剧场结构,但同时又在继承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技术加以修改。埃皮达鲁斯剧场可划分为三大分区:乐池、景屋、观众席,而这三大分区与《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区位相对应的是:答题区、后台、百人团。乐池通常位于建筑中央的圆形区,是演员表演和歌队吟唱的地方,在圆形区的中央往往设有祭坛,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在“诗词大会”的演播厅中,答题区相当于乐池中央的祭坛,主要进行答题活动,即诗词仪式的狂欢;在乐池的后面是一个名为“景屋”的矩形建筑,是古希腊戏剧的后台。随着戏剧艺术的发展,人们有时候会在景屋外表绘制图案作为舞台背景,故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主舞台背景上的LED大屏与诗词主旨相呼应;百人团相当于戏剧场中的观众席,呈现形态为半圆形,次第升高,像一把巨大的展开的折扇,仿佛把演播厅变为4D电影的球幕放映室。而《中国诗词大会》布景格局中一系列道具和环境所营造出的仪式感“幻象”,使参与者进入一种具有暂时性、隔绝性以及超脱日常的净化空间,在达至人天同构、超凡入圣的同时,产生了宣泄情绪的仪式狂欢。
演播厅本质上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戏剧场”,而格塔式心理学派则将其引入人类知觉感知事物的过程,认为个体的意识经验也有着与物理“场”相同性质的结构,并且这两个“场”可以相互作用而产生向四周扩散的效应力。如果将效应力置于审美过程便是艺术表现力的产生,艺术审美就是通过“场”这个传播介质来达成艺术审美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将其置于美学理念中,就是源自无数审美体验过程的凝聚。这种审美过程的凝聚在外部形态来看是一种富有周期性、目的性、充满符号表达和隐喻性的过程,通过“具象的表达”而凝结成一种次序化、反复化的模式。“运用任一名词时,在潜意识里都会对这个词加以解释,且是因人而异的,而想要对这一名词形成固定的观念就需要培养固定的思维习惯。”④就此看来,《中国诗词大会》就是通过具象的“诗词竞赛”将其所要传达的精神宗旨在观众的意识层面进行不断地反复记忆,促使观众形成一致心理与行动模式,而节目传达出的特定价值观就得以再现和强化,选手对于答题的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回归诗词文化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一次强调。在内在体验上,这种周期性的重复以及目的性的诱导引发一种心理期望,对文化受众形成一种期待视野,并通过特定的播放使参与者的意志、情绪与节目的宗旨发生互渗而达到统一。
这种审美情感的凝聚过程是具有历史性的,属于一种感性的原始体验,即“原型”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感性的凝聚过程也具有了新的形式。王一川曾言,原型问题“是感性自然如何凝聚为理性模式的问题”⑤。诗词是古代文人骚客对于自然感性集中反映并且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高度凝练语言,通过历史的沉聚,当下社会将其转变为“朗读、吟诵、竞赛”的一种理性化的“原型”。同时,又会周而复始地重新演化为新的感性自然,亦即“审美体验”,这在节目中体现为“演播厅”场景仪式化的建构。正是在这样仪式化的场景中,文化个体的宣泄才得以进行,其所营造出的的仪式化氛围为诗词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有利条件。
二、内容参与性
文化学者瞿杉认为:“在传统的仪式观中,成员的亲身参与是必不可缺的要素,只有在仪式现场,个体才有可能体验到典礼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产生群体意识,从而融入社群之中。”⑥就此看来,文化个体想要获得仪式效力,就必须亲临仪式现场。相较于以往的文化竞赛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对于参与性的强调是建立于传播者与受众的平等基础上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电视媒体作为意识表达的传播载体承担着某种特定的政治使命,其所拥有的权威性必须由赋予其仪式性来体现,此时节目的受众群体与主角是一种仰视与俯视的视角关系。《中国诗词大会》则通过对主持人权威性的分割与削弱来打破这种不平等性,从而建立起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平等关系。在该档节目中,主持人不再是单一的“主导者”而是有着双重身份的“调动者”和“参与者”,其权威性的弱化随之带来参与性的强化,这主要体现于两大群体——“专家团”与“选手团”。
“专家团”在节目中类似于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从新的时空维度中去审视和思索其职责,不难发现,“专家团”作为当代“歌队”,对以往既有继承,也有超越与发展。黑格尔认为:“凡是有歌队的戏剧,无论剧本和演出都是一种‘双元结构’——歌队承载着超个体、超个性,形而上的‘神性’;歌队之外的具体任务则担负着现实层面的意义。”⑦“专家团”继承了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神性”职责,在节目中代表着对诗词权威性的阐发以及引导着观众进行历史、伦理、善恶的见证与评介。在席勒看来:“通常对歌队的评价都习惯于谴责它抵消了幻觉,破坏了情感冲动,这种谴责是对歌队最高褒奖……歌队把全剧分割为几个部分,并以它的冷静观察插入痛苦中间。通过这种方式,歌队把我们在情感狂澜中失去的自由又还给了我们。”⑧从这个意义上说,“神性”的职责又掺杂着理性元素。当竞赛的氛围达至一种“迷狂”或者“狂欢”状态,此时“专家团”的点评得以使我们在诗词狂欢后的情感逐渐诉诸理智。相较于以往的歌队,其超越体现于不再是戏剧中固定的站立或者演出中以一种圆形或者半圆形的队列调度,而是有着多重的自由组合形式,在仪式化传播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负载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中国诗词大会》中,“专家团”的作用可以归纳为:间隔时空、多重身份透视、代表诗人抒发感情、创造诗意与哲理的审美空间,融合升华情感体验等等。
在格洛托夫斯基看来,“‘质朴戏剧’就是在从根本上强调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关系,没有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感性的、直接的、‘活生生’的交流关系,戏剧是不能存在的”⑨。《中国诗词大会》将“选手团”分为“场外观众、百人团、竞赛者”三层,并对这三层进行了逐级选拔,由场外观众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晋升为百人团,而百人团作为场外观众的代表通过抢答的方式晋升为竞赛者。这种设计使得“演员”与“观众”发生了联系,加强了剧作者通过演员与观众的对话,而“场外观众”可以由此间接性介入“场”中,实现与“剧作者”(即“专家团”)的一种对话。“如果把审视的角度再拓宽,就自然地产生了对戏剧的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说法可以称之为‘三个圆圈说’。所谓‘三个圆圈’就是指构成戏剧艺术活动中的里、中、外三个领域。”⑩在《中国诗词大会》中可以指认为:答题区、演播厅、社会体系。这三个领域可以看作三个引力场,也就是说在进行仪式化狂欢中,演播厅是以答题区为引力场,而将其置于社会环境中,演播厅乃至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外围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场”,而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又成为这个更大范围的“场”的中心,它们三者的关联使得节目与所处的环境处于一种复杂的生态关系中。丹纳认为“每一种艺术品种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而艺术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满足社会环境的要求,否则就要被淘汰。”⑪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诗词大会》不仅对内联系着核心因素,对外也联系着整个社会。
《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强调受众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参与,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将电视观众与仪式现场的观众进行身份转换,满足文化个体参与,从而实现《中国诗词大会》的仪式传播。
三、意境象征性
《中国诗词大会》的意境象征性不仅体现于内容上对传统诗词的选择,还体现于仪式的符号表达。诗词文化为仪式提供了象征基础,仪式为诗词文化提供了符号表达。传统文化在农业时期曾被指认为主流文化,而如今工业生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挑战。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社会意义”被倾覆、解构,而后被重构为一种大众、商业、流行、网络文化的复调体例。其存在于当下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物理形态存在的文化实体形态,二是意识存在的内化精神。而诗词文化正是兼具两种存在方式而为仪式传播提供象征基础。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指明:“‘只要存在集体生活’,就必然存在着‘产生和复制社会关系的作用’的仪式。”⑫首先从本体层面来看,诗词的本体形态中就蕴涵着大量的仪式特性。例如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感和群体主义价值。这些价值在共同意义上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而优秀的诗词文化对民族的认同、维系有着重要作用。布罗凯特教授认为仪式属于知识的一种形态,可以起到说教作用,并且可以影响和控制事物,产生预期效果。社会主义学家德克利夫·布朗同样认为“仪式”极具功能性,它可强化集体情绪和整合社会。也正是因为诗词具有超脱于语言形式本身的仪式意义,在效用上具有象征的基础,即仪式所具有的合法性建构、弘扬文化、社会控制和经济功能,才能使其与仪式发生关系互动。符号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乃为一个‘符号的聚合体’,仪式行为是一个象征性的活动过程,人们可以透过仪式的符号表象去理解、领会那些‘隐藏’在仪式象征‘背后’的要义。”⑬从符号学来看意境所具有的象征性,符号是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这两部分在一级符号系统中都是最为直观的形式与内容,在《中国诗词大会》中体现为传播的画面、声音与节目内容,而三者传达的节目信息以及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即二级符号系统的所指。二级符号所指超越了本体的形象,即诗词竞赛形式,而产生对传统诗词文化的一种回归与反思,这种反思又对大众的认知态度隐秘地施加着影响。
当下新型媒体有着互动性较强的特征,这就导致受众在已呈现分众化、零散化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私人化、多元化。这种状态有利于人际圈内部的强化,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圈与圈之间独立性的扩大,产生一种归属需要与认同需要。《中国诗词大会》的出现正是央视认识到了社会个体之间的疏离感,并通过一种仪式传播的方式弥补了这种需要。涂尔干认为:“宗教仪式不管是从外部来看,还是表面来看都显得毫无理由的活动,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精神机制,这个机制不仅为这些活动赋予了意义,而且还为其提供了道德意涵。”⑭故此,社会的集体意识狂欢等一切就都发生着改变。主持人变为仪式传播活动的引领者,评论嘉宾变为仪式传播活动的承载者,百人团是仪式传播活动的现场参与者,场外观众是仪式传播活动的场外参与者,他们都同时认识到自身的存在及力量,从而激发起集体性亢奋,产生一种超越行为和元素本身的表现形式更为深刻的隐喻。
仪式化传播过程不仅仅凝结着共同的情感历程和审美体验,还作用于消费媒介下文化个体的现代性困境。植根于当下的仪式传播方式的创新使其在社会信息共享与维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并非巧合,它攫取“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中心要素,通过改进传统文化中娱乐仪式化的传播途径,在当下过度“娱乐至上”的喧嚣追求中形成了一股难能可贵的“清流”。
①②[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英]马丁·埃斯林《戏剧剖析》[M],罗婉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④[苏格兰]休谟《人性论》[M],张同铸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⑤王一川《意义的瞬间产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⑥瞿杉《仪式的传播力——电视媒介仪式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⑦[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4页。
⑧[德]席勒《论歌队在悲剧中的作用》[A],见[德]歌德,席勒《论戏剧》[M],第372页。
⑨[波兰]耶日·格洛托夫斯基《迈向质朴戏剧》[M],黄佐临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⑩⑪叶长海《戏剧:发生与生态》[M],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第54页。
⑫转引自范志忠《作为仪式的戏剧表演》[J],《艺术广角》,1999年第4期,第46页。
⑬[德]阿克瑟尔·米歇尔斯《仪式的无意义性及其意义》[A],见王宵冰《仪式与信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⑭[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重庆市“十二五”教育规划课题重点项目“电影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4-GX-024)阶段成果]
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