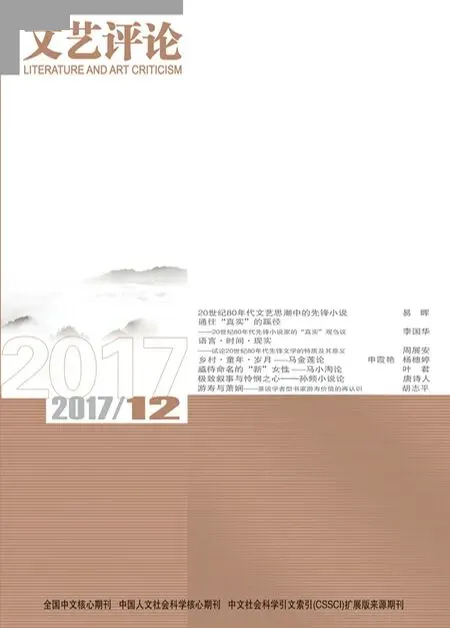民间述史维度及偏向
——兼评《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
○王海峰
民间述史维度及偏向
——兼评《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
○王海峰
《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任雅玲、张爱玲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最突出的贡献,便是将“民间述史”这一行为,纳入文学范畴。从文学视角,审视民间述史问题,会展现“民间述史”的某些属性,同时,也会赋予“民间述史”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关于这一主题下的概念性概括有很多。有人称之为“非虚构写作”“民间文学”“个人述史”,或者,干脆叫“民间史料”,不一而足。事实上,它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梳理其历史脉络,了解其本质属性,从而才能洞见其历史走向。
一、视角的回归与新生
我们知道,“民间”是相对政府和官方而言的概念。这就类似朝与野的区别。唐代以前,我们还能看到,民间有很多人著史、修史。拿晋史来说,其版本不下十数种。然而,魏征等人奉命修史之后,其余版本的《晋书》便逐渐泯灭了。后来,修史、述史便成为统治者独有的权力,在清代,这种思想达到极致。而在春秋时期,各国并没有指定的修史人员。修史的工作也并未独立出来。待到孔子著《春秋》之后,始有“乱臣贼子惧”。掌权的人才恍然大悟,史的作用原来如此大。当然,因为科学不很发达的关系,王莽掌权时,也还是要凭借很多臆造的坊间谶纬之书。总体而言,修史者的身份是由民间向政府集束的。当然,期间也有很多个例,比如南宋的郑樵,隐居浃漈山,著述《通志》。不过,他写完那书,也要不远千里多次呈请皇帝认可(那时政府禁止私人修史),以便流芳百世。这在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述史与接受的辩证关系问题。
《研究》一书,将研究范围锁定在中国当代,很是必要。中国当代的述史环境与中国古代有很大不同。出版成为一种相对自由的表达方式。《研究》一书中说:“民间述史大多以抗战、反右、‘文革’、知青上山下乡等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回忆个人或家族的小历史,使读者透过血肉丰满的小历史形象地感知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这个述史视角,显然与中国古代士子文人的述史初衷有很大不同。我们且不说司马迁,单说郑樵。他的述史,是一部意欲囊括古今天地的大书。而中国当代的述史者,则并非要成就“立言”之不朽,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亲身体验之后的“验伤”和纪念。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如梁鸿这类的述史者,其出于对社会或历史的某种责任感和研究意图,而进行了有意为之的更大主题层面上的立意与构思。然而,不论古代的宏观述史(我们且将其叙述心态称之为“不朽心态”)、当代学术研究者的中观述史(“研究心态”),还是当代百姓的微观述史(“纪念心态”),其叙述视角都始自民间。从述史的发展脉络上看,这是一种叙述立场的回归。只是,民间立场的各自叙述态度颇有不同而已。
这种不同,恰恰让人看到一种“新生”的力量。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叙述与表达迅速变成极为随意之事时,更激发了民间历史见证者的个体表达欲望。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将后两者(中观与微观)的叙述文本与心态混合而谈,有些笼统。不过,《研究》的切入点是“文学”,文学研究的起点是文学文本,所以,这便不再是个问题。《研究》中“民间述史的个案解读”部分,都是从述史的文本出发,从每个生活者的记忆与观察出发,进行述史方式、方法及意义解读的。事实上,叙述的个人化与个性化,就是民间化的具体表征。而“文学”,从古至今,从来都是一种亲民的表达形式。当人们将过去体验到和见闻到的故事与情节注入笔尖,汩汩流出,抒发所思所感之时,便已经开启了一段段文学表达的历程。
二、作为现象的文本阐释
历史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也不是仅有一面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由于见证者立场与视角的不同,历史便存在着不同侧面。当权者对历史“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时,民间个体对历史的所见所感却更加复杂多样,且体味精细。任何人和任何努力都无法还原历史本真。而在不断接近历史本真的过程中,记忆是尤为珍贵的。王学泰在其个人述史类作品《监狱琐记》(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的《后记》中说:“个人提供的史料中最不可靠的是回忆录,最可靠的是日记。这是一般规律……”但是,很多事实证明,日记也并非百分之百可靠。况且《研究》中所论及的民间述史者绝大多数都是凭借记忆(而非日记)来进行写作,所以,在这个视角之下,将“民间述史”与“文学创作”融合来研究,是一条十分必要且可以走得比较长远的路。而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恰如当年盛行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样,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与“还原历史”。
写《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的梁鸿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梁庄”并非真名,在中国河南穰县的地图上,我们也找不到“梁庄”。书中两个女人春梅和巧玉的名字也是虚拟的。书中也有太多内容和情节,都属虚构。同样的内容,在其他民间述史者的文本中,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这与其说是述史过程中文学的自觉参与,毋宁说是现实因素对述史过程与结果的干涉。这就像一个史学家无法书写和定义其现实所属时代的历史一样,仿佛所有民间述史者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恻隐之心”。《研究》的第二作者张爱玲,2016年7月出版的《咱们学生》(济南:山东画报社,2016年版)一书,属于纪实性质散文作品集,其中便有很多学生的名字用了别名。而近两年图书热销的姜淑梅老人,曾出版了多本民间述史作品,比如《乱时候,穷时候》(姜淑梅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的原稿中,就有很多篇目无法出版,至今无法与读者见面。
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可以多重多样。但是,作者(亲历者)对于历史的阐释,则只有一种,那就是呈现或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而对于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有两种呈现或还原方式,一种是形象上的真实,一种是本质上的真实(同步)。然而,述史者多数只能呈现形象上(即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历史,而少有表现本质者。丹尼尔·笛福说,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假的故事来陈述真实,两者都可取。他的意思就是要读者体会历史的本质真实,而不必在意历史的形象真实。而换个角度讲,他的这句话,也隐含了所有小说家的悲哀和无奈,希望和出路。
但是,当文本阐释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便出现了阐释学。阐释学的关键,往往不在于文本,而在于阐释者的素质或目的。这是一种阐释行为。“民间述史”行为,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叙述者对亲历历史现象的一种阐释。叙述者将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诉诸文本,形成第一个层面的阐释。读者阅读文本(被限定在“出版”范畴之内的文本),又对叙述者的“本文”进行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第三个层面)的阐释。然而,从出版学的角度看,到达读者层面的阐释,已经是第三个层面。因为,出版活动往往受到时代、政治、经济、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以致于叙述者的本文在出版层面经常发生很大的变化。
三、文献、史与史料价值
如果单从述史和史料的角度,理解如姜淑梅、饶平如、梁鸿等人的写作,而非从《研究》所言的“文学”的角度对这些述史者的文本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大众读者是很难接受的,史学专家也是无法接受的。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大众史观关注的并非是历史的宏大作用和意义,而是需要将历史放进个人的感受和经历中,需要有一种亲民性质的有血肉的现场感。然而,这些历史现象注定不能得到全然呈现。当很多人修国史、整理国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做地方史、民间志。章学诚曾经修过很多地方志,这是他在中国史学和文献学上的重要贡献。他在《文史通义》中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对社会发展而言,国家之史,是骨干,家人之史,是血肉。如张泽石的战俘记事之类自述历史,则是借个人之命运表达历史之变迁。与大国天朝历史记录不同之处,这些个体叙述更富血肉,更加生动,更有“感觉”,更显真实,而非如历史档案、会要之类冰冷、粗略、无趣。与此相似,一些小说家虽然没有亲历很多历史事件,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虚构故事、人物,完成由家人到家国的命运表现和传达,如巴金《家》《春》《秋》之类小说,便是借家庭之变迁表达家国之命运。
然而,我们无法将这些民间述史作品一概而论,笼统地列入文献或史料之列。这些述史作品必须得到一定意义上的历史“印证”,否则他们只能被单纯列入文学和叙事范畴。《研究》中谈及民间述史的史学价值与民俗学价值。《研究》认为,民间述史文本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述史方式(讲故事)和述史视角(平民视角)。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辩证地看。首先,这种述史方式在我国古代史书(如《史记》《三国志》)中便以纪传体(讲某个人从生到死的故事)的形式普遍存在;其次,述史视角的平民化在我国古代也有,如郑樵的《通志》(布衣分身记录历史人物和事件)等。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如此繁多的民间述史(亲历亲述)现象却委实发生于当代社会。在我国古代,接受教育者或能著书立说者,多为士子文人,又多朝廷臣子,无法以民间视角体察历史的另一面;而在中国现代,或者乱世时代,人们忙于奔命,疲于生计,更无从用笔墨书写亲历史实。故而,改革开放之后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和相对宽松的网络与社会表达环境,为民间述史提供了丰厚的生命给养。《研究》的这种判断便有了根基。
民间述史文本内容本来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单用文学、史学、民俗学的价值来估衡,显然不够。如果将民间述史文本作为活的文献来考量,那么,它的价值便丰富了。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于述史作品中。这是史料学上所言的“活史料”,也是文献学上所言的“活文献”。这些述史作品与崔永元所做的“口述历史”一事,价值等同。崔永元之所以要做“口述”,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很多亲历者无法自己完成笔端叙述。
四、传播与阅读的偏向
《研究》在谈及民间述史热因时说:“民间述史作品热与纯文学处境尴尬有直接关系,尴尬的纯文学处境为民间述史热提供了契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不论古今,都有所谓的“纯文学”与“俗文学”之分。《诗经》有“风”“雅”之分,歌诗有绝句律诗和词曲小道之别。在古代,虽然封建政府和当权者曾有意无意打压俗文学的发展,但是在民间,俗文学向来较纯文学受欢迎。民间百姓,自然是喜欢那些耳熟能详、通俗易懂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古今不同之处,在于文学作品出版与传播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阅读,因移动网络而变为随时随地随手可得。古代的阅读,从需要传抄(如传抄《红楼梦》),到大量雕印,都是极为缓慢且需要不少人力物力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出版和传播的环境相对宽松,民间的文学阅读范围也随之拓展。这个时候,一度出现纯文学热现象,相较而言,俗文学(如武侠、言情小说)也十分火热。因为,二者都在同样的平台出版。而网络出版兴起之后,二者因为受众不同,表达姿态不同,便在出版平台上迅速发生分化。加之纯文学出版平台故步自封,稿酬制度与纯文学作者收入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俗文学的刺激的原因,虽然二者的创作数量与阅读群体都在增长,但是,俗文学创作队伍与读者数量速度增长,而纯文学则增长缓慢。最终,很多纯文学出版平台在被迫中转型。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对民间普通读者而言,阅读的兴趣显然大于阅读的意义,而阅读的切身意义又明显大于阅读的社会意义。二者比较,也恰恰构成俗文学比纯文学更能招徕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民间读者而言,在内容表达与传播方式上,俗文学都优越于纯文学。此外,影视作品多脱胎于俗文学,如《甄嬛传》《盗墓笔记》等,都属网络小说改编而成。在这个大背景和原因下,民间述史作品也便自然热兴。其深层原因:一个是述史者表达的需要,这类似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伤痕文学”的出现,述史者也需要在和平年代“验伤”和纪念;第二个是读者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经历的兴趣使然;第三个是市场经济与新媒体环境下出版形态许可、社会文化需要及经济利益诉求的综合作用。换句话说,即便没有纯文学发展冷落的现象,民间述史作品在上述背景原因中也会繁荣。
事实上,在当今出版与阅读环境下,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线已经很模糊了。纯文学如现代文学中表现宏大主题的作品越来越少,而更多地转向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社会感受的表达。个人与群体、经历与历史、民族与世界正在融合到一个人或一家人的生命进程中。《研究》注意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包容和现代公民意识觉醒的问题。这个发展趋势与世界整体文明进程及民主发展趋势是同步的。
在世界范围内的民间述史写作有很多,历史也很久远。比如,二战之后,很多从集中营里走出来的人,写了回忆录。很多人写了自己在特定历史下的自传。海外华语文学创作者也撰写了很多家族变迁史。但因为文本传播受诸多因素限制的关系,时至今日,我们才能看到这些作品。这就像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后回意大利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而其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尤其是在文化和出版体制改革之后,出版才有了国际化视野。随着出版节奏和效益的加快和增加,这种镶嵌于普遍历史背景下的有血有肉的民间述史作品便得以快速发展。不过,在民间述史作品传播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切实的问题。即,虽然民间述史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当代文学史料、丰富了历史和史料的内容,给予了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新的研究视角,但是,无可否认,民间述史作品的视角是自在的,表达的也是自身经历,现实与历史的交会,记忆与感受的融合,以致它的本质属性仍然是文学的。民间述史作品其实就是扩大版的写实纪事散文。故而,《研究》将民间述史作品纳入文学视域,也正是抓住了现象与问题的关键和本质。
2017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2017绥化学院应用研究项目“黑龙江省数字出版IP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以纯文学在近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现身为例
——有流产史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女性健康行动
——有流产史女性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女性健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