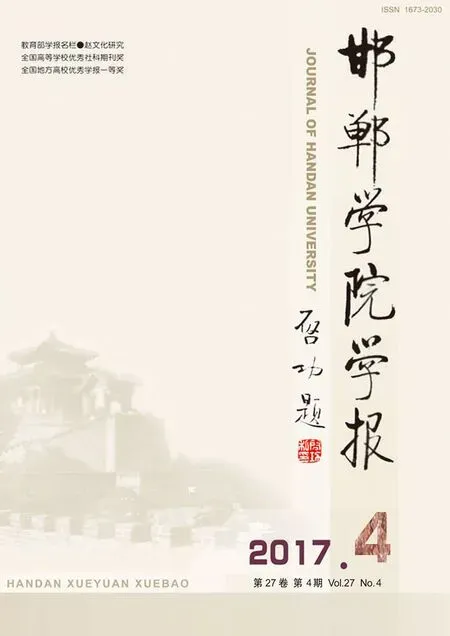荀子“道”论思想探析
——从礼乐法度到形而上之道
孙 伟
荀子“道”论思想探析——从礼乐法度到形而上之道
孙 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101)
对荀子哲学中的日常伦理政治生活与形而上学终极价值关联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荀子哲学中的形而上之道如何以日常伦理政治实践作为基础,而日常伦理政治实践又如何通过心性途径能够导向最终的形而上之道。
荀子;道;心性;虚壹而静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人类整体生活所设定的最高目的。对儒家哲学而言,一方面实现“道”的礼乐法度实践活动是人类自身德性伦理建设和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内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道”的形而上属性,也导致了礼乐法度实践活动和最终形而上目的之间的张力,即具体而现实的礼乐法度实践活动如何能够上升成为抽象超越性的形而上之道,也即“下学”如何“上达”的问题。本文旨在从荀子哲学的道论思想入手,深入分析荀子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探讨荀子的心性论思想怎样能为解决礼乐法度实践活动和形而上之道的张力问题寻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当前学界对荀子“道”论思想的研究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荀子哲学中的“道”论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的“道”主要是指现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摄之道。陈大齐先生认为荀子所谓的“道”主要是以价值方面的道为主,而自然的道因为有助于价值方面的道,也就兼摄在“道”内。[1]刘宗贤认为,荀子的心以“道”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通过对“道”的认识和实行以禁止不合礼义的行为。[2]张家成认为儒家的天道观到了荀子那里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神秘的、有意志的“天”、“道”变为自然之“天”、毫无神秘意味的“道”。[3]孔繁认为,荀子的“道”是认识的最高层次,是支配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而“虚壹而静”则不只是一般的认识方法,更是超凡入圣的修养途径。[4]黎红雷认为,荀子将“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而“礼道——礼教——礼治”就构成了荀子哲学的主体。[5]廖名春认为,荀子的“道”是万物变化遂成的所以然,也即是万物的普遍规律,同时它也是一种客观的是非标准,其本身固有的规律性就体现在事物的无穷变化之中。[6]
另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荀子的“道”超越了现实世界的价值关怀而进入了更高的形而上领域。惠吉星认为,道是统摄礼义、贯通五经、流布天地之间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和规律,既是人类社会历史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也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超越时空并具有普适性。同时,道本身还是检验一切认识和实践的最高标准。[7]丁四新认为,荀子的“天”通过下落为心性而内化为人的一部分,因而“知天”就意味着认知这种通过心性内化的“在人者”的天。外在的天只有通过内在的天,才能达到真正的知、真正的治。而荀子所说的“虚壹而静”实是知性主体在对道体的把捉中,与道合一进而与天合一的明澈朗照,心外的事事物物也完完全全消融在纯思的把握中而毫无隔碍。[8]李翔海则认为,荀子提出的“虚壹而静”修养功夫使得人心平正而不邪僻,清明而不昏昧。秉此“大清明”之心,就足以认知理义之道,逐渐将礼义之统所提揭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理性自觉并渐臻“至诚”之境。[9]储昭华认为,虽然荀子的“道”更多是指人类社会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但“道”还指超越礼义法度这种具体之道的普遍之道。后者属于隐而不显、无形而功的超越世界,但同时又以各种具体之道的形态体现出来。[10]东方朔也认为荀子的“道”有两层涵义,一是作为具体行事方式方法或典章礼法制度之道,一是作为典章礼法制度何以可能之根据之道。对于前者来说,“道”类似于礼;对于后者来说,则是君子之心知所自觉创造的作为礼之根据的“道”,也是一种个体通过自觉修行所实现的最高境界而非外于人心的存在。[11]杨国荣认为,荀子的“道”既体现了存在的统一形态,又作为整体的形上智慧,为超越一偏、达到全面之知提供了视域。[12]
国外学界对荀子哲学中的“道”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Paul Rakita Goldin指出,荀子的“道”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本体论。道就是宇宙的“道”,是关于现实的“规范和模式”,而所有的理论都应当遵从这一最高的道。同时,道并不只是阴阳的混合与统一,而是主宰宇宙任何进程的永恒不变的道。[13]与Goldin的道本体论观点不同,Janghee Lee则认为荀子的“道”并不是通过心的神秘转化而具有的超越性视角,“道”是人对具体情境做出正确判断的整体性道德视角。[14]
除了对“道”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荀子哲学中的“天”及“礼”的形而上属性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牟宗三认为荀子的“养心莫善于诚”及“天德”的思想颇有形而上意味,与《中庸》相一致,但又认为荀子只知君师能造礼义,而不知能造礼义之心即是礼义之所从出。[15]张奇伟认为,荀子以天地自然而非人为的运行过程为原型,以人间礼义制度为摹本,认为人间的礼本是模拟天地而来,力图营造一个礼学的形而上学的基地。[16]陆建华认为,荀子对礼的形上化使得礼由社会主宰扩展和上升为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宇宙的主宰力量。[17]梁涛认为,荀子的礼根据天道而设立,它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原则,也是宇宙自然的原则。天和人共同依据礼而存在变化,表现为某种共同的秩序性和规律性,因而是天人合一的。[18]张方玉则认为,荀子的德性幸福在性恶的理论基点上,经由礼乐为学和积善等后天的教育修养,最终也实现了与日月同光与天地相参的理想境界,从而延续甚至提升了儒家德性幸福的超越性境界。[19]国外学者Robert C. Neville认为荀子哲学中的礼具有相当重要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地位,因为礼在荀子看来是人与天地构成完整关系的主要元素。[20]Edward Machle则认为荀子的“天”是其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荀子对探讨宇宙的秩序并无兴趣,但他明显采纳了他那个时代的宇宙观来说明他的哲学目的。[21]Robert Eno则认为荀子在“神”和“太一”的概念中体现了一种系统的形而上学,将自然和人在宇宙中的整合看作是具有超越性的存在。[22]Tan Sor Hoon则同意Robert Eno的观点,认为《荀子》一书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形而上学的预设,但这一预设也只是为了证明荀子关于礼学的思想。在《荀子》一书中存在的形而上学应当基于荀子的伦理学而不是伦理学基于形而上学。[23]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荀子的“道”论思想及其与心性论的思想关系研究已初步展开,对“天”、“礼”等的形而上学问题研究也已经较为深入。然而,当前学界对于“道”在荀子哲学范畴中的最高地位、礼乐法度与“道”之间的关系以及“道”与荀子心性论的重要概念(如“心”、“义”等)之间的关系尚未展开系统、深入地分析和研究,这是本文尝试完成的主要任务。本文将对荀子哲学中的“道”论思想展开深入分析,探讨荀子心性论思想与“道”和礼乐法度之间的内在关系,尝试用荀子的心性论思想来解决日常礼乐法度实践与最终形而上之道的张力问题。
二、儒家的“道”论传统
要谈论荀子的“道”,就必须要探讨“道”在整个儒家传统文本中的地位和涵义。在《周易·系辞》中有“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一句,说的是人的知识应当周遍于万物而用“道”来匡济天下。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句则是在说,道的广大足以拟范周备天地的化育而不致偏失,足以曲尽细密地助成万物而无所遗漏,足以会通于昼夜幽明的道理而无所不知,所以说事物神奇的奥妙不拘泥于一方而《易》的变化不定于一体。《系辞》中接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这就是说,一阴一阳的矛盾变化就是“道”,而仁者发现“道”有“仁”的涵义就称之为仁,智者发现“道”有“智”的涵义就称之为“智”,百姓日常应用此“道”却浑然不知,所以所谓“道”的全面意义就很少有人懂了。“道”显现于仁,潜藏于日用,鼓动化育万物而与圣人体认“道”时的忧患之心有所不同。这段话明确提出了“道”是一个包罗万象,蕴含世间诸多规律原理的综合体。将“道”只视作“仁”或者“智”只是说明了阐释者本身知识和视野的局限。对这段话中“道”的全面性的理解,王阳明的话也可以作为佐证:
“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智……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24]1
在王阳明看来,“仁”、“智”一定属于“道”的范畴,但同时“道”也一定包含了其他元素才能成为全面一贯的“道”。心即是道的本体,依孟子的解读,心包含了仁、义、礼、智等善端,这些也便是道的内涵。
《系辞》中后来提到,“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是在强调“礼”的知识积累的重要性。《系辞》中又提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段话是说虽然有仁德的人在管理国家中是最重要的,但也要通过礼法的约定,禁止为非作歹,才能确保有仁德的人管理国家。《说卦》也提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因此,“道”的涵义至少应该包括“仁”、“义”、“礼”、“法”等重要元素。同时,《周易》也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这是说儒家之道不是既定的规则或规范,它需要人们在不断的学习和思考中修改和完善“道”的内涵。
孔子对“道”的理解似乎也与《周易》暗中相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他的弟子曾参将这句话解释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所谓“忠”,即是指对待他人要忠实,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用孔子的话讲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实际上,忠恕二者在孔子的眼中就是仁的核心和本质内容。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说仁之方也已。”而《中庸》也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由此看来,“仁”本身就是道的本质和核心内容,至少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这一观点可以在《论语》的其他篇章得到印证。
《论语·学而》中,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的弟子有子认为,人应当培养自己的孝悌之心,这是成仁成道的根本。在这里,仁和道似乎是在同一个涵义上被使用。孝悌也就成为仁和道所必须具备的道德元素。那么,除了“仁”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要素在“道”中呢?“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在这里,先王之“道”又似乎包含了礼的内容。同样,在孔子评论子产时,说道:“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在这里,“恭”、“敬”似乎属于“礼”的范畴,而“惠”则属于“仁”这个更大的范畴,除此之外,“义”也进入了“道”的范畴中。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说,“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从这句话看来,“道”似乎才是人们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德”、“仁”、“义”似乎只是实现“道”的手段。因此,“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处于金字塔的最高层。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这样,除了“仁”、“礼”、“义”以外,“知(智)”和“勇”也是“道”的内容。
在孟子那里,“道”也似乎并不是一个有着单一成分的范畴。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在这里,“道”似乎就是“仁”。孟子又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这里,除了“仁”(“亲其亲”)之外,“道”似乎又有“礼”(“长其长”)的内涵。孟子还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按照朱熹的解释,此处的“大道”即是指“义”。这样,“道”同时也包含了“义”。同时,孟子也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因此,人的“道”包含了各种人伦关系的准则,“仁”、“义”、“礼”、“信”等就成为“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到了荀子那里,“道”依然沿袭着儒家的这一传统,并且用一种更为清晰而直接的方式将“道”的多元化构成要素表达出来。《荀子》中对“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解蔽篇》。荀子说,“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何谓衡?曰:道。”(《荀子·解蔽》)
由此可见,荀子所谓的“道”是在“兼陈万物”中的“道”,也就是万物的“中道”。荀子讨论“道”主要是从“解蔽”的角度来讲的。他认为,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各执一端,往往忽略了其他学派思想的合理成分。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荀子·解蔽》)
我们应该注意到,荀子在批评墨子等非儒学派思想家的学说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他们,而是承认他们学说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各家各派的学说也是“道”的一个组成部分(“道之一隅”)。然而,这些学说并不能完全涵盖“道”本身的全部内容。“道”本身是一个既包括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传统教义,也包含“法”(法律)、“辞”(语言与逻辑)、“天”(自然)等非儒学派思想合理成分的综合体系。虽则如此,仁、义、礼仍然是“道”的核心。荀子说,“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对荀子来说,“道”始终应该是儒家之“道”,贯穿始终的主线仍然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之道所关注的“道”是主张修身、立志、成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儒家既在现实层面强调了治国平天下这种外在的政治理想,也在内在修身的层面具有“天地万物一体为仁”这样的形而上诉求。儒家用自己的方式解释着这个世界,包括宇宙本体和人本身,它既将道德形而上本体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最高理想,也关注人如何通过修道的方式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一本体论理想。下面我们将详细探讨荀子如何将儒家的这种“下学而上达”之路阐释得更加清楚而明白,从而为儒家思想做出了独特的发展和创新。
三、荀子的“礼”、“义”与“心”
荀子的“礼”是针对人性之中的情感和欲望而言的。荀子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
所以,人的性中存在着诸多的情感和欲望。这些情感和欲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如果只是顺应这些欲望而不加以节制和规范,就会使这些欲望走向恶的后果。对荀子来说,人的自然本性是情感和欲望,而德性则是在后来的礼义教导下逐渐形成的,是后天形成的人的第二本性。荀子说:“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荀子·性恶》)因此,礼义和法度都是为了要矫正、教化、完善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荀子引入礼法制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完全消除情感和欲望。实际上,他是为了将这些欲望和情感转化成为可以控制的形式,从而它们能够被更容易地满足而不是被压抑。荀子说,“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荀子·礼论》)对荀子来说,尽管欲望和情感通常都是混乱而非理性的,但他们也不能被完全地压抑。通过礼义法度的约束和调节作用,能够缓和一个人的欲望和情感并将它们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因而,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上,荀子主张不能用理性取缔欲望,相反,应当用理性来逐渐教化和疏导欲望,使之能够为德性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荀子的礼乐法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礼乐法度对人情感和欲望的调节与疏导,逐渐转化人的道德意识,使之成为人们进行德性实践活动的伦理指导和根据。这一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心在内化礼乐法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下面我们就将详细探讨一下这种道德内化塑造过程的具体细节。
在荀子看来,放纵人性的结果是恶的,这也是为什么需要人为努力的原因。人性充斥着野心、贪婪、嫉妒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没有人为的约束或培养,就会脱离正确的轨道而泛滥成灾。虽然如此,在荀子看来,欲望和情感并不能体现人的本质特征,决定人成其为人的绝不是欲望和情感。那这种人类的独特特征是什么呢?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
在荀子看来,真正决定人的类特征的是人类具有“辨”的能力而不是欲望和情感这些生来就具有的东西。这种“辨”就是一种区别各种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的能力和界定社会等级的方式。荀子说的“父子之亲”并不只是说父子之间有着亲密的感情,更有父子之间存在的那种人伦关系以及各种制约这种关系的礼仪法则与制度。荀子接着说:“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这就是说,要用礼来指导“分”和“辨”。而荀子又提到“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这样,礼和义就联系在了一起。荀子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如果人类不能形成“群”,也就是社会的组织形式,就很难生活于自然界之中。然而,有了社会以后,也并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完善的社会等级制度和体系,也就是“分”,才能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因此,“礼义”在“分”的过程中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唯有通过礼义的作用,社会等级制度和体系才能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维持相对的稳定。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荀子在这里所说的“义”并不是孟子所主张的道德品质。事实上,对荀子来说,它只是一种需要等待道德品质来填充的理性能力。①“义”是人类所内在具有的一种理性能力,它能够保证人类在理性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群体。然而,这种内在的理性能力并不能使得人类就此就具有了控制自己行为,并主动走上道德之路的能力。事实上,人类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和管理,将很难自觉主动地趋向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圣人及其所创制的“礼”就会成为“义”的实质内容,“礼”通过影响“义”而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荀子认为,人同时具有了爱利和好义的倾向,但如何使得好义的倾向超过爱利的倾向,就必须要通过外在的力量将好义的倾向加以强化。这种外在的力量就是礼,它能将“义”这一理性能力加以充实并具体化,从而能够具有克制和改造人类欲望的能力。
这样,荀子就承认了人类在自身之中存在“义”的能力,这一能力却并未有任何具体的内容。这样一种“义”的能力需要道德和伦理知识来填充,这种知识就是儒家之道。一旦这种能力被儒家之道填充,普通人就能利用这种被填充的“义”来培养他们的“性”。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义”究竟存在于何地?是在性中,还是在心中?在笔者看来,荀子认为“义”应在心中。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这样,荀子将心定义为身体的“君”或“主”,心可以主宰身体的一切行为,因而心如何通过学习被充实成为道德的主体从而能够控制自己身体所具有的情感和欲望,就成为人走向道德之路的关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强调性与心的区别,性是本源性的情感和欲望,而心则是能动的、进行主动价值选择的主体“天君”,心中的“义”通过外在教育和学习的输入而获得道德知识,从而具有了指导情感和欲望的力量。
四、“虚壹而静”与“道”
在经历了“心”中之“义”的道德内化塑造过程,人的内心具备了进行德性实践活动的道德前提。然而,进行德性实践活动并不是荀子伦理学和哲学的最终目标。对他而言,人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是“道”。
正如本文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在荀子看来,儒家之道是包含了各种道德原则和伦理政治实践的综合体。然而,在这里我们也许会很容易忽略《荀子》书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大清明”。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它和“道”以及德性活动的关系是怎样的?荀子说:
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睪睪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知其形?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夫恶有蔽矣哉!(《荀子·解蔽》)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荀子认为“大清明”就是达到“虚壹而静”以后的状态。那么,“虚壹而静”又是什么状态呢?荀子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壹;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荀子·解蔽》)
荀子认为我们应该兼容万物和各种不同观点来避免偏见,但一个人要怎样做才能实现这种目的呢?荀子说:“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荀子·解蔽》)尽管我们已经在心中储存了有关知识的记忆,心却不能只集中于这些先前的知识而忽略了进一步的学习。即便我们要学的知识和已经学到的知识不同甚至矛盾,我们也应该不带偏见地去包容它。这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心中储存了多少知识,我们都要为容纳新的知识预留足够的空间。只有用这种方式,先前的知识才能成为我们未来学习的基础,而未来学到的知识也才能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添加进来。这样,荀子使用“虚”的方法来实现超脱的心,使之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个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虚”不是绝对、完全的“虚”。换言之,先前的知识应该储藏在心中,而未来获得的知识才能在先前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增加。荀子说,“心未尝不臧也”。(《荀子·解蔽》)对荀子来说,“虚”的使用是为了培养心成为一种理想的状态从而认知儒家之道。所以,对荀子来说,“虚”的使用是为了摈弃心中的偏见从而全面地认知儒家之道。
对荀子来说,为了建立儒家之道并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现实的境况中,人们就必须开放心胸,虚怀若谷,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偏见并兼容更多的观点。但是从各种不同学派中吸收的诸多观点要怎样才能保持一致并形成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呢?这就需要“壹”:“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壹,不以夫壹害此壹,谓之壹。”(《荀子·解蔽》)“壹”在《荀子》中指心在认知过程中维持一致性的能力。这就是说,尽管我们会对不同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有不同感觉,但心应该使不同的认知融会贯通,形成能够统摄不同片断知识的更高之“道”。
对荀子来说,既然人类应该驾驭和利用世上万物来服务于自己,那他们首先就应该去尽力认知万物。人们可能对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观点,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不同学派的原因。但既然万物是统一的,那关于它们的知识也应该是统一而不是孤立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同学派的观点都可以看作是真理整体的一部分,而它们理应结合为一个整体才能形成最后的真理。这就是说,不同学派的各种观点应该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于世界的完整认知。荀子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荀子·天论》)对荀子来说,既然所有观点都应该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不应该只拘泥于一种观点;相反,我们应该把所有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并保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知这个世界。在荀子看来,使“心”变“虚”并且接受各种不同观点只是真理认识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使各种不同观点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才能产生完满的认知。
在“虚”和“壹”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形成关于这个世界最完备的认识了。然而对荀子来说,要实现这个目的还需要另外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心中的“静”。没有“静”,“虚”和“壹”也不可能顺利完成。荀子说:“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荀子·解蔽》)“静”在《荀子》中意味着我们只有克服心中的所有幻象或迷梦才能实现“道”。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幻想或空想,比方说,梦境、胡思乱想等,但我们不应该让这些幻想影响我们的思维。对荀子来说,心应该保持如平静的水,只有这样才能毫无扭曲地折射出“道”。荀子说:“故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鬒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荀子·解蔽》)对荀子来说,只有心能够保持如平静的水一样,它才能准确地反映出儒家之道,正如平静的水面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的面部特征一样。
这样,在达到了“虚壹而静”,也就是“大清明”的状态之后,一个人能够用最完整、最包容的心态来认识这个世界,从而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道”。而一个人一旦得“道”,便可以“材官万物”,依照各个事物的特点来酌情处理,使人能称其任,物能适其用,掌握天地宇宙的“道”。荀子所讲的“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便是说,一个人达到“大清明”的境界后,就不仅能洞察万事万物,而且能进一步的参稽万物治乱而通其度,然后天地万物都在此大清明之心的处理擘划之中,宇宙间的一切真理,也都在此之中。
从这里可以看出,荀子的“大清明”是超越于一般的德性活动之上的。“恢恢广广,孰知其极?睪睪广广,孰知其德?涫涫纷纷,孰知其形?”就是在说,一般的德性活动总是有一定的界限,总是有具象的存在,而“大清明”则摆脱了这种外在具象的限制,不再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界限和规则。这其实就是一种自足性的体现,它虽然没有一般德性活动的具象特征,但却包含了所有的德性活动,是对所有德性活动乃至宇宙最高原则的抽象概括。人实现了“大清明”的境界,也就是实现了“道”。
对荀子来说,这种心与外在道德规范最终整合在一起的状态似乎就是“兼陈万物而中县衡”。荀子说:“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荀子·解蔽》)由此可见,荀子认为德性的最终目标就是位于中心的这个“衡”,也就是道。所谓的“道”,也就是儒家之道。
在荀子眼中,虽然人所能达到的“大清明”的最高境界就是“道”,但这种最高境界并不排斥低一层级的“道”。德性活动和礼仪制度是最高境界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属于低一层级的“道”。所有这些,也都是构成“道”的要素。也就是说,我们在说儒家之道是德性活动与外在善的结合时,这并没有错,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更高层级的儒家之道是对所有这些德性活动乃至宇宙的最高原则的思考。这正如“虚一而静”所体现出的那样,容纳所有德性活动乃至宇宙最高原则是为了对它们进行一种一致性的思考,从而达到“道”的境界。
我们知道,荀子认为“道”的实现在于“大清明”境界的实现,而这一境界的达到在于“虚一而静”的活动。经过“虚一而静”的活动,我们能够包容更多关于宇宙和社会人生的真理性认识。各种类型的德性活动和道德实践都潜藏在这一看似平静的状态之中,因而,“大清明”的境界并不排斥德性的实践活动,它本身也是对所有这些德性实践活动在理论层面的反思和总结。在这一点上,“大清明”和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是相互兼容的,它们之间并不会因为“大清明”的抽象性和道德实践活动的具象性而互不兼容。恰恰相反,“大清明”是所有德性实践活动在心灵层面的抽象和反思,而道德实践活动则是“大清明”境界在具体实践层面的呈现。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道”这两个层级的内容并不会因为它们的层级不同而互不兼容。就像“大清明”是所有德性实践活动在心灵层面的抽象和反思一样,德性实践活动则是“大清明”境界在具体实践层面的体现。
这样,荀子通过心本身具有的接受礼乐法度道德教化和教化“性”中欲望情感的双重功能,强调了“义”在内化礼乐法度制度和进行德性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心的“虚壹而静”功夫,将具体的礼乐法度实践活动塑造而成的道德人格提升到“大清明”即“道”的境界。这就使得儒家思想中长期存在的日常礼乐法度实践与最终形而上之道的张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从而为儒家日常伦理活动的实践找到了最终的价值依据。
[1]陈大齐. 孔孟荀学说[M]//陈百年先生文集:第1辑.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2]刘宗贤. 孟荀心性学说的不同倾向[M]//赵宗正. 孔孟荀比较研究.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3]张家成. 荀子“道”论探析[J]. 浙江大学学报,1996(2).
[4]孔繁. 荀子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黎红雷.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J]. 现代哲学,2004(4).
[6]廖名春. 荀子新探[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7]惠吉星. 荀子与中国文化[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8]丁四新. 天人·性伪·心知——荀子哲学思想的核心线索[J]. 中国哲学史,1997(3).
[9]李翔海. 从心性学说看荀子思想的学派归属[J]. 哲学研究,1998(10).
[10]储昭华. 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东方朔. “无君子则天地不理”——荀子“心与道”的关系片论[M]//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3卷.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2]杨国荣. 从“志于道”到“壹于道”——略议孔子与荀子关于道的论说[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3]Paul Rakita Goldin,[M], Chicago: Open Court, 1999.
[14]Janghee Lee,[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15]牟宗三. 名家与荀子[M]. 台北:学生书局,1979.
[16]张奇伟. 荀子礼学思想简论[J]. 中国哲学史,2002(2).
[17]陆建华. 荀子礼学之价值论[J]. 学术月刊,2002(7).
[18]梁涛.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9]张方玉. “天人相分”的人生幸福何以内在超越——论荀子的幸福境界[J]. 船山学刊,2014(2).
[20]Robert Cummings Neville,[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21]Edward Machle,[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22]Robert Eno,[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23]Tan Sor Hoon, “(Ritual/Rite) and(Heaven/Nature) in the: Does Confucianneed metaphysics?” [J],, 2007(1).
[24]王阳明. 传习录上[M]//王阳明全集:上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① 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教授(David S. Nivison)亦持此种观点,见David S. Nivison, “Critique of David B. Wong, ‘Xunzi on Moral Motivation,’” in T.C. Kline Ⅲ and Philip J. Ivahoe (eds.),, Chicago: Open Count, 1996, p. 324.
B222.6
A
1673-2030(2017)04-0011-08
2016-08-15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郭店楚简的早期儒家心性论问题研究”(15ZXA002)的阶段性成果
孙伟(1977—),男,山东临沂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