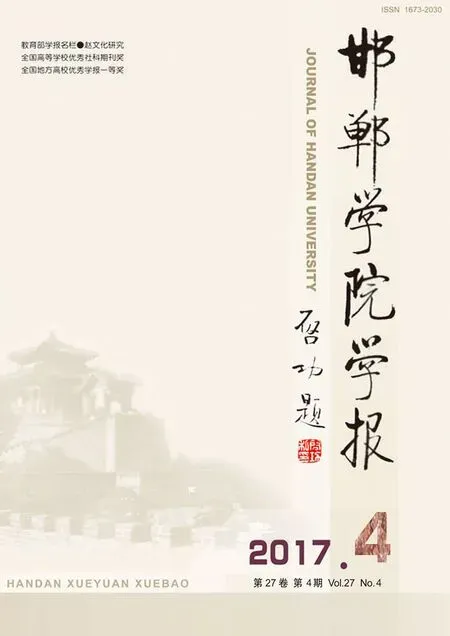“汲冢主人”新考
——兼及《穆天子传》的作者与时代
任乃宏
“汲冢主人”新考——兼及《穆天子传》的作者与时代
任乃宏
(邯郸学院 赵文化研究中心,河北 邯郸 056005)
通过梳理前贤今人之成果,考定《晋书》等关于“汲冢竹书”出自魏襄王墓的判断有误,“汲冢”或为“末代董史”墓,《竹书纪年》似为历代“董史”接续完成之“大事记”,并非“编年体通史”。《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官所作“起居注”,是由第一代“董史”带入晋国、并在三家分晋后流入魏国的。
汲冢竹书;穆天子传;起居注;末代董史
学界对新出古代简牍向来趋之若鹜,片言只字奉为至宝,且每喜引用陈寅恪之言为标榜:“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偶有“发现”,便“情不自禁”,一会儿说司马迁把哪儿哪儿搞错了,一会儿又说刘向总是乱改书。问题在于,司马迁著书,刘向校书,直接面对的就是尚称“新鲜”的先秦简牍,若论识读功夫,今人又何能望其项背。今天的许多所谓“发现”,很难说不是他们当年的“弃余”,以之补史、证史或有价值,动不动就据以质疑传世文献,则未免有些浅薄。事实上,如果不对传世文献下足功夫,所谓的新出简牍“研究成果”也八成靠不住。现在的问题似乎并非新材料太少,而是对现有材料的研究还远未深入。与其匆匆忙忙赶时髦,不如从从容容下些笨功夫,把多少有些夹生的冷饭炒熟,也许会有别一番的滋味溢出。关于“汲冢主人”生前身份之确定,应该就是这种尚待翻炒的“冷饭”之一。笔者以为,“汲冢主人”应非晋·荀勖推定之魏襄王,也非晋·王隐推定之安釐王,好像也不是朱希祖先生论定的“魏王”,他应该是魏襄王时期的史官之一,大概率是董狐的后人。
一、“汲冢竹书”的出土时间文字形式及内容
朱希祖先生视“汲冢竹书”的出土为中国文化三大发现之一,可与汉武帝时期在孔子府邸夹壁墙里发现的“古文经”及民国年间发现的甲骨文并驾齐驱[2]。
关于“汲冢竹书”的出土时间,朱希祖《汲冢书考》考之甚详:“‘汲冢’书所得年月,约有三说:《晋书》卷三《武帝纪》系于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月,阎若璩《困学纪闻笺》云《晋武帝纪》本《起居注》,此一说也。卫恒《四体书势》、王隐《晋书·束皙传》则系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书》卷十六《律历志》汲冢得玉律,亦云太康元年,此一说也。荀勖《穆天子传序》、唐修《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则系之于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亦云太康二年,此又一说也。雷学淇《竹书纪年考证》云:‘竹书发于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明年三月吴平,遂上之。《帝纪》之说,录其实也。余就官收以后上于帝京时言,故曰太康元年(280年)。《束皙传》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岁也。’案:雷说是也。惟云‘吴平遂上之’,恐尚嫌过久。盖出土在咸宁五年(279年)十月,当时地方官吏即表闻于朝,汲至洛京虽隔黄河,相去不过二三日程,及帝命藏于秘府,至迟必在太康元年(280年)正月。否则露积于汲冢,则有散佚之虞,保管于郡府,亦有疏失之虑,何能待至吴平而后献邪?当收藏秘府之时,正大举伐吴之际,军事孔亟,未遑文事。及三月吴平,论功行赏,吴土战乱,尚未全定,故至太康二年(281年)春始命官校理也。王隐《晋书·束皙传》云:‘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可以证明之。三事不同时也。”[2]1-2
“汲冢”竹简文字为“漆书蝌蚪文”,亦即“先秦古文”,证据确凿。一在晋·王隐《晋书·束皙传》:“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2]13二在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科斗文久废,推寻不能尽通。”[2]13三在晋·荀勖《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2]13三人皆曾亲见当年出土之竹简,故竹简文字为“漆书古文”一说,当不容挑战。
“汲冢”竹简整理后写成今隶者计十九种,凡七十五篇,唐修《晋书·束皙传》载之甚详:除《纪年》十二篇外,尚有《穆天子传》五篇;有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在内的“杂书”十九篇;有《易经》二篇;有《易爻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爻辞则异”;有《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有《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有《□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有《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有《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有《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有《缴书》二篇,“论弋射法”;有《生封》一篇,“帝王所封”;有《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有《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另有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3]1432-1433。
二、此前对“汲冢”主人身份之讨论
关于汲冢竹书出于何人之墓,之前大致有四种说法。其一认为墓主是魏襄王,主此说者为唐修《晋书·武帝纪》与《律历志》,晋·荀勖《穆天子传序》,晋·卫恒《四体书势》,以及唐修《隋书·经籍志》等,今人辛德勇等仍持此说[1];其二认为墓主是魏安釐王,主此说者为晋·王隐《晋书·束皙传》。唐修《晋书·束皙传》则对墓主究竟是魏襄王还是安釐王不置可否;其三认为“汲冢”当为“魏王冢”,主此说者为朱希祖;其四认为“汲冢”为“古冢”,主人不明。主此说者为晋·杜预,今人陈梦家、罗家湘等赞同此说。
朱希祖批驳了“襄王说”和“安釐王说”,提出了“魏王说”:“言汲冢为魏襄王冢者,盖因《纪年》终于魏之今王。荀勖《穆天子传序》云:‘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史记》之哀王,即《世本》之襄王,哀王二十三年而卒,故二十年时称为‘今王’。然二十一年今王未卒,何能即以竹书从葬?故荀勖所记诸年,盖指《纪年》绝笔后之年,后人误以为竹书入冢之年,则不可通也。……若为安釐王冢,不应缺昭王、安釐王两代事不书。……从古至今,未闻以其国史殉葬者,且亦未闻殉葬之国史必记至其所葬之王末年者。不知《纪年》一书为编年之通史,非编年之国别史;为魏国私家所记,非为魏国史官所记。自晋以来,都误认《纪年》为魏国国史,故诸家解释,牵强附会,多不可通。此说既明,则汲冢为魏襄王冢或安釐王冢,皆属臆测,非有他种书籍或物品以为证据,则不可断定为何王之冢也。惟汲冢中既有玉律钟磬,则为王者之冢自无疑义。而汲为魏地,《纪年》为魏国人所记,则谓为魏王冢,亦属合理。惟苟无其他实证,则谓为襄王冢或为安釐王冢,皆属武断,不足为训。盖所谓魏王冢者,自襄王、昭王、安釐王、景湣王皆可,惟不能出于襄王以前耳。”[2]3-5
杜预“古冢说”的实质即“汲冢”非“魏王墓”,相当于否定了“魏王说”。今人罗家湘认为:“说汲冢主人为魏襄王是不可通的。根据《西京杂记》卷六记载,汉广川王去疾发掘魏襄王墓,则魏襄王之冢不待晋时发掘。……朱希祖本明此理,却惑于‘汲冢中既有玉律钟磬,则为王者之冢自无疑义。而汲为魏地,《纪年》为魏国人所记,则谓为魏王冢,亦属合理。’战国之时,礼崩乐坏,玉律钟磬之设,何必王家。《纪年》终于今王二十年,又如何可以视其为‘私家所记’‘编年之通史’而移之他王?陈梦家以为‘魏自惠王至魏亡都大梁,帝王陵不当在汲,竹书出土于魏国大臣之墓,非必魏王之墓,杜、范、傅目为古冢是也。’笔者同意这一看法。与云梦秦简《大事记》比较可知,汲冢当为古冢。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余枚,就中《大事记》分写在五十三支竹简上,按年代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将近一百年间的国家大事和墓主人的几件私事。对秦王嬴政,《大事记》称之为‘今’,这与《汲冢纪年》称魏襄王为‘今王’相似。秦始皇享国三十七年,《大事记》只记录到三十年,表明此年墓主人死。《史记·魏世家索隐》:‘《汲冢纪年》终于襄王二十年。’而魏襄王享国二十三年,这表明汲冢主人死于魏襄王二十年。因此,与睡虎地秦墓一样,汲冢并非王墓,而只能是葬于魏襄王二十年的古冢。”[4]79
三、“汲冢主人”当为魏国史官之推定
笔者以为,“汲冢”当为魏襄王时期史官之墓。证据如下:
就汲冢竹书内容论,除《大历》《图诗》《缴书》及不可识读者计12篇不便归类外,其余63篇竹书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曰史类,二曰卜筮类,三曰《易》类。其中:史类44篇,即《纪年》12篇、《穆天子传》5篇、《杂书》19篇、《国语》3篇、《□名》3篇,《梁丘藏》1篇,《生封》1篇;卜筮类12篇,包括《师春》1篇,《琐语》11篇;其余7篇为易类。据之可知,史类和卜筮类为竹书之大宗,且史类明显为墓主生前之最爱。以常理推断,墓主生前当为史官。此其一。
史出于巫,卜筮、占梦、妖怪类知识亦为史官所必备。夏、商、周三代,巫与史密不可分。据斯维至考证:“古代巫史不分。……(《左传》中)或以祝宗连文,或以祝史并举;史能占卜,宗亦能占卜,则祝、宗、卜、史的职务必定是差不多的。……《仪礼·少牢馈食礼》云:‘筮者为史’,《国语》亦有‘筮史’,盖以筮占卜,与以龟占卜相同;筮从巫,故巫亦史。”[5]又,《礼记·礼运》:“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故先王秉蓍龟……宣祝嘏辞说。……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6]679-705再,据孔祥骅考证:“甲骨文中有一类史官称‘御史’,《说文》上说:‘御,祭也’,即主持鬼神祭祀之事。在商代,政教之职,多执于其手,然自文字通行之后,操卜筮则必记录日期、经过与结果,这些通文字、主职卜筮者,即为后来史官之滥觞。……至周代,此种兼掌祭祀与记事的巫官则称为‘大史’。《左传》闵公二年记载说:‘我大史也,实掌其祭’,可见‘史’为司祭之一员,其职能是祭司兼卜人。又《易·巽·九二》上说:‘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此可证史与卜关系十分密切。……清代的学者汪中在《春秋释疑》上说:‘周之东迁,官失其守,而列国又不备官,则史皆得而治之,其于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祝、宗、卜、史,明乎其为联事也’。他以《春秋》上的大量史料证实了当时之史官‘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司梦’的多种巫史职能。”[7]又再,据郑晓峰考证:“董作宾先生根据甲骨卜辞,列出20种商代卜事,‘卜梦’亦在其中。……按照孟学凯先生的统计,‘目前发现甲骨文中占卜梦的卜辞有一百七十余条(含残辞),其中绝大多数为武丁时期的占卜’。‘武丁时期占卜王梦的卜辞有近七十条’。……《左传》所记29梦,有26梦涉及的梦象,多与鬼怪神妖有关,……出现(了)6位专职的占梦人员:(4位)巫官(贞伯、桑田巫、巫皋、卜人)与(2位)史官(史朝、史墨)。”[8]综上可知,卜筮、占梦亦为史官之重要职能,汲冢竹书中有大量此类文献,似可印证“汲冢主人”生前或为史官。此其二。
最初的《易》本为巫史占卜之记录,成文《易》则成了指导占卜实践的理论指南。对此,孔祥骅的说法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易》,就是周初从总结占卜卦象中整理出来的。巫官中的卜官,亦即卜正、祝史即以《易》为宝典,夏代的《连山易》、周代的《归藏易》与《周易》,全称《三易》,即为卜官们整理出的文献。”[7]《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了一个晋国史官在晋楚“鄢陵之战”前运用《易》为晋厉公进行占卜的例子:“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集)于王卒,必大败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及战,射(楚)共王,中目。”[9]895-897既然《易》为史官所必备,汲冢竹书中有大量《易》类文献,似亦可印证“汲冢主人”生前或为史官。此其三。
晋·杜预亦认为《纪年》为魏国史记:“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9]1982如杜预所言不错,殉葬的《纪年》既为魏国史记,则“汲冢主人”自非魏国史官莫属矣。此其四。
四、“汲冢主人”或为“末代董史”之推定
笔者以为,《纪年》应系历代“董史”接续完成之“大事记”,并非“编年通史”,“汲冢主人”应即“末代董史”。证据如下:
其一,《纪年》用夏正纪时,符合“董史”身份。“董史”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夏后启之支子。《左传·昭公十五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杜预注:“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适晋为太史,因为董氏,董狐其后。”[9]1549又,辛有为周平王时人,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9]460再,据胡恤琳等考证:“相传夏后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遂演化为后来的辛氏。《国语·晋语八》记载晋平公‘祀夏郊,董伯为尸’。祭祖以同姓族人为尸(代神受祭者)是周代的祭祀通例。董伯姒姓,故能在祭祀夏代郊神的典礼中取得扮神的资格,由此可知董氏及其大宗辛氏确系姒姓丰族的后裔。”[10]据之可知,“董史”与夏代王族渊源颇深,《纪年》采用夏正纪时,并不奇怪。
其二,朱希祖断《纪年》非魏国国史,确为不刊之论。春秋战国之世,周王尚为名义上之共主,魏国既属东周,其国史纪时,焉有不用周正之理?问题在于,朱希祖以此为据,进而断言“《纪年》一书为编年之通史,非为魏国史官所记”则稍嫌武断。由《纪年》对于西周、春秋、战国,不分记各诸侯国事,独记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又独记魏国,且称魏襄王为“今王”来看,即便《纪年》属于私撰之史,其笔法却与国史无异,在史学依靠世袭家传的时代,倘无史官家族背景,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应该是不可能的。须知,“董史”的先祖是辛有,辛有的先祖则是辛甲。《史记·周本纪》:“(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刘向《别录》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11]116由辛甲事纣“七十五谏”可知,辛氏家族在商朝已任史职。以常理推断,辛甲的先祖或许在夏朝就已担任太史。此说虽无法证其实,欲证其虚却也万万不能,因为《史记·太史公自序》早就告诉我们:“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11]3285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笔者的推论成立,则历代“董史”的传承自夏至周从未间断,如果这个史官家族养成了记“大事记”的习惯,一代一代积攒下来,岂不就是一部活脱脱的《纪年》,又何须编年?!
其三,将《纪年》带入坟墓的应是“末代董史”,关于这一点,顾实《读穆传十论》有精彩论述:“(《穆天子传》)藏于魏之汲冢,则亦有故矣。考昭十五年《左氏传》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拜戎不暇。’又曰:‘昔孙伯黶司晋之典籍,及辛有之二子董至晋,于是乎有董史。’案辛有者,周平王时人。平王东迁,晋文侯有翊戴之功,宜乎周赐以世官之史矣。然则《穆传》者,盖出于董史之赍来,实镇抚戎狄之宝典,而与晋国以甚深之教训者也。春秋之世,魏绛以和戎著绩,故虽晋魏易代,而世史之守犹存也。迨魏文侯最为好古,其乐人窦公,尚至汉而献周官大司乐章。则穆王故事,自尤宜在保存之列。独惜魏自惠王至襄王,霸图已矣。故遂尽取竹书而藏之冢,抑性之所好,而用以殉耶!”[12]笔者以为,末代“董史”之所以将包括《纪年》《穆天子传》在内的竹书殉葬墓中,应系世守之史职已无法延续,因悲观而绝望,遂宁可藏入地下,亦不愿留予世人。
五、关于《穆天子传》作者与成书年代之讨论
《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中以较为完整之状态流传至今的唯一典籍。关于其文献性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列之于史部起居注类。宋元以降,《穆天子传》的地位每下愈况,先是《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将之列入了传记类;之后,《宋史·艺文志》又将之列入了史部别史类;最后,清季之《四库全书总目》干脆将之列入了小说异闻类。由信史而传记而别史而小说,到底哪种说法更靠谱一些呢?这确实是个问题。
关于《穆天子传》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此前大致有四种说法:一为“西周说”,谓书成于西周,作者即周穆王之史官。唐宋之前,此说几乎无人置疑。今人仍力主此说者似仅有顾实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二为“春秋战国说”,主此说者为当代学者王范之等。在《<穆天子传>与所记古代地名和部族》一文中,王范之写道:“我曾对《穆传》作过比较详细的考查,特别从它的语词和文法体例,将西周、春秋、战国这些时代的书籍一一加以参证较核,得出结论,知道并非是周代人的著作,更也不是汉后人的著作。……我考定《穆天子传》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春秋》成书以后《左传》成书以前,……这书可能是这时代的人根据着传说同时结合了他们的时代知识、设想,将它创造出来的。”[13]三为“战国说”,主此说者以顾颉刚为代表。顾颉刚撰有《<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一文,谓《穆天子传》的著作背景即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其作者当为赵国学者[14]。四为“汉以后伪作说”,始作俑者为清人姚际恒,今人童书业等亦表示赞同。
鉴于《穆天子传》出土于战国汲冢之中,“汉以后伪作说”几乎是睁着眼说瞎话,因此此说似已无人跟风。“春秋战国说”与“战国说”貌似无本质区别,照笔者看来,却比“战国说”略为高明一些,因为他说得更含糊一些。“战国说”为“疑古派领袖”所主倡,加上顾颉刚弟子众多,因此跟风者甚众,在学界已几成定论。问题在于,《穆天子传》中的人物已为地下出土文物所证实(如《班簋》等),周穆王的西征路线也越来越清晰且多与史合,此时再来坚持“战国说”,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走笔至此,忽然想起《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话:“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向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15]693-694笔者以为,“战国说”也好,“汉以后伪作说”也罢,其观点之所以破产,皆因与“亡鈇者”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他们眼里,《穆天子传》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无疑就是那位“邻人之子”。
真相只有一个。毫无疑问,笔者是赞同“西周说”的。而且,在“汲冢主人”身份既明之后,坚持“西周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风险了。
[1]辛德勇. 谈历史上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茂陵书[J]. 文史哲,2012(4).
[2]朱希祖. 汲冢书考·出版说明[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罗家湘. 《逸周书》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斯维至. 古代史官与典籍的形成及其作用[J]. 史学史研究,1982(2).
[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孔祥骅. 先秦儒学起源巫史考[J]. 社会科学,1991(12).
[8]郑晓峰. 《左传》叙事的巫史文化因素解析[J]. 北方论丛,2012(2).
[9]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胡恤琳. 从董氏家族看晋国史官的优良传统[J]. 沧桑,2001(3).
[1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顾实. 穆天子传西征讲疏[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8.
[13]王范之. 穆天子传与所记古代地名和部族[J]. 文史哲,1963(6).
[14]顾颉刚. 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J]. 文史哲,1951(1).
[15]吕不韦. 《吕氏春秋》新校释[M].. 陈奇猷,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K224.06
A
1673-2030(2017)04-0061-05
2017-09-10
任乃宏(1963—),男,河北魏县人,邯郸学院特聘教授,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