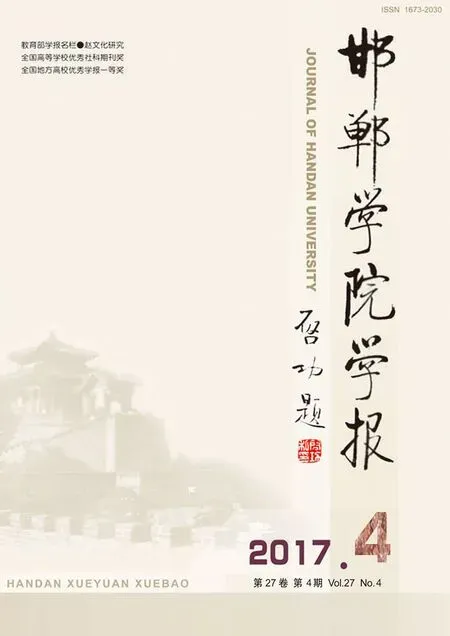先秦巫者的祝诅放蛊活动
[韩]赵容俊,[韩]金炫抒
先秦巫者的祝诅放蛊活动
[韩]赵容俊1,[韩]金炫抒2
(1.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2.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亚非学院,北京 100089)
运用商代甲骨卜辞的记录,并与先秦的传统文献及出土文献、考古学的报告,互相印证,探讨先秦巫者曾从事的祝诅放蛊方面的巫术活动。巫者职司交通鬼神,其本身虽不具超乎自然的力量,但古人相信巫者可藉鬼神之力以成就诸多事。祝诅放蛊之事,因古人相信巫者能为祝诅放蛊之事,遂成为巫者从事之重要职事。巫者不仅能解除人之灾祸,尚且能以其术害人,学术术语称为“黑巫术”、“凶巫术”,于制敌、制人、作弄敌对者时,便施行此法。
巫术;祝诅;放蛊毒人;传统文献;出土文献
一、绪 论
祝诅放蛊之事,因古人相信巫者能为祝诅放蛊之事,遂成为巫者从事之重要职事。巫者不仅能解除人之灾祸,尚且能以其术害人,学术术语称为“黑巫术”、“凶巫术”,于制敌、制人、作弄敌对者时,便施行此法。
二、甲骨卜辞所见之祝诅放蛊
首先,祝诅之术,又称诅咒、诅语、咒语、巫辞、巫术语言等,因以朗诵或歌唱的形式表达巫术语言,或属于其人的物件上施行祝诅巫术,故从而成为祈求危害对方的巫术形式。



蛊,以鬼物饮食害人。[3]683
此种放蛊毒人之术,于古籍文献中则多见之,如在《前汉书·江充传》中便有其记载,其云:
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4]206
由此可知,汉代喧闹一时的巫蛊之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于放蛊毒人之术的记载,可追溯至三千年前的商代,于商代甲骨卜辞中,即可见之,玆略举数例于下:
贞:母丙亡蛊?
贞:母丙允有蛊?(以上皆见于《合》02530正)
有疾,不蛊?(《合》13796)
贞:有灾,不隹(惟)蛊?(《合》17183)
贞:隹(惟)蛊?二告。不牾蛛。
不隹(惟)蛊?(以上皆见于《合》17184)
据此可以得知,于殷商时期,已盛行放蛊毒人之术。
由此观之,于殷商时期,此种祝诅放蛊巫术的流行,已可证实。尤其,于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放蛊毒人巫术的辞例,屡见不鲜,故可知此种放蛊毒人的巫术,已于商代之前便盛行。[2]644-646
三、两周文献中的祝诅放蛊
(一)祝诅巫术
1. 祝诅盟誓
巫者从事祝诅盟誓之术,由于其中保留不少晦涩的语言,以及属于其人的物件上施行的祝诅巫术,足以影响对方的观念,则加上更大的神秘性,正因为如此,颇为盛行于一般民间之中。此事如《尚书·吕刑》便有其记载,其云:
民兴胥(相)渐(诈),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反)诅盟。[6]247
由此可知,此种祝诅盟誓之术,于中国古时,颇为流行于一般民间之中。
不宁唯是,于两周古籍文献中,已记载祝诅盟誓巫术流行之甚广,又盛行于朝廷之中等事,如《周礼·诅祝》曰:
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禬、禜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6]816
又《周礼·司盟》亦云:
司盟:掌盟载之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旣盟,则贰之。[6]881
由此不难得知,于周朝朝廷中,已设负责诅祝盟誓之官之可能①。
除此传世文献之外,若视两周出土文献的记载,亦可多见盟誓的记录。如在2009年4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入藏一批战国楚简,此楚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40年。[7]1
其中在《春秋左氏传》篇中,便有诸侯在相会举行盟誓仪式时,古人重视执行其盟誓之言的内容,其简文曰:

由此可知,古人在举行盟誓仪式时,便重视其盟誓之言的执行。
除此在诸侯相会时举行盟誓载书仪节之外⑧,又由《诅楚文》⑨的“箸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8]298之句可知,巫者将盟诅之辞上告鬼神,且作为盟诅之监察者。此事在侯马盟书“委质类”的载书中,亦有其记载,其云:
由此可见,巫觋祝史所荐的“说释”即盟辞,其盟书之陈告必能沟通人神意旨,故证明巫者确实负责将盟诅之辞上告鬼神[10]327-328。由此观之,祝诅巫术,除民间之外,亦盛行于朝廷、贵族社会之中。
2. 诅咒巫术
(1)传世文献所见之诅咒巫术
就诅咒巫术而言,于浩如烟海的两周古籍文献中,亦屡见不鲜,如《尚书·无逸》便有其记载,其云: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譸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6]222-223
孔颖达疏于其下,曰:
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之祝,请神加殃谓之诅。[6]222-223
又《尚书·汤誓》亦云:
〔汤〕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何)?’夏王率遏(止)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何)丧?予及汝皆亡!’”[6]160
此文因夏桀凶德日深,百姓便欲与之俱亡,乃如此诅咒之。
又《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亦有其记载,其云:
公曰:“子为晋君也!”对曰:“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于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6]1972
此文中的食肉、寝皮等言,则为憎恶敌人的最恶毒诅咒。[5]332
又在《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晏子力谏于齐景公免杀祝、史之事,其云:
〔晏子对曰:〕 “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尢(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6]2093
故晏子认为,当时百姓向暴虐君主的诅咒,具有相当巨大的作用⑤。
此外,若视诅咒巫术的施术之例,尚有“祝移”之术,此术乃为巫者将罹祸人之灾难,转移至肇祸人身上,并使其人罹祸的巫术。又如“诅军”之术,此术不仅免除施术者一方遭遇败军之祸事,并且施以事先诅败对方为获胜免祸之手段。诅咒巫术活跃于战场的例证⑥,如《前汉书·匈奴传》便有其记载,武帝征伐匈奴(公元前92年至前89年),汉军追至漠北的范夫人城,范夫人则以诅咒巫术拦阻汉军。[4]350
(2)出土文献所见之诅咒巫术
若视出土文献的记载,自1979年始,于河南省温县武德镇公社西张计大队,曾出土春秋末期(公元前497年)的温县盟书。此温县盟书,目前共发现一百二十四土坑,其中十六土坑出土书写盟辞的大量石片。[11]78
若视其中在T1坎1:2182出土的载书记录,便有诅咒巫术的内容,其文曰:
上引盟誓辞文的答疑是说,乃为今后忠心服侍主君,若与乱臣为友,丕显的晋国神灵,将仔细审察,便绝子绝孙。[11]79-81
不宁唯是,于2009年4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入藏一批战国楚简,此楚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40年[7]1。其中在《春秋左氏传》篇中,亦有诅咒盟书辞文,其简文曰:
由此可知,于两周时期,便盛行盟誓诅咒巫术。
除此之外,古人将一切的疾病与灾殃,皆认为恶鬼作祟或受神灵惩罚的结果,故巫者以法术驱除缠身的恶鬼,以排难解忧且脱离其桎梏。此时巫者或用诅咒法,祓禳山川邪鬼作祟的疠疫与灾殃⑧,此乃属于巫者的一种祝诅法术之类,殆毋庸置疑矣。
若视出土文献的记载,此种巫者施行的诅咒法术,则不乏得见。如在1975年末,在云梦睡虎地M11号墓葬发现的秦简《日书》中,便有其记载。兹举其一二文为例,其简文曰:
行到邦门困(阃),禹步三,勉(进)壹(一)步,謼(呼):“皋,敢告曰:某行毋(无)咎,先为禹除道。”即五画地,掓(拾)其画中央土而怀之。(此简文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第111简背至第112简背)[12]223-224
据此不难得知,于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便有巫者施行诅咒法术的事实⑨。
此外,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大祝禽鼎》乃为周器,故可知周代时,祝官的设置已极普遍,此时人亦深信祝具咒诅之能⑩。
3. 小结
综上所陈,由上述几例可知,祝诅与诅咒之术,除民间之外,亦盛行于朝廷与贵族社会之中。不仅如此,亦可证明两周时期已有祝诅与诅咒的施术。尤其,中国古代的巫者运用咒术巫术,即运用某种特殊之语言、物品、符号、符箓,乃至配合其他器物、祭祀仪式之运用,以从事诅咒对方之巫术。
(二)放蛊巫术
1. 放蛊毒人之术
两周文献中的放蛊毒人之术,如《春秋左传·昭公元年》云:
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巽下☴艮上☶)。皆同物也。”[6]2025
此文之下,孔颖达疏云:
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6]2025
《周易·蛊》亦云: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6]35
孔颖达疏于其下,曰:
褚氏云:“蛊者,惑也。物旣惑乱,终致损坏。”[6]35
由此可见,放蛊毒人之术法,渊源悠久。
不宁唯是,对于中国古代原始毒人巫术的情形,如《论衡·言毒篇》便有其记载,其云:
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太阳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脤胎,肿而为创(疮)。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巫咸能以祝延(移)人之疾、愈人之祸者,生于江南,含烈气也。[13]950
此种记载未免夸大,即使如此,却充分表现秦代的社会心理。[14]304-305
此外,有关口舌有毒与毒人巫术的出土文献记录,于1975年末,在云梦睡虎地M11号墓葬发现的秦简《封诊式·毒言》篇中,便有其记载,其云:

此篇记载里人士伍丙口舌有毒,里人送府共同报告,且其外祖母曾因口舌有毒论罪,30岁时处以流放。由此可知,依其判例,若有毒言之疾,于当时的法律规定上,应将之处以迁刑[14]304。
此种放蛊毒人之方法极其为多,例如金蚕蛊、疳蛊、癫蛊、胂蛊、泥鳅蛊、石头蛊、蛇蛊、篾片蛊、蜈蜙蛊等等[15]230。此外,亦有养鬼放鬼作害于人,以及致人于死地为莫上之乐的黑巫术等,甚为无稽,此种放蛊毒人巫术之例甚多,举不胜举。
2. 治蛊之法
就治蛊之法而言,有关巫术性治蛊之术的记录,如《周礼·翦氏》便有其记载,其云:
翦氏:掌除蠧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6]889
又《周礼·庶氏》亦云:
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以〕嘉草攻之。凡敺(驱)蛊,则令之比之。[6]888
其下郑玄注云:
毒蛊,虫物而病害人者。……攻说,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药物,其状未闻。攻之,谓燻之。[6]888
此文中的“嘉草”,今人胡新生认为特指治蛊的蘘荷。[16]444-445
据此《周礼》的二文不难得知,巫术性治蛊之法有二,一为以“攻说”禳法祈求神灵除蛊,二为以草药“攻之”而燻虫杀蛊⑪。因此,于中国两周时期,不仅流行放蛊毒人之术,又有巫术性治蛊之法。
除此巫术性治蛊之外,亦有劝时王禁止放蛊毒人之术的记录,如传为周初吕望(即姜太公)所撰的《六韬·上贤》篇中,便有周文王问姜太公治国之道的内容,其中则有太公回答王人者应慎重六贼、七害之事,其云⑫:
〔太公曰:〕“七害者,……。七曰:僞方异技,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由此可知,于王人者应慎重的六贼、七害之事中,便提及放蛊毒人之术,且劝王止之。
尤其,如《礼记·王制》便记载周代制定的治蛊之法,其云:
析(巧)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6]1344
其下郑玄注云:“左道,若巫蛊及俗禁。”,可知巫蛊“左道”与“邪门”,已列入于周代的法制之中,乃变为严厉惩治之对象。[17]306-307
由此观之,于两周时期,随着中央王朝的逐渐确立,又基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原始时代的宗教、政治并存的局面,已发生变化,故制定各种措施,以防范危害社会的行为。[17]307
四、结语
巫者职司交通鬼神,其本身虽不具超乎自然的力量,但古人相信巫者可藉鬼神之力以成就诸多事。古代巫者其主要的活动类型,则可分为交通鬼神、医疗巫术、救灾巫术、生产巫术、求子生育、建筑巫术、丧葬巫术、祝诅放蛊、神明裁判等九项。
祝诅放蛊之事,因古人相信巫者能为祝诅放蛊之事,遂成为巫者从事之重要职事。巫者不仅能解除人之灾祸,尚且能以其术害人,学术术语称为“黑巫术”、“凶巫术”,于制敌、制人、作弄敌对者时,便施行此法。
古人对于祝诅放蛊的巫术十分注意,此事由商代甲骨卜辞的记录、先秦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考古学的报告等不难得知,古时巫者曾担任祝诅放蛊巫术的职责,则从事祝诅盟誓、诅咒巫术,以及放蛊毒人之术、治蛊之法等的巫术活动。
[1]许进雄. 古文谐声字根[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2]詹鄞鑫. 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许慎. 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上海书店编写组. 二十五史(全十二册)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许进雄. 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6]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全二册)[M]. 阮元,校刻. 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曹锦炎. 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郭沫若. 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9]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侯马盟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10]林志鹏. 殷代巫觋活动研究[D]. 台北:台湾大学中文所,2003.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J]. 文物,1983(3).
[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3]黄晖. 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全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14]徐富昌. 睡虎地秦简研究[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15]宋兆麟. 巫与巫术[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16]胡新生. 中国古代巫术[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17]邓启耀. 中国巫蛊考察[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贾建钢 校对:朱艳红)
① 若视盟誓载书的基本仪节,如《周礼·司盟》便有其记载,于“司盟:掌盟载之灋(法)。”之下,郑玄注云:“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周礼·秋官司寇》卷第36《司盟》第881页。
② 曹锦炎编《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春秋左氏传》第154-155页。此文亦可见于《春秋左传·襄公九年》之中,其云:“子驷、子展曰:‘……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洁)要盟,背之可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春秋左传》卷第30《襄公九年》第1943页。

④对于《诅楚文》写成的背景,杨宽在《战国史》书中曾提及,其云:“当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秦、楚初次大战前,秦王曾使宗祝在巫咸和大沈厥湫两个神前,举行这样咒诅楚王的祭礼,北宋出土的《诅楚文》石刻,就是当时宗祝奉命所作,把楚王咒诅得如同商纣一样的暴虐残忍,请天神加以惩罚,从而‘克剂楚师’。”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5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⑤ 除此《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的记载之外,晏子的此种多人诅咒具有相当巨大的作用的见解,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亦可见之,其云:“今自聊、摄以东,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众矣,百姓之咎怨诽谤,诅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诅,两人祝,虽善祝者不能胜也。”吴则虞编《晏子春秋集释》(上册)第一卷《内篇谏上·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第43-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⑥ 有关战场上施行的诅咒巫术,杨宽在《战国史》书中曾提及,其云:“对敌国君主咒诅的巫术:当时宋、秦等国流行在天神前咒诅敌国君主的巫术。他们雕刻或铸造敌国君主的人像,写上敌国君主的名字,一面在神前念着咒诅的言词,一面有人射击敌国君主的人像,如同过去彝族流行的风俗,在对敌战斗前,用草人写上敌人的名字,一面念咒语,一面射击草人。”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542页。
⑦曹锦炎编《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春秋左氏传》第148-150页。此文亦可见于《春秋左传·襄公九年》之中,其云:“将盟,……。公子騑趋进曰:‘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闲(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至)告。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春秋左传》卷第30《襄公九年》第1943页。
⑧ 有关巫者用诅咒法祓禳山川邪鬼作祟的事实,如《说苑·辨物》便有其记载,其云:“扁鹊曰:‘入言郑毉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难之曰:‘吾闻上古之为毉者曰:苗父。苗父之为毉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轝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鹊曰:‘不能。’”[前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第18《辨物》第471页。


⑪ 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第4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亦可参见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第641-642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⑫ [周]吕望撰《六韬》卷第一《文韬·上贤》,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子部三二·兵家类》,第726-15页。亦可见于曹胜高、安娜译注《六韬·鬼谷子》(重印本)《文韬·上贤》第36-3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B99
A
1673-2030(2017)04-0043-07
2015-08-15
赵容俊(1968—),男,韩国庆尚北道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专任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