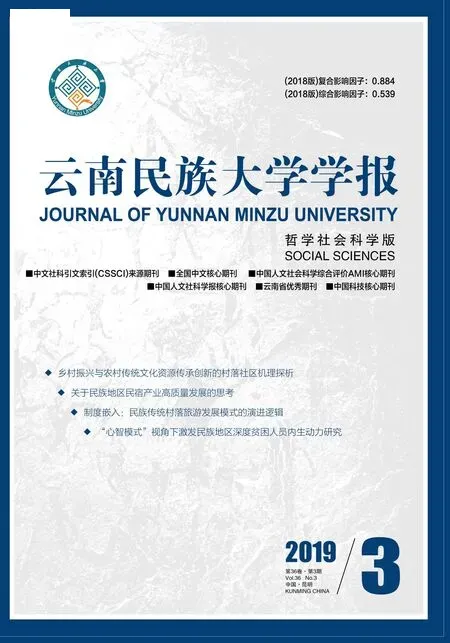地方行为与边疆治理: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研究
李良品
(长江师范学院 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涪陵408100)
盟誓作为我国一种朴素的社会规范形式,广泛存在于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社会之中。云南沿边土司自明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先后有五次大规模的盟誓活动。一是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大将王骥与麓川土司思禄的“麓川之盟”;二是雍正四年(1726)镇沅傣族土司与拉祜族反抗镇沅知府刘洪度而举行的“威远会盟”;三是雍正年间车里土司刀正彦联合茶山哈尼族反抗朝廷官吏敲诈勒索而举行的“茶山会盟”;四是1934年佤族土司联合佤山十七部落军民以及当地汉族、彝族、拉祜族等民族为抗击英国侵略军而举行的“班洪剽牛盟誓”;五是1951年原车里宣慰使司议事庭庭长召存信号召傣族、佤族、拉祜族等二十六民族举行的“民族团结盟誓”①陈斌,张跃:《云南少数民族盟誓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5页。。云南沿边土司是指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交界的原少数民族土司。这些沿边土司的盟誓活动虽然只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属于地方行为,但它体现了明代以降数百年间,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如果把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作为呈现和表达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行为的文化载体来解读,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文化载体中蕴含着各少数民族历史记忆、观念价值、宗教信仰等内容丰富的信息。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特殊的叙事方式,在实现公众性、建构性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从多维度践行了民族文化实践,构筑了民族文化空间。云南沿边土司作为地方性统治集团,他们出于自身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常有地方性行为的盟誓活动,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统一辖区内以及相邻统治集团民众的行动,促进国家对于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
一、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组织结构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活动的组织类型和构成要素形成了整个盟誓活动的组织结构。这个组织结构参与了盟誓的准备、发起、进程和仪式的献祭等过程。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社会组织结构是指包括氏族、家庭、团体、政府等在内的参与盟誓活动的所有群体,他们共同构成了土司盟誓的组织。
(一)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组织结构类型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组织结构类型是指土司盟誓组织的参与形式、内外环境、聚散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模式。②陈斌,张跃:《云南少数民族盟誓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从明清时期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主体的组织类型来看,它属于群体盟誓而非个体盟誓。
1.群体内部民众的共同盟誓。土司辖区内同一族群内部的村寨、宗族、家支有时因各自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出现矛盾、纷争、械斗甚至战争,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必须建立共同的礼仪秩序、和谐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盟誓。其形式就是共同议定规条,勒石碑盟誓。这类盟誓要么是建立土司宗族内部平等和谐的关系,要么是土司族群内部各村寨、各家支结成同盟关系以讨伐共同的敌人,大多由土司与族群内的各村寨、各宗族、各家支成员共同参与,反映群体内部民众共同的意志、愿望和利益需求,旨在加强群体内部民众的团结互助,这类盟誓具有强烈的权威性和强制的执行力。
2.不同土司群体之间的盟誓。据《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载,明正统十年(1445),兵部侍郎杨宁、侯琎筑腾冲城,征集今云南保山市、德宏州各土司助饷,南甸宣抚司刀乐硬遂与南甸宣抚司管源、干崖宣抚司刀怕便、干崖把文进管佐、陇川宣抚司多兴福、腾冲指挥使司管俊于同年三月十五日盟誓,其内容为:
以管、谢、刘、杨四姓从征有功,命同理司政,每姓给田二百箩……复以边境不靖,必需连防,遂约同三宣首长会于司属猛练寺后,歃血为盟,立誓词曰:盖闻连盟本义,颜真卿抱额吹血洒泪兴师,晋温峤勤王之略,况当离乱,誓言宜申。今属邻封,唇齿尤切,拨乱而返治,努力以同心,慨我各姓,自遭叛缅,或受其蹂躏,或经其夹持,莫不痛心疾首,共切誓仇,纠合同属。而城池未复,祸乱依然,惟恐结盟之生,没收涣散之心,爰聚同人,重申旧约之好,一司有警,各司赴援,近则御城以冲锋,远则行途而截敌,捍患分灾,扶危救困,不待告急之文,不争报酬之礼,闻风即至,退后在革除之科,争先受优劳之礼,从此连众志以成城,进可攻而退可守,依辅车以为固,修地利兼修人和,不但保卫疆宇之永安、带砺之铭,或克服城垣,稍展屏藩之职,刑牲歃血,贻誓神明,垂训子孙,永守勿替,有逾此盟,神天鉴察,所愿一体相连,浑如手足,千金不易,照若日月毫光,无畛域之分,互为犄角之势,庶奠苞桑于磐石,而挽乱世于升平也。①德宏州史志办公室:《德宏历史资料·土司山官卷》,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页。
这是不同土司群体在面对外敌入侵之时同心协力、扶危救困,以“保卫疆宇之永安”的共同盟誓。从明代到清末,在面对英国入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下,傣族土司不畏强暴,守望相助,谨遵盟誓,共同御敌,为保卫中缅边境的大片领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3.地方土司与明清中央王朝之间的盟誓。据《明史》载,明正统十四年(1449),“时王师逾孟养至孟那。孟养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余里,诸部皆震詟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骥还兵,其部众复拥任发少子思禄据孟养地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②[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20页。麓川土司思禄十分畏惧朝廷的大军,便听从了王骥的安排,表示遵守誓约。同时刻石立碑于江畔,使大明江山永固,民族团结融合。
无论是同一族群内部的村寨、宗族、家支,还是相邻而不同土司群体,抑或是地方土司与中央政府的盟誓,其起誓人大多是土司,其盟誓无不是以具有共同组织、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规约长期稳定地组合在一起,既体现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稳定的一面,也凸显了守望相助、社会现实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
(二)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组织构成要素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社会组织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盟主、祭师或巫师、盟员、规约,这四大要素的相互关系与联系构成了土司盟誓组织的基本结构。
1.盟主。从明清时期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相关史料看,无论是社会内部治理的盟誓,还是社会关系中的盟誓,任何一次隆重的盟誓都需要有召集人(即盟主)。盟主既是社会治理的管理者、内部事务的调停者,也是盟书内容的决定着、盟员利益的保护者,更是抵御外辱的领导者、违反誓约的讨伐者。盟主必须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殷实的经济实力。如云南南甸宣抚使之所以能多次以盟主身份约请周边土司盟誓,是因为该土司为“十司领袖”。
2.祭师或巫师。他们是土司盟誓仪式的主持者,在盟誓活动中担任重要角色。不同少数民族土司盟誓的主持人,其名称不尽一致,如壮族的宗教祭师叫“布麽”、拉祜族和佤族巫师叫“魔巴”、哈尼族的祭师叫“摩批”、纳西族的宗教祭师叫“东巴”、普米族的巫师称“丁巴” “韩规”或“师毕”、傈僳族的宗教祭师称为“尼扒” “卓巴”③陈斌,张跃:《云南少数民族盟誓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15页。。这些称谓各异的宗教祭师或巫师,由于他们能够自由出入于人、神、鬼之间,因此成为各民族表达诉求、传达神谕的重要媒介,自然就具有代表神灵监督人类行为、主持社会公议的社会责任。一般而言,凡是具备主持盟誓的人大多是具有能力主持村落重大公祭仪式的宗教祭师或巫师,他们在社会活动或行业内都具有广泛的权威,因此,其角色决定了主持盟誓的合法性。
3.盟员。盟员是指参与土司盟誓活动的成员。这种成员在联盟里可互称盟友,明清中央王朝与地方土司政权之间、不同土司群体之间、群体内部民众之间,只要是组成联盟,都是盟员,他们与盟誓召集人之间的关系是盟员与盟主的关系,如前面提到的南甸宣抚司管源、干崖宣抚司刀怕便、干崖把文进管佐、陇川宣抚司多兴福、腾冲指挥使司管俊与南甸宣抚司刀乐硬之间就属于盟员与盟主的关系。盟员之间以及盟员与盟主之间,相互之间的政治认同是基础,这不仅是盟员之间、盟员与盟主之间对政治体系的一种信任,更是盟誓正当性的基础。如果没有政治信任的基础,就无法将广泛的社会成员组织和凝聚在一起。
4.誓约。誓约就是盟誓时盟员之间订立的誓约或条约。“誓约”一词,属于宗教词汇。在土司盟誓中的誓约,多强调众神对盟员之间约定条款的坚守。在一般情况下,誓约往往被称为“规约”。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规约就是土司结盟过程中共同约定的规范条款。如明正统十一年(1446),南甸宣抚司刀乐硬会同三宣与管姓,签订同心协办誓约,其中就有“后世子孙,当知平起平落,勿相恃势,忠心辅保,耿耿在心,人人自奋,内外竭力奉公办事,呼吸相通……内治增修而外侮足御,永保疆土勿替也”等内容。①德宏州史志办公室:《德宏历史资料·土司山官卷》,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页。可见,南甸宣抚司与另外几个土司订立该誓约的目的在于限制各土司只能固守自己的领地,不能企图侵占其它土司的领地,并协同维护地区稳定,为边疆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活动的组织类型和构成要素无疑是以云南边疆地区各土司的地方行为作为联系的纽带、以“歃血为盟”的宗教形式为基础而实现的边疆地区社会关系整合以及国家对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有效治理。从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对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治理,就是通过土司家族内部治理、土司周边关系维系、边疆土司与国家关系构建等形式,巧妙利用云南沿边土司的威望以及通过土司盟誓活动的形式,使云南沿边土司各群体、参与土司盟誓的各方在确认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具体的权利与履行的义务的基础上,以实现云南沿边土司的社会整合从而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
二、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仪式程序
在常见的土司誓约中,一般要将双方或多方各自承担的义务、责任、承诺以及违背承诺应接受的惩罚等内容书写清楚。在信奉宗教的少数民族中,由于人们对神灵的崇拜与敬畏,土司盟誓一般以天神、地神等众神为证,如果双方或多方违背誓言,就是对众神的亵渎。因此,土司盟誓必须举行十分隆重的仪式,讲究一定的程序。虽然有学者将古代隆重的盟誓仪式分为“约会”“登坛”“发言”“歃血”“载书”“享宴与归饩”和“盟后朝聘”等七个具体程序,②刘伯骥:《春秋会盟政治》(内部资料),北京: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2年印刷,第248-266页。但笔者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其盟誓的仪式程序也不尽一致,土司盟誓虽然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但在具体祭仪过程中,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仪式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土司盟誓仪式所要表达的真正信息以及背后所隐含着的宗教和政治权威,而且可以揭示出蕴含着权威的土司盟誓在维持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稳定所发挥的作用。
(一)仪式准备
明清及民国时期,由于特定时期、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各地土司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周边土司的需要,具有号召力的在面对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往往发起族群内和族群外结盟立誓的提议,并经过空间准备和誓约准备,进入到仪式的履行过程。
1.结盟倡议。一般情况下,土司盟誓的主盟方需发出盟誓提议,向结盟方说明本次盟誓的原由,要求对方或多方加入会盟,并商定会盟时间、地点、誓约内容与盟誓程序。如《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载:正统十年(1445),兵部侍郎杨宁、侯琎筑腾冲城,征各司助饷。公(南甸宣抚司刀乐硬)回南甸宣抚司后,因为管、谢、刘、杨四姓从征有功,命同理南甸宣抚司相关政务,并“以边境不靖,必需连防,遂约同三宣首长会于司属猛练寺后”。这就将南甸宣抚司刀氏土司与管、谢、刘、杨四姓结盟倡议的相关情况作了简要交代。一般来讲,土司结盟倡议的发起人大多是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土司。
2.空间准备。所谓空间,也就是举行土司盟誓仪式的地点。无论那种类型的土司盟誓,对参与盟誓活动的任何一方来说,均是重大活动,因此,仪式场所都必须谨慎而认真地选择。因为土司盟誓举行仪式场所的选择,是虔诚守信的反映。一般来说,土司举行盟誓仪式的地方往往选择远离村庄的灌木丛、两个部落的交界地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专门的祭祀场所,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神灵降临、人神交通最容易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公共空间,各部落、各民族自由往来的地方。如南甸宣抚司刀乐硬与南甸宣抚司等五土司盟誓地点为南甸宣抚司所属的“猛练寺后”;而1951年普洱26个民族盟誓地点是云南普洱当时的政治中心——普洱红场。总之,土司盟誓场所的选择彰显了盟誓仪式的神圣性和公共性的特点。
3.环境布置。从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活动可见,其保证力量无疑是宗教信仰,参加土司结盟活动的双方或多方必须有一个共同认同的信仰对象。通过对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分析,当盟誓双方或多方确定盟誓地点之后,盟誓发起方就要举行筑誓坛、竖木桩、挂经幡盟誓仪式环境布置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堆土“筑坛”,这不仅是土司盟誓祭场的特征,而是最容易接近神灵之处所。从土司盟誓“筑坛”中能体会到众多神灵在盟誓中的重要位置。
4.订立誓约。土司盟誓是通过参与盟誓双方或多方承诺对某些行为规范的严格遵守,从而构建双方或多方的关系共同体,而双方或多方所承诺的行为规范就是土司盟誓中的誓约。土司盟誓以前,由参与盟誓的双方或多方共同商定誓约内容。如明正统十年(1445),南甸宣抚司刀乐硬与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干崖把文进、陇川宣抚司、腾冲指挥使司共同议定的誓约六条中有“议义定盟之后,击贼上报国恩,下安民社,不准私通降贼,如有背盟私通贼匪及暗降者,消息泄露,四姓合共征伐,并奏闻;各司设有警报,互相救援,以先到为首功,随后为次功,功之大小,众议酬劳,轻则酬以物,重则酬以村寨,不容偏袒”①德宏州史志办公室:《德宏历史资料·土司山官卷》,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361页。等内容。
土司盟誓各方在盟誓前订立的誓约,既是土司盟誓各方的依据,也是对盟誓各方加以约束的规范,由于誓约规条关涉参与盟誓的双方或多方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参与盟誓的各方在盟誓前慎重商讨。土司盟誓前议定的誓约内容既有参与盟誓的各方的行为规范,也有违背誓约受到惩罚的内容,还有请求众神监察宣誓各方今后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誓,就降临灾难以示惩罚。
(二)仪式进程
盟誓的本质是被埋藏在程序的夹缝里,只有通过对仪式进程各重要环节的剖析,方能洞悉土司盟誓仪式的本质所在。云南沿边土司盟誓要想达到有效治理边疆、维护边疆稳定的目的,就必须要确立盟誓仪式在参与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成员心目中的权威性人物,这个最具权威性人物就是神灵,并将神灵贯穿于盟誓仪式进程的各个环节,以实现其最终目标。
1.诏告神灵。神灵是各类神的总称。在古代人看来,神灵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具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凡能力。云南沿边各族民众认为,无论是双方或多方盟誓,不论多远,只要真诚邀请神灵,并告知双方或多方盟誓的内容,天地神、四方神以及其他众多神灵就一定能知晓,并会监督盟誓双方或多方有关内容的实施,对违背誓约一方或多方进行惩罚,对诚实守信者予以褒奖。如傣族土司之间的盟誓,必须邀请阿远多、盆多、丢瓦尚哈约等社神,天神帕雅英、地神帕雅捧、联络神帕雅荣玛拉以及32位丢瓦拉神等全体众神灵,并诚挚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土司盟誓集会,其主要职责是为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作证。②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308页。
2.集体宣誓。所谓集体宣誓,就是参与盟誓的各方面对神灵宣读誓约,通过口头语言的形式向神灵陈述自己的诺言及表达遵守诺言的决心,并进行自我诅咒,表明自己愿意遵守誓约、接受规约。③陈斌,张跃:《云南少数民族盟誓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土司宣誓不仅是盟誓活动的核心程序,而且更重要的是参与盟誓土司对盟誓公信力和强制性的认可。从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仪式宣誓的内容看,大多包括盟誓缘起、誓约要求、违盟恶果三个部分。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车里宣慰使司署召片领(即车里宣慰使)在众多下属土司面前由主持人简介盟誓缘起,即有众官员百姓的首领晋升为不同等级的土司,坐阵各勐,管理该勐全体官员百姓,现在前来在三宝面前饮咒水宣誓。紧接着,车里宣慰使司署召片领宣读誓约,提出三条具体要求:一是本地百姓自觉接受召片领及其下属土司的管理,“接任某某勐的召勐,某某地方的帷雅职官后,不要贪财如命,对千勐百姓(指不同勐的百姓)要同等爱护,旧制不能丢,旧礼不能毁,涉及差发银、贡赋、钱粮款、门户款等各种旧的规定,要与地方官员同心协力办理”①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二是对“从外地来投奔的人,不论是那一个民族,不论是百姓,还是有名望的官员,只要他们真心归附,自愿定居在某某勐某某村,都应该按照地方古规,批准他们定居,许他们与当地居民同等出负担”。三是外地来的人“到我们管辖下的领地内定居,必须写保证书两份,双方(指定居者与当地头人)各持一份;定居三年后,必须承担负担。这个规定是傣族自古就承袭下来的规矩,不能用其它任何地方的规矩来代替”。最后,车里宣慰使庄严宣读违盟恶果: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召勐某某人、帕雅某某人,若不忠于誓言,存心不良,挥动列戈,图谋反叛,抢夺我松榴帕兵召的领地,霸占我的农奴百姓,只要“帕翁”我一旦发现,就让他像芭蕉花一样日渐消失;让也有女儿难产送命,有儿子死于非命,让他遭受走水路被龙拉,走陆地被虎咬蛇毒,遭刀枪砍杀,断肠吐血致死,让他害麻疯等五种灾难而死于非命,死后下地狱,日夜啼哭。②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页。
由此可见,盟誓缘起、誓约要求、违盟恶果三个部分规定得十分清楚,多方的责权利明明白白。土司盟誓均是在众多神灵的监督之下进行,其中有宣读誓约、交换信物等环节,出于对众神的信仰,企图借助众神的权威,使土司参盟的双方或多方在内心深处意识到盟誓仪式的严肃性和对违背盟约后将要承受的惩罚产生的畏惧心理,从而达到对土司参盟的双方或多方起到行为规范和自我约束的作用。③陈斌,张跃:《云南少数民族盟誓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3.置放信物。土司盟誓之后誓约的物化,无外乎有两种形式:一是存券,也就是将誓约藏诸玉府、寺院库藏之中,或置于盟誓文龛之内;二是刻于石碑或木牌之上。如果说盟誓誓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质内容意义,那么,盟誓信物就具有非常特殊的外在符号意义。土司盟誓仪式作为国家治理边疆地区的地方性行为与活动,它除了表达性之外,更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它尤其是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土司盟誓仪式本身的象征含义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司盟誓的过程权威化,土司盟誓仪式既是权威表现的载体,也是权威确立与展示的平台。在这个载体与平台上,无论是记载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誓约内容石碑,还是木牌,虽然它仅仅是记载土司盟誓内容的一个实物而已,但它却是象征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确立诚信和保证诚信的一种物质载体。因此,参与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高度重视置信物这一环节。在云南沿边土司盟誓过程中,人们把置信物看作是最关键的部分。从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仪式看,在盟誓仪式中,土司盟誓各方除了口头宣誓外,他们往往把誓约内容记录在石碑或木牌等物品上,做成盟书,然后参盟各方面向神灵,宣读“载书”,告誓神明,这是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定制。大凡土司意欲取得霸主地位、寻求军事同盟、实现睦邻友好、调解内外冲突等,均可以记录于盟书之中予以实现。石碑或木刻等信物的形成后,只有通过“杀牲取血” “宣读载书” “昭告神明”“歃血”等一系列仪式程序完成之后才能发生效力。当土司盟誓所形成的置信物具有一般法律形式后,它就具有规范土司盟誓各方行为的作用。
(三)仪式结束
云南沿边土司在盟誓活动中用猪、狗、牛、羊等畜禽以献祭众神,除了具有人与神沟通的作用之外,还与人们长期形成的“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膜拜心理密切相关。在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仪式中,“杀牲歃血”既是盟誓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意味着盟誓仪式即将结束。如1951年元旦普洱县城红场隆重举行的“民族团结盟誓”仪式,同样也举行了剽牛、歃血、签字等仪式。④陈斌,张跃:《云南少数民族盟誓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页。代表盟誓仪式结束的“杀牲歃血”,彰显土司盟誓多样化的功能,其具体环节有两个方面。
1.“杀牲”。杀牲是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祭仪的前奏。宰杀牛、羊、猪的最终目的是对众神表示敬意并敬献给众多神灵的祭品。从原始信仰的角度看,宰杀牛、羊、猪等畜禽主要有供牲和取血两个作用。它期待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遵守盟约、自我诅咒,不致于背盟违誓。在云南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中, “杀牲”这个环节,往往用“剽牛”代替。按照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盟誓的规矩,歃血结盟能否成功,先要看剽牛的结果如何而定。剽牛的程序是,剽牛者在鋩锣声中头扎红布手持剽枪进场,并按剽牛习俗,将左手放在额头上,庄严地面对西方,念完咒语之后,双手紧握剽枪,举过头顶,用力将剽枪刺进水牛前肋中,经过三次准确的剽击,水牛终于倒地。见剽枪刺中水牛心脏,牛倒向左方,牛头朝向南方,剽口朝上,这就是天意保佑盟誓成功。①张泽洪:《论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宗教文化内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歃血”。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仪式中的“歃血”,或将畜禽之血涂于盟誓土司的口唇边,或盟誓土司双方或多方同喝咒水或“同喝鸡血酒”,这些均表示参与者信守誓言的诚意。如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月初一,车里召片领刀太康逝世,景洪地方不安定,亲缅势力召孟玛哈康朗父子与亲清王朝的刀正综之间的家族内部争位斗争,以西双版纳众头目的首领召景哈(议事庭庭长)以及众召庄等作出决策,尊重刀太康遗言,由刀正综继承宣慰使,于是举行盟誓,其中誓约有“共同集会,团结一致,坚如磐石,在三宝面前饮咒水,盟誓,祈求神灵作证”②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351页。等内容。由此可见,由于云南沿边少数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血液对于生命存在的巨大作用,所以,人们对血液产生了敬畏与崇拜。土司盟誓祭仪里的杀牲取血以及喝血酒,不仅在盟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具有与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加强关系的整合作用。
总之,土司盟誓仪式不仅可以充当形式上的公证角色,而且还可以形成地方性法律的行为约束力。土司盟誓往往需要借助各种仪式,在加深土司盟誓双方或多方对自身责任、权利和义务认识的基础上,构建起参与盟誓双方或多方的紧密联系。事实上,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仪式就是以地方行为为纽带、以宗教情感为基础而实现的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社会关系整合。从历史上看,国家对云南边疆地区土司的治理与管控,就是通过土司家族内部、土司与周边土司、土司与朝廷流官等多方面的纵横关系,充分利用土司盟誓仪式,使各群体将宗教感情外在于行、内化于心,从而确认土司盟誓参与的双方或多方各自权利与责任,进而促进边疆社会得以整合,边疆地区由此稳定。
三、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活动的边疆治理功能
众所周知,历代中央政府在土司制度实施过程中,各地土司首先归附中央王朝,认同中央政府的合法统治地位;中央政府在各地土司归附和认同后就颁给诰敕、印信、号纸、冠带、符牌(仅限于明代云南边疆地区)等信物,使之“世守其地,世管其民”。中央政府和各地土司通过“相互赋权”,达到各得其所的目的。尤其是云南沿边土司,除了要履行与内地土司相同的职责外,他们还肩负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传播中原文化的职责。换言之,云南沿边土司作为朝廷命官还担负着代行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职责。这正如车里宣慰使与西双版纳其他土司盟誓中所言:“不论内外局势有何变动,都要团结一致,保卫边疆,严守天朝疆土,遵守天(即清代中央政府)、缅(缅甸政府)双方的友好誓约。”③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页。他们在云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往往是利用宗教文化凝聚本族群和相邻各族群,从而实现巩固中央政府对云南边疆地区的控制。云南沿边土司在遇到祭祀、复仇、征战、联盟、议和、婚姻等社会活动中皆要举行盟誓。这就使盟誓活动成为一种地方性宗教行为。这种行为依赖众神之力对参与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予以保障,它以毁灭性的诅咒防范参与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联盟关系的破裂,又以美好的期望鼓励参与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遵守盟誓以获幸福。④田兆元,龙敏:《中国盟誓中杀牲歃血行为的动机探讨》,《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在能见到的誓约中不乏“要团结一致,保卫边疆,严守天朝疆土”⑤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等表达多民族团结、共同治理边疆的语句,说明云南沿边土司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少数民族的地方行为——盟誓活动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地方社会需求以及加强边疆治理的需要,以最终达到治理边疆的目的。
(一)族群整合功能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活动在整个族群社会内部治理和族群外部社会关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涂尔干认为:“宗教仪典的首要作用就是使个体聚集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之间更加亲密。”①[法]爱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蕖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活动的整合功能在于强化族群社会内部成员和族群外部社会成员的个体对参与盟誓的双方或多方族群社会的归附关系。如车里宣慰使在与西双版纳的各召庄、道帕雅等众官共同饮咒水宣誓时的誓约中说:
宣慰使管辖下的西双版纳遭破灭,景线、景栋、勐勇、孟连也不能立足,这些勐犹如同一血脉、同一心肝脏的一个人的整体。这些勐的召庄、道帕雅,应该爱戴百姓,同生死,共患难。西双版纳的各召庄、道帕雅,应该团结一致,心心协力,信守诺言,立下此誓约,署其名,在三宝面前饮咒水宣誓。②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355页。
车里宣慰使与西双版纳参与盟誓的各族群社会成员就是通过盟誓活动强化了个族群中的个体对参与盟誓集体一种的归附感,这无形之中就强化了表现为“宗教力”的集体力量,也就是通过盟誓活动将十分微小的个体力量整合成强大的集体力量。③牛绿花:《试论藏族盟誓仪式的动机和功能》,《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特别是在土司盟誓中杀牲歃血更具有族群整合功能。因为盟誓活动中的杀牲是为了警示参与盟誓的所有人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凡是背盟者,将如所宰杀牛、羊、猪等畜禽一样,遭杀身之祸。这就告诉所有参与盟誓者,庄严的承诺不可违背,神圣的盟誓不可背叛,让土司盟誓在众多神灵那里得到保障,盟誓共同体的所有成员能够获得幸福。④田兆元,龙敏:《中国盟誓中杀牲歃血行为的动机探讨》,《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因此,透过盟誓活动中杀牲歃血仪式,云南沿边土司的族群整合、社会凝聚功能就会得到最直接的保障。
(二)社会制约功能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活动的本质在于双方或多方受到制衡,实现互相制约的目的。参与盟誓的双方或多方的制约力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创建契约关系。这就要求参与土司盟誓的双方或多方构建起“命运共同体”,若盟誓前是不信任、敌对的关系,通过举行盟誓仪式建立起特殊的契约关系,并在盟誓仪式后保持并实施新创建的特殊契约关系。如明正统十年(1445),南甸宣抚司刀乐硬与其他五个土司议定的誓约其中两条就具备契约规定:
一、连结之后,各司祸福与共,休戚相关,不得各夹私见,趋利避害,不外侮同御,内事相安,倘有谋叛、反逆、藐法、欺官,勿论族、目、军、民,同心缉挈诛殛,不准收留坐视殉情。
一、自寻盟之后,各宜修和睦邻、息争讼斗殴,即有些微小怨,一切婚姻、田土,同商筹办,不得擅启兵端,败盟构衅,倘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众议处罚。⑤德宏州史志办公室:《德宏历史资料·土司山官卷》,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361页。
上述条款不仅规定各参与盟誓之土司应该怎么做,而且对违背该规定的也制定了处置的具体举措。这种具有契约精神的条款不会随着土司盟誓仪式的结束而成为一纸空文,反而会随着土司盟誓仪式的结束而进入具体实施阶段。⑥牛绿花:《试论藏族盟誓仪式的动机和功能》,《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第二,坚守道德信义。云南沿边土司的盟誓仪式都是在众神监督下举行,它能真正起到制约作用的最关键内容盟誓中的“自我诅咒”。吕静认为:“因为出于对人类的不信任,仅仅停留在契约内容的表述,很难达到制约当事者行为这一盟誓的最终目的。所以在盟辞的最后追加了‘自我诅咒’来强调宣誓者遵守誓言的决心”⑦吕静:《中国古代盟誓功能性原理的考察——以盟誓祭仪仪式的讨论为中心》,《史林》2006年第1期。。所以,对于参盟土司各方在盟誓仪式中的宣誓,所有语言中最有分量、最具杀伤力的莫过于对背盟者的诅咒。如如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月,新世袭车里宣慰使的刀正综,与其他土司盟誓时对背盟者的诅咒内容为:“如果西双版纳的那一个勐,不遵守誓约,蓄意造反,那他有儿不成才,有孙不成长,有男让别人杀害,有女死于非命;经商遭人杀,首级落入水,下水被龙拉,行路被虎咬蛇毒,让他死于非命,让他变麻疯、变疯子,死后下地狱。”⑧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355页。这些诅咒内容能够促使参盟者坚守道德信义,不做违约之事。
(三)民族团结功能
云南沿边土司凡遇大事都要结盟立誓,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盟誓的传统,因此,歃血盟誓能够为云南边疆各民族、各族群的人所接受。它的内在机理在于各民族、各族群的人普遍认为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土司盟誓的内容在冥冥之中能够受到神灵的监督,盟誓仪式象征天地神灵之意不可违背。①张泽洪:《论民族团结誓词碑的宗教文化内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因此,带有十分浓厚宗教色彩的盟誓活动具有团结各族民众的功能。南甸宣抚司盟誓规条中有 “勿论族、目、军、民,同心缉挈诛殛”“惟望金石同心,终始不二”②德宏州史志办公室:《德宏历史资料·土司山官卷》,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361页。的句子;车里宣慰使在誓约中更是不乏“要与地方官员同心协力办理”“要团结一致,保卫边疆” “共同订立友好誓约,扭做一股绳,团结一致对敌” “应该团结一致,心心协力”③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310,350-35页。等语句;尤其是云南普洱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碑文更加明确,表态坚决将民族团结、共同治理边疆的意愿表达得淋漓尽致。
四、结语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不仅是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朴素的社会规范形式,而且是特色鲜明的地方行为,彰显了明清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对云南边疆的治理。
第一,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中的边疆治理成分体现得十分明显。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基本逻辑体现在族群平等、民族团结和国家主导三个方面,它既有一个体系完整的组织结构,又有一套形式多样的仪式程序,还有不同民族对宗教的信仰。正是基于此,国家才能够通过云南不同民族土司的地方行为——盟誓仪式,以实现对云南边疆地区有效治理的目标。
第二,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中边疆治理呈现出逐渐加强的态势。从明代“麓川之盟”“南甸宣抚司盟誓”到清代“车里宣慰使盟誓” “威远会盟”“茶山会盟”,再到民国时期的“班洪剽牛盟誓”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 “民族团结盟誓”,虽然每次盟誓仍然都带有十分浓厚宗教色彩,但国家政权介入土司盟誓的成分越来越多,这充分表明国家治理边疆的能力越来越强,特别是1951年“民族团结盟誓”,更是以土司与多民族盟誓的方式,谱写了民族团结誓约,铸就了民族团结丰碑。
第三,云南沿边土司盟誓中国家对边疆治理始终占主导地位。明清以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云南沿边土司虽然有族群内部治理方面的盟誓、土司与土司之间的盟誓以及土司与非土司群体的盟誓,但在不同类型的盟誓中国家对边疆治理核心要素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只有中华民族长期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才能形成边疆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和谐、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