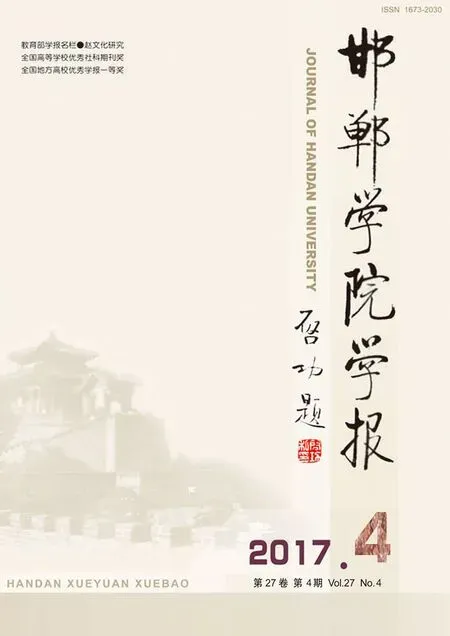日本侵华时期蒙疆沦陷区的学校教科书研究
吴洪成,蔡晓莉,李阳阳
日本侵华时期蒙疆沦陷区的学校教科书研究
吴洪成,蔡晓莉,李阳阳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抗战时期,日军为实现对蒙疆地区奴化教育需要,积极推行“防共亲日”、民族协和、“分而治之”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设置教科书编审机构,肆意删除、篡改教科书内容,编纂奴化教育所需的学校教科书,使学校教科书受到严重的扭曲,从而为毒害青少年学生的精神,实现殖民统治服务。
日本侵华;蒙疆伪政权;奴化教育;学校教科书;学校课程
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的边疆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行动中的重要棋子,蒙疆地区亦不列外。“蒙疆”是日本在侵华时期炮制出来的专有名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东北三省全境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完全划入日本殖民地版图后,日军为迅速实现“全面亡华”和“防共、反共”的目的,先后分别建立察南、晋北与蒙古三个自治政府。1939年9月,日军为发挥“防共”特区的作用,又将三个自治伪政权合并为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扶持下的建立起来的蒙疆伪政权极为重视奴化教育的推行,因而,在制定奴化教育方针政策,并建构起奴化教育管理体系的同时,又为各级各类的学校设置课程,编定教材,实施奴化教育的微观、具体而实质性的操作。依据教学论的原理,课程与教材在教学活动中是相互联系的,又有各自独立性的两个教学要素,而教材在教育内容的包容性上比教科书更为泛化的概念,无疑教科书是教材的精髓或核心。本文主要在分析日本侵华时期蒙疆沦陷区的课程编制基础上,探讨学校教科书的相关问题。
一、蒙疆沦陷区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学校课程
蒙疆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是受日本侵略者支配,在蒙疆伪政权的设计和推行中实施的,伪政权所辖的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并控制其中的相关因素与环节,课程的编制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它又直接影响学校教科书的编审和使用。
1936年5月,在当时的察哈尔盟化德县策划成立“蒙古军政府”,随后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绥远省大部分地区。1937年10月,在当时的绥远省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将蒙古军政府改组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云王(云端旺楚克)任伪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副主席。由于云王称病,德王纵揽政权一切事物。通过了伪“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以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市、包头市为统治区域”;“以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纲领;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定都于归绥市。[1]83该伪政府下设政务院,德王兼任院长。并于同年11月在张家口由德王为主成立统辖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撤销上述三个政权,并将“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至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寿终正寝,同时以德王为首的内蒙古分裂势力的“蒙古帝国”梦也宣告破灭。在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基础上于1940年正式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确定以张家口为“首都”,用成吉思汗元年号(简称“成纪”),并特地制定从上而下横条黄、蓝、白、赤四色七条的伪政府旗帜。1941年8月又改称伪蒙古自治邦。日本帝国主义严格控制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其实质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随着合并后的伪政权的建立,其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蒙疆沦陷区奴化教育由伪政权所辖各级教育行政机构负责,形成了一个殖民教育的体系。伪政府内部主管机构先后有总务部教育处、民政部教育科,盟伪教育厅,民政厅文教科,旗县有文教股。1941年伪蒙疆政府机构改革,设立兴蒙委员会,教育上也职权分开,蒙古族的教育由伪兴蒙委员会教育处掌管,汉族和回族的教育由伪内政部文教科掌管。实际上,蒙疆的教育完全由日本人控制,不仅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日本人顾问、参与官拥有决策权,就连各个学校的日本人校长、副校长、甚至普通教师都握有实权。如日本人直接掌管的总务部,就对其直属的蒙疆学院拥有很大的管辖权力。1939年9月1日发布的《蒙疆学院官制》规定:“第十四条,蒙疆学院之编制、教育科目及其他必要事项,通过总务部部长经政务院长认可后由院长定之。第十五条,蒙疆学院之分科规程,通过总务部长经政务院长认可后,由院长定之。”[2]193可见,蒙疆地区的教育管理权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丧失了蒙疆地区的教育主权。
(一)蒙疆沦陷区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建立之初,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第三条中就明确宣示:“以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纲领。这里的所谓的“民族协和”,除了其浅层所表示的蒙疆地区蒙、汉、回诸民族之间的“协和”外,还有其深层次的与日本“协和”的含义。1939年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教育纲领》指出:
第一,方针:基于蒙疆政权创建宗旨,发扬民族协和精神。和东洋道义之精华,陶冶德性,授以实际技能,养成坚实人物。第二,要领:根绝共产、抗日思想宏扬东方精神;着重劳作教育振作勤劳风气;重点置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着眼实业教育,高等教育将来伺机建立所需设施并施行之;普及日语;奖励体育,涵养健全之精神;指导训练一般青少年,振作朴实刚健风气;妇女教育着眼于培养妇德和实务性训练;学校以观公立为原则,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使之成为教化之中心;教育与实际方法适应民情和地方使态;教师的培养和鉴定由政府行之。[1]108
由此可知,任何政权教育政策的制定,都是该政权大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教育政策的实施,则是该政权性质的外在而具体的反应。“防共”、“反共”、“协和”日本并最终将蒙疆地区纳入日本“东亚新秩序”之中,其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以实现日寇分裂并占领蒙疆地区的根本目的为其指导原则,因此,教育政策也就具有明显的“防共”、“反共”特征和殖民地化的特征。
而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伪蒙疆政权,其实质也不过是日本实现“全面亡华”和“防共”、“反共”的工具而已。日本通过这一政权,在蒙疆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教育方针,即日本侵略者对蒙、汉、回采取不同的奴化政策:
教育方针是:“基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的宗旨,发扬防共、民族协和东洋道义的精华,陶冶德行,传授实际知识技能,培养有用的人才”。实施要领是:“拒绝共产主义、抗日思想,确认东亚民族团结的必要性。”具体指导方针如下:其对蒙族之方针有四:一、彻底实施产业实务教育;二、彻底推行体育、卫生、及宗教教育;三、日本语及其文化之彻底吸收;四、常识之养成及生活之改善。其对汉族之方针有三:一、彻底实施日本教育之精神;二、日满支协同体之精神培植;三、彻底恢复礼数并施产业教育之训练。其对回族之方针有二:一、除前述外,彻底实施道德教育;二、树立亲日思想,逐渐陶冶于日本教育之训练。[1]117
对蒙古人民,责其“彻底吸收日本语及其文化”;对汉族人民,“彻底实施日本教育及其精神;配制日、满、支、同一体之基本精神培植;彻底恢复礼教并实施产业教育之训练”;对回族人民,责其“树立亲日思想,逐渐陶冶于日本之训练”。日本侵略者在蒙疆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教育方针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蒙疆人民成为日本的附庸。这一教育方针,决定了亲日、反共、民族协和的奴化教育和实务教育的殖民化教育成为以后蒙疆教育的主题,而蒙疆沦陷区的课程设置与教科书编写及审定也是为此目的服务的。
(二)蒙疆沦陷区学校课程设置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之初,伪总务部教育处长陶布新曾主持召开过蒙古教育会议,讨论教育宗旨和学制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盟的伪文教科长、厚和市和包头市的文教股长、蒙古学院的教导主任和顾问,还有蒙古文化馆的代表。因为提交会议讨论的草案是参照原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学制制定的,这显然与蒙疆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民族协和”、“防共亲日”的教育宗旨和“奴化”、“分化”教育政策有所不符,所以遭到伪教育处日本顾问岸川兼辅等人的强烈反对,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当蒙古学院教务主任那苏图提出学生应当学习英文时,更惹起日本人的反对,因而学制暂时没有确定。[3]513
1939年9月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由主持教育的日本人在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制定的《教育纲领》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学制纲要》,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新学制规定,蒙疆沦陷区的教育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两个阶段,还有特殊教育及留学生教育、官吏培养教育等几个门类。初等教育分为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两种。小学学习科目为修身、国语、日语、算术、自然作业、体育、音乐、图画、实务、地理等11个科目,使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编纂的教科书。
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女子中学、实业学校及实务学校。中学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种。1939年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曾制定公布了《公立中等学校官制》,1940年5月又修正公布了《官立中等学校官制》,规定各种中等学校设校长、副校长、教谕(一般学校)、主事(设有附属国民学校及高级国民学校的师范学校)、教导、书记等职员。官立中等学校归民政部部长管理,具体管理职责则由伪民政部部长委托盟长及政厅长官负责。[2]196普通中等学校学习科目为国民道德、国语、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音乐、体育、作业工11科。每周授课时间36小时,日本语授课7小时以上。使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编纂和检定的教科书;女子中学入学资格、修业年限与男子中学无异,学习科目中加授女子所必要的家事、实业、裁缝、手艺等;师范学校则以培养初等教育所需之师资为目的,其学习年限、入学资格等与普通学校没有多大差别;实业学校及实务学校则以接受实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养成勤劳的习惯为目的,入学资格与普通中学相同,实业学校学习年限为四年,实务学校为2至3年。[4]
蒙疆沦陷区的学制完全适应日本奴化政策的需要,将“亲日”、“防共”、“反共”的原则精神贯穿到学校教育中,高等教育是为培养各级傀儡官吏和高级奴才服务的,如在蒙疆学院中“让学生认识本地区历史、地理上的特殊性,整备防共第一的总动员体制”,并认定“共产主义思想是产生抗日思想及运动的温床”,“不仅是蒙疆政权的课题,而且是世界性的课题”。[5]322把如何克服这一思想当成学校教学任务的中心任务。总括上述蒙疆沦陷区学校教学课程设置有如下特点:
1. 日语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
从表面上看,日伪在蒙疆沦陷区开设的中小学均设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修身、音乐、体育、美术、劳作等普通课程,但在课时安排上和实际教学中却把日语放到主要位置,日语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如1938年,巴彦塔拉盟制定的教育计划,在促进各县小学开学、开设师范学校、开设教员讲习所和开设盟立蒙旗青年学校各项计划中,均有日本语教育的内容。[6]639-640并且在1940年1月,伪蒙疆政府民政部教育科规定,日本语的授课时数,小学每周为6课时,中学每周为7课时以上。1943年2月,伪蒙疆政府内政部发布训令第50号《视学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指导规程》,其中第十七条规定,视学的任务包括调查“日语之普及情况”。[7]16蒙疆教育会也把普及日本语教育当作该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要求所有学校必须开设日本语。日本语授课时间之长,甚至超过汉语、蒙语,连日常用语、体操口令都使用日语。
兴和县实验小学的课程设置包括汉语、日语、修身、自然、算术、图画、体操、音乐等。此学校从一年级就进行日语学习,每天至少一节课,甚至竟把日语列为“国语”之一。另外,校长到县公署请示汇报工作、领取薪水等,都要用日语向日籍顾问、参事官问好。托克托县第一完全小学,1941年后“取消了历史、地理、公民等科,增加了日语”。在包头的铁路职工子弟学校——扶轮学校,学生问候教师、进出办公室喊报告都要使用日语。[8]
中学的日本语教育比小学更甚。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的日语课,授课时数由原先每周的6节最多增加到12节,此外还要求课外加授。在日本分化教育的政策方针下,从事蒙古族教育的学校如蒙古学院、厚和蒙古中学、包头蒙古中学等,禁止学习汉语,除蒙文、日语课外,即使一般的中学课程,也要求蒙古老师上课用蒙语讲,日本老师上课用日语讲。对此,蒙古学院的学生指出:“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有益无害的,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下,专设日文课和军训、做操用日语口令等,赤裸裸的展示了伪蒙疆政府无耻的要求蒙古族学生践行‘日本话及其日本文化之彻底吸收’的教育方针。”[8]
厚和农科实业学校的情况也是如此。据在该校任教的日本人回忆:该校日本语的授课,比现在日本国内学校学习英语的时间还长。学校的校歌用中文和日文两种语言创作,学校集会的场合经常合唱校歌,毕业典礼等场合还特别用两种语言合唱校歌的方式,为即将离开的年轻人振作士气,鼓励他们的活动。校歌为该校教谕前田实则作词,由副校长上原淑助翻译成中文。校歌中有这样的词句:“地上和平溢欢喜,民族协和旗下立。新生东亚欲黎明,我们立志作先驱。”“岿然不动我决意,新生蒙疆之王基。将于东亚放光辉,大家携手志向立。”在包头蒙古中学的日本教师用日语写作校歌然后教给学生。歌词中充斥着反共反苏、大亚细亚的内容。[8]让学生用日语合唱校歌,既普及了日本语学习,又向学生灌输了民族协和、东亚共荣的奴化思想,对学生毒害之深,可想而知。
为强制日语教育,在教材方面,蒙疆地区使用过日本国内、伪满、善邻协会和蒙疆政府编审室编纂的各种教材,也有教师自己编写的讲义。1943年春,蒙古教育会发行了《日本语新教材集》,含有决战时局、日本精神的认识等奴化内容。是日本强制日语教育的教材之一,在各级机关和学校中供学习日语使用。[8]
日本侵略者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造成恶劣的后果。“有些中学毕业生,不能用蒙、汉文写通顺的文章,却能说流利的日语,甚至有的说汉语也夹杂着一些日语名词,变成不伦不类协和式语言。”[9]184-185
2. 设置各种奴化思想课程
日本帝国主义针对蒙疆制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进行的教育活动,以奴化、殖民化教育为主题,向师生灌输日蒙亲善、亲日反共反英美的奴化思想,其具体表现为:通过课堂教学与精神讲话、朝会与遥拜、武士道与军事训练、休学旅行、勤劳奉仕等方法,向师生灌输反共反苏、民族协和、日蒙亲善、反英美的思想;培养学生的服从意识和尚武精神;在学生中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
蒙疆的小学设有修身课,中学设有国民道德课(类似伪满的建国精神课)。伪蒙疆民政部颁布的《中等学校用认可教科书之件》规定:“国民道德(或修身)之教材以修养人格为基础,由齐家之德进而达及对于社会之人任务,以宣扬东亚之道义、防共、民族协和之精神为原则,给与以迈进东亚新秩序之自觉。”[2]296-297修身课和国民道德课,成为日寇对蒙疆地区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课。
朝会和遥拜,是日寇向学生灌输奴化教育思想,实施奴化教育的常用手段。日本侵略者强迫各级学校每天早晨集合全体师生,举行升旗仪式,向日蒙国旗敬礼,向东方的日本天皇遥拜。如伪安北县公署于1939年建了一所小学,设在县公署院内。招收学生50多名,有教师5名。采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统编教科书,开设日语、汉语、算术、唱歌、图画、体操等课程。灌输“天皇至上”的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及法西斯的服从观念,每天向东方遥拜。[10]821
3. 开设“轻工”、“重农”职业教育课程
日伪在蒙疆的中等学校教育中加强职业教育。这是日寇实行“工业日本,农业蒙疆”政策的具体体现。蒙疆的职业教育以实业学校与实务学校为主,实业学校学制四年,实务学校二至三年。从表面上看,日本推行实业教育的目的,是以教授从事农牧业生产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培养勤劳的习惯为目的,以掌握实务为重点。实业教育与基础教育相配合,适当地推行是有益的,但日伪单纯地推行实业教育可见其用心险恶。[11]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工业日本,农牧业蒙疆’的侵略政策,仅准设立农牧业中等学校,禁止设立工业中等学校。”[11]45此举亦表明日本将蒙疆地区变为日本殖民地的不轨意图。
1938年,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在师范部、临教部之外,成立了实业中学部,招收实业班。翌年该部改称为巴彦塔拉盟立农科实业学校,也称厚和农科实业学校,招收农科班,1941年学校迁到新城的关帝庙街。该校的课程设置分为文化课、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有植物学、动物学和生理卫生课,专业课有农业泛论、畜牧泛论、农业课、畜业课、商业薄记、商业算术等科目。学校还设有农场、气象观测站。该校从第六期又开始办土木工程专业班,但学生未及毕业日本就投降了,学校由原绥远农科职业学校接收。[12]日本侵略者“工业日本,农业蒙疆”政策,虽然没有以文件的形式公开出现,但在课程设置上所体现的“轻工业、重农业”特征证实了此政策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日寇在华推行奴化教育活动的重要手段。
二、蒙疆沦陷区学校教科书的编审
众所周知,课程、教科书是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集中体现了教育的宗旨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取向。教育目的及培养目标的实现也正是借助于课程及教学内容才能达到或完成的。可以说,学校教育的育人活动是通过课程、教材的实施及教学活动而实现的。奴化教育虽然是一种扭曲的或畸形的教育,但有教育行为及方式的特点,只不过其中实质本性发生了变异。以下集中探讨教科书编审问题。
(一)蒙疆沦陷区学校教科书的编写
教科书是实施教学的主要工具,它对实现教学目标关系极大,因而得到日伪当局的特别重视。伪蒙疆政权成立伊始,日寇便极力摧残原有教育设施,禁止学校使用原有教科书,并将“各校所有书籍,尽数查封,不允阅读”。下令“家有藏书,限10日内,如有抗命不交者,一旦查获,严惩不贷!”对已查获管制的旧日各种教科书及参考书,全部焚毁”,对于各地教会所办中小学和村镇私塾,“伪官方初不限制,仍照常上课,教科书亦未限制,惟迩来伪政府拟调查私塾用书,必将加以严格之统制矣。”[13]
1936年3月后,日寇在强化奴化教育的政策宗旨下,着手整顿教育内容,重点放在教科书方面。“为达到麻木儿童脑筋,灌输亲日思想之目的,故对已往课本及教材,一律摒弃不用。唯伪组织甫定,凡应兴应革之事,正在草拟,故迄今尚无适当课本颁发。只颁教材大纲一纸,令教员以此自编教材,印发儿童。因而一般奸人,为博日人之欢心,则所编教材,不曰‘解民倒悬者,为友邦志士’;便云‘中国政府,为政不仁’。类此言语,竟为彼辈教材之中心”。[13]
然而,编纂符合日寇奴化教育目的的教科书一时并未完成。1936年5月,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当局只好在其辖区内的小学暂时采用伪满洲国编纂出版的教科书,直至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在继续采用伪满所颁教科书的同时,还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了特别处理。把小学教科书国语一科中某些不适合蒙疆政权的内容删除,加入一些具有地方和民族色彩而同时适合政治需要的内容,供各地小学使用。
1937年11月22日,日伪在张家口组建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其内部附属一编纂委员会着手编纂适用于“蒙疆区域”之教本,“其主要内容,不外以‘防共亲日’、‘民族协和’造成亡国奴的思想为目的”。[14]“而此时的察省沦陷区中等教育所用课本,亦‘皆由伪满洲国学校课本脱胎’”。[15]兴蒙委员会教育处辅佐官中村勇在编纂教科书上仿照伪满洲国教科书,使得国文教科书出现“歼灭元寇日本纪念日”的文字,这无异于“等于当着蒙古人的面骂蒙古人的祖先是强盗,对于蒙古民族是奇耻大辱。”[9]175
1940年,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确定了民政部教育科制定的教科书修订编写计划,准备全面实施伪蒙疆沦陷区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为了保证在教材中贯彻奴化教育的思想内容,使教育更好地为殖民统治服务,日本侵略者特制定了教材《编纂要领》:1、为了建设作为东亚新秩序一翼的蒙疆,强调团结一致的精神;2、发扬东洋道义的精华;3、针对各民族的特点,突出其特征;4、特别强调民族协和、防共、厚生;5、认识到本地区的特殊性;6、适应时代的趋势;7、顺应高度国防政权的完成。[13]当时,教育科编审室共配备了9名教科书专业编审人员,计划编写小学日语、汉语、蒙语教科书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如国民道德、地理、历史、汉语和日语等中学教科书,而中小学其他学科科目编写则委托给相关部门。上述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历时一年时间便初步完成了。到1941年6月,准备印刷、制本小学的汉语教科书18种25万册,蒙语教科书6种1万册;到1941年底,准备完成小学的汉语教科书34种100万册,蒙语教科书6种13000册,中学的汉语教科书27种27000册。三年内,计划总共发行60余种130万册。[13]
因伪蒙疆政权境内蒙古、汉、回等民族交互聚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日本为进行奴化教育,意图通过语言侵略来养成亲日的氛围。日本侵略者强制把日语作为蒙疆境内民众的共同语,各民族间不能相互学习对方语言,严禁蒙古人学习汉语。日本善邻协会(专门对蒙古人进行教育的机关)在编撰教科书时就指出:“蒙人的汉化毫无益处,如有固有名词,用日本假名代替,在括号内添上蒙古文字。”如此,在伪蒙疆政权各学校中,“科学的书都是日文的,为日本人做事都靠日文吃饭”,这就“使得蒙文、蒙语实用不大”。[16]104
日本善邻协会还极力强调教科书编纂中的思想性,表现在“由本协会编写的蒙古儿童用小学教科书,不只在本协会,应在所有从事于对蒙文化工作的机关使用,而且由于该规定关系对蒙古国策的根本和数十年后的日蒙关系,具有重大的教化意义,有必要将以下各点作为重心:(1)唤起蒙古人的自豪;(2)认识乌拉尔、阿尔泰人种的蒙古人的世界历史地位;(3)使其关心蒙古国运的重大问题;(4)使其了解日蒙亲善的必然缘由;(5)重视产业教育;(6)使其认识教育的重要性。”[13]
蒙疆奴化教育组织管理及教科书编审活动,还受蒙古教育会团体组织干预或影响。1939年11月成立蒙疆教育会,表面称以改进蒙疆教育和加强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团结为目的。在伪蒙疆政府内政部设立会务机构,由伪内政部部长担任会长;各政厅、盟设立支会。1941年伪政府机构改革后,改组为蒙古教育会。后与日本人的教育组织合并,变成了一个以日本人为主的组织。所从事的活动主要包括:一、调查与研究有关教育事项;二、编纂刊行有关当地教育的图书杂志;三、召开有关教育的研究会、讲演会;四、培训教员及讲习;五、普及日语、蒙语、汉语;六、介绍教育事业及教育团体的国际联络;七、与各种文化事业团体的联络和协作;八、教育视察;九、表彰教育功劳者;十、日语教育用图书及其教材、教具之斡旋;十一、当地学生用品的输入和配给。1942年4月18日,又召开该年度第一次理事会,确定举行全蒙教育状况报告会、时事讲演会、展览会、演剧,征集日语作文,绘制“大东亚共荣圈”地图及中学地理附图等工作计划。1943年春,又编纂出版《日本语教材集》,作为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及其他日语教育机关研究班学员的日语教材。当时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出资购得全部教材,转赠伪蒙古自治邦政府,并配送给有关学校及机关使用。
由此可见,“蒙古教育会”虽以民间组织形式出现,但其从事的业务不仅仅调查、研究蒙疆民族教育和举办有关教育的各种活动,而且还参与教科书编审、经营学生学习用具等,事实上已经具有半官方机构性质,成为日本在蒙疆地区确立的殖民地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为强化对在校学生的奴化思想渗透,伪蒙疆当局在小学《历史》《地理》教科书中,特别强调日本和满洲国,“而反无中国字样”。《暂行初等学校规程》第八条规定:“历史以使知我蒙疆地区,友邦大日本帝国,‘满洲帝国’,及东亚之史实大要,阐明政府并蒙疆政权创建之意义,及东洋精神,以涵养蒙疆精神为要旨。”第九条规定:“地理以使知我蒙疆地区之地势、气候、区划、都会、物产、交通之概要,并邻接各国及日本国势大要,并与我蒙疆区及日本有重要关系之各外国国势之简单知识,更进而及于地文之初步,养成爱蒙疆心为要旨。”在教授课程表内,历史程度为“蒙疆地域日本及东亚史之大要”,地理程度为“蒙疆地域日本及东亚地理之大要”,而对中华民国的历史地理知识毫无关注。在《教科规程》第二条中又有如下规定:“确认与友邦日本大帝国、‘满洲帝国’之亲善不可分之关系,并体认防共民族协和之精神,因教育上最重要务期于在全学科目及凡设施之机会彻底之。”第三条规定:“修身以咸使体会友邦大日本及‘满洲帝国’之亲善不可分之关系,并防共民族协和陶冶德性与指导道德之实践为宗旨。”[17]40-41以上各点,充分反映了伪蒙疆政权所谓“树立亲日思想”及培植日“满”支协同体的奴化教育的精神实质。而该思想指导下所编制的一系列的教科书内容中与中国民族国家政治及文化之间的联系消失的无影踪,以此来麻痹学生,泯灭蒙疆地区儿童的民族性,充分暴露出日伪侵略者的险恶用心。
(二)伪蒙疆政权对学校教科书的审定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政务院民政部下设教科书编审室。编审室作为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以下事物:“1.关于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及检查事项;2.关于教科书之发行事项。”但其具体内容由日本顾问全权决定和直接掌握。日本顾问在其制定的《蒙古国史教科书》“要领”中明确规定,要求教授蒙古史内容须主要反映:“1.带来蒙古人的自觉及自豪;2.知道民族的产生过程;3.对成吉思汗个人及其伟业的强调;4.元及其他蒙古帝国的大概情况;5.明代以后雄踞北方及其地位;6.援助清朝君临中国的史实;7.中华民国与蒙古——汉人移民;8.外蒙古和赤化;9.满洲蒙古;10.蒙古的地位和使命。”[13]到1939年底,该编审室编审了全部高级小学用的日本语读本,初级小学用的蒙古语读本4册、蒙古语算术教材4册。当时在蒙疆地区的中、小学校使用的主要教科书有算术、日语、自然、国(汉)文、修身、日本史、地理等四十余种。1941年,伪蒙疆政府机构改革后,原来的民政部编审室分别属于内政部文教科和兴蒙委员会教育处,前者编写汉回教材,后者编写蒙文教材。1942年12月,上述两个机构又合并为总务厅临时编审室。
为了加强对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实施更有效的管理,伪蒙疆政府还专门颁布了一些法令。如1940年4月17日,民政部以第54号训令《中等学校认可教科书之件》,规定了1940年度认可中学教科书的注意事项:“办理本年度认可的教科书之教材时应严守下记事项:应适于本政府成立的意义及使命;阐明本政府之特质;合于当地区的特殊性。”并对国民道德(或修身)、历史、地理等有关思想教育的教科书,提出了特别注意事项。其主要内容为:“国民道德(或修身)之教材以修养人格为基础,由齐家之德进而达到对于社会之任务,以宣扬东亚之道义、防共、民族协和之精神为原则,给予以迈进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自觉”。[2]296-297其中《历史》教科书:“历史之教材使明了历史上之重要事迹,理会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之过程、并阐明本政府成立之意义,以养成蒙疆人民之信念;东亚史以蒙疆为中心而研究各国历史之发展;关于民族争斗史实应以民族协和精神为原则留意办理”。地理教科书:“地理之教材使理会地球及人类及生活状态,并阐明两者之关系,尤须使知蒙疆之现势,而促进蒙疆人民之自觉;关于蒙疆之地理,使知自然状态政治、经济、产业、交通之状态和其关系,并授以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之概要”。[13]
伪蒙疆政府还仿照伪满的做法,于1940年8月20日成立了“教育用图书审议会”,颁布了《教育用图书审议会管制》,规定“教育用图书审议会属于政务院长监督,而应其咨问审议关于教育用图书编纂重要事项。”[7]24-25同年12月18日,民政部又颁布第19号令颁布《教育用图书采定规程》,其中规定:“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及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青年训练所等类此训练机关,须有民政部长著作权之教育用图书或经民政部长检定或审查之教育用图书,经监督官厅之认可方可使用”。[2]294-295
从这些法令中即可看出,蒙疆伪政府严格控制教科书的编审与使用,各科教材的审定内容都以围绕“建立大东亚新秩序、”“防共反共”、“中日亲善”、“蒙疆中心论”展开,其中有关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内容已被删改,以此制造民族分裂,以绝断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
日本势力为便于教育分化,还积极劝诱内蒙古王公一心向日,此举反映在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便十分明显:学校所教的历史,都是明治维新的故事,对于三皇五帝的盛绩,则一字不提。唯有提到成吉思汗,则竭力恭维赞扬,甚至不惜“矮化”本民族,篡改历史,向内蒙古百姓撒下弥天大谎,声称成吉思汗是日本人的祖先辈,把蒙古人的元太祖,假说成日本人。[13]这种谬论对蒙疆儿童产生相当严重的思想毒害。
(三)蒙疆沦陷区学校教科书的发行
为适应培养忠于日本“良民”的奴化教育的需要,伪蒙疆政权指使伪民政部发行系列教科书,供应沦陷区中小学校采用,这些教科书有些采用伪满洲国编纂的,有些由伪满组织人员对原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机构出版教科书加以篡改后印刷发行的,有些教科书编纂和发行都由伪满洲国机构负责,直接输入蒙疆沦陷区供学校教学使用。甚至有些学校还直接选用翻译日本学校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封面设计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封面有“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国民学校用”、或“高级国民学校用”、“中等学校用”字样;第二种是封面有“蒙古自治邦”“国民学社用”“初级国民学校用”的字样;第三种则是封面有“满洲图书株式会发行”字样(此书多为中等教科书)。各种教科书版权页信息则用“成纪”年(成吉思汗纪元),说明使用地区;编著者一般都署名“民政部”或“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民政部”,也有“蒙古联合自治邦政府”的,同时多有“民政部检查”字样,一般是标注“成纪”735—738年间发行(成吉思汗元年为1206年,735—738为公元1941—1944年)。
在1939年之前(包含1939年),伪蒙疆联盟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及伪晋北自治政府都编写出版和发行教科书。1939年9月,撤销上述三个政权,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以教科书编辑出版的署名就是“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8月改为伪蒙古自治邦,教科书署名就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出版时间对此也有一定的体现。
日伪统治初期,为使沦陷区中小学教育适合形势需要,在查禁原政权通行教科书同时,一一制定各学校教学用书。绥远抗战前,日军控制下的百灵庙小学的“教材和教本都是东洋方面预定好的”。厚和蒙古中学成立后,对于蒙授课目,学校“当时根本没有现成的蒙文数理科课本”,所需教材全都是由教职员自己用蒙文编成后再“油印发给学生”。例如,蒙文教师额尔恒毕勒格所编辑的油印课本内容“都是他从汉文书上选译来的”,在该校女子部,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教师“只好根据大家的文化程度自编教材,进行分组教学辅导”。在包头蒙古中学,除蒙语课外,日语、数学、历史等所有课本都是日本国内用的课本。
在初等学校教育用图书的汉、蒙语文选择方面,日伪当局进行了明确划分,“施行市县制之地域内采定汉语,其他之地域内采定蒙古语,县旗并置及市旗并置之地域内,须依管辖该地盟长之规定而采定或蒙古语”。“对于蒙古中学校得使用日本语、蒙古语,对于其他中等学校得使用日本语、汉语图书。但关于语学之教授不在此限”。关于各类教育用图书的使用,日伪当局规定,经伪民政部检定或审查的教育用图书及中、初等学校用教育用图书,须经市(县)长、札萨克或总管认可;“中等学校、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用教育用书,须经过政厅长官、盟长受民政部长之认可,由校长或所长采定之;青年教练所及类此训练机关教育用图书,由政厅长官、盟长或市县长札萨克或总管采定之”。如果上述规定实施有特别困难时,“由民政部长决定之”。同时,当局如发现某学校“不法采用”“有民政部长之著作权教育用图书或经民政部长之检定审查教育用图书以外之书籍”,“或令采用为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并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青年训练所及类此训练机关之教育用图书者”等擅自行为,或者某些学校对“有民政部长之著作权教育用图书或经民政部长之检定审查教育用图书”随意增加书价,仍然让师生采用,“或令其采用为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并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青年训练所及类此训练机关之教育用图书者”等行为,明令处以“二百元以下之罚金”。[2]294-295
到1943年初,鉴于战争局势的紧张,侵华日军加紧了对伪蒙疆的教育文化渗透。7月14日,伪蒙疆组织所属各盟旗兴蒙学校、喇嘛寺院义务教育部教师及有关人员参加了在锡盟西苏尼特旗兴蒙学校举办的兴蒙教育练成会,后转到张家口召开文教人士报告会。会议就“大东亚地理教育”和“配置教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大东亚地理教育”问题,会议认为“在大东亚共荣圈体制下激发蒙古人的气势,所以僻处草原一隅的学校也应让他们了解大东亚全境的地理、历史及其他,以增强其热情。倘利用挂图、照片、图片等参考用品讲解,便能充分理解,现在西苏尼特家政女子学校女学生关于大东亚地理问题的解答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她们对日本地理也特别明了。”关于“配置教材”,会议认为,“最近草原教育热骤然兴起,教材的配给无法保证。现拟以行政力量解决对符合蒙疆特殊条件的新教科书等学习用品的妥善配给,同时开拓些新的学问领域。随着一些新词汇的引进,需编纂日蒙新辞典,否则会出现诸多不便”。[13]日伪政权对教育教科书的使用规定之严格,并以此来控制蒙疆沦陷区中小学所受教育的内容和范围都在“反共亲日”、“分而治之”的奴化教育之下。
三、蒙疆沦陷区学校教科书的特点
日伪在蒙疆沦陷区推行的奴化教育是一种典型的殖民教育,这种教育必须有相应的内容、组织及方法为保障,其中教学内容是以课程编制及教科书的媒介形式出现的,尤其是学校师生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最能体现殖民主义教育侵略的特色。
(一)教科书的设计以殖民者的利益需要为中心
伪蒙疆政府所编写发行教科书的目的旨在为日本侵略者培养“良民”,为了体现侵略者意图,在教科书的封二,都刊有所谓“政府施政纲领”五条,包括:“昂扬东亚教育以期其实践”,“大同协和各民族以国民之总意为宗旨”,“与友邦同盟相结合”,“同志相契以参翼建设东亚新秩序”。在部分教科书的扉页,则印有“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宣言”。教科书在形式上却力求图文并茂,旨在更有效地感染学生,传播奴化思想。[18]483-484
蒙疆沦陷区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中非常重视日语的教学,把它作为必修课和主课来看待,在教学时间安排上也有很大的倾斜。如小学三年级课程表规定:每周总计教学时间为34学时,其中,日语占12学时,蒙语占6学时,算术占6学时,还有修身、地理、讲话、时事常识也多讲日语。各级伪政府人员均需参加日语讲习班,经常举行日语考试。并为鼓励学生学习日语起见,举办日语作文比赛、日语学会等。日伪甚至在学校之外的社会教育机构中也将日语列为奴化教育的主要科目,如通过开办日本语学校、讲习班、夜校、青年训练所,推行日本语教育。日本语学校及其场所,有的是伪蒙疆地方政府开设,有的是日本人团体开设;学习期限不等,学员年龄、性别也没有限制,大部分免费。日伪妄图依靠日语的推行来打下同化蒙疆地区人民的基础。强化日语教学的同时,弱化、甚至限制学生学习汉语。与此相应,教科书的种类及编写设计也明显这种计划方案。
从世界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共性来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一旦被他国殖民地化或是军事占领,一个共同的问题便会出现,那就是通过教育,支配者的语言被强制性地根植于被支配者。其方法有时是怀柔的,有时是强制的,甚至是暴力的,同时被支配者学习母语,使用母语的权利也被限制或禁止。支配者用强制与根植自己语言的手段,将自己的语言定为新的公用语,或者置于国语的地位,并且通过教育来普及它。同时,被支配着的语言被排斥,被无价值化,进而从教育对象中被删除。
被支配者若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则被视为“违章”,作为惩罚规则,“言语惩罚”曾经被实行。这些主要指是的学校教育中,殖民地的儿童若是讲母语,会受到教员的警告,有的会受到体罚。母语本是从母亲或是地域社会中很自然地付之于自身的民族属性,使用母语会成为惩罚对象,这种非人性的事情在殖民地与占领区总是出现。而在中国沦陷区,日伪所实施的教育中,这种民族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到了无法复加的地步。
关于史地教科书,蒙疆沦陷区实际上是完全按日本意图编写的。《中国地理》《历史》大讲特讲日本、蒙疆的地理、历史,在沦陷区的学校连张中国地图都不许挂。日寇还成立儿童读物审议会,销毁抗日进步书刊和与其谎言不一致的书刊,编撰以奴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儿童用书。他们篡改历史,混淆是非,完全按殖民统治的需要杜撰历史,蒙骗中国幼童,同时又假手汉奸、文人或媚日知识者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删去书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权的内容,换上“中日亲善,共荣共存”、“同文同种”、“日本皇军来解救中国人民”之类的鬼话,把伪满洲国说成是合法的独立国家,中国人民是“侵略者”。其中,关于“国家”的内容竟然是:建国精神、万寿节、满洲国民、国运、皇道等;宣扬的都是“日满一德一心”、“五族协和”等。
(二)教科书内容渗透封建道德伦理及宗主国殖民奴化思想
日伪统治者还利用封建伦理道德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在蒙疆沦陷区开设的学校中,通过“修身”、“国民道德”课对学生进行封建道德教育,养成他们逆来顺受、绝对服从的性格;他们通过汉奸之口叫嚷要从根本上铲除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就要学习日本实行“圣道”;课外活动中还有供日伪驱使奴役的义务劳动课“勤劳奉仕”,这是中小学学生均不得免的,这种强化的苦力劳动,造成了对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严重摧残。这些实质上都是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野心服务的。
小学使用《修身》教科书中,重点向小学生开授“礼义廉耻”等封建思想,并加以歪曲,给以奴化解释。其中对“礼义廉耻”是这样讲授的:“中国人对日本人要有礼貌,出入城要向日本士兵行礼,这就是‘礼’的具体表现与行动。”所谓“义”,解释为:“日本并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要求,皇军是用来帮助中国驱逐欧洲白种人,以建立王道乐土,所以中国人不应当敌视日本人。”所谓“廉”,就是要中国人吞糠咽菜,勒紧裤带想日军提供各种的物资,任其掠夺。所谓“耻”,解释为对日本不“义”不“礼”,对自己不“廉”即为“耻”。[19]这实际上是要蒙疆青少年忘掉国耻,心悦诚服地接受日本奴役。
《体育》教科书主要是对于法西斯训练,向学生进行武士道教育,《历史》教科书则向学生宣传日本的“天照大神”、“三件神器”、“日俄战争的胜利”。《地理》教科书的项目内容及知识技能加以介绍则向学生描绘日本东京、大阪等城市景象和建设成就。
作为课堂组织教学中使用上述教科书的延伸与补充,日伪在蒙疆沦陷区还作出许多强制性命令:各级各类学校每日清晨必须举行升旗典礼,集合全体师生向日本太阳旗敬礼,并向东方遥拜;经过日本神社时,必须鞠躬致敬;每逢“天长节”等日本节日来临,各机关、团体、学校必须举行放假纪念仪式,悬挂日本国旗致庆。甚至还强迫广大师生经常参加为被抗日军民打死的日军将领举行的慰灵祭,参加为日军攻陷我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而召开的“庆祝”仪式和游行。总之,利用一切手段营造日式社会、学校的环境气氛,以潜移默化影响学生。[3]549
日伪强迫蒙疆沦陷区青少年通过学校教科书学习日语及其他服务于军事侵略和殖民占领所需的课程,压缩其他学科课程,注重宣传“王道精神”,忽视基础知识学习,所有这些一方面是为了淡化中国青少年的民族意识,使他们逐渐淡忘自己祖国的语言和历史,降低他们的文化科学素质;另一方面欲使他们从语言、习惯、感情上尽快日本化,成为其二等臣民,以达到其最终灭亡中国,同化中华民族的险恶目的。
今天,部分正直的日本学者通过深刻反省,对此也深有认识,如日本宫城学院女子大学宫胁弘幸先生就认为:
殖民地的居民,在被迫要求与宗主国一体化后,无意识地同化于支配者文化,渐渐地失去了固有的民族性,民族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国家意识)。另外,原有的传统习惯,文化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这样,在所有的文化领域,支配者与被支配着这两种文化形态的混在,以及两种文化的变种形态出现了。特别是情报,教育领域,因为支配者的语言变成了主流。被支配者的文化开始被侵蚀、被侵略、被同化。报纸、广播、教育均使用支配者的语言进行的。殖民地原居民对原有文化额归属意识丧失,民族自豪感脱落,民族意识也变得淡薄。这就所说的“自我认识”与“归属意识”丧失现象。也是原日本殖民地与被占领区中汉奸身上所见到的现象。[20]8
教科书作为教育材料的核心,是教学的要素之一,成为教师或教育者向学生或学习者实施教学活动的中介或媒体,教科书是课程向教学活动工具性的转化,这之间是相互联系并相互贯通的。课程与教科书的设计不仅是纯粹内容问题,还体现了教育观念及组织管理的因素。日本侵略者联合中国沦陷区伪政权规定课程与教科书,实施教学组织控制,在蒙疆沦陷区学校中强制使用合乎其殖民统治利益的教科书,恶意篡改中国原有教科书,加入“反共亲日”、“民族协和”、“共建大东亚”等等奴化的思想内容,强化日本教学,企图淡化蒙疆沦陷区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对其进行精神毒害。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国家危亡之际,蒙疆沦陷区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与日寇进行斗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奴化教育洪流。日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领导下建立起来一批群众性的抗日爱国团体组织,如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他们曾以“蒙疆道教会”作掩护进行各种抗日斗争。到1940年初,抗救会已拥有会员200余人,会员们大力宣扬抗日救亡思想,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反对日伪的奴化教育,号召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同时,搜集政治、军事情报,筹集粮款,购买军需物资,支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等,他们为蒙疆地区的抗日救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作为抗救会的主要负责人刘洪雄就是其中典型榜样,他在生死危亡时刻,不畏敌人威逼利诱,坚决与日寇作斗争,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志,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他举起戴着镣铐的手,咬破中指,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下了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著名诗句:“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梵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这种抗日爱国的大无畏精神深深的感动蒙疆人民,并激励蒙疆人民在抗日救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斗争道路上不断前进。这种反奴化教育的英勇斗争,为瓦解日伪通过教科书实施奴化教育的阴谋,并促进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功绩彪炳史册,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汪伪政权[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 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1辑上册[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
[3]宋恩荣,余子侠.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2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4]金海,姚金峰.蒙疆政权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教育述略[M]//蒙古史研究:第9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5]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北支那经济通讯社.北支·蒙疆现势[M]. 北支那经济通讯社,1938.
[7]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总务部.蒙古法令辑览:第1卷[M]. 蒙古行政学会,1941.
[8]任其怿.日伪时期内蒙古西部的日本语教育[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9]陶布新.伪蒙疆教育的忆述[M]//内蒙古文史资料:第7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10]乌拉特前旗志编委会.乌拉特前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
[11]德穆楚克栋鲁普.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与瓦解[M]//内蒙古文史资料:第7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12]任其怿.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06.
[13]张建军.伪蒙疆时期蒙古学校教科书编辑与使用情况浅述[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4] YC.日寇宰割下的察哈尔[J]. 察省青年,1941(4).
[15]建设厅.察哈尔省现状调查[J]. 察省青年,1942(2).
[16]云泽.关于蒙地工作问题的报告(1946年7月)[M]//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Z]. 档案出版社,1988.
[17]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编.伪蒙政治经济概况[M]. 南京:中正书局,1943.
[18]石欧,吴小鸥,方成智.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19]张理明,张静娴. 日本侵华期间对山西沦陷区的奴化教育[J]. 教育史研究,2001(1).
[20]齐红深. 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研究——第三次国际学术研讨文集[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贾建钢 校对:朱艳红)
A Study on the School Textbook of the Mongolia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s Invasion
WU Hong-cheng, CAI Xiao-li, LI Yang-yang
(Educational College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order to achieve enslaving education in Mongolia and Sinkiang area, Japanese and puppet regime actively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colonial rule and enslaving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pro- Japanese”, “ national union”, “divide conquer”.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lonial rule, they set up textbook editorial organization, delete and distort the textbook content recklessly, compile the textbook for enslaving education, make the textbook distorted seriously, the aim of these policies is to poison young students, service implementation rule.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he enemy occupied area; Mongolia and Sinkiang puppet regime; Enslaving education; School textbook; School curriculum
G529;K265.62
A
1673-2030(2017)04-0089-10
2017-11-10
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晓莉(1993—),女,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李阳阳(1989—),女,河北沙河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