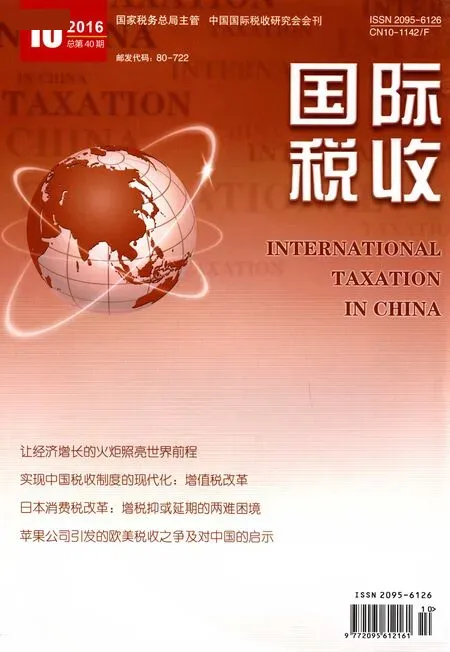外商投资企业非公允股权稀释的涉税问题探析
郭富礼(滨江区国家税务局 浙江 杭州 310051)
陈 展(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浙江 杭州 310006)
外商投资企业非公允股权稀释的涉税问题探析
郭富礼(滨江区国家税务局 浙江 杭州 310051)
陈 展(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浙江 杭州 310006)
近年来,税务部门不断加强对非居民股权转让行为的监控管理,“一元转让”、“平价转让”等股权转让行为作为重点风险事项均受到税务部门的调查调整,非居民股东无税转让股权的筹划空间受到限制。为减轻或消除非居民股东投资退出环节的税收成本,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开始采用其他方法进行避税,非公允股权稀释就是其中之一。非公允股权稀释,是指公司一个或多个股东按账面注册资本等非公允价不对称增资,导致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下降、股权受到稀释的现象。本文从两个非公允股权稀释案例入手,分析此类案例的税务处理思路,并对如何加强税收风险防范提出建议。
一、两个股权稀释案例的涉税问题分析
案例一:某化工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100万元,由非居民企业股东A全资控股。2013年,该化工公司市场估值达到400万元,股东B以现金100万元的形式对该公司进行增资,合同约定,股东A和B各拥有公司50%的股份。
分析:股东B这种非对称增资方式使股东A的股权受到稀释,表面上看股东A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这与我们反稀释的正常思维明显相悖。在私募交易的法律实践中,私募投资人通常会要求增加反稀释条款,防止在目标公司进行后续项目融资或者定向增发过程中,自己的股份被过分稀释。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却看到完全相反的一面,原股东轻易地接受了股权稀释的方案。从税收角度看,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股权转让所得应当缴纳所得税,但增资不同于股权转让,实践操作中一般不对增资环节征收股权转让的所得税。虽然很多税务干部觉得这个案例有疑点,但却找不出依据征税。
案例二:非居民企业股东甲全资控股一家食品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10年后,股东乙出资100万元对该食品公司进行增资,不久后,股东甲从食品公司收取100万元现金后退出,股东乙100%控股该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又减至100万元。
分析:通过先增资后减资的筹划,该食品公司的股东完成了从甲到乙的转换,注册资本未发生变化。针对股东甲的撤资行为,当地税务局提供了两种税务处理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五条的规定,股东甲撤回投资取得的资产应区分为投资收回、股息和股权转让所得,其中股息和股权转让所得应进行纳税申报。由于股东甲撤资回报过低,属于“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情形,当地税务局可以依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按照公允价值核定股东甲撤资时应该拿回的补偿。第二种思路,如果该食品公司不能解释短期内吸收投资又减少投资的行为具备合理商业目的,当地税务局可以按照《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将连续增资减资的行为重新定性为股权转让,从而对非居民股东甲转让食品公司100%股权的所得进行征税,股权转让收入按照公司增资时公允价值确定。对比两种处理思路,前者是按照撤回投资,将所得区分为股息和股权转让所得进行征税;后者是直接定性为股权转让所得。在股息与股权转让所得的协定税率不同的情况下,缴税金额会有差异。
厘清了案例二的解决思路,我们尝试能否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案例一。首先,非居民企业股东A未撤出或减资,无法用第一个思路确认减资或撤资所得。其次,引进战略投资者对企业进行增资,是非常普遍的商业行为,仅因为另一个股东增资就重新定性为股权转让,不符合《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第五条“税务机关应当以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的类似安排为基准”的规定,适用会比较困难。因此,解决案例一需要另辟蹊径。
案例一中,问题的根源在于增资过程中,新老股东的股权比例是按照账面注册资本确定,而不是按照增资时公司的公允价值确定。按照增资时公司价值400万元为基础,增资后股东A应当享有80%的股权,而投入100万元的股东B应当只有20%的股权。但根据增资协议,股东A和股东B的持股比例各为50%。这样一来,可以认为股东A无偿让渡30%的股份给股东B。通过上述分析,企业的增资行为又转变成股权转让行为,于是税务部门便有了征税依据。股东A无偿转让的30%股份的公允价为150万元(500万×30%),成本价为47.5万元(100万/80%×30%),应对股权转让所得102.5万元征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企业减资必须严格按照7个程序进行,包括股东会作出决议或者决定、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前置审批、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和对外公告、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尽管非对称增资或减资都能达到股权稀释的目的,但由于增资程序相对简单,大多数企业会选择增资方式。
二、非公允股权稀释现象背后的避税逻辑
通过非公允股权稀释筹划,可以达到以下效果。第一,如同案例一那样,原股东实现了股权部分转让,由于披上了增资的外衣,不容易受到税务部门的调查,可以避免缴税。一些企业在进行公司架构重组时,往往以非公允增资方式,实现关联股东间的股权传递,搭建目标持股架构。第二,通过一次或多次上述增资后,原非居民股东的持股比例降至25%以下,再过一段时间,原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因为很多税收协定都规定非居民在持股不超过25%的情况下转让股权,来源国没有征税权,此时股东申请享受协定待遇,就可以实现无税收成本的退出。实践发现,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最终转变为内资企业。第三,股东为了规避外汇管制,也会考虑利用关联企业非公允股权稀释,人为调整各方持股比例,再对公司的未分配利润进行“按需分配”。比如,在中外合资企业中,通过非公允股权稀释,人为抬高境外股东的持股比例,再对大量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这样境内资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境了。第四,由于非居民股东取得股息要征收预提税,而居民企业取得股息可以免税。部分公司会先以居民企业股东按非公允价增资,尽量降低原非居民股东的持股比例,再对企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这样居民公司取得的股息就可以免税。还有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这种手段,将应分配给其他国家股东的利润尽可能多地分配给香港股东,以享受大陆和香港的税收安排优惠。
三、加强税收管理的建议
第一,转变增资环节不存在应税行为的观念。如果股东以实物或无形资产增资,可能存在评估增值,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投资环节实物或无形资产所有权的转移,也会涉及增值税。即使股东以现金方式增资,尤其是非对称增资,可能是非公允股权稀释,税务部门需要高度关注。
第二,严密监控增资行为。税务部门应将增资行为纳入风险管理范畴,对于非对称增资,应评估企业的公允价值,已经发生大幅增值而按账面价值协商增资后持股比例的,应进行深入调查。对于短期内频繁发生增资减资行为的企业,更要了解其是否具备合理商业目的,是否存在与上述两个案例类似的避税筹划。税务部门与商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中,应将企业增减资信息列入共享范围,扩大源头监控范围。
第三,严把增资后的协定待遇享受后续审核关。如上分析,企业可能先通过非对称增资稀释股权,以达到符合享受协定待遇的法定条件,再申请享受股息、股权转让等协定优惠,这就可能构成了协定滥用。税务部门可以将企业增资行为与享受协定待遇备案联系起来,将二者作为一组风险特征组,具备这组风险特征的企业要作为重点对象进行排查:一要排查增资环节是否存在纳税义务,二要确定协定待遇是否可以享受。笔者认为,非公允股权稀释的情况下,补缴了增资环节视同转让股权的预提税后,可以享受协定待遇;如果没有补缴,则视为协定滥用,不应给与协定待遇。
责任编辑:高仲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