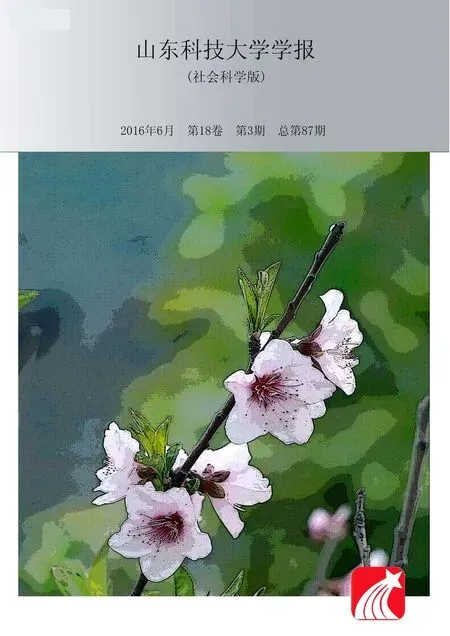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性质的理解
陈常燊
(1.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2.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性质的理解
陈常燊1,2
(1.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2.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维特根斯坦哲学具有很强的治疗性特征。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哲学病”进行诊断、对语言理论/语言哲学/语言实践的区分,以及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通过揭示“十足的胡话”和克服“误解的冲动”,从而给出“如其所是”的描述,指明了这种哲学治疗的异质性和非理论化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实践;哲学治疗;非理论化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这种难以捉摸不仅在于他的个人经历跌宕起伏,众说纷纭,更主要是在于他的哲学本身变化多端,似乎难以确定。西方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研究在他生前就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种争论截至目前也没有平息。最近,国内学者张学广教授发表了《近年来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趋向述评》,对国际上各种观点做了较为全面的点评。[1]尽管各派哲学家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提出了不同观点,但重要的是需要深入阅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应当从他本人的论述中去寻找他的思想的真实含义。本文将从哲学疾病的产生及其治疗、语言的三个层面、哲学的任务就是给出如其所是的描述等三个方面论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是一种对哲学疾病的治疗活动。
一、语言与“哲学病”
在传统的“标准解释”(standard interpretation)看来,维特根斯坦前期提出语言(思想)与实在对应的图形—镜象理论,而后期转向“语言即用法”的意义—编织理论。然而,人们发现这种解释根本没有抓住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治疗性,因为治疗哲学不仅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明确宣布的主旨,也是他前期哲学的主旨。近年来,在国际维特根斯坦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新维特根斯坦(New Wittgenstein)研究的展开。以科南特(J.Conant)、戴蒙德(C.Diamond)等为代表的“新维特根斯坦学派”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意旨是治疗。[2,3]
冯·赖特(G.H.von Wright)和哈克(P.M.S.Hacker)最早持有下述倾向:《论确实性》在维特根斯坦著述中的地位堪与《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相媲美。进入21世纪后,以莫洛尔—夏洛克(D.Moral-Sharrock)为代表的青年学者,称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著作为“第一个维特根斯坦”,称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著作为“第二个维特根斯坦”,而后《哲学研究》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新阶段,“这种区分取代将维特根斯坦哲学集中于《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传统二分法,表明维特根斯坦思想中不仅存在新阶段,而且其代表作不是两部而是三部”[4]。缘于《论确实性》在某些方面对《哲学研究》的拓展乃至超越,从而使维氏对“哲学病”的诊断最终取得新的消解(dissolution)。
《哲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哲学成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肇始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而终结于他的《哲学研究》。这种“语言转向”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logos的语言的功能、特征和界限是什么,以及作为logos的语言与being(存在、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聚焦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基于语言的)理解如何可能?在维氏看来,这依赖于基于语言的误解何以避免。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即在语言层面上,如何让一切如其所是。他的批判包括:基于误解语法的诸如指称论的、工具论的、本质主义的语言观如何损害了being的本来面目。从他这里完成了一个关于being的从“本质”到“如其所是”的转变,以及关于logos的从“理性”到“语言”的转变。他暗示我们基于情境主义的语言观来消解本质主义的哲学问题,并进一步基于个体主义的哲学观来消解传统的普遍主义哲学观。*个体主义哲学观认为,哲学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业,他的哲学问题无法由他人来代为回答;回答一个问题的意愿(will)甚至比理智(intellect)更为根本。譬如笛卡尔认为,每个人都只能自身去经历怀疑或沉思(cogito)而作出属于自己的判断,才能进入他的哲学世界。参见Anthony Kenny,The Legacy of Wittgenstein,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4:60.
大量文献表明,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拉塞洛维茨(Morris Lazerouitz)甚至直言不讳地称维氏为“哲学上的精神分析学家”:“他的哲学谈话弥漫着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氛围,对他来说,就像是哲学从人们需要解除的负担变成了语言学的病症,而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曝光创造幻觉(被无意识地用语言玩弄)的把戏才能达到。”[5]而我们在此之所以用“诊治”这个词,乃是由于它包含了“诊断”(diagnosis)和“治疗”(therapeutic)的双重含义。*与“新维特根斯坦学派”侧重于“治疗”(therapeutic)相比,其他一些学者,如林兹考(D.Lindskog)更加侧重于“诊断”(diagnosis),除了措辞上的不同,他们之间还存在某些旨趣上的差异,但二者都是本书的思想资源。参见Dale Lindskog,Diagnosis and Dissolution: From Augustine’s Picture to Wittgenstein’s Picture Theory,Frankfurt an Main:Eutop?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2007.这种诊治实际上包括双重功能:一是治疗性的(curative),二是预防性的(preventive)。[6]565
然而,从德文“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英文“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到作为书名的《哲学研究》,只能说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因为它的意思恰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而只是哲学“勘察”,这样比较切合维氏原意:“探察”这类词着眼于“看”(to see),而“研究”这类词着眼于“想”(to think)。“想”相当于琢磨、设想、研究、思考、论证这些,意味着是单线条的推理,从现象中发现找寻规律、发现本质、建构理论,而“看”相当于观察、检视、探察、探索、勘探、勘察之类的,意味着多向度的综观——用维氏自己的话说,是“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7]序言,*根据惯例,以下引述该书均采用如下方式:书名缩写PI+节码。更像是医生检查病人的身体,医生所关注的是有病的部分,没病不需要看医生——在此意义上,诊治疾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消极的工作——“哲学家诊治一个问题,就像医生诊治一种疾病。”(PI,255)我们这里谈“综观”,其中也着眼于“看”(观)而非“想”(综合研究)。而整部书乃是“在漫长而错综的旅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风景速写”(PI,序言),同样是“看”到的而非“想”到的成果结集——“这本书其实只是本画集”(同上)。
根据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的阐释,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本性的洞见包括“作为一种诊疗法的哲学”和“作为一种整体而清晰的世界图景的哲学”两方面。[8]“综观”或“综观式表现”作为维特根斯坦后期核心用语之一,就像枢纽一样联结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诉诸哲学的语法治疗功能,通过揭示我们的智性困惑以及困扰我们的矛盾或悖论是如何由于误用了我们的语言而导致的,从而解决或更准确地说是消解这些困惑、矛盾或悖论;另一方面,维氏视之为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在哲学上扮演着一种类似于“世界观”的角色,通过他常说的“不要想,而要看”(即不要解释而要描述)、“看到联系”等途径,形成我们对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清晰图景。作为对综观式表现的体现或补充,奥斯卡里·库瑟拉(Oskari Kuusela)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工具箱”里包括以下10种方法:语法规则的列举、对照和类比的使用、对众多变体的例示、居间情形(intermediate cases)的揭示、作为比较对象的语言游戏的使用、准人种学或准人类学、观念史的梳理、自然史的梳理、提问法和玩笑幽默法。[9]270
二、语言的三个层面
古斯塔夫·博格曼(Gustav Bergmann)1964年提出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通过里查德·罗蒂(Ricahrd Rorty)主编的同名文集,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短语,它意味着哲学的核心主题从知识转换成语言。*博格曼指出,所有语言哲学家都是通过谈论一种适当的语言来谈论世界的。这就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语言转向,它是日常语言学派和理想语言学派的共识之所在。当然他们之间就何为一种“语言”以及何以使它成为“适当的”这些问题产生了同样根本的分歧。参见Gustav Bergmann,Logic and Reality,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177.从知识的证成替换为语言的意义和指称;从知识的范围界限替换为可说与沉默、有意义地说与胡说的界限;从对知识的(非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和结构的分析转变为语言的起源(非发生学意义上的)的起源的分析。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转向”的一个大贡献是,明确区分关乎语言的三个层面:语言实践、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语言实践相当于古希腊人说的逻各斯的运行或康德的理性的运用。当然语言实践的范围比理性运用的范围更广泛,语言不仅可以表述理性的所有运用(理论运用、实践运用和公共运用),还可以表述超出理性之外的领域,比如康德意义上的感性和判断力,或者一般意义上情感和“非理性”。数学语言和文学语言都属于语言实践,但文学创作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理性运用。语言理论乃是关于语言实践的理论。语言理论当然也可以是一种语言实践,但它与一般的语言不同,前者属于二阶实践,而后者属于一阶实践。此外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二阶的,即它是关于logos的logos。其中前一个logos指语言,后一个logos指理论。理论意味着规律、法则、基础或本质。
在语言转向之前,哲学家们并不强调或至少并不特别强调语言理论与语言哲学之区分。然而在维氏那里这一区分是根本区别。语言哲学并不着眼于建构理论,或为语言实践提供某种还原论的、本质主义的解释。实际上这些都是语言学(语言科学)的工作。如果非得说语言哲学无非也是一种理论,那么它与一般的语言理论之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二阶理论,即关于理论的理论,而后者是一种一阶理论。语言哲学的任务不是直接关于语言实践的,而是关于语言理论的。它并不试图去“理解”或“指导”语言实践,而是试图通过批判语言理论而间接地作用于语言实践。这种批判主要体现在澄清或诊治语言理论对语言实践的“误解”(misunderstanding,与“理解”相对)及“误导”(misguide,与“引导”相对)。
我们主张将维特根斯坦哲学看作是实践哲学,但它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等作为学科分支的实践哲学,而是实践哲学本身,也就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以及与人类实践相关联的语言、规则、道德规范等问题的本质思考。“哲学的恰当的毁灭性是实践性的”[10],倡导语言的实践性和异质性,正是维氏哲学“解构”特征的鲜明体现:它并不试图指出人类实践“是什么”,而是为实践划清界限,指出它“不是什么”;它也不试图对语言提供理论解释,而只是高扬“太初有为”“唯做而已”,而这种无思的行事正是实践;用约翰·康菲尔德(John Confield)的话说,“实践是语言的基石”[11]。以语言实践为例,如果说人类的语言活动乃是基于遵循先验的语法规则的实践,那么毋宁说不存在人类语言这种东西。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令人满意的意义理论必须回答诸如“语言习得如何可能”这样的根本问题。显然不可能为此列出一个详细清单,于是有人试图在芜杂的语言现象背后寻求一种基础主义的还原论解释。像乔姆斯基这样的语言学家甚至将语言的可学习性归结为人体生物构造的“递归机制”。与此相对的立场是,将语言规则看作是数学演算规则或生物学机制的概念在这里将我们引入科幻故事的领地,这意味着,有关语言学习的概念问题无法由这些方法和理想化解决,因为这些问题恰好是由它们导致的。[12]
从表面上看,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关注同一个问题,即“理解如何可能?”(其冗余形式是“语言理解如何可能?”)但前者关注对于语言的理解至少是可能的(如果不是必然的话),它更侧重扮演一个正面的理论思考角色,而后者关注对于语言的误解至少也是可能的(如果并非必然的话),它更侧重于扮演一个哲学反思角色。用维氏的话说,“我们将语词从形而上学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PI,116)与形而上学用法不同,语词的日常用法既不是发明,也不是发现新东西,而只是让语词如其所是。这些形而上学用法,只不过是一些“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而哲学的任务正是在于“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PI,118)。
但仔细一想,语言理论对于“理解如何可能?”的回答是不得要领的,如果不是徒劳的话。因为种种语言理论无非是对种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或现实中的语言提供一种事后的解释,它试图帮助人们理解语言实践。这是一种经验研究,但哲学所关注的是一种先验研究。这种经验研究关注的是对业已存在的理解给出一种作为二阶理解的解释,而非一种可能的理解的必要条件。语言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理解,它包括自我理解、理解世界、与他人相互理解等多个维度。
对于一种可能的理解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角度是消极意义上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种可能的理解的必要条件至少有许多个,如果并非不可穷尽的话。他从消极意义上给出了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即回答“如何避免误解?”这一问题。因为如果误解不可避免,那么正确的理解将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对语言的误解源于语言理论。这些理论包括指称论的、观念论的意义理论,还原论的名称理论,本质主义的规则观以及非公共性的感知语言观,等等。
研究的方式,不管是通过演绎还是通过归纳来建构理论,提出假说,更适合科学研究,而不是哲学探察。科学研究自然现象的现实性,它永远不能根绝不确定性和怀疑论,无法断言某事不可能发生——逻辑上的不可能性。逻辑学和《逻辑哲学论》似乎可以做这种工作,但它仍然预设了某种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创造了大堆“超级概念”(“逻辑”“可能性”本身就是)或“超级表达式”——与之相对应的是“超级事实”(PI,192),而这是维氏后期要拒斥的。关于确实性和怀疑的真正的界限,并不是逻辑能做到的,这件事情只能留给语法研究,即“综观”。
哲学探察是一种语法研究,但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根本不同。应当说There are many things need be done.而不能说There is many things need be done.这是语法上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这是语言内部的问题——考虑到语言的约定性和任意性,假设一开始英语就不区别is和are的用法,也不会导致什么哲学问题。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汉语就不同于英语。显然,哲学上的语法研究,它是为所有的语言所共通的,它不是正如乔姆斯基所说的先天语法,而是通过考察我们实际上如何使用语词来反思、批判我们的哲学。哲学家也不像语言学家那样求取语法规则,甚至为之制定规则,“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而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因为它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它只是让一切如其所是”(PI,124)。
这样,哲学上的语法研究——在此意义上,这是一种语言哲学。它不同于后来的英美语言哲学,原因之一是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关于哲学语言的语言哲学。当然,维氏也许会反对将哲学语言(或学术语言)与非哲学语言明显区分开来——实际上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为便于讨论,此处做一个权宜的区分。实际上,这是一种传统的区分,“先验”“规定性”“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些一看就是哲学语言(语词),而“桌子”“今天下雨忘记带伞”一看就是非哲学语言(除非使用了修辞或隐喻)。所以,与其说维氏批判了哲学语言,毋宁说它判断了传统哲学家对哲学语言与非哲学语言的区分。在他看来,不管哲学家是否作了这种区分,他们都存在一个问题,即误用了我们的语言。而维氏的语言哲学,就是诊断哪里出现了误用(主要是哲学上的误用,而不是语法上的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误用),考察其病因,并对症下药——这些恰是医生的工作。一方面,哲学离不开语言,“只有凭借一种语言我才能用某种东西意为某种东西。”(PI,35)另一方面,哲学常常滥用语言,其中充斥着种种“误解的冲动”(PI,109)。只有在对语言的使用(这种使用产生理解)出了毛病的地方(在语言休假不工作的时候——哲学家通常不是使用语言而是“研究”语言,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用语言研究哲学,而真正要做的是研究哲学所使用的语言(对之进行研究)和研究(我们实际上如何使用)语言的哲学,才会产生(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哲学的真正工作是医治这种毛病,让语言回到正常状态——它原本就是用来使用的,而不是用来“研究”的——让语言如其所是,让传统上由语言所表述的(并且,在比如《逻辑哲学论》的意义上,还包括那些尚未用或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一切如其所是。这种诊治语法疾病的工作,是“看”的工作,有点类似于中医的“望、闻、问、切”的工作,而不是自然科学那种“研究”(对应“想”)的工作。
上面我们澄清了三个问题:(1)不是“哲学研究”而是“哲学探察”;(2)哲学探察作为语法研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研究,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语法研究;(3)这种哲学探察的对象或内容,乃是哲学家们实际上如何使用语言(用语言提出概念、研究问题、建构理论等)——这是与常人如何使用语言(用语言做游戏、办事情等)相对照的,像医生诊断疾病一样勘察和诊断哲学家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哪里出了问题,所以,这种哲学探察是一种语言哲学,一种维氏风格的(实际上后人没有继承甚至无法理解的)语言哲学。显然并没有单独一种哲学方法,而只不过是各式各样的治疗法。
《哲学研究》中的“研究”(investigations)用的是复数形式,其中确然包括了一大摞形形色色的、粗看起来有些零碎的研究。这正表明“综观”的重要性,我们并不试图“研究”维氏的《哲学研究》,而只是综观它,但即便为了综观,找到这些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并且这种联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是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2009年最新出版(英德对照本第四版)的《哲学研究》将原先的第二部分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心理学哲学——一些片断》,它在内容上与维氏后期关于心理学哲学的两卷评论和两卷最后著作更为密切。结合这些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当然能更好地综观维氏思想,但议题会显得过于庞杂。为此我们将本文综观对象从《哲学研究》进一步缩小为其第一部分,即截止于§693的那些内容。
《哲学研究》的写法,乃是多个论题连成一串的札记性质,即便在写法上也与《逻辑哲学论》形成鲜明对照,貌似没有条理,但从中仍可看出段落之间的自然过渡。貌似没有论证——论证属于“想”而不是“看”的范畴,但时而能见到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不过,在维氏后期哲学中见不到苏格拉底式的本质主义:追问“什么是知识?”或“什么是正义?”。许多段落是用对话体写成,假设两个人在对话,这正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习惯采用的。当然最典型的情况是,对话的一方是维氏,另一方也是他自己。维氏曾经说过:“几乎我的所有写作都是跟我自己的私人谈话。我跟自己促膝而谈的话。”[13]随之也带出一个类似的问题:要弄清楚破折号前面的那些话,哪些代表的是维氏本人的立场,哪些代表的是他假设出来的向他提出问题、困惑或反驳的对立面。
三、哲学的任务
诚如江怡所言,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工作,与其说是像传统哲学那样解决哲学中的问题(the questions in philosophy),毋宁说要解决的是哲学的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6]565而作为维氏后期重要哲学方法的综观式表现,亦称“显明的表现”(perspicuous representation),依据贝克(Gordon Baker)的解释,其目的正是要使得哲学问题最终得以消失,使得每一个有效的诊治都是对症下药的。[14]37
奥斯卡里·库瑟拉形象地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努力比作是“针对教条主义的战斗”[9]3。在维氏那里,哲学的斗争对象是我们的智性,因为智性对我们进行蛊惑,而这种蛊惑正是通过借助语言而进行的。我们针对智性所做的斗争,同样除了借助语言别无他法。智性是我们的智性,语言也是我们的语言,被智性借助语言所蛊惑的还是我们。为了避免再被我们自身的智性所蛊惑,我们只能限制我们的智性,使之不再能够通过借助语言来蛊惑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对智性借以蛊惑我们的语言进行批判。对智性的限制于是转变为对语言的限制,这种限制意味着我们要为语言划定有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logos的“尺度”功能在这里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语言批判实际上是logos的自我批判、自我划界的过程:通过约束其自身的某些功能——比如理智主义、基础主义、法则论和本质主义功能——从而为其他一些功能留下地盘,比如尺度、运用尤其是一致性的功能。赫拉克利特的“矛盾”和巴门尼德的“和谐”都是logos的应有之义,logos自身充满了内在张力。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这体现为语言自身的内在张力。
“哲学的成果是揭示出这样那样的胡话,揭示我们的理解撞上了语言的界限撞出的肿块。”(PI,119)理解作为一种理智活动也就是logos的活动,而语言的界限也就是logos的界限。这就意味着所谓的胡话也就是logos撞上自身界限之后所撞出的肿块。诊治这个肿块的除了借助logos自身别无他法——当然不是借助其本质主义功能,而是借助其“尺度”功能。“哲学”或“做哲学”(philosophizing)本身也是一类语言游戏(Sprachspiele/ language-games)。对一般语言游戏的哲学上的批判性描述当然也适合这个特殊的语言游戏。维氏注意到,这里存在一种可能的反驳:既然哲学是语法研究,它考察语词的用法,那么谈“哲学”一词的用法(哲学谈及自身)不就要第二层次(二阶)的哲学吗?维氏的回应是,讨论语词的用法并不导致无穷倒退。用法不是基础,不是“本质”,也不是定义和解释。“正音法可以为‘正音法’一词正音,而这里并不需要一种第二层次的正音法”(PI,121),哲学的情况与此类似。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的恰当方式是“综观”: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PI,122)。——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Ubersichtlichkeit)。综观式表现方式居间促成某种个体化和情境化的理解,[14]42-43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现或发明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维特根斯坦还说:
综观式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PI,122)
综观在维氏后期哲学中起到了一种类似于世界观的地位,尽管他只是用疑问的语气提及“世界观”一词,毕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一切如其所是”(PI,124),那么它正是我们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让一切如其所是”的恰当途径。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到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它只是描述,就像画家写生一样如其所“视”地描述。这种描述出来的东西正因为不惹人瞩目,才容易被掩蔽着,人们极少注意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那些“极其普通的自然事实”(PI,142),它们的重要性极易被忽视,但恰恰是哲学的真正基础。掩蔽的最深的东西,恰恰是摆在眼前的东西。而我们为什么这么描述不那样描述,这取决于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而我们能看到什么,这不取决于我们想看到什么或愿意看到什么。“我无需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描述。”(PI,139)到了生活方式这里,解释走到了尽头。终极根据只在行动中、实践中,不在理论中。这就表明了我们的工作不是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根据一张图表或者规则来作出解释,解释原则上是无穷尽的,只能举例,但又无法穷举。很难给解释作出不需要举例的定义或概括。怎么才算解释?解释的确定性和唯一性来自何处?我们又该如何消除怀疑?
本文所言“语言的实践”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是指“显见的”(explicit)语言实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提及语词或使用语言的人类实践,比如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语言游戏;广义是指“隐含的”(implicit)语言实践,也就是作为“会说话的”、使用语言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类实践。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可能没有说话,但他们仍然在用语词进行思考,用概念在下判断,这些都在根子上离不开语言。比如人们在遵守规则的时候可能保持沉默,但他们经由解释或描述的对规则的理解仍然离不开语言。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的思考应该说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此外还要注意,当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语法”这些词时,“他所指的不只是有着精确规则的记法系统,而是使用符合的整个活动”[15],换言之,乃是人类的语言实践或语词的实际用法。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对于“哲学病”的治疗,必须依赖于患者的密切配合。“我们要让另一个人相信自己犯了错误,只有在他本人承认确实感受到了这个错误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到。”[16]而且这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点一点地形成困扰他的问题之本性的一种新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还必须使他意识到,之前一直所寻求的智性满足所采取的是一种错误的方式。[17]遏制解释和理论建构的欲望,克服误解的冲动,还人类语言实践以其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非理论化(non-theorization)特征,这正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思考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张学广.近年来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趋向述评[J].哲学动态,2014(1).
[2]CONANT James, “Wittgenstein’s Method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tgenstein(ed)[M].Oskari Kuusel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DIAMOND C.The Realistic Spirit[M].Cambridge: MIT Press,1991.
[4]MOYAL-SHARROCK Danièle.(ed.)The Third Wittgenstein: The Post-Investigations Works [M].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1-3.
[5]莫里斯·拉塞洛维茨.弗洛伊德与维特根斯坦[M]∥威瑟斯布恩,等.多维视界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陈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3.
[6]江怡.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下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7]WITTGENSTEIN Ludwig.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fourth edition[M].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9.
[8]KENNY Anthony.The Legacy of Wittgenstein[M].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1:38-39.
[9]KUUSELA Oskari.The Struggle Against Dogmatism: Wittgenstein and the Concept of Philosoph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马丁·斯通.维特根斯坦论解构[M]∥威瑟斯布恩,等.多维视界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陈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0.
[11]约翰·康菲尔德.维特根斯坦与禅[M]∥威瑟斯布恩,等.多维视界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陈志敏选编;郝亿春,李云飞,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37.
[12]S.斯太恩拉德.语言与哲学问题[M].张学广,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126-127.
[13]WITTGENSTEIN Ludwig.Culture and Value, Peter Winch (ed.)[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77.
[14]BAKER Gordon.Wittgenstein's Method: Neglected Aspects: essays on Wittgenstein[M].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15]汉斯·斯鲁格.维特根斯坦[M].张学广,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178.
[16]WITTGENSTEIN Ludwig.Philosophical Occasions: 1912-1951[M].James C.Klagge, Alfred Nordmann (ed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p.165.
[17]玛丽·麦金.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研究》[M].李国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27.
(责任编辑:黄仕军)
Wittgenstein’s L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CHEN Changshen1,2
(1.Institute of Philosophy,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235,China; 2.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has a strong therapeutic characteristic.In later stage,after he diagnosed “philosophical” disease,distinguished between language theory,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practice,and regarded the task of philosophy as revealing of “absolute nonsense” and overcoming “misunderstanding impulse”,which gave a “description such as it is”,Wittgenstein expounded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heterogeneity and non-theorization of his philosophical therapy.
Key words:later Wittgenstein;language practice;philosophy therapy;non-theorization
收稿日期:2016-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方现代公共理性前沿问题研究”(14CZX043)
作者简介:陈常燊(1980—),男,江西瑞金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主攻现代英美哲学.
中图分类号:B5;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6)03-008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