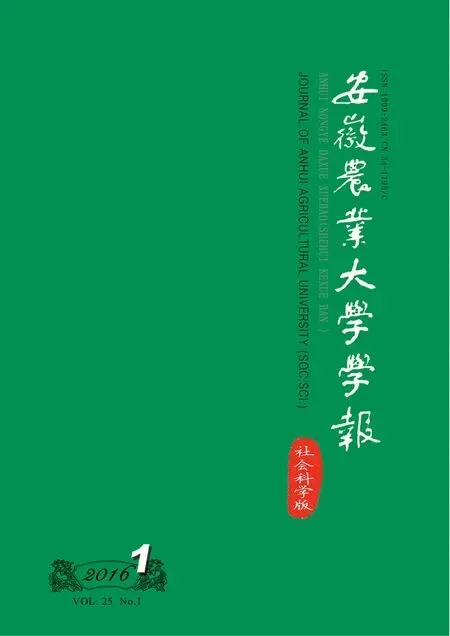凉州农耕信仰中的生殖崇拜文化解读
刘玉忠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甘肃合作747000)
凉州农耕信仰中的生殖崇拜文化解读
刘玉忠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甘肃合作747000)
摘 要:借助于两性之间的性巫术来促进农业丰产的现象业已消失,但它作为华夏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仍然在农耕信仰当中有所反映。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方,因此安土重迁、丰衣足食、风调雨顺自然成为当地农耕文化追求的目标。凉州地区的农耕习俗中的送耙齿、送“粪馍”、种子的贮藏、男耕女播等事象中,至今仍留有先民生殖崇拜的印记,它既是凉州人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的延续,也积淀着劳动人民的理想和追求。
关键词:凉州;农耕信仰;生殖崇拜;耙齿;粪馍;民俗事象
在远古初民的眼里,大地母亲孕育万物、繁衍生产,因此远古初民借助于两性之间的性巫术来促进生产,期盼丰收。尽管起源于远古时代的这种以两性行为来影响农业的原始信仰与巫术已经不再以庐山真面目出现,但它潜伏在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构成浓厚的民族文化的积淀。从凉州的民间俗信中我们仍能够依稀感受到性巫术的巨大作用。例如在许多地方将结婚选在春节期间举行,一则是春节是农闲季节,人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庆贺这一盛大的人生喜事。其实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还是借助于男女婚庆来促发和诱导万物的生长繁育。因为在远古初民的眼里:“人是一个与宏观世界功能酷为相似的微观世界。男女的性结合是二元自然力的互相作用的小型复制品。因而人类婚姻和天地的婚姻基本上一样,天与地是在暴风雨中交媾。从荒古时代以来中国人就认为云是地的卵子,它靠雨即天的精子而受孕。在人类范围内,国王和王后、男人和女人的结合,真正体现了世界上正负两极的平衡。如果它们的结合不和谐,整个大地都会遭受旱涝和其他自然灾害之苦。因此,统治者和其配偶的性关系要按礼仪的周密调节。”[1]凉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方,因此安土重迁、丰衣足食、风调雨顺自然成为农耕文化追求的目标。为了上述的目的自然使得生殖崇拜成为酣畅淋漓的生命表达而且渗透于具体的民俗事项当中。本文就撷取几个活着的例子以此透视凉州人民生殖崇拜现象。
一、送耙齿
在凉州地区的婚俗中母亲为了自己的姑娘嫁到婆家后能“把持”家庭,在姑娘出嫁时要在梳妆匣内装一对“耙齿”。这种特殊的习俗折射出深深的农耕文化情韵,也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生殖现象的崇拜。
凉州婚俗中送耙齿的奇特习俗看起来神秘莫测、光怪陆离,但这种习俗却保留了劳动人民对男女生殖崇拜的缅怀。就像著名民俗学家欧内斯特·琼斯所说:“当某种民俗学家们将某种风俗解释为祈求更多的食物或更好的收成时,他们将这种愿望假定为人类的一般属性与经验,认为无需进一步证实,而且说那是属于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事情,然而这种观点却含有许多危险,因为现代心理学不容置疑地表明,人类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哪怕是对表面上看来极简单的行为进行考察,也会发现其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深层结构。”[2]46同样对“耙齿”而言尽管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之下不可避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作为一种古老的农耕用具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用来疏松土地、保蓄水分的耙齿形似于男性生殖。因此在婚俗中被赋予古老的生殖崇拜的文化意义和民俗情味,通过这种形象的类比赋予耕作以某种性意味,并不意味着人们把农业视为与自然一场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具有极为深刻的农耕文化意义。在早期的新石器时代的神话中,:“丰收被看做‘hierogamy’即‘圣婚’的成果——土地是女性,种子是神圣的胚胎,雨水则是天地交合的产物。在播种季节,男女之间举行欢好燕合的性交仪式极为常见。性交被视为神圣之举,它将激发土地的潜力、促进万物生长;农人的犁铧也像神圣的阳具,它将深入大地的子宫,并以种子让它受孕。”[2]46其实在古代人的眼中农业的丰收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这种恩赐又依赖于天地和谐、阴阳顺畅。在他们的眼里耙齿直插大地母亲的怀抱,无疑等同于男女之间的性交。因此耙齿被换喻为一种阳刚文化的象征,大地母亲毋庸置疑被看做是培育种子的容器。“倘若植物能够一次又一次从大地(植物的子宫)中生出,那么即使人无法看到整个过程,也可以相信,女神——她创造了昼夜的循环,大麦和小麦的循环,以及春秋的循环——也会创造人类生命的循环。还可以相信,通过与神秘的性力量合二为一的色情仪式——女神就是通过这种力量创造了生育和再生的奇迹——我们人类不仅能得到庇护,在不可避免的痛苦、悲伤、死亡中寻到安慰,而且有许多更多的机会世世代代过上快乐富足的日子。”[3]148通过这种性巫术的方式促使天地和谐,万物丰产,可见耙齿之所以在婚俗中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其原始意义恐怕也在于此。
二、送“粪馍”
古浪一带当男方与女方定完婚返回的时候,女方家要给男方带一个里面装有牲畜粪的馍馍,后来为了卫生起见,换为能吃的东西让男方带回家。其一“粪”谐音为“丰”。因为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农业是第一位的,希望男方家能够五谷丰登,年年有余,这样以后在婆家也能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再者“粪”亦即“缘分”,圆圆的馍馍加上“粪”意味着这桩婚姻美满幸福,毕竟“千里姻缘一线牵”“万年修得同床眠”,能够结为婚姻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另外粪便是强大生殖力的表现:“粪便形象跟所有的物质、肉体下部形象一样是正反同体的,其中生育力、分娩、更新的因素蓬蓬勃勃。于此揭示了粪便形象的正反同体性。他和再生和更新的联系以及它在克服恐惧中的特殊作用。粪便这是欢乐的物质,在远古的粪便形象中,粪便与生育力和肥田力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粪便被当作介乎大地与肉体之间的一种中介体,一种使大地和肉体彼此接近的东西。同时粪便也是介乎活着的肉体与被分解、转化成土壤、肥料的死的肉体之间的一种中介;肉体在世时把粪便献给土壤;粪便就像死者的身体一样,肥沃着土壤。……粪便还是欢快和令人清醒的物质,这种物质同时既是贬低性的,又是温柔的,它用一种最轻松的、毫不可怕的诙谐方式将坟墓与分娩集于一身。”[4]由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施肥的最佳方式就是牲畜的粪便,它可以促使庄稼茁壮成长,这样就认为把粪便送给男方,希望娶的新娘也会拥有强大的生殖力。可见这些看似荒诞离奇的行为恰恰反映出民间实物的物质附着性,它使民间实物产生灵性,反映老百姓的思想观念和乡村规矩,使得这些特殊礼物成为他们表达美好祝愿的最好表征。
三、种子的贮藏
每到收获的季节,尤其在打谷场上,人们用自家的种子换取别人家长势比较好的种子,以备来年种植。在这一简单的交换中,恰恰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利用巫术促生的原理,它的根源就在于利用长势较好的种子本身的生命力,促使来年庄稼的成长及丰收,在其他地方,“这些古怪仪式早已变成陈旧的事物,变成农民的娱乐和学者的哑谜”[5],而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却是活生生的现实,被当作金科玉律一直加以奉行。同时将换来的种子由女子精心地保存,贮藏种子本来是农事活动之一,远在仰韶文化时期已把粟种存放在陶罐里,精心保存,以备来年春播之用,但是更多的贮藏方法是挂之高处,既通风干燥,不易霉烂,又可防止鼠虫之害,这是很正常的活动。之所以由妇女贮藏种子,是因为:“妇女是农业的发明者,又是原始农业的主要经营者,而且当时的家务也是由妇女掌握的,所以贮藏种子的责任就落在妇女,特别是主妇的肩上了;不仅如此,妇女又是生儿育女的体现者,由妇女怀孕、哺乳、养育成人,因此妇女是生育的核心和体现者,她们有巨大的生殖能力,这也是妇女藏种的信仰根源;王后是妇女的领袖,是生育天子的女性,‘有传种繁殖之祥’,一旦种子经过王后之手,必然产生交感巫术效果,即种子一与有旺盛生命力的王后接触,种子就获得了王后一样的孕育能力,会长出茁壮的庄稼,给人们带来丰收。”[6]可见,当人们意识到土地丰产与人自身有某种联系时,通常通过性巫术来保障生产,而种子的成长如同女性之怀孕一样可以保证农业取得丰收。所以许多农耕仪式都是对“浪漫爱情”的模仿以及对女性神奇魔力的崇拜。“女人性爱的特殊魔力,从神秘的月经到制造新生命的天赋,普遍表现于整个处理某些神圣葬礼的女神崇拜期间。明亮强烈的红色在许多宗教里都与女人的经血有关……女人的经血是自女神的天赋的表面及象征意义,古希腊人以经血做肥料,将种子抹上经血再播种。”[7]14
四、男耕女播
由于凉州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耕作于田间垄头,他们相信自己的艰辛努力最终会创造出“神话”。“在新石器时代,神话也不是人类的避世工具,它仍然保持着远古神话的核心力量:迫使人们面对死亡的来临。神话并非田园牧歌,大地之母也并非温柔和善、令人慰藉的女神,因为在那时,刚刚起步的农业生产还不像在后世那样代表牧歌式的安宁和平静。那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斗,一场孤注一掷的挣扎,向贫瘠、干旱和大自然充满神力的反复无常发出挑战。人类的繁衍生育本身对母婴来说也极具生命危险。同样的道理,耕种土地也只有在千辛万苦、筋疲力尽的劳作以后才能得到收成。”[2]50因此老百姓对播种格外重视。甚至在一些地方在春天播种前要举行神圣的性交仪式或性交的禁忌,之所以对这种仪式非常重视,是“因为春季是万物复生、农作物播种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对中国的农民来说非常重要,因而在季节性转换的重要关头举行盛大的集会礼仪,一方面感染着春天的神奇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希望从自身的生殖行为感染自然界和农作物播下的生命种子,获得又一次新生”[8]51;另外,“春季具有生死转换的魔力,这种魔力与农民种下的种子的魔力一样。种子是生与死的转换体,在秋季,成熟的谷粒(种子)是(庄稼)生命的完结。在春季,死亡了一个冬天的种子下土以后又成为新的生命的胚胎。因此播种之际是死亡向新生的转折关头,人们便集会狂欢,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把天地万物、宇宙人类的生殖力全部调动起来,以便顺利通过转折的关键。当种子融入大地‘便意味着转折已经告一段落,这时人们与自然之责任使命均已完成,于是集合春天的狂欢便宣告结束’”[8]54。随之进入正常的生活当中。除了播种的辛勤劳作和神圣的性交仪式之外,对播种的方式也颇为重视,一般要求男耕女播,所以时至今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人能看到男子扶犁,女子播撒种子的情景。因为:“在远古时期,女人就被称作是大地母亲、夜晚、月亮、潮水、蜕皮的蛇、任何令人联想到柔软、流动、有生殖力的事物。男人自命是皇天父亲、白昼、太阳,任何坚硬、有穿刺力、向前迸射的东西。性行为变成耕田与播种,或大地与皇天的结合。使阴茎勃起、子宫膨胀的力量,也就是芽苗穿出肥沃、长成谷物的力量。要确保田地丰收的农家夫妇,会趁月圆的晚上,在刚播下种子的田地里做爱。”[7]141而“种子的成长,被视同女性之怀孕;女性之多产,正可以象征农业之丰饶。正如地上万物被认为是地母所孕生一样,女性具有无穷之可能性,可化无为有,化小为大,化少为多,可生生不息。既同样是怀孕行为,则两性之交合对触发植物之成长,当然可以发挥一种咒术般的效果。……女性既是农业丰饶不可或缺之中介,也是农耕仪式的参与执行者,或者可以这样说:女性是丰饶与多产之根本要素”[9]。
所以每当漫步于田间垄头或行走于山野田间都可以看到一幅幅男人扶梨、女人撒种的美丽画卷。可见女播的习俗也是希望女性能将强大的繁殖力传递给庄稼,希望农作物能够颗粒饱满,取得丰收。远古初民的眼里男女之间的性交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不带有任何秽邪的味道。他们通过男女之间的和谐来象征天地之间的和谐,通过这种性巫术来获取丰产丰收。除此之外对播种的姿势也有讲究,笔者曾经调查,在古浪一带,当人们扶耧播种时,“脚踏土块手扶耧,眼里瞅的是稀么稠”。而且要求左手四指并拢掌心朝上与大拇指扶住耧把的左面,右手依然,只不过要求掌心朝下,扶住耧把的右面。这种姿势取其男女交媾、天地和谐之意。
总之,生殖器崇拜作为一种古老的农耕文化信仰,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文化的情韵。这种对生殖崇拜所表现出的信仰强烈的生命意识,带有神秘的宗教信仰感情,具有神圣化的特点。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本来并不把自己与自然分开,因此也不把自然与自己分开;所以他把一个自然对象在他自己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了本身的形态。有益的、好的感觉和感情,是由自然的有益的东西引起的……因此人们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亦即必然地……将自然的东西弄成了一个心情的东西,弄成了一个主观的,亦即人的东西……把自然当成一个宗教的、祈祷的对象。”[10]正因为如此凉州人民把大地作为祈祷的对象,通过对生殖的崇拜以此祈求大地母亲的庇佑,获得强大的生殖神力,实现旺盛的生殖目的。无论婚姻习俗、生产生育都倾注了凉州人民美好的感情与愿望。凉州地区的农耕信仰习俗中表现出的生殖崇拜现象是凉州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深刻地反映了凉州人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积淀着劳动人民的理想和追求。这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农耕文化、民俗风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直接的生殖崇拜渐趋消失,但生殖崇拜通过各种潜在的方式以及具体的民俗事象得以生动地展现,通过农耕信仰中生殖崇拜的解读有助于深刻地认识当地的民俗风情及生活风貌。
参考文献:
[1][荷兰]高佩罗.中国古代房内考[M].李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9.
[2][英]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M].胡亚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3][美]艾斯勒.神圣的欢爱[M].黄觉,黄棣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卷6[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99-120.
[5][英]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6]宋兆麟.地母信仰与繁殖巫术[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94(1):104-108.
[7][英]爱理斯.人性[M].莎文,黑子,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4.
[8]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51.
[9]王孝廉,吴继文.神与神话[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368-369.
[10]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59:458-459.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production Worship in Liangzhou’s Farming Faith
LIU Yuz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ansu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ezuo 747000,China)
Abstract:Sexual sorcery,which was used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has disappeared.However,as a kind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it is still reflected in farming faith.Liangzhou has been a place with developed agriculture since ancient time,so it is advocated in its farming culture that people should attach to his native land and never leave it,that people will have ample food and cloth,and that there will be good weather for crops.So far there are still some traces of reproduction worship in such farming customs as“giving the rastellus”,“sending‘steamed buns’made of dung”,seeds preservation,“men plough and women sow seeds”and so on,which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ine wishes of the Liangzhou people who pray for a golden harvest,and reflects the ideal and pursuit of laboring people.
Key words:Liangzhou;farming faith;reproductive worship;rastellus;“steamed buns”made of dung;folk custom
作者简介:刘玉忠(1976-),男,甘肃古浪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汉语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校长科研基金项目(2015-05:《丝绸之路文化带中的民间生殖学科的文化考察及其研究》)
收稿日期:2015-05-07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6)01-01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