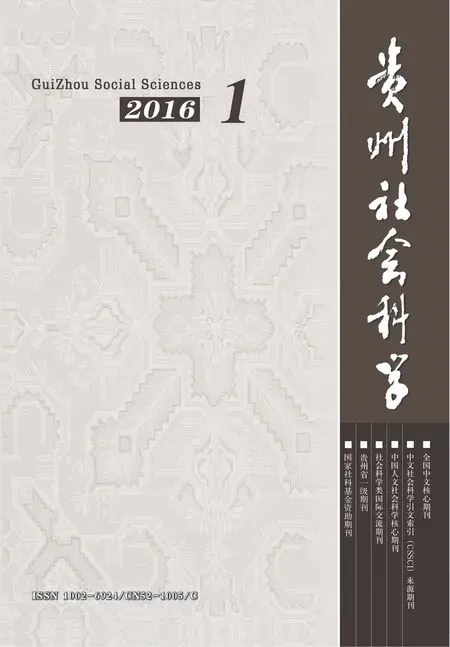从文类到文体:中国小说文体身份与地位的确立
熊 明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6)
从文类到文体:中国小说文体身份与地位的确立
熊明
(辽宁大学,辽宁沈阳110036)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中,是与“大达”相对的小道,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立小说家一类,使小说具有了文类称谓的含义。表明“小说”在指言论、思想的含义外,又有了指称表述或承载这一类言论或思想的文章的总称的含义。作为文类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四个关键节点,但其在文类意义下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书写体制,直至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这一强烈有力的理论阐释与实践示范,无疑是新小说兴起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小说、文体中心地位的确立,也使得其在现代文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小说;文类;文体;文体身份
中国古代小说,从“小说”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庄子·外物》篇开始,一路走来,至于近代,其实经历了一个从文类到文体的演变过程。小说文体身份的获得与确立,成为与诗歌、散文、戏剧等并列的文体之一,一般认为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与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密切相关。
一、小说文类与中国古代小说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立小说家一类,由此所谓的“小说”,不仅指一种思想,还跟文献分类有关,是一类文章的总称,具有文类称谓的含义。
作为文类,班固等对小说的文类特征做了相应的描述。在著述的材料和结构方法上,“小说”所囊括的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刍荛狂夫之议”(班固),“丛残小说”(桓潭),都是一些不被主流重视、被主流蔑视、为主流鄙弃的,与经典、圣人的言论不一致的,或出自民间鄙野之人之口或干脆来源于传闻的言论。小说家们从民间得到材料后,经过他们的整理(合)、组织(造),并贯以自己的观点,以一定的文法(饰、譬论),最终结构成篇,成为“小说”。其次,在小说的体制和形制上,是“短书”,其不仅记录“另类的”见解和观点,从体制、形制上看,亦很短小。再次,在渊源上,班固以为小说“盖出于稗官”,张衡又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二人关于小说起源的看法不同,可见,在汉代,关于小说渊源已有了不同看法。但这两种观点,都对后世小说文类的范围界定即对小说内涵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影响。班固之说,使小说文类的范围向着史的方向延伸,出现了向叙事之文靠近的趋势;张衡之说,使小说文类的范围向着医巫厌祝之类扩展,虚诞之文渐被延入其中。
因此谈论中国古代的“小说”,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广义的小说,即作为文类的小说,无论是在子书身份之下,还是在史流身份之下,亦或在“亦子亦史”的双重身份之下,它都是一个涵纳甚广的集合;一是狭义的小说,即通常所谓的中国古代小说,是综合考虑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性,按照叙事性原则、传闻性原则或虚构性原则、形象性原则、体制原则等遴选出来并符合作为文艺学意义上的文体概念的小说。
作为文类的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四个关键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作为文类的小说,溯其根源,当是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但因其已佚,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又主要依据其而成书,故班固《汉书·艺文志》应为现存可溯的小说文类含义的起点。《汉书·艺文志》所录十五种书,为诸子九家之外的子书杂著,“或托古人,或杂记古事”。[1]都是言辞议论,杂考杂事之书。
第二是刘知幾的《史通》。刘知幾在《史通》中,以具体详尽的理论阐释,将小说纳入史类,称之为“偏记小说”, 并将其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种类型。[2]这样,小说文类所包括的范围,就由《汉书·艺文志》仅包括言辞议论,杂考杂事的子部杂著,拓展到一切史类杂著。
第三是李昉等的《太平广记》。《太平广记》是宋初李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张洎、王克贞、董淳、赵邻幾、陈鄂、吴淑、吕文仲十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全书共五百卷。《太平广记》所收录,李攸这样概括其类型:“又谓稗官之说,或有可采,令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编为五百卷,赐名《太平广记》。”[3]王应麟略有不同:“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 少了李攸的“故事”。李攸、王应麟语中的“小说”,当即刘知幾的“偏记小说”,可见《太平广记》的小说文类,在刘知幾小说文类的基础上又有扩展,加入“野史”、“传记”、“故事”等类。
第四是永瑢等的《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文类,“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4]排除了“诬谩失真”、“猥鄙荒诞”,亦即那些原本包含在小说文类中而涉荒诞、虚构的作品。也就是说,《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文类,较之《太平广记》等所涵纳的范围明显缩小。
通常意义上的小说,一般指唐前已出现的志怪、志人、杂传小说等雏形小说,[5]但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文类所录十五种小说,如明人胡应麟所云:“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也。”[6]至 《隋书·经籍志》,则可见属于杂传小说的《燕丹子》、属于志人小说的《郭子》、《世说》、《笑林》、属于杂事小说《小说》等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出现了,但作为先唐大宗的志怪小说,如《冥祥记》、《宣验记》、《搜神记》等则被著录在了史部杂传等类中。
刘知幾的偏记小说,根据其定义和举例,逸事、琐言、杂记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逸事即所谓杂事小说,琐言即是所谓志人小说,杂记则是志怪小说。基本囊括了初唐以前的所有通常意义上的小说类型。而偏纪、小录、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中许多作品,是有显著小说品格的。刘知幾的小说文类,可以说基本涵纳了所有当时通常意义上的小说作品。
《太平广记》分类庞杂,数量宏大,其小说文类,如依据李攸、王应麟之语,则包括了刘知幾的小说文类在内,又有野史、传记、故事之类。正如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中所说,“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7]特别是纳入了唐代兴起的传奇小说。唐人传奇,在其产生兴盛的唐代,人们并不称之为传奇,而是视之为史部的杂传记,称之为传记。裴铏将自己的小说集名为《传奇》,当是取其记奇怪之事的含义,北宋时,陈师道《后山诗话》言:“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裴铏所著小说也。”[8]可以为证。《太平广记》单列传记一门,收录唐人单篇传奇,这是李昉等编纂者见识高明的体现。
传奇有通称唐代新小说之意,当始于南宋,谢采伯曾云:“经史本朝文艺杂说几五万余言,固未足追媲作者,要之无抵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9]谢采伯把稗官小说、志怪、传奇并举,似乎对唐人小说和六朝志怪之间的不同已有所认识,并有区分之意。至元代,以传奇呼唐人新小说的意思就更为明显了,虞集于《写韵轩记》云:“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传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9]虞集把唐人的那些闲暇无可用心时所作多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传会为说、以为娱玩的小说称为传奇,指称甚明。降及明代,传奇小说的指称则更为明显和具体,杨慎云:“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10]胡应麟区分小说为六类,其中有传奇一类,而“唐人传奇”一语,亦创于明代的臧懋循:“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11]
《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文类,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叙述杂事者”为杂事小说,“记录异闻”、“缀辑琐语”者为志怪小说。但有严重缺失,不仅传奇小说没有纳入,宋以来新兴的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如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长篇章回小说等均未纳入。造成小说文类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之间的差异和分离。但在民间小说观念或者文史理论家那里,小说的广、狭二义则有合流而走向一致的趋势,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云:
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费。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极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秀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于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宋元以降,则广为演义,谱为词曲,遂便瞽史弦诵,优伶登场,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盖自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矣。[12]
其小说所指,基本指向历代通常意义上主要的小说类型——志怪、传奇、章回小说。不用连类引申,将《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小说类型与章学诚所言小说类型合并,则中国古代所有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都涵纳其中了。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书写体制
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亦即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没有统一的书写体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书写体制。
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类型是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二者书写体制相似。鲁迅先生多次在与传奇的比较中论及志怪小说的书写体制。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三讲《唐之传奇文》中说:“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13]在《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中说:“唐代传奇文可就大两样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13]综合鲁迅先生所言,志怪小说书写体制的特点大致是“粗陈梗概”、“都很简短”、“简古的文体”、“一点断片的谈柄”等。志人小说与之相类。也就说,作为雏形小说的志怪与志人,篇幅短小,一如断片;文字简洁,粗陈梗概。不论是志怪还是志人,其文本存在形式都是丛集。
唐五代时期,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类型是传奇小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传奇小说“文章很长,并能写得曲折”,“文笔是精细、曲折的”,“有首尾和波澜”,和志怪、志人“大不相同了”,它有完善的书写体制,即借鉴脱离纪传体史书列传发展而来的杂传文体而成,且如宋人赵彦卫所言:“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4]有 “文备众体”的显著特征。其文本存在形式则有单篇和丛集两种形式。至于杂事小说,上承志人、志怪体制传统,基本仍是短小的片断体制,文本也以丛集形式存在。
宋元时期,传奇、志怪、杂事小说的书写体制大致沿袭唐五代传统。话本小说是新兴的小说类型,因其源自“说话”,是说话人的底本,因而有着鲜明的“说话”特征。从外在形式看,由题目、入话、正话、篇末诗几大部分组成。话本小说的题目通俗简练,多能画龙点睛地概括小说的主要内容。有的话本题目下还有另外的题目,如《简帖和尚》,下注“亦名《胡姑姑》、又名《错下书》”。入话即引入正题的叙事内容,与正话相对而言,是开篇的引子。入话是说书人在勾栏瓦舍表演时用以暖场,目的是稳住场上的听众,等候尚未到来的听众。正话是话本小说的主体,由于其本为说书人备忘之用,故其中保留了说书人的口吻,有许多套语和韵语。套语如“话说”、“却说”、“且说”、“正是”、“只见”、“但见”等。韵语则如文言小说中诗词。篇末诗位于篇末,与入话相对,一前一后。篇末诗侧重对正话故事情结的总结,其作用不仅雅化了故事,也能增强听众对故事的印象和理解。
明清时期,长篇章回小说是新兴的小说类型。章回小说的形式最初孕育于话本小说,在以演绎历史内容的说话中,由于无法一次完成,因而将内容分割成若干单元,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前后连续的体制。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分三卷十七段,每一段故事都相对完整,并有标题,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带回目的话本。《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标志着章回体的真正诞生。经过《西游记》、《金瓶梅》等的实践完善,逐渐由粗糙到精致,最终定型并成为白话长篇小说的固定体制。《中国小说通史》概括章回体有这样三个特点:首先是分回标目,其次是“说书体”(或“类说书体”)叙事,最后是韵散结合,文备众体。[5]另外,明清时期还有模拟宋元话本小说的拟话本,拟话本是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标准体式。冯梦龙“三言”是典型的拟话本。“三言”将前代话本小说题目字数不一,随意命名的代之以统一的七言句或八言句,又将每两卷的题目依次构成较为工整的一联。同时,注重“入话”和“正话”的关联衔接,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作为文类的中国古代小说,从其产生起,无论是归于子书之下,还是史流,亦或“亦子亦史”的双重身份之下,都是一个涵纳甚广的文类,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书写体制。而我们认定的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则兴起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类型,有着不同的书写体制,且各具特点,有着多样化的特征。
三、“小说界革命”与小说文体身份的确立
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即作为文类的小说,自其出现直到清末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都是一个涵纳多种体制作品的集合,因而是不具备文体观照意义的。而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则类型各异,体制各异,呈现出不同的文体特征。考察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与小说发展史,不难发现,作为广义的小说即小说文类,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其涵纳“范围由广而狭,大大缩小了”,[15]逐渐与狭义的小说即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重合,走向同一。最终,小说由文类转变为文艺学意义上的文体概念,也就是小说成为与诗歌、散文、戏剧等并列的文体之一。这一转变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与清末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密切相关。
中国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战败和次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特别是知识阶层造成极大的震动,以去弊强国为宗旨的变法维新运动随即展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认为,要变法维新,就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于是《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相继创办,刊载政论与译介西方文化科技。同时,还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改良革新,于是先后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在《新小说》第1期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阐释“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他说:“故近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6]当然,在此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已为新小说的诞生进行宣传鼓吹。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志〉识语》、严复、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已开始大力提倡小说、抬高小说地位和作用。在“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下,梁启超等人重在从理论上论述小说的功用,强调小说于改良世道人心、启发民众最为“有用”。因而大力提倡政治小说的创作。
梁启超等所谓的“新小说”,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使小说新”,即开创小说的新面貌;二是指与传统小说不一样的全新小说作品。前者是“小说界革命”的主要任务,后者是“小说界革命”的产物。在“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下,新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陈大康统计,单计算通俗小说的出版数量,1895—1911年为1524种,1903—1911年为1422种。
“小说界革命”的兴起和成功,其原因的探寻是学术界的重要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比如李剑国、陈洪在《中国小说通史》认为,“晚清小说的繁荣自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原因,但不可否认,其与传播媒介关系委实密不可分”。[5]“小说界革命”的兴起和成功,也与梁启超等人声势浩大的理论阐释和实践示范分不开。自1897年开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自办报刊、杂志等,大量发表鼓吹“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文章,它们不仅反复强调小说的“国民之魂”的功用,也涉及对小说艺术、小说审美的阐释,并创造了全新的专题论文和“小说丛话”体等批评方式。梁启超在1898至1903年间,先后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译后语》等文章,并与侠人等在《新小说》上连续刊载文章,以《小说丛话》的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论述。不仅如此,梁启超等人一方面译介外国小说,树立榜样,一方面还亲自进行小说创作,以为示范。梁启超就创作了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共五回,第一回至第四回于1902年11月到1903年1月在《新小说》杂志第一号至第三号上连续刊载。第五回刊于1903年9月《新小说》第七号。所以,“小说界革命”发起者的这种强有力的理论阐释与实践示范,无疑是新小说兴起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显然,这一话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小说界革命”改变了小说自《汉书·艺文志》以降的“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不在主流的边缘定位,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17]不仅赋予了小说文学身份、文体身份,而且被置于各种文学体裁的中心位置。小说实现了华丽的现代转化,从此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文体身份,脱胎换骨,并在现代文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如《中国小说通史》所言:
清末新小说已由古典小说原所固有的传统题材,开始向反映时代风云、社会现实、新的生活及作家理想过渡,出现了大量具有时代意涵、新型意识和批判反思精神的新小说。这些小说已不再是古典小说的消极延续,它已具有一种新质,一种近代社会才有的新的特征,可以说是真正近代意义的小说。尽管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粗糙,但它蕴涵着前所未有的力量。[5]
毫无疑问,“小说界革命”对小说文体身份的确立以及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有着无法低估的影响,并由此实现了小说的现代性的转化。
综言之,中国小说由于其自身环境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由最初的思想与文类含义,经历漫长的历史演变,最终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实现了由文类到文体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实现。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无疑是一个关键节点。在这一关键点,中国小说获得了与诗歌、散文、戏剧等一样的文体身份,并实现了华丽的现代转化。但很显然,“小说界革命”所带给在中国小说的变化是迅猛的,故而也显得十分粗鲁,传统与现代之间缺乏细致与平和的交流,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反思的。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3.
[2]刘知幾,撰,浦起龙,释.杂述[M]//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3.
[3]李攸.圣学[M]//丛书集成新编.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37.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M].北京:中华书局,1995:1182.
[5]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胡应麟.九流绪论下[M]//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371.
[7]鲁迅.破《唐人说荟》[M]//北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3.
[8]陈师道.后山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1:310.
[9]谢采伯.密斋笔记·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4册:644.
[10]虞集.写韵轩记//道园学古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7册:545.
[11]杨慎,撰.王仲镛笺证.升庵诗话笺证:卷一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13.
[12]臧懋循.弹词小序//负苞堂集[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57.
[13]章学诚,撰,叶瑛,校,注.诗话[M].//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2004:560.
[1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8:135.
[16]马振方.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
[17]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0.
[18]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M]//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8.
[责任编辑:郑迦文]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13BZW064)。
熊明,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及小说文论、文献整理。
I054
A
1002-6924(2016)01-065-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