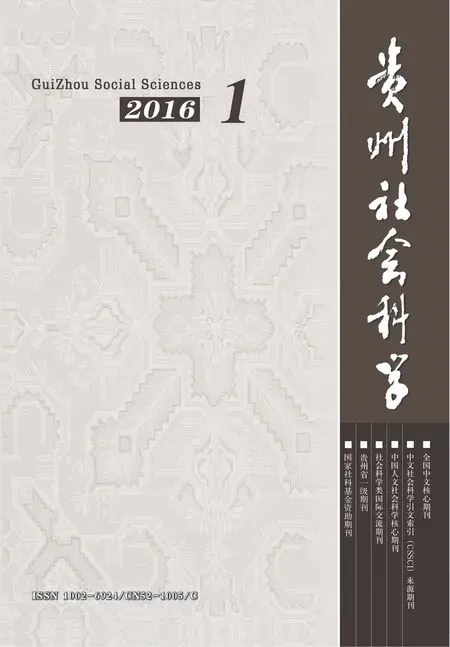外部力量介入下的农村基层矛盾化解
——基于内蒙古GZ村的考察
王海侠 李 行 温铁军
(1.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2.中共南平市委,福建 南平 353000;3.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外部力量介入下的农村基层矛盾化解
——基于内蒙古GZ村的考察
王海侠1李行2温铁军3
(1.清华大学,北京100084;2.中共南平市委,福建南平353000;3.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农村基层矛盾的形成有着社会与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其破解自然也非单纯的“官治化”和“法治化”治理诉求所能化解。基层农民抗争既对我国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又同时损害农户生计,鉴于此,村社矛盾最好在村社内部解决,以避免村民走向长期上访和诉讼的“不归路”。在既有村社力量和格局存在的前提下,适当引入外部力量(社会资源)介入村庄事物和纠纷化解,有利于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外部力量介入对于村庄矛盾化解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法治;官治;外部力量;征地;抗争
一、背景与问题
土地纠纷已经取代税费争议成为后税费时代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全部上访中土地征用为主要原因的占39.4%,东部地区这一比例更高,为48.1%。[1]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调查结果亦显示,土地因素最易引发群众不满,形成冲突隐患,当进一步考察土地问题的具体矛盾因素时,发现征地补偿不公和土地征用不合法是两个突出因素。[2]
基于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突出和土地问题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学术界以农民抗争为切入点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诸如农民抗争的概念、工具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其中以社会学界中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最为突出,具体体现为发表于《社会学研究》上的于建嵘、应星以及吴毅的三篇文章,在此之后研究农民抗争的文章逐渐增多,涉及到农村各个方面的抗争,但基本上这些抗争研究都与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和承接。
于建嵘的研究作为中国农民抗争的引领之作,通过与斯科特“日常的抗争”以及欧博文、李连江“依法抗争”概念的对话提出了农民“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3]在这之后很多研究农民抗争的文章都借用了这一概念,如“依势抗争”、以理抗争、“以死抗争”、“以身抗争”、“以网络抗争”,以及以“伦理抗争”等等。不过后来的概念框架学术影响力不大,其解释框架多基于个案研究,没有对农民社会抗争的整体形势作出评估。
于建嵘所总结的农民“以法抗争”经验较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其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提出了农民维权抗争向着政治权利要求方面发展,这一抗争有明确的宗旨以及组织,还有领导精英和利益激励机制等内容。应星和吴毅的研究则指出,“非政治化”是当前农民维权抗争的基本特征。只不过应星是从农民组织和动员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指出草根动员中自身面临的资源性弱势问题以及抗争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4]而吴毅则是从国家的转型中所出现的权力和利益之网对精英的吸纳这个角度来讨论的。[5]应文提出的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的解释遭到了吴毅的批评,认为应星,包括于建嵘这种对于“法治化”或者合法性困境思维的考量忽视了中国仍旧是个官治化的社会,而且这种思维容易陷入“民主—极权”这一泛政治化陷阱。后来于建嵘在回应中指出应星和吴毅的主张是精英式主张。
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其实在于将解决农民问题的努力交给官方,而不是第三方或者农民自身,即农民上访不是官治化的吸纳,就是法治化的重新建构。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二元悖论:如果“法治化”而非“官治化”能解决问题,那么为什么农民更多的时候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上访?然而,如果承认中国是一个“官治化”为主导型的国家建构,那为何一定要“送法下乡”?其实,从实践经验来看,目前无论“法治”还是“官治”都已经很难解决农村的问题,对于任何一方面的过分执着都显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那么,究竟该如何突破农民维权抗争的这一困境呢?笔者认为首先需要突破法治和官治的二元对立思维,从第三方的角度来看待农民矛盾化解的可能。这一观点,正是基于笔者在内蒙调研实践而来。
本文试图超越“官治”与“法治”的视角,即从第三方介入的视角动态地来考察农民的抗争,从村庄维权抗争的层面和过程来揭示普通农民、带头精英、知识分子以及各级政府的隐藏文本,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待抗争的演进及其中所蕴含的启示,尤其是外部力量在矛盾梳理上所起到的作用。本文的案例描述和讨论分别基于研究小组三年来4次对于内蒙古GZ村的跟踪调查。
二、村庄上访事件的结构及过程
(一)村庄基本情况及矛盾点
GZ村隶属于元宝山区美丽河镇,距元宝山城区6公里。该村原有10个生产小队,2014年后被分为6个村民小组,总户数980户,常住人口3775人,耕地面积5300亩。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村庄农民的土地不断地被侵蚀和破坏,而且由于煤矿的生产所造成的污染以及工业园区污水的排放问题也造成了很多村民的不满。村庄主要涉及两家煤矿,隶属于国电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平庄区的工业园区。GZ村的经济矛盾主要集中在征地和塌陷土地补偿两个方面,征地主要涉及三个村民小组,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涉及一点;采媒造成的土地塌陷主要涉及另外的三个村民小组。
工业园区共占用GZ村1380.05亩土地,合同金额共涉及2216万元。村委会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所有合同,从未主动向村民公示。工业园区的征地始于2003年,第一次征地征了788亩,规模较大,后来又陆续征地几次,但是规模都比较小。2000年刘明当选村委会主任时,GZ村村委会累计负债230万,2006年刘明离任前将此笔外债还清,而款项部分来源于工业园区占地补偿款。当时村民对于去世或新增人口如何分配存在争议,村委会没有把这部分补偿款发放到个人,用于支付了村庄债务。2007年9月11日以前补偿标准为每年550元/亩,2007年提高为每年800元/亩。由于当地近年来大力发展蔬菜大棚,经济效益较高,按蔬菜大棚的产值计算,至2025年的现值损失约为7949万元。此外,由于工业建设用地难以复垦,部分村民也担心2025年以后自己和后代的生活会缺乏保障。
除煤矿建设占地外,煤矿开采导致的耕地塌陷,是GZ村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共涉及1393.09亩耕地,补偿协议总金额共计3056万元,塌陷补偿协议书也没有向村民公开。由于除少数特殊补偿款全归村民外,煤矿塌陷地补偿款由村委会与村民按比例分配,村民获得补偿款的2/3,村委会留1/3,所以村委会2006年至2010年共留存1556万元。2005年涉及的合同补偿款,于2007年才开始发放,1556万元的煤矿塌方补偿款全由现任村主任李志支配。2005年签订的煤矿塌方土地补偿总金额546万元,补偿款分七期(2005-2011年)还清,实际情况是:迄今为止,只在2007年发放了一期,实际发放款53.9万元,比应发金额少24万元。2007年签订的煤矿塌方土地补偿协议里规定不同类型的土地的补偿标准不同,水浇地1024元/亩,温室大棚5079元/亩,简易大棚3069元/亩,旱平地460元/亩,但实际发放全按460元/亩发放。以第3村民小组(原6队)村民马英为例,该户村民涉及塌陷地3.5亩,2007年至今共领取了5次补偿款,分别是2800元、2800元、2800元、1900元、5000元,共计1.5万元,对于每次领的是对应的哪份合同、哪段时期,都不清楚。同一块土地,同组(同队)的张素荣每亩领取的补偿金额却更低,对于补偿标准是什么,村委会没有给出清楚的解释。
村民对塌陷的土地补偿中涉及的款项归属有所争议,复垦费现全归村委会所有,大棚损失补偿发放不均,大棚地上附着物和大棚土地损失的补偿标准和去向不明,正是这几个问题导致了初始的几个村庄内的农户(精英)上访,他们均有一定的文化和经济实力。
(二)维权事件的动态演进
GZ村的上访事件始于2006年的选举,选举使得各方利益开始浮现于村庄之中。9月份,第3次村委会直选工作开始。通过预选,刘强、李志被确定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并确定10月14日进行正式选举。由于李志与上世纪90年代的村干部车方正、宋华等有着亲戚和经济联系,2001年的审计报告也审查出其承包的村基建公司拖欠村10余万的管理费,因此,一些村民对李志不信任。10月上旬,李志带领几十名村民到元宝山区林业局反映刘强任期内随便批准砍伐树木,10月12日刘强被元宝山区公安局以“滥伐林木”为由拘留,13日部分支持刘强的村民去公安局,以进行选举为由把刘强接回了GZ村。14日正式选举,李志当选。但是,一些村民认为存在严重的贿选、威胁恐吓、重复投票等情况。通过查看投票录像,确定有村民重复投票后,强烈要求本次选举无效。22日前后,元宝山区民政局正式宣布选举无效。11月5日,镇党委宣传办和镇政府司法所联合发布致GZ村全体党员和选民的《倡议书》中指出:“在10月14日选举中,出现了在未办理委托票的情况下一人一次多张投票、一人多次重复投票、未成年人参加投票和户口已迁出人员参加投票的违法现象。”12月27日进行第2次投票,刘强超出李志148票,但是因两人都没有过半数,选举无效。12月29日进行第3次投票,此次规定超出票数达到1/3就符合规定,李志当选村委会主任。有村民反映,李志在28日晚和29日早上花费10万元买选票。
2007年1月开始,齐司义、刘强等多次上访,向公安局反映选举中李志的贿选行为。2007年元宝山公安局发布了《关于齐司义反映GZ村换届选举中存在“严重贿选”问题的调查处理意见》,指出:“经过对康志国、丛日发、杜荣等17人调查询问,均否认为李志、张俊买选票之事,也没有接受李志、张俊的钱物。经对李志、张俊询问二人均否认花钱买选票之事。举报中反映李志、张俊指使他人于2006年12月24日晚,向本村丛日利家投放恐吓纸条,25日凌晨将村民安玉军家窗户玻璃用砖头砸碎。此案,古山派出所当时已出警并做了调查取证,没有证据证实此事为李志、张俊二人唆使他人所为。”“通过调查取证,举报人提供的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举报候选人李志、张俊在2009年12月29日举行的GZ村村委会选举过程中,进行贿选的证据不足。”
之后齐司义、刘强等村民先后去元宝山政府、赤峰市政府反映贿选问题,持续1年左右的时间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同时,孟浩宇、齐司义、高继玲等村民对元宝山工业园区(平庄工业园区)占地合法性问题、煤矿塌陷耕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产生严重质疑,也相继到元宝山区政府、赤峰市政府上访。在去元宝山区政府、赤峰市政府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村民先后到中央机关、国家部委上访6次,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2次,平均每次5名上访人员,每次持续一星期左右。同时,到赤峰市政府和元宝山区政府询问和反映情况超过100次,几乎每星期一次。表1列出了到中央机关、国家部委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上访的主要时间、人员、反映的问题和结果。
在上访过程中上访者和利益受损的村民逐渐团结在一起,并组成了一个农民的大棚蔬菜合作社组织,即赤峰市元宝山区园茜蔬菜专业合作社,大家形成经济与组织上的联合。合作社以户为成员单位,成员约230户,占全村总户数的23.47%。孟浩宇是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术良是合作社副理事长,齐司义是合作社成员,他们都是上访的主要人员。2006年以来,他们的上访费用共计34371.61元,其中不包括为上访所作准备的各种费用。上访人员留存的支出原始凭证显示,费用支出均为差旅费、餐费、打印费、邮递费、电话费等,其中到北京的上访费用每次大约2000元,到内蒙古1400元,到赤峰市100元。2007年9月,村民筹集了1600元用作上访,但是由于被认为是非法集资,其中1400元至今封存。

表1 2007年至今 GZ村村民主要上访情况
(三)外部力量介入下维权抗争问题的化解
2009年3月之后,由于上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使得上访带头人也开始灰心丧气,上访的过程充满各种艰辛,村镇干部的“截访”和黑社会的威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然而既然接受了村民的委托,就不好作罢。在上访即将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请求外部力量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009年初,上访带头人孟浩宇认识了在内蒙做调研的某大学教师陈博,讲述了GZ村多年上访的经历。同年8月,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时,这位老师带着两个学生对于村庄情况进行了调研。在这次选举中,上访村民推选孟浩宇竞选村主任,另一候选人是原村委会主任李志。
在选举进行前,陈博老师带领同学做了如下两件事:一是在征得上级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审计上届村委会账目;二是做村庄范围的问卷调查,以证明村庄在征地和补偿环节是否公正和透明。虽然审计过程遭到干扰,但基本正常进行。此次调查共等距抽样了30个农户,调查结果显示:30位被访农户中,29户表示承包地有部分被占;均表示征地时没有参加过民主讨论,也没有看到过占地单位与村委会签订的占地协议;除了1户农户表示参加过占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讨论外,29户均表示没有参加过,更不知道占地款具体的分配和使用。同时,有农户反映所在村民小组的村民代表和村民组长都是未经过村民选举,而被村委会指定委派的,在土地征占和补偿事宜上,他们并没有联系过村民,更没有表达村民的意愿。
这次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得原来一团乱麻、无人厘清的村庄账务和征地问题有了明确的结果。陈博老师及学生依据调研情况撰写了账务审计和征地报告,呈送给区、乡政府。在看到报告之后,区里一改原来不介入的态度,开始积极处理GZ村的问题。根据此次审计出的村主任和村副主任的经济问题,对两人进行了处理。区委书记还于2010年5月,邀请陈博老师一同观摩了此村的村民选举,这次选举程序公正、演说公开,村民对此次选举都非常满意。历时5年的集体上访事件终于得到平息。从后期的回访中看到,在新村委班子带领下,GZ村开始走向良性的村社治理,道路得到修缮,基础设施也有了维护,原本一团散沙的村社渐渐地能够融合。
三、维权事件演进的机制总结
通过对GZ村上访事件的考察和分析,发现村民长期上访有着深层的社会与经济制约,村民上访的抗争之举本质上构成对整个社会经济惯性的挑战,加之维权者无论是诉诸“法治”还是“官治”的解决策略,最终都不见融于整个体制,因而上访和维权普遍没有好结果。而在矛盾解决中恰当地融入第三方力量,便会改变原有的村社格局,使得矛盾有可能在村社内部解决,而内部解决往往代价最小、效率最高。具体经验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结构性束缚下的农民抗争困境
普通农民难以组织起来固然与农民只关心具体利益有关,但是也与两种结构性机制的存在有关。一是在现代化和商品化过程中的“暴力”及所形成的“依附”。[6]卡尔·波兰尼曾经说过:市场经济的进程实际上是要将劳动力、土地、人都商品化的过程中。[7]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作为最弱势群体的农民实际上被日益卷入商品化的进程。实际上工业园区的开发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给当地农民带来很多工作机会,GZ村不少农民都在工业园区以及煤矿工作,因此如果索要补偿款过高或者跟随其他村民去工厂门口堵路则会影响自身的就业。这种状况就使得部分农民的利益与其他村民和村庄集体利益存在不一致,这一分化的状态为乡镇和村委对于征地问题处理预留了操作空间。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暴力”和“暴利”。以地生财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主要模式,而这其中“国家权力的去中心化、中央政府无配套资金的地方事务授权、政府规模的扩大、模糊的财政制度和这种制度所创造的腐败机会”[8],使得地方治理中用土地寻租的动机极大,因而,强行征地事件层出不穷,暴力也不可避免。而如果地方政府和老百姓谈判,那么又面临着老百姓的漫天要价。2011年的调查表明农户将一亩地的价格要到了10万元,超出了地方政府规定的3万元的补偿标准的3倍多。因此城市化又加速催生出了“暴利”和“刁民”。
正是这种特征加之转型中的中国农民由于处于关系网络、市场网络、传统意识形态的交织之中,使得政府也逐渐形成了针对普通农民的分类对待和处理,这种治理手段被称为“捆绑型”治理的手段。[9]这也是多数村庄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人情治理、法治、暴力化治理等手段交叉使用的原因。这种经济环境和治理手段,加之于村民有两种结果。对于普通农民,他们常常是束手待毙;而“精英型”农民却因为懂得“以法抗争”,而状告地方政府,最后却被排斥于整个体制之外,因此他们的斗争策略变成“瞅准机会、适时地制造结构性混乱”,这也是2006年和2009年村庄选举问题周期性爆发的原因。
(二)“精英型”抗争农民陷入“法治化”与“官治化”双失灵困境
在农民抗争的普遍性困境中,普通农民可以忍受,但“精英型”农民却很可能奋起抗争,但通过对整个维权和上访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上访就是“不归路”。“以法抗争”和“青天治理”从本质上都很难有实质效果。
“精英型”农民一旦开始上访,就会发现上访过程其实是不断学习和发现新问题的过程,他们往往会发现更多的地方违规运作,如GZ村村民在上访过程中发现地方政府“以租代征”的情况。案例中显示出农民上访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多就是如此,这是因为农民在上访过程中也在逐步地学习和适应。但由于农民本身缺乏获取实在证据的手段,常使得他们的主张得不到有力支撑,加之不能突破组织和制度困境,常常使他们的诉求得不到伸张和法律的保护。
在“法治”诉求无果的情况下,这些上访者同时也失去了“官治化”的可能。因为“维稳”是政府的硬性考核指标,但凡出现集体上访,地方政府要承担极大的政治压力,因此,虽然是村社内部的事务,上访后却使得上级政府更倾向于掩盖问题而不是公正地解决问题。而对于这些上访精英,除了通常的“拖”以外,还可以施以惩罚,如在GZ村,给上访人的合作社断水断电等。
(三)外部力量介入所起到的撬动作用
在本案例中,可以看到外部力量的介入对于矛盾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撬动作用,外部力量介入改变了原有的力量结构,一方面补足了上访农户证据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引起了上级政府的重视。具体来看,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有效地克服了上访农民的三大困境。一是技术困境。之前其实也进行过审计,但是官方的审计结果显示没有问题,而这一次的审计却发现很多问题,从而找到了突破口。二是法律困境。村委会签署的征地协议和征地过程本身存在很多违法之处,比如说村庄被征用的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民小组,村委会没有权力将村民小组的土地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卖出去。但对于这一基本事实,不熟悉法律的农民却根本不了解。三是制度困境。实际上“官治化”和“法治化”有时候将农民引向了对整体机制的挑战,可是单凭上访的农民却不足以挑战整个制度,这只会让农民踏上“不归路”。如果能在问题出现时引入第三方力量,温和地处理问题,那么矛盾可能在初期就会化解,同时农民也可以在自身权利的维护中,构建良性的治理环境。
四、结论
农民本身力量弱小而且被卷入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浪潮之中,缺少农民自组织力量的发育,这就是农村现实境况的真实写照。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之下,精英操控下的法治化和官治化的顽疾将会直接导致农村社会的病变,也导致农民的被动性上访。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Tsai)的著作就表明,由于农村各种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缺乏监督机制而导致农村容易失衡。[10]这里面第三方的介入所形成的治理结构对农民抗争困境的化解只不过是在制造一个独立的农村公共政治而已,使得它既不会被政府操控,且由于外界的监督也不会被市场侵蚀。[11]
中国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极度复杂而且漫长的过程,这里面各种话语体系也在互相争夺各自的空间,“官治化”或者“法治化”也许只是诸神之争,实质上两者都与农民没什么关系。在这两种争论之中连接农民的社会性纽带消失了,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怎么重建农村社会来抵制各种结构机制引发的抗争问题,这里面其实既涉及到价值重建的问题,又涉及到权力的边界问题。亦如刘伟在《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中指出,村民的群体性活动之所以难以达成,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对村落的介入方式有关,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国家的“不在场情况,国家时而“越位”,时而“缺位”。[12]目前农民抗争问题就同时存在着权力的“越位”与“缺位”,因而使得任何单向度的努力,在不改变既有结构的前提下都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何运用外部力量,如社会资源来介入村社调节之中,就显得很有必要。
本文的案例表明知识分子的参与对于农民的抗争来说,不一定会导致所谓的激化冲突和触犯既有权利安排,而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帮助农民突破结构性机制之下的利益和权力之网,重建农村的良性治理以及理顺农村的社会秩序。其实知识分子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在中国至少是一个很久的传统。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749个村庄调查[J]. 农村金融研究,2007(8):10-23.
[2]温铁军,郎晓娟,郑风田. 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状况及其特征:基于100村1765户的调查分析[J]. 管理世界,2011(3):66-76.
[3] 于建嵘.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 社会学研究,2004(2):49-55.
[4]应星.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7(2):1-23.
[5]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7(5):21-45.
[6]折晓叶.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J]. 社会学研究,2008(3):1-28.
[7](英)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5.
[8]Thomas P. Bernstein,T.& X. Lü.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22.
[9]陈柏峰. 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J]. 中外法学,2011(2):227-247.
[10](美)蔡晓莉,刘丽. 中国乡村的公共品提供:连带团体的作用[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2):104-112.
[11]张静. 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M]. 上海书店,2006:178-190.
[12]刘伟.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85-289.
[责任编辑:赖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14ZDA064)。
王海侠,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李行,福建省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科技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
D668
A
1002-6924(2016)01-15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