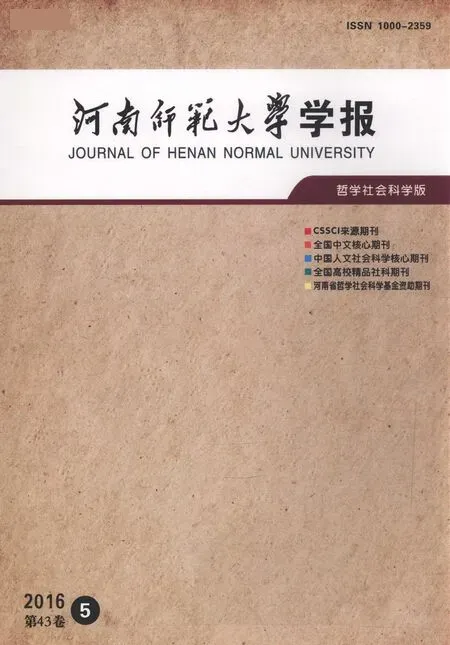国外文学中的贞操观念及其表达
——从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几个长篇小说谈起
周 聪 贤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国外文学中的贞操观念及其表达
——从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几个长篇小说谈起
周 聪 贤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当代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贞操观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谭恩美认同以爱情为基础的非婚性行为,寡妇有再嫁自由、女性遭强暴不属于失贞,男女应共同遵守贞操道德。谭恩美的贞操观孕育了以人为本、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寄予了作者对两性关系“平等、善待、和谐、尊重、忠贞”的审美理想。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贞操观的感性反叛,更是一种理性超越,彰显了作者对个体追求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对女性情欲、贞操、人生命运等问题的热切关注和理性思考。
谭恩;长篇小说;贞操观
当代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美国出版业对新华裔美国作者的兴趣,特殊地讲,要归功于谭恩美。”[1]244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谭恩美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两部儿童文学和一部散文集。她创造的既有永久历史意义又具有广泛商业成功的神奇文学作品震动了美国社会精神的的意识之弦,作品多次荣登美国畅销书榜首,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其中,小说《喜福会》《灶神之妻》和《接骨师之女》均以母女关系为叙述主线,讲述了母亲们在中国大陆的生活波折,以及她们解放前夕移民美国后的生存境遇、与美国出生的女儿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等。在这三部小说中,谭恩美以民国这个传统与现代尖锐对立的时代为背景,塑造了一些离经叛道、具有鲜明个性解放色彩的女性,她们走进了“饮食男女”非传统婚姻形态下的性禁忌领地,应该怎样理解这些女性的行为?又该以什么的标准和态度臧否人物?这是涉及小说文本情节结构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审美情趣的高下等诸多方面的关键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势必触及到作者的贞操观等意识形态的东西。鉴于谭恩美作品中这些乏人问津的问题,本文拟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探究作者对非正常婚姻形态下两性关系的书写内涵及其审美理想。
一、中国传统贞操观的历史衍变
所谓贞操,从现代婚恋观角度来说,是指“夫妇相待的一种态度,是双方交互的道德。”“夫妇之间爱情深了,恩谊厚了,无论谁生谁死,无论生时死后,都不忍把这爱情移于别人,这便是贞操。”[2]163-164贞操观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家庭的产物。剩余财富和私有制的出现催生了一夫一妻家庭制,其产生的“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3]57。为满足此内在需要,为夫者要求妻子对自己绝对忠诚,严格保持贞操,贞操观由此而始。先秦时期,贞操观只是一种相对松散的伦理要求。《周易·恒卦》曰:“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遵守恒久专一的道德对女性来说是吉,而对男性来说是凶,这是理论上对贞操问题的最早表述。事实上,这种男女双重贞操标准主要是为维护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内需,对个体观念和行为制约极为有限,所以,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婚外通奸屡见不鲜,寡妇再嫁也是司空见惯。秦汉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贞操观由维护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内在需求逐渐转变为政治意识形态。儒家提出“从一而终”、“妇人有三从之义”[4]71、“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4]72等贞操观念,“王道三纲”的政治伦理规范将其渗透、扩散到社会文化层面。但由于汉代以降玄学、佛学的盛行及盛唐气象中世俗享乐的需要,儒家的贞操观念一度遭到冲击。所以,此阶段的贞操观念虽比先秦时影响深远,但它仅是作为一种道德观而存在,和其他普通道德的约束力并无二致。总体而言,贞操观念相对宽泛、淡薄。
宋代程朱以后,随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的强化,贞节观念逐渐严酷,贞节的含义由以前的人格自尊演变为生理上的不失身,对女性贞操道德的要求走向异化。“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好女不嫁二夫”[4]75成为束缚女性身心的“紧箍咒”;婚外性行为更是一律以奸论处,严加惩罚;男子“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4]77。总之,“不特有夫之妇须守其贞,即未嫁之女亦须预守其贞,寡居之妇并须继守其贞”[4]79。这种灭绝人性的贞操观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被理论化,贞节按节妇身份分为贞女、烈女、烈妇、贞妇、义妇、义妾、义姑,节烈档次也有高低级别之分。女性在生活中如履薄冰,人性尽颓。在明清五百多年时间内,女性的贞操观一直处于不断强化的状态,程朱理学被发展到极致,社会对女性贞节的要求发展到宗教化、绝对化的程度。“贞操观念的宗教化,就是完全摈弃了人类的理性和事实,而只是迷信于那代代相传的‘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照之仪;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的哲理说教。贞操观念的绝对化就是在贞操的问题上揉入了因果报应的神秘色彩,认为男子若娶寡妇或失贞者为妻,必定会触犯附之于她们身上的披麻星、克夫星等天罡地煞,搞不好会中途夭折的。”[5]368统治者甚至将女子守节与臣子尽忠等同起来,明文规定对各类节妇、烈妇的旌表、奖励措施。道德领域的贞操观一旦受到理念、政权及法律的干预,必将走向病态扭曲和宗教化。在国家力量的推波助澜下,在社会与家庭的塑造、需求、支持下,“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6]56成为全社会遵从的信条。“贞节”不仅幻化为一种文化传统,而且也积聚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心态,慢慢转化为广大女性自然而然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伤肢守节、割股疗夫、夫死殉节等守节方式受到狂热追捧,崇尚贞烈在明清两代蔚然成风,甚至演变为光耀门庭、为地方博取名利的工具。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在不足三百年的明代史上,节烈妇女竟多达三万五千多人,因性侵犯或异性之间的身体接触而自杀的女性达到八千七百人。而清朝仅在雍正三年之前,节烈妇女已多达一万二千余人。及至民国初年,社会对贞操的迷信和固守并未因西方激进思潮的涌入而衰微,反因民族危难和政治纷争而愈演愈烈。北洋军阀政府烦布的《褒扬条例》明确规定:“(一)守节至五十岁以上者,若年未五十而身故,以守节满十年为队;(二)女子未嫁,夫死自愿守节省,(三)烈妇烈女,凡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忿自尽及夫亡殉节者,其遭寇殉节者同”[7]。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民国殉夫殉节之事屡屡发生,并得到大众媒体和舆论的盛赞和褒扬。
贞操观念出现之初本是维护一夫一妻制家庭并生育纯正父系血统的继承人,是人类社会摆脱群婚乱交的蒙昧时代的一个巨大进步,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父权制的发展,它逐渐蜕化为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的一种单向设置,演变成男性强权社会要求女性单方面实行性禁锢的一种道德观。一夫一妻制也蜕变为“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3]58。当厚重的贞操之墙愈来愈紧地包裹着女子的人性时,男性却可以荒淫纵欲,逍遥于贞操的藩篱之外,他们不仅有再娶之义,而且还可以“公然漂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4]71传统的封建贞操观实质上是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物化的结果,女性被视作男性的私有财产,只是宗族延嗣和被动地供男子任意发泄取乐且被任意处置的工具。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生命价值,没有权利和享受,只有义务和奉献。在封建贞操观种种违背人性的清规戒律的桎梏下,女性原本鲜活的欲望和温情被冰冷的伦理纲常所剥夺,无数的青春和生命惨遭窒息与吞噬。针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和畸形的道德观,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僵化变态的封建贞操观进行了无情的口诛笔伐,尖锐指出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8]10束缚中国女性数千年的贞操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批判和否定。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谭恩美作品中出现了背离、颠覆封建传统文化的叛逆女性形象,反映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和大胆抗争。
二、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贞操观
在谭恩美的长篇小说中,作者以略带浪漫色彩的笔触,塑造了一些敢于冲破封建礼教藩篱、勇于追求个体生命意义的“另类”女性。在贞操观问题上,作者不以封建传统贞操观为参照标准,简单化地以单一道德伦理臧否人物的非婚性行为,而是以一种开明、宽容的态度,从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角度对女性非婚姻状态下的性行为予以肯定或谅解,表现出对女性情欲、贞操、人生命运等问题的热切关注和理性思考。
(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前性行为合乎情理
谭恩美认为,理想的两性之爱应该是灵与肉的和谐结合,即情爱和性爱的完美统一。也就是说,两情相悦的爱不应该仅仅是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它还应该包括肉体上的性。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现象,由性行为而产生的性权利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除了繁衍后代,性行为的价值更多是为了爱情和快乐。所以,以爱情为基础的非婚姻性行为合情合理,不属于失贞,它是男女双方倾心爱慕基础上的性爱与情爱的交融,渗透着男女双方之间的感情和理性因素。在《接骨师之女》中,谷流星自幼丧母,身为接骨师的父亲对其疼爱有加,亲自教她读书识字,甚至带她外出行医救人。宽松的成长环境孕育了她自由、无拘无束的性格。及至和刘沪森一见倾心,父亲也尊重她的个人选择。当刘沪森带着自己写的小诗到她家谈情说爱时,这一对大胆的年轻人无视传统婚姻伦理规范的束缚,在没有正式婚约作保障的前提下,他们就“忙不迭地享受洞房花烛之乐”[9]144。同样,《接骨师之女》中另一对年轻人刘茹灵和潘开京也在热恋中提前偷尝寓于爱情中的自然幸福。刘茹灵在亲生母亲去世后被赶出刘家大门,无家可归的她在美国人创办的育婴堂里身兼教师和学生双重身份。于此,她邂逅了优秀考古学家潘开京。志趣相投使心有灵犀的二人很快坠入爱河,尽享鱼水之欢。“我没有感到羞耻或是罪过,只有狂野而新鲜的感觉,仿佛我是在天国遨游,在浪尖上飞翔。”[9]199未婚刘茹灵的首次性爱感受表明:基于两心相照的男欢女爱是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个人追求爱情和幸福的一种表现。这彰显了作者不仅认可女性情欲作为“人之大欲”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赞同乃至怂恿女性以有违常规的“不节”方式释放“人欲”以确保生命质量,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此外,谭恩美也强调人类性行为的社会属性,认为性爱是原则的,人的性行为要遵守必要的道德观念约束,即使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圣洁的性也不例外。所以,谭恩美用婚姻的形式将未婚谷流星、刘茹灵的“偷情”行为合法化,使她们有一个天遂人意、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使其行为得到社会的认同,表现了谭恩美对婚前性行为和女性张扬情欲的理解与默许,对婚姻寄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愿望。
(二)妻子没有为无贞操丈夫守贞的责任
谭恩美认为,贞操是婚姻关系内夫妻间应遵守的道德,贞操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而是夫妻双方面的事。如果妻子对丈夫忠贞不二,那么丈夫也应持同样的态度,若丈夫不这样做,则不配享有妻子守贞的待遇。此外,作者认为,无爱的婚内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这种抽去灵魂的性只是把性对象当作发泄性欲的工具,是将人类的性行为还原为纯粹的动物本能需要的行为,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和尊严,所以,没有爱情的婚姻应及早解除。在《灶神之妻》中,从小寄人篱下的江雯丽不幸嫁给了性变态丈夫文福,饱受身心摧残。在文福眼里,雯丽只是纯粹的泄欲工具而已。为满足自己欲求,文福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多次实施婚内强奸,完全不顾妻子感受,即使妻子怀孕也不能免遭此厄运。残酷无情的性虐待给雯丽生理和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痛苦。更糟糕的是,性变态的文福还是一个性淫乱恶魔,不少女子深受其害。一个不知名的姑娘死于他制造的车祸中;家中十四岁的小保姆因他怀孕,年纪轻轻就走向死亡;一个叫敏的姑娘被他像小老婆一样乱性,最终凄然离世;他还经常与小学教师、街头妓女等发生关系。“他的习惯就是找一个女人,玩几星期,然后就把她抛弃了。”[10]353忍无可忍的雯丽最终设法逃出文福的魔掌,在没有和他离婚的情况下,携子投奔情人吉米·路易,过上了浓情蜜意的神仙眷侣生活。在此,谭恩美虽未旗帜鲜明地对雯丽的行为予以赞扬,但仍以含蓄的理解和首肯委婉地表明了“若丈夫没有贞操,不知道关爱妻子,夫妇之间已没有爱情恩意,妻子便没有守贞的责任”的思想。《灶神之妻》中还多次以雯丽在与情人吉米的性爱中获得的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为叙述焦点,强调她如梦初醒般的惊喜和因此而焕发出的生命活力。这些描写无疑暗示着:贞操并不是女性婚恋生活的第一准则,更不是目的,它可以灵活地服从于人的幸福原则——生命的快乐是比贞操更重要的东西。在此,谭恩美淡化贞操观,但并不意味着宣扬无节制的性自由,她同样将江雯丽的“外遇”行为合法化,让吉米与雯丽的幸福婚姻成为雯丽婚内出轨行为的最终归宿。在谭恩美看来,无论未婚已婚,只要其性行为是由情而发,而且最终是以婚姻为指向,就不能被视为失贞、失节。
(三)寡妇再嫁不属于失节,女性遭强暴身体被污不是失贞。
谭恩美认为,寡妇再嫁与否要取决于其本人的自由意志,要取决于个人境遇、家计、体质、恩情。如果妇人对已故丈夫有割舍不断的情义,她会不忍再嫁;如果已有孩子,且家道殷实,她不必再嫁;如果年事已高,她可能就无法再嫁。但如果她年纪尚轻,孩子幼弱,家道艰难,那么为个人计,为人道计,为社会计,她都应该再嫁。当然,每个个体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寡妇也不例外。寡妇守节或改嫁完全是个人私事,任何人不能强迫干预,只要本人愿意,寡妇再嫁行为就不属于“礼不可逾”、“义不可免”,寡妇本人也不能被冠之以“淫妇”,更不能用忍心害理的“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论调一言以蔽之,这彰显了作者对女性人格尊严的尊重和对其人生幸福的真诚关注。《喜福会》中,许安梅母亲本是位明媒正娶的妻子,但身为读书人的丈夫却英年早逝。年轻貌美的她本打算心无旁骛地守护一双儿女在娘家度日,然而却不幸惨遭强暴。于此,她却只能黯然隐忍,三缄其口,因为在男权至上的封建观念里,“凡是涉及到男女私通,女性总是被视作该受惩罚或该负主要责任的一方。把女性物化的倾向往往将她当做一个性对象,而不是当做一个人,当女性处于奴隶地位、被剥夺了人权的时候尤其如此。”[4]108但在民国那些依旧倡导女性节烈风气的年代,众人投来的风刀霜剑终使她无立锥之地。为了一双年幼儿女的幸福和安全,她委身富商吴青为妾。在此,作者认可安梅母亲为了抚养幼子的再嫁之举,因为在那个男权中心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子生长深闺,以无才为美德,即偶有才貌者,社会亦无相当职业,足以容身。除仰男子之鼻息外,生计即难维持。”“女子甘居下流,为人簉室……实经济压迫。”[11]当为吴家生下唯一的男孩,她与前夫的孩子仍得不到她期望的照顾时,她故意选择在小年夜吞生鸦片自杀,以此胁迫吴青答应将其与前夫的儿女视为己出。安梅母亲用对自己身心的暴力形式成就了儿女的未来,呈现了她广袤无垠的母爱。她的再嫁行为不是失节,值得肯定鼓励,表现了作者以个体为本位、尊重人性的情怀。
对于那些不幸遭到男性强行霸占、身体被污者,谭恩美不认为她们失去贞操,其人格尊严并没有降低,更谈不上为其家族蒙羞。社会对遭此厄运的受害者应该怜借,而不是轻视甚至迫害。《灶神之妻》中,在江雯丽生孩子住院期间,其丈夫文福屡次强迫年仅十四岁的小保姆与他发生关系,并使她怀上了孩子。当小保姆没打招呼悄悄离开后,江雯丽十分担心。为防止意外发生,她四处寻找其下落,当最终在一间破屋里找到她时,江雯丽给了她一笔钱,希望能在经济上接济一下这个弱小的姑娘。在作者看来,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女孩子根本没有力量阻止恶人的强暴,她的遭遇只是对残酷力量的无奈的屈服。作为一个被迫情境下的身心受害者,她不应该承受任何的非议与鄙视,不应该遭受社会的孤立与唾弃,罪不可赦者应该是无耻的施暴者文福。所以,当未成年的小保姆自行流产致死时,懦弱的雯丽第一次冲文福发火,愤怒地指责文福:“她死是因为想把你的孽种弄下来,你这头猪!”[10]261。表现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对懦弱、无力反抗而遭到侮辱的女性的保护。
(四)男性也应该遵守贞操道德
谭恩美认为,贞操是爱情的基础和社会的公德,是男女都要恪守的个人修养。它不应是对女性的单向要求,认为女子失贞就要遭谴责,而男子偷情“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3]71男女双方是平等的,不是一方支配或占有另一方。对于那些为了满足一己之欲而不择手段、毁人节操的淫徒恶棍,谭恩美总是毫不留情地安排他们受到嘲讽、道德谴责和现世报应的人生命运,彰显男性淫乱的恶果。《喜福会》中,顾映映的前夫是一个典型的性淫乱者。他与不三不四的女人发生关系,从来就没有将自己的妻子放在眼里。“他有好多姘妇:舞女、美国太太、妓女、甚至他的一个很年轻的表妹。”[12]221作为对其恶行的惩罚,顾映映就打掉他们尚在子宫中的孩子,让那个淫棍丈夫落个断子绝孙的下场。《灶神之妻》中,谭恩美无情批判了淫乱无度的文福造成的恶果:他的两个女儿不幸夭折,唯一的儿子染上急性传染病,一天之内就死了,最终落得个无子无女的凄惨下场。《灶神之妻》中的另一位男性家国,则为其始乱终弃的行为承受一生的道德煎熬。家国在洛阳国民党军队做飞行员时,他和当地一个姑娘偷食禁果。可当那个姑娘临产要生孩子的时候,家国却不肯娶她,任凭姑娘低三下四求他也无济于事。在俩人的拉扯中,可怜的姑娘难产毙命。姑娘死前的愤怒诅咒“我们一死,你也活不了,我们母子俩要把你从天上拉下来”[10]177使家国满怀惶恐不安。为了减轻自己的的恐惧,家国娶了姑娘的妹妹胡兰。而胡兰“嫁给他就是要他这一辈子不得安生,要他想到我姐,想到他做的孽。”[10]177虽然家国后来对姑娘的死“是那么后悔,那么悲伤”[10]177,虽然他待姑娘的妹妹胡兰很好,给她买好衣服,纠正她的纠正她的举止,从不嘲笑她,虽然胡兰也原谅了他,但他们结婚多年,胡兰却一直没有怀孕,而且抗战一结束,家国就染上鼠毒迅即死去,而胡兰在新嫁他人不久就怀孕生子。在谭恩美看来,上述非婚性行为的发生固然是涉及男女双方的事情,但男性作为主动方或过错方应对女性负主要责任。他们遭遇现世报应是祸反及身、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谭恩美反对纵欲滥淫,以及对淫邪恶人的谴责,体现了作者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对男女两性关系的理性关照。
三、对谭恩美长篇小说中贞操观的评析
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贞操观不仅是对封建传统贞操观的一种感性反叛,而且是一种理性超越。谭恩美既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认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生俱来,又考虑到欲望实现过程中的社会道德要求。她认为性与爱相辅相成,爱情是性行为的基础,性离不开爱,性也离不开道德约束,任何非婚性行为最终都应回归婚姻,回归家庭。其次,谭恩美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的自由、平等,倡导充分发挥个体生命价值的“个性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人性的回归,从而使个体真正实现做人的尊严,享有更完善的人性,彰显了人的精神解放的重要价值。此外,谭恩美摒弃了男权文化下封建贞操观对女性的单向度设置,从男女平等的角度观察女性,以让女性摆脱苦难为出发点,使“贞操”成为一种朴素的道德观,不再具有制度性的强制力;在凸现女性的自我觉醒和生命觉醒的同时,使女性的抗争闪耀着追求人性的精神光辉。
谭恩美的贞操观符合民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民国时期,国门开放,人心思变,社会原有文化的基本价值趋向发生了位移,社会结构及伦理观念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传入以及城市与商业化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逐渐向近代化转型,社会原有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与此同时,社会宽容度明显提高。反应在贞操问题上,以往被传统伦理道德严重压抑的人的本性欲求和自我空前觉醒,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关注,性观念比较开放。“从一而终”的封建传统贞操观遭到了摧枯拉朽式的否定和批判,并在现实生活中较大范围内受到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背弃和颠覆。具体而言,真正能从思想上否定封建贞操观念并敢于以自身行动作出回应者主要是城市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少数知识女性,而大量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则因生存所迫不自觉地汇入到这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批判和颠覆封建贞操观念的潮流中,而非基于对不合理的封建传统贞操观念本身的清醒认识所做出的选择。究其原因,虽然当时的社会文化处于转型期,但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交锋中,封建社会形态还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封建伦理文化依然是主宰社会文化的主流,如影随形地沉潜在多数人的头脑中,使其观念、情感、理想依旧蹒跚而行在封建社会的生活轨道上,即使在充满现代特性的五四作家的潜意识里,封建传统文化的桎梏同样根深蒂固。五四时期,不少男性作家的贞操观呈现出矛盾性,他们在性观念上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但对性开放的女性却持鄙夷的态度;他们对压迫女性的传统贞操观给予无情批判,但作品中的男性却打着恋爱自由的旗帜追求婚外恋,而要求女性恪守贞节。此外,女性缺席、男性话语霸权现象也是作品的常态。这折射出男作家实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封建男权思想的羁绊,他们对封建传统贞操观仍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在五四女作家笔下,描写男女自由恋爱的题材很多,但人的本性欲望问题却讳莫如深,甚少涉及。封建传统贞操观的毒瘤可见一斑,这是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五四女儿的时代局限性。
谭恩美对民国贞操观的书写寄予了她对两性关系的审美理想:两性之间的关系应是平等、善待、和谐、尊重、忠贞。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美国历史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在这次以男女平等为基调的女权运动中,女性要求改变自己的从属地位,建立“无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此次运动动摇了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作为这种社会结构支柱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改善和提高当代美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以及家庭中的地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次运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性解放就是其中的副产品之一。作为女权运动在性权利方面的具体表现,性解放的宗旨是追求独立、自由、健康的性生活,将性和爱结合起来,使男女平等享受两性关系。性解放运动兴起之初,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遭遇解构,人们摆脱了性愚昧和性禁忌,开始重新审视处女贞操、重视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重视性快乐等,这对女性冲破人身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具有进步意义。但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性解放逐渐背离初衷,走入性放纵的误区,对传统的美国婚姻道德观念和家庭结构造成严重危害,引发了诸如性生活混乱、同性恋、离婚率激增、非婚生儿童增多、家庭教育职能骤降、青少年犯罪现象加剧等一系列道德危机和社会问题。最为严重的是,性解放造成全球范围的性传播疾病蔓延,出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性艾滋病大流行。
性解放使美国社会付出了惨痛代价,它迫使人们开始反省和检点自己的性行为,重新审视性道德的价值,积极重建健康向上的的两性关系。亲历了性解放恶果的谭恩美在禁欲和纵欲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她尊重个人的性权力,肯定“人欲”的自然属性,又强调“人欲”的社会属性,让爱和性同时回归家庭,在家庭内部实现性与爱的共融、平等、忠贞、和谐,实现两性做人的神圣与尊严。
谭恩美以当代华裔美国人的身份书写的民国贞操观超越了中国传统贞操观狭隘的贞操意识,体现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崇尚独立、自由,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对我国当代两性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2]李心年.名人谈性[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王歌雅.中国婚姻伦理嬗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石方.中国性文化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6]张廷玉.明史:卷三百零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袁世凯.褒奖条例[N].政府公报,1914-03-12.
[8]鲁迅.鲁迅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谭恩美.接骨师之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0]谭恩美.灶神之妻[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11]谭志云.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妾的权利及其保护[J].妇女研究论丛,2009(5).
[12]谭恩美.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海 林]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26
2016-01-19
I106.4
A
1000-2359(2016)05-0149-06
周聪贤(1967-),女,河南西峡人,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