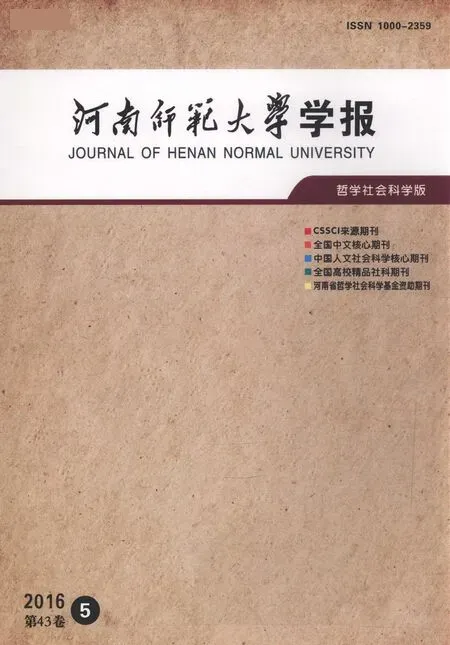教与宗教:康有为对教之概念的热衷与对宗教之概念的拒斥
魏 义 霞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教与宗教:康有为对教之概念的热衷与对宗教之概念的拒斥
魏 义 霞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一词是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一起在中国出现的。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与宗教近似的概念除了教化,便是更笼统的教。就康有为所使用的概念来说,相对于宗教或教化等概念,他显然更热衷于教之概念。康有为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上的新旧交替在概念上的反映之外,主要出于以源自中国本土的教排斥日本之宗教概念的目的。康有为所讲的教既包括宗教,又包括教育。这一做法在使教泛化的同时,淡化乃至模糊了教与学之间的界限,导致教学相混。
康有为;宗教;教;教学相混
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一词是随着西学的东渐和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一起在中国出现的。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与宗教近似的概念除了教化,便是更笼统的教。就康有为的思想来说,新旧蜕变的性质除了表现为理论来源和内容构成上的中西杂糅、古今和合之外,还集中表现为对教之概念的界定——如果说新旧蜕变的性质属于近代思想的共性的话,那么,康有为对教之概念的界定则带有强烈的康氏印记。这是因为,教之概念源远流长,在先秦典籍中频繁出现。自东汉时期起,道教、佛教的流行更是使教除了教化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内涵。就康有为所使用的概念来说,相对于宗教或教化等概念,他显然更热衷于使用教之概念。可以看到,康有为一面从不同角度拒斥宗教一词“不典不妥”,一面对教钩沉索隐,探源释义,将教与宗相剥离。康有为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上的新旧交替在概念上的反映之外,主要出于以源自中国本土的教排斥日本之宗教概念的目的。康有为所讲的教既包括宗教,又包括教育。这一做法在使教泛化的同时,淡化乃至模糊了教与学之间的界限,导致教学相混。事实上,他对教之概念的热衷与对宗教概念的排斥互为表里,目的是凭借教之概念为孔教正名。
一、教宗分疏
对于中国人来说,宗教概念是舶来品。就对宗教的态度和概念的使用来说,康有为显然更热衷于教之概念。事实上,他不仅对教之概念情有独钟,而且对教具有自己独特的界定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对教之释义本身就蕴含着他的宗教理念和宗教主张——甚至可以说,康有为热衷于教之概念具有排斥、解构宗教概念之意:一方面,他指出,教与宗不可相提并论而名为宗教,宗教一词不能成立;另一方面,康有为不惮其烦地从不同角度反复对教进行释义,同时指出宗具有固定内涵,借此将教与宗剥离开来。
康有为坚决抵制作为日本译名的宗教概念,理由是教与宗在中国文化中是分离的,不可将教与宗相提并论而称为宗教。对此,他论证说,从出现来看,宗教一词“不妥”,中国自古并无宗教之说,宗教一词从日本译文而来;而日本之所以会出现“宗教”一词,则是在效仿中国文化时不解其意而误读所致。对于这一点,康有为解释说:“日人之于华文训诂多所未惬……此今人述日文而视为不刊者,实考之而皆极不通者也。夫宗之与教二文本不相关,中国自古名词有言祖宗者,有言宗庙者,未有言宗教者。日人之为此名词也,始生于佛学者也。自唐世佛学分离,于是《传灯录》分五宗,乃有禅宗、天台宗、慈恩宗、华严宗之目也。其后禅宗中又分宗曰临济宗、沩山宗、仰山宗、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所谓宗者,犹战国诸子之分曰某子,后世汉宋之争曰某学,又曰某派、某门云耳。又如人家族姓所谓继别为宗,太史公所作《五宗世家》,今人所谓某房云耳。……日人以其复文之俗习读传灯之书,乃取宗字加于教上。盖当时教者专指佛教言之,宗者专指佛教下诸宗派言之也。教大宗小,以宗加教上已大不通矣。”[1]126依据他的说法,日本人对中国文字的训诂大都文辞不通(“未惬”),翻译自然漏洞百出,宗教一词便是如此。在此基础上,康有为进一步挖掘了日本生搬硬造宗教一词的根源,指出日本之所以造出宗教一词,是对中国文化曲解的产物,缘起于中国佛教的东传——总之,与中国佛教的宗派之分密切相关。他进一步解释说,佛教尽管产生于印度,却在传入中国后才渐渐有了宗派之分。在中国佛教的语境中,“教”指佛教,“宗”则特指佛教内部的不同派别。《传灯录》分五宗,遂在佛教中有了禅宗、天台宗、慈恩宗和华严宗等宗派;后来,佛教以及禅宗内部的宗派之分越来越细——仅以禅宗为例,其中又分为临济宗、沩山宗、仰山宗、云门宗、法眼宗和曹洞宗。由此可见,宗在佛教中是宗派之义,原本就无法与教相提并论或等量齐观。最简单的道理是,教大而宗小,教包含宗,二者并提合称原已不伦不类。更为重要的是,宗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且拥有相对固定的内涵,如言祖宗、言宗庙、言某房以及家族中继别为宗等等。正如《史记》中所讲的五宗世家都与宗法血缘联系在一起一样,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始终与宗法密不可分,而与教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也与宗教无涉。
经过上述分析,康有为得出结论,宗教一词不能成立。对于这一点,他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宗与教原本毫不相干;第二,教大宗小,日本人加教于宗上宗教一词的文意不通。如此说来,宗教一词的出现原本就是一个笑话。
二、揭露宗教一词不妥
康有为的上述解释似乎撇清了教与宗之间的关系,在表明宗不可与教并称为宗教的同时,却引发了新的疑问:既然宗与教原本各不相涉,日本人为何将二者拉扯到一起而生编硬造出宗教一词?对此,他的解释是,问题恰恰就出在日本人不谙中国文化之旨,故而在解读中国文化时生搬硬套,将宗加于教之上,于是出现了宗教一词。沿着这个思路,康有为进一步追踪日本臆造宗教一词的文化心理和过程,以期从源头处解构其合理性。他指出,日本好用“双字”,也就是“重文”“复文”,习惯以“复文”之俗诵读佛教经典。出于这一习惯,他们便将原本是“单文”之“教”改为“重文”之“宗教”。这样一来,日本人使原本作为“单字”的教变成了双字之宗教,并且用作为双字之宗教一词指称作为“单文”之“教主、立教之教”也就不可避免了。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鉴于由教蜕变为宗教是日本的“重文”之俗使然,康有为则将排斥宗教一词的重心转向从文字的角度进行分析,借此揭露宗教一词在语用上、语法上“不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
故日人之加宗于教以为名词,义不可通。夫欧人文法无合两字义为一字义者,稍有重复字义以为极劣,其在蒙学,蒙师亦即以笔涂之。中国古者形容之词行文偶有一二,至六朝人之文必用骈语凑足字数。野僧不学,当译佛典乃全用双字。日人不知其本,无论述何字义、行何文词,必用双字。若如其例,则“天命之谓性”必当曰“天帝命令之性质”,“大学之道”必当曰“广大教学之道术”,“在河之洲”必曰“止在河水之洲渚”,“若嵇古帝尧”必曰“顺若嵇考古先帝尧”矣,“乾元亨利贞”必曰“乾元始亨通利益贞正”矣。此在注家训诂则可,否则岂复成文乎?在中文固无理而可笑,在欧人则以为鄙劣而不通。今以日人所学我数千年文明之汉文,我乃舍而从日人不妥可笑之名词,愚陋甚矣。[1]127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宗教一词的出现是从“单文”到“重文”以讹传讹的结果,所以带有与生俱来的硬伤,同时还有语法、语用方面的舛误。原因在于,日本人使用的宗教概念对应的是西方之厘利尽(religion),当初之所以用宗教翻译译西方之厘利尽(religion),是因为喜欢“重文”“双字”——这与习惯于“重文”“双字”,当初将中国之教译为宗教是一个道理。问题在于,经过日本人的翻译,西方之厘利尽原义顿失。这是因为,日本人以宗教译厘利尽的过程包含两个偷梁换柱的步骤:第一步,先将作为“单文”的中国之教译为“重文”之宗教;第二步,再以“重文”之宗教译西方的厘利尽。在此过程中,教在语法上、字面上经历了一个由“单文”到“重文”的嬗变过程。康有为强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双字、骈语、重文都不是主流——或者不入流,或者被视为错误。在中国,古文字原本是单文,六朝时才盛行骈文,那是为了以字凑数。僧侣不学无术,喜欢用双字译佛典,双字之风由此渐兴。同样,在厘利尽之发源地欧洲,西方人在语法上并没有合两字义为一字义者。即使是在儿童教学中,也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因此,一旦发现儿童使用重复字便认定为语法不通,老师即令改之。日本人不考中国文化之本,无论用字、译文皆用“双字”。日本人以宗教一词翻译从中国传入的佛教特别是将教与作为佛教之派别的宗混为一谈,原本是对中国文化不明就里而误读、误用的结果,以宗教译西方之厘利尽亦是如此——从中国文法来看“无理而可笑”,从欧洲语法来看则“鄙劣而不通”。
康有为的上述解释只为证明一个结论,那就是:宗教一词“不典不妥”,不能成立。基于这一结论,他对宗教一词极力排斥之,号召中国人拒绝使用宗教一词。于是,康有为写道:“是故宗教二字之不典不妥,在日人已不可,况在吾国人,必不可引之于笔端。吾国数千年文词只有教字之一字一义,吾国人行文只可曰教,安有宗教之不妥贴而令人迷惑者乎?”[1]127在他看来,日本造出的宗教一词原本就无任何权威性、合法性,对于中国来说更是情理不通——如果使用不妥帖的宗教概念,便会由于文辞不通,令人迷惑。
三、指责宗教一词不典
对于康有为而言,宗教一词不仅由于文意不通而“不妥”,而且由于在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任何根据而“不典”。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澄清教之原义,以便更好地还原、界定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义。康有为给教下的定义是:“夫教者中国之文词,教者效也,凡学、觉、交、效、爻、孝皆从此义。大意以二物相合,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一人先立一道术,后人从其道而效之云耳。”[1]126在这里,通过厘清教之本义,他训教为效,给教下了一个“教者效也”的定义,并从中引申出教的“二物相合”之义。这样一来,就教的内涵来说,“凡学、觉、交、效、爻、孝皆从此义”。沿着这一思路,康有为对教之内涵的揭示、诠释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先知先觉觉后知后觉者,即可谓之教。第二,举凡一人创立一种道术,后人从其道而效仿之,皆可归入教之范畴。
沿着教即一人创教、后人从其道而效仿之的思路,康有为进一步由教之效引发出教之道的含义,从而宣称“教者犹道也”。对于教之道德内涵,他解释说:“夫举国数千年皆尊奉其道而效之,不谓之有教、不谓之教主而何?及佛、道之起,于是有各从其道术而效之者,故谓之佛教、道教,合儒教言之曰‘三教’。中国虽尊儒而辟佛、道,然既有此教,即不能不谓之为教。……故教者犹道也,佛典称九十六外道即九十六外教。道与教皆有是道、有是教云尔,苟非率天性而修之道、教未必皆精美也。故教乃事理之一名词,有之非必足贵也。有教未必足贵,然苟非野人若禽兽则未有无教,若无教则惟野人及禽兽耳。惟教术之不一故有美恶,亦惟教术之不一而有人神。然无论其教之术如何,终不能不谓之为教也。”[1]126如果说“教者效也”是康有为从逻辑上、学理的维度给教下的定义的话,那么,“教者犹道也”则是他从经验上、实践的维度给教所下的定义。正如前者厘清了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义、成为权衡宗教的标准一样,后者则是康有为叛教的标准。可以看到,正是以“教者犹道也”为圭臬,他将儒教、道教和佛教以及佛教典籍中的九十六外道都归入教之范畴。这一做法从狭义上说旨在为孔教正名,使孔教与道教、佛教一样拥有了教之名;从广义上说,则在日本的宗教之外找到了叛教标准,从而为孔教、儒教代表的中国之教争得了话语权。
康有为强调,从源头处厘清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义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甚至是界定、诠释教之本义的不二法门,当然也是判定日本之宗教一词不能成立的获胜法宝。其中的奥秘在于,教不是日文,也不是西文,而是中文、国文。这一不争的事实本身即意味着要明确教之内涵,必须对中国本土文化追根溯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探究、还原教的本义。
四、探究教之本义
厘清了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义、证明了宗教一词由于在中国古籍中找不到证据而“不典”之后,康有为对作为日本宗教一词之滥觞的厘利尽予以探析,旨在从发源处明辨“宗教”一词的本义。他指出,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与中国之教意思相近的有一词,曰:厘利尽(religion),而厘利尽正是日本宗教一词的出处所在。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特意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教就等于宗教,当然也不等于说日本人将与中国之教大致相似的厘利尽翻译为宗教就是正确的。为了证明日本人将厘利尽译为宗教并不妥帖,他对厘利尽一词进行剖析,通过还原厘利尽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原初含义,证明日本人以宗教一词作为其译名的不正当性和不正确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写道:“今日人宗教之名,本于译欧美之书而定此名词。盖因欧人向宗耶氏,别无他教,故其名曰厘利尽(religion)。厘利尽者,谓凡能树立一义、能招徒众者之义。然则与中国所谓教别无殊异,所含广大。或谓含有神道之义,则因耶氏尊上帝,而欧土之教只有耶氏,故附会之,并非厘利尽必限于神道也。若令厘利尽必限于神道,则当以神道译之,而不可以宗教译之;又或以神教译之,而不可以宗教译之。”[1]126-127依据他的剖析,日本宗教之名源于对厘利尽的翻译,而厘利尽在欧美文化语境中原本是“谓凡能树立一义、能招徒众者之义”。由此不难看出,作为日本宗教译名之源头的厘利尽,其本义与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含义如出一辙,他将之概括为“别无殊异”。更为重要的是,厘利尽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本义表明,正如教在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名义奥赜一样,厘利尽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内涵丰富、内容广大,范围无所不包——凡能树立一义者皆可名之,凡能招徒聚众者亦可名之。与西方本土意义上的“宗教”(厘利尽)大相径庭的是,经过日本人的翻译,原本无所不包的厘利尽在译名宗教的同时,含义被狭隘化,最终等同于神道、神教之义。在此基础上,康有为进一步指出,日本人在翻译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将原本含义广大的厘利尽狭隘化为神道、神教的情况,根源有二:一是由于基督教崇尚上帝,一是由于欧洲大陆盛行的宗教只有基督教——一言以蔽之,源于用基督教的教义附会宗教之义。对于这种状况,他指出,厘利尽含有神道、神教之义,却不仅仅限于神道、神教;退而言之,如果厘利尽只是指神道、神教的话,那么,日本人在翻译厘利尽时就只能以神道或神教译之,而不能以宗教译之。
议论至此,结论不言而喻:日本人以源于佛教宗派的“宗”加诸教之上,硬造出宗教一词是错误的。如果说宗教之词已经“不典不妥”的话,那么,以宗教译西方之厘利尽更是错上加错。这样做使厘利尽的内涵急剧狭隘化,最终等同于神教、神道。更有甚者,日本人在使神道、神教成为宗教的第一要义的同时,反过来以神道、神教界定、诠释宗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康有为断言:“今日人以佛氏宗教之词译耶氏厘利尽之义,耶少变佛而本出于佛,回少变耶而实出于耶,其同为神道固如一矣。然若限于神道为教,则宇宙甚大,立教甚多,岂必尽言神道者?凡能树一义以招徒党而传于后者,苟非神道则以何名之?以何译之?既无他名词则亦不能不以哩利尽目之,则哩利尽亦为凡教之广义,而不能为神道之专词矣。”[7]127这就是说,凡树一义招徒聚党或学说传承后世者,均谓之教((religion),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厘利尽、哩利尽)。可见,教属于泛称,故而范围广大;这表明,教不可为神道所专有,因为神道是专称、特指(“专词”)。在此,康有为旨在强调,宇宙之大,立教甚多,不能皆言神道。由此不难想象,如果将教限制在神道之内的话,将会引发诸多问题。例如,既然立教甚多而非皆言神道,那么,如果将教只限定在言神道之内的话,非言神道之教何以名之?何以译之?如果由于除了宗教之外,别无其他名词而不得不归于厘利尽的话,便意味着宗教之含义宽泛广大,必不限于神道,自然也就不得为神道所专有。
借助对日本宗教一词的出处——厘利尽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之本义的厘清和解读,康有为着重阐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西方所讲的宗教(厘利尽)与中国所讲的教在内涵上十分相近,并且皆含义广大;另一方面,中西方的宗教形态和样式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存在佛教、儒教、道教和白莲教等多种宗教形态,而欧洲存在的宗教形态较为单一,以基督教为主,甚至可以说盛行的只有基督教这一种形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之基督教尊崇上帝,有人便从崇尚上帝的角度理解厘利尽,进而以神道、神教释宗教(厘利尽)。其实,无论中国之教还是西方之厘利尽都不限于神道、神教,二者也共同证明并非宗教只限于尊崇上帝。换言之,以神道译宗教与以崇尚上帝释厘利尽一样,是妄加附会的结果。假设宗教只能指尊崇上帝的话,那么,便应该将作为日本宗教一词之滥觞的厘利尽译为神教、神道而不应该译为宗教。
对于康有为来说,问题的尖锐之处在于,无论宗教一词如何“不典不妥”,谬之千里,但其极为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并且给中国造成了既成危害——这一点也是他对宗教一词耿耿于怀而极力拒斥的原因所在。有鉴于此,如何解释宗教一词的盛行以及成因便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对教之释义将重点放在厘清教的本义以及宗教一词的由来上,经过解构宗教一词的合法性为之祛魅。于是,他在探本溯源、钩沉索隐中一面逐层揭示宗教之歧义,一面深入挖掘教产生歧义的原因。对于这个问题,康有为在将宗教一词出现的根源归结为日本对中国文化误解的前提下,进一步将宗教在中国流行的直接原因说成是中国人步日本的后尘,由于对日本的盲目崇拜而以讹传讹。通过上述分析,康有为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日本人在以宗教一词翻译西方的厘利尽(religion)时,由于基督教的盛行并且因为基督教尊崇上帝而带来了两个相应的后果:一是使宗教(religion)成为基督教的代名词,一是使厘利尽一词涵义尽失,变得内涵不再广大。第二,因为西方只盛行基督教这一种宗教形态,尊崇上帝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所以,日本人将在西方原本是泛指的厘利尽与崇尚上帝(神)混为一谈,最终将泛指之宗教演绎为特指之神道或神教。第三,由于日本文化受佛学影响颇深,并且喜欢“重文”,便在译文时将中国的“单文”之“教”译为“重文”之“宗教”。这本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邯郸学步的结果,没想到中国译名却反过来对日本之译名亦步亦趋。正如对于本该是“操体”的体操等等名词沿袭日本译名之舛误一样,中国不仅在用语上、概念上以宗教翻译、界定源自西方的厘利尽(religion),而且在内涵上、理解上以神道、神教释宗教。
五、反观中国之教
无论是康有为对教之释义还是对宗教的拒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凭借教为孔教正名,为中国之教争得话语权。这一理论初衷和致思方向决定了他所讲的教必定要落实到中国之教上。事实正是如此。通过对教之释义和西方之教的考察,康有为坦言,中国与西方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日本人对于religion的宗教之译名即便对于西方或可,对于中国则不可。对于其中的原因,他特意给出了如下解释:“故如日人之名词,无一而可也。今日人之号名学派译自欧人,自宗教外有哲学、政治、教育等名词,而以宗教为神道、神教。中国之大教主孔子者既非神道、神教,则无以名之。而孔子又适四通六辟无所不在,故谓之曰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也。夫以欧人自罗马中绝,仅有三数百年之学术复光,其阅历至浅,本不足该摄宇宙。至百年来则又书籍太多,业难兼该。故欧人于其十九纪之人才多专门,而少如彼十八纪之通学者,时为之也。故彼今之俗,政党之政客日夜运动,无少休息,机谋日出而德心浅,奔走应酬日多而学问浅。故为政客者不为学者,为学者则教授穷理不为政客,几若绝域而居。而我中国则实无此数者之分……故日人所译述欧人之名词,在彼欧土则可,在我则大不当也。”[1]128康有为的解释试图让人相信,之所以以宗教译西方之教(religion)或可、译中国之教则不可,奥秘在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各自拥有自身的学科分类系统——“号名学派”,日本人在以宗教译西方之厘利尽的同时,又在宗教之外加设了哲学、政治和教育等等学科。而中国历来以经史子集作为分类系统,素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囊括宗教、哲学、政治与教育等分门别类的学科划分。这样一来,如果将中国之教译为宗教或宗教所指的神教、神道的话,便遮蔽了中国之教其他方面的内容。
与此同时,康有为强调,宗教译名的可或不可不仅表明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学科分类系统,而且表明中国之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远非西方可比。一方面,就西方的学术状况而言,学科分类泾渭分明,既由于擅长分门别类的研究而多专门、专业人才,又由此导致专门人才有余而通学之才不足。对此,他陈列了三条理由:第一,西方文化在罗马时期中绝,此后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再度崛起,如此算来也不过三百年。仅三百年的历史表明西方学术阅历浅薄,远不足称博大精深。第二,西方近百年来学术兴盛,却由此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发展太快而新书太多,令人难以兼通。因此,西方在十九世纪多专门人才而绝少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兼通各门学科的饱学之士。第三,雪上加霜的是,当今政客将精力投入到政治运动之中,机谋出而德心浅,忙于应酬而荒于学术。以上种种原因造成的最大弊端就是政治与学术不能兼得。于是,在西方出现了政治家与学问家不可兼得的现象:政治家不能成为学问家,而学问家亦不能成为政治家。另一方面,就中国的学术状况而言,情形与西方大不相同,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学科壁垒和政教之分。这不惟不表明中国学术落后,反而是中国学术的优长所在。具体地说,由于素来无政客与学者的截然划分,中国并不存在像西方那样的政教二分,甚至不存在宗教与教育的明确界线。这奠定了中国学术的博大精深,可以使一人集宗教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于一身。
在凸显中西学术之别的前提下,康有为特别强调,孔子的思想“四通六辟无所不在”,孔子兼哲学家、政治家与教育家于一身。这既证明了中国之教的内涵广大,又突出了中国之教的特殊性;同时沿着孔子是中国教主的思路,大体上框定了中国之教的宗旨、内容和特色。
六、教学相混与教之泛化
康有为认为,宗教一词除了语法不通、“不典不妥”之外,还在语用方面存在致命弊端。这集中表现在,使中国之教、西方之厘利尽的内涵变得狭隘,广义尽失。这一认定促使他在排斥宗教一词的同时,热衷于使用教之概念。在康有为那里,教是一个十分笼统、博大的概念,包罗万象,宗教、教育皆囊括其中。换言之,教既包含宗教,又不限于宗教。在他的视界中,教与中国古代的教化一词相仿,与其说指宗教,毋宁说更接近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文明、文化等概念。对教的这一界定使教在他那里最大程度地被泛化,外延大,内涵广,不仅包括教化、教学和学术,而且包含教育、宗教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内容。
接下来的问题是,由于教中既有宗教,又有学术,康有为本人却始终没有对教与学予以区分,致使二者处于相混状态。他本人对于教与学也是混用的,对于这一点,下列说法即是明证:
是时诸子并兴,而儒与杨、墨三教最大,学者互相出入。兼爱甚,则厌而思静,故必归杨。为我甚,则天良时发,故归于儒。有教无类,来者不拒,不必问所从来。其道广大,乃可以化异道而归一,其或门墙自高,责其既往,适以自隘其教而已,故孟子非之。佛氏之起,皆招梵志,此传教之大要也。[2]498
墨子虽异孔子之道,而日以利天下为事,故《吕氏春秋》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盖与孔子有同焉。子莫无考。《吕氏春秋》曰:皇子贵衷。衷者,中也,当即子莫执中,盖类孔子之道。然无权衡其间,不知精义入神之学,又有背于孔子,故以为贼道也。然皆概乎有闻者也。[2]498
在第一段引文中,康有为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直接称为儒教,并在这个前提下将孔子之道与杨(朱)教、墨教相提并论,并将儒学的传播与佛教的传教等量齐观。在这个维度上,教具有宗教之义。然而,正如教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包括宗教而不限于宗教一样,他在以教称谓孔子(儒)、杨朱和墨子之教的同时,以“学者”而非信徒或教徒称谓三教后学。在这个维度上,教具有学说之义。结合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教与学在他那里并无严格界限,完全可以混用。不仅如此,无论是康有为所讲的教还是学,其中都包含教育。一方面,教有学之义,此处之教指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拿《论语》记载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来说,其中的教就有教育之义。另一方面,学有教之义,此处之学指学习、效仿,而这已经是康有为所讲的教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如前所述,康有为给教下的定义是“教者效也”“教者犹道也”,以此凸显教之本义是先学后行——学习、效仿。这表明,学在他那里不仅指学习,而且包括如道一样的学习、效仿。有鉴于此,第二段引文直接用孔子之道称谓孔教、儒教或儒学,文中还直接出现了“学”的字样。
正因为教与学之间没有区别,在康有为的表述中,教与学同时使用、混用以致教学相混是普遍现象。下仅举其一斑:
诸教皆不能出孔学之外。[3]
孔子后有孟、荀,佛有马鸣、龙树;孔教后有汉武立十四博士,佛后有阿育大天王立四万八千塔。诸家盛衰,颇为暗合。[4]
孔、墨弟子,各以其学教天下。见《吕氏春秋》。[5]
老子之学分两派:教学、治学也。[5]
《书》教胄子,专言学。[6]
这些引文共同证明,康有为的教学相混从他对孔子、墨子和老子学派的称谓及说明中即可见一斑,至于“诸教”不出“孔学”之外的说法更是将教与学的相混表达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康有为还援引韩非“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的记载阐明儒是孔子创教之名,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孔子之教与孔学、儒教与儒学对于他来说异名而同实,甚至可以视为同一个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声称:“儒为孔子创教之名。春秋时,诸子皆改制创教,老子之名为道,与孔子之名为儒、墨子之名为墨同。墨子则即以墨为教名。故教名儒教,行名儒行,从儒之人名儒者,犹从墨之人名墨者。群书以儒、墨并称者,不可胜数。《韩非子·显学篇》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可知儒为孔子创教至明。《庄子》:郑人缓也为儒,其弟为墨。如为僧为道之义,此言从教之人亦至明。故墨子《非儒篇》专攻孔子。墨子亦称尧、舜、禹、汤、文、武者,而儒教为孔子所创。刘歆欲篡孔子之圣统,假托周公,而灭孔子改制创教之迹,乃列儒于九流,以儒与师并列,称为以道得民。自此,儒名若尊,而为教名反没矣。惟儒中之,品诣迥分,有大儒、圣儒、贤儒、名儒、硕儒、魁儒、巨儒,君子儒也;小儒、纤儒、偷儒,小人儒也。故孔子教子夏以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盖子夏初从教为儒时,孔子勉而戒之若此。”[7]在这里,康有为将韩非称为“显学”的儒家学说置换成了儒教,借助韩非描述的战国末期的“儒分为八”证明孔教的传播及盛行,从中推出儒为孔子创立之教——“可知儒为孔子创教至明”。沿着这个思路,他进一步将儒墨之分理解为佛教与道教之别——断言儒教与墨教的关系“如为僧为道之义”,以此证明从儒、墨之学者也就是“从教之人”。经过康有为的这番诠释,作为孔子高足的子夏跟随孔子学“文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演绎成了在孔子那里“从教为儒”。依据康有为的说法,由于刘歆假托周公,削灭孔子创教之迹而将儒列于九流,儒之教名由此被湮没了。事实却是孔子创立儒学就是创立儒教,教之名在孔子创教之时即已“至明”,在韩非所处的战国末期已经蔚为大观,居于“显学”地位。
上述内容显示,康有为对宗教之概念的拒斥与对教之概念的热衷互为表里,同步进行。有鉴于此,他一面直接对宗教一词进行解构,指责其“不典不妥”,难以成立;一面在教与宗分离的前提下热衷于教,在概念使用上以教抵制宗教。前者侧重于解构,在破的维度上进行;后者侧重于建构,在立的维度上进行。这使康有为对宗教之概念的拒斥与对教之概念的释义成为同一过程。事实上,康有为对宗教的排斥与对教之释义不仅具有逻辑上、学理上的论证,而且出于强烈的现实动机——一言以蔽之,就是为语出中国的教争得话语权,进而为孔教正名。由此反观康有为的思想不难发现,无论是教学相混、对教的泛化还是教与孔教的如影随形,都印证了这一点。
[1]康有为.欧美学校图记 英恶士弗大学校图记[M]//康有为全集:第8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康有为.孟子微[M]//康有为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孔子改制[M]//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8.
[4]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荀子[M]//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2.
[5]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M]//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4.
[6]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乐学[M]//康有为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1.
[7]康有为.论语注[M]//康有为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19.
[责任编辑 张家鹿]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01
2016-03-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ZX012)
B258
A
1000-2359(2016)05-0001-07
魏义霞(1965-),女,安徽濉溪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