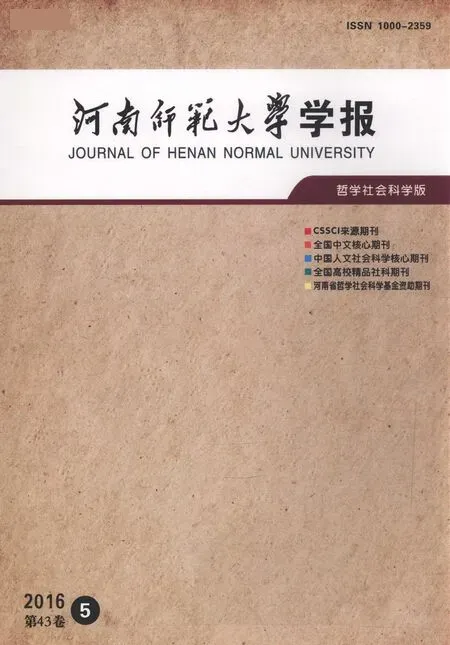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政治意识的构建
高 斐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政治意识的构建
高 斐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农民政治意识萌生和构建的一个关键时期,通过划分阶级成分、推翻地主阶级、削弱宗族影响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促进了农民阶级意识的形成;通过乡村基层民主政权和党群组织的建立、农民成为政治骨干、农民参与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保障农民享有民主权利,培养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通过树立示范典型和表彰模范人物给予农民政治荣誉,增强了农民的责任意识。农民政治意识构建的过程是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民政治认同同构的过程。
农民;政治意识;新中国成立初期
一、提高政治地位:农民阶级意识的形成
土地改革后,昔日把持农村社会、处于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上层的地主、乡绅威风扫地,跌落到社会的底层,成为被批判、管制和改造的对象,而贫下中农则成为农村中的主人。从土地改革影响的延续性上看,其社会和政治影响甚至超过了经济影响,因为土地改革所形成的自耕小农制的土地制度在农业合作化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但农村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却被保存了下来。
(一)划分阶级成分
1950年8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各类阶级成分的划分作了具体的说明,主要以土地、劳动等要素作为区分各阶级成分的标准。地主占有土地,一般不参加劳动,主要靠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为生;富农一般占有土地,少部分存在租入土地,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以剥削雇佣劳动作为生活来源;而中农与贫农的区别是,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而贫农要出卖小部分劳动力[2]。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作为阶级划分的参考,实际上在阶级成分划分标准中增加了生活水平、职业、家庭出身、政治态度等要素,使之渗透到整个农村社会。具体进行阶级划分的办法一般是先划地主,后划富农,最后划农民内部。先在贫农、雇农会上学习政策,划分阶级,然后在农代会上划分阶级,统一后再集体进行划阶级,强调从政治上划倒地主阶级。阶级成分的划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来的权力结构、阶级与身份地位的认知评价,开始以阶级身份指标来区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阶级成分越低微,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越高,阶级身份成为农民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象征。地主、富农阶级从农村社会的上层人物变为社会的底层,而贫苦农民成为新政权的主人。虽然阶级划分带有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和实践中的“符号化”趋向*关于理论上的先天不足是指这种阶级划分的理论主要是根据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即生活富裕的程度来划分,会造成“越穷就越富有革命性”的观念;而关于实践中的“符号化”,周晓虹指出,土改之后地主、富农,以及与此相应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实际上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阶级身份符号,已不具备原来的意义。参见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2)》,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231页。,但在当时通过阶级划分,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基于阶级成分上的地位提升和占有各种资源的优先权。“农民”这一称谓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令人自豪和骄傲的身份,出身贫农成为明显的政治优势。
(二)推翻地主阶级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如果说在财产的剥夺和再分配过程中尚留了一部分给地主,那么在政治权力的剥夺和再分配过程中,地主则变得一无所有,也就是说地主在土地改革中不仅失去了财产,也失去了权力和社会地位。地主过去的养尊处优地位丧失殆尽,而且成了贫雇农批斗、控诉的对象和管制、镇压的对象,而原先处在社会底层的贫雇农成为农村新的主权阶级,他们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通过从肉体上、精神上“推翻”地主阶级,体验到了“翻身”的喜悦。
首先,在“镇压反革命”中严惩地主恶霸。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农村主要是镇压地主恶霸,首先把他们管制起来,进行示威游行,然后放手发动群众,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控诉会、公审会等,进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揭发地主罪恶,清算地主发家史,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大部分地主恶霸遭到了致命打击。镇压反革命运动摧毁了地主阶级的“社会权力”,使他们从乡村社会的上层跌落到最底层,铲除了乡村社会的毒瘤。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农民在集会,可以听到农民们的呼喊:“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打倒恶霸地主!我们要翻身!”[3]
随着白内障手术的日益成熟和人工晶状体的不断发展,白内障手术后患者的视力越来越高。我们都知道,随着微切口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发展,散光及散光明显降低,术后视力主要取决于眼底。准确评价白内障手术前的眼底,正确、客观地预测术后最佳矫正视力,可以减少医患之间不必要的麻烦,为选择合理的手术方式和不同类型的人工晶状体提供有力的依据。[1]OCT在对术后眼底功能变化的准确客观分析及视觉功能评估有重要价值。
其次,在“诉苦”中沉痛打击地主阶级。土改前期,中国共产党派驻农村的工作队启发引导农民开展“诉苦”运动。“诉苦”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4]。虽然目前学界对“诉苦”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诉苦”在增强农民政治认知和阶级意识构建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诉苦”运动中,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受的苦难凝练成通俗有力的政治口号,激发农民的苦难记忆;通过召开集体“诉苦”大会,将农民的个人苦难上升为一种阶级的苦难意识,使农民找到阶级归属感,从而消除不敢诉苦的种种顾虑;通过将诉苦与“分配”“算账”结合起来,帮助农民挖掘苦难的根源,激发农民对地主的愤懑与仇恨。通过“诉苦”,广大农民认识到,自己贫困的根源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地主并不是什么“生来富贵”,农民并不是什么“八字不好”;不是地主养活农民,而是农民养活地主;地主的土地不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而是从农民手中掠夺去的[5]。地主成为旧制度、旧政权的代表,成为农民批斗、控诉和精神发泄的对象,也成为一种政治和精神地位翻覆的负面参照。广大农民深深体会到“如今的剥削阶级是的确要打倒了。‘地主’已成了耻辱的代名词,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光荣的!”[6]
(三)削弱宗族影响
地主阶级被推翻,冲击了乡村社会的宗族血缘关系,削弱了传统乡村的宗族影响。土地改革之后,没收了大量宗族群体所属的族田、学田等,摧垮了血缘群体的经济基础,血缘群体之间靠经济维持的联系逐渐减弱。与此同时,一些新型的超越宗族血缘关系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比如农民的群众性组织,再加上各种宗族组织和制度化的家族活动被取缔,原先的血缘群体的认同感和宗族血缘意识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逐渐成长起来的阶级意识。“农民们感到,正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7]。伴随着农民阶级观念的增强和自我意识的增长,传统血缘群体的主导地位被颠覆,原先握有相当权力的族长不仅被剥夺了权力,而且要接受农民的监督和管理。农民不仅摆脱了“家族系统”的“权力支配”,而且实现了政治地位的跃升,农民成为“新农村”的主人。
二、享有民主权利: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获得了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机会和条件。
(一)乡村基层民主政权和党群组织的建立
首先,废除保甲制,建立乡级基层民主政权。具体规定是:乡与行政村并存,同为农村基层行政区划。各乡人民行政权的机关是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乡人民政府;在乡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由乡人民政府行使政权。乡行政村政府由同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的正、副乡(村)长(须经区报县政府批准)和若干名委员组成,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为了便于人民管理政权,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当时实行的是小乡制。“据统计,管辖人口在3000人以下的乡占乡总数的74%,3000—5000人口的乡占22%,5000—10000人以上的乡仅占4%,平均每乡为1000—3000人。除西藏以外,1952年,全国县以下共有区18330个,乡(行政村)284626个”[8]。乡建制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为农民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保障。
其次,建立农民协会。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充分调动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政权建立了乡村基层群众性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保护雇农、贫农、中农等贫苦农民的利益,为他们提供了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平台。农民协会不仅成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关,也成为农民执掌农村政权的主要组织形式和农村政治生活的中心,有关农民利益的许多事宜都要经过农民协会委员会或农民代表大会讨论。比如应该怎么划阶级成分,谁家划为地主、富农;应该怎么分配土地,谁家的土地该拿出来分,分多少;应该怎么严惩恶霸地主,哪个该杀该判等,都要由农民协会集体讨论。农民通过参加农民协会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变革和基层政权更替中,开始在乡村政治中占据优势。农民参加农民协会的积极性很高,农民协会会员仅“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即达8800余万人,其中妇女约占30%左右”[9]。
再次,发展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全国各地的乡一般设有党的总支委员会。“到1954年11月,全国22万个乡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近400万人”[10]。同时,农村还新组建了民兵、妇联、青年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的主体都是贫苦农民。在土地改革中,通过召开妇代会、青代会、人代会等,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充分调动这些组织代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展开串联,形成了一支较强的战斗力量,起到了先锋作用。
(二)农民成为政治骨干
发现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并将他们培养成骨干力量是改造乡村政权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构建和增强农民政治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选拨和培养了一大批农民积极分子、骨干和群众领袖。
首先,贫苦农民担任农民协会的干部。农民协会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群众组织,代表农民的利益,农民协会干部一般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他们成长为新的村庄领袖,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国家政治意图的传达者。
其次,贫苦农民担任乡、村、队干部。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人民民主政权,经过土地改革以后更加巩固。在土改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被党组织吸收到乡、村等基层政权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取代传统乡绅的新的乡村政治领导者和管理者。“例如,陕西省3798个乡,就有172874个积极分子被选拨为乡村干部。浙江省在土改中共涌现出300多万个积极分子,其中有41.1万余人成为乡村领导干部。干部成分亦有了很大的变化。据苏南行政区15个县的统计,在土地改革后的89500名干部中,贫雇农占65.13%;中农占30.05%,其他占4.82%”[11]。据湖南省统计,到土地改革结束时,在新建的13274个乡中的9443个乡的乡长、乡农协主席、团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会主任等主要干部47215人,95%以上是翻了身的农民[12]。这些在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一般都能积极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其后,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各级各类干部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通过对当时25个省(区、市)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进行的调查表明,在支委、社管委、生产队长和社会计四种领导职务中,均是贫农所占比例最大,分别占到42.8%、43.3%、43.7%、35.1%;其次是新下中农,均占20%以上,其中支委中的新下中农占到将近30%[6]。由此可见,贫下中农已占据农业合作社领导干部的主体,成为基层政权的支柱,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贯彻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及维护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身于贫农下中农的乡村干部控制了农村政治生活的各种组织,他们成为新制度下的乡村精英”[13],凭借国家权力的支持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承担着在乡村传播革命和阶级话语的光荣使命,国家政权依靠他们向乡村渗透国家意志,以此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三)农民参与民主选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选,以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方式选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4]。1950年12月颁布的《乡(人民政府)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凡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共同纲领,年满18岁的人民,除精神病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外,不分民族、阶级、性别、信仰,均可当选为代表。500户以上的乡可选代表50—80人;100—500户的乡,可选代表30—50人;100户以下的乡可选代表20—30人。虽然由于农民的民主意识不强,农民的选举是一种上级机关和干部主导型的选举,但这体现了对农民民主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政治权利,纷纷踊跃参加选举。“选举的方法有豆选、票选、烫香洞、圈名、写号码和举手表决等”[15]。据统计,“在全国区、乡基层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有2.78亿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566.9万名”[16]。据《人民日报》报道,1950年2月,察哈尔全省除察北外,各县召开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村人民代表大会。各县此次会议与前次相比,代表更具有广泛性,各阶层代表均占有一定比例,农民代表中,中农代表比例提高,妇女代表也增多了,一些劳动好的并已改变了成分的地主、富农也当选为代表。会后各界代表回去结合春节文娱活动等,将会议精神和指示在农民中进行了宣传,帮助群众解除了顾虑,提高了政府威信。代表们感到人民政府真是“尽为老百姓谋福利”。左云的代表反映:“来时老百姓要问一下政府种什么庄稼好?政府叫种啥,就种啥,保险没错。”阳高县接受各界代表会建议处分了失职区长,代表反映:“这才是人民作主了,区长也交人民管着啦!”[17]
在1954年9月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把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一位农民,他是山西代表李顺达。他从前没有出过家乡的山沟,新中国成立后才到了县里。他说:“过去国家大事哪捞得上管!”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上北京,到苏联,现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啊!”[18]
(四)农民参与民主监督
人民代表会议赋予农民选举、检查、批评、检举直至罢免政府任何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农民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行使民主监督权,反对官僚主义。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前,向农民进行思想动员,培养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组织群众认真审查政府的工作,揭发、批评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交给代表带到人民代表会议中来。比如1952年9月,山西省陵川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吸收了提案928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沁源县吸收的提案达到1068件,为上次代表会议提案的十倍。这些提案绝大部分是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农民代表具有揭发、评判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的神圣权利,任何人不能侵犯,还可以提出处理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员的意见,比如对情节较轻的令其进行检讨,情节较重的给以纪律处分,对严重违法失职的依法处理。山西省介休县代理县长暴国唐在之前任供销合作社主任期间,推销豆饼时不检查用途,代表们纷纷提出责问,他因为害怕落选而几夜睡不着,但代表们在批评了他的缺点以后,也表扬了他工作中的优点,最后还是选上了他。事后他说:“我并不是怕当不上县长,而是因为这次选举是人民对自己的一次鉴定,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验。以后不敢再有一点官僚主义了”[19]。农民享有的民主选举权和民主监督权使他们认识到人民民主政权是确实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的。
总之,农民通过享有民主权利,增强了政治意识,提高了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增进了对新的民主政治体制的了解和认同,这种认同感又使他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组织中。
三、获得政治荣誉:农民责任意识的增强
政治荣誉是个体或群体得到所属政治体系的承认与重视后产生的,比如,个体或群体为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得到政治上的褒奖和认可所带来的政治自豪感或精神愉悦感。政治荣誉是人们对自己社会价值的一种自我认识、自我肯定,既满足了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增强了人们的责任意识。
(一)农民成为示范典型所带来的集体荣誉感
典型示范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了一批典型,比如,全国最著名的典型是“穷棒子社”,它是在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领导下成立的,当时23户贫农自愿组成合作社,但凑到一起只有三条驴腿,所以被称为“穷棒子社”。他们发扬“勤俭办社”的精神,“‘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发展壮大起来,成了全国的典范。早期的典型还有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山东省莒县吕家庄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吉林省延吉县金时龙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当时影响很大。比如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各部门都来参观访问、考察学习,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艺术家来体验生活,作家赵树理来到了川底村,并以川底村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体情况。而吕家庄因为吕鸿宾领导的互助组而获得了“全县第一模范村”的荣誉称号,1950年,吕鸿宾被沂水地委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遇到了农业部农政司司长刘定安,刘定安请他试办合作社,他回去后在沂水地委的支持下成立了合作社,成为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全国许多报纸作了报道。1952年夏,小麦亩产达到317斤,华东军政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奖励[20]。还有河北省安平县的三户贫农,他们在三户老中农退出后继续办他们的小小合作社,也一样成为合作化运动的楷模,毛泽东更是鲜明地表态:“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21]其实,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收入的176篇文章,篇篇树的都是合作化运动的典型,正是在这些典型的带动下,中国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高潮。这些被树为典型的合作社和被评为模范的个人也从这些政治荣誉中获得了自我肯定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增强了他们建设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责任感,从而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来。
(二)农民成为模范人物所享受的政治待遇
个人荣誉称号是对先进典型人物进行精神激励的一种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模范”等荣誉称号使农民享受到至高无上的政治待遇,从而使他们在产生无上光荣的自我认同感的同时,增强了政治责任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开展了各种生产竞赛,选举模范人物,给予他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有的还被选为人大代表等。1950年4月,河北省武安县在全县扩大干部会上表扬了领导生产运动的模范干部,经各机关、各区的选举,全县共选出甲等模范10人,乙等模范43人,丙等模范24人。这些模范干部,在1949年的生产运动中,都做出了不少模范事迹,因而在大会上对他们进行了表扬,并给以物质奖励[22]。湖南省湘阴县濠河区仁和乡第一村农民张在田由于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帮助全村人渡过了春荒、夏荒,被评为湖南省生产模范,1950年6月1日,参加了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省农协会委员。他说:“过去,我们打赤脚的农民,莫说参加咯(这样)大的会议,冒得(没有)资格;就是站在伪县政府的门口望一下,也要受到喝骂。现在,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使我们能够参加省农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政府主席同坐在一条凳上谈话。”[23]
1950年9月,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两代表会议,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毛主席也亲临会场并给予这些模范高度评价:“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24]这给了与会的农业劳动模范代表莫大的鼓励,增强了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1952年4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派出了由农业劳动模范组成的中国农民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访问期间,农民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庆典,听取了苏联有关方面关于农业情况的全面介绍,然后分为5个组,在乌克兰、高加索、哈萨克等地参观了72个集体农场、28个国营农场、22个机器拖拉机站及多个研究机构和工矿企业,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这次参观增长了农民的见识,他们看到苏联集体农场拥有土地几百几千公顷,并且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集体农场农民每日有5公斤粮食和10个卢布的报酬,住着宽敞的房屋,装有电灯、收音机,种着花木,订阅着报纸;集体农场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有俱乐部、图书馆、托儿所、幼儿园等。他们不禁感叹道:“集体化的好处说不完”[25]。回国后,农民代表在各级党政机关的礼堂里向无数听众讲述在苏联的见闻和感受。各地报刊对他们的报告活动进行报道,这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政治荣耀感。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尊重,同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回报这种尊重。他们做好关于苏联集体化优越性的宣传,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其实质就是废除了封建地主经济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也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农民成为“新农村”的主人,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培养了农民的阶级意识,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在获得政治荣誉的过程中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和责任感,他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和各项政治运动中。这既是构建农民政治意识的过程,也是结果。农民政治意识的萌生和增强使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政权,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民政治认同的同构。
[1]章秀英.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3(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83-386.
[3]刘晓晞.衡山的农民[N].人民日报,1950-03-31(2).
[4]陈北鸥.人民学习辞典[M].上海:上海广益书局,1952:331.
[5]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335.
[6]王员.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基本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2.
[7]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杜蒲,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46.
[8]金太军,施从美.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70.
[9]廖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 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1952-09-28(2).
[10]王员.建国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基本经验[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0:39.
[11]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573.
[12]徐国普.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J].求实,2001,(5).
[13]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250.
[14]季丽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广泛化轨迹探析[J].农业经济,2009,(7).
[15]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11.
[16]全国基层选举胜利完成[N].人民日报,1954-06-20(1).
[17]通过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察哈尔大力动员生产 推广农业科学技术评奖英雄模范[N].人民日报,1950-05-20(3).
[18]钱守云.中国共产党保障农民利益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47.
[19]山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山西省沁源等十四县召开县人民代表会议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N].人民日报,1952-09-09(3).
[20]《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编辑室.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选编(下册)[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670-671.
[2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4.
[22]邓世英.保证把今年生产运动领导好[N].人民日报,1950-04-14(3).
[23]唐士淳.过去的赤脚农民今天当了省农协委员[N].人民日报,1950-07-11(4).
[24]新华社.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两代表会议 昨在首都联合举行开幕典礼[N].人民日报,1950-09-26(1).
[25]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97.
[责任编辑 张家鹿]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05
2016-02-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BKS042)
D663.2
A
1000-2359(2016)05-0027-06
高斐(1980—),女,河南安阳人,法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