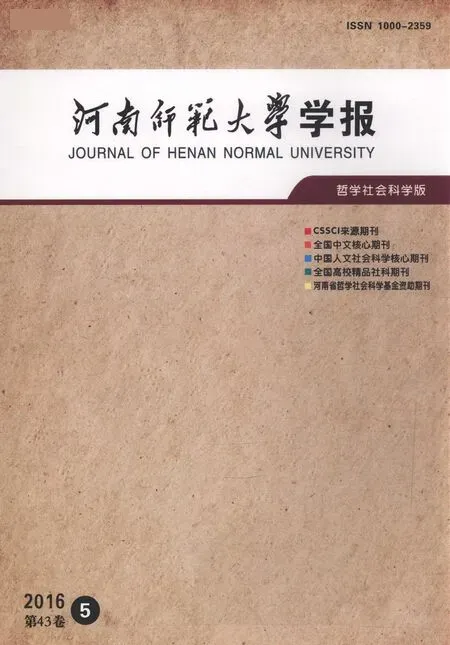语言哲学认知范式的意向性嬗变与知识再生产逻辑
周 彦 每
(新乡学院 大学外语部,河南 新乡 453000)
语言哲学认知范式的意向性嬗变与知识再生产逻辑
周 彦 每
(新乡学院 大学外语部,河南 新乡 453000)
意向性是当代心智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语言哲学的认知范式与理论流变过程体现了认识论的语言转向与价值定位,通过修正语言哲学的意向性行为,厘清从语言分析到意向建构的意向性议题。意向性嵌入语言行为凸显了语言习得的知识生成逻辑,具体而言,语言认知主体基于意向性心理与社会规制维度的引入,借用主体性意识涌现的桥梁,达到语言习得的知识生成。对于语言哲学研究的知识再生产而言,基础主义引导了语言哲学建构的知识旨趣,必须将知识问题纳入语言哲学框架,在意向性哲学论证过程中挖掘知识再生产研究的学术自觉。
语言哲学;意向性;认知;知识生产
语言是疏导沟通的意图和探究心灵的渠道,也是贯通隐性真实的表达力量。心智抑或思维之所以能够超越语言和束缚,就在于人脑中存在意象性的思维。诚然,任何知识的获得并非可描述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头脑的意会能力。西方哲学研究围绕知识问题的论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是柏拉图,他立足于本体论哲学,认为“理式”是哲学的核心,进而剖析了客观存在、认知对象和运行客体三者的关系。笛卡尔作为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从主客体认知关系出发,致力于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探究。第三阶段以哲学的“语言转向”为核心靶向,围绕逻辑实证主义、言语行为理论、生成语言学三条线索进行研究。具体而言,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皆为语言哲学知识论的生成作出了卓绝贡献。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研究的勃兴为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认知基础。毋庸赘言,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论)贯彻始终的核心问题是知识问题。在经验主义哲学看来,知识源于经验,是对感觉、知觉印象的归纳和概括。而理性主义哲学的范畴却将知识体系归纳为主体理性的主观推演。认知心理学引入中介变量(O),规避了既有S-R双维图式的缺陷,将行为主义的发展逻辑拓展为S-O-R的三维图式,从而凸显了认知主体在知识获取中的主动性。奥苏贝尔将认知语言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认为“言传知识本身具有清晰的逻辑演绎规律,知识传承的动力在于主观认知的概念化和客观体验的实践活动”[1]。交际主体吸纳新知识的能力在于其自身认知结构中固有的理念,知识获取的过程取决于新知识与认知结构的互动程度。
一、语言哲学研究的言语行为与理论流变
西方早期语言哲学以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将语言视为静态表述系统。进而,意向论认识的发展围绕由否定、拒斥到肯定的研究主线。其中,维特根斯坦在诠释语言转向的基础上,以交际主体的日常语言和实际使用为切入点,将“语言游戏”视为终极语言范式,指明了语言哲学研究的意向性论域。奥斯丁进一步把语言看作人类的行为,认为交际主体的“语言游戏”受到“言语行为”主体心理意向的支配。当代语言哲学家塞尔为人、语言、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总体性判断,推进了语言哲学意向性认知范式的研究空间。
(一)认识论哲学的语言转向与价值定位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认识论哲学也由“可以认识什么”向现代哲学“言说什么”转换。弗雷格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为了把数学置于可靠的理性基础之上,较早就注意到了日常交际符号中存在含混性和多义性缺陷,因而创造了形式化的语言流程,引发了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进程中,弗雷格提出的“逻辑主义计划”,理清了数理逻辑的运行规律,初创了现代形式的符号逻辑,这种“新逻辑”吸纳了数理逻辑的优势,以符号的形式补充了语言哲学认知范式中的话语体系。随后,为了建立一套全新的心理主义解释框架,弗雷格对逻辑的性质和语言表征重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的研究也由此发端。
弗雷格认为,“认识一个存在性的符号(名称,词组,文字符号等),不仅要考虑到交际双方被表达物具体的表征,还要关照到交际主体给定的既有方式”[2]。首先,弗雷格提出,语言折射了思想认知的基本结构和表征理论思想的具体内容。所以,语言哲学的研究框架中形式理论和语言意义是不可分割的系统整体。诚然,语言产出的微观形式是铺垫,语言的意义提升了语言形式的具体内涵。其次,对语言形式的透视就是要分析交际语言中尚存的固定逻辑命题。唯此,自然语言固有的含糊性和歧义性才能不断消解,模拟数学逻辑的语言构造最终凸显出语法要义的深处表达。再次,交际语言中处于宏观语境中的句子是语言的基本形式和句义单位。语言的逻辑结构彰显了语句间的逻辑递进关系以及语句内部的逻辑演算进程。语言篇章结构中一个单独的语句形式体现了形式语言的逻辑公式。总之,弗雷格将语言的归结为语言符号演变的逻辑规律,语言哲学第一个研究范式由此得以确立,开辟了以语言哲学为价值定位的“符号—命题”分析时代。
(二)语言哲学的重新定向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
维特根坦斯认为,语言交际主体的审视,语言的本质、功能等语言哲学命题,为普通语言哲学研究范式做了先驱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具体而言,首先,在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他将“人—语言”置于中心位置,通过全方位透视语言认知主体的意向、感觉等语言生成机制,分析了人、语言与世界的内在关联,突出了“人—语言”在语言哲学的核心位置。其次,关于语言本质的认识,维特根坦斯提出了与“图像论”和“逻辑形式”相比对的“游戏论”和“生活形式”[3]。“语言游戏论”和“生活形式论”构成新语言哲学范式的基本内核。针对语言哲学的意义,维特根坦斯提出与早期的“图像—确证论”相对应的“用法—工具论”。可见,按照“语言游戏论”的假设条件,语言交流的附加意义恰恰就在于认知主体在特定语境中所履行的任务[4]。具体而言,意向植根于具体的交际情境,形成于人类日常交际的惯习。
在维特根坦斯将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奥斯丁明确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在奥斯丁看来,“在整个言语环境中,言语行为是语言哲学的主要且唯一所阐述的研究对象”[5]254。可见,奥斯丁已经把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论纳入了语言哲学研究视野之内。同时,奥斯丁进一步提出言语行为的“工具说”,他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说话人达到某种目的的交流工具,具体涵盖“以言表意、以言行事的、以言取效”三层言语行为的认知含义。同时,奥斯丁也明确指出,“真假问题”并不能完全建构记述句和完成行为句的分界线,但应该从“适当性”和“真假性”两方面把握语言及其句子的确切释义。奥斯丁还将“语力”作为考察人类语言行为的前提条件,认为“交际主体一旦说出一个句子,必须满足某种假定条件、批判并明晰讲话人的价值取向”[5]77。“语力”这一评价维度正视了对言语行为“意义性”的狭隘偏见。
(三)从语言分析到意向建构的意向性议题
如前文所言,奥斯丁推翻了“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中心的观点,区分了言有所述和言有所为的异同[6]。首先,奥斯汀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的内在规定,认为陈述言语的作用要么描述某种语言状态,要么陈述某一事实,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泾渭分明的真实抑或谬误。其次,他初步论述了言语行为与心理意向的关系,提出了言语行为的基本认知框架。具体而言,奥斯丁认为言语行为就是“说话即做事”,言语行为是交际双方通过话语表达意义的基本功能和分析单位。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言语行为实施者的主体作用,具体区分的标准就是句子中有没有施为动词。更确切地说,“以言行事”行为就是语言交流单位的集合体。但奥斯丁最终并未建立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也鲜有提及心理意向与言语行为的性质、具体的分类及其内部深层运作逻辑结构。
塞尔继承了奥斯丁的语言哲学思想,深入到人类心智的层面,充分挖掘语言意义的源头,将言语行为的意向性分为内在的和派生的创造性语句,以言行事的行为和命题行为是基于人脑意向而说出某些语句。塞尔基于言语行为“意向”和“惯例”的工具性目的,将言语行为区分为不同的整合方向。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与涉及说话者双方所发出的一个特定话语情相联系的多种行为”[7]。可见,塞尔试图沿着“语言、心智与世界”的路线,以此打开心智哲学的奥秘,进而提出意向性建构的基本路标。因此,对言语行为的探究最终要依赖于人的心理意向这个范畴。按照塞尔的理解,意向性议题关注到了当代哲学的核心,语言哲学正是从这里发端才进入了意向性逻辑,进入了对人类心智构造的研究[8]。因此,从语言分析走向意向建构实现了心脑机体与客观实在相对接的某种回应。
二、意向性嵌入:管窥语言习得的知识生成逻辑
就人与语言意义的关系而言,在言语行为意义论的认识中,形成了以戴维森“实在论”理论和达麦特“反实在论”的观点。尽管对“意义是什么”存有激烈争论,但传统意义理论在认识论层面观点上分歧,都属于“被动的语言意义观”。奎因由此引入了语言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制维度,真正深入地开拓了认知意义的意向性维度。现代语言哲学家认为语言知识的获得体现为主体意识的涌现的过程。
(一)心理意向与社会规制维度的引入
奎因主要继承了罗素的传统,从整体主义立场理解语言哲学的任务。他着重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证实论中“同义性”和“分析性”的相关概念,期望用“标准记法”对自然语言进行语义整编,用整体化的语言讨论哲学,初步提出了语言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制维度。奎因十分注重注重语言发生的经验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哲学通过奎因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了心理认知主义。奎因认为心理意向等精神的东西只能通过交际主体对语言刺激所作出的社会性行为进行回应。相反,奎因的学生戴维森继承了整体主义和外延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心的东西,既是自立的,又有其特异性”[9]77。戴维森建立了意义与真理相匹配的语言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认为“只有通过给出这语言中的每个语句(和语词)的意义,才能给出任何一个语句(或语词)的意义”[9]200。他进一步指出,诠释语言行为的一个完整句式,必须把握说话者的整个意向结构来理解其微观语言行为旨意。
在戴维森看来,言语行为体现于人的社会性应用的范畴之中,不与具体强加于人的“行为图式”相契合[9]126。这是因为,交际双方言语行为与其异常复杂的“认知结构”休戚相关。可以看出,戴维森把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制维度明确引入到了意义性论域之中。达麦特基于戴维森的语言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意义在于提供证据,而不在于其真值条件。达麦特提出“意义在于应用”的鲜明观点,立足于“反实在论”的立场,阐明了意义的社会性与意向性的裙带关系。他认为,“语言意向的原子成分应彰显句词建构形成的意义,立足于完整的句子,进而研判整个语言意向的有效映射范围”[10]。通过言语行为的映射,特定语境中交际双方赋予语言的特定意义才能得以凸显,可见,达麦特从“反实在论”的立场进一步强化了意义的社会性和意向性维度。
(二)主体性意识的涌现与语言习得的知识生成
戴维森的“异常一元论”观点认为物质有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的双重“涌现”因素。涌现论是自然科学家们在研究自然界动态复杂非线性系统中提出的混沌复杂理论和动态系统理论[11]。提出涌现论的语言习得是经验和普遍认知机制互动的任务。涌现的产生主要表现为大脑复杂有机体之间互动耦合的系统动力行为,是由系统整体表现出的新奇性[12]。具体而言,主体性意识的涌现是从范例或简单构式开始,经过归纳概括,最终习得复杂抽象构式的过程。可见,涌现是整体性的思维系统的演化,对于语言哲学而言,对涌现现象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大脑应激性反应的意向形态。查默斯中区分了意识中的“易问题”和“难问题”,指出了主体意识的感受性是知识内化的逻辑[13]。他还进一步指出,精神实体是物理实体,意识的发生机理只承认本体论上的还原,而不承认概念上的还原。意识涌现的本质就是系统整体及其性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逐渐的浮现。
莱考夫认为,人们基于感知感觉系统逐步认识所存在的环境和时空范畴,形成空间、时间、运动等的意象图式,最终形成了各种关于世界认知的意象结构[14]。意向性是说话主体意图的体现,话语表达和生成是在一定条件下与心智意向性的结合,意向性体现了语言表达的目的。因此,意向性是大脑思维活动在特定限制下信息定位时的镜像,呈现预判、估评作用。正如塞尔所言:“意向性是心灵折射的特定语言特征,基于语言的某类特征,指涉关于、论及、针对能指路向。”[15]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对事物形成的感官映象是一种原初状态的初级体验,从意识活动的角度来说可称为原初意识。这是因为,认识是一个多环节过程,“知”只是它的一个主观环节。因此,意向性是交际主体的一条主线,在意向性的作用下,交际双方完成了从“事件”到“用例事件”的格式塔的转换。从言语交际上来说,代体宾语的意向性就是语言使用者思维的目的性,其也是语言交际的本源。
三、知识再生产:语言哲学知识论的意向性重建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在认识论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语言框架都是围绕意向性心理的基底而开展知识重建活动的。语言知识的建构依赖于人的生理条件、认知机理和语言事件高频率的交叉互动。因此,语言范畴的边界处于形式和意义两极网络上的节点,要在知识论和价值论的整合过程中,维护知识论视域下意向性价值的公允地位。
(一)基础主义对语言哲学建构的知识旨趣
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在于归纳了语言哲学框架中基础主义的基本内涵,系统阐释了逻辑实证主义对基础主义知识理论框架生成的具体要求,提出了“世界—事实”“事实—命题”“语言—逻辑”“基本命题—复合命题”“事实结构—语言结构”等应用范畴[16]。据此,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将语言科学应用于知识问题的系列研究。基础主义语言哲学认为人类一切知识皆发端于直接和间接经验直接给予的多元整合。卡尔那普对基础主义哲学有这样的描述:“逻辑实证主义对语言中逻辑句法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陈述语序的基础性地位,基础主义奠定了意义性论纲中知识结构的基本线索。”[17]基础主义对语言哲学建构的知识旨趣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基础主义从原则上规定了一切有价值的理论陈述必须与经验陈述相吻合,另一方面,意义证实理论通过考察语言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到知识问题的真实辩护,基础主义确立了对知识本质的认识。
费厄舒伦认为,知识建构其实是话语人基于主观心理作出自我修正与内化的过程。主观认知的心理反应其实就是元语用意识的应激反馈[18]。意识反应程度涉及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知识生成过程中的心理维度。乔姆斯基语言也明确指出,“语言知识是先天习得的”[19]。若把乔姆斯基语言知识先天论置于哲学传统的大背景下进行甄别,乔姆斯基的观点与苏格拉底和康德并无分别,这是因为,唯理主义知识论中人的语言知识不可能天生。乔姆斯基的哲学误区在于把结构误归为内容,把形式错当成了意义,没有关照到语言知识习得过程中语境的强制渗透力和意向性。因此,知识科学的稳定性就在于自然语言的陈述逐渐被固化为一连串包含言语主体的知识表达。诚然,基础主义对语言哲学建构的起点是将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中介工具。把基础主义建基于意向性哲学的大厦基底之上,通过语言和逻辑的互动为基础主义增添了无可辩驳的论据。
(二)把知识问题纳入语言哲学的框架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近代认识论流派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认为感觉、内省、知觉均建基于心灵机能的预设之上。随着“逻辑哲学”向“语言哲学”再到“心灵哲学”转向的命题置换,预设概念也将从“语言转向”逐步切换为“心理转向”。按康德的划分,心灵可以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脑是思维的工具,所以心灵的反思贯穿于思维的升华。诸多关于心灵机能运作的预设都无法给予现实世界一个精确的表征[20],因此,传统语言哲学认知范式中并没有把知识的可靠性建立于牢固的惯习之上。把知识问题纳入语言哲学的框架就明确将知识认同作为一个语言体系,进而从语言和实证逻辑的视角探究知识生成的生态,最终通过语言篇章结构中的逻辑特征建构知识理论。当然,要进一步对主观心理难以管控的观念、知觉、判断等表征内容进行分类研究,从语言规划与社会维度的行政性规制研究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过程,充分理清知识的逻辑、知识的基础和知识的辩明等知识生成问题。
把知识问题纳入语言哲学研究框架之中,就是摒弃以陈述的经验代替实证方式的知识生成基础,以确定语言使用者的大脑中知觉存在的弊端,从而更新科学研究领域中知识大厦的长久性。同时,语言哲学中“意义性”的分析是区分科学与伪命科学的有力判据。毫无疑问,语言哲学研究中知识生成问题体现了逻辑分析在心灵感受中的客观依据,也为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式提供了可资利用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语言哲学中关于“意义性”的探究往往把经验确证和观察陈述作为大脑认识的极限,这种“言说出来”的言语认知为探究知识问题提供了重要窗口,但也阻碍了知识问题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机会。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语言研究者构筑了语言知识理论的生成基底。因此,科学知识体系宛若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这个系统完整记录“事实陈述”就是知识生成的语言逻辑形式,这也是自然语言形成的基础。
(三)知识再生产的价值证成与语言认知意向性的契合
基础主义知识理论将大脑主观认知的知识体系分为所直接授予的知识和推论性的知识两个层面,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在语言哲学和归纳逻辑的框架中获得了系统知识的梗概。传统认识论中“证据—理论”关系范畴认为科学知识就是运用归纳逻辑概括出语言哲学知识论的一般运行机理,因为,推论性知识源于知识授予的直接证据,是从观察证据中得到的。但是,这种对知识结构语言哲学的辩护方式遭到休谟的毁灭性还击。鉴于近代知识论研究者对推论性知识辩护的失败,逻辑经验主义才开始着手将科学知识的发现区别对待。这是因为,科学知识论的研究过程就是为科学知识的辩明,仅仅依靠心理的主观认知无法对知识生成的本质进行逻辑解释[21],因此,知识结构的语言哲学论证要专注于对理论知识科学性的证伪。进一步而言,逻辑经验主义者研究者归纳了逻辑的雏形并建立起各种现代归纳逻辑模型,其根本旨意在于为推论性知识的可靠性提供科学的申辩过程。
概言之,以自我辩护为基础的基础主义知识论无疑是以笛卡尔的“我思”或“作为思维的我”为前提的[22],其最大的优越性在于由发现辩护转变为证实辩护,将辩护引向科学理性的心灵预设,完全避免了“休谟悖论”现象,进一步而言,推论性知识已经成为可公开操作的意向性知识取向。因此,笛卡尔关于“心”的发现为语言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无限可能的探究领域[23]。当然,对于洛克来说,人类知识的边界性争论都是以对人类理智运作的实际过程为前提和基础的。洛克提出的“白板说”是对人类理智精详的心理—生理学全方位的透视。洛克确保了既有的经验论学说更加规范有序,当然,洛克并未在特殊性感觉的基础上普遍形成的知识性规律。反观之,哲学应该将语言行为纳入其研究框架,在批判的同时反思科学知识的形成机制。当然,这种反思并非传统哲学知识论对其问题的最合理回应。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对知识结构的解构有助于从语言哲学的论域中挖掘出与知识体系相契合的知识再生产逻辑。
结语
在现当代西方哲学框架中,知识论都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它所要探究的中心问题是人类知识的本质和限度。但是,真正说来,作为研究显学的逻辑实证主义仍然存在主客二分的悖论逻辑,从而以经验陈述作为知识论陈述的最终基础。毫无疑问,语言能够在语言哲学的架构中对基础主义作出有力的辩护,知识问题作为公理形式存在的静态语言系统,应该从动态语用和心理意向两个层面考察语言知识的生产方向。同时,逻辑实证主义知识理论自身也存在各种自身发展的羁绊,就言语行为的形成意义来说,“意义证实论”“经验还原论”等语言知识也曾经遭受到了多方的质疑。诚如考克斯所言:“未来无法预见,但我们基于现有知识,在众多貌似可行的方案中,总有一个朝较满意的方向发展。”[24]在社会科学中,“关于‘真实世界’的问题,单靠某一个学科的知识是不可能解决的,诸多富有创造性的挑战源于与‘真实世界’中的现象、问题联系紧密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计划”[25]。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知识再生产研究的学术自觉也必须顺应语言哲学发展的“处境化”经验。唯此,关于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律的探究才能以“知识”的形式加以传承。
[1]刘大椿.科学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76.
[2]周彦每.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二维嬗变与价值评介[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76.
[4]侯国金.语用学精要:语用能力对阵语用失误[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273.
[5]约翰·兰肖·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M].张洪芹,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6]J·L·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180.
[7]John R.Searle.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39.
[8]John R.Searle.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vii.
[9]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与方法[M].牟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0]M Dummet.Truth and Other Enigma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426.
[11]高新民.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817.
[12]贾光茂.争议与应对:二语习得涌现论研究的进展与启示[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2).
[13]chalmers.D.The conscious Mind: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6.
[14]Lakoff,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3:76.
[15]塞尔.心、脑与科学[M].杨音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66.
[16]张庆熊.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77.
[17]鲁道夫·卡尔那普.世界的逻辑构造[M]. 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6.
[18]王寅.语言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77.
[19]Chomsky,N.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77.
[20]刘高岑.意识经验问题昭示的新科学理念及其哲学理解[J].哲学动态,2015(4).
[21]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6.
[22]D·W·海姆伦.西方认识论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96
[23] 勒内·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录[M].徐陶,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76
[24]Jeffrey A.Hart,Prakash A.Conclusion,PrakashA,Hart JA.Globalizationand Governance[M].London:Routledge,1999:159.
[25]迈克尔·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1.
[责任编辑 张家鹿]
Intentional Transmutation and the Logic of Knowledge Reproduction of Cognitive Paradigm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
ZHOU Yan-mei
(Xinxiang College,Xinxiang 453000,China)
Intention is one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gnitive paradigm and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language philosophy reflect the shift of language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pistemology. By modifying the intentional behavior of language philosophy, the intentional issues from linguistic analysi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ntions can be made clear. The intentionality embedded in linguistic behavior highlights the logic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is actuall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knowledge generation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body language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social intentionality.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foundationalism guides the knowledge purport of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problem knowledge must be put into the framework of language philosophy to refine the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academic knowledge reproducti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intentionality;cognitive;knowledge production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04
2015-12-09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5YJC740145)
B085
A
1000-2359(2016)05-0021-06
周彦每(1982—),女,河南信阳人,新乡学院大学外语部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