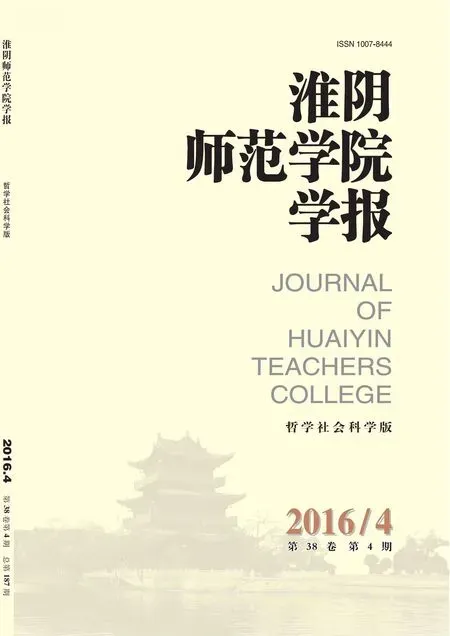破解《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之谜
韩亚光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工运研究所, 北京 100865)
破解《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之谜
韩亚光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工运研究所, 北京 100865)
摘要:今天国人所经常见到的100回本的《水浒传》和120回本的《水浒全传》,都不是《水浒》成书时的原著。《水浒》成书时的原著,本来包括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在内;在原著流传过程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被剔除,形成100回本的《水浒传》;后来,征田虎、讨王庆故事被恢复,形成120回本的《水浒全传》。《水浒全传》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是重新撰写的,所以不完全相同于《水浒》成书时原著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
关键词:水浒全传;征田虎;讨王庆;形成过程
《水浒》的版本很复杂,总起来说包括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今天出版社公开出版、国人经常见到的100回本和120回本,分别被命名为《水浒传》和《水浒全传》,它们都属于繁本系统。100回本的《水浒传》与120回本的《水浒全传》,存在许多区别。其中的最大区别,在于《水浒传》没有征田虎、讨王庆的故事,而《水浒全传》有这两段故事。在《水浒全传》中,征田虎出现于第91回至第100回,讨王庆出现于第101回至第110回。探讨《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形成过程,成为《水浒传》和《水浒全传》关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本文的主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使用的《水浒传》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系列之一——《水浒传》,系1997年1月北京第2版,2013年8月第14次印刷;本文使用的《水浒全传》版本,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之一——《水浒全传》,系2013年4月北京第1版,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前一部书的前言认为,对于征田虎、讨王庆故事,120回本“根本没有留给活动的时间,矛盾显然”,明代万历间有本子“明标‘插增’,可见是后人补写后硬插进去的”;只有100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定型成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1]2。笔者以为,这些说法并非完全符合事实;一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既然如此,本文就以小说中的若干时间问题为切入点展开探讨。
一、鉴于《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中若干时间问题,提出质疑:100回本先问世,还是120回本先问世?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是后来增加,还是早已存在?
《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中的若干时间问题,显得云山雾罩。现在,对其作如下分析。
(一)推敲一些时间表述,使人认为:其中依稀呈现修改痕迹,它们似乎同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出现时间以至100回本、120回本的问世时间具有关系。
在《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中,一些文书提到的时间表述需要留意。
在《水浒传》中,文书提到的时间表述如下:
在第8回中,林冲给妻子的休书,提到“年月日”[1]109。
在第71回中,宋江向众兄弟下发的号令,提到“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1]902。
在第75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三年孟夏四月日”[1]948。
在第80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年月日”[1]996。
在第81回中,闻焕章致宿太尉的书信,提到“宣和四年春正月日”[1]1019。
在第82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四年春二月日”[1]1027。
在第82回中,宋江派人张贴的告示,提到“宣和四年三月日”[1]1030。
在第89回中,辽国主向宋徽宗上呈的表文,提到“宣和四年冬月日”[1]1112。
在第89回中,宋徽宗向辽国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四年冬月日”[1]1114。
在第99回中,宋江等人向宋徽宗上呈的表文,提到“宣和五年九月日”[1]1248。
在《水浒全传》中,文书提到的时间表述如下:
在第8回中,林冲给妻子的休书,提到“年月日”[2]79。
在第75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三年孟夏四月日”[2]691。
在第80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年月日”[2]726。
在第81回中,闻焕章致宿太尉的书信,提到“宣和四年春正月日”[2]743。
在第82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四年春二月日”[2]748。
在第82回中,宋江派人张贴的告示,提到“宣和四年三月日”[2]750。
在第89回中,辽国主向宋徽宗上呈的表文,提到“宣和四年冬月日”[2]807。
在第89回中,宋徽宗向辽国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四年冬月日”[2]808。
在第101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五年四月日”[2]885。
在第119回中,宋江等人向宋徽宗上呈的表文,提到“宣和五年九月日”[2]1038。
《水浒传》中文书提到的时间表述与《水浒全传》中文书提到的时间表述,存在细微差别。首先,在《水浒传》第71回中,宋江向众兄弟下发的号令,提到“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在《水浒全传》第71回中,宋江向众兄弟下发的号令,没有明确涉及时间表述,但是号令之外的正文提到“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2]659。其次,在《水浒全传》第101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宣和五年四月日”,该诏书意在命宋江等人讨王庆;然而,该诏书在《水浒传》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在《水浒传》第99回中,宋江等人向宋徽宗上呈的表文,提到“宣和五年九月日”;然而,这个细节在《水浒全传》中出现于第119回。除了这些差别,《水浒传》中文书提到的时间表述与《水浒全传》中文书提到的时间表述都是相同的。
总的来看,《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中文书提到的时间表述,大部分精确到“月”,小部分精确到“日”“年号”,或者只有空头“年”“月”“日”,完全白板。完全白板的情况出现很早,精确到“日”的情况出现也较早,所以这里不去管它们。真正令人诧异的是,在第80回中,宋徽宗向宋江等人下发的诏书提到的时间表述,精确到年号“宣和”;而第75回以后的其他时间表述,都精确到“月”。这些状况,使第80回中精确到年号“宣和”的时间表述显得极其特殊、十分反常,让人朦胧感到其中有修改的痕迹。无论在《水浒传》中,还是在《水浒全传》中,第80回以后都有5个提到“宣和四年”的时间表述;而在《水浒全传》中,宋江等人征田虎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季开始的。在这种条件下,第80回中精确到年号“宣和”的时间表述,似乎与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出现时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甚至与100回本、120回本的问世时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斟酌少量时间安排,使人感到:100回本问世先于120回本,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乃后来增加。
在100回本的《水浒传》中,有这样几个时间关节点值得关注:
第89回提到“宣和四年冬月”[1]1112,这时宋江伐辽国成功。
第91回提到“初春”[1]1134,这时宋江打方腊开始。
第96回提到“四月”[1]1196,这时宋江打方腊正在进行。
第99回提到“宣和五年九月”[1]1248,这时宋江打方腊成功。
以上这些材料,从宣和四年冬月,到宣和五年初春,再到宣和五年四月,最后到宣和五年九月,时间没有冲突,情节也很连贯。
在《水浒全传》中,有这样几个时间关节点值得关注:
第89回提到“宣和四年冬月”[2]807,这时宋江伐辽国成功。
第93回提到“宣和五年的元旦”[2]831,这时宋江征田虎正在进行。
第100回提到宋江“五月之内,成不世之功”[2]882,这指宋江征田虎成功。
第101回提到“宣和五年四月”[2]885,这时宋江讨王庆开始。
第106回提到“八月中旬”[2]918,这时宋江讨王庆正在进行。
第110回提到“暮冬”[2]947,这时宋江讨王庆成功。
第111回提到“初春”[2]956,这时宋江打方腊开始。
第116回提到“四月”[2]1001,这时宋江打方腊正在进行。
第119回提到“宣和五年九月”[2]1038,这时宋江打方腊成功。
将以上材料汇集起来,具体情况是:从宣和四年冬月,到宣和五年四月,宋江征田虎;从宣和五年四月,到宣和五年暮冬,宋江讨王庆;从宣和六年初春,到宣和五年九月,宋江打方腊。很明显,在打方腊的时间上出现了逻辑错误。
通过前述对《水浒传》和《水浒全传》的考察,可以发现:在《水浒全传》中,伐辽国成功与打方腊成功所形成的时间段,无法完全容纳征田虎、讨王庆故事,而这个时间段恰恰与《水浒传》相同。这使人感到:100回本的《水浒传》问世先于120回本的《水浒全传》,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由后人加写插入。
(三)细想个别时间状况,使人觉得:120回本问世先于100回本,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应早已存在。
在《水浒传》第90回中,伐辽国成功的宋江等108人朝见天子时有下列细节:
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宋江再拜奏曰:“皆托圣上洪福齐天,……”再拜称谢。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计议封爵。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方今四边未宁,不可升迁。……”[1]1123
在《水浒全传》第90回中,伐辽国成功的宋江等108人朝见天子时有下列细节:
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宋江再拜奏道:“托圣上洪福齐天,……”再拜称谢。天子特命省院官计议封爵。
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宋江等官爵,容臣等酌议奏闻。”……不觉的过了数日,那蔡京、童贯等那里去议甚么封爵,只顾延挨。[2]815
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讨王庆成功的宋江等108人朝见天子时有下列细节:
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宋江再拜奏道:“托圣上洪福齐天,……”再拜称谢,奏道:“臣等奉旨,将王庆献俘阙下,候旨定夺。”天子降旨:“着法司会官,将王庆凌迟处决。”宋江将萧嘉穗用奇计克复城池,保全生灵,有功不伐,超然高举。天子称奖道:“皆卿等忠诚感动!”命省院官访取萧嘉穗赴京擢用。宋江叩头称谢。那些省院官,那个肯替朝廷出力,访问贤良。此是后话。
是日,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计议封爵。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目今天下尚未静平,不可升迁。……”[2]947-948
现在,对上述三个材料进行一些分析。在《水浒传》第90回的材料中,正文写完天子与宋江的对话以后,没有时间的转换,即提到“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计议封爵”,而蔡京、童贯明说宋江等人“不可升迁”;这意味着蔡京、童贯当着宋江等人的面反对天子重用宋江等人,这种情节安排与蔡京、童贯的奸臣身份相矛盾;作为奸臣的蔡京、童贯,即便要说反对的话语,也应当把时间错开,而不是当着宋江等人的面。在《水浒全传》第90回的材料中,正文写完天子与宋江的对话以后,也没有时间的转换,即提到“天子特命省院官计议封爵”,蔡京、童贯则说“宋江等官爵,容臣等酌议奏闻”,但是此二人“只顾延挨”;这种并非当面反对而是暗中怠工的办法,符合蔡京、童贯的奸臣身份。在《水浒全传》第110回的材料中,正文写完天子与宋江的对话以后,没有立即提“计议封爵”的事情,而是讲了“那些省院官,那个肯替朝廷出力,访问贤良”等话语;在讲完这些话语以后,说了“是日”二字,随即才提到“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计议封爵”。“是日”二字虽然意味着还是在同一天,但是可以理解为已经对天子与宋江对话时的场景进行了转换;“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计议封爵”的时间,可以解释为已经是宋江等人不在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蔡京、童贯在天子面前明说宋江等人“不可升迁”,就符合蔡京、童贯的奸臣身份了。
综上所述,《水浒传》第90回的情节讲不通,《水浒全传》第90回的情节和第110回的情节讲得通。《水浒传》第90回的情节之形成,好像来源于《水浒全传》第90回的情节与第110回的情节之嫁接:保留《水浒全传》第90回中蔡京、童贯当着宋江等人的面说出奏言之安排,但是奏言表述更换为《水浒全传》第110回中蔡京、童贯在宋江等人不在场时的奏言内容。有意思的是,在《水浒全传》的这两个情节之间,就是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所有这些情况,使人觉得:120回本问世先于100回本,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应早已存在。
总之,《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中的若干时间问题,使得100回本、120回本的问世时间与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出现时间显得扑朔迷离。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有根有据地考察100回本与120回本问世的先后顺序。
二、通过《水浒传》和《水浒全传》若干环节对比,以及这些环节与《大宋宣和遗事》对照,进行确认:100回本问世先于120回本
考察100回本与120回本问世的先后顺序,应当对《水浒传》和《水浒全传》的很多环节作出对比。因为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尚属于悬案,所以考察过程不涉及《水浒全传》中出现这两段故事的第91回至第110回,以及与之有紧密关系的第89回和第90回;相应地,也不涉及《水浒传》第89回和第90回。《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有关故事,是《水浒》成书时的原著之重要来源,所以考察过程还需参考《大宋宣和遗事》,这样有利于最终确认100回本和120回本问世的先后顺序。鉴于所有这些考虑,笔者对《水浒传》和《水浒全传》若干环节作出了对比,并将这些环节与《大宋宣和遗事》进行了对照,结果发现三种情况。
(一)《水浒传》少许环节优于《水浒全传》,这些环节与《大宋宣和遗事》没有关联。
《水浒传》第37回与《水浒全传》第37回故事相同,但是标题有所不同。《水浒全传》第37回标题后一句是“船火儿大闹浔阳江”[2]343。相关的故事主要情节是:宋江和两个公人上了一只船。“只见那梢公放下橹,说道:‘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却是要吃馄饨?’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怎地唤做板刀面?怎地是馄饨?’那梢公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还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艎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宋江听罢,扯定两个公人说道:‘却是苦也!……’那梢公喝道:‘你三个好好商量,快回我话。’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们也是没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怜见饶了我三个!’那梢公喝道:‘你说甚么闲话!饶你三个!我半个也不饶你。老爷唤做有名的狗脸张爷爷,来也不认得爹,去也不认得娘。你便都闭了鸟嘴,快下水里去!’宋江又求告道:‘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财帛、衣服等项,尽数与你,只饶了我三人性命。’那梢公便去艎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大喝道:‘你三个要怎地?’宋江仰天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那两个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罢,罢!我们三个一处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跳下江去。跳便跳,不跳时,老爷便剁下水里去。’”“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恰待要跳水,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橹声响,……一只快船飞也似从上水头摇将下来。……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星光明亮”,“那船头上立的大汉,正是混江龙李俊”。“这李俊……跳过船来,口里叫苦道:‘哥哥惊恐。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误了仁兄性命。……’”“那梢公呆了半晌,做声不得……”[2]347-348故事中的“梢公”,就是“船火儿张横”。可以说他“闹浔阳江”,但是谈不上“大闹浔阳江”。所以,《水浒全传》第37回标题后一句“船火儿大闹浔阳江”[2]343,概括得并不准确。《水浒传》第37回标题后一句是“船火儿夜闹浔阳江”[1]463,这个概括倒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水浒传》第75回与《水浒全传》第75回故事相同,但是标题也有所不同。《水浒全传》第75回标题后一句是“黑旋风扯诏骂钦差”[2]688。相关情节是:“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甚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众人都来解劝,把黑旋风推下堂去。”[2]691-692这些内容,与其叫“黑旋风扯诏骂钦差”,不如叫“黑旋风扯诏骂皇帝”。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李逵虽然打了钦差陈太尉,但是言语中骂的对象是皇帝,或者说骂的对象主要是皇帝。《水浒传》第75回标题后一句,将这个事情概括为“黑旋风扯诏谤徽宗”[1]942,这个表述就比较准确。
《水浒传》第92回与《水浒全传》第112回是对应的。二者都提到卢俊义分将佐攻打宣、湖二州,将佐名单是:正将包括副先锋玉麒麟卢俊义、军师神机朱武、小旋风柴进、豹子头林冲、双枪将董平、双鞭呼延灼、急先锋索超、没遮拦穆弘、病关索杨雄、插翅虎雷横、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没羽箭张清、赤发鬼刘唐、浪子燕青;偏将包括圣水将单廷珪(这是《水浒全传》的写法,《水浒传》则写作“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摩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病大虫薛永、摸着天杜迁、小遮拦穆春、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催命判官李立、青眼虎李云、石将军石勇、旱地忽律朱贵、笑面虎朱富、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白面郎君郑天寿、金钱豹子汤隆、操刀鬼曹正、白日鼠白胜、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活闪婆王定六(这是《水浒全传》的写法,《水浒传》则写作“霍闪婆王定六”)、鼓上蚤时迁。关于这些将佐,《水浒全传》第112回概括为:“正偏将佐共四十七员,正将一十五员,偏将三十二员,朱武偏将之首,受军师之职。”[2]965《水浒传》第92回概括为:“正偏将佐共四十七员,正将一十四员,偏将三十三员。朱武偏将之首,受军师之职。”[1]1146两种概括都将朱武作为“偏将之首”,纳入“偏将”范围。既然将朱武纳入偏将的范围,那么,就不能说“正将一十五员,偏将三十二员”,而应当说“正将一十四员,偏将三十三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传》第92回的概括优于《水浒全传》第112回的概括。
《水浒全传》第112回说,卢俊义在攻打宣州的过程中,“智深困于阵上,不知去向”[2]972。然而实际情况是,鲁智深根本没有跟随卢俊义,而是在宋江手下攻打别处。《水浒传》第92回在描写卢俊义攻打宣州时,没有说“智深困于阵上,不知去向”,而是讲“程胜祖自阵上不知去向”[1]1154;这里提到的“程胜祖”,乃是方腊的部下,这讲得通。
以上这些例子,涉及的《水浒传》有关环节优于《水浒全传》;然而,这些例子无法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找到线索。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由于篇幅所限,就不继续列举了。所有这些例子,尚不能说明100回本与120回本问世的先后顺序,还需要进一步作出考察。
(二)《水浒全传》大量环节优于《水浒传》,这些环节与《大宋宣和遗事》没有关联。
《水浒传》第13回和《水浒全传》第13回,都讲到青面兽杨志在北京东郭的故事。《水浒传》第13回说,杨志与周谨在比枪法前,向演武厅后“去了枪尖,都用毡片包了,缚成骨朵,身上各换了皂衫,各用枪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1]158。二人上马,出到阵前。“两个在阵前来来往往,翻翻复复,搅做一团,扭做一块。鞍上人斗人,坐下马斗马,两个斗了四五十合。看周谨时,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看杨志时,只有左肩胛上一点白。”[1]160随后,杨志与周谨比试箭法,周谨仍然败给杨志。“梁中书见了大喜,叫军政司便呈文案来,教杨志截替了周谨职役。杨志喜气洋洋,下了马,便向厅前来拜谢恩相,充其职役。”[1]161这时,急先锋索超出面,要与杨志比试武艺。二人“纵马出阵,都到教场中心,两马相交,二般兵器并举。索超忿怒,轮手中大斧,拍马来战杨志。杨志逞威,拈手中神枪,来迎索超。两个在教场中间,将台前面,二将相交,各赌平生本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当下杨志和索超两个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梁中书……传下将令,叫唤杨志、索超。旗牌官传令,唤两个到厅前,都下了马,小校接了二人的军器。两个都上厅来,躬身听令。梁中书叫取两锭白银,两副表里来,赏赐二人。就叫军政司将两个都升做管军提辖使,便叫贴了文案,从今日便参了他两个。”[1]164-165《水浒传》第13回的这些情节,在《水浒全传》第13回得以再现。基于这些情节,《水浒传》第13回将标题概括为“急先锋东郭争功”和“青面兽北京斗武”[1]158,《水浒全传》第13回将标题概括为“青面兽北京斗武”和“急先锋东郭争功”[2]116。显然,《水浒传》第13回标题的两句话将事情的顺序弄颠倒了,而《水浒全传》第13回标题的两句话符合事情发展的逻辑。
《水浒传》第26回与《水浒全传》第26回相比,正文的故事一样,但是标题的表述不同。《水浒传》第26回标题的两句话,分别是“郓哥大闹授官厅”和“武松斗杀西门庆”[1]330。其中,“武松斗杀西门庆”的表述没有问题,而“郓哥大闹授官厅”则存在问题。《水浒传》第26回说,武松把何九叔、郓哥带到县厅上。“知县见了,问道:‘都头告甚么?’武松告说:‘小人亲兄武大,被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药谋杀性命,这两个便是证见。要相公做主则个!’知县先问了何九叔并郓哥口词,当日与县吏商议。原来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得说,因此官吏通同计较道:‘这件事难以理问。’知县道:‘武松,你也是个本县都头,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便问他杀人公事,莫非忒偏向么?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即行。’武松怀里去取出两块酥黑骨头,一张纸,告道:‘复告相公,这个须不是小人捏合出来的。’知县看了道:‘你且起来,待我从长商议。可行时便与你拿问。’何九叔、郓哥都被武松留在房里。当日西门庆得知,却使心腹人来县里许官吏银两。”“次日早晨,武松在厅上告禀,催逼知县拿人。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回出骨殖并银子来,说道:‘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狱吏便道:‘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收了银子和骨殖,再付与何九叔收了。下厅来到自己房内,叫土兵安排饭食与何九叔同郓哥吃,留在房里”[1]337-338。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郓哥到厅作证了,但是并没有什么“大闹”。因此,《水浒传》第26回标题前一句“郓哥大闹授官厅”的表述是不对的。《水浒全传》第26回标题的两句话,分别是“偷骨殖何九叔送丧”和“供人头武二郎设祭”[2]245,这两个表述都可以与正文的内容对应起来,不存在问题。
《水浒传》第64回标题的两句话,分别是“呼延灼夜月赚关胜”和“宋公明雪天擒索超”[1]817;《水浒全传》第64回标题的两句话,分别是“呼延灼月夜赚关胜”和“宋公明雪天擒索超”[2]599。前者有“夜月”对“雪天”,后者有“月夜”对“雪天”。显然,“月夜”对“雪天”,强于“夜月”对“雪天”。所以,《水浒全传》第64回标题的表述比较好。
《水浒传》第72回标题前一句是“柴进簪花入禁院”[1]906,《水浒全传》第72回标题前一句是“柴进簪花入禁苑”[2]662。前者出现“禁院”,后者出现“禁苑”。《水浒传》第72回的正文提到“禁门”“内苑”[1]909,《水浒全传》第72回的正文也提到“禁门”[2]664“内苑”[2]665。因此,标题中宜使用“禁苑”而非“禁院”。可见,《水浒全传》第72回标题前一句的表述比较好。
《水浒传》第81回标题后一句是“戴宗定计赚萧让”[1]1010。相关情节是:“……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议:‘……萧让、乐和在高太尉府中,怎生得出?’戴宗道:‘我和你……扮作公人,去高太尉府前伺候。等他府里有人出来,把些金银贿赂与他,赚得一个厮见,通了消息,便有商量。’当时两个换了结束,带将金银,径投太平桥来。在衙门前窥望了一回,只见府里一个年纪小的虞候,摇摆将出来。”[1]1019-1020戴宗许诺给小虞候银子,让他引乐和出来相见一面。小虞候应允,急急入府去了。“戴宗、燕青两个……等不到半个时辰,只见那小虞候慌慌出来说道:‘先把银子来!乐和已叫出在耳房里了。’戴宗与燕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就把银子与他。虞候得了银子,便引燕青耳房里来见乐和。那虞候道:‘你两个快说了话便去。’燕青便与乐和道:‘我同戴宗在这里,定计赚你两个出去。’乐和道:‘直把我们两个养在后花园中,墙垣又高,无计可出。折花梯子尽都藏过了,如何能勾出来?’燕青道:‘靠墙有树么?’乐和道:‘傍墙一边,都是大柳树。’燕青道:‘今夜晚间,只听咳嗽为号,我在外面,漾过两条索去。你就相近的柳树上,把索子绞缚了,我两个在墙外各把一条索子扯住,你两个就从索上盘将出来。四更为期,不可失误。’那虞候便道:‘你两个只管说甚的,快去罢。’乐和自入去了,暗暗通报了萧让。燕青急急去与戴宗说知,当日至夜伺候。”“且说燕青、戴宗两个,就街上买了两条粗索,藏在身边,先去高太尉府后看了落脚处。原来离府后是条河,河边却有两只空船缆着,离岸不远,两个便就空船里伏了。看看听的更鼓已打四更,两个便上岸来,绕着墙后咳嗽。只听的墙里应声咳嗽,两边都已会意,燕青便把索来漾将过去。约莫里面拴系牢了,两个在外面对绞定,紧紧地拽住索头。只见乐和先盘出来,随后便是萧让,两个都溜将下来,却把索子丢入墙内去了。”[1]1020-1022这些内容与其叫“戴宗定计赚萧让”,不如称“戴宗定计赚乐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正文用大量笔墨写乐和出入太尉府,不久乐和翻墙到太尉府外又先于萧让。《水浒全传》第81回标题后一句将这些事情概括为“戴宗定计出乐和”[2]736,这比较恰当。
以上这些例子,都着重于分析章回标题。现在,探讨一些只涉及正文内容的例子。
《水浒传》第54回写到宋徽宗设朝时,提到一首七律:“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列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1]703第99回写到宋徽宗设朝时,又提到一首七律:“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宣召边庭征战士,九重深处见天颜。”[1]1245两首七律略有差别:前一首七律的第四句和第五句分别有“列”字和“佩”字,后一首七律的第四句和第五句分别有“拥”字和“珮”字;前一首七律第七句和第八句分别是“独有凤凰池上客”和“阳春一曲和皆难”,后一首七律第七句和第八句分别是“宣召边庭征战士”和“九重深处见天颜”。两首七律除了这些差别外,其他内容完全一样,重复太多。然而,与《水浒传》第54回相对应的《水浒全传》第54回,以及与《水浒传》第99回相对应的《水浒全传》第119回,则没有这两首诗,避免了重复。
《水浒传》第93回与《水浒全传》第113回是相互对应的。二者都提到:关胜战刘赟,秦明战张威,花荣战徐方,徐宁战邬福,朱仝战苟正,黄信战郭世广,孙立战甄诚,郝思文战昌盛。关于这些对阵,《水浒传》第93回作出这样的描绘:“征尘迷铁甲,杀气罩银盔。绣旗风摆团花,骏马烟笼金革占。英雄关胜,舞青龙刀直奔刘赟;猛健徐宁,挺金枪勇冲邬福。节级朱仝逢苟正,铁鞭孙立遇甄诚。秦明使棍战张威,郭世广正当黄信。徐方举槊斗花荣,架隔难收;昌盛横刀敌思文,遮拦不住。”[1]1159《水浒传》第93回的这些描绘,用很多文字写谁与谁交战,同前文重复很多。《水浒全传》第113回则作出这样的描绘:“征尘乱起,杀气横生。人人欲作哪吒,个个争为敬德。三十二条臂膊,如织锦穿梭;六十四只马蹄,似追风走雹。队旗错杂,难分赤白青黄;兵器交加,莫辨枪刀剑戟。试看旋转烽烟里,真似元宵走马灯。”[2]974《水浒全传》第113回的描绘避免了与前文的重复,明显优于《水浒传》第93回的描绘。
《水浒传》第94回与《水浒全传》第114回是相互对应的。《水浒传》第94回说:“宋江使人送徐宁到秀州去养病。不想箭中药毒,调治半月之上,金疮不痊身死。这是后话。”[1]1176隔了四五句话,正文即说:“后半月,徐宁已死,申文来报。”[1]1176在两个材料距离非常近的情况下,既然后一个材料说“后半月,徐宁已死”,那么,前一个材料就没有必要说徐宁“调治半月之上,金疮不痊身死”,当然也没有必要说“这是后话”。这些问题,在《水浒全传》第114回中得以避免。《水浒全传》第114回说:“宋江使人送徐宁到秀州去养病,不想箭中药毒,调治不痊。”[2]987隔了三四句话,正文又说:“后半月徐宁已死,申文来报。”[2]987显然,《水浒全传》第114回的处理办法优于《水浒传》第94回的处理办法。
《水浒传》第99回与《水浒全传》第119回是相互对应的。《水浒传》第99回说:“宋兵人马,迤逦前进。比及行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手下军人来报宋先锋。宋江见报,亲自领医人来看治李俊。李俊道:‘哥哥休误了回军的程限,朝廷见责,亦恐张招讨先回日久。哥哥怜悯李俊时,可留下童威、童猛看视兄弟,待病体痊可,随后赶来朝觐。哥哥军马,请自赴京。’宋江见说,心虽不然,倒不疑虑,只得引军前进。又被张招讨行文催趱,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自同诸将上马赴京去了。”“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商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1]1244-1245宋江回到东京以后,在呈天子的表文中,将李俊、童威、童猛三人纳入“不愿恩赐,于路辞去”[1]1247的人员范围。这些内容前后存在矛盾。既然李俊在宋江面前诈病,称病体痊可即回京,而宋江“不疑虑”,那么,为什么宋江在呈天子的表文中,将李俊等三人纳入“不愿恩赐,于路辞去”的人员范围呢?这些情节前后冲突。《水浒全传》第119回继续保留了这些情节,但是增加了这样一个细节:宋江回京以后、朝见天子以前,有人“从苏州来,报说李俊原非患病,只是不愿朝京为官,今与童威、童猛不知何处去了”[2]1036。这样,就能够自圆其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水浒全传》第119回强于《水浒传》第99回。
以上这些例子,涉及的《水浒全传》有关环节优于《水浒传》;然而,这些例子无法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找到线索。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由于篇幅所限,就不继续列举了。就已经提到的例子而言,分别涉及《水浒传》第13回、第26回、第54回、第64回、第72回、第81回、第93回、第94回、第99回,《水浒全传》第13回、第26回、第54回、第64回、第72回、第81回、第113回、第114回、第119回,可以说涵盖的范围很广泛。在这样广泛的范围内,《水浒全传》大量环节优于《水浒传》。而前文所提《水浒传》一些环节优于《水浒全传》,仅仅涉及《水浒传》第37回、第75回、第92回和《水浒全传》第37回、第75回、第112回,可以说涵盖的范围非常狭窄。这些情况说明,总的来看,《水浒全传》对《水浒传》有许多改进和完善,《水浒全传》的质量高于《水浒传》。因此,可以初步判断:100回本问世在先,120回本问世在后。当然,这只是初步判断,有待继续验证。
(三)《水浒传》某些环节劣于《水浒全传》,这些环节与《大宋宣和遗事》存在关联。
无论《水浒传》第20回和第21回,还是《水浒全传》第20回和第21回,都有“郓城县月夜走刘唐”和“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但是有关具体情况存在明显区别。
在《水浒传》中,从“郓城县月下走刘唐”到“宋江怒杀阎婆惜”,有这样四个材料:
第一个材料:受梁山首领晁盖派遣,刘唐赍书一封,并黄金一百两,到郓城县看望宋江。宋江只留下一条金子,连同晁盖书信,插在自己的招文袋内。刘唐离开时,“天色昏黄,是八月半天气,月轮上来”[1]251。当晚,宋江遇到阎婆,给了一些施舍。
第二个材料:“忽一朝,那阎婆因来谢宋江,见他下处没有一个妇人家面”,想把自己的女儿阎婆惜与宋江,便托人于次日向宋江说成了此事。宋江“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金玉”。“宋江又过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1]254-255
第三个材料:“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一日,宋江带张三来阎婆惜家吃酒,张三与婆惜相互喜欢上了,此后打得火热。阎婆惜“并无半点儿情分在那宋江身上。宋江但若来时,只把言语伤他,全不兜揽他些个。这宋江……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张三和这婆惜,如胶似漆,……有些风声吹在宋江耳朵里。宋江……自此有个月不去。”[1]255-256
第四个材料:“忽一日晚间,却好见那阎婆赶到县前来”[1]256。阎婆硬缠着将宋江弄到婆惜处。当夜,宋江与婆惜话不投机。约莫已是二更,婆惜躺下睡了。宋江“把头上巾帻除下,放在桌子上,脱下上盖衣裳,搭在衣架上。腰里解下銮带,上有一把压衣刀和招文袋,却挂在床边栏干子上。脱去了丝鞋净袜,便上床去那婆娘脚后睡了。半个更次,听得婆惜在脚后冷笑。宋江心里气闷”[1]262。宋江在婆惜处捱到五更,穿衣下楼。在街上,宋江遇到卖汤药的王公。宋江在吃二陈汤以后,猛然发现招文袋没有带在身边。当宋江返回婆惜处时,婆惜已经发现了招文袋中的秘密。婆惜激怒宋江,宋江杀死婆惜。
在以上四个材料中,相继使用了“八月半”“忽一朝”“没半月之间”“又过几日”“半月十日”“有个月”“忽一日晚间”等用语;它们意味着,从刘唐回梁山,到宋江杀婆惜,相隔时间起码有一两个月。问题在于,刘唐都离开这么久了,宋江还将存有晁盖书信的招文袋带在身边,以至将其忘在婆惜处,导致机密泄露;其中的时间跨度过于长久,情节安排不够合理。
与《水浒传》不同,《水浒全传》先写宋江结识阎婆,与阎婆惜建立起关系,可是婆惜私通他人;再写刘唐与宋江见面,宋江收下晁盖书信和一条黄金,并放入招文袋;最后写在刘唐离开的当晚,宋江到婆惜处,结果婆惜在凌晨发现招文袋的秘密,最终引发宋江杀死婆惜。这样的情节安排,比《水浒传》的有关情节安排要合理得多。
《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其中说,晁盖“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忽一日,宋江父亲作病,遣人来报。宋江告官给假,归家省亲。在路上撞着杜千、张岑两个,是旧时知识,在河次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姓索名超的在彼饮酒;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粗棍限棒,也将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会。是时索超道:‘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写着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泺,寻着晁盖去也。”“宋江回家,医治父亲病可了,再往郓城县公参勾当。却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3]40-41。这些情节,同《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中的有关情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别。然而,《大宋宣和遗事》中的这些情节,同《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中的有关情节仍然具有可比性。《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有关情节,有四点比较重要:第一点,先提到刘唐,后提到婆惜;第二点,刘唐离开不久,婆惜就知道了宋江的秘密;第三点,刘唐离开与宋江杀人之间,婆惜私通他人;第四点,从刘唐离开到宋江杀人,相隔时间较长。其中,第一点、第三点、第四点与《水浒传》比较一致,第二点与《水浒全传》比较一致。所以,从“郓城县月下走刘唐”到“宋江怒杀阎婆惜”,《水浒传》与《大宋宣和遗事》一致的地方比较多,《水浒全传》与《大宋宣和遗事》一致的地方比较少。
既然《水浒传》与《大宋宣和遗事》一致的地方比较多,《水浒全传》与《大宋宣和遗事》一致的地方比较少,那么,就可以说:受《大宋宣和遗事》的影响,100回本的《水浒传》中相继出现刘唐见宋江、刘唐回梁山、宋江收婆惜、婆惜私通他人、宋江杀婆惜等故事,可是婆惜发现宋江秘密的时间,则由《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很早改变为《水浒传》中的很晚,从而出现了前文曾分析过的不合理之处;后来,120回本的《水浒全传》消除了这些不合理之处,先写宋江收婆惜、婆惜私通他人,再写刘唐见宋江、刘唐回梁山,很快又发展到婆惜发现宋江秘密、宋江杀婆惜。如果说前文提到“100回本问世在先,120回本问世在后”时,还只是“初步判断”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完全断定:100回本的《水浒传》问世先于120回本的《水浒全传》。
三、基于《水浒传》若干现有事实,作出推理:100回本中应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
100回本的《水浒传》问世先于120回本的《水浒全传》,但是,《水浒传》中没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不过,在《水浒传》中,却具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赖以存在的一系列因素。
(一)乱世之中田虎、王庆已现。
《水浒传》反映的时代是北宋末年。当时,官府腐败,人民苦难,这种现实在《水浒传》中得到体现。就以西门庆为例,第24回说他“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1]303。这里说的仅仅是阳谷县的一些情况,其实京城也是一团糟。第12回说,牛二“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被叫做“没毛大虫”,“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1]151。天子脚下,一个小地痞就能闹成这个样子。在第85回中,辽国的欧阳侍郎说得再清楚不过:“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1]1062。与此相联系,与北宋同时并存的其他一些政权纷纷对北宋用兵。这种事实,连北宋朝廷内部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承认了。在第82回中,殿前都太尉宿元景就在宋徽宗面前提到了这类事情。完全可以说,北宋朝廷内外交困。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不但出现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而且发生田虎起义和王庆起义。在第72回中,柴进入禁苑,在睿思殿见到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1]909这就说明,田虎、王庆与宋江、方腊一道上了朝廷的“黑名单”。
(二)宋江始终愿意报效朝廷。
《水浒传》的主人公宋江秉持忠义精神。从宋江内心深处来说,他一直不想造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宋江还是上了梁山。上梁山以后特别是宋江成为当家人以后,他脑子里报效朝廷的念头仍然存在。这里提几件事情。在第71回中,英雄排座次之前,宋江提出“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1]893。英雄排座次之时,宋江为首盟誓说,众兄弟“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1]903。英雄排座次之后,宋江曾作一首《满江红》,其中提到:“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1]903-904不久,宋江又对部下说,“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1]904在第72回中,宋江作乐府词一首,其中提到:“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1]916在第82回中,宋江对部下说,“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1]1029。宋江至死都崇尚忠义之名,他也是这样要求众兄弟的。
(三)朝廷精于利用归降人员。
面对诸多造反者,朝廷能镇压就镇压,不能镇压就想办法招安,招安以后加以利用。在第78回中,高俅征讨梁山泊,受其指挥、为其出力的有十个节度使,他们“旧日都是在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1]977。高俅说,这十个节度使“多曾与国家建功,或征鬼方国,或伐西夏,并大金、大辽等处”[1]977。对于宋江等108人,朝廷也希望招安和利用。不过,招安宋江等人的过程并不顺利;为了招安宋江等人,宋徽宗前后三次降旨。第一次降旨时,由于蔡京、高俅捣乱,未能招安。但是,宋徽宗很有耐心,又有第二次降旨;第二次降旨时,高俅再次从中作梗,仍然没有成功招安。然而,宋徽宗招安宋江等人的兴趣不减,又有第三次降旨,终于招安宋江等人。招安宋江等人,不是为了把他们养起来。在第74回中,御史大夫崔靖向宋徽宗奏道:“臣闻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此是曜民之术。民心既伏,不可加兵。即目辽兵犯境,各处军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为不便。以臣愚意,此等山间亡命之徒,皆犯官刑,无路可避,遂乃啸聚山林,恣为不道。若降一封丹诏,光禄寺颁给御酒珍羞,差一员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伏乞陛下圣鉴。”[1]940这就清晰地说明,朝廷酝酿招安宋江等人时,已经考虑利用他们伐辽国了。伐辽国以后,自然还得去平息朝廷“黑名单”上的王庆、田虎以至方腊。
综上所述,既然乱世之中田虎和王庆都已出现,而宋江始终愿意报效朝廷,朝廷又善于利用宋江,那么,宋江征田虎、讨王庆,就是符合逻辑的了。这就意味着,《水浒传》中应当有征田虎、讨王庆的故事。
四、依据《水浒传》和《水浒全传》若干内容出入,得出判断:100回本剔除原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
虽然100回本的《水浒传》中应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但是实际上这两段故事在该书中并没有出现。笔者通过探讨《水浒传》和《水浒全传》若干内容的出入,发现《水浒传》剔除了以前曾经存在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
(一)关于宋江征战的两首五律。
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有这样一首诗:“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2]947
在《水浒传》第78回中,有这样一首诗:“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1]975
在《水浒传》第99回中,有这样一首诗:“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内中有四个,谈笑又还乡。”[1]1240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水浒传》第78回中的诗,在表述上与《水浒全传》第110回中的诗完全一样;《水浒传》第99回中的诗,在表述上与《水浒全传》第110回中的诗略有不同。这样来看,实际上一共有两首诗。这些诗都提到了“三十六”和“十八双”。由此,笔者联想到,在《水浒全传》第39回中,黄文炳向蔡九知府提到街市小儿的四句话:“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关于小儿话的前两句,黄文炳解释为“宋江”。关于小儿话的后两句,黄文炳的解释是:“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数;‘播乱在山东’,今郓城县正是山东地方。”[2]367在《水浒传》第39回中,也有这些情节。那么,在前面提到的诗中,“三十六”和“十八双”该如何理解呢?是从人数角度理解,还是从时间角度理解?下面,结合诗在小说中出现的背景,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并且对诗进行整体研究。
首先,分析和研究《水浒全传》第110回中的诗。
《水浒全传》第91回至第110回的故事线索是:宋江等108人从东京出发,到河北征田虎;征田虎成功以后,宋江等108人没有返回东京,而是到淮西讨王庆;讨王庆成功以后,宋江等108人返回东京。第110回在写到宋江等108人朝见天子时,提到了这首诗:“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2]947
诗的前两句是:“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从人数角度来理解,字面的意思就是:去的时候有36人,回来的时候也有36人。然而,实际情况是:宋江等众兄弟去的时候是108人,回来的时候也是108人。在108人中,包括天罡星36员、地煞星72员。如果将诗句中的“三十六”与“十八双”理解为借代手法,用天罡星36员代表108人,也是讲得通的。这样,从人数角度就解释通了。如果从时间角度解释,就是:去时三十六岁,回来也是三十六岁;或者去时三十六年,回来也是三十六年。这种解释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所以不宜采用。
诗的后两句是:“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宋江等人河北征田虎、淮西讨王庆,当然可以解释为“纵横千万里”。至于“谈笑却还乡”,如果理解为胜利以后返回东京,也不是绝对不行。笔者以为,作如下解释会更好:宋江等108人到河北、淮西征讨,表现得潇洒大方,把在这些地方作战看作回家乡。《水浒全传》第71回在讲“梁山泊英雄排座次”[2]651故事时,明确提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2]659在108人中,有一些人的确来自河北和淮西,这些人到河北、淮西作战,是名副其实的“还乡”;沾这些人的“光”,其他弟兄到河北、淮西也可以算作“还乡”。
可见,《水浒全传》第110回中的这首诗,摆放位置合适,反映事实准确。
其次,分析和研究《水浒传》第78回中的诗。
《水浒传》第78回开头有一首赋,其中提到:“……大闹山东,纵横河北。步斗两赢童贯,水战三败高俅。非图坏国贪财,岂敢欺天罔地。施恩报国,幽州城下杀辽兵;仗义兴师,清溪洞里擒方腊。千年事迹载皇朝,万里清名标史记。”[1]975随即正文说“后有诗为证”。该诗就是:“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1]975这样,这首诗就与《水浒传》中梁山英雄的全部活动联系起来了,特别是与伐辽国、打方腊故事联系起来了。这里谈谈这首诗与伐辽国、打方腊的关系。
诗的前两句是:“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如果从人数角度来解释,就是:去时有36人,回来时也有36人。宋江等众弟兄伐辽国,去时有108人,回来时也有108人;对此,可将天罡星36员作代表,说成“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可是,打方腊的情况就复杂了。在第90回中,宋江出师打方腊。出师以前,公孙胜辞别归山,“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1]1124;金大坚、皇甫端留京“驾前听用”[1]1129;蔡太师“索要圣手书生萧让”,王都尉“求要铁叫子乐和”[1]1130。这样算来,总计103员将领去打方腊。至于打方腊成功以后回到京师的将领,依据第99回的说法,只有“二十七员”[1]1245。所以,就打方腊而言,“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这两句话从人数角度解释不通。至于从时间角度解释为36年或36岁,更无法说明白。
诗的后两句是:“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单独说伐辽国,叫“纵横千万里”比较勉强;单独说打方腊,叫“纵横千万里”也比较勉强。如果将伐辽国、打方腊合起来,叫“纵横千万里”就比较合理了。宋江等人伐辽国,胜利归来,可以叫“谈笑却还乡”。至于宋江等人打方腊,伤亡惨重;作战江南也好,返回京师也好,均无法叫“谈笑却还乡”。
可见,《水浒传》第78回中的这首诗,无论摆放位置,还是反映事实,都出现明显的问题。
最后,分析和研究《水浒传》第99回中的诗。
在《水浒传》第99回中,宋江打方腊成功以后,班师回朝。正文在写到“宋江与同诸将引兵马离了睦州,前望杭州进发”时,提到一首诗:“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内中有四个,谈笑又还乡。”[1]1240
诗的前两句是:“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如果从人数角度解释,就是:宋江等36人去打方腊,回来时也是36人。前文提到过,在《水浒传》中,宋江打方腊,去的将领有103员,回到京师的将领有27员。如果对照这些事实,“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这两句话讲不通。“三十六”与103员将领无法对应,“十八双”与27员将领也无法对应。可能有人会说,可以用天罡星36员代表将领103员。然而问题在于,公孙胜是在天罡星范围之内的;打方腊前夕,公孙胜辞别,就剩下天罡星35员了,无法用天罡星36员代表将领103员了。不过,如果仅就打方腊成功以后宋江等人“离了睦州,前望杭州进发”这个时间段来说,“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这两句话还算讲得通,当时确实有36员将领率军行进。可是,这里的36人有拼凑的嫌疑。《水浒传》第96回说,在打方腊的过程中,“杭州城内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员将佐,是张横、穆弘、孔明、朱贵、杨林、白胜,患体未痊,不能征进;就拨穆春、朱富看视病人,共是八员,寄留于杭州”[1]1198。第99回说,打方腊成功以后,宋江在睦州“思念亡过众将,洒然泪下。不想患病在杭州张横、穆弘等六人,朱富、穆春看视,共是八人在彼,后亦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杨林、穆春到来,随军征进”[1]1239。既然说宋江在睦州“思念亡过众将”,就应当包括了在杭州死去的张横等六人。既然说“杨林、穆春到来,随军征进”,就意味着他们的到来以及张横等六人之死,发生在打方腊成功以前。可是,打方腊成功以后,宋江却在睦州“不想”张横等六人“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杨林、穆春到来”。这些情况有些矛盾,杨林、穆春两人似乎是被作者强行安排到睦州以凑足36人似的。退一步说,即使36人不是拼凑出来的,“宋江三十六,回来十八双”这两句话适用的时间范围也很短,等宋江等人到了杭州就不适用了,下文将具体说到有关情况。只截取这么短暂的时间,先说“三十六”,后说“十八双”,来回折腾这个数有多少意义呢?如果将“宋江三十六”解释为年龄,倒有些道理。第18回说宋江“年及三旬”[1]219,第99回说宋江36岁,大体解释得通。不过,“回来十八双”这句话,从时间角度就不好解释了;如果仍然说成宋江36岁,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诗的后两句是:“内中有四个,谈笑又还乡。”宋江军马从睦州回到杭州以后,鲁智深坐化,武松出家。宋江等人收拾军马回京,“比及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风病瘫了,杨雄发背疮而死,时迁又感搅肠沙而死。宋江见了,感伤不已。丹徒县又申将文书来,报说杨志已死,葬于本县山园。林冲风瘫,又不能痊,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视,后半载而亡”[1]1243。在从杭州返回京师的路上,燕青、李俊、童威、童猛又离开。至于返回京师以后,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所有这些情况很复杂,决不是“内中有四个,谈笑又还乡”两句话所能概括得了的。而就所谓“谈笑又还乡”的“四个”来说,也是存在问题的。这“四个”,指燕青、李俊、童威、童猛。根据第61回的表述,燕青是“北京土居人氏”[1]780;可是在第99回中,燕青离开时说要“寻个僻净去处”[1]1243,结果“径不知投何处去了”[1]1244。至于李俊、童威、童猛,据第36回中李俊所说,李俊本人“祖贯卢州人氏”,童威、童猛是“浔阳江边人”[1]460;可是,第99回说,李俊、童威、童猛等人“投化外国去了”[1]1245。鉴于这些情况,不能说燕青、李俊、童威、童猛四人“谈笑又还乡”。
可见,《水浒传》第99回中的这首诗,存在诸多问题:前两句表述不够准确,只能勉强适用于宋江等人从睦州返回杭州的途中;后两句说的是宋江等人离开杭州以后的一些情况,既不能涵盖全部情况,又与描述对象的行为存在出入。所以,《水浒传》第99回中的这首诗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水浒全传》第110回中的诗没有问题,《水浒传》第78回中的诗和第99回中的诗都存在问题。由这些诗,笔者联想到《大宋宣和遗事》中的一首诗:“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3]43-44《水浒全传》和《水浒传》中的这些诗,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这首诗。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大宋宣和遗事》中的这首诗,在《水浒传》中居然演化为两首大同小异的诗,它们分别置于两种背景下,并且都存在明显问题。《水浒传》第78回中的诗承接一篇赋而来,而赋中描述的内容包括打方腊在内;《水浒传》第99回中的诗,则出现于打方腊成功以后,正文在写宋江等人向杭州前进时提到这首诗。这两首诗出现问题,都是由于与打方腊发生了关联。《水浒全传》第110回中的诗,被用于征田虎、讨王庆之后,诗的成功之处在于与征田虎、讨王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两段故事恰恰是《水浒传》所没有的。这些情况说明:《水浒传》第78回中的诗是硬插进去的,《水浒传》第99回中的诗也是硬插进去的;不该存在大同小异的两首诗,而应当是一首诗;该诗出现的位置须与征田虎、讨王庆密切相关,然而《水浒传》将曾经存在的这两段故事剔除了。
(二)关于燕青射雁的两个地点。
《水浒传》第90回和《水浒全传》第110回,都有燕青射雁的故事。
在《水浒传》第90回中,燕青射雁的故事是这样的:
……且说宋江等众将,下到五台山下,引起军马,……
……在路行了数日,……前进到一个去处,地名双林渡。宋江在马上正行之间,仰观天上,见空中数行塞雁,不依次序,高低乱飞,都有惊鸣之意。宋江见了,心疑作怪,又听的前军喝采,使人去问缘由。飞马回报,原来是浪子燕青初学弓箭,向空中射雁,箭箭不空,却才须臾之间,射下十数只鸿雁,因此诸将惊呀不已。宋江教唤燕青飞马前来。这燕青头戴着白范阳遮尘毡笠儿,身穿着鹅黄纻丝衲袄,骑一匹五明红沙马,弯弓插箭,飞马而来,背后马上捎带死雁数只,来见宋江。下马离鞍,立在一边。宋公明问道:“恰才你射雁来?”燕青答道:“小弟初学弓箭,见空中群雁而来,无意射之,不想箭箭皆中,误射了十数只雁。”宋江道:“为军的人,学射弓箭,是本等的事。射的亲,是你能处。我想宾鸿避暑寒,离了天山,衔芦渡关,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此宾鸿仁义之禽,或数十,或三五十只,递相谦让,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遇晚宿歇,亦有当更之报。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不失其意。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空中遥见死雁,尽有哀鸣之意,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为义也;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预避鹰雕,衔芦过关,此为智也;秋南冬北,不越而来,此为信也。此禽五常足备之物,岂忍害之!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数只,比俺弟兄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兄弟今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燕青默默无语,悔罪不及。宋江有感于心,在马上口占一首诗道:“山岭崎岖水渺茫,横空雁阵两三行。
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
宋江吟诗罢,不觉自己心中凄惨,睹物伤情。当晚屯兵于双林渡口。宋江在帐中,因复感叹燕青射雁之事,心中纳闷,叫取过纸笔,作词一首:
“楚天空阔,雁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净,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的相思一点。暮日空濠,晓烟古堑,诉不尽许多哀怨!拣尽芦花无处宿,叹何时玉关重见!嘹呖忧愁呜咽,恨江渚难留恋。请观他春昼归来,画梁双燕。”
宋江写毕,递与吴用、公孙胜看。词中之意,甚是有悲哀忧戚之思。宋江心中郁郁不乐。当夜吴用等设酒备肴,饮酌尽醉方休。次早天明,俱各上马,望南而行。路上行程,正值暮冬,景物凄凉。宋江于路,此心终有所感。不则一日,回到京师,屯驻军马于陈桥驿,听候圣旨。”[1]1120-1122
在《水浒传》的这些材料中,宋江说鸿雁“离了天山,衔芦渡关,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这就意味着:鸿雁春天飞到北方,秋天飞到南方。然而,宋江又说鸿雁“秋南冬北”,这里存在问题,“秋南冬北”应为“秋南春北”之误。上述材料还指明:燕青射雁的时间是“暮冬”,地点是从五台山到东京路上的“双林渡”。可是,双林渡属于典型的北方地带,这里的暮冬时节怎么能有鸿雁呢?宋江的词提到“楚天空阔”,这与前面说的“双林渡”相矛盾;宋江的诗提到“山岭崎岖水渺茫”,可是前文写到双林渡时并没有涉及山。所以,在燕青射雁的故事上,《水浒传》的安排存在着错乱。
在《水浒全传》中,燕青射雁的时间也是在“暮冬”[2]947,但是其他一些细节同《水浒传》相比有所变化。在《水浒全传》中,燕青射雁发生在讨王庆结束的时候。该书第100回结尾在预说后文时,将宋江率军讨王庆称为“猛将雄兵定楚郢”[2]883。在第110回中,宋江讨王庆成功,“兵马共十余万,离了南丰,取路望东京来”。“于路行了数日,到一个去处,地名秋林渡。那秋林渡在宛州属下内乡县秋林山之南。”[2]946《水浒全传》中燕青射雁的地点,就在这里。内乡县也好,秋林山也好,都真实地存在着。更重要的是,秋林渡在京师的南方。暮冬射雁之事安排在这样的地方是否完全合理,姑且不论,但是起码比《水浒传》中安排在京师的北方要合理得多。《水浒全传》第110回将燕青射雁之事安排在秋林渡,能够与宋江词中提到的“楚天空阔”[2]947统一起来,起码是大体统一起来。《水浒全传》第110回在描写秋林渡时说,“那山泉石佳丽,宋江在马上遥看山景”[2]946,这里既有山又有水,能够与宋江词中提到的“山岭崎岖水渺茫”[2]947呼应起来。与暮冬时节秋林渡燕青射雁相贯通,宋江说鸿雁“秋南春北”[2]947,这有别于《水浒传》第90回中宋江关于鸿雁“秋南冬北”的说法。所有这些情况说明,在燕青射雁的故事上,《水浒全传》的安排是顺畅的。
无论《水浒传》第90回,还是《水浒全传》第90回,都有“五台山宋江参禅”的故事。在该故事中,智真长老送给宋江四句偈语。《水浒传》第90回将这四句偈语表述为:“当风雁影翻,东阙不团圆。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1]1119《水浒全传》第90回则将偈语的第一句表述为“当风雁影翩”[2]812,其他三句不变。总的来看,《水浒传》的表述和《水浒全传》的表述大同小异,没有根本区别。下面,将这四句偈语分别置于《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之中来分析。
在《水浒传》第90回中,智真长老送宋江偈语以后不久,就发生了燕青射雁的事情。燕青射雁,原来是“初学弓箭”,但是“箭箭皆中”[1]1120。发生这样怪异的事情,实际上意味着宋江等人的绝大多数将面临灭顶之灾。这些情况,与“当风雁影翻,东阙不团圆”这两句偈语可以贯通起来。燕青射雁的地点是“双林渡”,然而这个名称与“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中的“双林”无法统一起来。既然燕青于“双林渡”射雁是宋江等人的绝大多数陷入灭顶之灾的预兆,那么,“双林”就与灾难的必然性联系起来了;这种情况,与“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存在矛盾,两句偈语将“双林”与福寿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了。
在《水浒全传》第90回中,智真长老送宋江偈语以后,没有很快发生燕青射雁的事情,但是正文写宋江等众兄弟回京,仍然提到他们“雁行般排着,一对对并辔而行”[2]812,而且后来在第110回中于“秋林渡”终究发生了燕青射雁的事情。“当风雁影翩,东阙不团圆”这两句偈语,与秋林渡燕青射雁密切相关。秋林渡燕青射雁,意味着宋江等人的绝大多数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灭顶之灾。然而,在第90回中,宋江等人下了五台山以后不久,到达的地点叫“双林镇”[2]812。“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两句偈语,肯定与“双林镇”有关。在“双林镇”,燕青“遇故”[2]810,宋江也见到此人。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宋江见那人相貌古怪,丰神爽雅,忙下马来,躬身施礼道:‘敢问高士大名?’那人望宋江便拜道:‘闻名久矣!今日得以拜见。’慌的宋江答拜不迭,连忙扶起道:‘小可宋江,何劳如此。’那人道:‘小子姓许,名贯忠,祖贯大名府人氏,今移居山野。昔日与燕将军交契,不想一别有十数个年头,不得相聚。后来小子在江湖上,闻得小乙哥在将军麾下,小子欣慕不已。今闻将军破辽凯还,小子特来此处瞻望,得见各位英雄,平生有幸。欲邀燕兄到敞庐略叙,不知将军肯放否?’燕青亦禀道:‘小弟与许兄久别,不意在此相遇。既蒙许兄雅意,小弟只得去一遭。哥哥同众将先行,小弟随后赶来。’宋江猛省道:‘兄弟燕青,常道先生英雄肝胆,只恨宋某命薄,无缘得遇。今承垂爱,敢邀同往请教。’许贯忠辞谢道:‘将军慷慨忠义,许某久欲相侍左右,因老母年过七旬,不敢远离。’宋江道:‘恁地时,却不敢相强。’又对燕青说道:‘兄弟就回,免得我这里放心不下。况且到京,倘早晚便要朝见。’燕青道:‘小弟决不敢违哥哥将令。’又去禀知了卢俊义,两下辞别。宋江上得马来,前行的众头领,已去了一箭之地,见宋江和贯忠说话,都勒马伺候。当下宋江策马上前,同众将进发。”[2]813燕青到了许贯忠家中,二人坐地对饮。“数杯酒后,窗外月光如昼。燕青推窗看时,……云轻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燕青夸奖不已道:‘昔日在大名府,与兄长最为莫逆。自从兄长应武举后,便不得相见。却寻这个好去处,何等幽雅!像劣弟恁地东征西逐,怎得一日清闲?’贯忠笑道:‘宋公明及各位将军,英雄盖世,上应罡星。今又威服强虏。像许某蜗伏荒山,那里有分毫及得兄等。俺又有几分儿不合时宜处,每每见奸党专权,蒙蔽朝廷,因此无志进取,游荡江河,到几个去处,俺也颇颇留心。’说罢大笑,洗盏更酌。燕青取白金二十两,送与贯忠道:‘些须薄礼,少尽鄙忱。’贯忠坚辞不受。燕青又劝贯忠道:‘兄长恁般才略,同小弟到京师觑方便,讨个出身。’贯忠叹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妒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燕青点头嗟叹。”[2]814《水浒全传》第90回的这些材料,显示和展现了“双林镇道路”:许贯忠在实际上提出了宋江等108人应该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是单独对燕青讲的,但是其中的道理对宋江等人也是适用的,而且宋江本人也见到了许贯忠。这时还没有发生燕青射雁的事情,还未呈现灾难的必然性,宋江等人还有选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只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两句偈语是讲得通的。
以上这些空间问题,《水浒传》的处理不很合理或很不合理,《水浒全传》的处理比较合理或非常合理。这些问题,分别涉及《水浒传》第90回和《水浒全传》第90回、第100回、第110回。就《水浒传》来说,它的第90回使伐辽国已经成功的宋江等人直接过渡到打方腊,这与《水浒全传》有关内容出入很大。就《水浒全传》来说,第90回是宋江从伐辽国过渡到征田虎的重要中间环节;在第100回中,宋江征田虎成功,并且即将过渡到讨王庆;在第110回中,宋江讨王庆成功,并且过渡到打方腊。在《水浒全传》第90回中,也就是征田虎前夕,智真长老送宋江的偈语能够自圆其说;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讨王庆成功以后,燕青在秋林渡射雁,具体情节比较合理。而在《水浒传》中,没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在该书第90回中,智真长老送宋江的偈语不能自圆其说,燕青在双林渡射雁的故事存在不合理之处。所有这些情况,是在100回本的《水浒传》问世先于120回本的《水浒全传》之背景下发生的。这就说明,100回本的《水浒传》剔除了曾经存在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
(三)关于一些军马的两种称呼。
在《水浒传》和《水浒全传》中,很多时候把军马叫作“三军”,这成为军马的一般称呼;有些时候则把军马叫作“五军”,这成为军马的特殊称呼。
“五军”作为特殊称呼,有时是基于军马被分作五队、五起或五路而产生的。
例如,《水浒传》第55回说:“……宋江……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后军十将簇拥,两路伏兵分于左右。……为头五军,都一字儿摆在阵前……”[1]710
又如,《水浒传》第58回说:“饮筵中间,宋江唤铁面孔目裴宣定拨下山人数,分作五军起行。……梁山泊点起五军,共计二十个头领,马步军兵三千人马。”[1]742
再如,《水浒传》第68回说:“吴用……教会集诸将,一同商议:‘……我这里分调五支军将,可作五路……’……”[1]863“……宋江部领五军兵将大进,正是枪刀流水急,人马撮风行。”[1]865
以上这些例子,在《水浒全传》中也出现了。
“五军”作为特殊称呼,有时似乎基于军马被分作五队而产生,然而又好像笔误所致。《水浒传》第12回说:“……将台上竖起一面净平旗来,前后五军一齐整肃。将台上把一面引军红旗磨动,只见鼓声响处,五百军列成两阵,军士各执器械在手。”[1]157在这个例子中,既提到“前后五军”,又提到“五百军”,使人感觉“五军”称呼基于“五百军”被分作五队而产生;不过,正文毕竟没有明确说“五百军”被分作五队,所以不能完全排除“五军”系“三军”之误的可能性。这个例子在《水浒全传》中也出现了。
“五军”作为特殊称呼,有时肯定不是基于军马被分作五队、五起或五路而产生,的的确确是一种笔误。《水浒传》第88回说:“宋江……令裴宣且将衣袄给散军将。……当日……赏劳三军。”“来日,结束五军都起。……”[1]1100-1101在这个材料中,既出现了“三军”称呼,又出现了“五军”称呼。不过,材料中没有说把军马分作五队、五路或五起;所以,“五军”是“三军”之误。结果,造成了“五军”与前面的“三军”混用,两个称呼相隔只有几个字。这个例子在《水浒全传》中也出现了。
与由于笔误而产生的“五军”称呼不同,那些基于军马被分作五队、五起或五路而产生的“五军”称呼,是作者特意写出的;既然是特意写出的,就需要有意识地将“五军”与“三军”两个称呼适当加以区分,以免混淆。在这方面,无论《水浒传》,还是《水浒全传》,都有成功的例子。
《水浒传》第47回说:“宋江……传将令,教军士都披挂了。李逵、杨雄前一队做先锋,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穆弘居左,黄信在右,宋江、花荣、欧鹏等中军头领,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比及杀到独龙冈上,是黄昏时分,宋江催趱前军打庄。……庄上只是不应。……宋江……猛省道:‘……他必有计策,快教三军且退。’”[1]616第48回说:“……当下宋江……教小喽啰只往大路杀将去,只听得五军屯塞住了,众人都叫苦起来。”[1]618在这个由《水浒传》第47回有关材料和第48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中,第48回出现的“五军”称呼,基于第47回中军马分作五队而产生;“五军”称呼与“三军”称呼分别出现于第48回和第47回,没有直接连起来混用。这个例子在《水浒全传》第47回和第48回中也出现了。
《水浒传》第78回说:“高太尉……分拨王焕、徐京为前部先锋,王文德、梅展为合后收军,张开、杨温为左军,韩存保、李从吉为右军,项元镇、荆忠为前后救应使。党世雄引领三千精兵,上船协助刘梦龙水军船只,就行监战。诸军尽皆得令,整束了三日,请高太尉看阅诸路军马。高太尉亲自出城,一一点看了,便遣大小三军并水军,一齐进发,径望梁山泊来。”[1]980-981然而,高太尉所率军马被梁山军马打败;其过程,第78回有详细描述。结果,高太尉“忙传钧令,且教收兵回济州去,别作道理。五军比及要退,又值天晚,只听得四下里火炮不住价响”[1]983。在这个由《水浒传》第78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中,“五军”称呼基于陆路军马被分为五路而产生,该称呼与前面的“三军”称呼虽然出现在同一回中,但是在正文中隔着数个自然段,保持了明显的距离,没有直接连起来混用。这个例子也出现在《水浒全传》第78回中。
《水浒传》第90回,在写到宋江出师打方腊时说:“当有宿太尉、赵枢密亲来送行,赏劳三军。水军头领已把战船从泗水入淮河,望淮安军坝,俱到扬州取齐。宋江、卢俊义谢了宿太尉、赵枢密,别了上路,将军马分作五起,取旱路投扬州来。”[1]1131第91回又说:“……先锋使宋江,奉着诏敕,征剿方腊,兵马战船,五军诸将,水陆并进,船骑同行,已到淮安了,约至扬州取齐。”[1]1134在这个由《水浒传》第90回有关材料和第91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中,第91回出现的“五军”称呼,基于第90回提到的“将军马分作五起”而产生;“五军”称呼与“三军”称呼分别出现于第91回和第90回,没有直接连起来混用。
有些时候虽然军马被分作五队、五路或五起,但是正文并没有提到“五军”。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将“五军”称呼暗藏了,或者省略了。无论《水浒传》,还是《水浒全传》,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水浒传》第41回说:“……分作五起进程:头一起便是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刘唐、杜迁、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黄信、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顺、王矮虎、穆弘、穆春、郑天寿、白胜。五起二十八个头领,带了一干人等,……”[1]530在这个由《水浒传》第41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中,虽然说人马“分作五起”,但是没有提“五军”,甚至也没有提“三军”,从而避免了两个称呼的混淆。这个例子在《水浒全传》第41回中也出现了。
《水浒传》第99回说:“宋江领起大队军马,分开五路,杀入洞来,争捉方腊。……”“……阮小七杀入内苑深宫里面,搜出一箱,却是方腊伪造的平天冠、衮龙袍、碧玉带、白玉圭、无忧履。阮小七……便把衮龙袍穿了,系上碧玉带,着了无忧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圭插放怀里,跳上马,手执鞭,跑出宫前。三军众将只道是方腊,一齐闹动,抢将拢来看时,却是阮小七,众皆大笑。”[1]1236在这个由《水浒传》第99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中,虽然说军马“分开五路”,但是正文只提“三军”而不提“五军”,从而避免了两个称呼的混淆。这个例子在《水浒全传》第119回中也出现了。
《水浒全传》第89回说,宋江伐辽国成功,于是班师回朝,“将军马分作五起进发,克日起行”[2]809。第90回说,宋江在班师回朝途中,上五台山参禅。下五台山以后,“宋江传令,催趱军马起程,众将得令,催起三军人马,望东京进发。凡经过地方,军士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来看王师。见宋江等众将英雄,人人称奖,个个钦服”。“宋江等在路行了数日,到一个去处,地名双林镇。”[2]812在这个由《水浒全传》第89回有关材料和第90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中,第89回说“将军马分作五起”,第90回只提“三军”而不提“五军”,从而避免了两个称呼的混淆。
《水浒全传》第92回说:“……宋江统领军兵人马,分五队进发,来打盖州。”[2]824第93回说:“……宋江大队人马,入盖州城,便传下将令,先教救灭火焰,不许伤害居民。众将都来献功。……天明出榜,安抚百姓。将三军人马,尽数收入盖州屯住,赏劳三军诸将。”[2]831在这个由《水浒全传》第92回有关材料和第93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中,第92回说军马“分五队”,第93回只提“三军”而不提“五军”,从而避免了两个称呼的混淆。
《水浒全传》第110回说,宋江讨王庆成功,于是班师回朝,“将兵马分作五起进发,克日起行,军士除留下各州县镇守外,其间亦有乞归田里者。现今兵马共十余万,离了南丰,取路望东京来。军有纪律,所过地方,秋毫无犯。百姓香花灯烛价拜送”。“于路行了数日,到一个去处,地名秋林渡。”[2]946在这个由《水浒全传》第110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中,虽然说“将兵马分作五起”,但是没有提“五军”,甚至也没有提“三军”,从而避免了两个称呼的混淆。
《水浒全传》第110回,在写到宋江出师打方腊时说:“……当有宿太尉、赵枢密亲来送行,赏劳三军。水军头领已把战船从泗水入淮河,望淮安军坝,俱到扬州取齐。宋江、卢俊义谢了宿太尉、赵枢密,将人马分作五起,取旱路投扬州来。”[2]954-955第111回又说:“……先锋使宋江兵马战船,水陆并进,已到淮安了,约至扬州取齐。”[2]956在这个由《水浒全传》第110回有关材料和第111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中,第110回提到“三军”以及“将人马分作五起”,而第111回没有提“五军”,甚至也没有提“三军”,从而避免了两个称呼的混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的“五军”称呼并没有被暗藏或省略,而且基于军马被分作五起而产生,但是居然与“三军”称呼连起来混用了。《水浒传》第89回说,宋江伐辽国成功,于是班师回朝,“将军马分作五起进发,克日起行”[1]1115。第90回说,宋江在班师回朝途中,上五台山参禅。下五台山以后,“宋江传令催趱军马起程。众将得令,催起三军人马,望东京进发。在路行了数日,五军前进到一个去处,地名双林渡”[1]1120。在这个由《水浒传》第89回有关材料和第90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中,第90回中的“五军”称呼,基于第89回提到的“将军马分作五起”而产生;但是,在第90回中,“五军”与“三军”两个称呼相隔只有十多个字,这就混淆起来了。
从《水浒传》第41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到《水浒全传》第41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从《水浒传》第47回和第48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到《水浒全传》第47回和第48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从《水浒传》第78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到《水浒全传》第78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从《水浒传》第90回和第91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到《水浒全传》第110回和第111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从《水浒传》第99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到《水浒全传》第119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从《水浒全传》第89回和第90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到《水浒全传》第92回和第93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再到《水浒全传》第110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所有这些例子,都没有混淆“三军”与“五军”两个称呼。与这些例子不同,《水浒传》第89回和第90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却混淆了“三军”与“五军”两个称呼,显得非常奇怪,格外值得思考;这个例子,与《水浒全传》第89回和第90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关系特别密切,与《水浒全传》第110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关系也特别密切。《水浒传》第89回有关材料和第90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是从伐辽国成功到燕青射雁的过渡;《水浒全传》第89回有关材料和第90回有关材料共同构成的例子,是从伐辽国成功到燕青遇故的过渡;《水浒全传》第110回有关材料构成的例子,是从讨王庆成功到燕青射雁的过渡。在《水浒全传》中,伐辽国成功与燕青射雁之间的主要内容,就是征田虎、讨王庆的故事。问世较晚的《水浒全传》,在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边沿地带成功地处理了“三军”与“五军”两个称呼的关系;而问世较早的《水浒传》,却在从伐辽国成功到燕青射雁的过渡中没有处理好“三军”与“五军”两个称呼的关系,而且特别明显和怪异,这就暴露了修改痕迹。这种修改,就是100回本的《水浒传》剔除了曾经存在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剔除以后,小说在进行新的连接时出现了漏洞,在“三军”与“五军”两个称呼的关系上出现混乱。120回本的《水浒全传》解决了这个问题,将混乱纠正过来。
总之,从关于宋江征战的两首五律,到燕青射雁的两个地点,再到一些军马的两种称呼,充分说明:100回本的《水浒传》剔除了曾经存在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与之相对应的是,120回本的《水浒全传》恢复了征田虎、讨王庆故事。
五、依据《水浒全传》若干内容类似,得出判断:120回本重新撰写征田虎、讨王庆故事
100回本的《水浒传》剔除了原来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120回本的《水浒全传》恢复了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然而,这种恢复并非毫无差别地回到原样,而是重新撰写。这可以通过《水浒全传》中若干内容的类似得到说明。
(一)宋江等人伐辽国以后和讨王庆以后两见天子的类似。
在《水浒传》第90回中,伐辽国已经成功的宋江等人朝见天子;此后不久,宋江等人去打方腊。在《水浒全传》第90中,伐辽国已经成功的宋江等人朝见天子;此后不久,宋江等人去征田虎,随即又去讨王庆。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讨王庆已经成功的宋江等人朝见天子;此后不久,宋江等人去打方腊。《水浒全传》第90回中的朝见天子和第110回中的朝见天子,都来源于《水浒传》第90回中的朝见天子,是略加改造而来的;这些情况,使得《水浒全传》第90回中的朝见天子、第110回中的朝见天子与《水浒传》第90回中的朝见天子有一些近似之处,从而使得《水浒全传》第90回中的朝见天子与第110回中的朝见天子有不少类似之处。
《水浒传》第90回说:“先是宿太尉并赵枢密中军人马入城,宿太尉、赵枢密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京,已到关外。赵枢密前来启奏天子,说宋江等诸将边庭劳苦之事。天子闻奏,大加称赞,就传圣旨,命黄门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见,都教披挂入城。”“且说宋江等众将,屯驻军马在于陈桥驿,听候宣诏入朝。黄门侍郎传旨,教宋江等众将一百八员都要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惟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边塞用心,中伤者多,寡人甚为忧戚。’宋江再拜奏曰:‘皆托圣上洪福齐天,边庭宁息。臣等众将,虽有金伤,俱各无事。今已沙塞投降,实陛下仁育之赐。’再拜称谢。……天子命光禄寺大设御宴。”[1]1122-1123“当日天子亲赐御宴已罢,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等赏赐,尽于内府关支。宋江与众将谢恩已罢,尽出宫禁,都到西华门外,上马回营。一行众将,出的城来,直至行营安歇,听候朝廷委用。”[1]1123-1124
与《水浒传》第90回相近似,《水浒全传》第90回说:“……先是宿太尉并赵枢密中军人马入城,已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军,已到关外。赵枢密前来启奏,说宋江等诸将边庭劳苦之事。天子闻奏,大加称赞,就传圣旨,命黄门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见,都教披挂入城。宋江等众将,遵奉圣旨,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惟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边塞用心,中伤者多,寡人甚为忧戚。’宋江再拜奏道:‘托圣上洪福齐天,臣等众将,虽有中伤,俱各无事。今逆虏投降,边庭宁息,实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劳之有?’再拜称谢。”“……天子……仍敕光禄寺大设御宴,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给赏金帛,尽于内府关支。宋江与众将谢恩已罢,尽出宫禁,都到西华门外,上马回营安歇,听候圣旨。”[2]815
与《水浒全传》第90回相类似,《水浒全传》第110回说:“……先是陈安抚并侯参谋中军人马入城,已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京,已到关外。陈安抚前来启奏,说宋江等诸将征战劳苦之事,天子闻奏,大加称赞。……传下圣旨,命黄门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见,都教披挂入城。”“且说宋江等众将一百八人,遵奉圣旨,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惟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进劳苦,剿寇用心,中伤者多,寡人甚为忧戚。’宋江再拜奏道:‘托圣上洪福齐天,臣等众将虽有金伤,俱各无事,今元凶授首,淮西平定,实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劳之有。’再拜称谢”“天子命光禄寺大设御宴,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赏赐有差,尽于内府关支。宋江与众将谢恩已罢,尽出宫禁,都到西华门外,上马回营。一行众将,出的城来,直到行营安歇,听候朝廷委用。”[2]947-948
《水浒全传》中宋江等人伐辽国以后和讨王庆以后两次朝见天子的相似之处,初步说明该书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是重新撰写的。如果是原汁原味的故事,不可能存在这些连成一片的相似之处,原作者绝对不会那样写小说;正因为是重新撰写的,有关人员才参考甚至照搬了其他地方的不少语言。
(二)征田虎和打方腊两个故事导出过程和手段的类似。
《水浒传》第90回的部分文字,交代了朝廷派宋江等人打方腊的由来;《水浒全传》第110回的部分文字,交代了朝廷派宋江等人打方腊的由来;《水浒全传》第90回的部分文字和第91回的部分文字,交代了朝廷派宋江等人征田虎的由来。《水浒全传》中宋江等人打方腊的导出过程和手段,来源于《水浒传》中宋江等人打方腊的导出过程和手段,二者几乎一模一样;而《水浒全传》中宋江等人征田虎的导出过程和手段,又与《水浒全传》中宋江等人打方腊的导出过程和手段有很多类似之处。为了便于观看,笔者选取其中比较明显的内容,进行列举和对比。
在《水浒传》第90回中,一位老人对燕青说:“……如今江南草寇方腊反了,占了八州二十五县,从睦州起,直至润州,自号为一国,早晚来打扬州。”[1]1128与此相对应,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一位老人对燕青说:“……如今江南草寇方腊反了,占了八州二十五县,从睦州起,直至润州,自号为一国,早晚来打扬州。……”[2]952与此相类似,在《水浒全传》第91回中,一位公人对戴宗说:“田虎那厮,侵州夺县,官兵不能抵敌。近日打破盖州,早晚便要攻打卫州。……”[2]817
《水浒传》第90回说:“燕青、李逵听了这话,慌忙还了茶钱,离了小巷,径奔出城,回到营中,来见军师吴学究,报知此事。”[1]1128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燕青、李逵听了这话,慌忙还了茶钱,离了小巷,径奔出城,回到营中,来见军师吴学究,报知此事。”[2]952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1回说:“戴宗、石秀得了这个消息,也算还酒钱,离了酒店,回到营中,见宋先锋报知此事。”[2]817
《水浒传》第90回说:“吴用……来对宋先锋说知江南方腊造反,……宋江听了道:‘我等军马诸将,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于天子前保奏,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1]1128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吴用……来对宋先锋说知江南方腊造反,……宋江听了道:‘我等诸将军马,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于天子前保奏,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2]952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1回说:“宋江与吴用商议道:‘我等诸将,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奏闻天子,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吴用道:‘此事须得宿太尉保奏方可。’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2]817
《水浒传》第90回说:“次日,宋江换了些衣服,带领燕青,自来说此一事。径入城中,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闻知,即忙教请进。宋江来到堂上,再拜起居。”[1]1128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次日,宋江换了些衣服,带领燕青,自来说此一事。径入城中,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闻知,忙教请进。宋江来到堂上,再拜起居。”[2]952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1回说:“次日,宋江穿了公服,引十数骑入城,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知道,忙教请进。宋江到堂上再拜起居。”[2]817
在《水浒传》第90回中,宋江对宿太尉说:“……上告恩相。听的江南方腊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润州,早晚渡江,来打扬州。宋江等人马久闲,在此屯扎不宜。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望恩相于天子前题奏则个!”[1]1128与此相对应,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宋江对宿太尉说:“……上告恩相。听的江南方腊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润州,早晚渡江,来打扬州。宋江等人马久闲,在此屯扎不宜。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望恩相于天子前题奏则个!”[2]952与此相类似,在《水浒全传》第91回中,宋江对宿太尉说:“上告恩相,宋某听得河北田虎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侵至盖州,早晚来打卫州。宋江等人马久闲,某等情愿部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望恩相保奏则个。”[2]817
在《水浒传》第90回中,宿太尉对宋江说:“……下官当以一力保奏,……”[1]1128与此相对应,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宿太尉对宋江说:“……下官当以一力保奏。……”[2]952与此相类似,在《水浒全传》第91回中,宿太尉对宋江说:“……宿某当一力保奏。”[2]817
《水浒传》第90回说:“宋江辞了太尉,自回营寨,与众弟兄说知。”[1]1129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宋江辞了太尉,自回营寨,与众兄弟说知。”[2]953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1回说:“至晚,宋江回营,与众头领说知。”[2]817
《水浒传》第90回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与百官文武计事,正说江南方腊作耗,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年建号,如此作反,自霸称尊,目今早晚兵犯扬州。”[1]1129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与百官文武计事,正说江南方腊作耗,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年建号,如此作反,自霸称尊,目今早晚兵犯扬州。”[2]953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1回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省院官正奏:‘河北田虎造反,占据五府五十六县,改年建号,自霸称王。目今打破陵川,怀州震邻,申文告急。’”[2]817
在《水浒传》第90回中,宿太尉向天子奏道:“……陛下已遣张总兵、刘都督,再差……宋先锋,这两支军马为前部,可去剿除,必干大功。”[1]1129与此相对应,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宿太尉向天子奏道:“……陛下已遣张总兵、刘都督,再差……宋先锋,这两支军马为前部,可去剿除,必干大功。”[2]953与此相类似,在《水浒全传》第91回中,宿太尉向天子奏道:“……今有……宋先锋,屯兵城外,乞陛下降敕,遣这枝军马前去征剿,必成大功。”[2]817
《水浒传》第90回说:“天子闻奏大喜:……急令使臣宣省院官听圣旨。……省院官到殿,领了圣旨,随即宣取宋先锋、卢先锋,直到披香殿下,朝见天子。拜舞已毕,……”[1]1129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天子闻奏大喜,急令使臣宣省院官听圣旨。……”“省院官到殿,领了圣旨,随即宣取宋先锋、卢先锋,直到披香殿下,朝见天子。拜舞已毕,……”[2]953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1回说:“天子大喜,即令省院官奉旨出城,宣取宋江、卢俊义,直到披香殿下,朝见天子。拜舞已毕,……”[2]817
《水浒传》第90回说:“……天子降敕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骑,彩段二十五表里。其余正偏将佐,各赐段匹银两,待有功次,照名升赏,加受官爵。三军头目,给赐银两,都就于内府关支,定限目下出师起行。”[1]1129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天子降敕,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封卢俊义为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骑,彩缎二十五表里。其余正偏将佐,各赐缎匹银两,待有功次,照名升赏,加受官爵。三军头目,给赐银两。都就于内务府关支,定限目下出师起行。”[2]953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1回说:“天子……降敕封宋江为平北正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各赐御酒、金带、锦袍、金甲、彩缎,其余正偏将佐,各赐缎匹银两。待奏荡平,论功升赏,加封官爵。三军头目,给赐银两,都就于内府关支。限定日期,出师起行。”[2]818
《水浒传》第90回说:“宋江一面调拨战船先行,着令水军头领自去整顿篙橹风帆,撑驾望大江进发;传令与马军头领,整顿弓箭枪刀,衣袍铠甲。水陆并进,船骑同行……”[1]1130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宋江一面调拨战船先行,着令水军头领整顿篙橹风帆,撑驾望大江进发,传令与马军头领,整顿弓、箭、枪、刀、衣袍、铠甲。水陆并进,船骑同行,……”[2]954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1回说:“宋江与吴用计议,着令水军头领,整顿战船先进,自汴河入黄河,至原武县界,等候大军到来,接济渡河。传令与马军头领,整顿马匹,水陆并进,船骑同行,……”[2]818
征田虎、打方腊两个故事导出过程和手段的类似,再次说明《水浒全传》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是重新撰写的。重新撰写者将打方腊导出过程和手段的不少东西,移植到征田虎导出过程和手段上来了。
(三)伐辽国成功到打方腊成功期间一些零碎内容的类似。
《水浒传》第89回说,伐辽国成功以后,宋江“唤令随军石匠,采石为碑,令萧让作文,以记其事。金大坚镌石已毕,竖立在永清县东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迹尚存”[1]1115。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89回说,伐辽国成功以后,宋江“唤令随军石匠,采石为碑,令萧让作文,以记其事。金大坚镌石已毕,竖立在永清县东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迹尚存”[2]809。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101回说,征田虎成功以后,“宋江令萧让、金大坚镌勒碑石,记叙其事”[2]886。《水浒全传》第110回又说,讨王庆成功以后,“宋江教萧让撰文,金大坚镌石勒碑以记其事,立石于南丰城东龙门山下,至今古迹尚存”[2]946。
《水浒传》第89回说,伐辽国成功以后,宋江“一面先送宿太尉还京。次后,收拾诸将军兵车仗人马,分拨人员,先发中军军马,护送赵枢密起行。宋先锋寨内,自己设宴。一面赏劳水军头目已了,着令乘驾船只,从水路先回东京,驻扎听调”[1]1114-1115。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89回说,伐辽国成功以后,宋江“一面先送宿太尉还京,次后收拾诸将军兵车仗人马,分拨人员,先发中军军马,护送赵枢密起行。宋先锋寨内,自己设宴。一面赏劳水军头目已了,着令乘驾船只,从水路先回东京驻扎听调”[2]809。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110回说,讨王庆成功以后,“宋江一面先发中军军马,护送陈安抚、侯参谋、罗武谕起行,一面着令水军头领,乘驾船只,从水路先回东京,驻扎听调”[2]946。
《水浒传》第90回说,燕青射雁以后,宋江等人赶路。“不则一日,回到京师,屯驻军马于陈桥驿,听候圣旨。”[1]1122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0回说,燕青射雁以后,宋江等人赶路。“不则一日,回到京师,屯驻军马于陈桥驿,听候圣旨。”[2]947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0回说,燕青辞别许贯忠以后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恰好宋先锋屯驻军马于陈桥驿,听候圣旨,燕青入营参见”[2]815。
《水浒传》第93回描写太湖时说:“双双野鹭飞来,点破碧琉璃;两两轻鸥惊起,冲开青翡翠。”[1]1160又说:“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1]1161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3回描写太湖时说:“双双野鹭飞来,点破碧琉璃;两两轻鸥惊起,冲开青翡翠。”[2]976又说:“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2]976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93回说,在盖州城的众头领见到:“空中白鹭群飞,江上素鸥翻复。”[2]831前两个材料都提到“野鹭”“轻鸥”“白鸥”,第三个材料提到“白鹭”“素鸥”。
《水浒传》第99回说:“张招讨已传下军令,教把生擒到贼徒伪官等众,除留方腊另行解赴东京,其余从贼,都就睦州市曹斩首施行。所有未收去处,衢、婺等县贼役赃官,得知方腊已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都来睦县自行投首,拜参张招讨并众官。尽皆准首,复为良民。就行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复为乡民,拨还产业田园。克复州县已了,各调守御官军,护境安民,不在话下。”[1]1239与此相对应,《水浒全传》第119回说:“张招讨已传下军令,教把生擒到贼徒伪官等众,除留方腊另行解赴东京,其余从贼,都就睦州市曹,斩首施行。所有未收去处,衢、婺等县贼役赃官,得知方腊已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张招讨尽皆准首,复为良民。就行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复为乡民,拨还产业田园。克复州县已了,各调守御官军,护境安民,不在话下。”[2]1031与此相类似,《水浒全传》第100回说:“陈瓘、宋江一面教把生擒到贼徒伪官等众,除留田虎、田豹、田彪,另行解赴东京,其余从贼,都就威胜市曹斩首施行。所有未收去处,乃是晋宁所属蒲、解等州县。贼役赃官,得知田虎已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陈安抚尽皆准首,复为良民。就行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复为乡民,给还产业田园。克复州县已了,各调守御官军,护境安民,不在话下。”[2]883《水浒全传》第110回又说,宋军擒获王庆以后,陈安抚、宋先锋“出榜去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八十六州县,复见天日,复为良民,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拨还产业,复为乡民”[2]945。
伐辽国成功到打方腊成功期间,这些零碎内容的类似,进一步而且全方位地说明:《水浒全传》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是重新撰写的。
六、关于《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总结和评价:形成过程、积极作用、主要局限
在前面一系列探讨和研究的基础上,现在可以对《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作出总结和评价了。
(一)《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形成过程。
《水浒》成书时原著本有征田虎、讨王庆的故事;在原著流传过程中,征田虎、讨王庆的故事被剔除,于是形成100回本的《水浒传》;后来,征田虎、讨王庆的故事被恢复,于是形成120回本的《水浒全传》。120回本的《水浒全传》在恢复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时,《水浒》成书时的原著已经失传。在这种条件下,120回本的《水浒全传》不可能使征田虎、讨王庆的故事完全回到原样,只能对其进行重新撰写。重新撰写的这些故事与《水浒》成书时的原著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之间,虽然有不同和区别的地方,但是也有相同和类似的地方;由于恢复了征田虎、讨王庆的故事,120回本的《水浒全传》在总体结构上比100回本的《水浒传》更接近于《水浒》成书时的原著。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和情况,笔者以前曾以为《水浒全传》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就是《水浒》成书时的原著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笔者以前持有的这种认识虽然有待完善,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在事实上坚持了《水浒》成书时的原著本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观点。现在,本文明确提出100回本的《水浒传》剔除曾经存在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而120回本的《水浒全传》重新撰写征田虎、讨王庆故事,这就将笔者以前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本文所说的《水浒》成书时的原著、100回本的《水浒传》、120回本的《水浒全传》,都是繁本;至于简本,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这里不去涉及。
100回本的《水浒传》剔除《水浒》成书时的原著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必然出现断裂地带,从而需要进行新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容易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某些差错,或留下某些痕迹。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有些时间问题,就应是这样产生的。在《水浒传》第90回中,当着宋江等人的面,宋徽宗命省院等官计议宋江等人的封爵之事,而蔡京、童贯明说宋江等人“不可升迁”[1]1123;其中漏洞的出现,应当是由于《水浒传》剔除原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时没有处理好正文的连接问题。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剔除者,应该对剔除以后的时间衔接问题进行过统筹考虑;也许在开始修改尝试时,选择了第80回中的文书,对其中提到的时间表述作出非正式的修改。结果,原来具体的“年”“月”消失了,只保留了年号“宣和”;100回本的《水浒传》中的这个时间表述,又为120回本的《水浒全传》所沿袭。
120回本的《水浒全传》在100回本的《水浒传》基础上重新撰写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必然产生新的搭界地带,从而需要进行新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某些差错。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某些时间问题,就是这样出现的。在《水浒全传》中,根据第89回和第119回的有关内容,伐辽国成功是在宣和四年冬月,打方腊成功是在宣和五年九月,这些时间与《水浒传》中的有关时间是一致的。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时间段却无法完全容纳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现在,分析一下这种情况的具体由来。在《水浒全传》中,从伐辽国成功,到征田虎成功,再到讨王庆成功,再到打方腊成功,以至到宋江在地方任职,正文叙事(不包括倒叙)过程中出现许多时间表述。这些时间表述依次是:第89回提到“宣和四年冬月日”[2]807,第93回提到“宣和五年的元旦”[2]831,第96回提到“二月初八日”[2]850,第98回提到“二月将终”[2]865“三月十六日”[2]869,第99回提到“三月下旬”[2]873“四月上旬”[2]877,第101回提到“宣和五年四月日”[2]885“五月五日天中节”[2]886,第105回提到“七月中旬”[2]912“八月初旬”[2]914,第106回提到“八月中旬”[2]918,第108回提到“深秋天气”[2]926,第109回提到“孟冬时候”[2]943,第110回提到“正值暮冬”[2]947“正旦节”[2]949“上元节”[2]951,第111回提到“初春天气”[2]956,第114回提到“时当春暖”[2]989,第116回提到“四月尽间”[2]1001,第119回提到“九月二十后”[2]1036“宣和五年九月日”[2]1038,第120回提到“宣和六年首夏初旬”[2]1045。这些时间表述,一小部分直接点出具体年份,绝大部分没有点出具体年份;前者中的“年”十分明显,后者中的“年”比较隐晦。如果不作深入考察,而是将直接点出具体年份的时间表述提取出来,并且加以排列和比较,就很容易出现错觉。直接点出具体年份的时间表述依次是:“宣和四年冬月日”,“宣和五年的元旦”,“宣和五年四月日”,“宣和五年九月日”,“宣和六年首夏初旬”。只对这五个时间表述加以考察,怎么也不会发现问题,越看越顺溜。实际上,第110回中的“正旦节”“上元节”,并非宣和五年的“正旦节”“上元节”,而是宣和六年的“正旦节”“上元节”。相应地,第119回中的“九月二十后”,并非宣和五年的“九月二十后”,而是宣和六年的“九月二十后”;第119回中的“宣和五年九月日”,应当是“宣和六年九月日”;第120回中的“宣和六年首夏初旬”,应当是“宣和七年首夏初旬”。然而,《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重新撰写者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当然会造成伐辽国成功与打方腊成功所形成的时间段无法完全容纳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之状况。虽然如此,但是,这两段故事仍然被加了进去,而且有其积极作用。
(二)《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积极作用。
《水浒全传》中重新撰写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不是鸡肋,也不是累赘,而是宝贝。其积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水浒全传》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使小说的结构趋于完善。《水浒传》没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由100回构成;《水浒全传》恢复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由120回构成。作为《水浒全传》主人公的宋江,在第36回中暂时上梁山,很快又离开;在第41回中正式上梁山,入伙成为重要头领;在第82回中正式下梁山,接受朝廷招安;在第83回中暂时回梁山,处理一些事情。在宋江正式上梁山以前,梁山的发展有四个关键环节:杜迁、宋万、朱贵初创业,林冲上梁山,晁盖等七人上梁山,花荣等九人上梁山。宋江正式下梁山以后,宋江等人有四个关键阶段:伐辽国、征田虎、讨王庆、打方腊。宋江在梁山期间,并非始终是当家人。第60回标题后一句是“晁天王曾头市中箭”[2]559;就是在这一回中,晁盖去世。此后,宋江真正成为梁山的“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说,120回本的《水浒全传》,前半部书以晁盖为主导,后半部书以宋江为主导。总起来说,120回本的《水浒全传》在结构上比较严谨,其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所在的第91回至第110回功不可没。
《水浒全传》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使小说的内容得到充实。按照小说的内在逻辑,本就应该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如果没有这两段故事,小说内容就不完整了。就拿第72回来说,宋徽宗的“黑名单”上清楚地写明宋江、王庆、田虎、方腊;后来如果只有打方腊,而无征田虎、讨王庆,那是讲不通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存在,还为打方腊作了重要铺垫。伐辽国时,宋江部将中无人死亡;征田虎时,宋江部将中的耿恭死去;讨王庆时,宋江部将中的文仲容、崔埜、金鼎、黄钺、山士奇、卞祥、唐斌、梅玉、毕捷、潘迅、杨芳、冯升、胡迈、孙安等人死去;打方腊时,宋江部将中的绝大多数面临灭顶之灾。如果没有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作为缓冲,宋江部将从伐辽国时无人死亡,一下子就跳跃到打方腊时绝大多数死去,显得太突然了。也许有人会说,宋军伐辽国时,有将领王文斌阵亡。的确,在《水浒全传》第88回中,一员番将抡起刀,“把王文斌连肩和胸脯,砍做两段”[2]800。其实,王文斌本是“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北宋朝廷特差他“起差民夫车辆,押运衣袄五十万领,前赴宋先锋军前交割,就行催并军将,向前交战,早奏凯歌”[2]799。所以,王文斌并非宋江部将,伐辽国时宋江部将无人死亡。在伐辽国的过程中,曾有罗真人告诫宋江:“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2]775伐辽国成功以后,有许贯忠向燕青畅言,这件事在前文中已经详细说过。在征田虎过程中,一个和尚对鲁智深说:“凡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地狱天堂,皆生于念。是故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一念不生,则六道俱销,轮回斯绝。”[2]873在讨王庆的过程中,有立了功的忠贞之士萧嘉穗不恋功名富贵,而是远走高飞。讨王庆成功以后,有乔道清、马灵向宋江告辞,飘然而去。这些情况,一次又一次地警示着宋江等108人应当适可而止,以避免灾难。然而宋江始终不能觉悟,终于将众弟兄的绝大多数带上死路。以上这一切都说明,在《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实际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三)《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主要局限。
前文探讨《水浒全传》中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曾提到时间冲突、称呼不当、内容重复等问题,但是这些并非大问题。时间冲突、称呼不当虽然产生一些矛盾,但是纠正起来比较容易,修改一两个字就可以了;内容重复,充其量是有些雷同,并没有形成矛盾。《水浒全传》中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主要局限,在于一些具体情节的失真和矛盾。
在征田虎、讨王庆的过程中,宋江等108人中没有死亡的,而是一些降将死亡,这不是不可以;然而,宋江等108人中连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就显得过于绝对化了。伐辽国时,宋江等108人中也没有死亡的,不过还是有人受伤。《水浒全传》第84回说:“那天山勇在马上把了事环带住,趱马出阵,教两个副将在前面影射着,三骑马悄悄直趱至阵前。”“张清……见了,偷取石子在手,看着那番官当头的,只一石子,急叫:‘着!’早从盔上擦过。那天山勇却闪在这将马背后,安的箭稳,扣的弦正,觑着张清较亲,直射将来。张清叫声:‘阿也!’急躲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双枪将董平、九纹龙史进,将引解珍、解宝,死命去救回。卢先锋看了,急教拔出箭来,血流不止,项上便束缚兜住。随即叫邹渊、邹润扶张清上车子,护送回檀州,教神医安道全调治。”[2]765第88回说,“孔亮伤刀,李云中箭,朱富着炮,石勇着枪”,“杜迁、宋万又带重伤”[2]797。这些材料说明,在伐辽国时,宋江等108人中至少有7人受伤,有些则是重伤。可是,在征田虎、讨王庆期间,宋江等108人中居然没有受伤的,这明显不真实。
100回本的《水浒传》剔除了曾经存在的征田虎、讨王庆故事,保留了伐辽国、打方腊故事;与此相适应,《水浒传》在一些地方只提伐辽国、打方腊,而不提征田虎、讨王庆。120回本的《水浒全传》恢复了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然而在某些地方仍然只提伐辽国、打方腊,而不提征田虎、讨王庆。这样一来,有时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水浒全传》中,第54回说,罗真人送给公孙胜八个字:“逢幽而止,遇汴而还。”[2]509第85回说,在宋军伐辽国的过程中,罗真人送宋江八句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始逢冬暮,鸿雁分飞。吴头楚尾,官禄同归。”[2]775罗真人还对宋江说:“……这个徒弟公孙胜,……从今日跟将军去干大功,如奏凯还京,此时方当徒弟相辞。却望将军还放。……”[2]775所有这些,与《水浒传》中的有关表述是相同的,或是基本相同的。在《水浒传》第90回中,伐辽国成功的宋江等人回到东京,不久公孙胜向宋江辞行;在《水浒全传》第110回中,征田虎、讨王庆成功的宋江等人回到东京,不久公孙胜向宋江辞行。在公孙胜辞行的问题上,《水浒传》能够自圆其说,而《水浒全传》则不能自圆其说。这个例子涉及道人,现在再看有关僧人的例子。在《水浒全传》第90回中,智真长老对鲁智深说:“……与汝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2]812四句偈语是:“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2]812所有这些话语保留着《水浒传》中的样子。然而问题在于,四句偈语只谈到打方腊期间和打方腊以后鲁智深的一些情况,而没有涉及征田虎、讨王庆过程中鲁智深的有关情况。在这种条件下,无法说鲁智深有了四句偈语能够“终身受用”。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水浒全传》第110回以后,也就是讨王庆成功以后,小说正文仍然有不少地方在事实上回避甚至否认征田虎、讨王庆故事的存在,这是应当改进的。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3]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刘海宁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4-0507-24
收稿日期:2016-03-20
作者简介:韩亚光(1972-),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