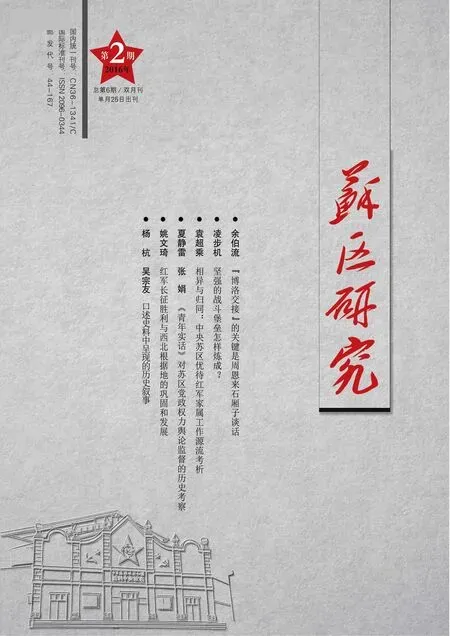红军长征胜利与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姚文琦
红军长征胜利与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姚文琦
提要:长期以来,人们对西北苏区的研究主要放在了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上,即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创造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陕北救了中央”。然而却忽视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对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央救了陕北”。重新审视红军长征胜利与西北根据地间的关系,对于深化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红军长征胜利;西北根据地;巩固;发展
今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80周年,笔者就红军长征胜利与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到达西北根据地的陕北,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根据国际国内局势,开展了扩大和巩固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并以西北根据地为大本营领导全国的革命,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1935年10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铁边城进入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吴起镇,时属陕西保安县,相传战国名将吴起曾在此驻兵戍边,为纪念而命名。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吴起”改名为“吴旗”,并设立吴旗县。2005年10月19日更名为吴起县。吴起镇现为吴起县县城。。
(一)保卫与扩大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
长征结束后,新的任务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去完成。当时,西北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一是外有蒋介石部署的重兵“围剿”(建立了“西北剿总”,调动东北军张学良部,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兵力达十余万人,形势十分危急;二是内有西北苏区“肃反”错误,西北苏区的党政军领导遭逮捕和杀害,造成根据地内危机重重,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三是中共中央立足未稳,对西北根据地的基本情况以及西北民情文化等都缺乏深入了解。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难以完成的。中共中央为此在吴起镇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目前的形势并制定了一系列新决策,坚定不移地依靠西北苏区广大军民,为解决这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会议结论,指出:第一,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第二,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毛泽东明确提出:结束了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481页。张闻天最后在报告中指出:到达陕北苏区,长征的任务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吴起镇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也开始了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西北苏区军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斗争。
为了保卫西北苏区,不使尾追中央而来的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部和宁夏马鸿宾部进入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吴起部署了“切尾巴”战斗,并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追击计划”,“使我们能在陕北站定脚跟,配合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苏维埃在西北的大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页。
(二)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壮大了西北苏区红军的力量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之后,先行出发的贾拓夫、李维汉已与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取得了联系。10月30日,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离开吴起镇向甘泉下寺湾前进。出发前,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对我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并特别强调:“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第741-742页。
11月2日,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历史、现状、政治、军事和地理情况,尤其是陕北“肃反”情况的汇报。会议研究了当前的行动方针与党政军的组织问题。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南下,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博古、李维汉、董必武、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在西北苏区的红军,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两军的汇合,使红军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军事行动接连取得胜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西北根据地。
11月5日,红一军团到达甘泉象鼻子湾。毛泽东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指出:“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295页。11月7日,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在道佐铺胜利会师。中央给红十五军团配备了电台,红十五军团向中央红军援助了5000枚大洋。为加强领导,中央先后为十五军团输送了周士第、王首道、陈奇涵等一批军政干部。两个军团会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壮大了西北苏区红军的力量,为彻底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打下了基础。
(三)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0月28日,“西北剿总”总司令蒋介石命令副总司令张学良重新调整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西北革命根据地进攻:西路以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的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〇六师、一〇八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向陕西富县推进;东路由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毛泽东、彭德怀分析了敌情,部署了直罗镇战役。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的率领下,由六架飞机掩护开进直罗镇,红军乘夜将其包围。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战至下午2时,歼一〇九师大部。此时,东西两路国民党援军迫近直罗镇。红军遂以少数兵力围困一〇九师残部和阻击由富县西援的国民党军一一七师,主力部队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的另两个师。五十七军沿葫芦河西进,红军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其一个团,其余国民党军退回合水太白镇。由富县出援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也仓皇逃回富县。与此同时,红军又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一个团。当日晚,一〇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自戕身亡。直罗镇战役,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于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毛泽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之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二、建立新的中央党政军领导机构,开始了中央直接领导西北根据地的新阶段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483页。从此开始了中央直接领导西北根据地的新阶段。
1935年11月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张闻天任书记。西北中央局并非中共中央派出机构,而是中共中央对外的暂用名称。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瑞金时,苏区中央局是履行中央职务、领导全国工作的;到陕北后,改称为西北中央局,同样领导全国工作。”*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页。同时,这也是中共中央“为了对外维护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的团结统一,为了争取南下红军重新北上,争取张国焘转变立场”而作出的“必要的重大让步”。*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19页。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后,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成立了中共陕北省委、中共陕甘省委和中共关中特委、中共神府特委、中共三边特委,1936年5月又设立了中共陕甘宁省委。
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布布告,决定在陕甘晋苏区(即西北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由博古任主席。西北办事处为西北苏区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其最高领导机构为主席团。它既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也是革命政权机关。西北办事处下设省、县、区、乡四级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西北办事处下辖陕甘、陕北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苏维埃政府及以后成立的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1937年9月,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原设的省级建制。
从1935年2月到1937年9月,经过两年八个月的艰苦斗争,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疆域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古长城、南至黄龙山,先后设立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和神府特区、关中特区、三边分区及53个苏维埃县(市)治。其中陕西境内39个县(市),甘肃境内10个县,宁夏境内4个县。
三、制止和纠正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的领导者,在西北苏区发动了“肃反”。原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干部被捕入狱,蒙受不白之冤;200多名干部被杀害。根据地内人心惶惶,干部战士无所适从;一些收编的游击队发生“反水”*即叛变之意。;国民党加紧了“围剿”,西北苏区危机四伏。这次“肃反”有其错综复杂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这里暂不赘述。只谈中央如何纠正错误“肃反”。
1935年七八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及上海临时中央局相继派河北省委原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朱理治、曾任闽浙赣军区政委和红十军团师政委的聂洪钧来到陕北,解决陕甘边苏区的所谓“右派反革命问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来到陕北后,对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和现状不作调查研究,反而听信一些人错误的汇报,指责刘志丹和其他负责人“右倾”。7月中旬,朱理治先后在延川县文安驿、永坪镇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和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北特委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中央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等5封信件,*王世泰:《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并作出《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9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为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以聂洪钧为军委主席;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通过整编,刘志丹等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众多领导人被排斥在主要领导之外。
永坪会议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六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西北苏区“肃反”的“一切问题都是在六人座谈中决定的”*《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郭洪涛、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都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商定:立即开始“肃反”,重点在张汉民(杨虎城部旅长,共产党员)和张慕陶(中共六大代表,曾任陕西省委常委)已有“布置”之处,即原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9月22日,“肃反”领导者在“火线上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印发了《陕甘晋新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第90页。9月底,在永坪召开的会议上,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
从10月1日起,在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下,“肃反”执行者开始进行大逮捕。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张策、马文瑞、王世泰、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等,以及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准备活埋的大坑都挖好了。*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除王世泰、康健民、刘约三、龚逢春、张邦英等几人因负伤或带游击队在边境活动暂未被抓捕外,陕甘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
面对“肃反”执行者的无情打击,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不低头、不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习仲勋回忆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肃反”执行者刑讯张秀山,他死不招供。张秀山忠勇刚烈的气概,就连“肃反”执行者也受到震撼,开始怀疑陕北“肃反”“肯定是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枉吧!”*《朱理治同志在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0日),参见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26页。
西北苏区的“肃反”,是王明“左”倾错误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85页。使西北根据地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是“肃反”引起苏区内极大的疑虑和恐惧。由于“肃反”,“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老百姓听到外地口音的红军也往山上跑。东地区群众听到他们的领导人马文瑞等被捕,大批向白区“跑反”*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仅宜川南原靠近白区一带就跑了700多户;保安、安塞、靖边等几个县发生“反水”。二是“肃反”导致西北苏区一些地区工作瘫痪。由于“肃反”使陕甘边区的主要领导人和有能力的青年干部悉数被捕,即使没有被捕的干部也因“肃反”的惊恐而藏匿起来,不少地方的干部不敢见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来人,听说省委来人就准备上山“打游击”。这造成陕甘边区党和军队、政府的各项工作基本处在停顿状态。三是“肃反”激起了西北根据地内的“赤安事变”,使得中共建立的一个特区政权、3个县级政府、20多个区政府、30多个乡政府受到严重破坏。
1935年10月中旬,就在西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84页。的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苏区吴起镇,并立即着手制止和纠正“肃反”。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先后听取了赤安县游击支队队长张明科,原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指挥部政委、赤安县独立营教导员龚逢春等关于西北苏区和“肃反”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明确表示: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22日,中央即派贾拓夫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等作为先遣队,携带电台寻找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贾、李二人日夜兼程,在甘泉县下寺湾找到程子华和郭洪涛,了解了“肃反”情况:“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84页。贾、李当即电告中央。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名义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84页。
11月2日,中共中央抵达下寺湾。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与郭洪涛、程子华、聂洪钧等会面,了解西北苏区“肃反”的情况。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和红军的历史与现状,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期间,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王首道:《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在下寺湾中央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制止和纠正陕北“肃反”: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先行前往关押刘志丹等的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控制事态,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成立负责审理“肃反”事件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亦称五人小组),由董必武任主任。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立即释放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杨琪、习仲勋、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朱奎、王居德、王家娃等18人。随后,其他被关押的干部也相继分批获得释放。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由前线回到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并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张闻天、博古等到齐家湾刘志丹家中慰问,并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革军委关于刘志丹履任新职的决定。周恩来亲自约张秀山谈话,帮助他打消顾虑和怨气,指出:陕北“肃反”是极端错误的。志丹、你们这些同志受了很大打击和委屈。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都是对共产党员的考验。
可贵的是,西北苏区“肃反”最大的受害者刘志丹,在备受迫害、险遭杀害之时,并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用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一再告诫蒙冤受屈的同志: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
经过20多天的调查审理,党务委员会认为,“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列举的刘志丹等人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都是莫须有的。*《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期。那些所谓的“罪状”,只能说明刘志丹等坚持了正确路线。11月18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也联名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错误,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487页。要求纠正“肃反”中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王首道:《怀念集》,第29页。
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而肃反机构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中共中央要求立即改组政治保卫局,纠正肃反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加强党的领导,保障肃反工作中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执行。*《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平反。张闻天主持会议,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接着,王首道代表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是无罪的。*《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第214页。戴季英在会上做了检查。刘志丹在会上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楚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一道奋斗。”*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西北苏区“肃反”得到及时制止,迅速纠正,挽救了西北的党、红军和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同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
中共中央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平反后,先后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刘志丹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中国人民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高岗被安排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领导骑兵团。习仲勋被安排在关中特委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任环县县委书记。张秀山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负责处理西北苏区“肃反”的李维汉后来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86页。但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顾全大局,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分配,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刘志丹、杨琪、杨森就牺牲在红军东征战役中。
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鉴于对西北苏区“肃反”的诸多问题存在分歧,中共中央对“肃反”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形成《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为此,中央对西北苏区“肃反”的主要领导者朱理治、郭洪涛给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销朱理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同时指出,程子华在这次错误“肃反”中,也应负一些责任。中共中央再次重申刘志丹、高岗等“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另外,“委托西北中央局负责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的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7-419页。
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1983】28号文件,指出“对于西北根据地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发生的错误肃反问题,我们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看到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犯错误的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姚文琦、姬乃军:《西北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
中央及时纠正了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挽救了广大的干部,挽救了革命,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保存了骨干力量。
四、中共中央巩固、扩大西北苏区的方针和政策
中共中央在制止和纠正西北苏区“肃反”的同时,还多次召开会议,发布指示,提出了巩固、扩大西北苏区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
(一)明确西北苏区的地位和任务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到达瓦窑堡的第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张闻天在会上做了《把陕北苏区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总结发言,指出:“要认识陕北苏区的重要”,“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张闻天:《把陕北苏区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页。从而明确了在历史转折关头“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思想。在此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陕甘游击战争问题、神府地区工作问题、陕北土地问题、苏维埃选举问题、反倾向斗争问题等,为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加强西北苏区军队、干部之间的团结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中央红军与地方红军的关系,尤其要求红十五军团中红二十五军“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自满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使红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500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十分关心西北苏区干部之间的团结。中央到达陕北后,苏区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到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的外来干部看不起西北地区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引起西北地区干部的不满。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认为西北地区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为此他做了耐心细致的协调工作,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中央的努力工作,加强了西北根据地军民的团结,确保了以此为中心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进程。
五、首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国。1935年11月18日,张浩到达瓦窑堡,先后见到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凭借记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其实,中共中央在张浩回国前后,对新的战略策略已有了设想。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和《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一切爱国的志士“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向全国郑重提出建立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应遵循的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473-474页。。在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到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两个月,在军事上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在政治上纠正了陕北“肃反”,克服了西北苏区的危机,团结了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组织上健全了各级机构;在物质上初步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12月中旬,国统区又传来了北平学生的“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同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恢复了,尤其是张浩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在这种新形势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势,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完满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决议》最后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50-551页。
瓦窑堡会议是在由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期间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共中央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立即投入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落实之中。12月27日,中央又在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153页。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要求,西北根据地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策略,调整了根据地内的阶级、经济等各项政策,使之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执行了中央一系列经过调整制定的新政策,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从而走向了全面发展的正确轨道。西北苏区虽然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政治上民主,人民团结,抗日情绪高涨,成为全国革命最先进的地区。
六、广泛开展西北苏区的群众工作
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后,为了实现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任务,强调西北苏区各级党政军组织必须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提出当前群众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扩大红军武装队伍;动员地方游击队担负扩大苏区的任务;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等。这些工作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立足、巩固和发展,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建立和发展西北苏区群众团体
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着手建立和恢复西北苏区的群众组织。基于过去西北苏区工会组织尚未建立和健全的状况,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页。。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36年相继成立了陕北省总工会、陕甘省总工会和几个特区、县级总工会。同时决定由共青团陕北特委领导团陕甘边区特委和整个西北苏区共青团的工作。11月,中共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共青团组织进行了改建,将共青团陕北特委改建为少共陕北省委员会、陕北省青年救国会;共青团陕甘边区特委改建为少共陕甘省委、陕甘省青年救国会。1936年2月,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统组织,改变了过去贫农团一度代替政权组织的做法。西北根据地妇女组织均设在县一级,先后在22个县设立了妇女会。工会、青年团、贫农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的建立、健全,为动员、组织苏区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二)争取哥老会和清剿股匪
哥老会是中国许多秘密结社之一,是“下层社会”人员结合起来的群众组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十分重视对哥老会的争取,先后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和《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558页。要求与哥老会在共同抗日救国的形势下联合起来,共抱义气,共赴国难。对哥老会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为了更广泛地争取民间各种帮会组织,更广泛地团结争取各种社会力量,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志丹县永宁镇马头山召开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及抗日救国军和游击队。救国会宗旨为:驱逐日寇,铲除汉奸。奋斗目标为:中华英雄大聚会,团结一致救中国,民主共和求解放,联合战线争独立。
为了打击危害地方的惯匪,中共中央和西北苏区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土匪问题,针对边区实际,制定了治匪措施,消灭了安边、三边、保安头道川、三道川的股匪,稳定了社会秩序。
中共中央和西北苏区开展的剿匪、争取哥老会的行动,为陕北民众的生活生产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使苏区人民安居乐业,从而赢得了陕北各阶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争取民众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社会基础。
七、在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进程中巩固、发展西北根据地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西北地区的集结,做好了奔赴抗日前线、保卫国土的准备。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封锁与阻拦,中国共产党人在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同时,积极倡导立即停止国共两党之间“相互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50页。
(一)东征、西征,巩固和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军事上,红一方面军总兵力虽然已有1.5万人左右,但西北人烟稀少,兵员匮乏;经济上,财政十分困难,群众负担沉重;政治环境上,西北苏区四面被国民党强敌包围。为了打破封锁,摆脱困境,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积极筹谋对策,先后组织了东征、西征战役,迎来了一、二、四方面军会师西北,巩固、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采用稳扎稳打的军事政策,进行东征。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使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番号。参战部队为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2月20日晚,红一、红十五军团1.3万人发起渡河战斗,接连取得战斗胜利,直逼太原。阎锡山致电蒋介石求援。
4月下旬,集结在山西的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已达51个团,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蒋介石的强令下向陕北推进。在敌我力量悬殊和“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的情况下,红军决定回师陕北,“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和“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等任务*毛泽东、彭德怀致周恩来、林彪等《关于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电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537页。。5月2日至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返回延长、延川一带。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效:在军事上,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并扩大红军8000多人,增强了革命力量;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在山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调动阎锡山入陕部队回防,打破了敌人对西北苏区的包围,扩大了苏区;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获得群众支持,并筹集款项30多万元,缓解了财政压力。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540页。
接着中央决定建立红军西方野战军,实施西征战役。1936年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分析政治和军事形势后,确定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任务,并做出了红军西征的决定。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从延长、延川出发,进行西征战役。经过两个多月西征作战,西方野战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据《红色中华》报道:西征以来至7月初,消灭马鸿宾部3个团,缴获长枪1500余支,俘虏2000余人,活捉旅长1人,缴无线电机两架;扩大红军800余人,筹款4.5万元,扩大新区纵横700余里,占领定边、花马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里营等地。*《红军胜利统计——西征以来至7月初止》,《红色中华》1936年7月9日。同时,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扩充了红军的队伍,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二)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大大增加了西北地区革命武装力量
在西方野战军取得西征胜利之时,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同日,西北苏区的68位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及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指出:“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林育英等庆祝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给朱德等的电报》(193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64-166页。7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由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随后,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协同北进。随着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步伐的加快,统一指挥显得十分迫切。9月19日,贺龙、任弼时要求中共中央成立军委主席团加以协调。21日,中央同意红二方面军建议,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进,红一方面军于9月30日派红一、红十五军团各一部南下,组成左右两个纵队。10月2日,右纵队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主力占领会宁。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祝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通电。10月19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城隆重举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大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大会。
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二军团到达将台堡,同红一军团领导人会师。23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与红一军团第一师陈赓部在将台堡南兴隆镇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达两年的长征宣告结束。
接着中央军委组织发动了山城堡战役,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联合作战,歼灭胡宗南部两个团,击溃一个旅。山城堡战役是中央军委正确指挥和三大主力红军协同作战的结果,对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彰显红军的作战能力和“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虽然对南京政府内部分化已有客观分析,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武力剿共政策,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把抗日和反蒋相提并论。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444页。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仍然强调党的任务是抗日反蒋。*《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36页。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开始提出“联蒋抗日”的口号。1936年1月29日,毛泽东在同《红色中华》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直率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中华苏维埃政府无时无地不在预备着和一切愿意抗日者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7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66页。2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以“抗日讨逆”取代“抗日反蒋”,并提议“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
4月9日到1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肤施即延安,是当时的县名,为延安府的州府驻地县,亦是延安的别称,肤施城亦即延安城。1937年2月,中央进驻延安后,肤施县改名为延安县,今为延安市宝塔区。会谈,张学良也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观点。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建议目前不要发布讨蒋令,指出:“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532页。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115-116页。没有再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首次使用“蒋氏”、“阎锡山氏”的称谓,表明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初步形成。
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策略的实际变化也起了关键作用。1936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共的统一战线问题,季米特洛夫提出“让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统一战线,让蒋介石率领南京军队的其他将领加入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黄修荣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8月10日,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都主张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第269页。1936年9月1日,在分析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至此,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最终形成。
尽管中共一再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策略,但蒋介石一意孤行,认为到达陕北的红军已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一方面试图通过谈判收编,一方面加紧部署军事围剿。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以谈判和防御两手应对。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随之而来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中共逼蒋抗日目标的实现。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央利用张学良参加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累遭失败、损兵折将,却得不到南京政府的补给,与蒋介石的关系逐渐恶化的时机,通过多种形式争取张学良加入统一战线。
在此期间,除中共中央释放被俘的东北军外,毛泽东还写信给东北军军长董英斌,提出“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489-490页。在对东北军高层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红军也遵照上级命令,开展俘虏教育和火线宣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认为:“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周毅、张友坤等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39页。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1936年元月,李克农与王以哲在洛川进行初步沟通,并与张学良举行正式谈判,就联合抗日等问题形成初步意见。4月9日,周恩来、张学良二人在肤施天主教堂进行协商,达成了停止内战、联蒋抗日的协议。
中共中央在争取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争取和团结工作。1935年10月,北方局地下党员南汉宸利用与杨虎城的旧部关系,通过申伯纯向杨宣传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南汉宸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西北军中开展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其亲笔信去西安面见杨虎城,推动与杨确立合作关系。信中说:“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493-494页。此举消除了杨虎城对共产党的疑虑和误会,他同意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派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的工作,更加坚定了杨虎城和中共合作的信心。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称赞杨“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并派秘书张文彬在杨虎城处联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达成了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
经过中共中央努力,到1936年冬,初步形成了由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三位一体的形成,首先使西北苏区停止了内战,为中共中央恢复和发展国统区党的工作、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最终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调停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出华北,参加全民族抗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落脚西北根据地后,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家;在这里与西北红军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纠正了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巩固了西北根据地;通过东征、西征,发展了西北根据地,迎来了三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面对民族危机,中央适时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并为之不懈努力,首先在西北形成抗日大联合,使西北根据地得到空前巩固与发展,并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解放战争指挥中心。
责任编辑:魏烈刚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and the Consolidation &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Revolutionary Base
Yao Wenqi
Abstract:For a period research regarding to the Northwest Red Army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it, together with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main impact of the contribution wa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at it created a reliable foothold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nd Long March Red Army of various branches, which explained that why Shanbei (Northern Shaanxi) saved the Central Committee. However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 Red Army to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has seldom been analyzed, which can be briefed as "the Central Committee saved Shanbei".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discuss such effect in details.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ctory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and the Northwest Revolutionary Base ,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victory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Northwest Revolutionary Base; consolidation; development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6.02.005
作者简介:姚文琦,男,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研究员。(陕西西安71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