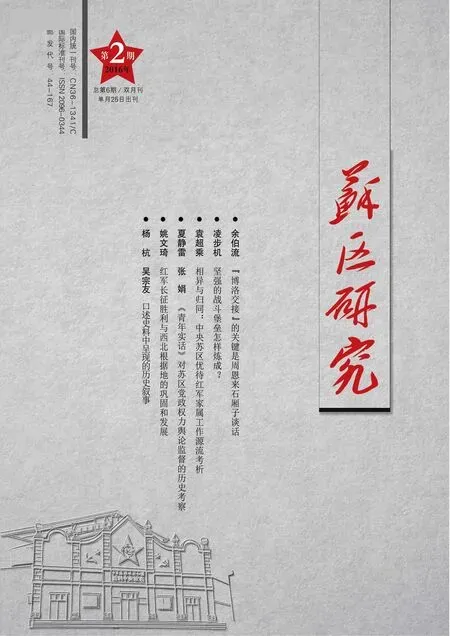试析秋收起义前委的成立及相关问题
陈洪模
试析秋收起义前委的成立及相关问题
陈洪模
提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近年来分析秋收起义的论著很多,但具体研究秋收起义领导机关前委的文章并不多。关于前委何时何地成立,目前已经大致形成了一种主流的看法,即前委于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成立;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秋收起义中先后有过两个前委。其实这两种看法不无商榷的余地。仔细比对历史文献,可得出前委是中共湖南省委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于9月10日到达铜鼓后成立这一结论。
关键词:秋收起义;毛泽东;前敌委员会;张家湾会议
秋收起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它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围绕秋收起义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但是专门探讨领导秋收起义领导机构的文章却不多见。事实上,围绕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以下有时简称前委)尚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谨就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前委的成立及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以求教于党史界的同仁。
一、长期以来许多书刊对前委成立的论述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由于档案资料公开极少,真正从学术角度对秋收起义历史开展研究的论文甚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极大改变,“实事求是”的原则得到了尊重和发扬,党史界对秋收起义历史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涉及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如何成立这一问题时,多数学者支持前委是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成立这一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书中讲到:
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安源市委委员宁迪卿,安源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杨骏,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安源军事会议主要解决了下述几个问题:成立湘赣边秋收起义暴动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原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的部队,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为驻安源的工农武装,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为驻铜鼓的部队,团长苏先骏;决定起义军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这里明确认为在安源军事会议上成立了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暴动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并且认为在这次会议上组建了起义部队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及下属的三个团,确定了三个团的领导人。
著名党史学者张侠在一本研究秋收起义的专著中也提出:“在安源会议上,首先应该宣布成立前委和有关县的行委,才能进行讨论和做出相应的决议。”他认为:“在安源会上,成立了前委的看法是比较入情合理的。”*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在这里他的口气不是十分肯定,仅认为从情理上来说,应该在安源会议上成立了前委。
《毛泽东年谱》在介绍安源会议时讲到:“会上,正式组成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这里不仅明确讲到在安源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前委,而且认为前委委员的人选也已经确定了,就是各路军的负责人。对于“各路军”的具体情况,《年谱》用引注的方式介绍是分别驻扎在修水、铜鼓和安源的三支部队。不过,书中并没有明确说这三路部队主要负责人就是前委成员。
还有很多书刊资料都提出类似的看法,*参见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安源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安源区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589页;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矿业集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黄爱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若干史实研究》,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1-2页;梅黎明主编:《峥嵘岁月井冈山斗争与中国革命》,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几乎都认为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是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成立的,区别在于有的直接说前委是在安源会议上成立,有的则没有那么直接,而是含糊地说安源会议是前委与行委的联席会议。据笔者所见,文革后最早提出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成立了领导秋收起义前委的人是何长工。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忆:“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于九月初从长沙赶到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重要会议,正式成立了有各方军事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对起义的军事行动做出了部署。”*何长工:《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何长工虽然参加过秋收起义,但是他并未出席安源张家湾会议,他的回忆是否忠实地反映了历史呢?
一本军史书提出了与上述说法相左的观点。该书认为毛泽东在安源召集会议之后,“又赶到铜鼓,召集位于修水、铜鼓的各部负责人或代表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同时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这里明确指出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是在铜鼓成立的。
还有学者提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湘赣两省工农运动的态势,中央和湘鄂赣三省省委及时调整了部署,适时改组了由湘中七县军事负责人组成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与‘师委会’进行了合并,组成了新的湘赣边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前委’)。”*涂开荣、晏迎春:《秋收起义领导机构考究——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的吗?》,《红色修水》(内刊),http://www.xiushui.gov.cn/Item.aspx?id=6125。这种看法认为存在先后两个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一个是在安源成立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一个是后来在铜鼓组成的湘赣边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有的著述虽然没有明确说先后组建了两个前委,但先说安源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面在介绍铜鼓、修水前委旧址时又将前委名称改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梅黎明主编:《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20天》,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53-54页。这种表述很容易给读者造成前后存有两个不同的前敌委员会的错觉。
至此,我们面对秋收起义的前委在安源成立、在铜鼓成立和先在安源成立而后又在铜鼓成立了一个新的前委这三种不同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在此试展开分析。
二、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领导机构的部署
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共湖南省委,在准备发动秋收起义时,一开始都没有把负责主持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称为前敌委员会的打算。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一份《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文件,准备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其中规定:“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222页。8月9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再次谈及组成湘南特委,领导暴动。“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1927年8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可见中共中央开始设想的秋收起义区域在湘南,领导机构的名称是湘南特委。
8月18日,改组后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召集第一次省委会议,选举常委,及讨论秋收暴动问题”。*《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1页。会上,毛泽东等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精力和经济力量等因素,力主缩小暴动的范围,而省委书记彭公达则主张全省暴动。
从湖南省委8月19日给中央的报告看,省委当天会议最终作出的决定实际还是采纳了彭公达的意见:“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另组织了一个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至万不能时,决夺取桂东、汝城、资兴三县,建立工农兵的政权。”*《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1927年8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4-15页。这份文件清楚表明,这时湖南省委设想的起义区域依然是“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起义的中心有两个:长沙和湘南。长沙领导起义的机构名称暂时未定,如一旦夺取长沙,这个领导机构的名称就是革命委员会;湘南的领导机构名称则为指导委员会。总之这时还没有出现前敌委员会的名称。
尽管湖南省委一度计划在全省发动暴动,但是仅凭中共在湖南省的力量,要在短时期内组织、发动全湖南的秋收起义确实没有客观基础。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最后确定“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会上“常委委员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6-117页。8月30日是文件首次记载湖南省委提出组织前委的时间,决定成立前委的机构是中共湖南省委,这两点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争议。不过,这份文件中所讲秋收起义的地域,只是长沙周围的湘中七县,后来起义实际发生地却是以铜鼓、修水和安源为核心的湘赣边界。为何出现这种重大变化,俟后分析。
有关前委成立的历史文献中,潘心源的报告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报告中转述毛泽东的话,“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5页。。这里明确说到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同时规定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前委成员,但对于前委成员具体包括哪几位军事负责人,无论是湖南省委的文件还是潘心源的报告均没有提及。如果依照前面中共湖南省委预定的湘中七县暴动计划组织前委,这七县的军事负责人自然应当是前委成员。实际情况是后来这七县中仅有安源的一支部队(负责人王新亚)参加起义,而七县之外铜鼓、修水的两支部队却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如果按湖南省委原来确定前委成员的原则,一旦参加暴动,这两支部队的负责人理应成为前委成员。可是从前面所引用的历史文献看,驻扎于修水、铜鼓两县的部队显然不在湖南省委原定的暴动计划之内,照原定计划,这两支部队的军事负责同志自然也不是前委成员。这显然是一种矛盾。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
三、具有转折意义的安源张家湾会议
要解答修水、铜鼓两支部队之所以参加秋收起义的缘由,还要从安源张家湾会议说起。
在8月30日湖南省委决定成立前委后,毛泽东从长沙经株洲赶到安源,大约在9月3日召集有关同志在张家湾传达省委指示,部署湘中七县的暴动。“到会者毛泽东、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俊等。”*《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6-157页。毛是前委书记,潘是中共浏阳县委书记,蔡是安源市委书记,宁、杨是安源市委委员,王是安源矿警队(即起义中组建的第二团)领导人。在原定举行暴动的湘中七县中,除了省委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参加张家湾会议的只有浏阳、安源两县的领导人,其他五个县的党和军事负责人并未到场,且浏阳军事负责人潘心源离开部队也近半个月,对部队最新状况并不是很清楚。如果对照湖南省委关于前委人员组成的决定,从出席者的人数、代表性来看,在安源会议上正式成立前委一说难以令人信服。
对张家湾会议记载最详细的历史档案是潘心源的报告,其中说:“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当时他们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比较多。”*《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7页。所谓“各县”,其实就是靠近湖南的修水、铜鼓(以及莲花、宁冈)等江西的偏远小县。修水、铜鼓驻有原定要参加南昌起义而未赶上的两团武装,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他们已经为秋收暴动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万建强:《中共江西省委及地方组织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历史性贡献》,《党史文苑》2007年第12期,第6-7页。潘心源来自驻铜鼓第三团的前身浏阳工农义勇队,对这些情况自然比其他同志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的发言比较多,实际上就是向大家介绍驻修水、铜鼓两支部队的情况。毛泽东得知潘心源介绍的情况后讲:“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然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9页。所谓贺、聂军队,应为贺、叶军队之误,即南昌起义部队。毛泽东一直认为光凭农民暴动难以击破敌人正规军的镇压,必须有成建制的军队参与暴动,才能与敌人的正规军抗衡。听取潘心源介绍驻修铜两团军队的情况后,毛泽东立即认识到应该将这两团部队成建制地吸收进工农革命军,作为暴动的主力,于是当即果断决定,将原定的暴动区域从“湘中七县”转变为湘赣边界,从安源、铜鼓、修水分三路向长沙进攻。毛泽东此刻果断将参加暴动的队伍由湘中七县转变为湘赣边三支队伍,但暴动进攻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依然是湖南省委原定的长沙,而且这样转变后胜算显然比较大。潘兴源的报告记录了这种转变的脉络。
会议决定将参加暴动的部队组建为工农革命军,分为三路: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为主力。*《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7-159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路部队除了安源,已经与原来“湘中七县”中其他六县都没有关系。如果还是按湖南省委原定的“湘中七县”暴动计划组建前委,肯定不合时宜。若此时组建以新确定的三路武装负责人为成员的前委,却又不明了修铜两支部队的具体情况,也没有与他们建立起直接联系。于是会后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铜鼓的部队,派人通知他们参加秋收起义。在安排了安源的起义事宜之后,毛泽东马上同潘心源赶往修水、铜鼓,去会见这两支部队的负责人。
余洒度在起义后一个月写给上级的报告可以佐证以上的分析:“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及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2页。可见,9月8日第三团领导人苏先俊收到了毛泽东从萍乡安源派人送来的关于暴动决议信件,得知了安源会议情况,苏先俊随即转告余洒度自己将响应萍乡的暴动。
有研究者认为,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向修水、铜鼓的各路部队发出通告和军事命令,通告安源会议决定,命令他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限时进攻长沙”。*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萍乡矿业集团:《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58页。这种“发出通告和军事命令”的说法不知有何依据。余洒度报告中“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和末句“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透露的信息很明确,说明接信时苏先俊和余洒度尚未正式成为前委的成员,他们所领导的部队也未正式隶属前委。假如9月8日接信时他们率领的这两支部队已经隶属前委,那么前委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达军事命令,而他们作为下级也只有坚决服从和执行命令的义务,苏先俊又怎么可能说出“决即响应萍乡”和“未便拒绝”这种不符合下级身份和军事常识的话来?既然领导——隶属关系尚未建立,毛泽东自然不可能向他们发出“军事命令”。这段话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毛泽东当时确有必要亲自赶到铜鼓、修水,现场组织前委,建立起领导机构,负起协调指挥这两支部队和与安源部队共同进攻长沙的重任。
毛泽东来到安源,本意是落实湖南省委制定的“湘中七县”暴动计划。但是在张家湾会议上他意外地获悉铜鼓、修水还有两支正规军可以加入起义,于是根据新的情况,果断决定把“湘中七县”暴动计划改变为湘赣边界的暴动。因为军情紧急,他已无法向湖南省委请示,只能亲自赶往修、铜去协调、落实新的方案。新方案对原计划是重大的改变,相应的,前委成员的人选自然也要发生变化。此时,前委书记毛泽东尚未与修铜的部队建立直接联系,更未建立直属的上下级关系,所以有关安源张家湾会议上就成立了前委的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四、毛泽东赶到铜鼓组织前委开展工作,指挥起义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由潘心源陪同,立即赶往铜鼓。9月9日,在赶往修铜的途中,潘心源不幸被反动民团抓住,毛泽东则机智脱险,死里逃生,于10日到达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第214-215页。
据苏先俊于起义后写给上级的一份报告记叙,毛泽东10日到达铜鼓(与苏先俊会合)后,“即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泽东同志为书记,先俊等为委员”。*《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1页。这是明确讲到毛泽东何时何地组织前敌委员会的历史文件。相比之下,前面那些提出安源会议上成立了前委的说法,无一能提供明确的历史文献作为依据。有一篇文章说安源“会议宣布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宣布成立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师长”,*庞振宇:《毛泽东与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创建》,《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3页。还在这句话后面标注了原文出处。可是笔者按所注查阅,却发现原文内容与安源会议毫无关系,那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9月8日联合署名发布的一份命令,命令中没有一句话提及前委,仅仅提到任命毛泽东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命令中还任命了另外六个团的团长,且这六个团长中偏偏没有毛泽东到铜鼓组建的第一师下辖的三个团长。*《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64-65页。可见湖南省委此时对湘赣边三支起义部队的情况并不清楚。
我们再看先后成立两个前委一说能否成立。假定在安源会议上已经成立前敌委员会,那么这个“旧前委”是领导湘中七县起义的前委还是领导湘赣边起义的前委?从前面所引用的资料看,这一问题并不明确。设想毛泽东在安源曾经组建过一个前委——不管这个前委是领导湘中七县起义还是领导湘赣边起义,他到铜鼓后如果再成立前委,岂不是要解散前几天刚组建的前委?否则就必然存在两个并列的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假如撤销前几天成立的前委,是否要通知上级和那些已经确定的前委成员(如果当时已经成立前委,就应当确定前委人员)?或许有人会说,成立新前委的同时就自然撤销了原来的旧前委。可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证过在安源不可能成立一个领导湘中七县起义的前委。假如安源成立过一个领导湘赣边起义的“旧前委”,那么“旧前委”与“新前委”所辖主力部队三个团都是同样的三支部队,在军情紧急的时刻难道有必要架床叠屋地再次宣布组建一个前委吗?故此笔者认为,在安源会议上虽然谈及了前委成员的条件等,但因起义的区域从湘中七县改为湘赣边三县,而三县部队的大部分领导成员并未确定,前委书记毛泽东与修铜两支部队也未建立领导——隶属关系,故在安源并未正式成立前委。前委是毛泽东于9月10日到了铜鼓之后组织起来的。
毛泽东和苏先俊会合组织前委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确定参加起义部队的序列和编制。安源会议期间,根据潘心源的介绍,毛泽东等人只知道驻扎在修水的警卫团和驻扎在铜鼓的浏阳农军两支部队,加上安源的工人武装,于是将三处部队分为三路,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修水的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安源的工人武装编为第二团,*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编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书认为:“安源组建工农革命军的时候,并不知道驻修水、铜鼓的部队已经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及其下辖第一、第三两团的情况,因此,按照安源会议决定,将安源的部队称为第一师第三团。毛泽东到铜鼓后,得知驻修水、铜鼓部队改编的情况,才决定将安源工人部队由第三团改称第二团。”但1996年出版的《安源区志》认为驻在安源的工人武装和其他县部分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张侠、李海量合著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也认为安源工人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铜鼓的浏阳农军为第三团。毛泽东到铜鼓后才了解修水此时还有一个第四团。关于第四团的情况可以证明毛泽东在安源时对修水的情况不是很清楚。警卫团在修水时曾经收编黔军邱国轩所部,将它编为第二团。之前张家湾会议上毛泽东等同志曾决定将安源工人为主体的暴动部队编为第二团。此刻毛泽东发现有两个团的番号都是“第二团”,于是将邱国轩团改番号为第四团。*龙正才:《邱国轩团的隶属关系及其被秋收起义部队改编过程》,《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314-315页。秋收起义爆发,“第一团从修水出发……到长寿街,遭到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的袭击,受到一些挫折”。*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写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尽管第四团临阵背叛,但它一度被编为秋收起义部队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一些严肃的党史军史著作对此亦有记载。*星火燎原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序列》(1927-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陈荣华、阎中恒编:《中国革命史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4-55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序列表(1)》,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潘心源当年在安源会议上因为不了解有关邱国轩团的情况,故没有提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不必回避这个团曾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到达铜鼓立即组织了前委,那么前委成员除了苏先俊,还有哪些人呢?笔者认为,有资格担任前委成员的人员还是各团主要军事负责人(依照原来湖南省委确定的原则)。具体来说,应该有安源二团团长王兴亚,这是毛泽东离开安源之前就安排的,还有修水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及师长余洒度等人,以及三团团长苏先俊。第四团团长邱国轩因为还不是中共党员,所以不可能成为前委成员。当然,这些只是我们按常理和实际情况作出的推断,无法找到确切的历史文献作为依据(除苏先俊外)。故此,一本权威的工具书中仅列出了前委书记毛泽东,其他前委成员均未提及。*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9页。至于卢德铭,蒋杰、段家作《卢德铭》提及,此刻他刚接受向警予代表上级党组织赋予他总指挥的重任,还在由武汉赶回修水的途中,9月9日才赶到渣津。*蒋杰、段家作:《卢德铭》,《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234页。此文讲到卢德铭等按照夏曦的指示准备从武汉经上海去广东,在汉见到向警予汇报了情况。向警予请示党中央后,要求卢德铭等三人仍回部队工作,带领部队,参加秋收起义,并要他们组织一个指挥部,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但是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谷茨撰写的《向警予》所述,向警予代表湖北省委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秋收暴动的计划,坚决否定了原先夏曦要他们丢掉部队只身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意见。由此看来,向警予究竟是代表湖北省委还是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卢德铭任总指挥,尚待进一步研究。他成为前委成员,应当是几天后与毛泽东会合之后的事。
毛泽东到铜鼓后,秋收起义全面展开。修水的一团和四团向平江进发,第三团向浏阳前进,第二团攻下老关后向醴陵进攻。“讵意第一团忽为假意输诚之第四团击败,第三团亦受挫于东门市。”*《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1页。第二团“在醴陵打了一仗,获得胜利并占领醴陵县城;十四日,由于敌人反扑,第二团撤出醴陵回老关,北向攻浏阳;16日占领浏阳城;17日受到敌人四面包围,失败”。*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第178页。至此,原定三路集中攻击长沙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
14日,在浏阳东门市受挫后的第三团撤到浏阳上坪。“当晚,在上坪的陈锡虞家中召开了第三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毛泽东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提出了暂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打算,与第二团会合,并研究以后部队的行动计划。”*李小山主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大事纪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会后,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余洒度,要求他率部队向文家市撤退。次日,第三团离开上坪。余洒度讲到:“第一团整理后,即绕道进攻浏阳,方至其界,闻三团不利,决心援助该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至中途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度因情况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余洒度报告》(1927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3页。这段话证明毛泽东此时已经正式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对部队实施指挥,余洒度也开始接受前委的领导了。
毛泽东和苏先俊带着第三团于17日“到达蒋埠孙家塅一带,第一团与第三团会合。前委委员毛泽东、苏先俊、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举行了前委会议,研究部队的现状和军事行动问题”。会后,一、三团分别向文家市前进,19日早饭后先后到达文家市,二团余部也闻讯赶到这里集合。*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8-19页。也有人认为一、三团到文家市才会师的,见张启龙:《秋收起义中的第三团》,《星火燎原》丛刊第3辑(1981年2月),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内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否定了余洒度等人坚持要部队继续打长沙的计划,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张启龙:《秋收起义中的第三团》,《星火燎原》丛刊第3辑(1981年2月),第7页。由此,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汇集一起,领导秋收起义余部,开始了新的征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并非在安源成立,也不存在于安源先成立了一个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委、之后于铜鼓再次成立一个湘赣边秋收起义前委的事实。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主持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时得知修铜有两支可以参加起义的部队,于是决定将湖南省委原定的湘中七县暴动改变为湘赣边秋收起义。会后他离开安源前往修铜,目的是就地建立指挥机关,协调三支部队的行动。毛泽东途中一度遇险,机智脱险后赶到铜鼓,与苏先俊会合,随即在铜鼓正式组织成立了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秋收起义。
责任编辑:魏烈刚
Analysis on the Founding of the Front Committee during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and Related Issues
Chen Hongmo
Abstract: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27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Many books and articles on this topic have been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but few are specifically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Front Committee during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 .A mainstream view insists that the Front Committee was founded at the Zhangjiawan Conference in Anyuan in early September.Some scholars maintain that there were respectively two Front Committees during 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Through a careful comparison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mmittee is appointed by the CPC Hu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Secretary of Mao Zedong in September 10, arrived in Tonggu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conclusion.
Key words:Autumn Harvest Uprising; Mao Zedong; the Front Committee; the Zhangjiawan Conference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6.02.008
作者简介:陈洪模,男,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江西南昌33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