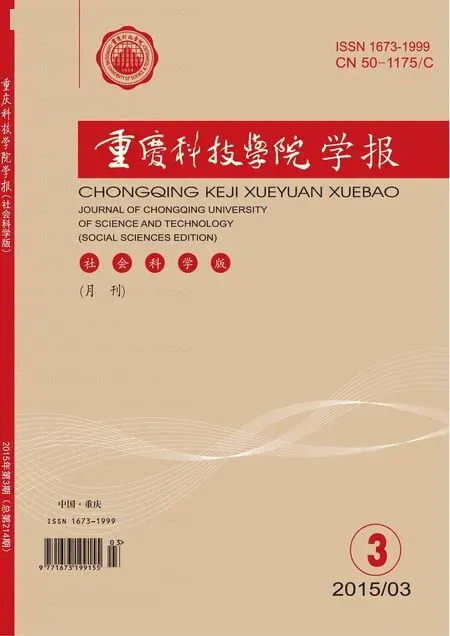《喜福会》“麻将式”叙述的建构
王 丹
一、“麻将式”叙事的建构
(一)非叙述者之叙述化
麻将本身没有生命力,是不能进行叙述的。谭恩美在小说《喜福会》中,独具匠心地把麻将的打法融入作品的结构中,营造出类似巴赫金“复调小说”独特的叙述模式,从而使小说散发着独特的韵律与美感。“《喜福会》全书是以8位女性的轮唱形式展开的,其絮叨的节奏和讲故事的语调是纯女性化的。”[1]纵观全书,女性化语言区别于男性过于直白和理性的表达方式,表现了女性特有的不重理性、反逻辑性的叙事。这种叙事方式往往与集体无意识联系起来,强调了女性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神秘色彩及其在家庭文化中的母性魅力。清一色的女性叙述者共同建构起《喜福会》独特的“麻将式”叙述结构。
在《喜福会》一书中,谭恩美对麻将的描写有两个目的,首先把它作为一种文化介绍给西方;第二,利用麻将的打法建构起整个故事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向西方推荐麻将文化主要体现为母亲们将中国麻将当作一种智慧,教授给吃着美国快餐长大的女儿们。麻将是中国人的一种娱乐方式,虽然只是娱乐但是在打法上颇为讲究,比如如何洗牌、如何计算、参与人数等,都是有一套规则的。文中在提到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的不同时,吴精美的妈妈解释说:“犹太麻将只需盯住自己的牌,只要用眼睛就可以打了。中国麻将要复杂得多,你必须好好动脑子,这里十分讲究技巧,你得记住别人出过的牌。如果不会这一点,那你就是在打犹太麻将了。”[2]在她看来中国麻将并不仅仅是游戏,还体现了中国人复杂的思维逻辑。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体会到作者对于祖国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中某些方面的不屑。
(二)“麻将式”的叙述结构
通过目录就可以体现出来,全书共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共讲述了4个故事,整部书就是由这16个故事构成的,通过叙述者吴精美的讲述将母女两代人的经历一一展示。这种奇特的叙述方式类似独唱与和声部的配合,使得文章结构更具音乐性。小说一开始以“千里鹅毛”为序曲,在序曲的结尾讲到了“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她能以流畅的美式英语,把这个故事告诉她的女儿”[2],进而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总基调——文化差异带来的母女矛盾。在小说的每一章都安排一个主要人物作为核心叙述者,核心叙述者与围绕在她旁边的作为“和声”的叙述者共同完成这个与主题相关的故事。这本书从开始到结尾构成一个更大的故事,这种大圆满的叙述结构跟中国麻将的打法相似。中国麻将的打法是4个人一桌,往往打上16圈才停止。在《喜福会》的结构中,全文被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有4个核心叙述者分别讲述4个不同的故事,由表一可以看出。
从上面的列举中我们能够很直观地看出,作者在结构上的编排就像麻将桌上垒起的4面墙,看似独立,实则相互联系,而吴精美贯穿整个故事的头尾,类似于麻将中的庄家,其余的叙述者在轮流坐庄的过程中叙述自己的故事,而且母辈叙述者与女儿的叙述相互交织,体现出母女之间的纠葛,由中西文化思想差异而产生的碰撞都在“麻将式”的叙述结构中娓娓道来。

表1 《喜福会》作品内容
二、《喜福会》的文化内涵
在文中“喜福会”是个麻将俱乐部,从母亲们在桂林第一次发起“喜福会”时,麻将就是她们的主要娱乐方式,那时国难当头,麻将就成为她们在绝望中的一丝安慰,等到她们穿洋越海来到异国他乡,麻将更是她们怀念故乡、寻求认同感的一种方式。这种在牌桌上建立起来的感情具有了穿越地理、跨越文化的意义,是漂泊于异乡的中国人血浓于水的华夏寻根情节。在作品中,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她们都生活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通过她们的叙述我们能感受到这种文化冲突,但是有结必然就有解,这种多元文化的症结中包含了解决冲突的调和,谭恩美旨在通过母女之间矛盾的调和来“揭示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与包容的必要性以及融合的可能性”[3]。
《喜福会》里的母亲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维护者。在母辈的叙述中,让人感受最明显的是她们在母国与他国的惨痛经历。这4人在中国都遭受过痛苦、历尽艰辛,吴素云经历战争的伤害及母女离散;许安梅童年看见母亲的自杀;龚琳达讲述的是早年与洪天余之间无性而痛苦的婚姻;顾映映讲述了早年与那个卑劣男人的痛苦生活。虽然历尽伤害,但她们不甘于逆来顺受,而是坚强勇敢地冲破逆境,怀着新的希望离开中国,踏上寻梦之路。从表面上看,她们是远离了故国,但在深层意义上,她们离开的是以男性为主宰的传统文化以求自立。在美国成家之后,她们并未按照中国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去教育子女,相反处处鼓励孩子们自强自立。在母亲的支持下薇弗莱成为了颇有名气的象棋手;许安梅鼓励女儿在离婚问题上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斗争。文中这4位母亲离开中国,选择了美国这个第二故乡,她们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由于长年居住在美国,她们的生活模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她们虽然有自己的中国麻将俱乐部,但她们也去基督教堂,参加教堂组织的《圣经》读经班以提高英语,她们虽然说中文,但也会点支离破碎的英语。除了这些显性的变化之外,她们的思维方式也无形中改变,例如,琳达为了让薇弗莱集中精力参加象棋比赛,免去了女儿洗碗等家务杂事,让哥哥代劳。哥哥们不服,抱怨道:“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逍遥,而让我们干这种家务活?”妈妈没商量的说:“这是最新的美国规矩。”[2]言下之意,在美国男女平等,就看谁有竞争力了。当然女儿们的文化身份也是二元的、杂合的。在家人,尤其是在母亲面前,她们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当她们在美国社会打拼时,又会被当作异己排除在外。当特德跟露丝交往时,遭到他母亲的反对,因为在特德父母眼中,露丝是“亚裔”美国人,他的母亲更是认为一个亚裔儿媳会影响儿子光明的前途,这种看似“混合”的婚姻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露丝而言,身体中不可更改的中国基因,使她的性格带有中国女人的温顺谦恭,在同美国丈夫的美国式交往中,内敛、敏感的她与开放、粗犷的他经常会产生分歧,而她总是表现了中国式的隐忍,事事顺从丈夫,听从他的安排,于无形中失去了自我。与此相同,丽娜也深陷在与哈罗德的AA制生活之中无从适应。相反露丝的母亲支持女儿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在母亲的鼓励下,她重新建立了自尊,找到了自我。
在《喜福会》的结尾中吴精美的大陆之行,既是她与母亲的和解,也代表了第二代华裔移民与母辈的和解。作品中这样描写道:当吴精美坐着火车抵达内地,真正踏上祖国的土地时,“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的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阵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2]她终于体会到母亲为什么一直教导他们不能忘本,并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身体力行不忘祖国的传统文化,她理解了母亲深受双重文化压抑的内心,母女之间的心结就此打开,此刻血浓于水的母女情彰显的是两代人的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包容。这种结与解的张力就体现在麻将式叙述之中,正是你一言我一语才促成了矛盾的解决,由此可以看出麻将式叙述的过人之处。
三、从《喜福会》看华裔作品的发展趋势
(一)向传统文化皈依
华裔作品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向母国传统文化回归的倾向,这种倾向符合美国主流文学中文化身份寻求的后现代观点,也符合华裔作家在双重文化氛围中的另类的生存方式。在作品中将寻找自我身份与寻找文化身份结合起来,是他们面临双重文化挤压下的选择,而写作作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显示了他们在面对选择时是如何恰当地将两种文化合理配置。从《喜福会》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描写可以看出,谭恩美将自身对于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思考与写作联系起来,一方面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优秀文化的魅力。而对于华裔作家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关于自身文化身份的思考以及对中华文化与自身关系的感悟,是他们在写作中突出强调的。
(二)女性话语权力增强
由于华裔作家群体“尴尬”的文化与生存处境,斡旋于主流社会的男子在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或多或少模仿主流话语模式,相对于女性来说他们更容易运用美国式的评判标准来观照事物,因此,在传承传统文化过程中的失真性会更大。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将叙事权交给女性,让围绕在美国社会边缘地位,带有更多中国传统印记的华裔女性讲述故事,由于她们的边缘性地位,使得她们较少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所以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时的真实性会更大。谭恩美希望借此树立她们在小说中的话语权,进而改变她们在主流社会中作为弱势话语群体的地位,通过她们的讲述传承失真性较小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且给予她们充分表达的自由。
(三)正视双重文化身份
《喜福会》中通过母女矛盾的结与解,预示了被符号化的子辈所承受的中西两种文化由结到解,由冲突到融合,这是谭恩美作为承受者的亲身体会,也是她在作品中所要传递的期盼,这种文化期盼“表达了华裔们既不愿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身份,奴颜婢膝迎合主流文化以挤进美国主流社会,也不愿以固守华夏中国的文化来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意愿。”[4]《喜福会》不仅是谭恩美的创作实绩,更是作家对自己文学思想的实践,母女矛盾的表层之下,掩盖的是中西文化求同存异的深刻内涵,双重身份的困惑激发了作家勇于打破桎梏的决心,所以谭恩美的《喜福会》是在母女矛盾中表现中西文化的冲突,在两代人矛盾的化解之中,号召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华裔作家们不应因为自己的双重身份备感受挫,而应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接受它,寻求文化融合,解决文化冲突问题。
四、结语
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喜福会》的成功一方面来自作品本身“和”的思想,另一方面来自作者在写作技巧上的探索。就像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赛义德在《东方主义》序言中所说:“长久以来,我感到我们这些学者与知识分子肩负着一种特殊的知识与道德责任。我认为将简化的表述和抽象、有势力的思想复杂化,对我们而言责无旁贷。”[5]在华裔作家们的努力下,我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这条道路上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因此在和谐世界的呼吁下,在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对《喜福会》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和”之道的研究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只有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互相理解、求同存异,才能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1]张琼.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1.
[2]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12.
[3]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出版社,2009:7.
[4]钟营.透过《喜福会》的人物来看谭恩美的双重身份[J].大众文艺,2009(19).
[5]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M].王根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