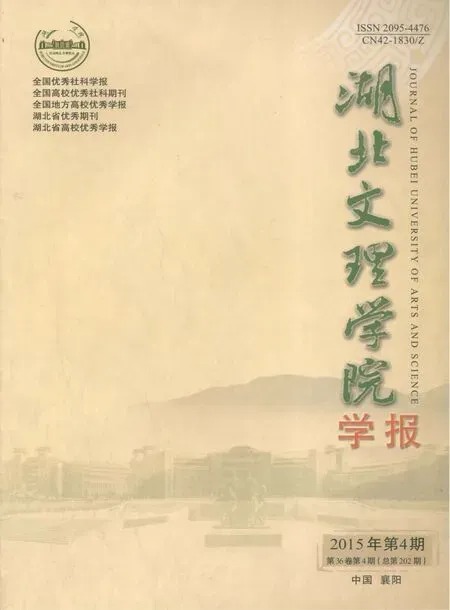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综述
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综述

谢正富1,许林洁2
(1.湖北文理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2.襄阳市田家炳中学,湖北襄阳441000)
摘要:从行动主体行动逻辑的角度来展开的基层治理研究主要有政府的“不出事”逻辑和民众的“闹大”逻辑。通过对中国基层治理相关研究和行动逻辑研究的综述来看,这两种逻辑在一定范围内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由于主体的单一性,容易忽略主体多元以及相互间的互动。因此,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今后的趋势应该将基层治理中两大行动主体都纳入视野,全面考虑双方的互动逻辑,提出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解释预测基层治理中的现象和问题。
关键词:基层治理;行动逻辑;乡村治理;社区治理
基层治理的核心是维持社会稳定,而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来化解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是当前以及今后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当前,中国基层治理陷入两大怪圈,一个是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翻烧饼”的怪圈,另一个是基层社会秩序“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我国有些地方基层治理体制改革之所以会出现“翻烧饼”,是因为行动逻辑在实际支配着政府和民众的行动,而政府和民众依然沿着其固有的行动逻辑运行,在行动逻辑没有转型情况下,治理体制改革出现反复就不足为怪了。一些地区社会秩序出现“越维越不稳”的现象,其根源是政府的行动逻辑是“不出事”逻辑,而民众的行动逻辑是“出大事”逻辑,这两大主体行动逻辑在行动目标上是相悖的,从而导致维稳失效。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就是探求突破基层治理困境、打破治理怪圈的研究,是寻求社会和谐稳定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就是针对这两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政府与民众互动的视角来为当前基层社会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寻找答案,刚好满足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实践创新的需要。因此,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也就是从行动逻辑的角度来为当前基层社会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寻找答案,为政府基层治理公共政策的制定寻找理论支撑,为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理论指导。
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不但讨论中国当前基层治理中的问题,而且也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的发展问题。当前基层社会的行动逻辑实质上就是政府的不出事”逻辑和民众的“出大事”逻辑,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的核心就是研究这两种逻辑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在基层社会,政府代表着国家,民众代表着社会,因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反映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所以,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问题虽然是“不出事”逻辑与“出大事”逻辑之间的关系,其实背后透视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探讨。另外,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还拓展了基层治理研究的领域,通过对行动主体行为方式规律的探究来推动基层治理研究的发展。
因此,对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两大行动主体行动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深化对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与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将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社会管理的目标。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通过对行动主体行动规律的研究来拓展社会管理研究的领域,深化社会管理研究的内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还有利于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新的发展。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政府与民众互动关系视域内的研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中国基层社会的实践创新,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的相关研究有哪些成果呢?这些研究留下了哪些研究空白需要进一步完善呢?本文将从中国基层治理研究和行动逻辑研究两方面来进行评述。
一、中国基层治理研究
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是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一部分。中国基层治理研究按照研究领域划分,可以分为乡村治理、社区治理两大领域。首先,我们对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做一个简单回顾。
(一)乡村治理研究
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可谓蔚为壮观。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文化本位出发来尝试通过乡村社区建设复兴中华文明,其代表作品有《中国文化要义》《乡村社区建设理论》和《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其代表作品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学院派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试图从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其代表作有《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乡土中国》。以林毅夫、张乐天为代表的学者对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公社制度的效率以及家族共同体瓦解的原因,代表作品有《集体化和1959-1961年中国的农业危机》和《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至今,经过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乡村治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其中在乡村治理研究方面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主要有:张厚安、徐勇、曹锦清、张静、吴毅、贺雪峰、肖唐镖、仝志辉、项继权、吴理财等等。乡村治理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有:张厚安和徐勇主笔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1995),该书探讨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农村治理的一系列对策和措施。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著《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一书将乡村治理研究从书斋引向田野,进行了实证研究的探索尝试。徐勇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系统地讨论了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制度特征和制度框架,为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支持,是一部对乡村治理研究影响深远的作品。另外,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也对乡村治理研究产生较大影响。
曹锦清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黄河边的中国》两部作品从传统的视角出发通过实证调查来研究当代乡村治理。温铁军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从经济基础及农民生活逻辑和乡村内生秩序方面来讨论乡村治理研究。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对农村基层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讨论。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以20世纪的百年变迁为历史背景,研究中国的村庄政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还有:吴毅、吴淼的《村民自治在乡土社会的遭遇:以白村为个案》,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贺雪峰的《乡村治理与秩序》《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中国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仝志辉的《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肖唐镖的《宗族政治:村治权力网络的分析》,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等等。
继前辈学者之后,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乡村治理研究方面也建树颇丰。如:田先红的《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2009》,万小燕等著《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湖北秭归杨林桥社区建设与治理的实践探索》,袁金辉的《乡村治理与农业现代化》,何俊、班杰明、许建初主编的《乡村治理、村民自治和自然资源管理:云南六个少数民族社区的实践》,于水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江苏为例》,彭勃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徐勇、徐增阳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等等作品大大丰富了乡村治理研究。
在乡镇治理研究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赵树凯的《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1],该书是对当代中国基层政府及其治理的实证研究,核心论题是中国基层政府的体制改革。陆道平的《乡镇治理模式研究:以昆山市淀山湖镇为例》[2]一书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对苏南乡镇治理的历史、现实困境及特点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做了一些前瞻性分析。袁方成的《使服务运转起来:基层治理转型中的乡镇事业站所改革研究》[3]一书以乡镇站所的改革为研究对象,从先期探索、治理困境、体系再造和制度创新等等方面来对乡镇治理中体制进行全景透视。张铭、王迅著《基层治理模式转型》[4]一书以苏南农村为分析对象,对当前基层治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未来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探讨。这方面的著述还有叶南客著的《都市社会的微观再造—中外城市社区比较新论》,袁秉达、孟临主编的《社区论》,李会欣、刘庆龙编著的《中国城市社区》,王振海等合著的《社区政治论》,窦泽秀著的《社区行政》,王邦佐等编著的《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王青山、刘继同编著的《中国社区建设模式研究》,中国城市社区党建研究课题组编的《中国城市社区党建》,雷洁琼主编的《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市城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研究》,李友梅、徐中振等著的《社会家园与社会共同体—“康乐工程”与上海社区实践模式个案研究》,林尚立主编的《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蓝宇蕴著的《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张纯洁著的《活力社区—温州城市社区研究》,林尚立等著的《社区党建与群众工作—上海杨浦区殷行街道研究报告》等等。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多数是从制度、体制和机制的角度来分析思考中国的社区治理的问题,对社区治理实践层面行动逻辑的研究尚显得不足,这也为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留下了研究的空白。
以上学者在乡村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研究,但是对乡村治理的内在实践逻辑的研究却不足。正如贺雪峰所言“一旦意识到一般政策和制度研究的不足,就需要深入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逻辑。”[5]贺雪峰较早认识到乡村社会内在运作逻辑研究的重大价值,也较早进入该领域。贺雪峰在《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5]一文中从农民基本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角度,来分析村庄社会关联,并由此讨论农民公私观念区域差异和行动逻辑区域差异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秩序的差异。制度层面的研究更多是研究者理想的建构,与乡村社会的现实逻辑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学界部分学者转向研究乡村治理中实践逻辑,转向对乡村社会本身的深度理解与学理追求。
(二)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比乡村治理研究起步晚,相关的著述也比乡村治理少。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也渐趋繁荣。代表性的作品有:于燕燕的《社区自治与政府职能转变》[6],该书分析了中国社区建设中的政党、政府、社会三者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归纳了中国社区体制的基本现状,论述了社区自治与政府职能转型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政府职能转型是社区自治的前提和基础的结论,展望了未来社区居民与政府合作治理的社区模式。武汉地区以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为平台,产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成果。如:徐勇、陈伟东《中国城市社区自治》,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尹维真《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以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为例》,孟伟《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以1998-2005年间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为例》,李雪萍《中国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王敬尧《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胡宗山编写《社区自治实务》等。
(三)海外中国基层治理研究
海外学者对中国基层治理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丰硕,很多作品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读经典。海外学者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事实,得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给中国学者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发展。这其中有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库尔普的《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爱德华·弗里德曼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中国的宗族和社会》《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阿尼达·陈、安格尔、马德生合著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民社区的现代史》,马德生的《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美国学者伯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加拿大伊莎贝尔·柯鲁克等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伯恩的《中国农村的政治参与》,斯坦福大学戴慕珍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萧凤霞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等等作品。这些作品很多都是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由于或多或少缺少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等变量的引入,对中国基层治理内在的逻辑规律的把握尚显不足。
二、行动逻辑研究现状
基层治理行动逻辑主要是基层治理中的两大行动主体——政府与民众的行动逻辑。学界对基层政府行动逻辑的相关研究不多,对农民行动逻辑的研究较为丰富。下面本文将从政府的行动逻辑和民众的行动逻辑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现状回顾。
(一)政府行动逻辑研究现状
理性选择理论在政府行动逻辑研究中的运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安东尼·唐斯在《官僚制内幕》[7]一书中指出:官僚机构的行动逻辑是由官僚的动机所决定的,要把握官僚机构的行动和趋势,准确把握官僚的动机是基础和前提。官僚并非是道德上的圣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是理性经济人。官僚与普通人在行为动机上是一样的,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僚作为个体在效率、诚实、努力工作、精确性、公共精神等方面比非官僚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他们通常也不一定比非官僚更令人钦佩。”唐斯的研究前提是把政府官员假设为“理性经济人”,当前学界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前提来研究政府及政府官员的相对普遍,也确实能解释很多社会现象。王振亚、王海峰在《利益视角下的乡镇政府行为逻辑分析——以甘肃A镇小城镇建设为例》[8]一文中归纳指出:基层政府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趋利性行为,并且行为的主体是政府集体层面、小团体层面、官员个人层面,这三个层面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可视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当然,政府行为关键是由主要负责的领导的行为所左右,领导个人的趋利性的影响下政府行为方式也主要表现为趋利性。
经验材料的概括归纳研究。李伟南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逻辑研究》[9]一文从县级政府行为的“实然逻辑”和“应然逻辑”两个层面来入手,分析了县级行为逻辑的影响因素、特征、成因以及行为失范原因并提出了对策。吴素雄在其博士论文《政党下乡的行为逻辑:D村的表达》[10]一文以一个村庄研究单元,以近现代中国政党发展为纵轴,以社会权力为焦点来分析政党下乡的行为逻辑。李永刚在《多重比大小:地方官员的隐蔽治理逻辑》[11]一文中为考察地方官员的治理逻辑提出四个观察变量,分别是权威指数、偏好弹性、规则意识和关系网络。该文根据经验事实,还归纳出地方官员的隐蔽治理逻辑,就是:权威—规则比大小、利益—风险比大小、关系—能力比大小。李祖佩在《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治理中诸种力量的表达及后果》[12]一文中指出基层政府是不择手段的“牟利者”、战战兢兢的“治理者”、悬置的“服务者”。叶麒麟,郑庆基在《论乡镇政府在征地中的角色定位——从乡镇政府行政行为的逻辑谈起》[13]一文中指出,乡镇政府行政行为的逻辑是国家意志、乡村社会利益和官僚利益三者的共同体现。韩志明[14]对街头官僚一般的行动逻辑进行了归纳,四个典型的方面:激励不足,职务晋升机会的缺乏导致激励不足;规则依赖,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促使他们在照章办事的逻辑中寻求免责;选择执行,即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执行;一线弃权,即刻意规避某些麻烦的、危险的、需要更多付出但难以见成效的工作,并日益远离一线或现场。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一方面是政府行为和政府官员行为逻辑的研究多采用的是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理论工具进行研究。不论是作为整体的政府集团,还是作为个体的官员都在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只不过政府集体追求的是公共权力的扩张,个体官员则是追求的职务的升迁和经济收益的提高。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在基层治理研究中对部分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在运用中还是暴露出其局限和不足,这需要我们在结合具体经验实际时做适当的调整和修正,由此也可以推动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对政府行动逻辑的研究还仅限于案例描述、初步的分析归纳和具体的对策研究,缺少理论工具的使用、深入的剖析。
(二)民众行动逻辑研究现状
研究民众行动逻辑的文献以农民行动逻辑研究的数量占据大多数。农民行动逻辑研究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作者提出“生存伦理”的概念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动逻辑。作者发现农民并不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首先确保“安全第一”,由此也产生了他们的反抗方式——欺骗、逃避、服从错误的命令、假装遗忘、离心离德、小偷小摸、造谣中伤、蓄意破坏等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斯科特的“生存伦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生存理性”,就是以追求基本生理需求满足为最高目标的理性追求。
费孝通先生眼中农民的行动逻辑就是指农民行动所遵循的原则和规律。农民的行动逻辑的背后是公私有别的行动逻辑,是遵循差序格局的行动逻辑。农民以家为界,但凡是家里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如果是家以外的事情,则是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15]。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16]一书中,通过具体分析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特性,进而揭示出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也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样的社会的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维系人们关系、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要素是道德,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称的礼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只要是符合道德要求,合乎于“礼”的,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即使此行为会违背法律规范。可见,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特殊行动逻辑:是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是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的[15]。中国人在家里倡导的是多尽义务少享权利,在家外则刚刚相反。所以,林语堂说:“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指导着自己的各项活动。互相帮助发展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一种道德义务和家庭责任荣誉感促使他们要互相提携。”[17]林语堂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17],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孕育了中国的个人主义[17]。翟学伟在《中国人行动的逻辑》[18]一书中从本土化视角出发来思考中国人的脸面观、土政策、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家族主义、社会心理承受力、社会行为取向、个人地位等方面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景之间的关系,力图建构起分析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理论框架。该书以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为研究对象,在本土化的问题和现象的基础上,来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对应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是本土化理论框架建构的尝试。该书还认为,影响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四因素是:家长权威、道德规范、利益分配、血缘关系。总体上看,翟学伟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探讨了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并提出了中国人社会行为的若干命题,这些命题有待通过后续的经验研究来证明。
贺雪峰是在农民行动逻辑研究方面颇有影响力的学者,他关于“农民行动逻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作品中:《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行动单位与农民行动逻辑的特征》。在《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一书中贺雪峰提出“农民行动单位”的概念,农民行动单位也是农民认同单位,它具体表现为农民的公私观念,而公私观念影响着农民行动逻辑,农民行动逻辑也就构成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19]。贺雪峰在《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20]一文中是利用公私观念来解释一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看似不合理的现象中内在的合理性。贺雪峰还从理论上分析论证了中国人行为的深层逻辑是私利或私域的逻辑。传统的私域是以核心家庭为单位,而非个人。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私域也在逐步瓦解,越来越凸显了个人主义的逻辑。因乡村的区域不同、时期不同,农民行动单位的划定也有所不同,不过行动单位对农民行动逻辑的影响还是基本一致的[21]。贺雪峰在《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21]一文中提出农民存在双层认同,其中一层是家庭,另外一层是超出家庭范围的认同单位。农民的双层认同也造就了农民行动逻辑的双层化。农民的认同单位决定行动逻辑,行动逻辑又可以推断农民的行动特征。贺雪峰认为要理解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就要建立双层认同的动力机制模型,而模型的建立有赖于通过社会调查来准确区分农民的认同单位。贺雪峰在《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22]一文中指出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与公众社会的行动逻辑之间有很多差异,差异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两者的公正观不同,实际上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境遇下不同行动者理性算计的约束条件是不同的。
江立华在《农村妇女婚后留守的行动逻辑分析》[23]一文中从制度、文化和理性计算等方面来分析了农村妇女婚后留守的行动逻辑。其中,制度、文化主要是国家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城乡文化、男权文化等,理性的计算多是考虑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吴理财在《农村社区认同与农民行为逻辑——对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思考》[24]一文中指出:农村社区认同以及农村社区场域情境都是影响农民行为逻辑的重要变量。邓大才在《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逻辑——劳动力社会化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一文中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三代打工者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不同,总结归纳出三代打工者不同的行为逻辑。第一代打工者是生存逻辑,第二代打工者是货币逻辑,第三代是前途逻辑。赵晓峰在其博士论文《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25]中指出,农民的公私观念决定着农民的行动逻辑。吴静在《被征地农民“种房子”行动研究—以安徽省芜湖市S村为例》[26]指出:被征地农民的应对行动并不是胡乱的反应,而是有其内在的行动逻辑,这些逻辑表现为“一切以生存为中心”道义原则,以及“非对抗性抵制”的行动方式,还有充满乡土气息的“自助式”反抗。张婷婷在《村庄社区认同与农民的行动逻辑探讨》[27]一文中指出:农民行动逻辑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村民的社区认同和村庄社区的公共性。该文的行动逻辑简单化地等同于农民的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了,它们两者之间有相关性但是还是有区别,行动逻辑是农民行动的内在规律,深度和广度都超过社区公共参与。段大丽在《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逻辑—基于孟村个案的经验研究》一文因孟村个案为研究对象,在案例中的村民采取了暴力性的对抗行动,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政府的关注,并没有政治意图。该文主要讨论的是当代中国农民为了实现利益表达的行动逻辑。这篇文章其实也是在探讨社会的行动逻辑,社会通过“闹”并闹“出大事”来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文章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形成对抗性行动,农民的行动逻辑与政府的行动逻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应星在其博士论文《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西南一个水库移民区的故事》[28]中描述了移民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使用“闹”、“缠”等策略来向地方政府施压,而地方政府则通过“拔钉子”(针对个别移民精英的打压)和“开口子”(突破政策的底线做出的让步)来摆平。应星在文中指出:“农民要使自己的具体问题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中,就必须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难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只有不断地上访及与之相连的‘闹事’才能带来问题的解决,甚至‘闹’与‘缠’的程度与政府解决问题的程度直接相连。”文中农民形成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认识,遵循着“踩线不越线”的行动策略,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应星的研究深刻说明农民的行动逻辑是针对政府行动逻辑的策略主义的体现。
马骏在《底层抗争的集体行动逻辑——民工讨薪现象的社会学解读》中描述了农民工为了讨薪采用“以死相逼”的方式来引起媒体关注和高层政府的注意的现象。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为了成功讨薪必须引起“政府关注”,否则很难成功。马骏最后得出除了用“自残”、“自杀”这样悲情的武器来唤起政府的关注外,就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引起政府关注。因为越是集体力量越敢于冒险触及法律的边界,也越是集体行动越能引起政府的注意。王晓强在《理法之间:个体农民在纠纷中的行为选择及结果》一文中将农民行动的行动策略归结为一个字就是“炒”。这里的“炒”就是炒作之意。农民充分利用基层政府怕“出事”的心理,为了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有意识突出事情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扩大影响来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具体“炒”的方式有这几种:其一,炒作“上访”本身,以“要上访”相威胁。其二,小题大做,夸大事实真相。其三,扩大声势,引起轰动效应。其四,借助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其五,期盼上级下乡调查,打破地方信息壁垒。其六,瞅准时机,专门赶在敏感时期。该文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农民各种“炒”的行动策略。陈定洋、谢太平[29]认为,农民的行动逻辑受中国传统文化制约。朱兴涛、喻娟娟[30]认为,农民行动单位是村庄,所以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到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类型,特别是乡村精英的影响。另外,农民行动逻辑的背后还有观念、利益、理性的影响。
高恩新在其博士论文《过程、行动者与危机管理——当代中国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中强调了社会结构关系对行动者行动逻辑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特定社会结构为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行动结构以及特定区域“地方性环境”。该论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行动逻辑都做了简要的分析,认为中央政府行动逻辑是政治合法性和稳定话语,地方政府行动逻辑是理性行动者,民众的行动逻辑是理性行动和传统资源。包艳在其博士论文《行动与制度实践—东北F市小煤矿场域整顿关闭过程的经验研究》[31]中从正式的规则和规范、风俗习惯和道德、行动者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行动者策略行动等方面入手研究行动者在制度实践中的行动逻辑。该文以东北F市小煤矿整顿治理为分析对象,运用社会实践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归纳总结得出行动与制度是建构与约束的关系。王扩建在其博士论文《转型期地方核心行动者行动逻辑研究》[32]中运用制度—行为的分析模式来分析制度环境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其研究结论是一定的制度环境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的选择,而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也在不断塑造着制度,促使制度不断变迁。陈立周在《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行动逻辑—以长沙市古井社区居委会为例》中从经验材料中发现:因为社区居委会双重身份,所以导致它遵循两种看似矛盾、实际却并行不悖的行动逻辑,也即一方面追求行政合法性,另一方面追求社会合法性。就是说,社区居委会希望得到居民和政府的双重认同和支持。陈水生在《动机、资源与策略: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33]一文中研究发现利益驱动、资源主导和策略组合型构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动逻辑。
三、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趋势
在现有的政府行动逻辑研究中,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行动逻辑的研究大都采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进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挥棒下发展起来的。在“GDP主义”至上的发展理念下,我国的政府及政府官员几乎都成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因此,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当前政府及官员的行动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现有的多数研究模糊了官员个人理性与政府集体理性的一致性问题。在具体实践中,个人的理性会导致政府集体的理性还是非理性?两者在什么时候会达成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什么时候会存在价值目标的冲突?本文的行动逻辑研究是要探索两者价值目标不一致时,个人理性下的政府非理性的行动逻辑。因为官员的理性导致了政府的非理性,那么政府的非理性行动逻辑的改变必须从官员的理性改变开始,影响官员理性的约束条件最终是我们要改变的关键。从而可以得出,行动逻辑悖论的转型应该从影响官员理性的约束条件的改变入手。
费孝通、林语堂、翟学伟、贺雪峰等学者研究了中国人特殊的行动逻辑,并指出中国人行动逻辑的形成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公私观念、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研究都强调了研究中国人的行动逻辑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否则将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贺雪峰还强调,如果直接简单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的一些现象,将会遮蔽真正的事实,还应该考虑地方性知识对农民行动逻辑的影响。[21]在宏观语境下中国人的行动逻辑更多是受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等因素的影响,而在面对基层治理中的问题时,特别是在政府“不出事”逻辑下,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行动逻辑是恰当的,不过我们也应该考虑地方性知识的影响,然后对理性选择理论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修正,以便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了政府的“不出事”逻辑和社会的“出大事”逻辑,但是对其特征内涵及特征分析不够透彻,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也没有认清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应星、马骏等学者认为民众通过“闹”、“炒”、“集体行动”等行动策略来引起政府关注是社会在政府维稳话语下的理性选择,所以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这类行动还是非常有解释力的。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既有基层行动逻辑研究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现有的研究将政府行动逻辑与民众行动逻辑割裂开来分别进行研究,忽视了两者间内在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第二,现有研究是一些理论简单直接的使用,影响了对事实的真实性认识;第三,现有的研究多是具体现象的归纳总结,没有深入探究行动逻辑背后的原因,更缺少如何破解行动逻辑困局的研究。第四,现有的研究缺少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国际比较。第五,现有的研究多停留于就事论事式的对策研究,没有从中观、宏观着眼和从深层次提出政策建议。鉴于当前基层治理行动逻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今后基层治理研究应将把政府行动逻辑与社会行动逻辑结合起来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应提出新的分析框架,来更好地解释目前的现象及问题,同时分析原因并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赵树凯.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陆道平.乡镇治理模式研究:以昆山市淀山湖镇为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袁方成.使服务运转起来:基层治理转型中的乡镇事业站所改革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4]张铭,王迅.基层治理模式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于燕燕.社区自治与政府职能转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7]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M].郭小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王振亚,王海峰.利益视角下的乡镇政府行为逻辑分析——以甘肃A镇小城镇建设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09-116.
[9]李伟南.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逻辑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大学,2009.
[10]吴素雄.政党下乡的行为逻辑:D村的表达[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大学,2009.
[11]李永刚.多重比大小:地方官员的隐蔽治理逻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2):145-150.
[12]李祖佩.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治理中诸种力量的表达及后果[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13]叶麒麟,郑庆基.论乡镇政府在征地中的角色定位——从乡镇政府行政行为的逻辑谈起[J].湖北社会科学,2006(10):30-33.
[14]韩志明.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J].公共管理学报,2008(1):41-48.
[15]贺雪峰.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J].天津社会科学,2006(1):56-60.
[1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8]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9]桂华.村治的逻辑[J].中国图书评论,2010(4):73-75.
[20]贺雪峰.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J].广东社会科学,2006(1):153-158.
[21]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J].开放时代,2007(1):154-157.
[22]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5-7.
[23]江立华,汤继容.农村妇女婚后留守的行动逻辑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2(3):105-110.
[24]吴理财.农村社区认同与农民行为逻辑——对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思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123-128.
[25]赵晓峰.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26]吴静.被征地农民“种房子”行动研究——以安徽省芜湖市S村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7]张婷婷.村庄社区认同与农民的行动逻辑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9(8):53-54.
[28]应星.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西南一个水库移民区的故事[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29]陈定洋,谢太平.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5-18.
[30]朱兴涛,喻娟娟.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逻辑的调查与思考[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15-119.
[31]包艳.行动与制度实践——东北F市小煤矿场域整顿关闭过程的经验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08.
[32]王扩建.转型期地方核心行动者行动逻辑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33]陈水生.动机、资源与策略: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J].南京社会科学,2012(5):64-71.
(责任编辑:陈道斌)

Research Summary of Action Logic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XIE Zhengfu1, XU Linjie2
(1.School of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 Law,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441053, China;
2.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in Xiangyang City, Xiangyang 441000, China)
Abstract:Action logic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s “no accident” and common people’s “getting it to be bigger”. Base on the summary of some related study, it holds that these two logics are of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however, of no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subjects. In future, the study on grassroots goverance of China should take these two logics into account and put forward a new analytic structure to analyze and explain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Grassroots governance; Action logic;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5)04-0044-08
作者简介:谢正富(1977— ),男,湖北枣阳人,湖北文理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城乡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北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项目(2014JDY007)
收稿日期:2014-10-27;
修订日期:2015-01-15